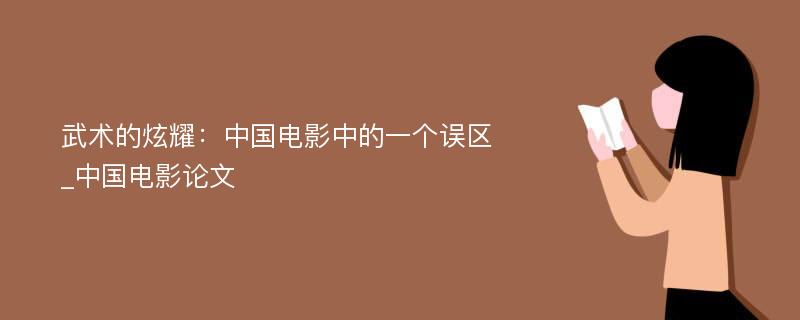
武侠的炫耀:中国电影的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电影论文,误区论文,武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毋庸置疑,凶杀、暴力、武打、刑侦戏是中国当下电影、电视的重要看点之一。作为 现代消费中的一种文化现象,自然有其存在的道理,笔者并不想简单地加以否定,而且 也无意于重复批判凶杀、暴力、武打、刑侦戏对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道德人格品质的 杀伤力。在这里,笔者想要深入探讨的是它对中国电影艺术创造力的严重损害。下面, 笔者将围绕“西部武侠”这一电影类型,对此进行一番分析。
说到“西部电影”,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曾一度风行美国的“西部片”,即好莱坞成功 地定型了独行侠或牛仔勇敢地闯荡西部荒野的“西部类型片”,并将其推向全球。不过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刚开始面向世界的中国电影人,却创作了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的 “西部电影”。最先是陈凯歌导演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它们是新时期初期 中国电影最富于探索性的影片,其最重要的艺术探索性在于对中国西部空间(主要是西 北空间)艺术审美性的发现。例如,《一个和八个》将故事的发生地安排在宁夏的一片 空旷贫瘠的石砾场,并且影片着意给予这一空间以张扬的表现:大量的全景镜头、自主 游移的摄影机运动、超常造型意象的运用,使影片逐渐偏离了革命及英雄故事的讲述, 重心逐渐向那片贫瘠、苍茫、雄浑的西部大地——受难中国的象征倾斜。这种倾向到了 《黄土地》就更为明显了。《黄土地》的基本线索是八路军顾干事到陕北黄土高原寻找 民歌源头。有异于经典的“革命——拯救”叙述,影片并没有让顾干事去发动农民,带 领他们翻身闹革命,也并没去刻意突出单个人的力量或悲剧。影片中各色人物的懦弱、 愚昧、勇气和挣扎,他们身上沉重的负担和一点点的向往,都更是属于整整一个群体或 者民族的。故事的讲述也变得次要了,影片常常用巨大的空间造型,或把人物挤压至边 角,或阻断、切割故事的演进;沉寂、广漠的黄土地时常占据着绝大部分的画面,而人 物只不过是其边角上移动的小黑点。影片用空间挤压叙事,使干旱、贫瘠而温暖的黄土 地成为影片中真正的叙述对象,成为亘古绵延的民族历史文化的“空间化”的象征。在 这之后,《盗马贼》、《人生》、《老井》、《黄河谣》、《红高粱》等影片,也都不 断地挖掘着中国西部空间独特的艺术表现力。虽然,由于主题与篇幅的关系,在此我们 无法分析这些影片所存在的问题,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这些影片,中国新一代电 影人完成了对于“中国西部”审美化的历史空间的发现与创造。这无论对中国文化还是 对世界电影,都堪称是可贵的贡献。
然而,1992年之后,商业化、市场化大潮加速奔涌,大众文化消费急剧飚升。伴随着 改革开放进程的拓展、国际化合作的加强,港台及海外电影到中国取景、拍摄日益增多 。中国西部更成为港台武侠片非常热衷的故事空间。如《新龙门客栈》(1992年)中一望 无际的大漠黄沙,《东邪西毒》(1994年)中孤独荒凉的榆林沙漠、废墟,《刀》(1996 年)中闷热的西南边境,都成为武侠影片及其故事展开的绝佳场所。中国西部大大开拓 了港台武侠片的表意空间,而武侠影片则大大开拓了中国的电影市场。“西部武侠”电 影由此而诞生了。
就在这时,《卧虎藏龙》“出山”了。它继承了港台武侠片的武打场面,强调动作激 烈华美的视觉效果,加入了非常具有诗意的中国山水画构图元素:竹林飞瀑、高山流云 等;还有富于东方哲理和心理分析的戏剧冲突和情节结构等。然而,《卧虎藏龙》中的 西部空间,既不可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部电影中所表现的贫瘠、干涸而又厚重如历 史板块的黄土地,但也不同于港台武侠片中黄沙滚滚、正邪对决的侠义天地;它更像是 一个在中国拍摄的美国“西部片”:典型的美国西部片环境造型,违法者的英雄化的人 物情节定式。这一切都构成了这部备受西方观众推崇的电影的一种中西文化合璧的华美 外表。
《卧虎藏龙》冲击全球文化市场的成功经验,带来了中国电影界的“西部大开发”。 部分参与过《卧虎藏龙》摄制的主创人员迅速拍摄了《天脉传奇》,它对《印第安纳· 琼斯》(又译《夺宝奇兵》)的模仿非常明显,只不过是把大致相同的故事放到了当代。 这个电影里的当代中国西部似乎远离政治、充满神秘,各国人物可以随意进入、任意闯 荡,它仿佛完全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夺宝空间。紧接而来的是张艺谋的大制作《英雄》。 《英雄》充分吸收了《卧虎藏龙》在视觉效果、空间运用上的经验,对西部景观的展示 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几乎就是在《卧虎藏龙》中罗小虎与玉娇龙打斗、热恋的同 一地方,《英雄》的侠客们跃马驰骋。张艺谋及其属下从农民手中收集大量的胡杨树叶 ,制造出漫天黄叶飞舞的胡杨林中打斗场面;电脑特技加工完成的八百里秦川的行军壮 景;还有西南九寨沟水气弥漫、仙境般的视觉图谱。《英雄》几乎成了西部奇观的一次 “大贩卖”,更像是一则“西部旅游广告片”。
当然,相互模仿的远不止于《卧虎藏龙》、《英雄》等影片,我们随手还可以举出更 多的例子,如《蜀山传》、《天地英雄》等等。影片《天地英雄》中呈现的是一个早在 唐代就已经“国际化”了的西部:一个日本的遣唐使,一个正义、善良的违法者“屠城 校尉李”,以及当地的邪恶响马,还有异域的军队。当然也少不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西 部地域奇观。这部电影被指责为对《英雄》的跟风和对韩国电影《武士》的抄袭。其实 追究其是否跟风或抄袭并无多大意义,因为消费娱乐型的电影之所以能够模式化、类型 化,正在于影片之间的相互借鉴、模仿。《天地英雄》的命名并未刻意回避与《英雄》 ——一个先于它出现的强势文本的关联,而且乐于让观众产生一种互文阅读;它也不介 意与《武士》产生雷同,甚至有意追求同样的影像类型。这都说明《天地英雄》有意加 入到一个互文网络中——由《卧虎藏龙》、《天脉传奇》、《英雄》、《武士》等建构 的“西部武侠电影”网络。
韩国电影《武士》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范例:韩国制造的关于韩国人在中国西部的故 事。韩国并没有大漠孤烟、飞沙走石的“西部”,可他们竟然也需要一个“西部空间” 来放置自己的英雄神话。这又让我们联想到中国人在美国的西部。如果说在《黄飞鸿之 西部雄师》、《中华英雄》等港台电影中,中国英雄在美国西部仍可辨出清晰的“港味 ”,那么到了成龙与好莱坞生产的《上海正午》,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身穿清朝官服的 西部牛仔所演绎的故事。从影片的命名《The Shanghai Noon》(《上海正午》),人们 已经能够窥见其浓重的后殖民色彩。《The Noon》(《正午》)是美国西部片中的经典之 作。在此,《The Shanghai Noon》(《上海正午》)有明显的拟仿和依附的意思。但它 与“上海”有什么关系呢?“上海”可以作为成龙所扮演的清宫武士的指称吗?笔者并不 了然。
到这时,人们已经难以分清银幕上的“西部”究竟属于哪国、哪地了。“西部”—— “国际化的西部”,进行着全球性的同步流动。不过,这并不是单纯的美国“西部”取 代了全球的“西部”,它通过杂交改变了各地关于“西部”的想像模式,而各地的“西 部”只是为这种想像提供新的空间。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不妨让我们再稍微回顾一 下香港武侠电影的发展历史。
应该说,中国的电影,最卖座的类型也是武侠片。中国的武侠电影产生于上世纪二十 年代的上海,其中最有名的要算很多人都知道但都没缘一睹的《火烧红莲寺》,一共拍 摄了18集,要不是因为日本开始侵略中国,武侠片还会继续成为当时卖座电影的主流。 不过,武侠片在三十年代末开始在香港复兴。1949年,香港导演胡鹏拍摄了第一部以广 东民间传奇武林人物黄飞鸿为主人公的电影,此后历经近50年,黄飞鸿成了中国武打片 的一个著名品牌,前后有关德兴、李连杰等十余位影星在近百部此类题材的电影和电视 剧中扮演黄飞鸿这个角色,有胡鹏、徐克等多位著名导演拍摄过这个题材,其中由胡鹏 导演、关德兴主演的黄飞鸿系列拍摄了近80集。在整个五十年代,港台的武打片大体有 两种类型,一种是像黄飞鸿之类的民国装功夫片,一种是神怪类武侠片,前者的代表作 就是黄飞鸿系列,后者的代表作有《如来神掌》等片。
在六十年代初期,港台武侠片的武打动作受日本武士片的影响,模仿里面的武打招式 ,题材也很窄,除了剑仙神怪就是学艺报仇。1964年,香港凤凰公司拍摄的《金鹰》, 在内蒙古实地拍摄,里面展示了摔跤、套马等传统民族功夫,还有蒙古草原的壮丽风光 ,是一部创新的武侠片。第二年,长城公司拍摄的《云海玉弓缘》被认为是武侠片的第 一部里程碑式作品。此后,武侠片的黄金时期来到了。自1965年开始,邵氏公司的老板 邵逸夫对泛滥的老套粤语神怪武侠片感到厌烦,决心要拍摄新类型的武侠片,几经尝试 之后,以《独臂刀》和《大醉侠》等为代表的六十年代后期“更趋暴力与写实的国语武 侠片”日渐兴盛起来。而这批新兴的国语武侠片,广泛地吸取了美国西部电影、日本电 影及好莱坞英雄电影的技巧,制作出了一系列打斗高超逼真、画面暴力血腥的武侠功夫 片。这些影片先是热销东南亚,而后迅速走向全球。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港台武侠片开 始走下坡路,这段时间,各种武侠片的内容无非是门派斗争、学艺报仇之类。然而,到 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终于出了几部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影片《蛇形刁手》、《少 林36房》、《中华丈夫》、《少林寺》等等,出现了几个现在驰名国际影坛的人物,如 袁和平、刘家良、成龙和洪金宝等。香港电影在1986年—1993年进入到了武侠片的全盛 时期。《蝶变》、《蜀山剑侠》、《黄飞鸿》、《笑傲江湖》、《倩女幽魂》、《新龙 门客栈》、《醉拳》等成为这一时期武侠片的代表作。这类影片的特点是武打设计天马 行空,想像力异常丰富。1993年之后香港武侠片开始衰退,不仅欧美、亚洲市场大大萎 缩,就是在香港本地电影市场也受到了美国好莱坞大片的强烈冲击。为了遏制香港电影 制造业的下滑,香港电影工作者利用合拍影片的方式拓展内地市场,最为明显的合作方 式就是将香港武侠片的技术与内地风景(主要是内地西部的风景)相互嫁接。西部武侠片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走红的。
一晃进入了新世纪,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获得了奥斯卡四项大奖,使得中国的武 侠片再次被世界瞩目!
大致了解了香港武侠片发展的脉络和李安在好莱坞的风光后,再回头看张艺谋导演的 武侠片就会发现,他不仅早已放弃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武侠片对历史的深度反思,而且将 沉重的土地、人民、历史漂浮为华丽的形式化的景观。其实,这种精美、浮华的形式追 求,并不是张艺谋单个“英雄”的招数,而是近年来中国主导影视的流行品位。例如, 电影系列,《英雄》—《天地英雄》—《周渔的火车》—《恋爱中的宝贝》等;再如电 视剧系列,《大明宫词》—《橘子红了》—《吕布与貂蝉》—《金粉世家》等。由此不 难发现中国影视由华美、精致而趋矫揉造作甚至支离破碎的走向。
《英雄》在北美票房的大获全胜,推动着中国武侠电影更深广地进入世界大众文化市 场。在笔者看来,中国西部脱“土”成“洋”全球共享,这不是中国电影单纯的成功, 也不是某国文化霸权的失败,而是大众文化生产、消费意识形态的全球普及。消费主义 的逻辑成为电影运用空间的逻辑,全球市场巨大的整合力按照资本运作的逻辑,剪裁着 西部的形象,改造着我们的感官,将我们带离地方、本土、家园,让我们成为“世界主 义者”。然而,正如全球化决不意味着全球各地的匀质性共在一样,“世界主义”对于 不同国家的人们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来说,“世界主义”可能意 味着焦虑的心灵拖着无根的身躯漂荡于虚空的浮华。而对于现实中中国西部的人民来说 ,“世界主义”则可能表示着另外一种境遇:我们栖息在自己的土地上,来自全球中心 的璀璨辉煌吸引了我们,将我们拔离脚下的土地去全球徜徉。可是在我们付出了渴望、 汗水、鲜血、土地之后,它只接收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却拒绝了我们的身体,使 我们身心两间。
全球化不再是遥远的潮声,而已成为我们时代的基本境遇。全球化过程中,“认为每 个生命或生命的方面都受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触及的说法也许有待商榷,但是全球资 本主义确实已经不再寻求内部的一切合作,而是通过边缘化地球上的多数人来获得利益 ,至于这些人是作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已经无关紧要了。”([美]阿里夫·德里克:《 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可是如果我们的 电影工作者们,对此毫无警觉,甚至还把被边缘化的命运视为进入中心的途径,那么就 可能完全丧失了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外想像西部的能力,失去了抵抗的可能。由此我们 联想到伊朗的乡土电影、巴西的《中央车站》和《上帝之城》、墨西哥的《你妈妈也一 样》等电影。虽然由于全球讯息的同步流动,这些影片并不能摆脱被“西方政治之眼” 窥视、定位的命运,但是它们对本土的生存现实的关怀,对地方性记忆的固守和捍卫式 的表现,构成了一种文化抵抗。它们“作为对全球化的抵抗性回应和对自身生存空间的 保卫”,成为全球化中的另一种电影序列。不知什么时候,能有更多的中国电影工作者 梦醒半空,重归土地,加入这一抵抗的系列。
标签:中国电影论文; 天地英雄论文; 黄土地论文; 武士论文; 卧虎藏龙论文; 英雄论文; 上海正午论文; 剧情片论文; 武打片论文; 古装电影论文; 史诗电影论文; 美国电影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武侠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