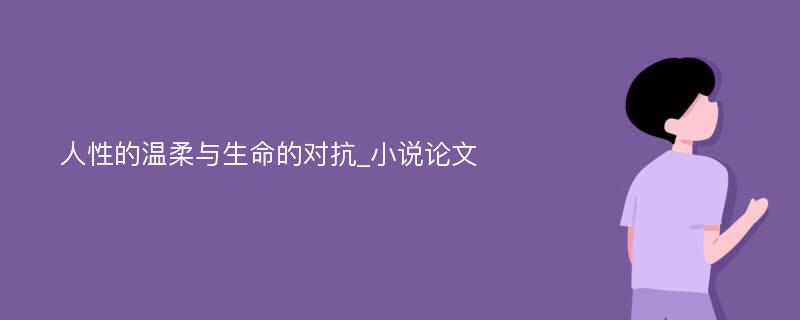
在人性的温情和生命的对抗之间——芦焚长篇小说《争斗》校读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札记论文,长篇小说论文,争斗论文,温情论文,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大约两年前的冬天,我在阅读中偶然发现了芦焚的《争斗》小说。当我告知导师解志熙先生之后不久,他又惊喜地对我说,他也偶然发现了芦焚一部不知名的长篇小说的两章《无题》,看来,《无题》和《争斗》显然有着主题和情节上的相关性。随后,我对《争斗》和《无题》两篇小说的校读,断断续续的完成了,确证《无题》正是《争斗》的续篇,这样,两篇小说就合而为一,统名之曰《争斗》。此处就这部新发现的芦焚长篇小说及其更大的“一二·九”三部曲,略谈一点校读的体会,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它们的关注和研究。
关于芦焚的长篇小说,解志熙先生在《现代中国“生命样式”的浮世绘——师陀小说序论》一文中,曾经说过芦焚“另有两部长篇小说《雪原》、《荒野》只发表了部分章节而未能完稿”;另一位研究者在《生命的挽歌与挽歌的批判——师陀的“果园城”世界》一文中,则认为就其完成的情况看,《雪原》依然可看做果园城故事。不过,作者自己在回忆文章中明确提到过,《雪原》是其所写的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三部曲之一。①从现有的发现看来,作者的这句话是需要研究者认真对待的。
如果将1940年1月-6月在上海《学生月刊》上连载的《雪原》,与1940年11月-12月间在香港《大公报》“文艺”栏和“学生界”栏发表的《争斗》,以及1941年7月在上海《新文丛之二·破晓》上发表的《无题》放置在一起,则可以清晰地看出芦焚以“一二·九”学生运动为主题所作的系列长篇小说的轮廓。其中,《争斗》应该是第一部,而最早发表,且已经收入《师陀全集》的《雪原》,应该是第二部,至于第三部则还未能确知。至于《无题》,则当是《争斗》一篇违碍于愈来愈严酷的香港文学审查政策的部分文字的残存。由于当时文学环境的错综复杂,要看到芦焚所作的“一二·九”运动三部曲的完整面貌,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比如,现在所发现的《争斗》本身显然就是未完稿。《争斗》在香港《大公报》停刊不久,该文的编辑者于香港《大公报·文艺》第1002期刊发的一则《启事》(1941年1月4日),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争斗》作者现在病中,续稿未到,此文暂停发表,敬希读者见谅编者。”而且,辗转于战乱中,作者艰窘的个人境遇,也使原稿发现的可能性化为泡影,他看来早已把原稿丢失了。因此1947年3月9日,芦焚在上海《文汇报·笔会》第190期发表启事:“师陀启事 长篇小说《雪原》(刊于上海出版之《学生月刊》),《争斗》(刊于香港《大公报》),及短篇《噩耗》(亦刊于香港《大公报》)存稿遗失,如有愿移让者,请函示条件,寄笔会编辑部。”
如果从创作主题和表现方式来看,师陀的《争斗》、《雪原》乃至《荒野》等作品,与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典型的左翼叙事方式也不完全吻合,而有着他自己生命体验与情感取向上的独特性。其中,不同的人在其不同生活样式中所濡染形成的不同性情,依然是其关注的焦点,即使是在时代斗争的幕布之下徐徐展开,对“人情”冷暖和“人性”善恶变奏的感受和呈现,依然不脱现世俗常的温情。比如《争斗》中有这样的片段:
杜兰若是瘦弱,憔悴,看起来有三十岁或者三十多岁了,虽然她的实在岁数要小的多。她有一个小小的浅棕色的脸,小小的好看的鼻子,她的各部分——手、脚、头都是小的,比起她的这些部分,她的身个是长了一些。然而,她是瘦得多么可怜啊,她的小耳朵是透明的,她的手是见骨的,她的嘴唇——自然它是红润过——是失了血色的。当她抬起头来喊的时候,一缕头发从她的干燥的额落下来。她手里拿着一本书,她整整一个下午就拿着这一本书。她是好像怕冷似的缩在火炉前面的椅子里,一匹小猫——一个灰色的小东西在她的脚边打着呼噜。她的眼睛——在不久以前还是澄明的,镇静的眼睛,它是润湿,发炎,怕光,当它看着她手里的书,它便像一个老婆婆的似的缩拢来。这本书上正说着,至少是在这个时候,它正说着跟她没有关系的话。②
处在肺病修养期的瘦弱憔悴的、瑟缩的小猫似的杜兰若,手中拿着一本通俗的鼓吹暴力革命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上留着俄国革命的深刻印记,“画出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巨大的变革的轮廓,同时它们又指出了过去的踪迹和未来的路径”,那些曾经强烈吸引着她的粗暴而富有召唤力的语句,在今天“时常要淌泪来的眼睛刚接触到这里她就很快的翻过去了”。“这些话是不连接的,高空中那些干燥的破碎的浮云似的,它们偶然把她的脑子遮暗一刻,接着它们,那些灰色的影子又很快的滑了过去,它们没有留下一点影响,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曾经深切投身于革命的杜兰若,此时显示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冷淡。她厌倦而无聊,有一种失意和被遗弃了似的感怀。杜兰若是革命的推动者,芦焚却并未将之纳入左翼叙述的那种典型模式中去处理,文字也毫无生硬粗率之感;而是以一种透视人情犹疑和脆弱、温暖和隔膜的广大透彻的笔墨,将之不加夸饰、不做贬斥地温润地呈现出来。在杜兰若身边,参差地设置了一个“李妈”,使这种视角和笔墨呈现得更为充分。
这个多言的老妇人现在好像是年轻了二十岁。她的话匣子一打开是连她自己也作不得主,连她自己也收不住了。她笑着向杜兰若走过来,她把手放到火炉上去。她问将来少爷他们结婚的时候是不是要用汽车;她说汽车是新派人用的,她说花了很多钱连看都不让人家看见,就呜的一声一阵烟过去了,她自己就不赞成;她说到底是一场大喜,她赞成用花轿。
“可不是吗?你想想看,小姐,吹鼓手吹吹打打的有多么好。要是汽车——”
杜兰若觉得李妈也着实可怜,她操劳了一生——一个人操劳一生便有许多积蓄,从生活中得来许多牢骚,但是在这个寂寞的院子里却没有一个人肯跟她说长道短。杜兰若看她的兴趣很好,便想跟她开一个玩笑。
“李妈,”她打岔道,“当初你出嫁的时候是用轿吗?”
李妈听见杜兰若讲到她,她向杜兰若极有风情的望了望,似乎更年轻了。她的皱褶的老脸上又回复了光辉,她满面笑容的说:“哟,我的好小姐!我们穷人用不着轿;有钱人跟城里人才用得着;我们是一辆牛车就什么事都办了。”③
在揭示一场即将波及社会各阶层的大争斗之前,以如此多的笔墨呈现一个与争斗无甚关系的老女仆的性情、感怀和梦想,并且饶有风趣地述说这个操劳了一生的老人的唠叨、玩笑和风情,甚至比《果园城记》中的笔调更为柔和有情,批判性的视角也隐匿得更深。在这种看似无关紧要的闲谈中,展现出不同身份的角色之间的温情,那种虽有隔膜,却真心互相关爱的温情。在失却家庭,且憔悴于革命路途的杜兰若的心境中,这种善良和温情有着怎样的分量呢?“李妈”身上的这种独特的光辉,与沈从文的《边城》中那个撑渡船的老人倒可加以对比。
芦焚这篇小说中的另一个类似于革命指导者角色的“马已吾”,也与左翼革命叙事中的那种激进的、富有煽动力的形象不同:
马已吾是那种昼夜不息的在历代典籍中生活,因此永远不会胖起来的瘦人。他大约是将近四十岁了,脸色——这种人的脸色永远不好,它是像蜡渣一样黄的,线条却是像一个艺术家刀下的一般的精确,瞭然,干净,但是毫不勉强。他的剪短了的浓茂的胡子使他的五官特别显豁,神情特别澄清。照实谈起来,他是一个教员,一个书生,一个学究。像这样的人在北方并不少;他们在大学里同时又在中学里兼几点钟功课,薪水是可怜的,他们就落着这一点可怜的薪水维持生活。这些新的“犬儒学派”,他们有的还没有结过婚,有的他们的太太是在他们老家的乡下。他们不常在公众的地方出现,他们没有野心,他们也不加入以饭碗为目的的任何派别。他们的一生大概是注定了要在冷落中过去的,他们并不以每月十二元的包饭为粗劣。除了书籍他们也没有别的嗜好,实际也正是只要能够读书他们便觉得已经是无限丰富了。
马先生是善良,温厚,缄默,在他的血管里保有着一种农民性质的,近乎原始的,不可动摇的倔强,他的祖先无疑的是跟任何人的祖先一样,他们是老根深深的伸进泥土里的,直到现在,读书人的血液还没有把它——那种原始天性——冲到十分稀薄。正是这些特性,现在被一个突然传来的消息——一个事变打击得七零八落的了。他在窗下坐了很久很久。外面是静寂的。这个庭院常常是静寂的,它早已陷入一种无声的渐趋灭亡的破落中。这时候房东们大概是听戏去了,再不然就是他们正围着火炉吃小点心,他们还保持着前代的静肃,他们很怕吵闹,甚至很怕高声说话。一个北方的十二月的下午。太阳快要离开这个大的古老的城市,快要落下去了,只有对面的屋脊上还残留一线薄弱的昏黄的光辉。天空是晴朗、干燥、无情的冷。在房子里,火炉在马已吾背后爆炸着。④
悲愤的马已吾先生在北平寂静的破落的院子里,在“沉静的、冷的、和无情的天空一样静默一样冷的”的氛围中,以一种自甘寂寞的新“犬儒派”的姿态,来对抗“现在他们却是用大刀向敌人谄媚,他们震慑反抗,用青年的血来筑他们的罪恶的交椅”的沉重现实,马已吾一面想像着屠杀的场景,一面用笔在纸上抨击着屠杀的罪恶。叙述笔调是激烈而内敛的:
一个观念——幻象包围着他,他连气都透不出的被围在核心。在上面是高的,清澈的,明亮的,其蓝如冰而又无情的冷天空,地面是完全冻结了的,石头一样冻结了的。在北方任何大的风雪都会使人感到一种温暖,惟独这种晴空都是使人要诅咒的寒冷。泥土、墙壁、树木都会发出细微的响声,连空气似乎也凝结起来,也在寒冷中爆裂。就在这样冷的荒凉的所有的门都为了保持温暖关起来,所有的树木都悲伤的弹抖着向天空伸出它们的枯索的手臂的街上,在那坚硬的地面上横七竖八的偃卧着年青人的尸体。……⑤
马已吾对这种丑恶的屠杀,感到的是憎恶。当过去的学生杜兰若来看望他,随意地询问时局状况时,马已吾先生对这个积极投身于革命而暂时居家养病的女学生的瞬间感觉,是相当出人意料的:
马已吾对着这个损害了健康的女子,他想起她还在做中学生时代,没有人能想到一个用红绒绳扎着发辫,自信力极强,看起来有几分近乎自负的沉静少女有一天会失去青春,变成十分憔悴。在平时,也许在昨天他还赞赏她的意志坚强,这时候——一阵风波刚刚过去,杜兰若的不幸触动他的怜惜心,他为他这个十年前的学生,为这种变化颇有些感慨。
“女人总比男人可怜,”他在一瞬间这样想。在平常他并没有考虑过这种问题。甚至反对这种见解,现在他却以为在时光没有过去以前——假如她有爱人——一个女子应该及时结婚。⑥
只是单纯地哀惋一个少女青春的消逝,并且发出庸常的感叹,这当然是以人性的角度,而非提倡暴力斗争的革命导师的角度所感所发的。简而言之,芦焚在《争斗》中虽然处理的是一个激烈对抗的、涉及宏大的社会斗争的主题,但他所选择的叙事角度和叙事话语,还是更接近于其最初的《果园城记》中的那种个人化的哀惋人性的调式,而非采纳当时所流行的强调阶级斗争、集体意志的调式。其旨趣和效果,显然也是意蕴颇深、独具一格的。
这样,芦焚的此类小说叙述,遂呈现出一种介于展示人性温情的个人叙述和揭示生命对抗的阶级叙述之间的独特景观,而作家芦焚的位置,也是在一种两面有缘却无所归属的边缘状态了。介于个人主义和群众心理的转换,这是芦焚此篇小说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芦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似乎是处于个人主义的温情和群众集团的狂热之中间地带。
有的研究者比较强调芦焚个人历程的左翼革命性,当然,芦焚和“左联”有过人事上的接近和观念上的共鸣,不过,同时,芦焚与正统“京派”也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虽然其对京派的某些观念与风格不无反抗之处。如何看待芦焚在二者之间的个人抉择,1934年10月发表于天津《当代文学》上的短篇小说《奈河桥》中的一句话,倒是可以给人几分启示——“从此我更知道,真正的同情,是在破碎的地方以及三等慢车里!”在这里,他省悟到“良心”是什么;并且在他眼中,种种永不再见且瞬间消失的善恶世相,是“和谐而且充满着无限生命”。这样,瞩目于诸种善恶世相,描摹那种被践踏后复苏的温暖,便是其作品中顺理成章的主体了。关于芦焚艰苦而成就非凡的作家生涯,以及其与左翼革命相亲近而又未被卷入的处世姿态,《奈河桥》中有一句告白也值得注意倾听:“自己虽也经过一些艰苦,毕竟还是一个书生。于是我就恨开初不当读那么两句书。我们这一代读书是最危险的。”⑦
另,左翼革命文学研究者尹捷博士,对于本文的写作,及芦焚佚文《争斗》中涉及左翼革命话语部分的理解和注释,有过直接的帮助,仅记于此,聊表谢意!
2009年9月着笔于旅途,2011年6月补作于紫荆公寓。
①刘增杰编:《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88页。
②芦焚:《争斗》(第一章1),香港《大公报·文艺》第960期,1940年11月2日。
③芦焚:《争斗》(第一章5),香港《大公报·文艺》第964期,1940年11月7日。
④芦焚:《争斗》(第二章7),香港《大公报·文艺》第965,966期,1940年11月9、11日。
⑤芦焚:《争斗》(第二章10),香港《大公报·文艺》第967期,1940年11月13日。
⑥芦焚:《争斗》(第三章13),香港《大公报·文艺》第969期,1940年11月16日。
⑦芦焚:《奈河桥》,《当代文学》第1卷第4期,1934年10月1日。
标签:小说论文; 人性论文; 文学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无题论文; 文化论文; 大公报论文; 雪原论文; 杜兰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