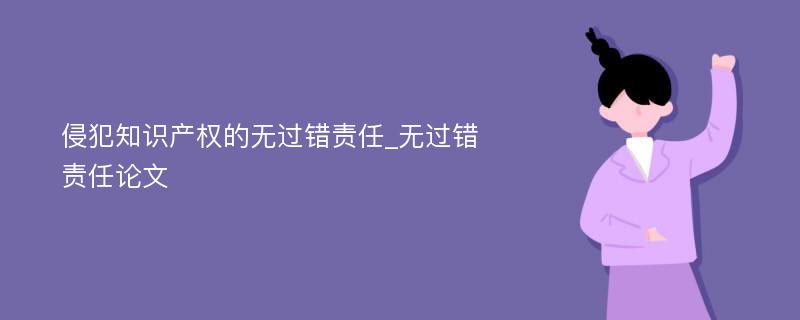
侵害知识产权的无过错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产权论文,无过错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产权侵权认定时应归入“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这是一个已由司法实践摆在我们面前不能不回答的问题,也是在中国知识产权法修订中应进一步加以明确的问题。因此本文打算就此展开讨论。而在中国知识产权立法框架基本形成的90年代初,它还属于一个很难展开讨论的问题。
一、对知识产权,在侵权认定中应分别不同情况,同时适用“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两种原则
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一样,各具独自的特殊性;但相对其他许多民事权利的特殊性来说,它尤为特殊的一点是:在各国制定民法典(包括“民法通则”、“民事立法纲要”等作用相近的基本法)时,人们对知识产权特殊性的认识,往往还不深刻。因为它毕竟是远在一般物权、债权、人身权等权利产生、乃至法律对这些权利的规定已臻完备之后〔1〕, 方才因商品经济及技术的充分发展而产生的一种较新的民事权利。近二百年前《法国民法典》的立法者,与十年前中国《民法通则》的立法者,在各自的立法阶段,对知识产权的认识深度,均以较相同的形式,反映在了两部法中。所不相同的是:法国现行《知识产权法典》的立法者公开承认了在基本法立法时,对知识产权特殊性认识不足,于是在知识产权基本法中适用本部门法的特殊规定。这些国家的学术著作也相应地承认上述认识上的差距。对上述认识差距在我国则是较多地在现行知识产权立法的条文中得到承认(但不及有些民法法系国家完全);而学术著作中对此的承认就较为不足了。更多著作是强调当年所订立民事基本法的一切,应毫无例外地完全适用于在后的、人们认识早已深化的时刻制定的知识产权法。面对这一观点,人们在讨论知识产权问题(不限于归责原则)时,应注意离开这一误区,并应把这与“否定民法上的一般原则”区分开。否则,等于自动把自己的知识产权法研究束缚在多年前他人的既定认识水平之下。
知识产权(特别是其中无需行政登记即可依法产生的版权),由于其无形并具有地域性、受法定时间限制等特点,所以,其权利人的专有权范围被他人无意及无过失闯入的机会和可能性,比物权等权利大得多、普遍得多。这就是说,无过错而使他人知识产权受损害,在某些情况下具有“普遍性”。而侵害物权则不然。他人的院墙你不应翻过去,他人的财物你绝不该占为己有,这道理是明明白白的。
于是,无过错给他人知识产权造成损害的“普遍性”,就成了知识产权领域归责原则的特殊性。同时,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原告要证明被告“有过错”往往很困难。而被告要证明自己“无过错”却很容易,这也是带普遍性的。
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及谈判后,因复制他人视盘、唱片而被关闭的厂家中,确有与“作品提供人”签了版权合同而对方作过“不侵权担保”的事例〔2〕。事实上, 也确实不可能要求任何厂家明确无误地了解全世界的作品提供者孰真孰假。可以说,个别被关闭的厂家是“无过错”的。但如果我国法院当时宣布这种印、售盗版(可能不宜称为“盗版”,因有提供人的担保)制品的厂家“不侵权”,则在世界上将引起哗然是可以想象的。
与此相近似的图书出版中,强调“过错责任”的弊病就更明显了。在许多情况下,被侵权人虽然能见到充斥于市场的侵权制品,但根本无法确认谁是抄袭者或是其他侵权人,乃至难以断定是否存在出版者之外的侵权人。他只能到执法机关起诉出版者。在出版者不承担侵权责任(也不负连带责任、不成为“诉讼中第三人”)的情况下,它没有义务向被侵权人指明侵权作品提供者的真实姓名、住址等等。而且,即使出版者提供了有过错之责任人(抄袭者或其他人)的姓名、地址,被侵权人在很多情况下也难以、甚至不可能主张权利。例如,如果抄袭者在广州,而原告及出版社均在北京,原告须赴广州起诉。因为北京既不是被告所在地,也不是侵权行为地(即使相关的侵权印制品在北京流通,由于出版者及其后与出版者同样有“非侵权担保”合同的发行者的行为,均因无过错而不构成侵权)。如果抄袭者在国境之外,权利人的处境就更糟了。
在作品尚未发表的情况下,实行“过错责任”原则,权利人(往往是作者)受到的损失更难以弥补。因为有的作品的价值正在其首次发表之时。
仅仅追究侵权作品提供者的侵权责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补足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也不可能阻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由于这里的假定前提是无过错的出版者及发行者均非“侵权人”,故不能说阻止“侵权”活动进一步扩大。虽然在国际条约如Trips中, 均强调“阻止侵权活动进一步扩大”。
有人认为被侵权人从抄袭者(或其他侵权作品提供者)那里获得的赔偿不足,可以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无过错出版者返还“不当得利”,并且是“原则上均依受害人所受损害程度确定赔偿责任”〔3〕。 这里有几个问题将在受害人请求赔偿的诉讼中难以解决。第一,按照“过错责任”原则,受害人所受之“害”并非来自无过错的出版者,他有何依据向出版者求偿?第二,出版者已被定为非侵权人,其“赔偿责任”从何而来?所以,在这种场合中,被侵害人真正获得补偿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君不见,即使在被认定是侵权人或负连带责任人或第三人的情况下,知识产权权利人都未必能从出版社那里得到实际赔偿。更不消说已把他们排除在“侵权”之外了。
至于说“无过错”的出版者的行为未必不违法,故可以以“违法”为由,阻止其进一步印制(及发行)有关权利人的作品,这在实践中也往往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往往是滞后的,也要在相关作品已经进入流通渠道难以收回之后。这是因为当权利人作为原告发现市场上有证据确凿的侵权印制品时,他的第一步往往希望在承担诉讼保证金的前提下,要求法院下临时禁令,尽快中止有关侵权制品的印制或(和)发行,而不是等最后法院判决有过错者侵权成立之后(从而出版者再印制发行也有过错)再去禁止,因为,那就太晚了。中国(及外国)有些知识产权要案判决的难度很大,许多侵权纠纷几年之后方能判决,那时再禁止印制发行已失去了意义。同时,在这期间(判决之前),依“过错原则”而不可能成为侵权人的出版社发出的印制品,在出售、出租、上网或其他过程中,已可能使第二级、第三级乃至更远的第四级“无过错”的经营者都获了利。要作者在几年之后,再逐一找这些“不当获利”者求偿,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
此外,我们应注意到:“违法”而无过错,并非一切国家侵权法的通例(当然,反过来说,有过错可能未必违法)。例如法国侵权法即认为违法均有过错,德国侵权法才把二者明显分开。
在专利权、商标权领域,也会出现相似的情况。不同的是,由于专利、商标授权前后都要“公告”。因此,有人可以认为凡未经许可而使用之人均有过失。但专利领域的律师(或其他人)也会以专利的不同技术领域过广、每年发布的专利文献过多,不可能要求某一特定小范围的生产者全部知晓等理由,申辩其“无过错”。
所以,我总感到,主张在知识产权领域全面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看法,是为未经许可的使用人(先不言其为“侵权人”)着想过多,而为权利人着想太少。如真正实行知识产权领域内全面的“过错责任”原则,那么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丧失了实际意义。
当然,并不是说“过错责任”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就完全不适用。在这点上,我很赞成不宜“不适当地扩大责任人的范围”〔4〕。 正如法理学家们常讲的一个例子:中世纪晚期一位北欧国王战败而导致亡国,责任追到其将士则可,但若追到钉马蹄的铁匠,就太扩大了(尽管国王战败的原因之一,是马失前蹄)。
在直接出版印制侵权出版物的人之外,发行者以及为侵权物品或侵权活动提供仓储、运输、场地、机器等等的人,亦即我们常说的间接侵权人或“共同侵权人”(Contributary Infringer),在确认其侵权责任成立时,则真的应考虑“过错责任”原则了。这就是为什么本文开始时讲,只是在“某些情况下”,而不是在一切情况下,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力求既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又不致把侵权责任者范围无限扩大。为实现这一两全之策,最可取的方案似乎是对于侵权的第一步,即未经许可复制,或作为直接传播的第一步,即如表演等利用作品的行为;对未经许可制作、使用等利用专利发明创造的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对其他行为,以及对一切间接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考虑采取“过错责任”的原则。
值得提出的是,有文章曾正确举出的复制者可证明自己无过错的例子(“受抄袭者欺骗、经适当查询权利状况后仍未能知晓实情”)。这种情况也正是许多作者与版权人所担心的,正是他们认为至少侵犯复制权应归入无过错责任的重要原因。因为,“过错责任”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全面适用,尤其是上述排除过错的例子,可能对不法复制者的下列做法是一种客观上的鼓励:在被诉侵权后,与抄袭者或其他侵权品提供者补签一份提前了缔约日期的“不侵权担保”合同,以此“约束”被侵权人及法院;再补作一份“查询证明”等。在“关系学”盛行的今天,在我国极难识别这些“无过错证明”的真伪。此外,“有过错”的侵权品提供人,往往根本找不到(或根本不存在)。这样一来,在全面适用过错责任的华盖下,中国的作者(或其他知识产权权利人)会吃惊地发现:与满街侵权复制品并存的,居然是无过错、从而不承担侵权责任的复制者。这时我们只能对作者(及其他创作者)说:谁叫你明知如此却仍旧搞创作,看来只剩下你们才“有过错”了。
二、国外成例中可借鉴的内容
同知识产权领域的其他问题一样,侵权认定时的归责原则,虽然在中国还“远远没有解决”,但在国际上则早已有之。不仅在一些国家国内法有、学者著作中有,在国际条约中也有,而且其中可供我们借鉴的成例是不少的。当然我们不可不注意中国的特点,但也不可拒绝借鉴国外成例,而徒劳地重复别人多年前已否定了的理论。
民法中侵权法比较发达的德国,在主要以《德国民法典》第823 条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却以第278条、第831条到836 条等诸多条款,规定了“无过错责任”原则。除此之外,德国还在1978年的《严格责任法》〔5〕以及许许多多专门法律中, 进一步明确与补充这一原则。这一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之外的适用,又与同是欧陆法系典型的法国有所不同。例如,德国1952年《道路交通法》在确认无过错责任时,将同时考虑受侵害人的相应过失,而法国1985年《道路交通法》却对此不予考虑。就是说,法国的“严格责任”原则,比德国更严格。这一点也相应地反映到了知识产权法中。
知识产权界的同仁们引用了某些国内已有的论述,阐明现代无过错责任原则可能在有的国家是工业革命后才随生产与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6〕。我感到他们应当再向前跨一步走入自己的领域, 即指出知识产权的许多受保护客体,也正是随着生产与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故在过错责任的原则上发展起来的无过错责任原则,顺理成章地适用于这一民法中发展起来的新领域,虽然现在我们没有理由要求研究一般侵权责任的论述做到这一点。如专门研究德国侵权法的B.S.Markesinis先生,在其著名的《德国侵权法比较导论》一书的1993年的最新版本中,也依旧只在第二章A节第1项的(e)分项中,擦了一点知识产权的边。 但对于专门从事知识产权的学者来说,如果只走到这一步,就显得不够了。
德国的知识产权法学者A.Dietz博士,则对这一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说:“当侵权行为(这里他使用了“acts of infringement”,即开宗明义告诉人们所论及的是已确认为侵权的情况)既非故意,又无过失时,德国1995年的《版权法》规定了司法救济的某些例外”。 〔7〕Dietz的论述并不是仅凭“推想”而来,是有德国法律条文为据的。
在德国1995年修订的《版权法》第97条(1 )款中规定:“受侵害人可诉请对于有再次复发危险的侵权行为,即刻就采用下达禁令的救济:如果侵权系出于故意或出于过失,则还可以同时诉请获得损害赔偿”。该法第101条(1)款也规定:“如果侵权行为人既非故意,又无过失,却又属于本法第97、99条依法被下禁令、责令销毁侵权复制件或移交侵权复制件之人,则在受侵害人得到合理补偿的前提下,可免除损害赔偿责任”。
这里规定得再清楚不过了:对有无过错的认定,是确认可否(并非一定)免除赔偿责任的前提,而不是认定侵权的前提。应当说,这种规定才对被侵权人与无过错侵权人均为合理。
在德国1994年修订的《商标法》第14条中,有近似的规定,这就是:一切对商标的侵害,被侵害人均有权对侵害者提起侵权诉讼,要求立即停止侵权:对明知的或因过失产生的侵害、则被侵害人有权进一步要求损害赔偿。完全相同的规定还出现在德国1994年修订的《专利法》第139条中,这里不再复述。
法国1995年修订的《知识产权法典》,在保护版权上是比较极端的,它根本不讲对无过错之侵权人的任何免责。就是说,不论侵权者的主观状态,只要客观上行为构成对权利的侵犯,则在下禁令、在可获赔偿等项上,被侵害人均可提出请求。有人可能认为这是我主观臆断的。因为法国版权保护条款在这方面与中国《著作权法》第45条、第46条一样,而与德国版权法不同。它既未讲“过错责任”,也未讲“无过错责任”。但人们应注意法国法在版权保护上与中国的一点重要不同:它是将版权保护、专利保护等收入一部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这一部法在行文上应是前后一致的。在该法前半部分的专利保护条款,即第L.615—1条,侵权责任被分为三段。 第一段规定:“一切侵害专利权人依本法享有的诸项权利的行为,均构成侵权”,没有例外。第二段规定:“侵权人应负民事责任”,也是泛指。第三段规定:“然而,如果提供销售、提供上市、自行存储侵权产品之人并不同时是侵权产品的制做人,则只有其确知该产品系侵权产品的事实,方负民事责任”。而在同一法的版权条款中,则只有上述三段中的前两段。所以,可以认为法国版权法中,没有对“无过错”予以免责的规定。
与法国同属一法系的希腊1993年《版权法》,象法国一样地进行无过错责任极端保护(即不象德国那样对无过错侵权者减轻责任),却又比法国的规定更加明确。该法第65条(3 )款规定:“不论侵权行为是否出于有意或过失,作者或其他权利人均有权要求侵权一方从未经许可的使用获利中,支付法定赔偿额,或支付其侵权所获利润”。
同样属于大陆法系的意大利,在1961年的一则法院判例中所确立的“严格责任”原则〔8〕, 至今被意大利版权学者及法院认为仍旧适用。而中国知识产权界目前所讨论的问题恰好涉及这一判例。该判例的案情涉及一家出版商,具体地说是一件音乐作品的提供人向出版商保证了不侵权,该案在审理中又无任何理由认为该出版商有其他过失,可是法院仍旧判定出版商侵权。
大陆法系的日本,其现行《著作权法》第113条在第(1)项a 项中,规定了直接侵权属无过错责任,在b项中, 规定了间接侵权属过错责任。日本版权学者尾中普子讲过:在受侵害人要求停止侵害时,“只要有侵权事实即可,不需要具备主观条件如故意、过失”〔9〕。 日本知识产权法学者纹谷畅男在其《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中,有同样的论述〔10〕。
现在我们再来看几个英美法系国家。
前文提到的“随工业革命的完成而产生无过错责任”这段历史,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却有些“例外”。若叙说完整些,似乎应当是:英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最早判例可以追溯到1353年,这是英国一位著名法官在1866年的一则判例中提到的〔11〕。就是说,英国侵权法几乎开始于无过错原则。那时过错原则反倒是特例。在工业革命之后,有些法学家感到过广地适用无过错原则的不合理性,才在侵权法中更多地引入了过错原则〔12〕。当然,对因技术发展而产生的应保留无过错责任的新领域,保留下来了(而不是“产生”出来)。对原来适用并仍将适用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同样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侵害知识产权(当时分为“工业产权”与“版权”)的责任认定,这是Cornish 多年前就明确阐述过的〔13〕。
就是说,与我国学者所了解的法、德等国有所不同的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英国不是上一世纪末或本世纪初提出的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不过,对当前我国要讨论的重点来讲,这些历史并不太重要。这里也就无需用更多的篇幅去考证了。
1892年,英国王座法庭(应是“女王座”,当时女王在位)的一则著名判例,曾被认为是法、德现代无过错责任出现前的一个典型。在判例中,一家拍卖商拍卖了一件不属于委托拍卖人所有的物品。虽然该拍卖商也与委托人有(类似我国抄袭者与出版者之间的)担保合同,同时也再无其他过失,但法院仍判拍卖商侵权〔14〕。与上面引用的意大利案例一样,外国历史上在司法实践中,与我国目前遇到的纠纷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在这些国家判定这些案子时,适用了无过错责任原则,而且未引起广泛的反对。中国则是在讨论是否适用无过错原则,反对的呼声却已经很高了。
1953年,英国只在Goddard 委员会讨论一项极特殊的民事责任时,提出过在该领域应排除无过错责任〔15〕。1967年,英国“法律委员会”(Law Commission)作出结论:经过再三研究,确认在某些领域继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有益的〔16〕。德国民法学者在论述侵权行为法时,往往不谈知识产权的侵权。而英国的侵权法专著,一直把“知识产权”作为一个重要领域,以较多篇幅论述其中的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17〕。
英国无论其1956年《版权法》,还是1988年《版权法》,均是以专门指出个别侵权行为归入过错责任,来反推其余均系无过错责任。这也不是笔者的臆断。不仅英国《舰队街判例集》所载当年版权法修订委员会主席Whitford法官对1978年的一个判例是这样解释的〔18〕,英国的知识产权法学家Cornish也是这样解释的〔19〕。
同样是英联邦国家的澳大利亚,其《版权法》从框架到内容,均出自英国法;在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规定上,也与英国法基本相同。只是在澳大利亚法中更加明确。该国1968年的《版权法》至今,历经多次修订,但其中第115条从未变更。 这一条明白无误地把“无过错责任人”称为“无辜侵权人”(这是直译Innocent Infringer)。就是说,首先认定这种无过错行为属于侵权,然后再规定如何减轻这种侵权人应负的侵权责任。这是因为澳大利亚司法实践或判例法远不如英国发达,故不能只等有判例再加以解释,须在成文法法条中特别阐明。对此,澳大利亚版权学家Jim Richetson 在其十多年前的《知识产权法》一书中,曾更明确地告诉读者:“请注意,Innocent(此外我们可译为“无过错”)并不能使侵权人免除侵权责任,只可以使他减轻赔偿责任,但亦不能减到低于其应支付的赔偿”〔20〕。我感到法律上的这种处理及学者的这种解释,比起我国同事们的意见(先认定并非侵权,再按“不当得利”确定“赔偿责任”)要更顺理成章,在实践中也更可行。
英联邦国家如加拿大〔21〕、新加坡、新西兰等一些国家的版权法,都与英国《版权法》相似,而更接近澳大利亚《版权法》的明确行文方式。这些国家(以及英、澳等国)的专利法、商标法,则在划分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上,也是同样明确的。他们从没有“一刀切”地否定过侵犯知识产权的无过错责任。这些英联邦国家的专利法、商标法,也无例外地采用(前文引述的Cornish 所说)在直接侵权上的无过错责任与间接侵权上的过错责任。在这些法中,1995年新加坡《专利法》第69条(1)款比较典型〔22〕。
至于美国,在其版权侵权上施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广为人知的。这无需引述法条及学者、法官(判例)对法条的解释,只需注意一下美国政府关于信息基础设施与知识产权的1994年6月《绿皮书》与1995年9月《白皮书》就够了。
在《绿皮书》中提出,又在《白皮书》中申明的一点是:不能因为上网的作品太多,“在线服务提供者”不可能加以控制,就改变美国法律以往对侵犯版权普遍适用的严格责任原则,也不能专为“在线服务提供者”(下称“网络服务公司”)开一个“过错责任”的口子。因为那将对版权人不公平,将使版权制度丧失意义〔23〕!1996年10月,一位中国学者在与美国专利局副局长C.G.Lowrey的面谈中,问及《白皮书》为何历时一年却不能成为法律被国会通过,其回答仍旧是:网络服务公司坚决要求对他们“例外”地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广大版权人坚决不同意。所以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虽然美国《版权法》上从来未出现“严格责任”(或与其同义的“无过错责任”)术语,但所有学者及法院均明白无误地知道既然未讲“过错责任”,即暗示无过错责任。因为在美国从来没有过版权侵权是否属无过错责任的争论。他们现在的争论集中在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要不要增加一个过错责任的例外(过错责任在这里仅是例外!)。该国与我国版权保护意识的差距,是可想而知的。
人们普遍认为网络服务公司的要求很难达到。因为与其争论的另一方的“版权人”中,大多数是出版商,他们比作者更有经济实力。在不同意对网络公司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问题上,出版商与作者联起手来了。值得注意的是:出版商并没有进行“趁火打劫”的讨价还价,即并未提出过:“为什么只给网络公司过错责任的优惠,而不给出版者?”他们只是反对对方的意见,并未同时提出改变法律,要求对自己也实行过错责任。
当然,如果读者认为必要,指出几个美国学者在这方面的论述也不困难,因为这种论述从几十年前的老Nimmer到现在的小Nimmer,是非常多的。
美国知识产权法学家Paul Goldstein 曾指出过:在知识产权领域,“要证明被告侵权,原告并不需要证明其有过错”〔24〕。美国版权学者M.Nimmer 指出:“虽然在一般情况下, 无过错这一事实并不能使侵权免责,但间接侵权中的Vicarious Infringement 要确定时, 总要在直接侵权的雇员行为中,找到与雇主的一定关联”〔25〕。
有关的判例也有许多。较近的又较有名的,应属1994年的Sega 公司一案〔26〕。在该案中,法院不仅认定了无过错责任依法适用于一切以往的直接侵权人,而且无例外地适用于今天的网络服务公司。
在例举并分析两大法系的立法、司法实践及学者有关侵害知识产权的无过错责任的规定及著述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看一下现有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
应当说,从公约中找到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这样具体问题的答案,是困难的。如果知识产权公约过细到能全面回答这样的问题,则这种权利的地域性特点就会面临消失。不过,近年来随着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有开始干预各国执法的趋势,在这种新发展起来的公约中,有关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的原则,不是完全找不到的。例如,在Trips 中即有相关的规定。
首先,Trips 在实体条文部分,述及各部分知识产权(尤其在专门规定专利侵权认定的第34条),均未规定“过错责任”。当然,如果仅据此就断言Trips 主张无过错责任,未免显得太武断。因为,Trips 实体条款中也未明文规定主张过错责任。但Trips 实体条款中确有多处指明了把过错责任作为例外,依此反推其他未指明之处,不言而喻归于无过错责任,应不属于武断。这就是集成电路销售活动中的无过错销售者及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无过失者的特例〔27〕。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当Trips 首次在国际条约中,把过去仅依合同产生的、非专有的商业秘密,放入专有的、不依合同也可以产生的知识产权之中时,给商业秘密的无过错获得者网开一面,是合理的。这也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在纳入商业秘密之前,一般的知识产权在受到侵害时,均不言而喻地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如果读者认为仅这样“推论”仍不足以服人, 我们可以进一步从Trips 执法条款的第45条得到印证。该条第(2 )款规定:“在适当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也无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国)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
在这里,不仅无过错可被定为侵权,而且可判其负赔偿责任,同时是双重的赔偿责任。“在适当场合”一语,又排除了“一刀切”地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至少它排除了对前文讲过的半导体芯片产品的无过错再销售人的赔偿责任。它还有可能排除一部分无过错而为间接侵权行为人的赔偿责任。但它又实实在在地规定了不可以象我国某些学者主张的那样不加区分地、在一切场合全面排除侵害知识产权的无过错责任。
三、我国现有的立法及司法应如何对待这一问题
在我国《民法通则》制定时,立法者们也许如《法国民法典》的立法者那样,尚未过细地考虑知识产权受侵害的特殊情况。但他们在起草法律的行文上还是慎重的,并不象后人解释时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排除了在知识产权(或其中的专门部分如版权)领域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可能性。因为该法第106条明文指出:“没有过错, 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里并没有讲:“仅仅本法规定了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无过错方才承担。”可以说,这项条款的文字表达避免了立法时的“因疏而漏”,是一种“疏而不漏”的行文。它给已有的,尤其是日后的特别法解释性地补充基本法留下了余地。
但又正是由于这一条的明文存在,我们就不能象前文讲到的德国专利法或法国版权法一样,在现行法中对无过错责任作任何“推论”。而必须由特别法明白无误地规定“虽无过错,也须承担民事责任”才行。现行的我国知识产权法中,不存在这种明确规定。
不过,现行专利法中有一款,如果不从它倒推出无过错责任或“准无过错责任”,则这一款就显得极不合理、也无必要。这就是第62条第2款, 该款规定:“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的”,不视为侵权。
按照对我国一切知识产权法本来就全面适用过错责任的理解,这一款至少有两点不通:
第一,如果制造或进口“不知”是未经许可的专利产品(且又无“应知”),不应视为侵权。为何法中仅仅提到了对“使用”与“销售”免责?
第二,按照本已全面适用于专利法的过错责任,这一款即“专利权人制造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制造的专利产品售出后,使用或者销售该产品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写与不写,有什么意义?
现行商标法第38条第2款也有类似的规定。
如果能象德国、法国法律那样反推,即把我国专利法、商标法的这两处特别指出的“不知者免责”,解释为“在其他情况下(例如侵害制造权、进口权等等),虽不知亦不免责”,就比较顺理成章了。这种解释的结果即“准无过错责任”(因为其未提“过失”这一面)。至于我国的《商标法实施细则》就明白无误地在第41条(1)、(3)两款中规定了仅“明知、应知”,方才构成侵权。如果不能依此反推其他款所指的行为,均属无过错责任,那么这两款更是完全失去了意义。
本来,可以从我国知识产权法作为一国统一的法律体系,专利法中仅有一款、商标法中仅有一款明文规定了不知者免责,商标法细则仅有两款规定了过错责任,推断在著作权法中的一切情况下及专利、商标法的其他情况下,不知者均不免责。可惜前面引述的《民法通则》的那段行文,似乎又排除了这种解释。当然,即使《民法通则》允许这种反推,反推的结果依旧是不完整、不尽合理的无过错责任原则。
较可取的作法是,在修订现有知识产权法时,全面考虑知识产权侵权的特点、平衡各方的利益和执法实践中的可能性,参考国外已有的成例,分别直接侵权、共同侵权、间接侵权不同情况,规定无过错责任及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场合,而不是“一刀切”地否认前者或后者。至少,较有代表性的外国知识产权法(尤其是版权法)中完全否定适用无过错原则的例子,是极少见的。在知识产权特别法修订并明确无过错责任的适用之前,执法机关对“无过错”应作严格解释。例如:出版单位超专业范围出书而未能查明有关作品属他人有版权作品,即应属过失;未超范围而未能在本专业中认出已出版之他人有版权作品,且在专业领域有较大影响,也应属过失,等等。而不能仅以其同作品提供者之间的担保合同,及“适当查询”的证明即确认“无过错”。唯此庶几弥补我国知识产权法之不足。当然, 最可取的路子, 仍是以多数外国法的成例及Trips 的要求为参考,制定出在适当场合,在知识产权领域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明文。
注释:
〔1〕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 资本主义前的简单商品生产的罗马法,就已经包含了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69页。
〔2〕 亦即我国一些学者常沿用的“瑕疵担保”。 我感到沿用这一既定术语,不能反映某些不侵权担保的实际内容。特别是经常引辞典来说明法学术语的同仁,对“瑕疵”一词也应查一下《现代汉语辞典》或其它的辞典。目前国内并不少见的全文抄袭他人的侵权作品,决不仅是“瑕疵”而已。
〔3〕 见《著作权》1996年第4期,第10页。
〔4〕 同上。
〔5〕 该法中所说的“严格”责任, 正是我们要讨论的“无过错”责任。这二者并无区别。在美国法中,严格责任也与无过错责任完全等同。可参看美国的Black's Law Dictionary 中“Strict Liability”词条。只是在英国,其刑法中严格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等同;民法中二者却有细微区别。可参看英国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 中“Strict Liability”词条。本文将在等同的含义下使用这两个术语。
〔6〕 见《著作权》1996年第4期,第14页注〔1〕、注〔2〕。
〔7〕 见M.Nimmer与Paul Geller 主编《国际版权法》, 美国Matthew Bender 出版社1996年版,德国篇第116页。
〔8〕 见Compare Court of Cassation,1960年10月8日,1961年“Dirittodi Autore”,第223页。 意大利学者意见转引自《国际版权法》,意大利篇第73页。
〔9〕 参见魏启学译日本《著作权法五十讲》, 中国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342页。
〔10〕 日本有斐阁1994年日文版,第152—153页。
〔11〕 见(1866)L.R.1 EX.第161页,(1868)L.R.3H.L.第330页。
〔12〕 见Wigmore1893年发表在《哈佛大学评论》(Harv.L. Rer.)第7期,第315页上的文章“Responsibility for Tortious Acts”。
〔13〕 见W.R.Cornish 著《知识产权——版权、专利、商标与有关权》,Sweet Maxwell 出版社1982年版、1989年版及1996年版中的第1部分第2章“The Enforcement of Rights”。
〔14〕 见Consolidated Co.V.Curtis一案,载(1892)1.Q.B.第495页。
〔15〕 见Cmnd8746(1953),Civil Liability for Animals.
〔16〕 见英国法律委员会1967年工作文件第13号(H.M.S.O1967)。
〔17〕 参看“Clerk与Lindsell论侵权法”,英国Sweet Maxwell出版社,自1889年第1版至1980年第15版。
〔18〕 见Infabrics V.Jaytex(1978)F.S.R.第451页。
〔19〕 见Cornish著《知识产权——专利、商标、 版权与有关权》,英国Sweet Maxwell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页。
〔20〕 见Sam Ricketson 著《知识产权法》, 澳大利亚Butterworths 出版社1984年版,第297页。
〔21〕 在加拿大1990年前后的几个判例中,都明确了认定侵犯版权时,有无过错均不考虑(is irrelevant)。见aff,d(1990)72 D.L.R(4th)第97页。
〔22〕 该款规定:“如果被告在侵权之时不知、也无正常理由应知有关被侵专利确系专利”,则可以不负损害赔偿责任,但须负其他侵权责任。
〔23〕 见《绿皮书》第65页,《白皮书》第109—118页。同时参看美国版权局长Peters1995年11月及1996年2 月在美国国会对此的解释。
〔24〕 见Copyright,Patent,Trademark and Related State Doctrines,美国The Foundation Press 出版社1981年版,第852页。
〔25〕 《国际版权法》,美国篇第165—166页。
〔26〕 见Sega Enterprises Ltd.V.MAPHIA,857F.Supp,679( N.D.Cal.1994).
〔27〕 Trips第37条,第39条注〔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