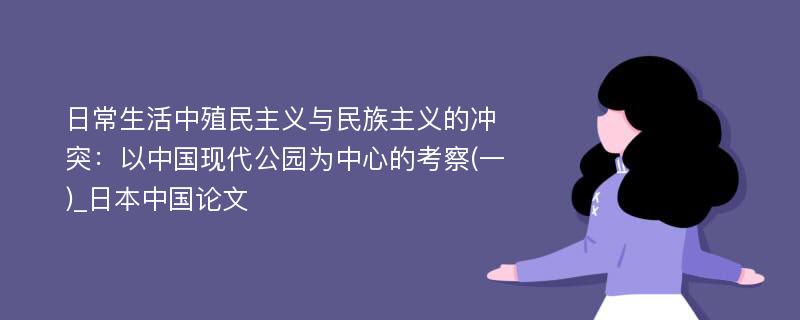
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殖民主义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日常生活中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常生活史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主题,因为它与普通大众的历史关系密切,而大众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主导力量,所以,关注大众生活史的研究更能从深隐层面揭示政治势力的实际影响。西方殖民势力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远不止于传统近代史研究所关注的主权、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它已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为,“殖民主义体系的运作,首先是外在的宰制,即军事侵略造成的征服与割地,但在完成征服以后,要完成全面稳定的宰制,必须要制造殖民地原住民的一种仰赖情结。这个仰赖情结,包括了经济、技术的仰赖和文化的仰赖,亦即所谓经济和文化的附庸。”[1](p.364)殖民主义在日常生活层面的影响对于大众而言更实际、更真切,也更容易形成切实的体验与反弹,从而建构起全民族的历史记忆,对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公共空间研究成为近十年来的新热点,近代公园问题也逐步引起学者的关注。史明正的《从御花园到大众公园:20世纪初期北京城区空间的变迁》和熊月之的《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较早开始研究公园与城市空间及公共空间发展的问题,以后陆续有学者撰文论述广州、成都公园的兴起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公园里的社会冲突。(注:参见Mingzhen Shi,From Imperial Gardens to Public Parks: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Modern China,Vol.24,№3,1998;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陈晶晶:《近代广州城市活动的公共场所——公园》,《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0年第3期;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城市史研究》第19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德英:《公园里的社会冲突——以近代成都城市公园为例》,《史林》2003年第1期。)研究者将过去学界所忽略的公园这一“场所”与公共空间联系起来,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史中现代性研究的深化。
实际上,公园不仅仅与公共空间有关,它还与人们日常生活、观念心态联系紧密,它曾经是殖民主义向中国渗透的重要象征与渠道,对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产生过强大的冲击并形成深刻的民族集体记忆,因而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但在这方面仅有《浅析中国近代租界花园——以津、沪两地为例》一文对租界花园的格局及园林小品进行了简要分析,(注:参见杨乐等:《浅析中国近代租界花园——以津、沪两地为例》,《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目前尚未有深入研究。近代租界公园不准华人入内而引发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曾引起学界热烈讨论,但学者们主要围绕外滩公园门口污辱中国人的木牌是否真实存在而展开,(注:参见薛理勇:《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世纪》1994年第2期;马福龙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上海党史与党建》1994年第3期;张铨:《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史林》1994年第4期;《中国人民被污辱的史实不得抹煞曲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史实综录》,《新文化史料》1994年第6期。)对于其作为民族集体记忆的意义却未能予以充分关注。因此,本文将全面考察近代西式公园的引入与华人公园的发展,透视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撞击及中国民族国家通过公园建设在日常生活层面的民族主义建构。
一、租界公园的殖民主义空间复制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殖民势力陆续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等地建立租界、居留地、租借地及附属地,并将西方市政建设及生活方式引入中国,公园就是其中的代表。工业化后,英法等国为缓解工业化大生产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压力,开始通过建造城市公园等绿色景观系统来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公园是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后的产物,最早出现于租界,而后影响至华界。目前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公园是由英租界工部局于1868年8月在上海建成开放的外滩公园,当时称“公家花园”。[2](p.473)[3](p.249)又据闵杰考证,自1903年留日学生在《浙江潮》上介绍日本公园后,次年,《大公报》在报道南京建公园时就全部用“公园”一词。1907年后因官方提倡并出资,各地渐兴修建公园之风,“公园”一词逐步取代“公家花园”而成为专用名词。(注:参见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上海是近代中国公园的发源地,大量外侨随着殖民势力的侵入而移居上海,建立起繁华的十里洋场,正如时人《租界》诗所云:“北邻一片辟蒿莱,百万金钱海漾来。尽把山丘作华屋,明明蜃市幻楼台。”[4](p.5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国花园”进入上海人的生活空间。英国人最早建立的外滩公园位于“英界虹口大桥沿江一带”,每天“西人挚眷携童游赏”。[5](p.5)继外滩公园之后,外国人在沪所建公园逐渐增至10多个。(注:据《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473—485页),吴馨、姚文楠修纂:《民国上海县志》卷二《政治下·名迹》,屠诗聘主编:《上海市大观》(中国图书杂志公司1948年版)整理。)1860年,天津辟为通商口岸,先后有9个国家在天津设立租界,面积达1 500多公顷。1880—1938年,英、法、日、德、意、俄等租界共修建了10座具有各国象征与文化特色的公园。(注:参见石小川:《天津指南》卷五《食宿游览》,天津文明书局1911年版,第7页;崔世昌:《租界里的公园》,《天津租界谈往》,《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97年第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天津通志·城乡建设志》,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8—541页。)关于公园统计资料保存完整的还有青岛,青岛在历史上曾为德国人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又从德国人手中夺得青岛,因此,青岛尽管城市不大,但近代西式公园数目较多,据《胶澳志》统计达15个之多。[6]上海、天津与青岛三地的近代公园见下表(未标注具体修建年代者,待考):
表1 上海、天津、青岛近代公园一览
上海公园
天津公园青岛公园
外滩公园(1868)、昆山花园(1895)、虹口 海大道花园(1880)、维多利亚公园旭公园、若鹤公园、新町公园、深山公园、
公园(1905)、法国公园(1908)、德国公园、
(1887)、德国公园(1895)、皇后公园、俄国千叶公园、官邸公园、天后公园、司令部
汇山公园(1911)、兆丰公园(1914)司德兰 花园(1900年后)、大和公园(1906)、法国 前公园、曙滨公园、万年町园、治德町园、
园(1918)、新康花园、宝昌公园(1920)、胶
公园(1917)、意国花园(1924)、久布利公 山东町园、大村町园、青岛神社、松板公
州公园(1935)、贝当公园(1935) 园(1937) 园
外国势力侵华后力图将其引以为傲的公园等所谓“文明”的艺术文化及生活方式移植到中国,因此,只要有外国移民定居之处便会有近代公园出现。俄国人、日本人先后在东北的大连、哈尔滨、沈阳等地建立起大批公园,如大连的西公园、北公园、电气公园,旅顺的植物园、动物园,哈尔滨的公立公园、极乐村,丹东的镇江山公园。(注:参见萧山、喻守真等编:《全国都会商埠旅行指南》上卷,中华书局1926年版,第124页;大连市中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山区志》,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李元奇:《大连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照片及说明:《旅顺口区志》编纂委员会:《旅顺口区志》,大连出版社1999年版,第686页;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外事对外经济贸易旅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1页; 丹东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丹东市志》(第二册),1996年版,第135—136页。)南满铁道会社在其铁路附属地如沈阳、辽阳、铁岭、长春各地,建立各种市政设施,“上下水道、公园、市场、学校、医院、墓地”等一应俱全。[7](p178)此外,外国人还在汉口等地建有各类公园。
著名社会学家福柯对空间特别关注,指出“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8](pp.13—14)殖民主义势力正是通过空间向中国渗透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专家亨利·列斐伏尔进一步指出:“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9](p.62)公园作为一种人造的空间同样体现历史与自然元素的模塑,折射出西方工业化后人们寻求新型娱乐休闲空间形式的特性。但由于近代公园是随殖民主义进入中国的,因此,其独特的空间建构与中国传统园林有着本质区别,体现出中西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冲突。
西式公园的重要属性之一是公共性、公众性与休闲性,因而一般占地面积较大,在空间布局上强调视野开阔、舒适明朗,普遍以草地、绿树、花卉、喷泉及西式凉亭为主要景观,迥异于狭小、精巧的中国官家或私家园林。最早的上海“公家花园……细草如茵,落花成阵。芊绵葱翠,一望无垠”,[10](p.133)且“遍地栽花,随处设座”,“中央为喷水池及音乐亭”,而法国公园“园址甚广,境颇幽静”。[11]天津最早的法租界海大道花园“地广百数十亩,路径曲折,遍植花木,小桥流水,绿柳浓荫”。[12](pp.538—539)这些特征是与西方工业化后空间的发展及人们在被制约后寻求放松、休闲等需求相联系的,所以,一般公园内还建有球场、运动场、游泳池、动物园,天津皇后公园就建有游泳池和儿童运动场,大和公园亦设儿童运动场并饲养小动物。其次,公园布局都带有其设计建造者本国的造园风格,如天津意国公园呈圆形,总体布局为规则式,中心建罗马式凉亭,园内有喷水池及花坛,花繁树茂。法国公园同样为圆形,空间布局则为典型的法国规则式,小区由同心圆与辐射状道路分割,设四座园门。园中心建西式八角石亭,亭四周草坪环抱,南端竖和平女神铜像一尊,右手持剑,剑尖向下,左手握鞘。而大和公园则是典型的日本园林风格。[12](p.540)日本在长春建的西公园从总体格局到建筑式样均为日本风格,园内供游人坐赏湖景的凉亭就是日本式方亭。[13]当然,也有极个别的外人所建公园具有中国园林风格,如上海“丽虹园在佘山路,洋商利得利建。亭台楼阁,悉仿中国古制”,[11]但绝大多数公园均按其本国风格建造。不仅如此,有的公园甚至在植物种植上也体现出象征意义。最初均从殖民母国引进花草,如最早的公家花园的“奇花异卉,大都来自欧洲。紫姹红嫣,名色各异。不特目所未见,耳所未闻”。[10](p.133)日本更为典型,将其国花——樱花移植到中国的公园。青岛旭公园(后改为第一公园)有一条通往纪念日本阵亡士兵“忠魂碑”的路,两侧遍栽樱花,因此,樱花成为该公园的主要植物,也成为该公园的象征,当时的青岛人称其为樱花公园。[14]丹东镇江山公园也栽种着从日本奈良吉野山寄来的樱花树木1000株。[15](p.136)这样的空间布局与植物种植显然是要将其母国的公园移植过来,并复制其母国文化以达到空间的殖民主义化。
在公园的空间构成中,除布局与植物外,建筑也具有重要地位,甚至是构成公园空间的核心。福柯曾说,“空间位置,特别是建筑设计,在一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建筑……变成了为达成经济—政治目标所使用的空间布署问题’。”[16](p.30)殖民者在公园中建造代表其文化意象和殖民侵略象征的建筑物,更直接地传达殖民者的政治理念,即透过这一空间炫耀其武力、种族及文明的优越感。这在最初上海的租界公园中就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而到后期日本的做法更令中国人发指。1880年英国人在外滩苏州路及外摆渡桥入口处建立纪念碑,纪念导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的英人马加礼(今译马嘉理),该碑于1907年移入外滩公园。[1](p.376)[17](p.146)天津英国公园内则建戈登堂。[18](p.257)日本在中国所建公园内修建纪念碑最多,以炫耀其战功。1906年,为纪念镇压义和团而战亡的日本官兵,日本人在天津大和公园内竖立“北清事变忠魂碑”,后增建日本神社,供奉天照大神及明治天皇之灵位,门口有日兵守卫,日人过此均虔诚敬礼,中国人则不许靠近。日本人还在春秋两季到神社祭祀,日本在津军政要人均参加仪式,极为隆重,神社成为日本推行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18](p.7)[19](p.258)[20]实际上,日本每占领一地均建神社、纳骨堂等建筑物,如大连东公园内建有“表忠碑”,纪念日俄战争在海城阵亡者,“每届四月十日,日人举行招魂大祭于此”。青岛太平山会前公园内也有日人修建的纳骨堂,奉祀青岛战役中的日本士兵遗骨。[21](p.125)日本人又在丹东镇江山公园内建“忠魂碑”、神社、八幡宫等,为日本侵略者歌功颂德。[15](p.135)到抗战时期,日本的做法进一步升级。1940年,日本在长春西公园入口处,竖立一座象征日本“皇军南进”的武人铜像——日俄战争中立有显赫功勋的儿玉源太郎大将铜像。儿玉头戴法式圆柱军帽,身着日俄战争时军服,腰佩长刀,肩披斗篷,骑马向南,并举手侧脸向东(园林正门方向)致礼。这座铜像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傲慢与蛮横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西公园也由此更名为儿玉公园。[13]抗战时期,日本人不仅在公园建立侵略者纪念物,有的甚至将整个公园改建为神社,并要求中国人表示敬意。据人们回忆,日本人在攻入广东佛山后一度进驻中山公园,并在园内修建一座“靖国神社”,供奉侵华日军的亡灵;[21]广州永汉公园则“被日本侵略者改建为供祭侵华日军亡灵的‘神社’,在里面设有‘神亭’、‘神龛’等,人人走过都要低头‘致敬’”。[23]这些建筑物显然在传达殖民主义信息,中国人对此深有感触,“帝国主义者掠人之地犹建大兵头花园,立其掠夺者之铜像以自豪”,[24]这使中国人感到耻辱与愤慨。
构成公园空间的“历史因素”,最突出体现在同一建筑物上所表达的政治内涵不断改变。1897年11月,德国侵占青岛后,为纪念其殖民主义政策的胜利而在一个小游园内建立“胜利纪念塔”。塔为六面体形,正面铜片上刻着占领青岛的德国军队首领肖像,其他几片则镌刻着占领年月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德国人手中夺取青岛,遂揭去纪念塔上的铜片,保留原塔未动,作为日本战胜德国的纪念塔。1922年,中国赎回青岛,原塔仍保留未动,只是在塔的正面镶了一块铜片,上书“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接收青岛纪念”,作为中国接收纪念塔。1937年冬,日本再占青岛,此塔再度更名为“东亚胜利纪念塔”。[25]这一小游园充分反映了殖民主义者在青岛统治的历史。
公园空间的构成除园内空间布置与建筑外,公园门口的布置与近旁的建筑物同样对于人们的影响甚大。1896年德国炮舰伊尔底斯号在暴风雨中沉没于山东海面,死难者77人。上海德侨得怡和洋行资助,在外滩公园旁建立纪念碑。[2](p.377)另外,外滩公园对面矗立着纪念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阵亡的5名英国士兵的红石纪念碑,碑身为英国运来的花岗岩十字架,上刻“英领署地上十字纪念碑”。[2](p.376)这些建筑物在空间上已经与外滩公园浑然一体,在视觉与精神上共同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
殖民主义在公园中的渗透不仅表现在空间上,同时也表现在时间上,即把特定的日期作为公园开放日,或在公园中举行殖民者的纪念日仪式。如天津维多利亚花园,又名“英国花园”,是英租界的第一个公园,是工部局专门为庆祝英国维多利亚女皇诞辰而投资修建的,其正式开放日就定于英皇诞辰50周年的1887年6月21日,[20]以此来宣扬维多利亚时代的殖民主义精神。无独有偶,在沪日本人则于每年4月29日“天长节”(天皇生日)举行庆祝仪式,如1932年的这一天,日人在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祝捷”阅兵典礼,由日军司令部至公园,沿途警戒,园内“高搭彩牌,小旗招展”,全体日军及日侨齐唱日本国歌《君之代》,后因朝鲜革命党志士在观礼台下所埋炸弹爆炸而中止。[26]
笔者认为建筑界学者所提出的“空间殖民主义”概念对于理解近代中国的租界公园极有参考价值。所谓空间殖民主义实际上是对过去殖民主义概念只注重军事、主权、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补充,强调空间为列强从事其侵略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基础。因此,空间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者奴役和剥削他国政策的一种延续和文化表现,其媒介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空间环境。空间殖民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在他人之乡,按自己的生活习性、文化偏爱去构造一个为自己所喜闻乐见的空间环境,以殖民空间移植来满足并宣扬自己的生活方式,去表现自己的文化优越感,无视他人、他乡的社会及生态环境,从视觉到物质感受上嘲弄地方文化,奴化他国民众的心身。(注:参见吴家骅:《论“空间殖民主义”》,《建筑学报》1995年第1期。)就空间本身而言,其所传输的象征意义与文化、政治内涵对于人们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涵化作用,而纪念性空间更具教育功能。因此,近代殖民势力进入中国后,以空间作为权力意志表征,完全按照他们的审美情趣、欣赏习惯对各地进行市政规划,建立起一座座带有其文化艺术风格的公园,不仅将一整套殖民主义空间复制移入中国,渗透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在精神上奴化、戕害中国人。公园作为空间殖民主义与文化殖民主义的产物,比政治、经济殖民主义更具隐蔽性,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及观念心态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
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集体记忆
租界公园不仅成为殖民主义空间的物化载体,而且因华人不能入园问题而成为歧视华人的象征符号,构成对华人精神的严重戕害,使中国人对殖民主义空间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反弹心理与深刻的民族集体记忆。
这一情境在上海最为典型,上海最早的公家花园开始并未公开禁止华人入园,只是授令巡捕,禁止下层华人入内,由于“门禁甚严,故华人鲜有问津者”,[10](p.133)但不到五年,英人即以华人不守规则为由禁止华人入内。后工部局明确告示的公家花园《游览须知》规定:“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小孩之车,须遵路旁而行;毋许拆毁鸟巢,损坏花木;小孩尤宜加意管束;乐亭栏杆内,游人不得擅入;华人无西人同行,不得入内。”[27]《申报》曾刊登外滩公园照片,标题为《不准华人入内之上海公园》。[28]法租界的顾家宅公园(即法国公园)于1909年6月落成,“当时该公园章程,第一条第一项便明白规定,不许中国人入内,但是照顾外国小孩的阿妈,加套口罩为条件。”[29]
殖民者的做法引起中国人的强烈抗议,上海要求公园对华人开放的呼声一直不断。早在1878年《申报》就刊登《请弛园禁》,认为“该花园创建之时,皆动用工部局所捐之银。是银也,固中西人所积日累月而签聚者也,今乃禁华人而不令一游乎?”[30]此后,华人继续据理力争,1885年11月,租界著名华商陈咏南、吴虹玉、唐廷枢等8人联名致函工部局,再度要求准许华人入园游观。 此举立即得到华人舆论的积极响应,《申报》予以支持,并批评工部局的禁例,指出公园“造之者西人,捐款则大半出自华人”,而且名称是“公家花园”,就应该“以见其大公无私之意”,然而,实际上“仍系私家。西人得以入园中游目骋怀,往来不禁,虽日本人、高丽人亦皆以公诸同好,听其嬉游,而独于华人则严其厉禁……此事似于公家两字显有矛盾”。而且,“以工部局所捐之款计之,华人之捐多于西人者几何?则是此园而例以西法,华人断不至被阻。且彼日本之人其捐尤少于西人,高丽之人则竟一无所捐,而何以颠倒若斯乎?”[31]但工部局对于华人的要求仍然置之不理。1889年,唐茂枝、吴虹玉等又呈道宪向英国领事交涉,结果,工部局允发给执照,执照不收费,但每张只能用一星期,且为数甚少,因此,问题仍然存在。
由于园小人多,1890年工部局又决定另建一公园。所选苏州河浜的涨滩,上海道声明“属中国官地,不能由外人任意处置”,工部局遂决定“对中外一律公开”,定名为“新公园”,次年改名“华人公园”,但新花园占地面积小,各项设施亦远逊于公家花园,“布置殊草草”。[2](p.474)[11]另据《上海闲话》载,“公园建筑,远不逮西公园”。[32](p.18)虽然华人有了专门的公园,但仅一个公园无法满足广大市民生活的需要,由此,为争取所有公园对华人开放的努力一直进行着,甚至被称作“公园运动”。[33]
1926年夏,上海“天时奇热,为十年来所罕见,时疫猖獗,死亡相继,而沪地空气不佳,游散无地,亦为重要原因”,因此,华人急切盼望公园对其开放,但工部局仍然只“允以黄浦滩草地开放于华人”,其他公园一律不开放。[34]《申报》在1926年8月18日详细记述了华人游公园纳凉时被西人巡捕迫令退出之事,[35]引起华人普遍不满。经过华人努力,工部局公园委员会中有3名委员由总商会推选华人出任,于是,华人纷纷要求委员会“力争华人入园免去凭证”,[36]公园委员会亦主张“中外市民应平等享受”。[37]但是,这个公园运动后来又有所消退。所以,1927年,郑振铎呼吁:“在去年,我们曾有一度热烈的表示,而至今却又销声匿影了。难道是因为冬天到了,公园用不到了,所以又沉寂下去了么?不,不,我们要热烈地持久地举行着‘公园运动’!”因为“主人翁是被放逐出自己的公园之外了!……难道我们竟袖手地听凭那些最少数的客民们紧握了我们的咽喉而要将我们窒息死了么?不,不,我们要求呼吸权!我们要求生存权!”而且“‘公园运动’表面上看来,也许比之最根本的办法,‘收回租界’,是不重要些。然而区区公园运动而尚不能成功,则还谈什么收回租界!”[33]公园问题已不仅仅是华人的地位问题,也是中国近代租界问题、华人生存与国家主权的问题。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1928年纳税外人年会通过《公园开放案》。同年6月1日,外滩、虹口、兆丰3公园对华人开放,同时开始售票制度:年券售价1元,零券每次铜元10枚。华人公园仍旧无条件开放,[38][39]但是,法国公园等仍然禁止华人入内。
上海关于公园问题的争议最为激烈,公园俨然成为殖民主义的象征物,提到公园必然联想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已经成为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对于中国人而言透心彻骨。关于外滩公园门前是否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直至几年前学术界仍在争论不休。著名学者熊月之等认为,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就是由公家花园《游览须知》的规定衍生出来的。[40](p.578)美国学者也著文讨论,指出外滩公园门前没有这样的木牌。[41]争论这一牌子是否存在对于追求历史真实性的学者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为什么会形成如此深刻的历史记忆,而且扩展为全民族的集体记忆?因为公园的确是不准华人进入,工部局的档案及公家花园《游览须知》上都曾有过华人不得入内、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的规定,而且华人为了争取同等的入园权利奋斗了半个世纪。可以想见,中国人不可能再将公园视为简单的游览空间场所,它完全成为西方列强进行殖民主义渗透的空间,是文化殖民主义影响中国人日常生活最鲜明的象征。于是,近代中国人对于公园有着难以言表的隐痛,许多人在著作、文章、 通信中都谈到公园问题。早在1907年,李维清在《上海乡土志》中就写道:“公花园……东西各国之人皆可游玩,即印度亡国之民、洋人豢养之犬,尚得出入自如,独禁华人入内,是彼之蔑视华人,且奴隶犬马之不若矣。喧宾夺主,实堪浩叹!可知当今之世,惟有强权足恃而已。我侪宜若何努力,以洗刷奇耻耶!”[42]对殖民主义的反弹情绪跃然纸上。 郭沫若在1923年愤然写道:“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43]同年,蔡和森发表《被外国帝国主义宰割八十年的上海》,再度质询“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那一点不是华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44]对于直接提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文章更多,廖沫沙曾撰文《中国人与狗》,谈到在公园门口“那时读书的中国人看见了,真是‘人生识字忧患始’,免不了感到侮辱,愤慨万分”。[45]因此,中国人对于上海公园均印象深刻,“上海的公园对于我的印象是不好的,那里边所有的人物,我都不欢喜;特别多的是洋太太,洋太太的孩子,领洋孩子的江北娘姨。好一点的地方和好一点的时间,全被他们占有了”。[46](p.367)有的人虽多次游览租界公园,但都是“红着脸去”的。[47]曹聚仁虽然有朋友邀请同游法国公园,但他却断然拒绝,“一则我是一直穿布长衫,犯不着去‘丢脸’;二则,我们那时‘反帝’的狂热,使我不愿低头。直到公园开放了,我才进入那里”。[48](p.216)所以,华人去租界公园游玩的并不多,正如1929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所记述的:“到公园去,全是小洋囡囡的天下,白发黄毛。”[49](p.72)也许相当多的华人没有用文本书写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却用实际行动表达着自己的思想。
租界公园给予中国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殖民主义禁区与象征,华人不能入公园这一事实真正让中国人认识到殖民主义政策的切实存在,华人将这一情绪升华至对殖民主义的认识。著名文人陈西莹对上海的记忆是这样的:“上海完全是外国人的上海,不久中国就会不知不觉地变成外国人的中国。……十年来添许许多多美丽的花园和舒服的别墅,里面住的又都是黄头发、蓝眼睛的人。……总而言之,他们西洋人是贵族,中国人是他们的奴隶;他们西洋人是享乐者,中国人是供给他们的生产者。”[50](p.94)方志敏在其所著《可爱的中国》一书中写道,“‘华人与狗不准进园’……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在中国的上海地方让他们造公园来,反而禁止华人入园,反而将华人与狗并列。这样无理的侮辱华人,岂是所谓‘文明国’的人们所应做出来的吗?华人在这世界上还有立足的余地吗?还能生存吗?”[51](p.8)此外,孙中山等政治家、文人都曾在文章中提到这一情结。(注:参见孙中山:《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1924年4月24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还有的文人因公园问题而上升至对整个上海精神与文化的批判,“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52](p.47)一般文人则用竹枝词的形式表达着这一历史记忆:“公园设备固然新,不许华人去问津。世界有何公理在,何称夺主是喧宾”;“英人游憩有家园,不许华人闯入门。绿树荫中工设座,洋婆间跳挈儿孙”;“狗与华人禁令苛,公园感想旧山河。而今各处都开放,又见倭兵列队过”。[53](pp.496—497)“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仅是中国人处处受奴役受欺凌的一个缩影,殖民主义奴役下的中国人只能是奴隶。著名诗人蒋光慈在《哀中国》中感叹道:“法国花园不是中国人的土地么?可是不准穿中服的人们游逛。哎哟,中国人是奴隶啊!……我的悲哀的中国啊!你几时才跳出这黑暗之深渊?”[54](pp.69—70)可见,这一深刻的记忆逐渐由个人的愤恨而上升为对国家与民族的忧患。
在上海以外的其他租界、租借地及附属地的西式公园也禁止华人入内。日本人内藤湖南1899年访问天津紫竹林租界公园时曾看到,“不能进入此园者有二,一为华人,另一为狗”。[55](p.81)天津英国公园至1930年仍规定“华人非与洋人相识者不得入之”。[18](pp.257—258)更有甚者,武汉华人若入简易公园游玩将遭拘罚。据曾做过巡捕的李绍依回忆,汉口英租界捕房依据《工部局市政章程警察附则》履行职责,其中第20条规定:“华人擅入江边草坪(坪内设有靠椅,从江汉关达界限路,接通俄、法、德、日租界,有似简易公园,专为洋人散步游览之区,华人不得越雷池一步)者,拘罚。”[56]从当时的竹枝词中也可见到汉口民间话语中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记忆,“鸿沟界限任安排,划出华洋两便街。莫向雷池轻越步,须防巡捕捉官差”。[57](p.198)有的公园虽然没有禁止华人入园,但在公园内专门划定华人游览区,如天津义国(意大利)公园“东有中国儿童之游戏场及避雨亭,西有西童游戏场及小花亭”,[18](pp.257—258)华人同样不能越雷池一步。不仅公园的规则严重歧视华人,而且有的游览场所内,华人还要受到侮辱。如日本满铁会社在奉天(今沈阳)建的附属地公园,园内绿树成荫,但“华人至其地者,多受日人侮弄,故有识者多不践足其间”。[21](p.76)
中国人到公园要受到如此多的精神伤害,自然而然会产生强烈的反弹心理与对殖民主义的深刻记忆,当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言说进入知识精英所主导的公共话语时,遂构成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而且这种记忆会转化为民族主义意识,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所言,“只要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历史事实渗透进入了这种记忆,就会被转译成一种教义、一种观念,或一个符号,并获得一种意义,成为社会观念系统中的一个要素。”[57](p.312)历史证明,公园问题所形成的社会记忆已经转化为民族主义情绪与实践,如1925年五卅运动时,上海东吴大学法科学生就在停课宣言中将公园问题与民族主义运动联系起来,“上海公共租界华人纳税据金额十之九,而工部局董事反不得参加;公园及其他娱乐场所,华人不能入内”,[58]因而,中国人感到生活在殖民主义空间时无处不受压迫,“直接伏处在洋人势力之下,往往在一个极普通的去处,可以使你感觉到一种不安”,但也因此让人们感到“国,是不可不爱的”。[59](p.28)毛泽东甚至将公园问题纳入民族战争领域来探讨:“上海有所谓‘外国火腿’,就是外国人踢了一脚,算作给一个‘火腿’。到上海的人,还看见过有的公园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民族战争就反对这些东西。外国民族压迫中国民族是不行的,我们要独立。”[60](pp.155—156)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愤恨不是少数人的感受, 而是全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已经上升为中华民族强烈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精神,这是公园问题上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撞击的结果。
标签:日本中国论文; 天津历史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公园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青岛生活论文; 申报论文; 工部局论文; 后殖民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