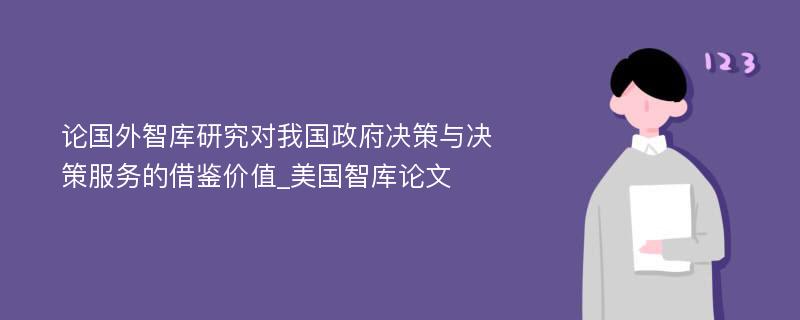
论国外智库的中国研究对我国政府决策以及决策服务的参考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国外论文,价值论文,我国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国外政策研究咨询机构有关中国研究的规模增大,人员增多,成果与日俱增。这些研究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和中国问题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各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中国的世界形象。国外的中国研究主题广泛,有政治经济议题,也有社会民生议题;既有宏观战略性研究,也有微观操作层分析。其研究成果借助互联网得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在海量的互联网信息资源中,国外中国研究信息和成果具备知识性、可靠性、及时性、针对性等高价值信息的特点。
国外政策研究咨询机构依据机构性质、运作方式和研究目的的不同大致可划分为三类。(1)专业智库。其组织宗旨和目标是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特点是媒体曝光率高、政策和舆论影响力大。其研究成果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媒体平台广泛传播。(2)政府和军队内部的行政或情报部门,其工作主要是进行特定情报的收集和研究。此类机构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也几乎不公开研究成果。(3)大学里的研究机构。具体到中国研究又可分为两类,一是传统的汉学研究机构,二是当代中国研究机构。近年这两类机构的研究内容有交叉和融合的发展趋势,此不赘述。大学研究机构的特点是重学术、轻实用,不以对政府短期决策施加影响为目的。从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实用性、影响力和可获取性考虑,本文着重分析第一类机构,即国外专业智库的中国研究对我国政府决策以及决策服务的参考价值。
1 国外智库中国研究具有全球视野和比较客观、严谨的研究态度
近年越来越多的智库正在逐渐突破立足于某国的立场,把发展目标定位在服务全球。他们研究并试图解决那些影响地球和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如环境、人口、气候、能源等,即使在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等传统智库研究领域,在顾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时,也日益关注对全球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影响。
在研究立场和研究内容具有全球化的特点之外,智库发展的全球站位思想还表现在研究阵地的全球化。有百年历史的美国知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率先提出并示范了一个全新的理念:在当今世界,一个肩负着为全球安全、稳定和繁荣做出贡献的重要使命的智库,应该在世界范围内设立永久性的分支机构,以跨国的视角开展其核心工作[1]。目前,卡内基已分别在华盛顿、莫斯科、北京、贝鲁特和布鲁塞尔设立办公机构,针对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国外智库发展的全球站位思想在中国研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很多国际知名智库在中国建立了研究基地。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2002年在上海设立了野村综研(上海)咨询有限公司,2005年设立了北京事务所,2007年与清华大学共同创办了清华大学·野村综研中国研究中心。2004年卡内基首次在北京设立办公室,2010年与清华大学合作创立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连续多年占据《全球智库评估报告》(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综合排名第一的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06年在华盛顿设立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同年在清华大学设立北京办事处,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德国两家知名的基金会智库都在中国设立了办公室:阿登纳基金会(Konrad-Adenauer-Stiftung)中国办公室成立的宗旨是支持中国的改革进程,特别是经济转轨和法治国家改革领域的改革进程;支持将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关系的网络之中[2]。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 Boll Stiftung),则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合作,成立了伯尔基金会—中国民促会项目合作办公室,在环境与气候、经济与社会变革、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等方面与中国的民间团体、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一起开展研究,积极促进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增进中国和德国之间的理解[3]。
国外智库在中国开展中国研究的优势,除了保持和加强研究的国际化视野之外,还包括:(1)更加近距离地观察和感受中国的变化,提高研究效率和研究质量;(2)便于同中国本土的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与研究合作;(3)有机会与中国决策者直接沟通,获取第一手的信息情报,建立“二轨外交”沟通渠道;(4)可以扩大这些智库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影响力。
目前把中国研究的阵地转移到中国的还只是少数资金雄厚的大型国外智库,更多的国外智库还是立足本国进行中国研究,但他们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通过研究人员互访、组织国际会议、开展项目合作等方式积极寻求与中国政府、学术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接触与交流。随着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日趋深入,国外智库对中国来说已不仅仅是观察者的角色,而是逐渐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参与者。
在全球站位思想指导下,国外智库的中国研究日渐脱离了西方中心观或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意识,开始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给予恰当的关注。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管、资深研究员李成所说:“我们的研究必须脱离美中关系的局限,要有全球的关怀和视野,为全球服务。”[4]正是这种全球关怀和视野使国外智库的中国研究成为对我国政府决策具有参考价值的关键因素。
2 国外智库中国研究的选题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和前瞻性的特点
国外智库研究工作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前瞻性的特点在中国研究上表现得非常充分。下面以近期国外智库在外交关系领域的中国研究情况为证。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是由美国联邦基金支持的服务于美国海军和其他国防机构的智库,素有“海军的兰德公司”之称,2012年是该中心成立70周年。该中心有20余人的中国研究团队,以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新角色为研究主题,为美国军队和政府提供中国战略和中国安全事务方面的分析报告和政策建议。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重返东南亚,越南、菲律宾等国也企图拖美国介入南海问题。海军分析中心2012年3月份发布了研究报告《美越关系中的中国因素》(The China Factor in U.S.-Vietnam Relations)[5]。报告指出,虽然美越两国已经开始寻求共同利益,但中国方面的行动将继续影响美越之间合作发展的进程和范围,特别是在安全事务方面,美越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是美越两国都想尽量避免破坏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既想遏制中国在亚洲的势力发展,又不想破坏美中关系,因此必然会小心翼翼地处理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中俄关系是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俄罗斯而言同样如此。2012年普京再度当选俄罗斯总统伊始就来华访问。6月6日,普京访华第二天,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Dmitri Trenin发表专栏文章《灵活的合作关系》(Flexible Relationship of Cooperation)[6]。文章指出,普京已经意识到当代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希望通过全面发展与欧洲、美国和亚洲的关系,最终达到全球政治格局的平衡。在经济贸易和地缘政治方面中国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俄罗斯不会做出任何破坏目前俄中两国友好关系的举动。文章最后建议,与中国建立更加灵活的关系比建立单纯的盟友关系对俄罗斯更有利。
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考验着欧中关系。2007年成立的欧盟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是第一个泛欧洲智库,致力于促进欧洲整体外交政策的建立。2012年5月该委员会发布政策简报《中国与德国:一种新型的特殊关系?》(China and Germany:A New Special Relationship?)[7]。文章指出,德国的外交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通过经济交流来引导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变革,而德国则被中国视为有助于其经济发展的国家。在中国需要技术、德国需要市场的情况下中德之间一种新型的特殊关系正在形成。作者认为中德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对整个欧洲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应该把这种关系发展为真正的欧中战略伙伴关系。
智库不仅对时政事件反应迅速,还对将要发生的事件进行前瞻性的长期的跟踪和研究。2012年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是美国国内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布鲁金斯学会早在2012年年初就设立了“Campaign 2012”研究项目。该项目计划针对国内外最紧迫的问题,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简报、评论和专家对话,为候选人和选民提供基于事实的思想观点,同时为候选各方提供讨论和辩论的平台。该研究项目设置了12个被认为是下届美国总统必须面对的国内外政策议题,包括经济增长、财政赤字、卫生保健、恐怖主义、制度改革、气候变化、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等。全球经济与中国(The Global Economy and China)是12个议题之一,对该议题的设置说明是: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美国必须面对诸如中国等新兴经济力量的竞争,未来的美国总统必须具有处理这一棘手局面的战略管理能力。在此议题下,3月16日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G.Lieberthal)与资深研究员Jonathan D.Pollack发表联合报告《建立信誉与信赖:下任总统必须处理好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Establishing Credibility and Trust:The Next President Must Manage America’s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8]。报告指出,美国自身财政状况重建的关键有赖于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建议下任总统应积极创造与中国新的领导层建立基于深度磋商和具体行动的互信的可能性。5月23日“Campaign 2012”项目主管、资深研究员Benjamin Wittes与Jonathan D.Pollack进行了一场名为“改善与中国的关系”(Improving Relations with China)的专家对话(Expert Q & A)[9],探讨下一任美国总统应怎样保持与中国政府的持久关系。
成立于1921年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作为外交领域的智库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力无与伦比。该委员会也设立了“Campaign 2012”项目,与布鲁金斯学会的项目不同,该项目专注于大选中的外交问题和候选人的外交立场,并对各位候选人的对华立场(The Candidates on U.S.Policy toward China)进行梳理和总结[10]。其中奥巴马最有力的竞争对手罗姆尼的对华态度值得关注,他认为美国在经济上应该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必须反对中国的贸易保护、违反知识产权以及操纵货币的行为,并声称将在当选总统的第一天就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他还强调美国需要加强军事霸主地位来应对中国不明意图的潜在威胁等。在2012年美国大选结果未卜的情况下,这些信息揭示出今后中美关系走向的一种可能性,也提示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的过程中对这一可能性做出应对准备。
3 国外智库中国研究人员具有较高研究水平,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力较大
智库的研究质量取决于研究人员的研究水平。智库研究人员的主体大致由两类人员构成,一是各项公共事务领域的学者专家;二是“退居二线”的政府官员。但是正如有人把智库比作“旋转门”,很多智库的研究人员其实已经模糊了上述两类人的界限,他们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穿梭,在政府、智库和大学之间流动,这种现象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博士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他的履历包括,1983-2009年任密歇根大学教授,其中1998年8月至2000年10月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局资深主任,负责制定美国的东北亚和东亚政策。2009年从密歇根大学退休后就任现职,继续活跃在政策咨询舞台。关于在布鲁金斯的工作,李侃如说,“布鲁金斯学会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严肃而认真的研究;二是坚持使这些研究产生影响。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平衡。我喜欢做研究,喜欢写书,喜欢通过研究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但我也喜欢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真实的世界产生影响。……现在我发现,布鲁金斯学会是一个真正适合我工作的地方,因为它把优质、独立和影响三者合一,而且非常认真地践行这个座右铭。”[11]
角色的转换使他们既具有专业学识,又具有实践经验;既能够有的放矢地进行公共事务和具体问题的分析,又能够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术角度,对理论问题、根源问题和长期性问题进行深思,是名副其实的沟通知识和权力的桥梁。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他们的成就决定了他们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影响力是评估智库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因此,智库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包括承接政府课题、出席听证会、发布研究报告、接受媒体访问、举办研讨会、向政府输送高级人才等来影响公众舆论与政府决策,以实现其研究价值。“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在内的美国智库对于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很难用数字来量化,我们不能自吹自擂,但我想‘旋转门’这个提法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智库的影响力,现在奥巴马总统首席亚洲顾问杰弗里·贝德正是从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出去的,而克林顿总统的首席亚洲顾问李侃如和布什总统的首席亚洲顾问韦德宁也都是我的同事。布鲁金斯学会目前已经有15名研究员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要职。”[4]
回顾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很多关键性的外交思想和政策建议都出自那些有过“旋转门”经历的中国问题专家。出生于中国上海,曾先后在美国驻港总领土馆、哥伦比亚大学、布鲁金斯学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机构供职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Doak Barnett,1921-1999),1966年3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指出,“我们对中国采取的是一种遏制与孤立的政策。在我看来,遏制的因素是必要的,在某些方面也还算是成功的,但孤立的努力是不明智的,从根本上讲也是不成功的,它无法为一种合理的长期政策提供基础。我们的政策目标不仅在于限制中国的力量,而且在于减少紧张局势,软化中国的态度,增进非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问题上的共识,并逐渐将中国纳入到更为规范的国际交往范式中。”[13]自此,“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外交思想开始深刻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直至促成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和中美建交。
曾任美国副国务卿、2012年6月30日刚刚卸任的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Robert Bruce Zoellick)宣布分别以高级研究员和客座研究员的身份加盟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美中关系方面,佐利克以提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概念而著称。他在2005年9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讲时说:“我们不仅仅考虑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打开大门,我们需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利益攸关的负责任成员”。“利益攸关方”的概念既避免了为中美关系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也回避了美国国内遏华派与接触派的争论,可以团结最大多数人的对华立场,由此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并被视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动向。佐利克任世行行长期间,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进行了大型课题研究,并于2012年2月发布了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Harmonious,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的研究报告。可以预见,佐立克加盟上述两家国际知名智库后,其对中国的关注与研究将继续在全球政策领域产生影响。
除了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外,智库中国研究的社会舆论影响力也不容忽视。特别是那些在某个专门领域对世界各国进行监测和评估的智库组织,比如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每年发布的各国政府和行政机构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行贿指数(Bribe Payers Index,BPI)、国家廉政体系测评报告(National Integrity System,NIS)、全球腐败趋势测评(GCB)。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和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发布的人权报告等都具有影响全球舆论和国家形象的力量。这些报告客观与否姑且不论,但它们的影响力却是我们不能不积极应对和认真思考的。
4 系统采集、分类整理和深入研究国外智库的中国研究成果是图书馆亟待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10]
笔者供职的国家图书馆承担着为中央国家领导机关立法与决策提供文献信息支持和保障的重要职能。我馆近年来承接的诸如国外医疗制度改革、国外生物安全立法研究、南美国家的行政执行法、发达国家的行政督察制度等文献信息查询委托,反映出我国立法机构和政策制定部门信息需求的国际化。与此同时,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社情民意、国际社会的反应与评价等舆情信息也成为立法决策机构关注的重点,在委托咨询和专题信息定制业务中的比例逐渐上升。从重视立法决策的前期文献调研、论证和借鉴,到关注立法决策结果的舆情和影响,无一不体现出我国立法决策日趋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发展态势。国外智库有关中国研究的信息和丰硕成果对于上述信息需求而言提供了一个领域较完整、相对独特且具有很高价值的参考信息源。与其他立法决策服务机构相比,文献信息咨询服务是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的特色和优势。重视并尽早着手开展国外智库中国研究成果的系统采集、分类整理和深入研究,使高质量、高价值的网络信息资源得以长久保存、有序整合和有效利用,使参考服务信息源在图书馆传统馆藏文献的基础上得到丰富和扩充,使决策者能够及时获取不同立场的观点和不同角度的分析,从而使以文献信息为基础和特色的图书馆决策参考服务水平得到切实提高。
据笔者统计,在2010年《全球智库评估报告》(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综合排名前二十位的智库中,大约有十五家智库建立了中国研究中心或中国研究项目(区域研究或主题研究)。这些研究项目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以文本、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媒体形式发布,诸如研究报告(Paper)、简报(Brief)、综述(Roundup)、分析(Analysis)、评论(Commentary)、证词(Testimony)、演讲(Lectures)、访谈(Interviews)、专栏(Op-Ed)、文章(Article)和专著(Book)等。发布渠道则囊括机构网站、E-mail、手机、RSS订阅以及Blog、Twitter、Podcasts、Facebook、YouTube等各种流行的互联网传播渠道。凡此种种,在为信息资源的全面采集和有序整合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图书馆等决策信息服务机构带来不小的挑战。
对收集到的国外智库的中国研究信息和成果进行解读和综述是另一种挑战。有别于其他文献和信息,针对国外智库中国研究的特点,除了结论以外,还应特别关注诸如问题分析的角度和方法,采用的事实和理论依据,引用的言论、文本和数据,智库和研究人员的意识形态背景,研究结果可能产生的决策和舆论影响等问题。全面的解读、理性的分析、准确的提炼和综述是决策参考工作人员的责任。
作为信息资源的集散地,图书馆在采集、组织、研究网络信息资源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包括人力条件——在信息查询、信息组织和信息解读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图书馆员;网络条件——国家图书馆、大型研究型图书馆和省级公共图书馆已具备互联网使用条件;技术条件——图书馆应用系统和网络信息采集软件的研发和应用。因此,对国外智库中国研究信息和成果进行收集整理并将之运用到决策参考服务中去,对于承担决策服务职能的图书馆来说,既是应为之事,也是可为之事。至于“何为”,笔者拟另文再论,此不赘述。
在《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一书的序言中,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写道,“在本世纪,所有国家都应当更好地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导人。对于中国和美国这样对国际事务有重要影响的国家,这一点尤为重要。”[13]
领导人的国际视野除了自身修为之外,部分也有赖于具有国际视野的“谋士”——决策服务工作者的支撑和帮助。图书馆的决策服务只有不断更新服务理念、拓宽服务思路、深化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手段,才能满足决策者的需求,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尽己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