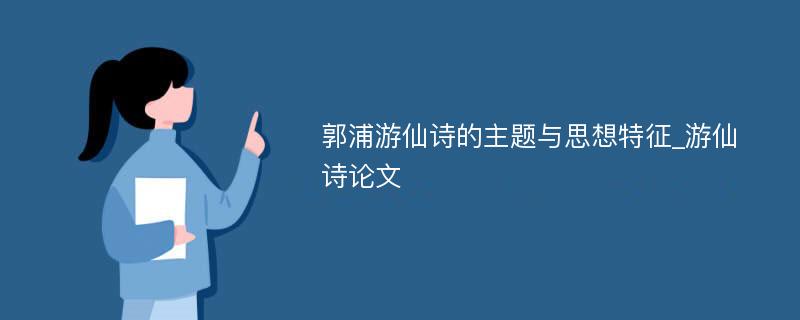
郭璞《游仙诗》的主题及其思想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游仙诗论文,特征论文,思想论文,主题论文,郭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3)06-0067-10
关于郭璞《游仙诗》的创作主旨,自古以来就有“列仙之趣”说和“非列仙之趣”说以及神仙世界是否有所寄托的争论,直至今天这一争论亦未稍减。在不同观点尖锐对立,又都不能正确解释作品主题的情况下,有些论著,特别是几部通行的文学史便“化整为零”,把完整的《游仙诗》划分为主旨完全不同的两部分或几部分,并对不同的主旨分别做了具体分析。①这种观点将《游仙诗》人为肢解,彻底否定了《游仙诗》具有完整统一的主题和结构,而视之为互不相干的十首诗的无序集合。实际上,这种颇为流行的观点是在没有搞清诗义情况下的严重误读,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与上述流行观点相反,本文认为,《游仙诗》的十首诗紧紧围绕中心展开描写,共同组成了主题统一、结构完整、特色鲜明的优秀诗篇。
长期以来,《游仙诗》研究进展缓慢的情况说明,要正确认识《游仙诗》的思想内容和主题,就不能停留在“列仙之趣”说和“非列仙之趣”说以及神仙世界是否有所寄托等传统认识上,更不能以《游仙诗》没有完整统一的主题和结构这样一种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测作茧自缚,而应当打破思维定式和传统观点的束缚,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另寻出路,继续前行。
作为作品思想内容集中概括的主题,是深藏于作品构架深处的灵魂和中心思想,而不是浮在表面的思想泡沫,主题涉及作品内容的方方面面,因此,要正确把握它,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它所涉及的所有问题,只有把这些局部性的具体问题搞清楚以后才有可能真正进入主题研究。撇开这些问题,直接面对主题是不太可能的。对于思想内容比较复杂的作品来说,这种“基础性工程”尤其显得重要,郭璞的《游仙诗》就是如此。要把握《游仙诗》内容构成和主题,除了认识一般作品所必须了解的作者生平思想和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字词训释和每一首诗的诗义等问题之外,还必须认真解决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如《游仙诗》中神仙世界的来源途径和思想性质;“列仙之趣”部分和“非列仙之趣”部分的思想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序诗的意义及其与正文之间的关系,等等。
长期以来,《游仙诗》的主题之所以得不到正确认识,重要原因之一正在这里,即不是从解决作品中的局部性的具体问题入手,而是直奔主题。由于一些重要的具体问题没有搞清楚,很多“障碍”横亘在那里,结果走了很多弯路,以致《游仙诗》的主题至今还是迷雾一团。鉴于这种教训,作者研究《游仙诗》主题时首先是把主题放下,而从解决上述局部性的具体问题入手。②解决了这些局部性的具体问题,也就为把握《游仙诗》的内容构成、通篇大意和主题思想基本上扫清了障碍,本文阐释《游仙诗》主题及其思想特征和贡献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由于篇幅的关系,关于这些局部性具体问题的观点这里不做一一介绍,只在下面的有关论述中出注说明其出处。
《游仙诗》内容的构成和段落划分
《游仙诗》共包括十首诗,由序诗和正文组成。
序诗即第一首诗(“京华游侠窟”),此诗通过从理想的高度对人生价值取向的抉择,否定了以“游侠”为文化符号的积极作为,倾力济世的人生道路,而肯定了以“山林隐遁”为文化符号的出世远游,学道修仙的人生道路。人生道路和方向的明确,坚定了诗人“高蹈风尘外”,即通过山林隐遁,学道修仙,追求神仙世界的决心。③显然,这是序诗为全诗所标明的思想指向,并构成了贯穿全诗的思想线索。
正文包括九首诗(第二至十首),是诗人学道修仙历程的“自叙”的全部内容,可以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二(“青溪千余仞”)、第三(“翡翠戏兰苕”)两首诗,主要写山林隐逸和初步的方术修炼,是诗人学道修仙实际践行的初始阶段。④
第二首是写山林隐逸生活,表现诗人对于高士许由的仰慕和对于神仙世界的强烈向往以及无由交接神女的惆怅和苦闷。魏晋时期,很多人把山林隐逸视为学道修仙的必经之途,由隐士转化而成为神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因而有“为道者必入山林”⑤之说。可见,写学道修仙从山林隐逸开始完全符合历史真实,而所写的心理活动,如“仰慕”“向往”和“惆怅”“苦闷”等也完全符合初学仙道者的心理特征。
第三首写初步的方术修炼:在远离喧扰人世的清幽环境中,以“歌啸”进行方术修炼并诱发了存想幻视,在存想幻视中诗人“看到”了赤松、浮丘和洪崖等神仙在祥和氤氲中驾鸿飞翔、逍遥同游的神奇场景。存想幻视之后又以“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描写从神仙世界对人间进行审视,不仅表现出诗人对于快乐自由的神仙生活的强烈向往,而且通过“蜉蝣辈”与神仙世界的隔膜,反衬自己心向神仙世界的强烈信心和希望。⑥
按神仙道教教规,信仰神仙道教不能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而必须同时进行严格的方术修炼,这样才有可能修炼成仙。《游仙诗》中所描写的方术修炼生活就体现了这一点。
第二部分:包括第四(“六龙安可顿”)、第五(“逸翮思拂霄”)、第六(“杂县寓鲁门”)和第七首(“晦朔如循环”)共四首诗,主要写学道修仙的原因和思想基础:对于生命悲剧及其所带来的焦虑和痛苦的深刻体验,以及为了摆脱生命悲剧,消解它所带来的焦虑和痛苦,通过反复探索最终选择了学道修仙的人生之路。
第四首主要写为了超越生命悲剧而进行的反复探索:先是幻想时光倒流,以使死亡的过程得以逆转;然后又幻想像鸟兽那样通过改变生命形式以延长寿命;接着,又走进神话世界,希望通过超自然的神奇力量改变生命的有限性;这一切都未能达到目的,转而寄希望于上天,幻想借助神的力量使生命得以延长,但最终仍然是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两句写由于探索失败,找不到摆脱悲剧性命运的出路而深感悲哀。可以看出,诗人在探索中所想出的各种办法都是针对“六龙安可顿,运流有代谢”,也就是为了克服时光不可逆转的流逝及其所造成的生命转瞬即逝的生命悲剧。
第五首主要写对于尘世束缚所造成的不自由的不平和无奈。“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诗人认为各种各样的尘世束缚使人的处境如同吞舟之鱼在浅水中无法游动一样,令人难以生存——这是生命悲剧的另一个内容。
第六首根据《史记·封禅书》等文献的有关记载,再现了燕昭王和汉武帝为了长生不老,永享荣华富贵,多次兴师动众出海寻仙以及远远地看到美妙神仙世界和群仙嬉戏的情景。
魏晋时期流行这样的观念:“求长生,修至道,诀在于志,不在于富贵。”⑦富贵之人特别是帝王贪恋权势,骄奢淫逸,对他们来说成仙比登天还难;而普通信众由于没有或较少贪欲和奢望,有利于恬和淡泊,澄静玄默,反倒比较容易得道成仙。最后两句“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正是根据这种流行的观念发出了令人震惊的议论和感叹,有力地表现出对于人间帝王一边醉心皇权,一边幻想成仙的愚蠢行为的极度蔑视和嘲讽,同时也表现了自己对于学道修仙的信心和虔诚。
第七首主要写了两个内容:前八句写对于时间飞驶的无奈和对生命短暂的焦虑:反映了诗人对生命的关注和对死亡的恐惧。后六句写诗人思想的重要变化:经过反复探索和失败,诗人终于认识到摆脱生命悲剧的希望不在人间而在神仙世界,因为那里的“园丘有奇草,钟山出灵液。王孙列八珍,安期炼五石”,足以使人从悲剧性的命运中解脱出来。在诗人的认识发生重要变化的基础上,诗人“长揖当塗人,去来山林客”,决心告别仕途,走学道修仙之路到神仙世界去。⑧
以上第二部分的四首诗,其中第四、第五和第七这三首诗直接抒写学道修仙的原因和对于摆脱生命悲剧的探索,但在它们中间却插入了抒写历史往事的第六首诗;表面看来第六首仿佛多余之笔,实际并非如此,此诗与其他三首之间在思想内容上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第三部分:包括第八(“旸谷吐灵曜”)、第九(“采药游名山”)两首诗,主要写修德悟道和进一步方术修炼,是诗人学道修仙实际践行的继续阶段。
第八首集中写修德悟道。所谓修德就是“希贤励德”,从道德精神上进行修炼,“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⑨。这样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所谓悟道就是探究和参悟道的真谛,以便按照道的精神修炼和处世,摆脱世俗罗网的束缚,实现精神超越和心灵自由,最终使自己复归于道。道教认为,学道修仙不单单要学那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术修炼的要领和技巧,更要修德悟道,以激发内在的自我超越并转向神圣的境界。就是说,方术修炼与修德悟道必须二者兼顾才有可能具备成仙的条件。诗人正是根据这样的认识和要求,既做方术修炼(如第三、九首所写),又坚持把修德悟道作为学道修仙的重要内容予以实际践行。
在写修德悟道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刻画其心理的变化:如“悠然心永怀”四句描述诗人心存高远、超然物外的悠然自得心理以及获得心灵自由之后超脱凡俗一往无前的神态等。
第九首写在初步方术修炼(第三首所写)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方术修炼:采药服食、行气、服炼津液等功法修炼及其所引起的飘飘欲仙的神奇效果:在存想幻视中诗人与神灵融为一体,随风驾龙,乘雷逐电,向神仙世界飞奔。⑩
第三首和第九首都写了方术修炼和从神仙世界对人间的审视,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这些差别无一例外地反映着诗人学道修炼的不断加深和进步以及内心世界的深刻变化:对于人间凡俗越来越鄙弃和疏离,对于神仙世界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和迫切。(11)
第四部分:包括一首诗,即第十首(“璇台冠崑岭”),写长期学道修仙的最后结局:实现了宗教理想,修炼成仙,到神仙世界永享自由快乐。
这首诗主要写了三个内容:一是开头六句所写的成仙的地点和环境,即位于西海之滨与招摇山相毗邻的美丽而神奇的昆岭,这是成仙赴神仙世界的必经之地。二是成仙的仪式,即“寻仙万余日,今乃见子乔。振发晞翠霞,解褐被绛绡”。其中“寻仙”二句是说通过“万余日”的修炼终于得到神仙王子乔的接引和点化,表示其虔诚信仰和修炼功夫获得了神仙的认可,愿意接引他到神仙世界。(12)后两句以道教仪式中摘下旧帽,戴上仙冠;脱去褐衣,换上仙服的习惯做法来代指成仙。(13)三是最后四句“总辔临少广,盘虬舞云轺。永偕帝乡侣,千岁共逍遥!”写成仙以后,到神仙世界与神仙同游,永享自由快乐。这四句描写赴神仙世界所用的车马舆服和所到的具体地点,像前面描写崑岭美丽而神奇的景象一样,完全符合教道有关赴神仙世界的具体节仪规定,并有其充分的文献根据。(14)
以上是《游仙诗》学道修仙历程“自叙”四部分的主要内容,简言之即:
第一部分(第二、三首),学道修仙实际践行的初始阶段:山林隐逸和初步方术修炼;
第二部分(第四至七首),学道修仙的原因和通过探索选择了学道修仙的人生之路;
第三部分(第八、九首),学道修仙实际践行的继续阶段:修德悟道和继续方术修炼;
第四部分(第十首),修炼成仙,到神仙世界永享自由快乐。
如果将这四部分按内容性质进行归类,那么,第一、第三和第四这三部分,即学道修仙实际践行的初始阶段、继续阶段和最后修炼成仙,显然都属于学道修仙的实际践行,而第二部分即生命悲剧所引起的焦虑和痛苦以及为了摆脱悲剧性命运通过探索而选择了学道修仙的人生之路,显然属于另一方面的内容,即学道修仙的原因和思想基础。
如此看来,那种认为《游仙诗》的内容头绪繁多、无法理清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它不过是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学道修仙的原因和思想基础(即第二部分);一是学道修仙的践行经历及其结果(即第一、三和四部分)。全诗内容集中明了,段落分明,脉络清晰。如果说与一般的写法相比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只有这样一点:《游仙诗》内容的四部分并没有完全按照先原因、后结果,先思想认识、后实际践行的一般顺序安排,而是把学道修仙的原因和思想基础部分放在了实际践行的过程当中,即在学道修仙的初始阶段与继续阶段之间。当然,如此安排内容自有其原因,这涉及《游仙诗》的结构特点。
《游仙诗》的主题及其思想特征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知道,《游仙诗》作为诗人学道修仙历程的“自叙”,是从学道修仙的原因和思想基础“自叙”起,经过实际践行,最终修炼成仙而告终,完整地反映了魏晋时代在神仙道教成为人们共同价值取向的条件下,一个有抱负而又高度敏感的士人为了摆脱悲剧性命运,是如何在痛苦、焦虑和苦闷中,通过反复探索而最终走上学道修仙人生之路的丰富而复杂的心路历程。就是说,诗人首先提出了如何超越生命悲剧的问题,然后又给出了答案:通过走学道修仙的人生之路来摆脱悲剧性命运。明确了《游仙诗》两个方面内容及其相互关系,那么,《游仙诗》的主题及其思想特征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通过学道修仙历程的“自叙”,说明学道修仙的人生之路是超越生命悲剧及其所带来的焦虑和痛苦的根本途径,反映了诗人对于生命永恒和自由的向往以及力图摆脱悲剧性命运的超越精神,这种为寻找和确立安身立命之本以安顿灵魂的形而上的追求,既是对于人的终极关怀的体现,也是愚昧落后思想观念的反映。
从《游仙诗》的主题不难看出,诗人创作的主观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和对人生的体验与思考,现身说法,说明学道修仙的人生之路是摆脱悲剧性命运及其所造成的焦虑和痛苦的正确途径,宣扬消极无为,逃避现实,保全个体生命永享自由快乐的神仙思想,肯定魏晋时期广泛流行的以神仙道教为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毫无疑问,《游仙诗》的创作意图所反映的思想观念,是完全错误并应当予以批判的。但是,如果仅就这一点便将《游仙诗》完全否定,认为没有任何可取之处,那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因为作品的形象大于思想,具体描写重于说教,在这方面《游仙诗》尤其显得突出:其创作的主观意图与诗歌艺术形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背离,这突出表现在它所提出的问题与给出的答案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诗人对于如何摆脱悲剧性命运所给出的答案是错误和荒谬的,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可言,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即通过形象描写所反映的对于悲剧性命运的感受和体验,对于如何超越悲剧性命运的探索及其所表现的对于人的终极关怀,则集中体现着《游仙诗》的思想艺术精华和价值。
由于诗人的历史局限性,使他十分荒谬地将这样两个具有完全不同思想性质和价值取向的内容捆绑在一起,纳入同一架构组成作品,这确实增加了《游仙诗》主题的复杂性,但并不能遮掩它们的不同的思想本质。大致说来,《游仙诗》主题的思想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浓重的悲剧性特征。
从前面对《游仙诗》内容构成和主题的论述可以知道,《游仙诗》虽然把追求神仙世界,成为神仙的宗教理想作为全诗表现的中心目的,但在全诗内容的安排中却没有局限于此,而是首先寻绎导致产生这种理想和追求的原因,即为了摆脱悲剧性命运,消解它所带来的焦虑和痛苦。就是说,诗人没有把反映学道修仙历程的诗歌局限于狭隘的宗教生活和宗教修炼的范围内,而是首先放在生命存在和人生理想的高度和广阔视域加以审视,从而赋予作品以鲜明的社会内容和浓重的人间色彩,这不仅极大地开掘了作品的思想空间和深度,提升了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也决定了《游仙诗》主题的浓重悲剧性特征。
在学道修仙原因和思想基础部分,如第四、五、七首中,诗人一方面把看不见、摸不着因而不引人注意的抽象时间的流逝形象化,描绘出时间“巨流”一去不复返的无情图景以及面对时间流逝的无可奈何,一方面又出色地描写出空间束缚使人不得自由的悲惨处境,寥寥数语便生动有力地表现出人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局限性所造成的生存困境,从而使这部分内容弥漫着强烈的悲剧气氛。
不仅如此,诗歌还突出反映了这种局限性所带来的毁灭性的结局:从时间巨轮碾压下万物走向衰败的惨相,使人自然联想到世事的急剧变化和生命的稍纵即逝,最终走向死亡的悲惨结局以及严酷束缚下失去自由所导致的创造力的毁灭和生命的枯萎。就是说,死亡和尘世束缚所摧毁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恰恰是作为创造的主体,一切意义和价值因之而生的人,因此生命悲剧也就意味着最珍贵希望的破灭和幸福的丧失。正是因为如此,关于人的价值观念才被进一步唤醒和强化,悲剧感也随之油然而生:面对生命悲剧使人如身陷困境,大难临头。“当悲剧意识成为人们对于实在的意识的基础时,我们就称之为悲剧情态。”(15)可以说《游仙诗》的上述有关描写充分表现了诗人的强烈悲剧意识和令人震撼的“悲剧情态”。
这样的生存困境,不分地域、民族,不论尊卑、贫富,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的必然性命运。“人生中的一切可怕的事件并不都是悲剧性的……真正的悲剧以历史必然性的观念作为基础。”(16)正是因为如此,生命悲剧也就使人饱受煎熬和折磨,它所引起的焦虑和痛苦远远超过一般的悲剧而显得更加凝重、强烈和深沉。在这方面,《游仙诗》通过浓墨重彩的描绘,形象有力地表现出诗人在陷入悲哀、痛苦和恐惧深渊之际的内心情状:
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吒。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悲哀和痛苦之情不止于内心,更外化为无法控制而又富有特色的动作和表情,从而把浓重的悲剧性特征十分巧妙地熔铸为诗人生动具体的形象。
第二,超越性特征。
虽然生命悲剧是一切人都必然面对的“现实”,但并不是每个人对它都有强烈的感受,而只有那些有所作为,努力创造生活,也就是珍惜生命价值,寄托意义于人生的个体,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才可能转化为悲剧。“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17)这说明,正是悲剧使生存悟出超越的必要,生命悲剧本身就是超越生命悲剧的压力和动力。所以,生命悲剧虽然令人痛惜,但却不属于自甘沉沦的人:对于生命悲剧体验越深,感受越强烈,摆脱悲剧性命运的诉求也就越迫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悲剧才被称为“伟大的悲剧”。
《游仙诗》的学道修仙的原因和思想基础部分正是按这样的逻辑抒写:从生命悲剧和探索摆脱生命悲剧的出路开始写起,进而描写了对于生命悲剧的深刻感受和体验,反映了生命悲剧所造成的巨大焦虑和痛苦。诗人的探索虽然都是借助幻想和神话通过象征的方式表现出来,不是生活的本来面貌,不具备历史“真实性”,但却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对于生命悲剧的态度:明知悲剧性的命运与生俱来,不可抗拒,但在强大的命运面前却没有退让,更没有束手待毙,屈服于它的威压之下,而是想尽一切办法与之抗争:为改变悲剧性命运,消解它给人造成的焦虑和痛苦进行了反复探索。即使历经了多次失败之后仍然没有灰心和气馁,而是继续其抗争的步伐。正是这种与命运抗争的超越精神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并使人的存在获得了意义和尊严。
“奋斗和克服困难则激起惊叹,因而就属于崇高。”(18)戏剧中英雄人物因“奋斗和克服困难”而“属于崇高”,以诗歌形式所表现的同样内容,当然也“属于崇高”——因为它们都体现了悲剧精神的核心:对于悲剧性命运的超越。
第三,哲理性特征。
如前所说,诗人对于生命悲剧之所以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和体验并充满了迷茫和苦闷,是因为生命悲剧直接毁灭了人的最珍贵的希望和寄托,这就是说,诗人的种种强烈反应归根结底是出于对于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能否实现的关注和忧虑,而这种关注和忧虑中所蕴含的实质性问题则是:人的命运是什么?人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什么?如何实现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沿着诗人对于自身命运的反观自照如此追问下去,最终必然涉及为人的生存寻找根据的人生终极问题。
要提高生命的价值,充实人生意义,关键是寻找和确立安身立命之本,亦即人生目标和生命的支撑点。有了这样的“目标”和“支撑点”,使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本体联系起来,生存便有了根据,人生便找到了方向,生命价值因而得以生成,从而人生也才有了充实感和归属感而使灵魂得以安顿。正是因为寻找和确立这个“目标”和“支撑点”是如此重要,所以从人成为一个自觉的人,即从关于生命的价值观念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寻找并且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而诗人在《游仙诗》中为摆脱悲剧性命运所做的反复探索,虽多次失败仍不肯罢休,归根到底也正是为了寻找这个“目标”和“支撑点”。这样看来,从一定的意义上完全可以把这段文本视为人类这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的艰难历程的象征。所以,如果说诗人提出的有关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问题是关于人生的终极问题的话,那么诗人寻找人生“目标”和“支撑点”的反复探索则体现了对于人的终极关怀。
正像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历史的作品往往具有现实性一样,涉及人生终极问题和终极关怀的作品往往具有哲理性。因为“悲剧是哲学的艺术,它提出和解决生命的最高的形而上学问题,它意识到存在的含义,分析全球性问题”(19)。这说明《游仙诗》实际是以哲学的眼光洞察人生,体验时间,关注生命,使哲理与对人生境遇的体验和思考结合起来,并融进自己的内心和感情世界,从而到达诗情与哲理之间、形象与思想之间的高度统一。这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涵,提高了其艺术魅力,而且使其意义远远地超出了个人:由于反映了一切人类寻求解脱的共同愿望,传达了人类心底的共同呼声而具有普遍的意义。
最后,是《游仙诗》主题所体现的错误思想观念:
上述三个特征仅仅是就《游仙诗》内容的精华部分,即学道修仙的原因和对如何超越生命悲剧的探索等内容所做的简要分析。随着诗歌内容从提出问题向给出答案的转换,有关内容的思想性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前一部分所具有的悲剧精神、超越精神和哲理性特征早已杳无踪影,而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荒诞、愚昧和自私的性质特征。
前面说过,人类寻找安身立命之本和生命“支撑点”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但这个安身立命之本和生命的“支撑点”究竟是什么,不同的人、不同哲学的回答是完全不同的。诗人在经历了反复探索和失败之后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以学道修仙、成为神仙到另一个世界的方式来摆脱悲剧性命运及其所造成的痛苦和焦虑。这说明,诗人是把神仙世界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和人生的归宿,也就是以此作为安顿灵魂的终极价值。诗歌后一方面内容所反映的学道修仙的实际践行正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十分明显,诗人给出的这个答案是完全错误的:世界上根本没有超现实的存在,神仙世界不过是宗教观念的形象演绎,人能成仙更是虔诚信仰者的痴心妄想。因为人间的问题从来只能在人间解决,幻想以超现实的力量解决现实问题无异于异想天开。这种违背客观规律的荒诞、愚昧之举只能说明信仰者精神的病态扭曲。
实际上,学道修仙的人生之路是一条远离现实、回避矛盾、毫无作为的消极之路,是迷失了人生方向的士大夫的错误选择。他们完全丧失了人的主体性而不得不匍匐于神的脚下,将自己的命运交给神来掌握。因此,那些关于神仙世界的美好想象,尽管十分具体,令人神往,但终究不过是他们的“自我意识”(20)和无奈的“叹息”(21)。这样的“自我意识”和“叹息”除了使精神得到暂时的安抚——实际是麻痹——之外,根本不可能改变悲剧性命运,更不可能给人带来幸福。
退一步说,即使诗人真的成了神仙,实现了长生不老,自由、快乐的宗教理想,那也仅仅是为了一己之私,除了满足个人的感性欲望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其他更高层面的追求。就是说,这条人生之路不但与他人没有任何干系,不可能对世界和社会有什么裨益,而且也根本无助于个人人格的完善;恰恰相反,它只能暴露其自私、狭隘的本质。因为如果生存仅仅是为了自己,而对他人没有任何意义,那么,其生存也就失去了意义。换言之,真正有意义的人生,除了对自己有意义之外,更要有超越于我的意义,而有益于社会群体和历史进步。诗人的选择恰好相反,所以,与前一部分所表现的悲天悯人情怀和不失崇高的超越精神相比,在后一部分中其精神境界可谓一落千丈而直接堕入了另一个极端:“与优美最处于对立地位的,莫过于无聊了;正有如降低到崇高之下的最深处的,莫过于是笑柄一样。”(22)从今天的角度看,诗人为了那个虚幻不实的神仙世界而沉溺于宗教修炼不能自拔的愚蠢、荒诞行为,确实显得滑稽可笑。
《游仙诗》对中国诗歌发展史的意义和贡献
以前由于没有正确把握《游仙诗》的思想内容和主题,所以根本无法正确评价它的思想艺术成就及其对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意义和贡献,现在,搞清了这些问题,可以说也就具备了分析评价其“成就”“意义”和“贡献”的条件。
第一,《游仙诗》主题具有全新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创新特征。
郭璞具有强烈的生命悲剧意识,十分注重感受时间和生命,体验宇宙和人生,(23)这使《游仙诗》与以前的诗歌相比,在关注的对象和题材方面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变化,并赋予其主题以全新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创新特征。
自先秦至汉魏的一千多年间,诗歌作品的关注对象和题材多集中于社会、家庭和个人出处等方面,诸如政治黑暗、社会动乱、民生疾苦、家庭婚姻乃至日常生活以及个人理想、抱负和经历、遭际等等,总之,多是一些具有较强社会性的现实问题,反映的多是对于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于不合理现实的不平和理想抱负不能实现的痛苦、悲哀等等。《游仙诗》虽然也是从人的生存状况出发,但所关注的却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人在宇宙中即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局限性所造成的悲剧性命运及其所带来的焦虑和痛苦。这说明诗歌题材和关注对象已经从社会、家庭和个人前途转向了人的生命,由人的现实生活转向了人的生存境遇,由对社会光明、公平、正义的追求转向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生命价值的追求。相应地,作品重点描写的对象也不再是社会历史和日常生活景象,而是与终极问题密切相关的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变化,主要揭露的也不再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黑暗和丑恶现象,而是抒发生命悲剧所引发的焦虑、痛苦和悲哀。概而言之,《游仙诗》写的不是社会、家庭和个人的悲剧,而是人所不可避免的生命悲剧;而诗人对于摆脱悲剧性命运的反复探索,说明《游仙诗》已经超越了世俗性的理想和追求,而具有明显的终极关怀的特征。
总之,正是郭璞的强烈生命悲剧意识使他在前人关注和惯用的题材范围之外,从另一个角度聚焦人的生存和命运以及如何超越命运的问题,并使他在诗歌创作中没走前人的老路,而是另辟蹊径,开拓创新,因而为中国诗歌发展史做出了新的贡献。
对于人的这种终极关怀与常见的对于人的现实境况和具体遭遇的关怀,尽管着眼点和具体内容不同,但关注的对象都是人,体现着相同的人文精神,并且对于人来说各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比较完整地写出了诗人在其人生价值取向形成过程中的丰富而复杂的心路历程。
《游仙诗》作为诗人学道修仙历程的“自叙”,其引人注目之处主要不在学道修仙过程本身,而在于这个历程所展现的丰富的思想内容,特别是诗人精神发展变化的心路历程。
诗人的心路历程开始于对生命悲剧及其所带来的焦虑和痛苦的感受和体验,继而为了摆脱悲剧性命运及其所带来的焦虑和痛苦,而开始了寻求解脱出路的探索。在经历了探索、失败,再探索、再失败之后,诗人认识到在人间要彻底摆脱悲剧性命运根本不可能,因而重又陷入极度痛苦和悲哀的深渊,与此同时其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世上之人要想得到彻底的拯救,摆脱生命有限性和人间的一切灾难和痛苦,唯一的希望是在人间之外的神仙世界。于是,诗人决心告别人间,走学道修仙的人生之路。就这样随着“希望”之光在诗人心中的升起,悲哀、愁苦的阴云一扫而光,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从此开始诗中再也见不到前面反复出现的悲哀、痛苦的描写即可证明。接着,在对其所选定的学道修仙人生之路的实际践行中,其心境又有了新的变化:从修德悟道时心存高远和对于神仙世界的强烈向往,到与世俗罗网彻底决裂,向神仙世界奋进,再到从九霄云外的神仙世界远望人间而“发现”世界渺小、人间可哀,反映诗人已经看破人世,超越世俗,亦即表示诗人经过不断的修炼已经超凡脱俗,距离神仙世界越来越近。最后,终于修炼成仙,在神仙世界永享自由快乐。
可以看出,诗人通过自己学道修仙历程的“自叙”,比较全面和完整地描述了内心世界发展变化过程。这个充满哲理性悲情的“感受”“体验”“思考”“探索”和“追求”的过程,在诗人内心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形成了内涵丰富而又充满曲折的心路历程,反映着魏晋时代一代知识分子在精神寻觅过程中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精神风貌和人格特征。
在先秦汉魏诗歌中,很少有作品能够反映出涵盖如此深刻、丰富而又完整有序的心路变化历程。从这个意义上,把《游仙诗》视为一篇诗人的精神“传记”并非没有根据。
第三,以抒情的方式表现悲剧美。
与叙事性作品如戏剧、叙事诗、小说等展示悲剧美的方式不同,《游仙诗》则是通过诗人对于悲剧性命运的感受和体验及其所引起的内心世界的深刻变化表现悲剧美,亦即不是通过再现悲剧性的真实“现场”,而是通过令人震撼的“悲剧情态”来感染和打动读者。由于诗人的富于感染力的引导和渲染,这种“悲剧情态”带给我们的感受之强烈和真切不仅不亚于叙事性作品的“现场”目击和“客观”描述,而且还使沉重感和压抑感油然而生。更为重要的是,《游仙诗》除了展示“悲剧情态”之外,还象征性地表现了对于悲剧性命运的挑战,反映了诗人的超越精神和对于人的终极关怀。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积极的思想因素,使我们在《游仙诗》所营造的“悲剧情态”中所感受到的恐惧和悲哀不仅不会转换为反感和厌恶,而且会由于体会到人的尊严和崇高精神而深感振奋和快慰。而这正是我们从《游仙诗》中所得到的审美心理体验!“至极的美就是属于悲剧的美!感觉到所有的事物终将飘逝的意识,使我们完全浸染于至极的悲痛当中,而这一份悲痛则又向我们展示启现那些不会飘散消逝的事物,那就是永恒的、美的事物。”(24)可以说,《游仙诗》以抒情的方式所展示的正是这种悲剧美的特有魅力。
第四,《游仙诗》在题目运用上的创新。
众所周知,“游仙诗”本是指通过描写神仙世界以寄托主观情思的诗歌,所以,如果从题目的本意出发去衡量郭璞《游仙诗》的思想内容,显然存在“文不对题”的问题。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是从传统的观点出发判定其对题目的误用,还是根据作品的具体内容重新定义“游仙诗”这个诗歌类别?我认为,后一种认识,即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更为符合包括诗歌类别在内的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诗人以旧题写新内容,实际是大胆突破了旧题的传统边界而将全新的内容输入,亦即以“旧瓶装新酒”,扩大了传统“游仙诗”题目的容纳范围。这样虽然使“游仙诗”失去了本意,但却换来了“游仙诗”类别的发展。
如此看来,诗人以“游仙诗”为题写全新的内容绝不是题目的误用,而恰恰是不受传统定义和现成“规则”的约束,勇于创新的生动体现。
以上四点突出体现着郭璞在诗歌创作中取得的突出成就和对中国诗歌史的重要贡献,(25)特别是前两点,无论是从主题的性质、题材的开拓上看,还是从思想内涵的深刻性和丰富性上看,在中国诗歌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收稿日期:2013-04-15
注释:
①如徐公持《魏晋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1、483页;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上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8页;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②解决这些局部性具体问题的文章和发表刊物如下:一、《两种不同人生价值取向的抉择——郭璞〈游仙诗·京华游侠窟〉试解》(以下简称“文一”),《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二、《郭璞的生命悲剧意识与〈游仙诗〉——试论“非列仙之趣”部分及其与“列仙之趣”部分之间的关系》(以下简称“文二”),《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三、《郭璞(游仙)诗中的神仙世界与宗教存想》(以下简称“文三”),《文学遗产》2012年第4期;四、《从郭璞的神仙道教信仰看(游仙诗)》(以下简称“文四”),《中州学刊》2011年第5期;五、《驾鹤仙去——郭璞之死解读》(以下简称“文五”),《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③详“文一”。
④下面对各部分和各首诗内容的介绍详略有所不同:凡在发表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则从简,反之则稍详;比较容易理解的内容从简,反之则稍详。
⑤《抱朴子内篇·明本》,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7页。
⑥详“文三”。
⑦《抱朴子内篇·论仙》,王明:《抱朴子内篇校注》,第17页。
⑧关于第四、五、七这三首诗思想内容的具体分析详“文二”。
⑨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53页。
⑩详“文三”。
(11)详“文三”。
(12)详“文四”。
(13)见道教经典《锺吕传道集·论证验第十八》关于成仙仪式惯行节仪的记载,《道藏精华录》上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14)达到神仙世界的地点“少广”,见《庄子·大宗师》;诗人是乘坐轻便而又显贵的轺车,并有虬龙“启道”而赴神仙世界的,轺车见《晋书·舆服志》;“盘虬舞”即以虬龙“启道”,见《云笈七籖》第一册,第459页。
(15)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16)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4卷,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67页。
(17)斯马特:《悲剧》,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朱光潜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416页。
(18)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0页。
(19)尤·鲍列夫:《美学》,冯申、高叔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
(20)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
(2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22)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何兆武译,第35页。
(23)详“文二”。
(24)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北京: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123页。
(25)《游仙诗》对中国诗歌史的贡献除以上几点外,在艺术表现和艺术处理方面,特别是对方术修炼内容的艺术处理也十分精彩和富于特色,同样值得认真总结,因与主题思想的关系不大,本文未加涉及,有关内容详赵沛霖:《郭璞〈游仙诗〉中方术修炼内容的艺术处理及其贡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