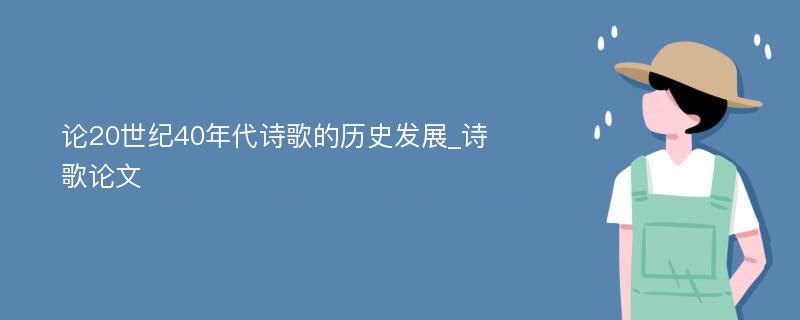
论四十年代诗歌的历史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十年论文,诗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40年代诗歌内容与形式的演变受制于现实需求规律。诗歌内容随时代现实生活和政治情势变化,而诗歌形式的运动与转换也随之同步。40年代诗人执著地投入生活的激流,在紧紧追逐时代主流的同时,探索并运用各种表现手段,用以与自身艺术地把握现实生活、传达思想感情的旋律结合起来,和日寇及其汉奸走狗进行搏斗,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正如李煌(王亚平)当时所说:“在此悲壮苦痛的伟大年代,我们有权要求诗人们创作出伟大的史诗、叙事诗;还要求诗人们创作出伟大的史诗、叙事诗;也同样要求诗人们写出不朽的抒情小诗,还要求诗人们写出极有诗趣的讽刺诗,正如我们抵抗敌人,有时需要长矛大刀,有时也需要短枪匕首一样。”[1]的确,抒情诗、叙事诗(史诗)、讽刺诗是40年代诗歌的主要文体,是诗人表现生活情感的主要形式。但由于各个阶段的时代生活内容有别,诗歌表现方式又呈现出不同的偏重和不同的特色。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各个阶段的社会生活又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因而表现生活的诗歌形式则有所不同。虽然同样一种生活题材,非用什么形式表现不可,未免有些绝对,但不可否认,某种生活题材比较适于某种表现形式。从40年代各个阶段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发展和诗歌形式的变化来看,正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表现形式与表现内容相适应的角度作纵向考察,整个40年代诗歌可以说是时代谱写的三部曲——抒情·叙事·讽刺。
一
“七·七”事变以后,中国人民长期被日寇侵略与凌辱,郁结于心底的爱国主义的抗日烈火终于爆发成伟大的抗日战争。正如胡风所说:“战争带来了一个高峰,我们看到了全面性的热情澎湃,我们看到了全面性的爱国主义放射着灿烂的光辉;人民的苦闷消散了,人民的热情爆发了,人民的希望燃起了。”[2]“在那热情蓬勃的时期,无论是时代底气流或我们自己底心,只有在诗这一形式里面能够得到最高的表现。”[3]茅盾也指出:“炮火使我们的血液沸腾,壮烈的斗争使我们的灵魂震撼,可歌可泣的事太多,此时此际,只觉得非用诗歌这一形式便不能淋漓尽致。”[4]的确,抗战爆发后,中国新诗进入了“最蓬勃发展的阶段”[5],“面向着这民族解放的战争,面向着勇敢地为祖国而斗争的战士与民众,面向着旧时代的暗夜与新世界的黎明,我们的诗人们,以对于土地的深沉的挚爱,以对于英雄战士的崇高的敬仰,以对于在火中、血中呻吟着的悲哭着的无数同胞的同情与哀伤,以对于法西斯强盗的兽行的仇恨……我们的诗歌唱起来了。”[6]臧克家这样写道:“诗人啊,请放开你们的喉咙,除了高唱战歌,我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我们要抗战》)这实际上表达了诗人们的共同心声。
抗战初期的诗歌负载着时代的激情,普遍充满着对于抗战的鼓动和光明的歌颂,洋溢着震撼人心的鼓舞力量和乐观兴奋的调子。郭沫若在《战声集·前奏曲》里歌唱道:“全民族抗战的炮声响了,/我们要放声高歌,/我们的歌声要高过,/敌人射出的高射炮。/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我们再没有顾虑逡巡,/要在飞机炸弹之下,/争取民族独立的光荣。”这可说是抗战初期诗歌的主旋律!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气氛中,诗人们亢奋地抒写出一曲曲抗战的颂歌,整个基调真切率直,激越粗犷。正如芦焚当时指出的:“这时期诗的主要作用在于传达抗战的任务,诗人是号手,是尖兵,是为祖国战斗的站在最前排的战士,因而出版的诗集或在各杂志报章上的副刊发表的诗都是热情的歌唱而洗脱了过去糜糜之音。”[7]这一概述是符合诗坛实际的。当时诗歌作为战斗的号角,“它已不复是湖上的清涟,而是海洋的汹涌的巨浪;它已不复是林中的鸟语,而是暴风的呼啸;它已不复是恬静的溪水,而是狂奔的激流。”[8]当时郭沫若也指出:一般的诗人们“受着战争的激烈刺激,都显示着异常的激越,而较少平稳的静观,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而初期的抗战文艺在内容上大抵是直观的、抒情的、性急的、鼓动的,而在形式上,则诗歌和独幕剧占着优势的地位。”[9]
抗战时期,诗歌最受鼓舞,因为战争本身的刺激性,又因为抒情诗人的特别敏感,随着抗战的号角,诗歌便勃兴了起来,甚至诗歌本身差不多就等于抗战的号角,所以抗战以来,抒情诗之多,产量之丰富,是超出于其它各部门的。而且这些抒情诗大都继承了五四以来的抒情诗的优秀传统,又特别把革命诗歌(政治抒情诗)的鼓动性、战斗性发挥到了极致。这时期的抒情诗大都是抗战热潮激荡中产生的,诗人们都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发为刚健的雄声。那些来自大后方、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特别是来自延安的战斗的怒吼,成为这一时代最激昂的号音与鼓点。这一时代诗歌的战斗精神的集中代表,无疑要算艾青和田间。艾青的《向太阳》是号角,田间的《给战斗者》是战鼓,它们概括地传达出那个时代洪亮、激越、沉浑的声音。诗篇感情激越,气势磅礴,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诗人在诗中更为圆熟地运用了他们那独特的抒情形式,鼓荡的激情和急风暴雨般的时代的声音,使诗篇成为全民抗战的进军鼓声与号角,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在这时代和个人生活的大转折时期,剧变的社会生活已经直接把激情提炼出来,涌动在诗人的胸间,使他们忍不住象江堤决口一样直泻出来,于是就成了真挚动人的诗篇。
在抗战初期的诗坛上,凸现的是与抗战初期的时代情绪相协调的各种各样的抒情诗体,如朗诵诗、街头诗、枪杆诗、传单诗等。这些“手榴弹”、“盒子枪”式的短诗都是鼓动性极强的政治抒情诗,它们是抗战现实生活中培育出来的花朵,是抒情诗领域中的奇葩,它们为当时的抒情诗创作增添了夺目的光彩。这些诗的最大特点是感情真挚,火药味浓,战斗性强;提炼了人民群众中优美的口语,充分表现出一种朴素的美、简明的美。
这时期的抒情诗大多以小型为主,呈现出短小精悍的特色,这是因为抗战初期强调生死攸关的战斗,又要求急速反映紧迫的现实,煽动人民起来为生存、为改变自己命运而斗争的激情,因而诗人们不可能有从容抒写的余裕。而他们自身生活的剧烈变化,使他们感受着强烈的生活印象和炽热的时代情绪,这强烈的生活印象和炽热的时代情绪逼着他们选取直截而单纯的形式。这就是说,生活和环境都不容许他们冷静地思考,从容地进行艺术的熔铸,他们只能抓到一点写一点,所以篇幅的简短是非常自然的。尽管这时期也有一定数量的抒情长诗、叙事长诗和讽刺诗产生,但影响并不大,成就并不高。而大量的抒情短诗既紧密地结合了时代,又是诗人发自内心的独白。诗人在斗争的生活中抱着强烈的战斗激情和坚强的战斗信念来反映当时的生活现实,因而这些诗歌能成为时代精神的号筒,体现时代的主潮。尽管大敌当前,国破家亡,却没有惶惑不安,消极颓废,每一行诗句都满溢着全民族大奋起的昂扬与乐观,较好地反映了初期轰轰烈烈全民抗战的时代风貌。
抗战初期的抒情诗大多采用赤裸裸的表现方式,大多在直抒胸臆的宣言式的呐喊战叫中又加入了大量的议论式陈辞,这就造成了一种时代所需要的气氛,容易产生现时性的鼓动效果,但由此也给诗歌带来了一种突出的毛病,那就是感情浮泛浅露。虽然充满了气势,但又不免令人感到干爆;虽然热烈奔放,但又深刻不足,精美、谨严不够。臧克家在谈到他初期的创作时说:“第一阶段:心里充满了热情、幻想和光明。这心境反映到诗上,显得粗糙、躁厉、虚浮和廉价的乐观,热情不允许你沉深、洗炼。《从军行》、《泥淖集》、《呜咽的云烟》中的诗大概可以这么说。”[10]王亚平也说:“在前方两年内写成的一些诗,虽然不敢存心偷懒,骗人骗自己,但苦功夫下的不够,不能执着在艺术的创作上,不能从生活到创作一点一滴的尽自己的血汗与精力,那些在浮浅的感情下产生的东西,却带着粗劣的宣传味,与火性的喊叫,多少壮丽动人的题材,却被自己糟踏了。那些诗宛似生柴生烟蒸的生饭一样,没有一点深厚的味道,只给那些战争中的可以歌颂的人物,动人很深的故事,画了一个不清楚的面貌,一个简单的轮廓。”[11]可以说,不只臧克家、王亚平如此,绝大多数诗人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在那热情蓬勃的时期,“诗人普遍受到了情绪底激动正是当然的,但激动的情绪并不就等于诗人用自己的脉搏经验到了;用自己的语言表现出了隐伏在表皮下面的、时代底活的脉搏底颤悸。”[12]一些诗人虽然已经深入生活,但又因技巧的贫弱而陷入无法深透表现的境地。所以,诗坛更多的是悲壮激昂的单一声调,“粗劣的宣传味”、“火性的喊叫”、“浮浅的感情”,是当时诗坛的一种通病。这时期的抒情诗,它的成绩和缺陷都明显地胶着在一起。
抗战初期的诗坛纵然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所反映的新主题和新的现象却表现了相当程度的真实。从抗战初期文艺的总的形势来看,诗歌有着长足的进步,“这进步在配合着整个抗战形势的行进上看来,容或还不够,但是在发展的本身上,依然可以预望着胜利的远景,依然可以从这新的基础上出发,向新中国的伟大的文艺阵地迈进了。”[13]
二
抗战初期,诗人们受着战争的激荡,情不自禁地发为时代的音响,大多数作品偏于抒情一途,且形式短小。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诗人们的心境由兴奋状态转入了沉炼状态,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也逐渐加深。于是,诗坛出现了从短诗到长诗、从抒情诗到叙事诗的发展趋向。
诗坛格局的这种变化,是随着战争的持续、生活的深入而产生的。武汉沦陷以后,政治形势逆转,国统区十分黑暗,诗人们面对新的形势,热烈昂奋的情绪消失了。随着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诗人们的情绪渐渐镇定下来,艰苦的战斗削弱了诗人廉价的乐观。对初期创作的认真总结和反思,必然引导他们回复到本来的静观,使得他们在现实体验既经饱满之后,不得不站在更高的层面来重新审视创作,提炼、构思新的作品。抗战初期,各类体制的作品多属短制,自然限制了生活内容的表达。抗战中期,形势的巨变,生活的深入发展,促使诗人探索表现新的世界的新形式与新风格,努力创作综合性的历史性的作品。于是,诗人们选择题材不再限于正面的英雄和战斗,而是要在比较广阔的画面上从多种角度反映抗战的现实生活,更深入地表现时代和社会的变动,揭露这些现实状态在人们心灵深处引起的剧烈变化,于是,诗歌的内容也渐渐地比较丰富和厚实了,形式方面也比初期更复杂了。在艰苦的劳作中,诗人们善于根据不同题材、不同内容而采取不同的形式,运用不同的笔法,写出风采格调不同的诗来;初期那种单纯的歌唱已成为过去,繁复的现实生活已成为诗篇的描写对象,因此这时期诗坛便有了大量的叙事诗、剧诗、抒情诗、朗诵诗、街头诗、讽刺诗。特别是长篇叙事诗形成“竞写热潮”,万行长诗的创作成了诗人们追求的一种风尚。诗人们试图在广阔的背景上全景式地反映生活,铸造时代的史诗,要求伟大的作品产生,因而叙事诗、史诗便在诗坛捷足先登了。
事实上,史诗般的作品是随着抗战的持续、生活的表层走到了生活的密林,上前线,到敌后,下农村,诗人普遍深入生活,获得了广大的生活领域。所谓“文章入伍,文章下乡”,已经不是流于标语口号,而是诗人实际上的行动与事业了。诗人们从兴奋状态镇静下来,突入生活的深处,是叙事诗兴盛起来的基本条件。其次,诗人们深入现实生活之中,苦难的现实时时槌击着诗人们的心,他们更多地看到了现实,触到了现实,理解了理实,他们看到了光明的一面,也看到了黑暗的一面;他们看到了抗战历程中许多值得颂扬与怒骂的现象;他们为许多抗战中牺牲的英雄感动得流泪,也为一些出卖祖国的丑类憎恨得咬牙。诗人们要描写这样的人物,表现这样的故事,只有倚重于叙事诗、史诗。可以说,这个时代既为抒情诗、讽刺诗的发展提供了良机,更为叙事诗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因为优秀的叙事诗,更能表现伟大时代的画面,更能描写人生社会之动态情景,更能创造出典型的人物,更能唤起广大民众的抗日情绪;它比火性的喊叫、空洞的抒情更具有感召力量。再次,抗战中期对现实主义问题的深入讨论,使诗人们对现实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把握。他们认识到抗战初期诗歌创作只反映了抗日而忽视了争民主,这种只反映了“半面”现实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更加全面地、深刻地、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成为他们创作上的一种自觉追求。要使诗歌在反映广阔的现实生活方面跨进一步,短小的抒情诗便受到了某种限制,而叙事诗则显出了它特有的优势。还有,文坛对叙事诗的理论倡导和呼唤,也是叙事诗的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仅以几位成就较大的诗人为例,即可说明抗战以来新诗从短到长、从抒情到叙事的一般发展趋向。
艾青在抗战前和抗战初的诗大都是抒情短章,很少写叙事诗,1939年3月写的《吹号者》是一篇半抒情的诗,是诗人开始探索新的创作风格的标志。随后所写的《他死在第二次》显示着诗人创作的新发展,诗人开始把描写空泛的感情与静物的图画的笔用来描写具象的人,绘写伟大的血与火的时代中的战斗者的形象,诗人能够以完整的章法与绵织的诗节获得成功。1940年创作的《火把》,无论在诗的章法方面或人物的描写方面,都比《他死在第二次》完整得多,诗人已经能自觉地把握新的发展方向了。
田间在初期创作政治抒情诗的同时,就开始了叙事诗的探索,他的小叙事诗创作是他从抒情转向叙事的过渡性产物。尽管他的小叙事诗也不失为一种创造,在表现当时的斗争生活方面具有突出的贡献,但小叙事诗还毕竟是突击性的速写,它只截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断或侧面,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也显得单薄。但田间并未就此止步,他不断探索新的创作道路,大胆作叙事诗的尝试。正如胡风所说:“小叙事诗毕竟是突击性的描写,而诗却总是不断地要求情绪世界的深厚和深长的。随着对于生活内容的坚韧的深入,诗人田间终于开辟了纪念碑式的大叙事诗的方向。”[14]他的《她也要杀人》以及《祝山》、《我底枪》、《亲爱的土地》、《铁的子弟兵》等初步展开了长篇叙事诗的规模;后来的《戎冠秀》和《赶车传》则标志着他的叙事诗的更大的成就。
臧克家自《烙印》之后就对自己那种谨严得“太觉局促”的形式有些不满,于是“想脱开过分的拘谨渐渐向博大雄健处走”。如何达到博大雄健呢?就是“运用大材料”来“写长一点的叙事诗”。他的这种探索自《自己的写照》就开始了,而《走向火线》、《淮上吟》、《向祖国》、《古树的花朵》、《感情的野马》、《和驮马一起上前线》、《六机匠》等规模可观的长诗,则标志着他在叙事诗创作上不断探索的足迹。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诗人们都由热情的歌颂转向冷静的叙写,都力图用长篇巨制来反映这场伟大的人民战争,反映繁复多变的社会生活,写出具有史诗般的作品来。在这个时期,几乎每个诗人都注意长篇叙事诗的尝试与探索,象艾青、田间、臧克家等不但以叙事诗创作为重,而且他们这时期的代表作也多为叙事诗。除此,力扬、绿原、邹荻帆、柯仲平、玉杲、戈茅、臧云远、何其芳、方敬、鲁藜、厂民、冀汸、常任侠、雷石榆、李岳南、李雷、锡金、柳倩、天蓝、韩北屏、魏巍、陈辉、公木等众多诗人都在长篇叙事诗创作上用力甚勤。这个时期叙事诗创作基本处于热闹的探索阶段,诗人们对它的性格还不十分把握得住,他们试探着,创作着,努力做栽培的工作。他们勇于写叙事诗,坚信它有辉煌的前途。他们由不断的探索中奠下了成功的基石,达成了40年代后期(1946年以后)叙事诗的进一步成熟和繁荣。但我们切不可只见后来的硕果而忽略了前面的诗人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要知道,那时有不少诗人在叙事诗的倡导与创作上一直十分用力,但最终并没有获取成功的果实,王亚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对叙事长诗作过长期的试验,写下了《地狱》、《血战亭子山》、《失地上的故事》、《血的斗笠》、《塑像》、《静静的修河》、《二岗兵》、《红蔷薇》、《同志,骄傲当属于你们》等一系列的叙事长诗,由于诗人艺术积累的不足和生活体验的不深入等原因,使这些作品艺术上都比较幼稚,但诗人在不断的失败中,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探索。他说:“我准备在不断的失败中,更坚毅韧性地写作下去”;“诗是永远结不成的果实,我自己愿为这果实付出终身的血力。”[15]在那时,叙事诗创作毕竟处于探索阶段,往往失败多于成功,即使象艾青这样杰出的诗人,也是成败得失皆有。
经过众多诗人的努力探索,基本确立了叙事长诗的文体特征和诗性品格。他们先后对叙事诗的阐释也基本体认了这一点:叙事诗这种形式,是兼有抒情诗的抒情与小说、戏剧的叙事的优点的特殊形式,这是别的文学形式难以取代的。这种叙事诗的抒情近似抒情诗,又有别于抒情诗;这种叙事诗的叙事近似小说、戏剧,又有别于小说、戏剧,它具有既能抒情又能叙事的特殊功能。当时比较优秀的叙事诗几乎都是“有情有景有人有事”的有机统一体,我们能够从“叙事的诗”中,看到较为完整的故事和鲜明的人物;从“诗的叙事”中,享受到那些感荡心灵的强烈浓郁的诗情、诗味。叙事诗与主观化的抒情诗和客观化的小说、戏剧之不同,在于它把客观叙述与主观抒情相结合,把实境和诗境、实情和诗情相统一。叙事诗的叙事因素的加强并不等于抒情因素的减弱。加强叙事是为了情溢于事,强化叙事因素乃是为了抒情的强烈。当时比较出色的叙事诗作者,都在叙事和抒情的巧妙的结合上呕心沥血,苦苦探索,从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火把》、田间的《戎冠秀》、臧克家的《古树的花朵》、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玉杲的《大渡河支流》等诗都在坚强的叙事中融合着昂奋的激情,都以饱满的热情和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打动人心。
从这时期叙事诗的内在形态来看,大都经历了由单纯到繁复、由紧凑到恢廓的发展过程。前期叙事诗大都规模较小,而后来的叙事诗在结构上更为铺张和宏大,在铺张的结构里,固然失去了先前的“单纯”和“紧凑”,但却得着了“繁复”与“恢廓”,这样就扩大了新诗的容量和负载力。同时,这时期优秀的叙事诗也摆脱了空洞的叫喊,大都对人民的苦难和反抗的主题进行沉思,具有广阔的叙事范围和沉重的抒情分量,表现技巧也趋于老练和成熟。由于国统区和解放区的环境不同,叙事诗风格也呈现出大致不同的两种倾向:国统区的叙事诗格调一般显得比较深沉凝重,而解放区的叙事诗格调则具有比较清新朴实的民歌风味。
尽管叙事诗本身的优势在抗战中期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但由于叙事诗的创作毕竟处于摸索阶段,因而成功之作并不够多,很多叙事诗不尽如人意,尤其在叙事诗的表现技巧上尚未达成艺术的完美,其情感的淡薄、形象的贫弱、组织的散漫、形式的松驰、手法的粗疏、语言的空泛呆板等,成为不少叙事诗的弊病。周钢鸣当时的尖锐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他说:“目前的许多长诗,是有着许多没有‘诗’的----不足以表现诗的情绪和意境的空疏的语言,和没有生命的形象,杂芜其中,于是变成一首很长很长的‘长诗’。这好象未淘过的一堆矿沙,里面的金子只是几粒,而沙子却是一大堆。这毛病是诗人企图把情感扩张,可是他的感情只有一点点。正因为这种‘擀面条’式的拉‘长’的诗,于是把诗的情绪拉细扯淡了,诗的情感思想稀薄脆弱了,诗的意境与印象模糊了,只看见沙子,寻不到黄金。结果,本来可以写成很动人的诗,也变成贫血的没有生命的苍白的语言了。”[16]这种“长”而无“诗”的现象,在当时是带普遍性的。但诗人们坚持不懈的追求和探索使叙事诗创作不断走向自我完善,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叙事诗创作有了更大的发展,结出了更加丰硕的果实。
抗战中期是叙事诗的时代,也是抒情诗的时代,在叙事诗创作成为普遍风气的情况下,抒情诗创作也得到相当的发展。大多数诗人都操着两副笔墨,既写叙事诗,又写抒情诗,叙事诗尚属试验时期,写起来还不那么娴熟,抒情诗对他们来说则得心应手,所以,一般诗人在叙事诗创作上虽用力甚勤却成效并非很大,反而在并非十分用力的抒情诗创作上却成效显得更好。与此同时,面对日益黑暗的社会制度和日益恶化的社会局势,诗人们并未屈服,并未沉寂,而是更加深沉地搏战,更加策略地斗争,他们又不约而同起操起了似匕首投枪般的武器——讽刺诗。
三
抗战初期与中期毕竟是抒情诗与叙事诗时代,讽刺诗虽然也在蓬勃生长着,但在量和质上都明显不足。讽刺诗的真正勃兴乃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事。
抗战胜利后广大人民不但没有享受到自己饱尝战祸、出生入死所获得的抗战胜利的果实,反而被再度掷入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面对着这惨酷的现实,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转向了对黑暗现实的揭露、鞭挞和讽刺。于是,在诗歌领域,讽刺诗便兴盛起来了。正如臧克家当时所指出的:“在今天,不但要求诗要带政治讽刺性,还要进一步要求政治讽刺诗。因为在光明与黑暗交界的当口,光明越见光明,而黑暗越显得黑暗。这不就是说,在今日的后方,环境已为政治讽刺诗布置好了再好不过的产床吗?”[17]讽刺诗是适应40年代中后期反帝反封建、反压迫、争民主的群众运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和当时的杂文、讽刺喜剧、讽刺小说一道,成为刺向国民党心脏的犀利尖刀,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讽刺诗因其独特的艺术效用,在这一时期的喜剧文学潮流中处于特别触目的地位。
在解放区歌颂救亡与革命的诗歌主潮中,涌现了一批揭露日寇、汉奸和国民党政权的丑行的作品,其中无不充满了强烈的政治讽刺意味,特别是置身于国统区的诗人,不管是老诗人或年轻诗人都拿起讽刺这支笔,郭沫若、臧克家、袁水拍、任钧、王亚平、邹荻帆、绿原、郑思、苏金伞、黄宁婴、黄药眠、穆木天、杭约赫、杜运燮、辛笛等诗人都在这方面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其中,成就最高的要数袁水拍,他在《人民》、《冬天,冬天》的诗集里就已显示了讽刺诗创作的才能,而他的声誉主要来自于《马凡陀的山歌》。《马凡陀的山歌》是用通俗歌谣的形式,暴露国统区城市一切荒唐、虚伪、腐朽、黑暗的现象。“凡是城市市民所感到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无论是可笑的或可气的,一为马凡驼所捉住,就成了他的山歌材料,加以嘲笑、拨弄,极尽辛辣讽刺之能事。从马路的泥浆到电车的拥挤,从外汇的开放到物价的飞涨,从吉普车撞人到取缔黄包车,从副官到张百万……一切一切,凡是城市市民生活中所遇到的事物,差不多都逃不出他的笔尖。”“他所挖苦嘲笑的事物,无一不是这个臭名远播的‘恶政府’的‘政绩’,他的讽刺的箭,是每一根都射中了黑暗势力的鼻梁的。”[18]《抓住这匹野马》、《上海物价大暴动》、《长方形之崇拜》、《王小二历险记》等篇,对国民党的经济政策从各方面加以揭露和嘲讽,特别把飞涨的物价比作野马、暴徒,其讽刺十分形象、有力。《发票贴在印花上》、《万税》形象地讽刺国民党的苛捐杂税,一针见血。《民主和原子弹》把达官贵人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副官自叹》把副官那副走狗的丑态刻画得穷形尽相。《张百万》把那些吮血的“英雄”们的脸谱描绘得微妙微肖。《主人要辞职》把反动统治者自诩为人民的“公仆”的假面具和狰狞面目揭露得鞭辟入里。袁水拍的山歌极精彩地展现出了当时黑暗社会里的人间悲喜剧。袁水拍思想敏锐,观察入微,对时代的弊病看得透,看得深,看得准,有胆有识,能迅速捕捉住有意义的题材,识破伪装巧妙的敌人言行,戳穿某些丑恶现象与畸形生活的本质,写得妙趣横生,痛快淋漓,意味深长。袁水拍的山歌读来使人痛快,催人深省,让人震颤。在那时群众民主运动的集会和游行中常常有人朗诵马凡陀的诗,在上海反饥饿、反内战游行中,有人把马凡陀的诗写在旗帜上。正如徐迟所评价的,“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九年,这么六个年头里,他是冷讽热嘲,嘻笑怒骂,他身不由己地勇敢地以山歌作武器而战斗了过来,他取得了在战场上不可能取得的另一种形式的精神世界里的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19]
臧克家从1942年就开始写讽刺诗,抗战胜利前后,产量更丰,锋芒更尖锐。他在1945年发表的《向黑暗的“黑心”刺去》中说:“这一年来,讽刺诗多起来了,这不是由于诗人们的忽然高兴,而是碰眼触心的‘事实’太多了,把诗人‘刺’起来了。”[20]特别是诗人到上海后,目所接触、心所感受的,全是令人悲愤的景况,诗人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收在《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冬天》里的诗,都是诗人这时期愤怒感情的爆发和凝结。他在抗战末期写的《枪筒子还在发烧》,在解放战争初期写的《发热的只有枪筒子》,都是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恶,这两篇火辣辣的讽刺诗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生命的零度》、《冬天》等感人的诗篇,对反动统治作了最严正的谴责。臧克家写这些诗,不愁没有材料,丑恶的现实就是“宝库”。他说他写《你们》这篇诗时“没有经过酝酿,淤积胸中的愤懑,一泄而不可止!我不象在写诗,象在写一篇檄文,一篇控诉书。它既不温柔敦厚,也不委婉曲折。写它的时候,只觉得眼中冒火,笔下惊雷。”“在这篇诗中,找不到隐约‘内向’的蕴藉之情,在艺术表现上也寻不到雕刻的痕迹。我是有意如此,我不得不如此。在当年那样时代里,需要带上火药味的诗。我这首诗是外向的,连发机枪似的向着敌人射出去,射出去!”[21]在这里,诗人实际上道出了他当时政治讽刺诗创作的整个情景与状态;这也决定了他的政治讽刺诗不是耍聪明,不是追求廉价的噱头,而是把握事物本质,击中反面事物的要害。他的诗不是想出来的,而是从抑制不住的愤怒里跳出来的,因而深刻犀利,发人深省。劳辛称赞《宝贝儿》“是从愤怒中爆发出的诗篇”,“有些诗颇有粗犷的崇高美,它的高亢和律动是能够感动读者的。”[22]
黄宁婴在湘桂战争后写下的《溃退》,是一篇带有强烈政治讽刺性的长诗,暴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指出中国的出路不仅是一个民族抗战,还必须展开一个民主的斗争。在1946年的民主巨潮中,诗人又献出了他的《民主短篇》,这些诗都是对现实政治作短兵的搏斗,对国民党的“假民主”、“剿匪”、“戡乱”等阴谋予以尖锐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邵荃麟当时就指出:“诗人能够那么泼辣勇敢地用他的艺术去为人民战斗,能够抓住每一现实事件给予敏捷有力的反击。把艺术和政治紧密地结合,这不仅为今日激烈的人民斗争所需要,而且也是今天诗歌运动的一个方向。”[23]
青年诗人苏金伞抗战胜利之后写下的诗几乎都是政治讽刺诗,其《台阶上》、《控诉太阳》、《民主和自由》、《国民身份证》等篇都是对国民党政权压制民主、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种种卑劣行为的无情嘲讽。邹荻帆在抗战胜利后写下了40多首讽刺诗,名为《恶梦备忘录》,沙鸥在这时期也写下了许多揭露国民党官场丑闻的讽刺诗,名为《百丑图》,这些诗集的标题已经令人感慨,再读这些诗,更使人心中隐隐作痛。杜运燮写的《追物价的人》、《一个有名字的兵》、《善诉苦者》、《排泄问题》、《论上帝》等诗都是在机智风趣的戏谑中,表现饱含辛酸的生活内容和对畸形现实的愤怒鞭打。杭约赫写的《感谢》、《最后的演出》、《严肃的游戏》、《噩梦》、《伪善者》、《丑角的世界》等诗都是富于喜剧效果的讽刺诗,对那个喜剧时代、丑角们的世界作了深刻的揭露。绿原的《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将上海的丑恶集中排列,在讽刺怒火的照射下显示出其光怪陆离的荒诞性。郑思的《秩序》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是非正邪都给颠倒了的生活秩序。这些讽刺诗都集中于剥画皮、撕伪装、割脓疮、扫垃圾,从而谱写出一支支人民的诅咒曲。
这时期的讽刺诗的总的特征是:不但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政治性,而且表现出多种多样的色调和风格:或揭露控诉、慷慨淋漓;或振笔直陈,尖锐泼辣;或委婉深沉,含蓄有致;或幽默诙谐,笑不自禁,等等。但在这多样的风格中,尖锐泼辣和幽默机智乃是其主导风格。这其中分别以臧克家和袁水拍为代表。如果说臧克家振笔直陈,以泄义愤,其诗也亢直有力,读之令人击节昂奋,那么袁水拍的诗则在热烈的颂歌中蕴含着冷峻的讽刺,斑斓的画幅里隐喻着深刻的哲理;较之其他人的作品,不但多了几分辣味,几分警钟,而且多了几分谐趣,几分冷笑。尖锐泼辣、幽默机智能成为多数诗人的主导风格,是因为时代需要能够挺身而出敢于和善于表示愤怒或冷笑的诗人。就这样,“马凡陀山歌主要以其冷笑、臧克家的讽刺诗主要以其愤怒,得到了读者的肯定。”[24]
这时期讽刺诗创作虽然显得繁盛,但真正成熟的作品并不多,这表现在相当一部分讽刺或油腔滑调,“随口溜”,使诗失却了机智的光采;或拖泥带水、画蛇添足,一览无余,或手法单调,甚至标语口号充塞其间,使诗肤浅乏味,不堪卒读。当然,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诗人缺乏喜剧感,缺乏讽刺才华。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诗坛热衷于讽刺的风气的形成,不是出于一种强烈的讽刺理性意识的自觉,而是出于一种现实的功利需求,即如臧克家一再所言,他的讽刺诗“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的指控和暴露”,讽刺“实际上就是暴露和打击的代名词”。尽管当时讽刺诗创作成风,但讽刺诗的理论探讨却相当贫弱、无力,诗人们在创作讽刺诗时尚缺少一种本体建构的雄心和魄力,因而在这时期表现了良好的讽刺素质,写出了切中时弊、尖锐泼辣、幽默锋利而又意趣盎然的讽刺诗的诗人并不够多。比较而言,袁水拍是比臧克家更具喜剧意味的诗人,袁水拍之所以能称得上真正的讽刺诗人,是因为他的诗“致力于把丑恶撕毁给人看,把注意力集中于反面的喜剧现象,所以他调动了一切能够达到喜剧效果的手段,他的讽刺诗里处处可以爆发‘笑’的力量,以辛辣、谐谑为突出的格调。”但相当一部分诗人如臧克家一样,“一般不把喜剧因素从生活中单独抽出来,而是把喜剧因素放在生活的多面体中来把握,他往往以写正剧的态度和方法来处理喜剧现象,写讽刺诗就象写一般抒情诗或叙事诗那样郑重严谨,一本正经,缺乏足够的幽默感。”[25]所以,从总体上看,那时的讽刺诗的面目在一定程度上还不那么清晰,讽刺诗还没有从一般(自然讽刺诗也还不能不是抒情的)诗的框架中独立出来,获得自己的独立品格,大多数诗人的讽刺诗还与抒情诗、叙事诗胶着在一起,难以分别其突出个性。这也许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必然。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毕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一个光明与黑暗激烈搏斗的时代,诗人们既直接鞭挞黑暗,也呼唤正义和光明;既嬉笑怒骂丑恶事物,也歌颂斗争的胜利。即如写讽刺诗,必然充满强烈的憎爱情感;写抒情诗和叙事诗,也不免带有讽刺色彩。不管是讽刺笑骂,抒情感怀,写实(叙事)批判,每一个执笔为诗的人,都无从闪避地以各自的方式和语言回答时代的逼问,参与时代的斗争。
无论怎样说,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讽刺诗的勃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观。在这个时期,诗人们以讽刺特有的犀利锋芒,在与黑暗现实的搏斗中,显示了无穷的战斗威力,诗人们以喜剧方式结束了一个时代。当然,在这一时期,歌颂人民革命斗争,表达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的政治抒情诗和叙事诗创作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并且在以前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解放区的民歌体叙事诗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把中国叙事诗推向了成熟的境地。所以说,这是讽刺诗的时代,又是叙事诗的黄金季节。
由上可知,尽管40年代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诗歌形式的运动与转换为其特定环境的时代内容所限制,呈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但从纵向上看,大致经历了从抗战初期的抒情短章——抗战中期的长篇叙事诗——抗战后期乃至解放战争时期的讽刺诗这样几个阶段;创作的审美重心大体上经历了一个情、事、理(亦即抒情、叙事、说理)逐渐推移的历史进程。而从横向上看,整个40年代抒情诗、叙事诗、讽刺诗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从此前新诗的形式发展倾向来看,抒情诗比较发达,而叙事诗、讽刺诗则较薄弱。40年代社会生活和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决定了诗体的全面发展趋势的形成。
与此相联系,40年代诗歌的表现技巧也大大提高了,这种提高,是指诗歌的艺术表现力的综合性增强了。可以说,这一时期真正的好诗,技巧是相当娴熟的,这主要不表现在对某一种技巧的单向掘进与发展上,而是体现在诗人能融多种技巧于一炉,创造出能够反映对代生活和思想情感的为一般读众所接受的好诗,而不象二三十年代的“好诗”那样存在一种普遍倾向,要么诗歌内容积极而艺术性则较弱(如革命现实主义诗歌),要么诗歌内容消极而艺术性则较强(如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而是二者得到了较好的统一。这时期的现代主义诗歌在现代情绪中融进了浓厚的时代内容(如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穆旦的诗),革命现实主义诗歌也常常把现代主义技巧化入诗中。因此,诗歌的纯粹性减弱了,综合性增强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整个40年代,由于社会生活变化太快,诗人生活的动荡不安和社会功利性的强化,导致诗歌的艺术性在一定程度上下滑,粗制滥造者较多,这无形中造成一些人对40年代诗歌评价的偏低,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诗歌的“倒退时期”、“凋零时期”。其实,从总体上看,40年代诗歌的成就并不让于此前新诗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诗歌的多样化特征与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保证了诗歌质量的提高。没有一定的数量则没有一定的质量。这时期诗人之多,创作之活跃,是从前不可比拟的。尽管那时诗歌的平庸之作占了相当的比例,但如果从40年代大量的诗作中挑选高质量的诗作,可以说,在数量上是多于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并且这时期诗歌的格调普遍表现出一种昂奋的时代情绪,这种诗歌风格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性、一致性特征,正是诗歌得以存在的价值。如同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恬静与神秘、唐诗的苍凉与豪放、宋诗的理智与做作,给人造成了一种深刻的印象一样,中国40年代诗歌的悲愤与激越的诗风,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印记。
注释:
[1]李煌:《再论小诗》,《新华日报》1942年8月4日。
[2]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页。
[3]胡风:《四年读诗小记》,《胡风评论集》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5页。
[4]茅盾:《这时代的诗歌》,《救亡日报》1938年1月26日。
[5]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文艺研究》1980年第4期。
[6]力扬:《抗战以来的诗歌》,《广西日报》1939年1月3日。
[7]芦焚:《二十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回顾》,《中国诗坛》新4期,1940年6月。
[8]《我们的广播》,《诗》第3卷第3期,1942年8月。
[9]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新华日报》1943年3月27日。
[10]臧克家:《我的诗生活》,《臧克家文集》第4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72页。
[11]王亚平:《抒情时代、叙事时代》,《时与潮文艺》1945年第5卷1期。
[12]胡风:《四年读诗小记》,《胡风评论集》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7页。
[13]罗荪:《抗战文艺运动鸟瞰》,《文学日报》第1卷1期。
[14]胡风:《给战斗者·后记》,《胡风评论集》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5页。
[15]王亚平:《抒情时代、叙事时代》,《时与潮文艺》1945年第5卷1期。
[16]周钢鸣:《论诗创作发展的偏向》,《周钢鸣作品选》,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页。
[17]臧克家:《向黑暗的“黑心”刺去》,《新华日报》1945年6月14日。
[18]默涵:《关于马凡陀山歌》,《新华日报》1947年1月25日。
[19]徐迟:《袁水拍诗歌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20]臧克家:《向黑暗的“黑心”刺去》,《新华日报》1945年6月14日。
[21]臧克家:《关于〈你们〉》,《甘苦寸心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2]劳辛:《〈马凡陀的山歌〉和臧克家的〈宝贝儿〉》,《文艺复兴》1947年第3卷4期。
[23]郡荃麟:《读黄宁婴的诗》,《文艺生活》光复版1946年第16期。
[24]吕家乡:《为了开拓诗的疆土》,《抗战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
[25]吕家乡:《为了开拓诗的疆土》,《抗战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