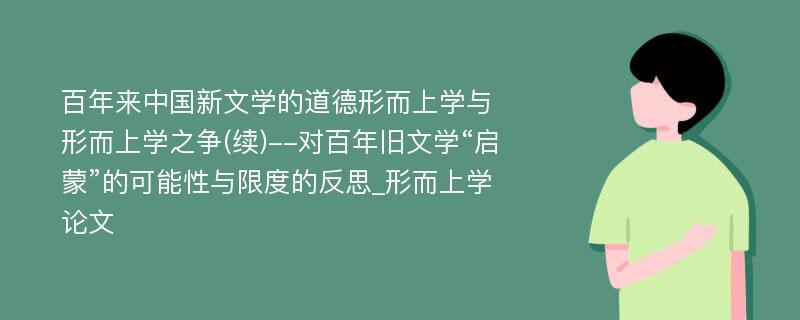
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争鸣(续二)——道德形而上主义:反思百年文学“启蒙”问题的可能与限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论文,道德论文,形而下论文,新文学论文,能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4-0181-16
在我们这个一向崇尚“以礼教立国”的国度,道德主义的光荣与梦想、阴暗与血腥造就了一种难以解释的历史记忆和难以排解的复杂心结,因而,道德问题也必然成为现代思想界难以轻易回避与轻松绕过的一个沉重命题。由此,“新民德”成为近现代以来知识分子的一种首先或优先的思考,而“伦理的觉悟”也成为其所召唤的“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P41)。而在对道德主义的历史问题进行清理与批判的同时,正是因为对泛道德主义的反感,曾为至善至上的“道德”概念在被逐出神坛后也似乎反转为了一个被唾弃与遗弃的恶性语词。然而,道德概念的沦落并不意味着道德问题的终结,恰恰相反,它因此暴露出了更多需要继续深思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语境之下,张光芒在《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2](以下简称张文)中提出道德形而上的问题,并呼吁重建一种新的道德主义,一方面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在许多人看来,“道德”概念至少已经沦落),一方面却也是一种必然(因为道德问题与道德问题的讨论还远未终结)。因此,张文引起批评与争议,似乎也不足为怪。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张文“不合时宜”的思考是其对一直所致力的启蒙问题论述的深化,它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也是深刻而严肃的。但殊为可惜的是,也许是太急于表达一种解决问题的主义了,其所论述的可能性意义并未得以充分的分辨与展开,论述逻辑的混乱与不合之处也多显示出理论结构的某种强制性。从学理意义来说,一种简洁清晰而又无所不包的主义看似能够化解复杂的问题,却也往往能够遮蔽问题的复杂性。因之,笔者在对其问题意识的意义表示出一种必要的同情时,也不得不对其所疏漏的问题作出批判性的辩答与解释。
一、必要的同情:道德形而上问题的意义理解与内在理路
阅读目下刊发的关于道德形而上问题讨论的一系列争鸣文章,或破或立,其所阐发的立场与见解不能不说各具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在笔者看来,他们所表达的观点其实并无什么根本的对立与矛盾。诸如对启蒙问题的理解,除了思路的差异外实在看不出有何本质区分。由此不难理解,原作者为何会在一次又一次的“质疑”与“反质疑”中反复申明自己并无二致的立场,又为何会在反复提醒对方注意自己的问题实质时所表露出的一种不被理解的苦恼。应该说,论争本身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它至少使最初稍显模糊与租糙的言说在反复辩解中更为清晰和细致,但从愈辩愈不明、愈辩愈离题的论争过程来看,笔者又不能不指出论争所存在的内在缺憾,这就是:作为对话或讨论前提的内在同情的缺失。这也是立论者各有所据却难以形成有效沟通的基本原因。试想,如果对不同意见首先在情感上采取一种激烈的排斥态度,如何能憭作者之本心,得原文之深意?而如果站在仅凭一己之意所划定的人为界限之内,又如何能真正切入问题内部来展开论析?因此,批判的前提性问题就在于,如何能首先排除罗素所说的一种情感意义上的“尊崇”或“蔑视”,达致一种学理意义上的“假设的同情”。这样,当我们以同情的理解去面对道德形而上的问题本身时,首先需要理解的几个问题是: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要表述的是一种什么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来源于什么样的知识背景与意义诉求;而来源于这种知识背景与意义要求的问题意识又是如何表述和被表述的?其表述之方法论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朱学勤在多年前的一篇近乎忏悔录式的文章中曾椎心痛问学界同人,至今读来仍觉振聋发聩,心有戚戚。他所感慨与质问的是,同时代的学人们当年在缺乏学术环境的特殊时期关心问题却苦无学理,而“身陷大学环境”之后,“学会搬弄学理,却可能遗忘了问题,更遗忘了勇气”[3]。实际上,从当下充塞于各处的大量为“做”而“做”的文章中已然可以发现:问题意识的缺乏已成为学术体制化之后知识分子思想能力相继萎缩的普遍性表征。而在笔者看来,道德形而上的提出,首要的意义即在于它所内含的一种自觉的问题意识。
在泛道德主义的旧问题尚在清理、仍需清理的时期,张文的新道德主义本意即使在澄清问题,却也可能使本来就枝蔓甚多的道德问题更加复杂难解。因此,道德形而上主义之所以引起争议,首先还在于它对道德问题的涉入。接下来的问题是,道德形而上主义为什么要重涉比较敏感的道德问题,它的旨意何在?如果仅仅从回应现实的时代意义来理解问题,道德形而上主义也许并无什么新奇之处。在一个社会转型与变革的时代,尤其在习惯以道德思维总结一切问题的文化结构中,往往会堆积出诸多真真假假的道德问题。从“五四”时期的道德革命的呐喊,到90年代以张炜、张承志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张扬,不就是虚虚实实的道德危机的一种表征吗?所以,如果仅仅从时代意义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就可能仅仅将道德形而上主义理解为一个道德问题,并从90年代余烟未散的道德理想主义那里找到根据,将其指斥为一个业已失败的“伪问题”。事实上,道德形而上主义虽然涉及道德问题,但并不必然是一个道德问题;准确地说,它应该是一个涉及道德的道德哲学问题。这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解释道德形而上学的原理却并不将其仅仅解释为道德问题是一个道理。道德问题与道德哲学的区分在于:前者是将道德作为一种标准来下结论、做判断,它回答的是正确与否的伦理问题;后者是将诸如理性、自由意志作为道德本身的原则,它回答的是一种道德原则为何可能与如何可能的知识问题。如果混淆了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所提出问题的真正意义。
在张文中,道德形而上学的思考与其说是来源于康德哲学的启示,不如说是在康德哲学启示之下对文学启蒙问题思考的一种内在延伸。原作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语境下的启蒙原创性问题的梳理与发掘,而道德革命问题则是其启蒙反思的一个内在命题。因此,道德形而上实际上是在启蒙问题意识的背景下所生发的一个文学启蒙的问题,而道德形而上的提出也正是去试图反思“未完成的启蒙”给历史、现实遗留下来的种种困惑与难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恰恰是‘反启蒙’文学起到了‘启蒙’作用,且启蒙效果要大得多,而功利性极强的启蒙文学反而尴尬地陷于启蒙功能的无效缺失状态”?从这一思路出发,张文认为,启蒙文学缺乏强大的审美力量就在于对道德形而上建构的忽略,而与此相对的实用主义则成为启蒙文学的一个盲点问题。
在张文中,道德形而上主义的所指实际上交织着两重含义:一是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表述,二是道德形而上问题的如何表述。前者指其内容意义,后者为方法论问题。从内容意义上说,道德形而上主义虽然直接来源于康德哲学的启示,但它更像是借鉴或借用康德的哲学理论与概念。比如,康德哲学是一种完全不涉及经验世界的超验本体论,它旨在解释具有普遍形式或纯粹的道德原则问题,而张文则是以康德哲学的概念来解释经验世界的现实问题。作者通过对康德的道德律令的强调,突出了道德的主体性问题,并由此指出,启蒙文学的功能疲弱在于缺乏将道德内化和提升为绝对命令的一种超越性的信仰力量。作者在这里对超越性的人文理性的强调,是针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倡扬科学、民主这类仅在工具理性、政治理性层面用力的问题而言的,因而自有一种救偏补弊的内在脉络与学理意义。在方法论方面,张文采取了一种与形而上主义相应的形式分析学。这种形式逻辑分析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丁一些论争不休的问题在义理上的限制,并由此抽取出了一种与内容不完全相合甚至相悖的二元形式结构,得出了一个与既定结论基本相反的观点,这就是:传统道德、保守主义与红色道德建构了一种强大的形而上学;而宣扬道德革命的激进主义、启蒙主义反而沦落为一种功利性的实用主义。显然,在形式学的方法论这里,所要挑战的不只是既定的结论,而更是结论背后的结构问题。仅从这一点说,它所引起的争议与反对就可想而知。对于自己由形式分析中抽取出来的观点,作者可能也意识到会发生“不必要的误解”,所以在文末谨慎地指出,“任何过大的理性概括与价值判断都不免充满更大的漏洞与冒险”。但这显然于事无补。一则,既然涉及封建道德、红色道德这些经验世界,形而上问题就不可能是“纯粹的”;二则,谈论道德自然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能否以“纯粹”的形式论抽取之,是值得商榷的。三则,形式学本质上是一种静态的结构分析,能否将启蒙与反启蒙反复交错的动态历史捏合成一个抽象问题,也是需要注意的。不过,形式学分析虽然在解释问题时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但它以一种冒险的勇气实验一种方法的可能性意义却是不可忽略的。
二、需要澄清的困惑:道德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能否解释启蒙问题
批判的意义不能等同于批驳,同情的理解也自然不会是完全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以必要的同情态度对道德形而上问题的内在理路进行考源辨流的分析梳理,并非是一种出于辩解的需要,而是为了深入问题的核心,在力图对原问题形成真实理解的前提下展开真正有效的学理批判。如前所述,道德形而上问题交织着意义与方法的两重意涵。那么,沿此理路而推进的追问与思考就是,百年文学的启蒙问题是否可以归结为一种道德形而上主义,道德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能否解释启蒙文学所存在的内在问题?
如果不注意张文所反复强调的纯粹形式立场,关于道德形而上主义与启蒙、反启蒙问题的论述,势必会让人陷入理解的混乱之中。即使这样,混乱引起的误解与争议仍然如作者所担心的那样发生了。这到底是人们的认识能力出现了问题,还是理论出现的漏洞引发了认识的混乱?换言之,张文关于“反启蒙”文学较之于“启蒙”文学的“启蒙效果要大得多”的论述,是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出现了错误,还是认识历史的理论出现了错误?在作为方法论的形而上分析中,“启蒙”、“反启蒙”的概念与所指显然发生了分裂和颠倒。正是通过这种语词与语义、理论与功能的形式分离,张文以一种独特而奇怪的思路深入到了他所提出的道德形而上问题。从效果最大化的原则看待启蒙文学的问题,张文的判断的确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同时让人感到困惑与不解的是,这种追求效果最大化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恰恰又是作者所标举的道德形而上主义所极力排斥与反对的。从这一方面说,它似乎又暴露出了作者理论立场的混乱与不彻底。
其一,为何在自觉反思启蒙的实用主义问题中又会不自觉地出现实用主义的心态?也就是说,反思启蒙的学术理论为何会出现矛盾与混乱的非启蒙的问题?这一大的问题,显然不是某些论者所指责的“个人作风”所能说明的。中国语境下的启蒙运动的发生就来源于现实问题的紧迫性,而这种紧迫意识与焦虑心态在启蒙运动屡遭外在因素困扰而屡遭挫折的发展进程中,不是随着问题的消隐自然而然地消隐了,而是随着启蒙未完成时态的不断延宕、问题的不断堆积越来越强化了,这种紧迫性的反常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养成一种特殊的“问题癖”的内在原因。虽然反思启蒙问题旨在揭示启蒙运动中所出现的包括功利主义在内的问题,但问题是,反思启蒙的实质与立场也同样是一种启蒙,这决定了我们对启蒙问题的反思往往是主观要求上超越而客观事实上难以超越,表面上超越而实际上并未超越。我们之所以要反思启蒙运动中由紧迫意识而出现的功利主义要求时,事实上也正是来源于启蒙心态的困顿与焦虑这样一个同样的因素。只有在这样的一种理解背景之下,我们才会更深刻地认识到:道德形而上主义为什么在自觉反对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时,却同时在以一种不自觉的功利主义心态来推行反功利主义的道德形而上主张;为什么这种悖论是一种一定要进入到启蒙问题深处才可能发生的深刻的悖论,而这种深刻的结果同样为什么又会导致一种悖论的深刻。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我更愿意把这种启蒙与反思启蒙的内在悖反看作是中国启蒙运动语境之下必然发生的普遍性的困境和问题。
其二,不涉及价值判断的纯粹形式分析在解释必然涉及价值判断的道德问题时是否可能?在某种意义上,理论形式的功用往往大于它所陈述的内容。对形式结构的重视实质上是对普遍性原理的重视,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古典哲学的一种本体论的传统。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那里,形式因是一种决定物质可能性的普遍原则,质料因则是完成这种可能性的物质实现。因而,“形式是实质,它独立存在于它所由以体现的质料之外”[4](P217)。可以说,形而上学之所以被称为第一哲学,形而上学的形式之所以高于或先于质料,就是因为形式代表了一种普遍性的原理和本体论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张文对启蒙问题的形式结构分析同样是在寻求一种“独特永恒”的普遍性“解释”,而且也的确从结构分析中提出了诸如道德形而上这样的原理性问题,其思考不能不说是深远的。但是,形而上学的分析对于道德伦理学问题是否可能或完全适合,同样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首先,道德形而上学回避了价值判断的问题,因为排斥特殊性、经验性的价值判断是保障形而上学获得一种最高普遍性与第一原则的“题中之义”。道德问题必然涉及价值判断,虽然从道德问题出发与从形而上学出发是两种可以互不相干因而也并无根本矛盾的思路,但是一旦以纯粹形式的方法涉及包含价值判断的道德问题,即使在理论上存在可能却必然会在实践中发生碰撞与冲突。因此,当张文将传统道德的“食人”悲剧解释为祥林嫂们“自我实现”的“幸福”,将红色道德的“献身”原则理解为“个体性的主动追求”与“‘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时,必然会引起既可能是误读又绝非仅仅是误读的强烈反对与抗议。
其次,道德形而上学回避了道德信念或信仰的现实实现问题,因为在道德形而上学那里,形式原理之外的现实问题又成了道德形而上的“题外之义”。这就牵涉到一个也许会被原作者称为实用主义的问题:道德形而上学解释道德原理,但能否通过解释自身来解决问题?客观上说,这并不是道德形而上学所应回答的问题,或者说是不应由道德形而上学来承担责任因此也无须回答的问题;因而,这类题外的问题并不能说明道德形而上学的“无能”,不过它至少也说明,道德形而上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道德形而上虽然首先需要哲学建构,而如何转化为一种强大的个体信仰力量却并不是仅凭自身的哲学建构就能完成的。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一种道德哲学的建构与实现都离不开它的社会基础和文化传统。西语“道德”(mores)的词源意义即是风俗习惯的意思,而在中国的《毛诗序》亦有“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语,其义大致略同。除了文化传统、经济组织、社会体制外,政治权力的介入也是需要注意的现实因素。所以,即使是讲求“以礼教治国”、讲求德治主义的中国,也采用了一种窜入法家学说的“德刑兼施”的策略。中国的传统道德一方面是与农业文明、宗法社会相适应的,一方面也是与专制权力的支持分不开的。而合于自然部分的儒家道德理想成为国人“头顶上的灿烂星空”也好,悖于自然部分的纲常伦理成为奴役的枷锁、绳索也好,都离不开一软一硬的两把刀子:数千年政教合一的道德教化濡染之功与政治权力的弹压强制之力。获得与传统道德同样效应的红色道德除了自身即是传统道德基因的革命变种或改造品之外,同样也离不开软硬兼施的现实支持。同样,强调个体理性与自由意志的新道德力量之弱小,与它的发生时间相对短暂,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相对滞后缓慢有密切关系。从这些或正或反的例证可以看出:(1)只有“有条件”,道德形而上学才能“无条件”地上升为一种“本体性的意义”,“一种永恒性的道德诉求”。传统道德与红色道德是因为“有条件”,才能够“无条件”地实现“信仰化、永恒化、绝对化”;反之,新道德没能够“无条件”地实现“信仰化、永恒化、绝对化”,是因为它缺少必要的“条件”支持。(2)在不同历史时期,传统道德力量与新道德力量相互消长,“有条件”与“无条件”不断在发生相对转换,说明了具体的道德准则具有无可避免的历史过程性。(3)曾经占据道德中心的纲常伦理在新时期的衰微,说明传统道德并没有因为形而上学的“无条件”力量获得张文所说“永恒”与“绝对”,新道德在因为社会变革而“有条件”之后获得了普遍认同,说明它过去缺乏的不只是形而上学的哲学建构而更是“条件”的有力支持。(4)“有条件”的外在支持与形而上学“无条件”的道德建构都是不可或缺或不可偏废的,如果顾此失彼或顾彼失此,都是偏于一见的。如果从形而上学的哲学原则出发强调道德主体“无条件”的信仰力量则可,而如果因为仅仅强调道德主体“无条件”的信仰力量而否认外在条件则不可。在理解“娜拉出走悲剧”这一象征意义的启蒙难题时,根据内在于道德主体的“无条件”的思路,确实可以触及过去人们所未曾注意的形上建构与自我启蒙的深刻命题;不过如果仅执此一端,就会与以往将“娜拉悲剧”解释为不走社会解放的道路而否认个性主义一样,同样有失偏颇。(5)黑格尔曾批评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只注意绝对理性而不注意历史合理性的问题。这说明,道德形而上学的哲学建构能够解释形而上学是如何形成的原理性问题,却不能仅仅依凭自身回答形而上学是如何实现的实践性问题。这样,对于启蒙问题的反思,更符合历史真实的表述应该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道德革命最缺乏的不是形而上学如何形成的原理性思想,而是支持形而上学如何实现的现实性条件。(6)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相关问题就是哲学探讨与现实实践的区分问题。在理论探讨时有必要将形而上的哲学问题与实践问题从思想认识上区分开来,而在现实实践中则是不能也不可能分离的。在这一点上,张文的论述逻辑显然发生了一种混乱。如果将哲学探讨作为践行道德的唯一可能的方式,人人都静坐书斋举头仰望灿烂星空,低头沉思道德律令,那么人人即是康德,“满街皆是圣人”,非但不可想象,事实上那也是不可能的。
道德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在解释启蒙问题时所遇到的困境既是中国的特殊语境所酿造的一种普遍性,也是纯粹形式分析遭遇复杂的道德哲学问题所内含的一种必然性。笔者的方法论批判并不否认这一形式本身的创造性意义,也不否认其之于启蒙问题解释所存在的一种可能性,而只是检验它在解释或表述复杂的道德启蒙问题时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界限或限度。其实,方法论本身作为一种理论主张,同样也存在着价值域限问题。如果将作为工具理性的方法论视为“根本解决”、“包医百病”的“主义”,就势必会变异为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时所反复提醒的“大危险”。当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在张文中被置换为一种道道形而上主义时,就似乎潜含着这样一种“危险”。而且,作为一种高调的理想主义的推行,也极有可能将道德形而上学的知识讨论回归为一种作者也曾担心的道德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形而上学的缺失如果是启蒙文学的盲点的话,那么道德形而上主义的提倡,则是反思启蒙文学盲点时的盲点;前者体现出了敏锐的问题意识,后者则反映出了反思自身的问题与限度。
责任编辑注:此组争鸣共有四篇文章,本刊转载了其中两篇。
标签:形而上学论文; 张文论文; 道德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百年中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形而下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