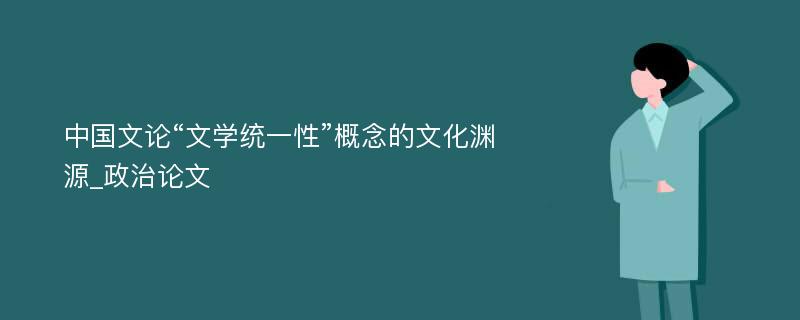
中国文论中“文统”观念的文化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渊源论文,中国论文,观念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趣味”一词的含义,作为古已有之的汉语语词,《汉语大词典》以“情趣;旨趣;兴趣”为其基本义项。在西语中(德语:Geschmack;英语:Taste),据日本美学家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的解释,是指“享受美的对象,判断它的价值的能力”;而“在一定时代、民族等情况下,全体一致的趣味,又可以成为一种‘客观的精神占统治地位(例如罗可可式趣味、中国式趣味等等)’”。根据这些解释,我们可以将“趣味”理解为:就“个体主体”而言,它是一种心理倾向,是人的兴趣之所在;就“集体主体”而言,则是一种在特定时期具有普遍性的精神旨趣①。
得益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反思视域,已故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对“趣味”的理解独到而深刻,特别是他能够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考察“趣味”,可谓独辟蹊径,发前人所未发。他认为社会出身、经济与政治地位固然是阶级划分的根本性因素,但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来说,绝不仅仅在于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人与人的阶级差异、等级差异更主要地是表现所谓“教养”方面。在这里“趣味”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它是“阶级区隔”的主要因素,他指出:“人们出生高贵,但人们还必须变得高贵……换一句话说,社会魔力能够产生十分真实的效应。将一个人划定在一个本质卓越的群体里(贵族相对于平民、男人相对于女人、有文化的人相对于没有文化的人,等等),就会在这个人身上引起一种主观变化,这种变化是有实际意义的,它有助于这个人接近人们给予它的定义。”②根据布迪厄的观点,趣味在贵族成为贵族、文明人成为文明人、“上等人”成为“上等人”、“上流社会”成为“上流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具有决定性的“区隔”作用,不同的趣味使社会明显地区分为不同的阶级与阶层。他认为,一个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趣味”是所谓“合法性趣味(Legitimate taste)”,也就是对合法作品——在社会上获得支配地位的阶级认可的高雅艺术作品——的趣味。他指出:“有机会和条件接触、欣赏‘高雅’艺术并不在于个人天分,不在于美德良行,而是个(阶级)习得和文化传承的问题。审美的普遍性是特殊地位的结果,因为这种特殊地位垄断了普遍性的东西。”③从这种“反思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趣味”——在一切文学艺术和日常审美活动中体现出来的雅与俗、美与丑、精致与粗糙、雅正与新奇等等判断标准,都是一种“文化政治”的产物,与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差异、社会等级秩序密切相关。
下文拟从“贵族趣味”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统”生成的历史轨迹进行探讨,以期从一个侧面加深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理解。
一 贵族趣味之构成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贵族时代是西周之初至春秋之末这五六百年历史。贵族时代的特征,在制度层面上最核心之点是“封建”,也就是“封土地,建诸侯”④。由于“封建”的主要依据是宗法血亲,故而封建的结果,一是形成了从王室、诸侯到卿大夫以至于士的许多个“相似形”——以嫡长制为主线的自然辈分构成的等级关系结构;二是造就了一个以统治者宗族为主要成员的新的贵族阶层。贵族身份是以其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为基础的,这也就是所谓“世卿世禄”之制。但是贵族之成为贵族仅仅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是远远不够的,这里还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这种合法性从何而来呢?对此西周的政治家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们一方面成功地利用了殷商以来一直具有莫大影响力的天命思想,把周人的胜利归结为上天的恩赐⑤;另一方面又在国家政权刚刚稳定之后就立即开始了大规模的文化建设,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礼作乐”。礼乐制度的确立是周人的一大创造,对此后中国三千年的政治和文化都发生了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西周的礼乐制度固然吸纳了殷商及以前历代传承下来的祭祀活动中的乐舞、礼器等仪式因素,但它与以往的祭祀仪式的根本不同在于;西周的礼乐制度根本上已经不再是一种巫术的或原始宗教的祭祀仪式体系,而是将政治体制与精神文化融为一体的全新的政治制度。在这里政治制度具备了“郁郁乎文哉”的外在形式;礼乐文化则包含了严酷冷峻的贵族等级制内核。二者互为依托,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政治统治形式。那套繁文缛礼不仅仅使贵族统治者的一切活动看上去都庄严肃穆,而且使既定的贵族等级身份不断得到确认与强化。只要人们接受了这套礼仪,也就在无形中认可其华丽外衣下面隐含的等级区分。于是在金奏弦歌、钟鸣鼎食、揖让进退之间,周人的统治及其统治形式——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得以确立。周人创造的全部文化符号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因此西周的礼乐文化与其政治制度成为一个难以分拆的整体结构。
贵族等级制度一旦确立,如何使贵族成为贵族则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换言之,贵族除了在经济和政治上拥有特权之外,还必须在精神修养乃至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获得不同于庶人的独特性质,也就是所谓教养。周代贵族采取的办法简单而有效,就是教育垄断——凡是贵族子弟理论上说都要受严格而正规的教育。《礼记·内则》载:“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这是对贵族从儿童到成年整个成长时期教育过程的记述。据《大戴礼记·保傅》,周代贵族更有“胎教”之说:“《青史氏之记》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周后妃任成王于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独处而不倨,虽怒而不詈,胎教之谓也”。“胎教”之说是否有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周代贵族对教育是何等重视。据各种史籍,我们不难看出,周代贵族教育的主要内容分两个层次:一是“小学”,教授“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学习贵族所应具备的各种基本技能;二是“大学”,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学习做人的道理,从而培养高远的人格理想。通过这种循序渐进的贵族教育,一个与其他社会阶层迥然不同的精英阶层出现了,这个阶层的成员都具备文才武略,他们不仅仅是执政者,而且是文化的创造者与领导者,是全社会的表率。他们创造了一套文化观念,并凭借其统治者的特权地位,使这套文化观念顺理成章地成为典则,为全社会所企慕向往。这样一来,贵族的统治地位和既定的等级秩序便得到巩固与强化。概而言之,经过分封诸侯和“制礼作乐”之后,周代贵族就完成了从制度建设到意识形态与文化建设的完整过程。其政治制度是以宗法制度为内核的贵族等级制,与之紧密相关的是一套细密繁琐到无以复加程度的礼仪制度,而与礼仪制度水乳交融般结合的则是贵族的价值观念系统。礼仪制度与贵族的价值观念系统又反过来成为其建基于其上的政治制度的维系手段。由此可见,三千年前的贵族阶层在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尤其是在二者的完美结合上是何等高明!
西周贵族的价值观念系统与贵族趣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这套价值观念是由若干核心价值范畴构成的,包括正、直、柔、刚、明、睿、圣、仁、勇、信等等,而其总名则是“德”。
“德”在周人心目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政治层面上,它被视为“小邦周”战胜“大国商”的主要原因,因而也成为周朝立国的根本依据。看《诗经》的说法:“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示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大雅·大明》)“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周颂·维天之命》)这些诗句都是歌颂周文王的——因为文王有高尚品德,得到人民和天下诸侯拥戴,因此才为克商打下坚实基础。再看《周书》的说法:“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康诰》)“尔克用观省,作稽中德……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酒诰》)在这些语例中,“德”都是指正道直行的好品行。对个人而言,“德”是一种自觉的道德修养,要求人们自觉奉行某种原则与规范,约束自己的欲望以维护贵族等级制和礼乐文化的各种规定;对他人而言,“德”就成为一种善政或善行,即用柔和的、符合道德规范的手段管理社会⑥。对“德”的重视与高扬是周代贵族政治的一大特色,也是周代文化的核心价值。
与“德”密切相关,“敬”也是周人念念不忘的重要价值范畴,一部《周书》,处处可见“敬”字。如《康诰》:“敬哉!天畏棐忱。呜呼!封,敬明乃罚。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召诰》:“呜呼!曷其奈何弗敬?王其疾敬德!王敬所作,不可不敬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洛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汝其敬识百辟享,亦识其有不享。”这里的“敬”字具有虔诚、恭敬、谨慎、小心、敬畏等义项,表现出周初贵族统治者谨小慎微的心态,是所谓“忧患意识”的显现。“敬”与“德”具有密切关联,“德”是克制欲望、正道直行的道德规范,而“敬”在根本上乃是对“德”的持守与维护。有了“德”的指引,“敬”方有落实处;有了“敬”的态度,“德”才得以践行。
对“德”与“敬”的高度重视与弘扬奠定了周代贵族治国方略的基调,从而也开启了中国古代儒家“以德治国”的基本政治理念之先河。用道德修养的方式达到政治的目的乃是这一政治理念的基本特点。后世儒家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三纲领”、“八条目”,亦即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可以说正是秉承周人的治国方略与政治路线而来。儒学于汉代以后能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也与周代贵族长达五六百年“以德治国”的政治实践有着密切关联。
政治上以宗法制为核心的贵族等级制,文化上以礼乐仪式为核心的符号体系,价值秩序上以“德”为核心的观念系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互为依托,共同构成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独特的文化历史语境,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贵族的趣味结构得以孕育形成。这种贵族趣味结构有两个层面:在社会生活层面上表现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向度,一是鲜明的身份意识,二是强烈的道德荣誉感;在精神层面上也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向度,一是对“文”之形式的热衷,二是对“和”之境界的向往。
贵族的身份意识是对自身在贵族等级制序列中的位置以及所应享受的权利、所宜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的自觉认同。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常见“礼别异,乐合同”一类的说法,这正是对贵族社会中“礼乐仪式”之功能的高度概括。“礼别异”是说“礼”的规定与仪式是用来发挥“区隔”作用的,这种“区隔”不是规定差异,而是使已有的差异合法化。就是说,分封制与世卿世禄制导致的贵族在经济、政治上的既定差异需要“礼”进一步予以认定和确证。因此可以说正是这种具有“区隔”作用的“礼”使得贵族成员的身份意识鲜明起来的。他们甫一降生就生活于“礼”之中,“礼”所给出的种种规定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久而久之则成为布迪厄所谓“惯习”。《礼记·檀弓上》记载的那个著名的“曾子易箦”的故事即表现了这种贵族的身份意识。曾子在弥留之际突然发现自己身下铺的竹席是“华而腕”的“大夫之箦”,坚持左右换掉,然后才死去,因为他的身份是“士”而非“大夫”。我们试再举一例:
冬,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左传·僖公十二年》
管仲见周天子,后者以上卿之礼招待他,为他所拒绝,因为他自认为自己虽然在齐国执政,但在身份上却还没有达到上卿的地位。在《左传》、《国语》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尽管春秋时期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已然遭到很大破坏,僭越违礼之事层出不穷,但是在许多有教养的贵族或者信奉贵族文化的士人那里,按照传统的礼制行事依然是他们自觉恪守的行为准则。一般而言,在春秋之时违反礼制的行为并不会像西周时那样受到制裁,甚至许多贵族,包括诸侯君主在内,已经不很清楚西周礼乐制度的那些规矩了,但是在舆论上,那些违反礼制的行为还是受到谴责或蔑视,而自觉遵守礼制的行为就会受到赞美。贵族的身份意识在失去了礼法的约束之后依然规范着他们的行为。这也恰好说明文化“惯习”的力量之大。对于春秋时期的许多贵族知识分子来说,礼乐文化依然是在他们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性情倾向”。在春秋战国之际发展起来的儒家学说可以说正是以这种“性情倾向”为社会心理基础的。
与身份意识密切相关的是贵族的荣誉感。如前所述,贵族之为贵族除了其经济政治特权之外,还必须有一套文化观念与符号作为表征与标志。贵族的荣誉感是指贵族们对这种文化观念与文化符号的高度认同与持守。为了维护这套文化观念与文化符号的神圣性,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与欧洲中世纪贵族不惜以决斗的方式来维护个人或家族的名声颇为相像。看《左传》、《国语》等史籍,这类事例可谓随处可见。如《左传·文公二年》载,狼瞫因勇猛而受到晋襄公重用,后又因为主帅先轸不了解他的勇敢而被废黜,他感到受了侮辱,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他在后来的一场战斗中故意犯险进入敌阵而战死。其间他的朋友怂恿他杀死先轸来报复,被他严词拒绝,因为在他看来那样做就不能维护自己作为勇敢者的荣誉了。也正是误解了狼瞫的那位主帅先轸,在殽之战结束后,因为晋侯听信夫人的意见而放走了秦国的重要俘虏,大怒之下,在晋侯面前“不顾而唾”,大失君臣之礼,后来晋侯并没有丝毫责怪他,但他却不能原谅自己的失礼行为,也在一次狄人入侵晋国时,不穿盔甲即驰入敌阵而战死,维护了一个贵族应有的尊严与荣誉。
看重身份、维护荣誉是周代贵族普遍的精神旨趣,这是贵族社会身份的必然产物。这一精神旨趣决定了贵族阶层对形式和秩序高度重视。身份感和荣誉感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上的特权。而这种精神特权是以政治和经济特权为基础的。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庶民百姓会有强烈的身份意识和基于这种意识的荣誉感。为了满足这种精神上的特权,贵族们在凸现身份和维护荣誉方面可谓煞费苦心。这集中表现在他们对形式的无比重视上。在当时的语境中,对形式——包括祭祀和政治活动中各种仪式、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礼的规定、言谈举止方面的贵族风度等等——的高度重视呈现为话语形式便是“文”⑦。在贵族生活中,“文”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贵族的身份意识和荣誉感需要“文”来满足;作为内在修养的“德”也需要借助“文”来获得外在形式,从而成为对全社会具有教化作用的话语形态。显而易见,“文”本质上是一套与政治秩序紧密相联的意识形态系统,但由于其特有的呈现方式,又不可避免地蕴含了诸多审美因素。这一“文”之趣味对后世两千多年中文学艺术思想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基于对等级秩序的高度关注,贵族阶层除了通过“礼”的严格规定来区分上下贵贱之外,还力求寻求贵族内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睦关系。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有序”必须与“和谐”结合起来才会构成稳定的社会状态。基于这种政治考虑,于是对“和谐”的追求就成为贵族趣味结构中一个重要维度,而其话语形式则是“和”。“文”作为礼乐仪式与话语系统,也要求具有“和”的秩序。因此,在春秋之前的贵族文化中,“和”首先是基于政治秩序的伦理范畴,然后又升华为一种与“文”密切关联的审美诉求。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贵族趣味结构之中,无论是表现于社会生活层面的身份意识和荣誉感,还是表现于精神生活层面的对“文”与“和”的追求,所传达的都是一种“集体主体”的声音,这里没有“个人趣味”或“私人趣味”的位置。这种情形并不是说贵族阶层人人都是一样的心理,一样的趣味,没有私人生活,而是说作为被认可的主流话语,或占主导地位的知识系统中,还没有个人趣味的立足之地。它们只能存在于个人生活的狭小空间之中,随生随灭。而且由于贵族阶层是一个整体——受教育相同,都居于社会统治者的地位,有共同的政治理念,遵循共同道德准则等等——故而他们的趣味结构也大体相同。
二 贵族趣味中的“文”与“和”
如前所述,“文”与“和”代表着贵族趣味结构中最高的层面。尽管这两个语词所代表的精神旨趣都深深植根于贵族阶层的政治利益之中,但由于它们已经升华为形式和风格,所以就与审美产生了直接的关联,并进而在古代文学艺术思想的生成与演变过程中发生重要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文”。这是最典型的贵族趣味,表现出周代贵族对人的精神创造行为及其产物的强烈兴趣与热衷。关于“文”的基本含义及其词义衍生前人已有极为丰富的研究梳理,我们这里无须重复。概括来说,在《左传》、《国语》的文化语境中,“文”大致有两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形式方面——凡属人为创造及自然之物而有光彩者大抵可归为“文”的范畴⑧。《国语·周语上》:“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韦庄注云:“文,礼法也。”⑨这个“礼法”基本上包括了礼乐制度全部内容⑩。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
这里的“文”是指语言的文采以及语言对人之情感与行为的显现功能。“文”的另一层意义是道德规范与人格理想,其功能是使贵族成一个不同于庶民阶层的高尚的、有教养的人。《周语下》云:“襄公有疾,召顷公而告之,曰:‘必善晋周,将得晋国。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韦庄注云:“文者,德之总名也。”(11)这里“文”又包含了周代贵族道德修养的全部内容。由此可知,在西周至春秋时期,“文”基本上就是礼乐制度、知识系统与道德观念的统称。“文”构成了贵族生活的整个文化空间。“文”的趣味就是这种文化空间在每一位贵族身上熏陶浸染出来的一种“情感结构”或“性情倾向”。这种趣味在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所表现,使贵族身上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风神气韵。在精神生活层面,贵族之为贵族而不同于常人之处,主要就在这种“趣味”的差异上。换言之,贵族就生活于“文”的包裹之中。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文”之“趣味”不是“文”本身,而是“文”在主体身上的内化形式,它决定着人们体验世界、感受事物的方式,但不是以观念或认识的形态存在,它是一种包含着感觉、情感、体验等非理性因素在内的综合性精神倾向。在功能层面上,“文”除了为贵族等级制提供合法性之外,它还是彼时阶级“区隔”的主要手段,是贵族自我神圣化的方式。对于后世而言,周代贵族开创的作为典章制度和道德观念系统的“文”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渐渐被抛弃和改造了,而“文”之“趣味”却得到历代知识阶层的继承与弘扬,成为一种历久弥新的文化惯习。
鲜明的身份意识与强烈的荣誉感,再加上这“文”的修养,这种“趣味结构”使得贵族不仅“实际上”是一个特权阶层,而且“看上去”也是不同于黎庶百姓的上等人。钱穆先生尝大加赞赏春秋时期贵族们的教养:
大体言之,当时的贵族,对古代相传的宗教均已抱一种开明而合理的见解。因此他们对于人生,亦有一个清晰而稳健的看法。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过富强攻取之上。……他们识解之渊博,人格之完备,嘉言懿行,可资后代敬慕者,到处可见。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12)
春秋文化是西周文化的延续,并且已经到了衰落的阶段,其文采风流尚且如此,这种贵族文化兴盛时期的辉煌是不难想见的。遗憾的是年代久远、文献不足,其具体样态我们是很难全面领略到,只能从“三礼”、《诗经》、《周书》、《逸周书》等典籍中,窥见其一斑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和”。
在周代贵族的趣味结构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即对一种亲密融洽的人伦关系的高度重视向往,此种心理倾向集中体现在一个“和”上。森严的贵族等级制需要某种柔性的因素来调节,而且周人的贵族制度毕竟是以宗法血亲为基础的,因此礼乐文化在严格冷酷的礼法规定的另一面,便是对人与人之间脉脉温情的向往与高扬。这就是“和”成为西周至春秋贵族文化中重要价值范畴的主要原因(13)。
荀子尝论“乐”之功能云:“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为者也。”(《乐论》)《礼记》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则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记》)“制礼作乐”、“礼崩乐坏”云云,“乐”作为礼仪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可以和“礼”相提并论呢?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古人之所以“礼”“乐”并提,主要是着眼于二者的功能,即所谓“礼别异,乐合同”。“乐”的全部价值指向就在于一个“和”字。细究“和”字隐含的逻辑,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周代以宗法血亲为根基的贵族等级制以及“以德治国”的政治路线决定了贵族统治者对和谐、和平之人伦关系的向往,于是试图用文化教育手段来达到这一政治目的,这就是他们赋予“乐”的政治功能。为了给“乐”的这一政治功能找到更有力的合法性依据,他们便借助于天地万物、阴阳四时和谐有序的自然状态作为“乐”的取象之源,于是天地万物的自然秩序也就成为人世之社会秩序的取法对象。音乐效法了天地自然的和谐有序,具有了“和”的特性,于是也就具备了反过来导致社会和谐有序的功能。周代贵族“制乐崇德”的奥秘即系乎此。
《国语》载周大夫单穆公语云:“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大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昭德。听言昭德,则能思虑纯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则归心焉。……夫耳内和声,而口出美言,以为宪令,而布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从之不倦。成事不二,乐之至也。”(《周语下》)在周人看来,音乐能够表现出“和”的特性,于是也会给听者心理造成“和”的影响。在音乐熏陶下心平气和的执政者,发为政令,则必为善政,从而导致天下归心。可知“和”虽然是一种美的风格,但在生活中却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功能。和谐有序的社会关系是周代贵族所衷心企望的,他们有见于食物的美味需要多种原料的恰当调和、图像的美观需要多种颜色的合理搭配,美妙的音乐需要各种声音的协调,于是在他们观念中音乐的“和”与人世间的“和”便产生了密切的关联。(14)
一般研究中国美学的人都愿意把“和”作为儒家的审美理想来看。这并不能算是错的,但却不能不说是过于简单、粗疏的概括。首先,“和”作为一种审美趣味绝不是儒家独有,事实上它原本是西周至春秋时期贵族趣味的集中体现,在儒家产生之前就久已存在了。其次,“和”也绝不仅仅是一种审美理想,而是一种内涵丰富的综合性精神趣味,是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的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它是一个复杂的“趣味结构”的最高表现形式。第三,“和”在春秋时期越来越受到普遍重视也与诸侯之间尔诈我虞、彼征我伐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表现出贵族思想家对现实的一种矫正的努力。当然,后世儒家的确继承了“和”之趣味,但是也为之赋予了某些新的内涵与意义。在贵族思想家那里“和”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目的是维护与强化已有的政治格局;到了儒家思想家那里,“和”就具有了某种乌托邦色彩,成了他们对社会的批判性话语之表征。再到后世文人那里,“和”的趣味得到进一步纯化,成了琴棋书画与诗词歌赋中的一种趣味、风格,例如琴声之协调、韵律之工稳、构图之虚实相配、笔墨之浓淡相宜之类。其所蕴涵的那些政治功能与文化意义渐渐隐匿不见了。
严格说来,“文”与“和”都不是纯粹的文艺思想,事实上,从西周至春秋这一贵族时代也还没有后世意义上的“纯文学”或“纯艺术”。那时的诗歌、音乐、舞蹈都不是作为文学艺术而存在的,他们是礼乐仪式的组成部分,承担着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但是尽管如此,“文”与“和”的观念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思想的生成与演变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奠基作用。
如前所述,在贵族文化系统中,“文”是指全部的典章制度、礼乐仪式以及官方话语系统。但在后世漫长的文化演进过程中,随着文化分类意识的渐趋成熟,这个概念的外延也逐渐收缩,到了汉代基本上已经不再包含典章制度的义项,仅指文化形式而言了。《淮南子》云:“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则乐,乐斯动,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歌舞节则禽兽跳矣……故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所以饰喜也;衰绖苴杖,哭踊有节,所以示哀也;兵戈羽旄,所以饰怒也。必有其质,乃为之文。”(《本经训》)这里的“文”是指表达情感的各种形式。贾谊《新书》云:“夫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文。”(《容经》)这里的“文”是指仪式和言辞。王充《论衡》云:“世称力者,常褒乌获,然则董仲舒、扬子云,文之乌获也。秦武王与孟说举鼎不任,绝脉而死。少文之人,与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将不任,有绝脉之变。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死於烛下,精思不任,绝脉气减也。”(《效力篇》)这里的“文”是指文章和文才。
魏晋六朝士族文人对“文”中本有之“文采”之义最为重视,经过著名的“文笔之辨”以后,“文”就进一步成为歌诗辞赋等有韵之文的专名。昭明太子萧统的一部《文选》,进一步确定了“文”的范围,基本上为后世文人所认同。到了唐宋之后,“文”与“道”的关系成为文人士大夫关注的焦点,就最基本的用法而言,“文”已经成为中国古代诔、铭、序、跋、书、论、表、记等各类文章与诗词歌赋之总名了。就现代以来从西方引进的“文学”观念言之,中国古代的“文”之外延显然是过于宽泛了,但就审美意义而论,则中国古代这一“文”之传统延绵三千年而不衰,是值得美学史、文学史大书特书的(15)。
至于“和”,在贵族趣味中主要表现为对音乐的审美诉求,而到了后世就渐渐演化为“温柔敦厚”的审美风格,表现于诗词歌赋、各类散、韵文体以及琴棋书画等一切艺术形式之中,成为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基调,此一现象久已为学界共识,这里不复赘述。
三 “文统”之形成
上述之“文”当然不是今日所谓“文学”,“文”的趣味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审美趣味”,但这种“文”的趣味却在中国古代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在很大程度上是规范与引导中国文学艺术发展演变的基本精神旨趣。这主要表现在“文统”及相关观念的形成上。
所谓“文统”就是“文”生成演变的历史统绪。古今学界历来有“道统”之谓。“道统”的观念造端于孟子,韩愈继其后,列尧、舜、夏禹、商汤、周文、武乃至周公、孔子之统绪。北宋儒者,如王禹偁、穆修、石介、程伊川等许多人均有此一观念,只是具体排列则互有出入。然“道统”一词则出于朱子。其云:“若只谓‘言忠信,行笃敬’便可,则自汉唐以来,岂是无此等人,因其道统之传却不曾得?亦可见矣。”(16)又“《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17)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更有“道统、学统、政统”之说(18),其“道统”说乃承孟子、韩愈及宋儒而来,指儒家“德性之学”的统绪;“学统”乃指古代“义和传统”,即“天文律历”之类的学问统绪;“政统”则是指“‘政治形态’或政体发展之统绪”。自牟宗三之后,“政统”与“道统”之说基本上为海内外学界所认同,常见于海外新儒家与大陆儒学研究者的著述之中。
除“政统”、“道统”之外,复有“文统”之谓。其说古已有之。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云:“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颜真卿:“公风裁征明,天才杰出。学穷百氏,不好非圣之书;文统三变,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气上跻而高情四达……”(19)元好问:“……胄子渐礼让之训,人士修举选之业,文统绍开,天意为可见矣。”(20)钱谦益:“世咸谓孔子以删述接千古帝王之道统,公独阐其终身任文统不任道统……”(21)清方宗成:“标名家以为的,所以正文统也。广取诸家,所以扩学识也。”(22)这里的“文统”都是指文章统绪而言。这说明,自六朝以降的文人们看来,“文统”实堪与“道统”并行而不悖。倘溯其源流,则“文统”与“道统”一样,亦以“五经”为嚆矢,《文心雕龙·宗经》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章学诚云:“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知文体备于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于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于《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23);“战国之文章,先王礼乐之变也。……后世之文体皆备于战国,而《诗》教于斯可谓极广也。……学者惟拘声韵之为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喻,抑扬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是以后世文集繁,而纷纭承用之文,相与沿其体而莫由知其统要也”(24)。
诸子百家为代表的“战国之文章”是中国古代“文统”形成之后的第一次辉煌表现。古人历来有“诸子出于王官”之说,现代学者则多有质疑。盖刘歆、班固等以诸子各家分别与某一官守相比附的做法的确过于机械,实难令人信服。故胡适等人的驳斥是可以成立的。但因此而忽视诸子之学与周代王官之间的紧密联系则亦大谬。近人刘师培即揭示文章与周代“清庙之守”的密切关系,其云:“盖古之文词,恒施祈祀,故巫祝之职,文词特工。今即《周礼》祝官职掌考之,若六祝六词之属,文章各体,多出于斯。又颂以成功告神明,铭以功烈扬先祖,亦与祠祀相联。是则韵语之文,虽匪一体,综其大要,恒由祀礼而生。欲考文章流别者,曷溯源于清庙之守乎!”(25)此说实为精辟透彻之论,无可辩驳。在刘师培先生看来,周人的礼乐制度为“文”的发展与繁盛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那些庄严隆重的祭祀仪式直接导致了韵文的产生与兴盛。从今天的角度观之,祭祀仪式的本质乃是人与神的交流,在这种人神关系中,为了彰显其超越世俗的神圣性质,在言说方式上必然有其特殊之处。于是韵文便适应这种需求而产生。事实上,《周易》中的卦辞、爻辞多是在占卜中使用的韵文;《诗经》中的《颂》诗是在祭祀仪式中使用的韵文,这是周代贵族对诗的最早用法。至于春秋时期大兴于世的“赋诗言志”,则是诗歌的衍生功能。可以说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频繁交往为“文”的勃兴增加了助力。不独诗歌被广泛用于诸侯间的聘问应对之中,而且各类言说也极重雕琢藻饰。刘师培尝言:“东周以还,行人承命,咸以辞令相高(见于《左传》、《国语》者,凡数百事)。惟娴习文辞,斯克受行人之寄,所谓‘非文词不为功’也。若行人失辞,斯为辱国。故言语之才,于斯为盛。”(26)可以说,春秋时期的行人辞令乃是导致战国诸子勃兴的直接原因,而战国诸子之文则开启中国两千多年“文统”之洪流。可见,此一关于文章源流统绪之见解已成为古人共识。于此亦可见周代贵族的精神旨趣对于中国文学史所具有的奠基之功。
“文统”生成之后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使文人士大夫们高度重视一切言说与书写的审美修饰。贵族的言说方式具有文采风流的特点。赋诗、引诗是他们在正式场合经常运用的表达方式。委婉、含蓄、巧妙、博雅都是他们在语言表达时所刻意追求的。贵族的这一特点经过士大夫阶层的接受与弘扬,成为一种影响强大的“文化惯习”,在后世一切言说与书写中显现出来。文言(散文)、韵文、骈体莫不如此。总之,古代知识阶层在书写,甚至比较正规的日常交往的言谈中,都不愿意用民间通行的“白话”,而要用“文言”。对于“文言”产生的原因,古人多以为是为了方便记录与传承。如,清人阮元认为:“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使传久远;其著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27)这种说法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无法说明到了“笔砚纸墨”已然很方便的魏晋之后,文人们何以还乐此不疲地运用文言来书写,而且在形式上愈加讲究了。所以,文言的产生与流传,除了技术层面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还有社会方面的原因,那就是从贵族趣味到士大夫趣味、文人趣味中始终存在的“阶级区隔”诉求。“文”使贵族成为贵族,也使士大夫成为士大夫、文人成为文人。大凡古代知识阶层有所言说,无论是诗词歌赋、诔铭表赞还是书论序跋,不管多么具有实用性,一律极其讲究格式与文采,都可以看作美文——至于美丑妍媸,那就是才情高下的问题了。
注释:
①关于“个体主体”和“集体主体”,是借鉴法国社会学家吕西安·戈德曼的说法,他用“集体主体”指称某社会阶级、阶层、集团的整体性,而用“个体主体”指称人的个别性。参见其《文学社会学方法论》一书,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第114页。
②[法]皮埃尔·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3页。
③[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④关于“贵族时代”之“封建”特征的论述可参考王国维《殷周制度论》、钱穆《国史大纲》第三章、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黻著《中国史纲》第二章、杨宽《西周史》第三编等。
⑤《周书·大诰》:“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周颂·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周颂·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这些周初文献都是周人用以证明自己剪灭殷商,建立周朝乃是上天之意志的。
⑥《周礼·地官·师氏》:“以三德教国子。”郑玄注:“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可知“德”首先是发自内心的道德意识,其次才表现为一种社会行为。
⑦《国语·晋语五》有“言,身之文也”之谓,表明贵族对包括言谈在内的外在表现的高度重视。
⑧《淮南子·齐俗训》:“礼者,实之文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都是在周人的意义上对“文”的理解,强调的是“文”作为政治与文化之形式的性质。后世儒者的“天文”、“地文”之说(见《易传》)乃是在“天人合德”、“合外内之道”之语境中“文”义的衍生。
⑨(11)《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第96页。
⑩参见《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熹《四书集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近人刘师培尝云:“故三代之时,凡可观可象,秩然有章者,咸谓之文。就事物言,则典籍为文,礼法为文,文字亦为文;就物象言,则光融者为文,华丽者亦为文;就应对言,则直言为文,论难为语,修辞者始为文。文也者,别乎鄙辞俚语者也。”(见《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页)
(12)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1页。
(13)参见下列语例:《书·康诰》:“惟民其勑懋和。”《周礼·天官·大司徒》:“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14)表达这一见解的先秦文献很多:《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人以食兆民,周训儿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志也。”《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吕氏春秋·仲夏纪》:“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条也。”
(15)张法教授在“全国第一届文艺学高峰论坛”的大会发言中曾提出我们编撰“文学概论”和“文学史”应该以中国传统之“文”的概念为核心范畴,而不应仅限于西方的“文学”概念,是极有启发意义的见解。
(16)《朱子语类》卷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5页。
(17)朱熹:《四书集注》,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1页。
(18)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88—99页。
(19)颜真卿:《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颜鲁公集》,四部丛刊本,卷十二。
(20)元好问:《重修真定庙学记》,《遗山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卷三十二。
(21)钱谦益:《朝列大夫管公行状》,《牧斋初学集》卷四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1页。
(22)方宗成:《〈桐城文录〉序》,《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7页。
(23)(24)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第25—26页。
(25)刘师培:《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见《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
(26)刘师培:《文章学史序》,同(25),第222页。
(27)阮元:《文言说》,《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第100页。
标签:政治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贵族等级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先秦时代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国语论文; 周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