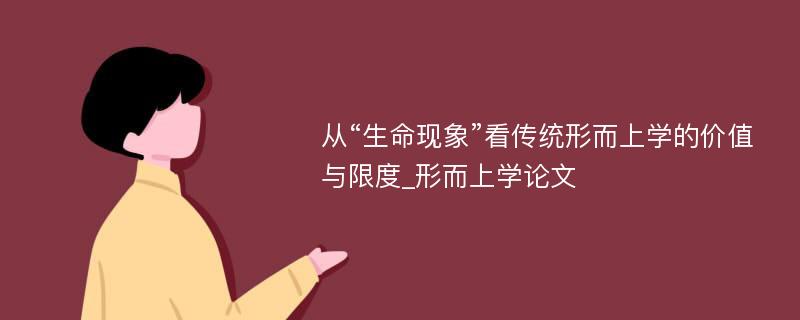
传统形而上学的价值及其限度——从“生命现象”的视角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学论文,视角论文,限度论文,现象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作为“理论体系”的形而上学与作为“生命现象”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构成了传统哲学的核心,这一点恐怕不会有什么疑问,在此意义上,反思传 统哲学,实质上就是反思形而上学。在反思和估价形而上学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理 路。一种是从思想和理论体系的角度来把握形而上学,另一种则是把形而上学理解为一 种“生命现象”。作为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形而上学”是与“知识论”、“伦理学”等 相区别的、以超验“存在”为研究对象的一种专门的理论类型和哲学形态,它有着自己 特定的问题和专门的研究方法,是哲学史上哲学家们最钟情的研究领域。作为“生命现 象”的“形而上学”,则是一种表达着人们渴求超越“未成年”的幼稚状态、憧憬和追 求自身“成熟状态”或“理想生命”的强烈的生命意志和生存意向,代表着一种人不满 足于有限的、不完美的生存状态而追求无限的、完美的生命存在状态的心理定势和生命 冲动。在这个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所表达的是,人为了升华自我,以理论形式所表达 的那种人对自我生命本性的自觉理解。
在哲学史上,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作为思想理论体系的形而上学中,贯注着人 们对“理想生命”的理性设计、情感投射和精神寄托;而作为“生命现象”的形而上学 ,也通过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形而上学得到集中而系统的体现。但是,二者又能够、而且 有必要相对地区分开来。人们常常仅从思想理论体系的角度去理解形而上学,结果它作 为一种特殊而深刻的“生命现象”的意义被繁复的概念之网和宏大的理论外壳深深覆盖 而得不到彰显。把二者相对区别开来,将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形而上学与人的生命存在之 间的深层关联,洞察到形而上学概念之网和理论外壳背后所蕴涵的生命涌动,从而对形 而上学达到一种更深层次的把握,并为理解和评价形而上学提供一个坚实的坐标和参照 。
形而上学的最早形态是古代“神本形而上学”,古代哲学家企图否定和超越“现象世 界”,去寻找一个更“本真”的世界,由此导致的理论后果便是出现了“两个世界”的 尖锐对峙:本质世界与现象世界、真相世界与假相世界、超感性的理性世界与世俗的感 性世界、灵魂世界与肉体世界,等等,哲学由此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双向度的领域,即“实在界”——人与物本质地存在着,“现象界”——人与物非本质地存在着。以此双向度世界为基础,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和深度模式:存在与非存在、现实与潜 能、实是与应是、真相与显相等由此相应而生。在这种“异常思”背后,所蕴涵的正是 对“人的成熟状态”和“理想生命”的憧憬和梦想。分裂世界意味着承认现存世界是“ 不真实”、“不完善”的;分裂世界去寻求一个“本原”和“本体”的世界,意味着对 一个至善的世界的渴望。在它看来,现存的一切并不是按其“本来面目”存在的,它与 其“所应是”是相矛盾的,因此,现存一切必须被超越和改变,以回归和实现其“应当 所是”。于是,“现象”必须趋向“本质”,“现存”必须趋向“应当”,“显相”必 须趋向“真相”,“潜能”必须趋向“实现”……马尔库塞说得好:哲学“按照真理来 思考就是答应要按照真理去生存”,哲学“寻求正确的定义、寻求善、正义、忠义和知 识的概念,于是变成一项颠覆性的事业,因为所要寻找的概念意指一种新的城邦”(注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120页。)。在此意 义上,虽然它所悬设的“本体世界”属于这个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但它在实质 上是人现实的生存愿望和生存冲动的外在投射,表达了不断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否定现存 世界,从而不断超越现状的“生存论冲动”。在它对“本质”和“本体”的描画中,所 蕴涵的是对人的生命的理想形象的承诺,即对自身“成熟状态”的自我理解。
“主体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在近代的表现形态,它试图通过揭示人的“主体性”来 实现对“人的成熟状态”和“理想生命”的自我理解。在它看来,人要达到“成熟状态 ”,最重要的是驱除外在实体的统治,而把自身确定为真正的实体。为此,近代哲学的 根本目标就是要把以异在的方式投射到超验实体中的人性内容收回到人身上。由于“上 帝”观念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异在化”,因此,近代哲学的根本任务又可以概括为“上 帝的人本化”,即要把“神本形而上学”对神圣形象的顶礼膜拜,变为“天上地下,唯 我独尊”的人的“主体”力量。而“主体”作为“主体”的特质,就在于他的“理性” 。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规定,也是人能实现“自我救赎”、达到真正“成熟 状态”的最可靠的手段和工具。虽然对理性的具体理解各不相同,但通过“理性的自觉 ”使人摆脱不成熟的稚童状态,成为一个可以支配自身命运的有力量的成熟的“主体” 则是其共同的诉求。人的这种主体地位体现在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世界的“图像化 ”,它设想在这种“图像化”中,“合理生活形式的设计同合理控制自然及动员社会力 量结合成一种幻影式的共生体。在生产力中脱缰而出的工具理性,各种组织和计划内容 中展现出来的功能主义理性,被认为应当开辟出达到合乎人的尊严的、平等而自由的生 活的道路”(注:哈贝马斯:《新的非了然性》,载薛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附 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人的这种主体地位体现在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 人能够在社会公共事务中运用自己的理性,让自我判断、自我思考成为每个人在社会生 活中的主宰,就像柏林所说的:“我的生活和决定,依靠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外部的什 么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工具,而不是别人的工具,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我希望成 为一个主体,而不是客体;我希望由我自己的理性和我自己的自觉意志来推动,而不愿 受强加给我的外部力量的驱使”(注:转引自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分析与批判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人渴望长大,渴望摆脱“未成年”的幼稚状态,形而上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 以一种凝聚的方式表达着人的这种强烈的渴求。这一点构成了形而上学最深层的底蕴, 无论“神本形而上学”还是“主体形而上学”,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二、“人的成熟状态”的憧憬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摆脱人的有限的、不完美的状态,寻求超越性的“人的成熟状态”和“理想生命”的 自我理解,这一点构成了作为“生命现象”的形而上学的深层动机和内核。纵观哲学史 ,我们看到,形而上学的这种生存论冲动是通过一种特定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表达 出来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如下特点:
1.它把寻求终极实在、最高实体和事物的“最后本质”作为人的思维和生存的最高宗 旨和目标。在它看来,“存在有或者必定有一些永久的与历史无关的模式和框架,在确 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行和正义的性质时,我们可以最终诉诸这些模式和框架 ”(注: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发现这种终极的实在与永恒的框架,从而为我们的认识、行 动和生活奠定一劳永逸的基础。因此,认识和理解事物,关键在于超越“相对”、“偶 然”和“历史”,而找到“绝对”、“终极”和“永恒”的东西,惟有绝对和永恒的东 西,才是真正的“知识”,因而也才是“真理”之所在。这种绝对,在古代体现为“神 ”,在近代体现为拟人化的“主体”。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属于一种超历 史的、绝对化的基础主义的思维方式。
2.它把寻求单极统一性的“一元化原则”当做解决思想和生存问题的最根本保障。传 统形而上学的全部合法性都奠基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等级模式之上:超感性的“实体”一 极所代表的是本质、真理、理性、独立、必然、至善等,感性“现象”一极所代表的是 偶然、无常、被动、不真、卑污等。这两极之中,前者是主宰性、支配性和决定性的, 后者是从属性、依附性和次要性的。因此,前者有充分的合法性来统治后者,后者必须 无条件地服从前者并以前者为最高目标。在思想和行动时,重要的是否定和抛弃后者, 形成以前者为绝对中心的单向格局。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是一种在两极对立关系中寻 求一元统一性、在二元等级关系中寻求单极绝对权威的思维方式。
3.它把寻求非时间、非语境的“非历史”的、“永恒在场”的“本真存在”作为思维 和生存的最高支撑。在传统形而上学看来,超感性的实体是在“时间”之外的“非历史 性”存在,“非时间”、“非历史”的存在才是可靠、真实的,而历史与时间中的存在 不过是飘泊无根的幻象。因此,“历史性”与“时间性”是终极实在的敌人,超越时间 和历史的永恒才是思想和生命的归宿。必须“杀死”“时间”,“消灭”“历史”,把 历史之流中的一切还原为与时间无关的永恒在场者,人的知识、行动和生存才会获得充 分的合法性并因此逃避“怀疑论”的质疑,人的生活才会获得内在的坚定性并因此逃避 “虚无主义”的威胁。
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其中所贯注的是它对“人的成熟状态”形象的 自我理解。
首先,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绝对主义原则”所隐含的是:“成熟的人”应该是一种 超越有限性、不完善性的“圆满”、“无限”的存在者。有限和不完善乃是人“不真” 的存在样式,必须超越这种“不真”,去“发现”人“本真”的、避免了一切限制和瑕 疵的神圣生命。古代神本形而上学把人的这种无限和圆满形象投射为人之外超感性的实 在,它意味着一个无限圆满的“神学世界”。这个“神学世界”是一个理想化的纯粹的 属人世界,它完全摆脱了事实性的、因果世界的有限性和不完善性,是一个完全应然性 的至善至美的终极王国,置身其中的人可以彻底跳出因果性的羁绊,超越有限现实的支 配,达到了一种绝对自由、完善的人格和生活。近代主体形而上学把人实体化,人被理 解为纯净透明的理性实在,一切生命的冲突和纷争、一切现实的局限和矛盾,都在理性 力量之下被中介和溶化,纯粹理性化的生命成为自足、自因因而彻底自由的“主体”。 无论在神本形而上学还是主体形而上学中,“圆满”而“无限”都构成了人的成熟的理 想生命的特质。
其次,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非历史性”隐含的是:“成熟的人”应该是一种超越历 史和时间的“永恒”、“终极”的存在者。按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历史和时间是人 “成熟的理想生命”必须予以摒弃的“囚笼”。对人而言,历史和时间意味着束缚和局 限,超越历史和时间,去成就永恒而终极的生命,是真正符合人的“本性”的使命。海 德格尔曾把形而上学的这种时间观称为“现在时间观”。它在古希腊存在论那里即已形 成,亚里士多德是其奠基者和完成者,并一直延续到黑格尔(注:参见海德格尔《存在 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01~510页。)。这种时间观意味着,人乃是一种“ 永恒在场”的特殊存在者,它置身于时间和历史之外,却能掌握历史和时间中的存在者 。古代神本形而上学把人的这种“永恒现时性”投射于神化的实体,其最根本的特质之 一即是“不动”和“常驻”。在近代主体形而上学那里,人更被自觉地确立为不为感性 现象所动的先验实体,“先验”意味着他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逻辑上的在先者。
最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总体主义原则”所隐含的是:“成熟的人”应该是排除 了矛盾、冲突和磨擦的“通体透明”的绝对和谐的同一性统一体。按照形而上学思维方 式,矛盾、冲突和磨擦乃是人性幼稚和不成熟的表现,它意味着人受外在力量的控制, 处于分裂状态,只有超越冲突,化解矛盾,实现人格的绝对同一,达到人性的和谐统一 ,才能通达理想成熟的人生。古代神本形而上学中的绝对和谐同一性的超验的感性实体 ,所表达的就是对理想生命的这种理解和信念。近代主体形而上学中的主体之为主体, 一个重要标志正在于它的凌驾于一切矛盾和冲突之上的人格的绝对和谐和同一性。
可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表现的每一个特征,都对应着其对“人的成熟状态”的设 计和憧憬。可以说,它们是关于人的“理想生命”最集中的理性映照。
三、“梦想”的价值与边界
做梦是人生活的一部分,形而上学正是这样一个梦,一个渴望“人的成熟”和“理想 生命”之梦。
对于这个梦想,19世纪末以来的西方哲学众多流派虽然主张各异,但大多对之采取拒 斥态度,温和者称之为“迷梦”,激烈者视之为“梦魇”,极端者斥之为“噩梦”。“ 拒斥形而上学”、“后形而上学”等,已成为我们时代的哲学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主题之 一。
联系前文内容,我们不难看到,评价形而上学的关键,在于究竟如何看待形而上学关 于“人的成熟状态”的理想及其建构这种理想的思维方式,在于反思形而上学对于“人 的成熟状态”的追求及其追求方式,以及今天究竟应该如何评价。
我们认为,形而上学关于“人的成熟之梦”所具有的价值是不能简单予以抹杀的。从 历史上看,在人追求成熟的过程中,这个“梦”曾经切切实实地产生过重大的推动作用 。它作为内在于人的成长过程并促进人的生成的一种内在力量,有力地促进了人走向成 熟的进程。面向未来,如果人类把形而上学的这种梦想置于一定的范围和界限中,它仍 将发挥其巨大的精神力量,成为引领人们去过一种自律的、有尊严的生活的重要精神资 源。
形而上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启蒙”力量而产生和演化的,它曾承当着“去 伪解蔽”、把人从蒙昧和教条中解放出来的重大功能,并因此对人的自我提升产生过重 大的历史作用。形而上学的诞生,把人从原始宗教神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以一种理 性的方式去寻求人与世界的终极解释,这标志着人开始自觉地思考“何为人的成熟状态 ”、“何为人的理想生命”。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原初动机是欲启“神性”之“蒙”, 把人从教条化和经院化的“神本形而上学”以及中世纪宗教神学的专制下解放出来,以 “人”的“主体性”来代替“神”的“实体化”,今天人们常以“主体的觉醒”来概括 它所具有的解放意义。可见,无论是神本形而上学,还是主体形而上学,在历史上都曾 发挥着引领人摆脱受制于独断力量的幼稚状态、推动人走向成熟的作用。我们可以像尼 采一样批评柏拉图主义是“僧侣主义”,可以像柯拉柯夫斯基一样批评笛卡尔等是“形 而上学的恐怖”。但如果我们将其置于历史的坐标,难以否认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的形而上学是人类迈入文明门槛后第一次重大“思想解放”运动的理论表现和结晶, 他们关于“人的成熟状态”的思考,标志着人类第一次行使自由理性和意志,去反思和 追寻“理想生命”的内涵和实质。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形而上学是中世纪以后对“何为人 的成熟状态”的再次反思,它对个体的独立性、理性的自足性、意志的自由性等的阐发 ,有力地祛除了神学独断力量的魔咒,使“个人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这对 于个人脱离种种超人的神圣实体的专制,摆脱受外在权威监护的“未成年状态”,具有 不可否认的历史功绩。
与此内在相关,形而上学曾代表着一种以自我反思和批判否定的方式,引导人们从现 有规范束缚中摆脱出来的“自由精神”。通过自我反思和批判否定,不使人的心灵的怀 疑、创新和开拓精神昏睡,而使人永远保持自我创造与自我超越的自由精神,这是哲学 最为宝贵的品性,在历史上形而上学正集中地表现了这种品性。今天人们更多地看到了 形而上学教条、独断的一面,却常常忽视了形而上学曾发挥过的这种作用。但如果采取 一种历史的眼光,我们就必须承认,通过“反思”、“批判”、“超越”,来确证思想 的自由和人的尊严,乃是形而上学的深切眷注。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我们认取哲学为 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页。)。黑格尔同样说道:“哲学的出现属于自由的意识,在哲学业已起始的民族里必以这自由原则作为它的根据”,“思想必须独立,必须达到自由的存在,必须从自然事物里摆脱出来,并且必须从感性直观里超拔出来。思想既是自由的,则它必须深入自身,因而达到自由的意识”(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3~94页。)。自由的批判和否定精神乃是形而上学留给哲学最珍贵的遗产,即使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这份遗产仍然是哲学在反思和推进“人的成熟状态”这一根本事业时所不可缺少的。
最重要的是,形而上学本身凝聚着一种激励人们不断“超越自我”、摆脱“未成年” 的幼稚状态、追求和创造理想生命和成熟人生的“乌托邦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人类文 明的发展曾产生过巨大深远的激励作用。在今天,只要人们仍然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这种精神依旧是不可“解构”的精神财富。人的存 在是自我意识到的存在,人的本性是人的生存活动中自我创生的本性,人总是渴望不断 “长大”,从“幼稚”走向“成熟”,在这个意义上,人也就离不开“未来”的向度。 而“未来”作为人的理想,在形而上学中得到了最为深沉的思考和最为集中的表达,它 要求人们克服自身的自然惰性和对现实的消极默认,启示人们不要放弃这样一种希望— —去寻找一个先前不曾有过的世界,在那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注:柏拉图:《理 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3页。)。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奠定这种“乌托邦 精神”的经典形态开始,这一精神就源远流长,成为哲学发展最为根本的动力。即使在 今天那些具有“反形而上学”倾向的哲学家那里,“形而上学”所具有的这种“乌托邦 精神”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延续和表现自身。我们不能否认,这种“乌托邦精神”构 成了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对于人不断摆脱种种强加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实现“自 我启蒙”,具有重大的价值。
当对形而上学的价值做上述阐发时,我们也同时充分意识到,这些积极价值始终是与 其对立面相伴随的,即与形而上学的“反思批判”的“自由精神”相伴随的是形而上学 的窒息批判意识和自由精神的独断主义,与形而上学试图超越“在场”的“乌托邦精神 ”相伴随的是形而上学把“在场”者中心化的权威主义。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是一个 充满内在冲突和悖论的结合体,它的正面价值面临随时被其负面价值颠覆并因此消失殆 尽的危险。这正是现当代哲学对形而上学口诛笔伐的根本原因。然而,当形而上学被当 成“死狗”痛打的时候,那些与人的生命内在相关,与人追求自身“成熟状态”紧密相 联的积极价值,也与脏水一同被倒掉了。
在我们看来,造成形而上学的这种内在悖论和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边界意识”的缺 失。前述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绝对主义原则”、“总体主义原则”和“非历史性原 则”,集中地体现了这种“边界意识”的缺失,这使得它表现出一种无所不在的、“永 恒在场”的具有浓厚独断和专制色彩的绝对“规范性”。作为生命现象的形而上学所欲 表达的本来是人不断超越自身、去创造理想生命的“梦想”,前述的启蒙精神、反思批 判的自由精神和乌托邦精神,正是这种“梦想”的具体体现。然而,这种强制的、绝对 的“规范性”,却恰恰是以窒息“梦想”、抹平“超越”、抑止“自由”、拒绝“批判 ”为意向的,它的“总体性”、“绝对性”与“非历史性”诉求削平和压制了一切超越 它的冲动,形而上学于是变成一个终极的绝对静止的体系。由此造成的最严重后果便是 :推进对“人的成熟状态”和“理想生命”的自我理解,本来是形而上学的基本出发点 ,然而却因为其包含的内在缺陷,恰恰成为了人仍然处于“幼稚状态”的最好证明。
人渴望走向“成熟”。形而上学的“幼稚性”表明,人们必须寻求一种真正能够表达 “人的成熟状态”的“成熟”的理论意识,这种新型的理论意识即是“边界意识”。通 过“边界意识”的确立,将有力地摒弃形而上学的与“人的成熟状态”追求相悖逆的独 断、专制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并使其正面价值在一种特定的边界范围里得以延续和 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