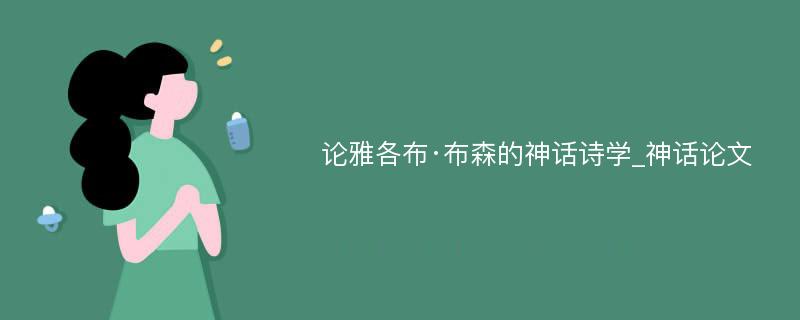
雅可布逊的神话诗学研究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神话论文,雅可布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兴起的结构主义文艺学方法“跨越了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疆界,扩展到诗歌、小说、戏剧等所有的文学形式中去,促使文学研究从经验层次深入到非经验的深层结构层次,从意识层次进到无意识层次”[1](6)。毫无疑义,结构主义神话学为文学阐释开拓了新的领域。但我们也常常发现,这种方法真正应用到文学批评,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神话学批评则一般是以叙事体裁居多,主要是针对民间创作和小说作品的神话学诠释。在文学批评界,涉及诗歌的神话学分析的文艺学力作还是凤毛麟角。应该说,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罗曼·雅可布逊在结构主义神话学领域可以称得上诗歌的神话学批评的先驱者之一。众所周知,他的诗学思想甚至影响过法国著名结构主义神话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思维和神话的探索[1](49)。可以说,雅可布逊在20世纪30年代对一系列诗歌作品进行内在的结构分析和神话学阐释,在同当时盛行的无论是庸俗的传记主义文学批评还是反传记主义的形式主义诗学的论辩中,可谓独领风骚。雅可布逊在60年代同其夫人克里斯蒂娃·帕穆尔斯卡的《对话录》中曾这样写道:“话语和雕塑、相似与相邻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符号学问题,以及关于俄国精神传统中对作为偶像的雕塑的认识问题,引发了关于艺术符号学和关于符号学与神话学关系的新思想”。[2](555)而对于雅可布逊来说,这种新思想的诞生就在于,将现代诗学研究置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框架下,为分析诗歌作品创立了语言学诗学的批评方法,也为诗歌的神话学研究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一、雅可布逊的神话诗学观
雅可布逊早在20世纪30年代曾极富有远见地指出,“对艺术家个性化的神话进行重构是科学的首要任务”[3](146)。在雅可布逊的学术生涯中,他曾对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等创作中的神话与诗人的生平之间的联系进行过专门的精辟的探讨。他的神话诗学研究极富特色,既有对诗歌神话的内在结构的分析,也伴随着对诗人生平传记的深层含义的解读。作为科学研究的客体之一,传记被雅可布逊巧妙地运用到诗歌创作的个性化神话的诠释当中。美国学者R.布莱福德在评价雅可布逊这一诗学研究的贡献时就说过:诗人、文本和语境“三者关系模式被应用到特定诗人的生平和作品研究中,这种实践是极其复杂而富有创意的。”[4](177)为了证明自己的内在的结构分析原则适用于各个时代甚至是不同的民族的诗歌分析,雅可布逊提出不能忽视对文学的外部背景的内涵阐释的观点。他研究俄国的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和勃洛克等诗人诗歌作品中的神话就是在结合对诗人生平的神话学阐释情况下进行的。雅可布逊认为,要想掌握一位诗人的象征体系,首先要找出构成这位诗人神话学的那些常用的象征结构;同时还要考察诗歌话语与语境的相互关系,且不是人为地孤立诗歌的象征,而是使这些象征与作品的整体结构和诗人的生活背景加以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这种分析可以揭示诗歌中神话的基本常量,而这些常量恰是在诗人的创作中实现的,是与诗人的个人生活事件密切相关的。这些恒常的、有组织的元素就构成了诗歌作品的统一的载体,打上了诗人个性化的烙印。正是这些元素“使普希金的诗歌成为普希金式,马哈的诗歌成为真正的马哈式,而波德莱尔的诗歌是波德莱尔式的”。[3](145)雅可布逊还确信,“诗歌和神话是既彼此依赖又有着尖锐冲突的两种力量”,二者的差异就在于“诗歌指向于变量,而神话则指向于常量”。[2](557)由于诗歌中神话是建立在相同和差异、相似和相邻的彼此对立之中,所以神话和诗歌的关系应从不同的层面来考察,神话既是诗歌中公开表现出来的各种“变量”,也是已流传下来的具有潜在个性的各种“常量”。
我们知道,雅可布逊对诗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为文学研究确立了形式和结构的本体分析方法,而且还把文学研究引领到更为广泛的符号学考察文本之路径,是最早在作者维度上融进了文本和读者等多维度解读文学的文艺学家之一。他认为,如果一位诗人的主要基调能够深入读者的意识并能控制读者,那么这位诗人的诗歌形式就会被他人接受,其诗歌的基调在日后就会被多次重现。这就意味着,诗人在读者的意识中植根得越深,他的崇拜者和反对者就会越适应于该诗歌的声响,就越难以把这些独特的元素从诗人的作品中割舍出去。就像基调作为话语的基础一样,它们是诗歌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此,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说读者能凭借直觉感知这些固定的恒常的元素,那么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循着这种直觉,通过内在的分析直接从诗歌文本获得这些恒常的成分(常量),而如果是变化的成分,那么就应明确在这种辩证运动中哪些成分是合乎规律的和稳定的,找出变量的基础”[3](145)。
神话,在远古时代是指讲述的故事和各种传说;在近代则是指关于传说中的英雄,关于创世和大地上生命起源的民间传说;在20世纪神话又被看成是超越时代、跨越历史的一种现象,它存在于各个民族的生活和社会意识进程中。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将各种神话意象或原型用于一定的艺术目的,其中有民间传说的、宗教的、英雄的,社会乌托邦的,不一而足。文学的神话有集体永恒的,也有作者个人的。文学的神话与创作者的个人生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生活阅历和审美取向的不同,文学创作者的神话图景,以及他们对人类的神话创作经验有着不同的创造性的继承。关于诗歌、神话与诗人生平的关系问题,雅可布逊在《对话录》中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将自己的方法与纯粹的传记主义以及脱离于传记研究的形式主义加以区别。他在研究普希金诗歌中雕像的神话时曾开门见山地写道:“当然既不能陷入庸俗的传记主义中,即它通常把文学作品看做是对情境的复制,认为作品是从中而产生的,并且从作品中生发出这样或那样的事件;也不能落入反传记主义窠臼之中,教条地否认文学作品和生活背景之间的任何联系”[3](146)。下面我们就基于雅可布逊在《耗尽了自己的一代诗人》(1930)、《普希金诗歌中雕像的神话》(1937)及《亚·勃洛克诗歌的预言》(1981)三篇论著中的神话诗学观,对雅氏关于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和勃洛克三位俄国诗人诗歌中的神话进行解析,并对他们的诗歌神话与诗人生平的关系做进一步的补充性阐释。
二、普希金:“复活的雕像”的塑造者
在普希金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对雕像的大量刻画,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悲剧《石雕客人》、叙事诗《青铜骑士》和童话《金鸡的故事》这三部作品,而且在这三部作品中每一部都是他不同体裁创作中的最后一部:《石雕客人》是最后一部戏剧,《青铜骑士》是最后一部叙事诗,而《金鸡的故事》则是最后一部童话。从普希金的创作中可以看出,雕塑的形象是普希金特有的象征财富。为此,雅可布逊撰写了《普希金诗歌神话中的雕像》(1937)一文,运用结构主义诗学和符号学原理,对包括以上三部作品在内的雕塑这一神话形象做了富有说服力的阐释。
从这三部作品的名称上看,它们所表达的都不是“活着的人”,而是看似静止实为“致命的”雕塑,而且每个故事的修饰语都说明了每个雕塑的材质:“石雕的”、“青铜的”和“金制的”。其中,《石雕客人》的名称表明骑士团统领的雕像就是悲剧中的主人公;《青铜骑士》的名称则把凡尔孔奈的作品——彼得一世的纪念碑作为叙事诗的主人公;而达顿国王虽然在作品开头就已出场,但也不是中心人物,金鸡才是童话情节的载体。所以,这三部作品的共同点就在于主人公的典型性以及作品情节重心的相似性。雅可布逊对每部作品的象征含义概括为:(1)疲倦的而逆来顺受的人渴望安宁的主题同渴望女性相互交织;(2)雕像凌驾于与雕像紧密关联的“活着的人”,并且对心仪的女性具有超自然的、不可思议的驾驭权力:雕像或者是一种偶像、神,或者是某种灵魂、恶魔的体现;(3)人在抗争失败后,由于雕像以神奇的方式参与故事行为而丧命;女性同时也随之消失。[3](148-149)
依据雅可布逊的观点,对普希金作品中雕像神话的内在的结构分析“涉及到一种艺术类型向另一种艺术——诗歌类型的转化”,即雕刻艺术向诗歌艺术的转化。雕像是一种特殊艺术符号,描写雕像的诗歌作品则是“符号的符号”或“形象的形象”。[3](166)没有生命的、静止的、用来塑造雕像的材料与运动的、有生命的人物的雕像呈现出对应的状态,这种对应单从普希金作品的标题上就足以明证:“石雕客人”,“青铜骑士”和“金鸡”。泥土变成了鲜活的形象,雕像的语义层或符号的内在层消解了没有生命的、不能运动的符号的物质层。“双重性是符号存在的必要条件,一旦符号的内在双重性被消解,符号与其所指的客体之间的矛盾性就必然消失”。“雕像虚拟的空间便与现实的空间发生融合。”[3](167)现实的雕像参与到艺术事件的时间连续中。
雅氏认为,普希金神话诗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二律背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作品符号与所指客体的相似与差异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在普希金的作品中,雕像符号既是符号的主体也是具有意义的客体,故而符号又成为主题成分,伴随着内在的二律背反式矛盾。譬如:雕像的“静止”和“运动”就是普希金象征诗学中具有二律背反特性的重要主题之一。静止和运动的关系在普希金的作品中时而是本体和经验之间的哲学矛盾,时而又是雕像材料与雕像所反映的内容之间的冲突。作为叙事客体和行为主体,雕像与活人的冲突始终是普希金创作的出发点。这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在普希金作品的情节中。因此,普希金作品中的雕像往往是“致命的”,是参与作品行为的唯一固定形式:存在的雕像和消失的人所构成的对照就是这一行为的体现,而追求女性和追求安宁的内在对立则确定了女性在这一行为中的作用。为此,雅可布逊得出,在普希金作品中首要的并不是相似性(模仿关系),而是相邻性(感染关系),诸如死人对雕像的态度,时间与空间的连续性,死人为纪念碑献词[3](171)都具有这种关系。
雅可布逊还着重阐释了普希金神话诗学的另一特征——动态性。雕像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并不是孤立的象征形象,相反,在他的作品中雕像与其它动态的神话形象一起构成了动态的整体。如普希金经常使用的奔流的水的形象。普希金笔下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和“能呼吸的”,一切对象都被看做是运动的。一切生命,无论是宇宙的、个人的还是社会的,都可以看作是连续的过程。这样一来,在普希金的神话诗学中,安宁、静止就成为与生命、动态构成强烈对照的主题,它或以被迫静止的形式出现(如各种囚徒的变体形象:“受安宁折磨的人”,被奴役的人,笼子里的活体等),或者以自由安宁的形式出现(如被雕刻的、超人的甚至是超自然的状态)。如果人的生活是宇宙活动的有力体现,而安宁是对这种生活的否定和偏离、反常,那么雕像却相反,安宁是自然、“无标记的”状态,而它的运动则是偏离于静止的常规。对于神话创作天才的普希金来说,雕像总是要求参与或运动,但由于它本身是静止的,所以它又是纯粹的超自然的、自由的、创造性的安宁的体现。
此外,普希金作品中雕像的多神教特性也引起雅可布逊的极大关注。雅可布逊指出,“俄罗斯诗人——无论是不信上帝的普希金,异教徒勃洛克,还是反宗教的马雅可夫斯基——他们都是在东正教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的创作并不依赖于自己的意愿,而充满了正统教堂的各种象征。”[3](173)但雅可布逊又指出,正是由于东正教传统对雕塑艺术加以严厉批判,不准许这种艺术形式进入到正统教堂之中,认为它是多神教或者是魔鬼的缺陷,所以才使普希金对雕像产生了崇拜,视之为魔力和巫术。对于普希金来说,“静止的思想”的法力就是拥有多神教的联想。在他的作品中,“雕像不仅只是一件雕塑,而是变形为一种超自然的深不可测的力量和偶像”[5](621)。
必须强调的是:在研究中雅可布逊对作品的内在结构分析始终伴随着对作品的深层内涵阐释。关于普希金作品中的雕像,雅可布逊明确地揭示了普希金的神话与其个性及读者理解之间的关系。普希金的私人生活对其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唐璜身上,能看到普希金对女性、母爱的渴望;在普希金的《石雕客人》中,达顿国王这一人物角色融合了现实生活中普希金的敌对人物,例如亚历山大和尼古拉的一些特点。雅可布逊以雕像这一符号作为象征中介,将普希金的作品和普希金个人生活加以联系,从而使普希金作品中符号化的雕像与现实的雕塑之间形成冲突和对立,展示诗人对现实和理想连续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如前所述,“静止和运动”不仅成为普希金作品情节的一部分,还是普希金作品的主题成分,表达普希金关于青铜雕像(“创造出来的神奇”)和骑士彼得(“奇迹的创造者”)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马奔跑在“震动的马路上”,把手伸向汹涌的浪涛;而策马而立的骑士的静止则体现出青铜主人公在自然灾害和暴动面前永恒的威力。彼得一世在凡尔孔奈建造的纪念碑上,一方面,是不动的,永恒的捍卫者,他用冰冷的面孔阻挡敌人的侵犯;另一方面,他准备从险峻的石头上向敌人进攻。同时,被神化的雕像形象还体现了普希金关于生命延续的观念:“生命的思想蕴含在雕像的意义之中,雕像外形所表达的延续的思想融合在生命延续的形象之中。”[3](169)纪念碑中已故的彼得“永远的梦”和他的青铜同貌人永远的安宁之间的平衡,以及他的尸骸的昙花一现和他雕像的永恒性之间的冲突,引发着雅可布逊对所雕刻的物质进行生命的思考。正如美国学者R.布莱福德所评价的那样,“普希金对雕像的处理手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在诗人的神话世界中凸显了文本和语境这两个维度之间的相互依赖性”[4](178)。
三、勃洛克:“意外的喜悦”的歌唱者
神话几乎贯穿勃洛克所有的诗歌创作。早期创作中的神话是永恒的女性温柔,而长诗《十二个》则是勃洛克全部诗歌主题的结束,也是其神话创作的终结。关于勃洛克的神话题材,P.雅可布逊发现,《骑士团长的脚步》明显继承了普希金观念中恋爱的唐璜、悲剧性消失的多娜和“沉重的脚步”等情节;而组诗《城市》中勃洛克呼唤的则是对钢铁彼得的永恒生命的记忆。[3](173)勃洛克的诗歌既充满多神教情节,又具有独特的东正教意象,其作品中的神话大多是宗教性质的。关于勃洛克诗歌的宗教神话特性,P.雅可布逊则撰写了《亚·勃洛克诗歌的预言》(1981)这篇颇有分量的文章,对勃洛克的《少女在教堂唱诗班里的吟唱》一诗进行了多层面的探讨。
P.雅可布逊首先从形式角度对这首诗的语言体系进行了分析,继而又转到了内容层面,特别是对这首诗的“正统教堂的象征意义”和“教堂文献”进行了探源。其实,这种对诗歌文本的“正统教堂”因素的分析,恰好是与普希金的创作中具有多神教特征的雕像的象征意义相悖的。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看出,在俄罗斯诗人创作中多神教因素与东正教因素始终是并行而存的。为了说明这一点,雅可布逊在着手分析勃洛克这首诗作时再次重申了他在《普希金诗歌神话中的雕像》一文中所阐明的观点:“俄罗斯诗人——无论是不信上帝的普希金,异教徒勃洛克,还是反宗教的马雅可夫斯基——他们都是在东正教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的创作并不以自己的意愿为转移,而是充满着正统教会的象征。”[3](173)
在该首诗的第一诗节中,明显地体现出勃洛克这种正统教堂情结:“Девушка пела вцерковном хоре//О Всех усталых в чужом краю, //О всех кораблях,ушедших в море,//О всех забывших радость свою.”在这里,与教堂情结同时并存的是诗人关于神秘的大海和船舶所具有的无穷魔力的感受。驶向大海而一去不归的船舶和教堂里祈祷中合唱,大海和教堂、遥远和近距等画面交相辉映,多神教和东正教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在第二诗节中,透过教堂里“唱诗班”、“圆顶”、“圣障”等细节进一步表达了抒情主人公对基督教的深层的道德思考:“Так пел еёголос,летящий в купол,//И луч сиял на белом плече,//И каждый из мрака смотрел и слушал,//Как белое платье пело в луче.”在这里,迎着“飞向圆顶的合唱声音”,天上的“光线”映照在“白色的衣衫”上。这种听觉与视觉独特的合一感受不禁使所有的“从暗处凝视和聆听的人们”都聚集为一体,共同投入反复的神圣的联想之中;而在第三诗节中则描写的是教堂以外的画面:“И всемказалось, что радость будет,//Что в тихой заводи все корабли,//Что на чужбине устали люди//Светлую
жизнь
себеобрели.”诗节中的“他乡”、“异邦”、“船舶”等细节暗示了人们寄托于“光明的生活”、“寂静的河湾”和“喜悦”等一切希冀的渺茫。
P.雅可布逊认为这首诗的神话基原之一就是东正教祷告,这是一种被称为“叶克千尼亚”的祈祷:“ О плавающих, путешествующих,недугующих,страждующих,плененных
и о спасении
их Господупомолимся.”雅可布逊凭借直觉发现,第一诗节里少女的祈祷之歌似乎正是对“叶克千尼亚”这种祈祷话语的回应,[3](257)而第三诗节中的“意外的喜悦”一词同样也是勃洛克创作的神话源泉之一,该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圣母祈祷的圣像。在最后一个诗节里我们又看到:袒护者—圣母“为了所有忘却了自己喜悦的人们,从意外的喜悦圣像上来到唱诗班加入合唱中,并向人们宣告喜悦正在降临”[3](259):“И голос был сладок,и луч былтонок,//И только высоко, у Царских врат,//Причастный Тайнам, - плакал ребёнок,//О том,что никто не придётназат.”在这里,少女的吟唱意味着圣母的祈祷,而抒情主人公耳闻目睹着这一切,仿佛沉浸在“甜蜜的声音”和“细腻的光线”之中,只有“孩子”(指“圣子”)独自一人留在圣障旁,预测着残酷的“秘密”(真理),为不归的人们而哭泣。
我们知道,勃洛克文本中的关键词经常有“喜悦”一词,该词语在东正教传统具有特殊的精神的神圣的涵义。正是这一特殊的词语引导雅可布逊将它同“意外的喜悦”,即圣母的形象联想起来。而这个形象是雅可布逊从勃洛克本人于1907年出版的诗集名称和《夜间紫罗兰》(诗中这样写道:“ Чтонечаянно Радость придёт…”)一诗中得到启示的。从勃洛克以往的诗歌创作中可以看出,“意外的喜悦”的圣像意义与勃洛克惯用的“圣母袒护有罪之人”这一主题相互交织,在这种圣像中有罪之人通常是跪在手抱圣子的圣母面前。圣母与喜悦相联系,圣母就是“永恒的喜悦”的体现者和保护者。所以,一切圣典、颂歌、圣母祷告,无论是“悲伤者的喜悦”的圣像还是“悲伤的神圣之母”的圣像,都应该看做是勃洛克诗歌的神话源泉。这些神话在勃洛克的诗歌中反复出现,于是其呼语—修饰语便会发生诸多变体,如“所有悲伤的喜悦”,“被欺侮者们的袒护人”,“渴望圣母的补养”,“漂泊者们的慰藉”等等。勃洛克研究者И.С.普里霍季科曾说,勃洛克作品中有两种关于“所有悲伤的喜悦”的圣母圣像的研究变体:一种类型的圣像中圣母头戴王冠,以神圣的女王形式出现,其左手抱着永恒的圣子,右手握着最高权力的象征;而另一种圣像中则可以看到:她身穿白纱或者双手擎起,呈现出保护者的姿势。这两种变体又都表现为:(1)圣母再现为全身;(2)圣母出现在中心人物的两侧或在人的下方,人们的悲伤由于她的神圣力量而转化为喜悦;(3)她的脸颊和周围闪烁着明亮的光芒。[6](136)
此外,雅可布逊还对该诗中代词的使用进行了联想式分析,指出代词все (всех,всем)在这首诗的单数诗节里反复地重复使用,这不禁“使教堂里的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异乡人的思想融合起来”。[6](136)因此,应该说,勃洛克诗中的圣母形象已经具有了更广泛的全人类的意义。在勃洛克的圣母形象中,悲伤与喜悦( “ скорбящих радость”)永远是统一的概念,这种对立的构思,作为一种整体,已成为他特有的神话的诗学特征,如“Радость - страданье”(喜悦与悲伤),“ Розаи крест”(玫瑰与十字架)等,甚至成为其全部创作的背景。我们认为,诗中少女充当的正是安慰者的神灵,这个形象可以理解为以女性面貌和东正教传统方式出现的圣母。正是少女的祈祷式的吟唱,赋予了大地悲伤以外的喜悦之诺言,而诗歌的悲剧性冲突表现为介于神圣的天国里永恒的喜悦和大地生活的永远的悲伤。
四、马雅可夫斯基:“一代悲剧诗人”的代言者
在早期的《论俄国新诗》(1921)中,雅可布逊从形式主义立场出发,着重描述了俄国未来派诗人赫列勃尼科夫的诗歌语言的内在结构特征,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带有传记主义的“异己的”大杂烩,只是在该书的结尾部分,用雅可布逊后来在《对话录》中的话说,才“从诗人的语言试验转到了诗人对这些实验的感受”,即从作品的内在分析转到了对作者生平的关注。为此,他在该书以及《对话录》中都援引了赫列勃尼科夫文学传记中的一句自白式话语写道:“创作的故乡在未来,从那里刮着语言的上帝之风”。[3](272);[2](547)这句引文表明了雅可布逊对未来派诗人赫列勃尼科夫诗歌语言的兴趣,实际上就始于对这位诗人生活本身的感受。雅可布逊在《对话录》中还肯定地说道:自己在研究赫列勃尼科夫诗歌创作的时候,的确对诗人这句话感到“十分亲近”,并认为这句孕育着“未来”思想的话语“涵盖了诗人所经历的生活”[2](547)。
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后,雅可布逊又撰写了《耗尽了自己情感的一代诗人》(1930)这一篇幅较长的悼念文章,深深表达了“诗人之死”所带来的“剧烈的悲痛”。[7](355)文中指出马雅可夫斯基与赫列勃尼科夫、勃洛克、叶赛宁一样,在辞世前都预见了自己未来的命运:“他已经在用后天的读者的眼睛审视了自己生前的诗行。”[7](357)雅可布逊满怀深情地论述了马雅可夫斯基诗歌中隐含的神话基原,发人深省地揭示了诗人生平所饱含的忧郁和浓烈的悲观主义色彩,敏锐地洞察出马雅可夫斯基在一系列叙事诗里所警示的为了革命精神而奋斗的“一代诗人”的神话。“在诗人心中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同时代人的痛苦”。[7](371)
“Убиты;—/и все равно мне,/я илион их убил.”——这是雅可布逊在文章开头以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写上的题词,它不仅再现了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绝望,而且也表达了批评家雅可布逊对这种绝望的哀思。在雅可布逊看来,马雅可夫斯基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个与时代和环境进行抗争的代表人物,而造成马雅可夫斯基悲剧的根源——这就是“一个受难者”的神话,一个注定要自愿了结自己生命的诗人的神话。著名文艺理论家韦勒克在评论雅可布逊这篇文章时说过:“通常人们知道的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位不主故常的乌托邦空想家,笃信布尔什维克革命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人间天堂而且解决一切矛盾”,而雅可布逊通过诗人的系列诗篇揭示的则是诗人的“绝望的潜流”,这不仅是对人类的未来同时也是对人类真爱的可能性的绝望。[5](621)
马雅可夫斯基一生的创作,从《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到最后的诗行,始终都在辨证地发展着同一象征主题,无论是通过幽默手段还是转到情绪化的讽拟手法,所刻画的形象都是对同一个象征意义的两种模式的再现:一是悲剧的,另一是喜剧的。如:在诗集《我》和叙事诗《人》以及《150.000.000》中,诗人自己扮演着主人公,成为“诗人之我”所熟悉的“一亿五千万”集体中的一员,一个力大无穷的“集合性的伊万”。“诗人之我”是无法穷尽的,也是先验的现实无以囊括的,这个灵魂没有名字,没有父称。“Новое имя/вырвись/лети/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ирового жилья/тысячелетнее/низкое небо/сгинь синезато./Это я./Я,Я /Я /Я/Я/Я/земливдохновенный ассенизатор…”在诗人笔下“大地被窒酷”,伟大的彼得在哀思——这是一个“被束缚在自己城市里的囚徒”,而“诗人之我”则是一个被弃至最后境遇而渴望再现未来、渴望绝对完整之存在的意志:“надо вырвать радость у грядущих дней.”马雅可夫斯基不止一次强调自己追求的现实主义“不是拾人牙慧和模仿现实,而是对未来富有创造性的预见”[2](548),据此,雅可布逊说道:“诗人的糟糕的命运的确被诗人自己预先讲述了”,尤其令雅可布逊难以平静的是,早就熟悉诗人诗歌的包括雅氏自己在内的读者们,都未曾发现也不愿承认蕴藏于这些诗歌中的先见之明,而是在诗人过世后竟充当了诗人讽刺诗中早已预见到的各种讽拟性的角色[2](548)。
对比雅可布逊在1921年和1930年撰写的这两篇代表性文章我们不难看出,他在前一篇文章中强调的主要是文学内在的(即“文学性”)分析的宗旨。譬如:在马雅可夫斯基的Я вам открою словами, простыми,как мычание,/Ваши новые души, гудящиекак фонарные дуги...这两行诗句中雅可布逊把“普通的话语,像牛叫一样”曾称为“诗的事实”,而把心灵视作“第二性事实”[3](275),这表明雅氏在当时关注的只是作为“诗的事实”的话语本身。然而,当马雅可夫斯基去世后,雅可布逊显然又证明了另外一个事实——诗的每一个话语都是用“心灵”和“生命”所换来的。这就意味着,心灵和生命,同诗的话语一样,也成为马雅可夫斯基的重要的“文学手段”之一。在《何谓诗?》(1933)一文中雅氏继续阐发了这一观点:“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中自杀的情节在某些时候被人们当做普通的文学手段”[8](112)。这也许可以理解为,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仿佛“使现实的生命转变成为诗的话语和事业”,正是由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死,伴随着他所经历的生命之路一起,骤然以新的方式引导了作为学者的雅可布逊走上了解读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之谜的道路,使之“诞生了某种关于历史的统一以及自己作为统一体中的一部分的感受”。[9](163)正像雅可布逊在给Hugh Mclean的信中写道的那样:雅可布逊认为自己“有责任说出徘徊的一代人……”。[9](165)有学者认为这句话意味极其深长,因为“一代人”一词,雅可布逊在诗人去世之前从未使用过。[9](163)看来,雅可布逊也同样把这个专门的事业视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种意识使他的个体存在转变到共同的历史进程当中。
在雅可布逊的阐述中,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位为了“未来”同“日常生活”进行不懈斗争的战士。“日常生活”指的是对“牢固的世界秩序”,庸俗的“休闲与舒适”,以及当今一切的“稳定化倾向”。[7](359)“В осень,/взиму,/в весну,/в лето/в день/в сон/не приемлю/ненавижу это/всё/всё/что в нас/ ушедшим рабьим вбито/все/чтомелочинным роем/оседало/и осело бытом/даже в нашем/краснофлагом строе.”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世界中,“未来”已进入其所献身的宗教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革命——这是指全面的精神的反抗,是一种精神演变的隐喻,然而恢复适合于新条件下的“日常生活”乃是十月革命的直接成果。“诗人之我”正是在同这些新条件做斗争中逐渐毁灭的。从本质上看,诗人与日常生活的对立,体现了浪漫主义的二元论传统——受难的诗人与守旧的环境相抗争。诗人革命前的叙事诗《关于这个》和革命后的讽刺剧都体现了这一对立的主题。但诗人在苏维埃时期的诗学遗产部分包括《列宁》和《好!》等叙事诗,雅可布逊则论及不多,似乎有意地避之不谈。有的学者认为,这也许是因为该时期创作与雅可布逊的观点恰好相悖的缘故。[6](210)也有学者认为这部分创作是“马雅可夫斯基的个性化神话的象征模式所发生的不可避免的物质变形”[6](210);我们以为,从这部分遗产也许恰好能看出,俄国未来派代表马雅可夫斯基在自我意识中介于自由和责任两极之间发生了矛盾,这也恰是诗人的悲剧所在。在解决马雅可夫斯基这两种身份(即浪漫主义乌托邦和现实主义的苏维埃)之间矛盾时,雅可布逊似乎在有意识地、有针对性地前后改变着自己的立场,将心灵的理想主义方法同纯形式主义方法并行而用。马雅可夫斯基的这两重身份,还可以在其关于莫斯科工农业的广告诗与《穿裤子的云》中的悲剧之间的对立中可见一斑,它们同样是日常生活与复苏的理想主义之对立。苏维埃时期描写的纯粹日常生活构成了马雅可夫斯基工农业题材的诗歌模式,这也许是马雅可夫斯基在对日常生活的敌视中又在不断地赋予其日常性。
雅可布逊在该文中正像克里斯蒂娃·帕穆尔斯卡所指出的那样,“首次全面展现了诗人有力的身姿,他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无畏地与束缚人性的时空斗争,竭力战胜死神而为未来的全人类赢得不朽。雅可布逊以他的文章不仅揭示了马雅可夫斯基,而且揭示了整个俄国未来派的真正面貌:他们充满着普罗米修斯式的乌托邦幻想:冲向宇宙,战胜宇宙”。[10](445)
标签:神话论文; 诗歌论文; 马雅可夫斯基论文; 普希金论文; 神话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勃洛克论文; 青铜骑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