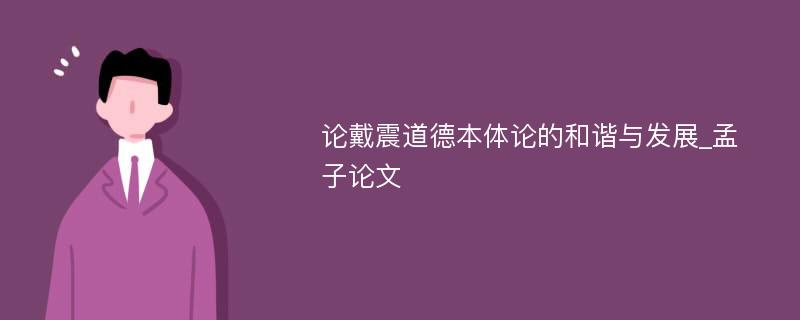
“一本”与“性善”——论戴震对孟子道德本体论的圆融与展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本体论论文,圆融论文,一本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适曾评论说,戴震是八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与朱熹、王阳明并列的三个极重要人物之一,甚至说他是朱熹之后的第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参见胡适,第139、144页)戴震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博采六经、孔孟之言所作的思考之中,尤其对孟子思想的发展值得重视。孟子倡言性善论,为人的道德生存活动奠定了基础,戴震则抽勒出“一本论”与“性善论”来深化孟子的道德本体论,在三个方面作了富有意义的展开:其一,在道德存在论的视野下,人的道德存在与自然存在之间常相背离。如何在人的整体性生存中安顿道德和自然,孟子语焉不详。戴震则通过对孟子不甚引人注目的“一本”论的强调,突出了道德和自然基于“行事”的统一。其二,对于孟子的性善论,历代主流理解都倾向于认为是先天本体自身圆满自足,本体自身之本质即善。戴震则在道德与自然“一本”于“行事”的基础上,强调道德主体经由自觉行动实现自然与必然之间的连续性展开,即继继不已之展开为善的根本所在,从而用“以善为性”取代了简单的“人之性善”。其三,孟子对道德主体性的高扬,突出了道德行动的个体性担当,但他又以“心之所同然”强调了道德原则的普遍性,故在孟子哲学中,个体性与普遍性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紧张关系。在后世主流(尤其宋明理学)理解中,普遍主义、本质主义的一面不断加强。戴震则明确强调,现实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本身就是本体论性的,他悬置了本体的普遍性,鲜明地突出了道德生存活动的个体性。戴震在以上三方面对于孟子道德哲学的展开,透露出某种近代气息。
一、“一本”的奠基:道德与自然统一于具体行事
“本”,《说文》解为树木的根部。在哲学上,“本”表示“万物之所从出”,与“本”相对的物则是本或本根所生者。(张岱年,第8、10页)在《孟子》中,所谓“一本”,是在批评墨家兼爱时提出的: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孟子·滕文公上》对此,朱熹说:“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爱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则是视其父母本无异于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朱熹,2001年,第262-263页)照朱熹的理解,墨者(夷子)“二本”在于割裂了两种根据:“视父母路人为一之本”与“施行所始之本”,即观念的本体依据与行动的本体根据应当为一,这是孟子一本论的基本意思。在孟子哲学中,这个一本,即“必有事焉而勿正”的具体行事活动本身①。但是,在后世的解释中,如朱熹的理气论框架的解释,却将观念的抽象扭曲为脱离具体现实而独立存在(净洁空阔的理世界),与现实具体人生之身体性的气血活动之间(气性的人欲或私欲人生)割裂为二。故戴震以为,宋儒与荀子都将道德行动所遵循的理义(礼义)与人自身的存在(性)割裂为二,陷入了二本,而非孟子之一本:
循理者非别有一事,曰‘此之谓理’,与饮食男女之发乎情欲者分而为二也,即此饮食男女,其行之而是为循理,行之而非为悖理而已矣。此理生于心知之明,宋儒视之为一物,曰‘不离乎气质,而亦不杂乎气质’,于是不得不与心知血气分而为二,尊理而以心为之舍。究其归,虽以性名之,不过因孟子之言,从而为之说耳,实外之也,以为天与之,视荀子以为圣与之,言不同而二之则同。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荀子推以礼义与性为二本,宋儒以理与气质为二本,老聃、庄周、释氏以神与形体为二本。然而荀子推崇礼义,宋儒推崇理,于圣人之教不害也,不知性耳。老聃、庄周、释氏,守己自足,不惟不知性而已,实害于圣人之教者也。”(《戴震全书》第6册,第134-135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荀子之失以礼义与性为二本;宋儒之失以理与气为二本;老庄释氏与告子之失以形神为二本。道德与生命、理与气、形与神,严格说是有区别的,戴震在此溶为一处言之。他尤为关注的是:将道德行动的根据——理义(礼义)视为一个脱离具体现实的、抽象的独立自在之物,与行动自身基于饮食男女之情欲的驱动相割裂,也就是将人的整体存在割裂为二,从而理义对于人之生存活动就完全是外在强加和约束的。戴震坚决反对宋儒人性二重说将气禀和理义分而为二,而特为突出生命自身存在之一本:
古人言性,但以气禀言,未尝明言理义为性,盖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时,异说纷起,以理义为圣人治天下之具,设此一法以强之从,害道之言皆由外理义而生。人徒知耳之于声,目之于色,鼻之于臭,口之于味为性,而不知心之于理义,亦犹耳目口鼻之于声色臭味也,故曰‘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盖就其所知以证明其所不知,举声色臭味之欲归之耳目鼻口,举理义之好归之心,皆内也,非外也,比而合之以解天下之惑,俾晓然无疑于理义之为性,害道之言庶几可以息矣。孟子明人心之通于理义,与耳目鼻口之通于声色臭味,咸根于性,非由后起。后儒见孟子言性,则曰理义,则曰仁义礼智,不得其说,遂于气禀之外增一义理之性,归之孟子矣。”(第155页)就人的生存实情而言,具体而现实的人总是身体性存在与心思性存在的统一。虽则心思对于身体的主宰与支配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但是身体感官与心思之官却是作为一个相互勾连的整体而存在于人自身的。脱离二者的联系,抽象地将感官作为纯粹生物性的本能欲望,而将心思作为纯粹的道德根源,这是思辨的虚构与错觉。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就是在身体感官与心思之官的“活生生的勾连”中展现自身的,就是身体性气禀与心思之理义的共同基础(一本)。
在戴震看来,身体性气禀与心思之理义的一本,实质上即统一于具体之事物:“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而言,非别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心之神明,于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照不谬也。”(第155页)传统以事训物,戴震则事物连用,此事物当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自在客观之物,而是与人的具体活动一体的自为之物。事物关联于人之所作为的事情,理义即内在于事情之条理,戴震说:“味与声色,在物不在我,接于我之血气,能辨之而悦之……理义在事情之条分缕析,接于我之心知,能辨而悦之”。(第154页)以事情自身为理义与血气心知之所本(一本),这无疑区别于宋明理学心与理、理与气二分之旧说。事情总是人作为主体之所行,戴震明确指出道德之理义根于人之“行事”:“圣贤之道德,即其行事。释、老乃别有其心所独得之道德。圣贤之理义,即事情之至是无憾,后儒乃别有一物焉,与生俱生而制夫事。古人之学在行事,在通民之欲,体民之情,故学成而民赖以生。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辩。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第479页)戴震以活生生的行事活动作为理义之所本,更为切中孟子道德哲学的本意。
二、以善为性:源起与展开的统一
以具体行事为理义与血气之一本,这就摒除了将善理解为一种抽象而普遍的理智规定性的可能,也就不能将善视为脱离行动的一种超然状态,更不能将此看做某种抽象思辨本体的僵死属性,从而才能将善理解为一种实现。实质而言,将善理解为一种活生生的实现,是理解性善的一个根本方向。
戴震以“天地继承不隔”来理解本体论意义上的善,延续了大程以《易传》“继之者善”来诠释孟子性善论的观点:“‘继之者善也’,言乎人物之生,其善则与天地继承不隔者也。”(第346-347页)所谓与天地“继承不隔”,即是说善基于一个自身绵延连续的过程。人的存在及其继续存在,是人存在的实然,《易传》以“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为说,戴震解释说:“《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不徒曰‘成之者性’,而先曰‘继之者善’。继谓人物于天地其善固继承不隔也;善者,称其纯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实体实事之名。”(第199页)戴震之意,《易传》所突出之“继”强调了人之实体实事(性)之绵延不绝的自身实现,对于此自身实现之绵延不绝的自为肯定,即是“善”。以继承而绵延展开为善,以展开之所成就为性,这是以善论性的基本理路。
所谓性之实体实事,在戴震看来,即指任何具体的个体主体,总是身体性血气与心思(心知)的统一,两者融合为一个整体,其实现就是所谓善。戴震说:“欲者,血气之自然,其好是懿德也,心知之自然,此孟子所以言性善。心知之自然,未有不悦理义者,未得尽合理义耳。由血气之自然,而审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谓理义;自然之与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尽而无几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后无憾,如是而后安,是乃自然之极则。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转丧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归于必然,适完成其自然。夫人之生也,血气心知而已矣。”(第169页)明于必然,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夫人之异于物者,人能明于必然,百物之生各遂其自然也”。(第166-167页)所谓自然,是指生存延续的基本本能欲望(生存之实然),必然则是生存之本能欲望的限制或制约法则与规范(生存之应然)。这里有三层要义:其一,血气与心知原始即为一体,生命之本能欲望与其实现,同对自身的觉悟及其限制是一本而有的;其二,必然性的应然规范,是为了生存之本能欲望的更好更多的实现,而非对之加以扼绝或杀灭,其并不以自然之实然为手段、作为自为目的而独立存在;其三,由自然之实然而达于必然之应然,是一个自身一致的、自我完善的过程,二者在过程中的统一是活生生的个体作为整体的自我实现。在戴震看来,综合这三个方面的意义,就是孟子性善论的要义。如果善的根源性含义在于主体之自我完善,那么,自然与必然在过程中的统一作为个体之自我实现,即是以善为性。在此,血气与心知的统一整体与二者彼此融而为一的具体展开过程,是理解善的基础。脱离了血气心知在自身实现过程的具体统一,设定先天的生物学本能与先天性道德本体,便是抽象的虚构。对自我实现着的人而言,“人性本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而更重要的是,人之所为即变成了人的本性”。(罗思文、安乐哲 主编,第108页)
基于必然之应然乃对于自然之实然的实现与完成,戴震明确反对必然而应然之理的独立存在:“人之心知,于人伦日用,随在而知恻隐,知羞恶,知恭敬辞让,知是非,端绪可举,此之谓性善。于其知恻隐,则扩而充之,仁无不尽;于其知羞恶,则扩而充之,义无不尽;于其知恭敬辞让,则扩而充之,礼无不尽;于其知是非,则扩而充之,智无不尽。仁义礼智,懿德之目也。孟子言‘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然则所谓恻隐、所谓仁者,非心知之外别‘如有物焉藏于心’也。”(第181-182页)在孟子那里,仁义礼智尚有“根于心”的先天性倾向的理解可能,但在戴震不离于人伦日用的意义上,扩充的含义则有了隐微的转折:前者是由内而外——先天如何实现于后天经验;而后者更多的是由此及彼——从“此时此地之此事”扩而及于“彼时彼地之彼事”。从而,作为生命存在之应然要求的规范、法则,在强调人之“人伦日用”的经验实现的意义上,就不可能被抽象思辨地虚构为独立自存的理世界:“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而后儒以为别如有物凑泊附著以为性,由杂乎老、庄、释氏之言,昧于六经、孔、孟之言故也”。(第182页)将人性视为独立于活生生的真实之人的独立存在,这是理学的虚妄抽象。
将理视为独立自存之物,成为超越于人与万物之上的普遍本体,造成了一种悖论:似乎人和万物都是同样的善的存在物。戴震于此明确指出:“孟子不曰‘性无有不善’,而曰‘人无有不善’。性者,飞潜动植之通名;性善者,论人之性也……自古及今,统人物与百物之性以为言,气类各殊是也。专言乎血气之伦,不独气类各殊,而知觉亦殊。人以有理义,异于禽兽,实人之知觉大远乎物则然,此孟子所谓性善”。(第188-189页)具体而现实的人,其身体性血气与运思之心知,从其绽现自身之原初,即有别于人之外的禽兽百物。在戴震看来,孟子所谓性善,就是将此一原初具体而现实的别于百物之差异实现出来。那种认为人的身体性血气与禽兽百物一致的观念,是悖于人的现实存在的错误假设。戴震认为人与禽兽之别是一种具体而现实的区别,而非抽象的理智规定的差别。但在朱熹的理气架构的理解中,在人物之别上,则搅扰为说,混杂不清②,其实质,就是将具体而现实的人物之别,抽象化为观念上的区别。戴震反对抽象虚构出脱离人伦日用的理或法则,反过来置于现实人伦日用之先,指出自然之达于其必然,是“乃要其后,非原其先”(第87页),人的自身实现不是用理智抽象以回溯于一个玄虚不实的“先在本原”,而是以具体的行事成就于现实。
孟子关于性命之辩有一个说法,即“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戴震解释说:“‘谓[性]’犹云‘藉口于性’耳。君子不藉口于性以逞其欲,不藉口于命之限之而不尽其材……不谓性非不谓之性,不谓命非不谓之命。由此言之,孟子所谓性,即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为性;所谓人无有不善,即能知其限而不踰之为善,即血气心知能底于无失之为善;所谓仁义礼智,即以名其血气心知,所谓原于天地之化者之能协于天地之德也。”(第191-192页)孟子的原意在于突出人在自身实现过程中的能动选择,将此视为人之本质的基础之一。戴震则以虽“谓之性”而“不谓性”,虽“谓之命”而“不谓命”突出了这一点,并给出一个关于“善”的深刻说明,即以不断突破外在限制以实现自身与不逞欲越界的统一为善:一方面,人当竭力实现自身,不以外在限制为借口而懈怠;另一方面,人当自觉于本能欲望及其限制而有尺度地实现自身,不能借口其为天生之本能而越界逞欲。如此,在血气心知一体、理欲一体的意义上,戴震推进了孟子关于善的观念。
在自然与必然的统一中,戴震强调作为具体主体的多样性和整体性的实现。就人之存在而言,这样的整体性实现使得善的意蕴具有了更为丰富生动的特点。不过,在活生生的具体主体作为整体的自我实现过程中,善表现为此一主体不断升华了的自觉的自身肯定,其中,必然的自觉会越来越取得相对的独立性,并且渐渐具有对于生命历程进一步展开的主宰与支配权,也越来越彰显人之为人的高贵与尊严。简言之,对于道德应当的自觉及其在生命历程中的积淀,逐渐具有了本体论意义,而这一点却多少被戴震所忽视。
三、普遍性的悬置与个体性的厘定
主体本于其具体行事而完善自身,这是性善的本义。在孟子的义理架构中,一方面,特别强调道德主体自身的个体性担当;但另一方面,孟子又有所谓“心之所同然”的说法:“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孟子·告子上》)“心之所同然”的确切意涵,颇难确定,但多被理解为某种普遍性。如朱熹认为,心所同然就是某一个体之行为合于普遍之规范,并得到所有主体的普遍认可:“‘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且如人之为事,自家处之当于义,人莫不以为然,无有不道好者”。(朱熹,1999年,第4册,第1390页)所以,在朱熹,所谓“同然”即是普遍性的理义或理义的普遍性:“理义是人所同者”,“义理都是众人公共物事”。(同上,第1391页)此普遍公共之理独立存在于所有个体之外,存在于事情之外。戴震对宋儒将理视为独立存在的“如有物焉”表示了反对,他指出:“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则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非理也,非义也。凡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第151页)就思想与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而言,从未出现“一人以为然”而“天下万世皆奉为不可置疑的普遍性之理”的情形,相反,很多人却以自身狭隘而偏私之个人意见当做所谓普遍的理,戴震批评为“以意见当理”:“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见,执之为理义。吾惧乎求理义者以意见当之,孰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也哉!”(同上)宋以来儒者所谓“天理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就是以意见当理:“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第153页)“自宋以来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第152页)戴震之所论则在正反两重意义上对普遍性加以了悬置:其一,从思想自身的历史来看,一人以为然而众人奉为不可易者的普遍真理,从未出现过;其二,历史与现实中所谓的“普遍的公理”,究实而言,无一不是某些个体挟一己之私意而僭越为所谓公共普遍之理。
与朱熹理学将心所同然之理视为普遍公共的独立存在事物恰好相反,戴震将“理”界定为具体事物彼此之间的细微差别:“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第149页)他并引许慎《说文解字》说:“‘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古人所谓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理者矣。”(第149页)后儒尤其宋儒将理视为万物的普遍性本质是所以“使物为一”者。戴震则明确指出,所谓理是所以“使物为异”者。
将“理”界定为“万物各如其区分”(第151页),注重万物彼此之不同或差异性,这并非是说万物彼此隔绝而成为孤立的原子式存在。毋宁说,“区分之理”更为关注的是人之类存在的个体性及其相互关联的统一,是在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之中得到确定的。戴震引入“情”来加以说明:“以我絜之人,则理明。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也……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第150-151页)在我与他人之间各自之情都恰如其分地得到实现,就是理。也可以反过来说,所谓理就是使我和他人都能恰如其分地实现自身之情。
分析地看,孟子所谓“心之所同然者谓理也谓义也”,其中一方面内涵着心自身的活动本身,一方面蕴含了心在自身活动中认可与接受的秩序与规范。因此,“心之所同然”可以分为“心之所然”(心作为理智力量之所认可与接收的秩序与规范)之同,与“心之然”(心之活动本身)之同两个方面。从认识论上说,“心之所然”通常指抽象的普遍性结论;而“心之然”则指认识活动本身。在道德生存论上,心之所然指与道德认知相应的普遍秩序与规范;心之然则指道德活动本身。简言之,“心之所同然”可以表达为:道德生存活动本身的相同以及道德生存活动中道德认知所认可与接受的规范或秩序之同。心之然的道德活动主要体现为觉悟着的行动或行动中的觉悟,心之所然则主要体现为行动的秩序或规范,两者统一在行动中。在抽象理智看来,秩序或规范可以脱离具体道德活动的独存,并以此“脱离”而彰显其超越于众多具体个体的“普遍性”、“绝对性”。但是,这样超越的绝对普遍性,常常是平凡生活之人难以理解的。
从戴震所理解的情得其平的主体间关系而言,他强调“理使得每一个体之情各自得到自身恰如其分的实现”。而每一个体之恰如其分的自身实现,一方面是每一个体对于自身生存活动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是每一个体区别于他人的实现自身的个体性。戴震明确地以理作为道德生存活动之个体性的担保,以义作为道德生存活动之主体性的担保:“举理,以见心能区分;举义,以见心能裁断”。(第151页)“区分”表明每一个体之不同于他者而具有个体性,“裁断”则是每一个体对于自身生存活动的主体性担当。所以,在戴震看来,所谓“同然”在实质上就是说每一个体的道德生存活动都具有个体性与主体性。从差异性的个体道德生存活动出发,就消解了抽象而玄虚的普遍性公理;而强调每一个体对于自身道德生存的担当与主宰,则瓦解了独立于具体道德个体主体之外的那个客观自在的“净洁空阔的世界”。
对道德生存活动的个体性,戴震解释孔子的“恕”道说:“曰‘所不欲’,曰‘所恶’,不过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尽于此。惟以情絜情,故其于事也,非心出一意见以处之。苟舍情而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未有任其意见而不惑斯民也。”(第153页)一方面,自觉于一切所谓理都是他人之意见而不以其意见妨碍自身之自我实现;另一方面,自觉于自身所见之局限,而不以自身所见之意见为理,而能“让”他者得以实现其自身。一旦失却对于其情之觉悟,而以意见当理,就会导致某些个体用自身之意见当作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公共普遍之理”,从而扼杀其他个体实现自身的可能,此即戴震所谓“以理杀人”:“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第479页)将理从事中分裂开来,以自己之意见当做理,必然也就会阻碍和扼杀他人由其行事以达其情:“理与事分为二而与意见合为一,是以害事”。(第158页)在道德生存论上,以理杀人意味着一些个体以自身之在湮没扼杀了他者之在,它成就的不是所谓“普遍性”自身,而是扭曲、膨胀了的特殊个体性。真正的个体性是以意见止于其自身而不僭越为理。
就道德生存活动的主体性担当而言,戴震消解了独立而先在的“净洁空阔的世界”,在身体与心知的统一中彰显道德活动本身的切己性。在孟子对于“心之所同然”的讨论中,表面上以“口之于味有同嗜,耳之于声有同听,目之于色有同美”(《孟子·告子上》)为类比,论者也多在类比意义上,以眼耳口鼻有生物学上的先天共同倾向来论证心也有先天性的普遍共同本质。这种对于感官与心官的割裂式理解为戴震所批评。他说:“盖耳之能听,目之能视,鼻之能臭,口之知味,魄之为也,所谓灵也,阴主受者也;心之精爽,有思辄通,魂之为也,所谓神也,阳主施者也。主施者断,主受者听,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则思。’是思者,心之能也。”(第154页)在戴震看来,孟子之所以能从耳目口鼻之所同而论心之所同,恰好在于每一个体之感官与心思,在其具体活动中都是统一为一整体而实现的;换言之,道德生存活动的主体性,一个重要方面即在于其身体性活动本身就渗透了心思之明觉的主宰与支配。人的感官与肢体活动,并非如禽兽一样的本能蠕动,而是在心思主宰之下的、合于人之本质的举动。
戴震之突出差异性、个体性与主体性,具有区别于宋明理学的“近代性”。他明确批评了宋明儒学的“复性说”,反对“复其初”:“形体之长大也,资于饮食之养,乃长日加益,非‘复其初’;德性资于学问,进而圣智,非‘复其初’,明也”。(第165页)不过,他消解普遍性而突出个体性,并未完全合理地说明普遍性与个体性的关系。从理论上说,就每一个体之区别于他者实现自身而言,是多样性或差异性;但就所有个体都能“同样地”如此实现自身而言,又是统一性或普遍性。就其担保所有个体之实现而言,理是普遍性的;就其即是每一个体之自身实现而言,理又是个体性的。就其是每一个体之自身担当与主宰而言,义是主体性的;就其担保每一个体都能成为自身之主体而言,义又具有客观性。当然,在个体与他人基于相互制约关系而展开的历史中,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理义作为传统或规范往往具有某种普遍性、超越性与客观性,在普遍性与个体性的关系上,二者的相互性及其关系的展开也具有历史性,这当然已超出了戴震的关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戴震在以“一本”论“性善”之际,多少忽视了孟子哲学中极为重要的“心”这一概念。对于心之于具体行事活动的基础性意义,并未有充分的自觉。但从思想与现实历史的互动来看,戴震哲学在道德问题上对于行动、身体、欲望、情感等方面的突出,对于善的重新诠释,对于个体性的强调和对于普遍性的消解,均折射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生活趋向近代及与之相应的思想启蒙的特征。
注释:
①《孟子·公孙丑上》载:“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正”,据焦循,作“止”解(焦循,第204页),强调了心事一体的“具体行事”的本体论地位。
②比如《答黄商伯》载:“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气之异者,纯驳之不齐;理之异者,偏全之或异。”(朱熹,2002年,第22册,第2130页)
标签:孟子论文; 朱熹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戴震论文; 道德论文; 本体论论文; 国学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