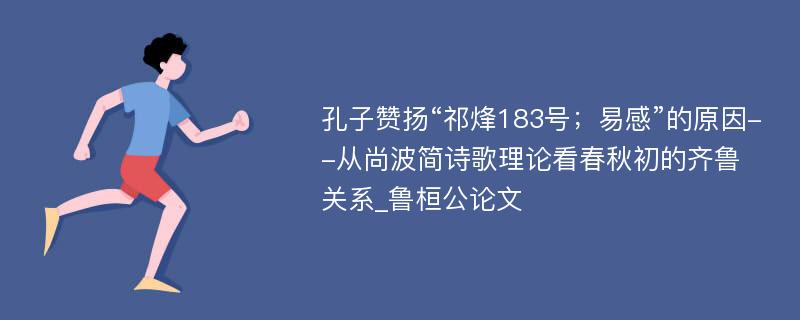
孔子何以赞美《齐风#183;猗嗟》——从上博简《诗论》看春秋前期齐鲁关系的一桩公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齐鲁论文,公案论文,一桩论文,春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上博简《诗论》第21简和第22简两次提到《诗·齐风·猗嗟》篇,简文如下:
孔子曰:“……,吾喜之。”(以上第21简)……《於(猗)差(嗟)》曰:“四矢弁(反),以御乱,吾喜之。”(以上第22简)(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云:“古读‘反’如‘变’,《诗》‘四矢反兮’,《韩诗》作‘变’。《说文》:‘汳水即汴水。’”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九谓:“‘反’古音如变。故韩诗借作‘四矢变兮’,反通作变,犹卞通作反也。”可以说卞、弁、反诸字古音相同可通。简文的弁,诸家一致读“反”,与经文吻合,应当是正确的。)
简文表明,第22简的内容,是对于第21简所谓“《猗嗟》,吾喜之”的具体解释,说明了孔子喜爱《猗嗟》一诗的最主要的原因所在。《猗嗟》一诗汉儒将其纳入美刺说的范围进行解释,于诗意可以密合,所以古今学者多信而从之。汉儒最为典型的解释,见于《诗序》。《诗序》云:“《猗嗟》,刺鲁庄公也。齐人伤鲁庄公有威仪技艺,然而不能以礼防闲其母,失子之道,人以为齐侯之子焉。”
但是,关于《猗嗟》一诗,明清之际大儒王夫之则指出汉儒将其列为“刺”诗不妥。他从圣人不会赞成淫诗的角度提出问题,谓:“辱子以其母之丑行,而廋文曲词以相嘲,圣人安取此浮薄之言,列之《风》而不删耶?”[1] (《诗经稗疏》卷一)清儒方玉润继续这个思路再加辨析,说:
此齐人初见庄公而叹其威仪技艺之美,不失名门子,而又可以为戡乱材。诚哉,其为齐侯之甥也!意本赞美,以其母不贤,故自后人观之而以为刺耳。于是纷纷议论,并谓“展我甥兮”一句为微词,将诗人忠厚待人本意说坏。是皆后儒深文苛刻之论有以启之也。愚于是诗不以为刺而以为美,非好立异,原诗人作诗本义盖如是耳[2] (卷六)(注:按,方氏此处所谓“戡乱”,并不正确。诗中赞美鲁庄公之射艺足可“禦乱”,是指他能够抵禦戎狄之乱,而非戡定鲁国内乱。且鲁庄公时国内局势平稳,尚无内乱可言。)。
专家在研究上博简《诗论》时肯定方玉润此说,谓:“从简文‘《猗嗟》吾喜之’看,方说是。下文又说:‘《猗嗟》曰:四矢反,以御乱。吾喜之。’其‘美’而非‘刺’更清楚。”[3] 对于方玉润此说,有的专家认为仍然不够彻底,指出其“仍未走出《诗序》‘美’‘刺’之误区。……齐侯与其妹通奸而生鲁庄公,此乃人所不齿之丑事,齐人恐深讳而不及,岂有公开赞美之理?”[4] (第207页)这个疑问应当说是很有道理的。
原来,齐襄公与其妹文姜(鲁桓公夫人)通奸,文姜受到鲁桓公指责,齐襄公听了文姜之诉,便在鲁桓公聘齐时,派人将其杀掉。关于此事,诚如专家所云,正为齐人所忌讳,怎么会公开赞美呢?
再说,一位堂堂的诸侯国君主不明不白地死在所出访聘问的国家,此事还由其夫人通奸所致,这在周代应当是绝无仅有,这件事情理所当然地要引起轩然大波。鲁桓公夫人文姜,也由此被钉在万劫不复的耻辱柱上。文姜与其兄齐襄公通奸为世之“大恶”,“有关伦常大故”,为人所不齿之丑闻。不唯如此,连她的儿子——鲁庄公的出身,也一时间成了问题,断定他是私生子的说法亦甚嚣尘上。如此淫诗竟然被圣人载入经典,这是颇为令人怀疑的事情,难怪清儒方玉润大为感叹,说:“吾不能不于此三致嘅焉!”[2] (卷六)今得上博简《诗论》对于《猗嗟》一诗的评析,可以启发我们较为深入地认识这桩公案,透过迷雾而接近真实。
二
为了研讨方便计,我们先来讨论《猗嗟》一诗。此诗全文如下:
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仪既成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猗嗟娈兮,清扬婉兮。舞则选兮,射则贯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注:《猗嗟》第二章的“终日射侯”的侯字,依全诗文例,疑原当作“兮”。“侯”字疑本为注文,手民写入正文而夺“兮”字。)
这首诗的字词训诂并没有多少疑难歧异,需要说明的是其次章的“甥”字。这是因为,从诗意可以看出,这位“甥”,正是全诗所颂赞的主人公。其身份的确定对于认识此诗意蕴关系极大,所以应当特加说明。关于“甥”,《说文》云:“谓我舅者吾谓之甥”;《尔雅·释亲》云:“姑之子为甥”;《猗嗟》毛传:“外孙曰甥。”甥舅关系的本质,唐代大儒孔颖达在解释“舅氏”之词时说:“谓舅为氏者,以舅之与甥,氏姓必异,故《书》《传》通谓为舅氏。”在兄——妹、姐——弟关系中,姐妹之子皆被称为甥,外孙也被称为甥。这种关系,古今皆然。甥所表示的是血亲关系中的出身姓氏差异。那么,《猗嗟》诗中的“甥”,具体所指的是谁呢?古今学者多肯定诗中的甥即鲁庄公(注:关于此诗中的甥,有专家以为当依据《尔雅·释亲》的说法,指的表兄弟,具体来说是表妹赞美表兄。按,此说虽然不为无据,但是表兄弟之间并不互称为甥。还有学者说此诗是女子夸夫的歌,然称夫为甥者,古今皆无此例。比较而言,甥大体上应当是“舅”的对应称谓,表兄弟与夫妻之间似无称甥之例,若将《猗嗟》理解为爱情诗似应有更多的证明。)。愚以为这是很有道理的。
首先,诗中所赞美的人物的身份是“甥”,这点表明他应当是姜齐以外之人。与姜齐结为婚姻的国家比较多,离齐国最近的、与姜齐联姻最多的国家是鲁国。可以推测这位“甥”可能是鲁国人。
其次,射礼非一般人可为,据《大戴礼记·朝事》篇说,它是天子教养诸侯之礼,“古者天子为诸侯不行礼义、不脩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义,故使射人以射礼选其德行;……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法也。”春秋时期,礼乐下移,诸侯间盟会时亦可进行射礼,再往后,卿大夫和士阶层才可入射礼的行列。《猗嗟》诗中的主人公,像貌俊美,威仪出众,箭法高超,不太像一般的平民百姓或一般的贵族,而应当是贵族中有影响的人物,如诸侯、大夫之类。射礼,有大射、宾射、燕射三类,所用箭靶各不相同。大射张皮侯而设“鹄”,宾射则张布侯而画“正”,燕射则画兽为“兽侯”。诗云“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可见所言之射当即宾射。宾射是特为招待贵宾而举行的射礼,主要行用于诸侯之间,可以推想此诗的主人公应当是诸侯级别者。
再次,诗的主人公是一位箭法娴熟的善射高手。而鲁庄公箭法之精,有史可征。《左传》载庄公十一年鲁宋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公右歂孙生搏之”,南宫长万是宋之名将,被鲁庄公用称为金仆姑的箭射落受擒。“金仆姑”遂成为历代形容壮美武将所携弓矢的美称。如杜牧《重送》诗谓:“手撚金仆姑,腰悬玉辘轳。爬头峰北正好去,系取可汗钳作奴。”韦庄《平陵老将》诗谓“白羽金仆姑,腰悬双辘轳”,陆游《独酌有怀南郑》诗云“投笔书生古来有,从军乐事世间无。秋风逐虎花叱拨,夜雪射熊金仆姑”等等,其事皆源自鲁庄公善射。
总之,《猗嗟》诗所写主人公应当肯定是鲁庄公,方才符合诗意。明乎此,我们不妨将此诗意译如下:
唉呀,多么美貌呀,
身材高大挺拔啊。
隐藏不住的动人呀(注:“抑若扬兮”句的“抑”字,韩诗作印,毛传释为美色。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六,谓“抑、懿古通”,按,懿意为美(《尔雅》:“懿,美也”),抑通懿,可证成毛传“美色”之说。又按,抑除通假读懿外,另有表示语气和表示压抑之意。其本义为压,《说文》“抑,按印也”(印字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九篇上加),段玉裁说:“即今俗云以印印泥也。此抑之本义也,引伸之凡按之称……,又引伸之为凡谦下之称。”《诗·筵之初宾》“其未醉止,威仪抑抑”,毛传“抑抑,慎密也”,慎密之意即由压抑引伸而来。本诗的抑,疑用若压抑之意,谓鲁庄公本气宇轩昂,像貌出众,但他保持低调,不取张扬之态。然而,他的压抑自谦的行止中亦透露着一种非凡之美,故谓“抑若扬兮”。)
美丽的眼神在飘动啊。
射场上的跑动巧妙得像舞蹈呀,
射起箭来真是娴熟啊!
唉呀,长得多么精神呀,
美丽的双眼清沏明亮啊。
射礼上的仪法多么熟练呀,
射礼进行一整天,
也是箭箭射得准啊!
真是我们齐国的好外甥呀。
唉呀,多么令人赞美呀,
神采飞扬又婉转多情啊。
舞动的节奏真好看呀,
箭箭都贯穿箭靶啊。
连续四箭都只射在一个点呀,
如此箭术真能够抵御祸乱啊!
《猗嗟》诗的首章,写鲁庄公貌美,次章写他的箭法精良,末章写箭法可以御乱保国。诗中对于鲁庄公的赞叹可谓溢于言表。那么,这种写法的真正用意何在呢?
关于《猗嗟》一诗的主旨,学者们几乎众口同声地肯定它的主旨是“刺”,争议较大的只是“刺”向谁的问题。古代学者认为它所“刺”对象有三:一是“刺”鲁庄公,说他空有材艺,并不能防范其母与齐襄公通奸,让人说自己是舅(齐襄公)之子,前引《诗序》之说就是典型。二是“刺”齐襄公淫其妹,古代学者多认为包括《猗嗟》在内的《齐风》自《南山》以下六篇,皆为斥责齐襄公之作,如《南山》诗郑笺曰:“襄公之妹,鲁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与淫通。及嫁,公谪之。公与夫人如齐,夫人愬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搤杀之,夫人久留于齐。庄公即位后乃来,犹复会齐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齐师。齐大夫见襄公行恶如是,作诗以刺之。又非鲁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这说明丧失伦理的齐襄公与无能的鲁桓公同为被“刺”的对象。三是“刺”鲁桓公不能禁其妻非礼,依《齐风·南山》孔疏的说法便是“鲁桓纵恣文姜”。比较多的学者认为具体到《猗嗟》一诗(而不是《齐风》中其它的诗),其所刺的主要对象还应当说是鲁庄公,因为只有他才符合诗中所说的“甥”的身份。
既然所“刺”的对象是鲁庄公,那么他是何时到齐国参加了射礼,以其俊美和射艺引起轰动而让人写出《猗嗟》之诗来热情称颂呢?学者或谓是鲁庄公四年与齐人狩于禚时事,或谓是鲁庄公二十二年到齐纳币时事,或谓是鲁庄公二十三年如齐“观社”时事,或谓鲁庄公二十四年如齐“逆女”时事,诸说皆以情理推而论之,于诗中尚找不出确切证据。比较而言,鲁庄公二十二年如齐纳币时事之说,较为近是。纳币为送呈定婚礼物,鲁庄公亲自到齐纳币,引起人们极大关注和兴趣,势所必然。由于鲁庄公是诸侯国君主,所以齐襄公举行宾射之礼款待,也是很自然的事。
依汉儒所论,《猗嗟》一诗所“刺”鲁庄公者,在于他空有一身好武艺,但却不能防闲其母文姜淫乱,结果便是“失子之道”。上博简《诗论》载孔子两用“吾喜之”之语表明他对于《猗嗟》的喜欢。那么,孔子喜欢这首诗的什么内容呢?是喜欢“刺”鲁庄公失子之道吗?要弄清这一点,必须先来说明由文姜所引起的春秋前期鲁桓公非正常死亡于齐国这桩公案。
三
研讨《猗嗟》篇诗旨,不能不说到鲁庄公之母(文姜)其人。汉儒对她与襄公的敌忾情绪非常强烈。例如,《诗·南山》序即谓他们“鸟兽之行”,郑笺则进而历数文姜之恶,谓:
襄公之妹,鲁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与淫通。及嫁,公谪之。公与夫人如齐,夫人愬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搤杀之,夫人久留于齐。庄公即位后乃来,犹复会齐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齐师。齐大夫见襄公行恶如是,作诗以刺之。又非鲁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
按照这个说法,文姜与其兄在其出嫁之前就已经有奸情。唐儒孔颖达《诗经正义》卷五,为郑笺之说张本弥缝,谓:“笺知素与淫通者,以奸淫之事生于聚居,不宜既嫁始然,故知未嫁之前,素与淫通也。”《公羊传》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挥,谓:“夫人谮公于齐侯:‘公曰“同非吾子,齐侯之子也。”’齐侯怒,与之饮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搚干而杀之。”这里替鲁桓公造出一个“同(按,鲁庄公名)非吾子,齐侯之子也”的说法,《诗·猗嗟》序亦谓“人以庄公为齐侯之子”。总之,依照汉儒之说,文姜早就品行不端,而且其出嫁于鲁之后,依然如故,以至于鲁庄公也是她和齐襄公的私生子。
我们于此当辨明两事。
其一,文姜的品行问题。文姜于鲁桓公三年嫁到鲁国,其兄齐襄公不顾古礼限制,亲自将她送到称为“欢”的地方,由鲁桓公到此迎娶。《左传》桓公三年评论此事谓:“齐侯送姜氏,非礼也。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然而,这也只能说明齐襄公与文姜,兄妹关系甚好,尚不足以构成私通的罪名。不仅如此,文姜当时似乎还曾以“贤”著称。《诗序》谓“《有女同车》,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昬于齐。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关于《有女同车》一诗是否为“刺忽”之作,我们这里可以暂且置而不论,我们于此要指出的是《诗序》所谓那位被誉为“贤”的齐女正是文姜。据《左传》记载,文姜尚未嫁于鲁的时候,齐襄公曾经想把她嫁给郑太子忽。《左传》桓公十八年载此事谓:
公之未昬于齐也(按,指鲁桓公未婚于齐),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人问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君子曰:“善自为谋。”及其败戎师也,齐侯又请妻之。固辞。人问其故,大子曰:“无事于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奔齐之急,而受室以归,是以师昬也。民其谓我何?”遂辞诸郑伯。
这个记载可以表明,齐襄公对其妹文姜十分关心。文姜并未有品行不端的恶名,相反,还可能是一位贤慧之女。鲁桓公在位十八年,多次与齐襄公相会,文姜皆未随从见齐襄公,仅鲁桓公十八年随从至齐,结果,鲁桓公正是这次走上了不归路,被杀于齐。要之,未嫁前的文姜即使不“贤”,也可以肯定她尚未戴私通的恶名(注:关于出嫁之前的文姜是否“贤”,汉儒曾有讨论,《诗·有女同车》篇孔疏载:“《郑志》张逸问曰:‘此序云“齐女贤”,经云“德音不忘”,文姜内淫,适人杀夫,几亡鲁国,故齐有雄狐之刺,鲁有敝笱之赋,何德音之有乎?’答曰:‘当时佳耳,后乃有过。或者早嫁,不至于此。作者据时而言,故序达经意。’”按,此处所谓“当时佳耳,后乃有过”,是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说法。)。
其二,鲁庄公是否齐襄公之子的问题。《公羊传》首先造出鲁桓公有“同非吾子”的说法,然而,这一说法却是不见于《春秋》和《左传》,所以,《公羊传》此说很值得怀疑。较早对此明确辨诬的可能是唐儒徐彦(注:在徐彦之前,郑玄解释“展我甥兮”一语时有以下的说法:“云:“展,诚也。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艺如此,诚我齐之甥。言诚者,拒时人言齐侯之子。”这个说法微有辨诬之意,只是说得不大明确。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说,这是汉儒中关于此事难得的一个比较清醒的声音。)。他在《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六中解释《公羊传》的这个说法,谓:“夫人加诬此言,非谓桓公实有此言,何者?正以夫人之至在桓三年秋,子同之生乃在六年九月故也。”后来,朱熹《诗集传》卷五解释《猗嗟》“展我甥兮”一句时谓:“言其为齐之甥,而又以明非齐侯之子。此诗人微词也。按,《春秋》记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齐’,六年九月‘子同生’,即庄公也。十八年桓公乃与夫人如齐,则庄公诚非齐侯之子也。”他所说的道理与徐彦说同。从《春秋》《左传》详记文姜行止的情况看,她在鲁庄公出生之前最后一次赴齐见到齐襄公是三年前的事情,此足可证明,断定鲁庄公为齐襄公与文姜私生子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分析汉儒对于文姜的痛诋,很用得上《论语·子张》篇所载子贡的一段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文姜,诚然是一个与其兄有奸情之人,其夫鲁桓公之暴死,她有摆脱不掉的干系。然而,由此推测她在出嫁前既已行为不端,并且说鲁庄公是她与襄公的私生子,这些都是臆测不实之辞。汉代的男女之防,远甚于春秋战国时期,文姜与其兄私通之事,为人所痛恨,事在情理之中。然而,其中难免夹杂推测、想象的因素。人们将其恶名扩大,并从而痛加诋诬,亦事属必然。总之,在当时的社会伦理观念之下,汉儒的义愤,虽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们的相关说法毕竟与事实有一定距离。明乎此,也就知道汉儒对于《猗嗟》一诗主旨在于“刺鲁庄”一类的论断,便很值得重新认识和辨析了。
四
《猗嗟》一诗由衷地赞扬了鲁庄公的材艺之美,从他的像貌到他的射仪箭法,无一不在诗人的赞赏范围之内。由此而言,说《猗嗟》是一首鲁庄公的赞美诗,并不为过。在这里,我们应当说明的是,此诗是赞美鲁庄公,而不是赞美其生母文姜。说《猗嗟》是一首赞美诗,并不是说这首诗赞美了齐侯与其妹通奸的丑事。另外,上博简《诗论》第21简孔子所云“《猗嗟》吾喜之”之语,并不是肯定此诗为“美”诗的根据,就是一首“刺”诗,孔子也可以喜而赞美它,所以说孔子的赞许与诗的主旨的美刺并无必然关联。《诗论》第22简谓:《猗嗟》曰:“‘四矢弁(反),以御乱’,吾喜之。”孔子在这里说明了他喜欢《猗嗟》一诗的原因所在。《猗嗟》诗的第三章说,“四矢反兮,以御乱兮”,表明鲁庄公确有治国本领,能够消弥鲁国的祸乱。分析鲁庄公行事,《猗蹉》篇所云良非虚语。
尽管鲁国在诸侯国中并不算强大,但是鲁庄公的武功在春秋前期却是不可小觑的。《左传》庄公九年载:“秋,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公丧戎路,传乘而归。”《公羊传》认为此战,鲁庄公虽败犹荣,故以“伐败”称之。乾时之战的败北,并没有影响鲁庄公的奋进。就在这次败北的第二年,鲁庄公便于一年之内取得两次败宋、一次败齐的连续胜利(鲁庄公十一年,鲁又两次败宋。《春秋》庄公十一年:“夏,五月戊寅,公败宋师于鄑。”《左传》载“夏,宋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御之,宋师未陈而薄之,败诸鄑”)。《春秋》庄公十年“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败宋师于乘丘。”“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左传》“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公弗许。白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左传》庄公十一年述去年事谓:“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公右歂孙生搏之”。鲁庄公曾经于十八年和二十六年两次伐戎,亲自率军“追戎于济西”。
鲁庄公武功虽强,但他并非只是一介赳赳武夫,而是一位颇有头脑的人物。《左传》庄公八年:“春,治兵于庙。礼也。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仲庆父请伐齐师。公曰:“不可。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脩德以待时乎?秋,师还。君子是以善鲁庄公。”这件事情表明鲁庄公重德守礼。《左传》记著名的长勺之战,曹刿论战固然出尽了风头,但鲁庄公亦提出施惠于人、敬慎祭神、明察刑狱等三事,以为赢得战争胜利的三项要事,其见识虽然不及曹刿精辟,但亦实属不易。
鲁庄公识大体,注重大事,不以小误大。齐为鲁的近邻强国,并且双方历来交往颇多。鲁庄公从鲁国利益出发,对于齐鲁关系格外重视,不再纠缠于其父死于齐国之事,这是明智的做法。《春秋》庄公四年:“冬。公及齐人狩于禚。”鲁庄公在继位之初就与齐侯共同狩猎,似乎并没有将其父死于齐人之手的事耿耿于怀至此时。依照《礼记》记载,与仇敌是应当有明确敌忾情绪的,何休总结此事谓“礼,父母之讎不同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国,九族之讎不同乡党,朋友之讎不同市朝”[5] (卷六)。然而,与齐的关系实为鲁的头等大事。且鲁庄公父死于齐之事,已经通过齐满足鲁的要求,杀掉直接凶手公子彭生而得以初步解决。《谷梁传》释《春秋》此年鲁庄公“及齐人狩”事谓:“齐人者,齐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敌,所以卑公也。何为卑公也?不复讎而怨不释,刺释怨也”。这里所说,实为汉儒的迂腐之论。鲁庄公与齐襄公一同狩猎,是鲁庄公四年冬天的事,就在此年夏天,齐、陈、郑三国诸侯会见,成结盟之势;此年夏天,齐还实际上灭掉了鲁国的近邻纪国。在齐襄小霸、对于鲁国构成严重威胁的时候,鲁庄公采取了灵活的外交策略,力图化解强齐威胁而取得主动。鲁庄公不汲汲于个人“复仇”,而力求“释怨”,这在当时的形势下,实为明智之举。从庄公八年郕降齐而不降鲁开始,鲁国内部酝酿着对齐的不满,然鲁之实力弱于齐,故而翌年鲁庄公在乾时之战中大败于齐。但庄公十年春天,就在著名的长勺之战中,鲁庄公即大败齐国,捞回面子,并于同年夏天于乘丘之战中战胜与齐结盟的宋国。翌年,又一次打败宋国。庄公十三年春,齐联合宋、陈、蔡、邾等国举行北杏之盟,对鲁构成威胁,此年冬鲁庄公与齐“盟于柯”,寻求与齐和解。
鲁庄公十一年,在齐襄公被弑、齐国内乱形成之时,鲁庄公发挥了重要作用,先是与齐国大夫盟誓,后又送公子纠返齐继位,虽然没有成功,但此时鲁对齐的影响在诸国中亦可谓无出其右者。鲁庄公与齐本有杀父之仇,后来又因送公子纠返国而与齐结怨,引发了乾时之战和长勺之战。此后,鲁庄公以修好关系为重。庄公十五年,鲁庄公参加了以齐为首的幽之盟。庄公二十二年又与齐会盟于扈。庄公晚年与齐关系应当是良好的。所以他于庄公二十三年还“如齐观社”,观看齐的社祭。翌年又迎娶齐女哀姜为妻,还让大夫和宗妇以隆重礼节拜见哀姜(注:《春秋》庄公二十四年“夏,公如齐逆女。秋,公至自齐。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妇觌,用币”。《左传》载此事谓:“秋,哀姜至。公使宗妇觌用币,非礼也。御孙曰:‘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贽不过榛、栗、枣、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而由夫人乱之,无乃不可乎?”按,鲁庄公此举,当时就被认为是“非礼”,然而他坚持这样做,这反映了他对于齐鲁关系的特别重视。)。这其间就有显示特别重视齐国的因素在内。
分析鲁庄公的作为,可以说他是一位遵守孝道的人。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于其母文姜的态度上。文姜在鲁桓公时期只有一次,即鲁桓公十八年赴齐,此次她与齐襄公私通,导致鲁桓公被杀于齐。史载齐襄公与文姜私通,仅有此例(注:按,明确指出文姜与齐襄公奸情者尚有《春秋》庄公二年的一条记载,谓“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左传》评论此事谓:“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公羊传》何休集解云:“书者,妇人无外事,外则近淫。”《左传》和《公羊传》何休集解于此所云,皆非正式记载,而是推想之辞,非必为是。)。此后记载鲁庄公时期的文姜之事,我们综合《春秋》《左传》记载,可以排列如下:
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
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公羊传》作郜)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
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齐师。
六年,冬,齐人来归卫宝。文姜请之也。
七年,春,文姜会齐侯于防。齐志也。
七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谷。
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齐。
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注:关于文姜年岁,可推测如下。据《礼记》记载,女子二十而嫁,若依此则可以推定鲁桓公三年文姜20岁时嫁于鲁。文姜35岁时夫死,57岁时去世。)。
总结上列记载,可以看到文姜在21年的时间内10次赴齐会见齐襄公,次数之多,远甚于鲁桓公时期。这反映了鲁庄公对于母亲的尊重态度。这里可以将他与同是春秋前期重要的诸侯国君主郑庄公进行比较。据《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先是纵容其母和其弟“多行不义”,然后一网打尽,又将其母软禁,还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后得颖考叔劝谏,才想办法与其母“隧而相见”。鲁庄公并不像郑庄公对母亲软硬兼施、隧而相见,而是取尊重态度,不干涉其母的行动自由。鲁庄公还能够正确对待关于其母的传言,以对于母亲的敬重表现自己的孝道。文姜于鲁桓公十八年春至齐,由于桓公被杀,所以她直到翌年春还未归鲁。可以推想当时鲁国国内一定是舆论大哗。鲁庄公元年春,要举行鲁桓公的丧葬之礼,文姜未回鲁,但依礼又应当有她参加,所以鲁国史官记上一笔,说“夫人孙(逊)于齐”,这表示文姜有悔过之意,有对于回鲁的恐惧。然而,《左传》庄公元年却说这个记载“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似乎鲁庄公极其厌恶其母,与之一刀两断。其实不然。不称姜氏,并非对于文姜之厌恶。《左传》隐公元年载郑庄公与祭仲对话:“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称其母为“姜氏”,正是郑庄公鄙夷其母的一个表现。这里不以“姜氏”相称,并不应当视为鲁庄公要与其母断绝关系。《公羊传》解释《春秋》的这个记载,应当是近乎实际的。它说:
孙者何?孙,犹孙(逊)也。内讳奔,谓之孙(逊)。夫人固在齐矣,其言孙(逊)于齐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念母者,所善也。则曷为于其念母焉贬?不与念母也。
何休《解诂》云:“礼,练祭取法存君,夫人当首祭事。时庄公练祭,念母而迎之,当书迎,反书孙者,明不宜也。”这里是说,为桓公举行练祭时当以桓公夫人为首祭,庄公怀念其母而欲迎其返鲁。鲁庄公“念母”,本为孝子之“善”事,而《春秋》只记“夫人孙于齐”,所以《公羊传》认为这其间便寓有对于鲁庄公的贬意。不管此处是否有贬意在(注:关于此处的贬意,唐代徐彦《春秋公羊注疏》卷八谓:“文十八年夏,‘齐人弑其君商人’,而不书其葬者,以责臣子不讨贼也。似文姜罪,实宜绝之,公既不绝,宜尽子道,而反忌省,故得责之。”),都可以说,鲁庄公在为其父举行练祭时曾经“念母”而欲迎文姜返鲁,则必当为事实。庄公的杀父仇人公子彭生已应鲁国要求而被齐处死,在这种情况下,鲁庄公欲迎母返鲁,表明他已取宽容态度来对待其母。鲁庄公的宽容应当是付诸实践了的,大约在鲁庄公元年文姜即已返鲁,所以《春秋》才于翌年有文姜赴齐的记载。
儒家所强调的子女的孝道,是将孝敬父、母连在一起的。孔子论孝,从来没有忽略对于母亲之孝。孔子此类言论甚多,可举《论语·阳货》篇论为父母守丧三年的一段话为证。是篇载孔子语谓:“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子女对于父母的缺点、错误可以谏劝,但这并不影响对于父母的孝敬。按照《论语·子路》篇所载孔子的说法,便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按照《孟子·离娄》下篇所载孟子的说法便是“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所谓“隐”,所谓“不责善”,并不简单地是隐藏或不批评之意,而是包含着对于父母的深切理解。从根本上说,这是为父母与子女间的血缘关系及父母对于子女的“恩”情所决定的。将犯有过错的父母视同路人而寡情少义,当即儒家所不赞许的劣行。
五
《诗论》第21简载孔子语“《於(猗)差(嗟)》,吾喜之”,这是对于《猗嗟》全诗的肯定,其中当然也包括着对于鲁庄公的赞许。第22简指出“《於(猗)差(嗟)》曰:“四矢弁(反),以御乱”,吾喜之。”这是孔子具体指明他喜欢《猗嗟》一诗的主要原因。
儒家关于“家——国”的伦理观念,集中见于《大学》一篇,其中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化为一个系统格式便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之前者,是个人道德修养问题,其后则是参与社会实践以实现理想的问题,而治国平天下则是人的远大目标之所在。这种伦理观念,即古人所谓的“修齐治平”。用《孟子·离娄》上篇所载孟子的话来说便是“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赞许鲁庄公重视国家利益、顾全国家利益这个大局,可以看出孔子已具有家国一致、国重于家的观念。《论语·颜渊》篇载仲弓问仁,孔子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作答,可见邦(国)与家是并重而不可偏废的。并且“邦(国)”、“家”二者相比,前者应当是重于后者的。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有二,一是忠,一是孝。国家观念在孔子时期已经兴起。忠于君与忠于国,事同一理。国家利益摆在“孝”之前,所以《论语·颜渊》篇排列的次序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与鲁庄公虽然有杀父之仇,但事过境迁,再耿耿于此,于鲁国并无益处可言。“忠”,一般说来是忠于君,但对于作为诸侯国君主的鲁庄公而言,他的“忠”就是忠于鲁国,即国家利益至上。《论语·阳货》篇载孔子语:“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关于文姜之事,鲁国当不乏好事之徒喋喋不休,鲁庄公取不理睬的态度,而将其关注的重点放在调整好与齐国的关系及稳定鲁国内部局势上,应当是最佳选择。他的这种做法显然为孔子所赞许。那些孜孜于传播文姜丑行而攻讦鲁国君主的做法必然被孔子视为旨在颠覆邦家的“利口”者之作为,一定会被孔子置于厌恶、排斥之列的。
《猗嗟》诗谓“四矢反兮,以御乱兮”,鲁国当时的形势有何“乱”而必须早作准备、未雨绸缪呢?愚以为这“乱”,就是戎狄的威胁。鲁庄公时,戎狄势力已迫近鲁地。《春秋》庄公十八年载,这年夏天,“公追戎于济西”。过了两年,“齐人伐戎”。鲁庄公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羁出奔陈。”曹与鲁为近邻,曹世子羁的出奔(注:关于羁的身份这里取《左传》杜注之说,《公羊传》以为是曹大夫,不大符合《春秋》文例。按,《春秋》庄公二十四年春,葬曹庄公。此年冬,戎侵曹,即载曹羁出奔之事。盖世子此时尚未正式继位,故称“曹羁”。),说明戎的势力之强大。鲁庄公二十六年,鲁再次伐戎。鲁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齐鲁两国虽然有矛盾,但在对付戎狄势力时则是团结一致的。《左传》载,就在这次齐伐山戎之前,鲁庄公与齐桓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双方所商讨的正是伐戎的大计。第二年夏天,齐桓公又派人到鲁国“献戎捷”,表现了两国在对付戎狄势力方面的一致与合作。庄公以后不久,邢国被戎狄所逼不得不迁移;卫国为戎狄所亡,不得不复立。此正是戎狄势力炽盛的标识。《公羊传》僖公四年曾总结当时的形势说:“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在咄咄逼人的戎狄势力面前,华夏诸侯国之危殆,可谓千钧一发。《左传》闵公元年载,在狄人进攻邢国的时候,管仲曾向齐桓公进言,说:
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
这段话充分表现了华夏诸国对于戎狄的同仇敌忾。齐桓公正是在这个形势下进行尊王攘夷而成就了一番霸业。在他的霸业中,鲁乃是一个可靠的伙伴。赞美鲁庄公的《猗嗟》诗中说“四矢反兮,以御乱兮”(注:“以御乱兮”的“御”字本作禦,唐写本省作御,唐代徐彦注《仪礼·大射》亦引作御(见黄焯《经典释文汇校》卷五)。禦义为抵挡、抗拒,而御义为驾驭车马,引伸为治理。按,知“御”乱本作“禦乱”,可知诗意不是指治理鲁国内乱,而是抵禦戎狄之乱。),所表现的就是在齐国人的心目中,鲁庄公精良的箭法乃是抵御戎狄威胁的一个重要条件。通过孔子对于《猗嗟》一诗的赞许,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出孔子“内华夏、外夷狄”的观念。鲁庄公是齐桓公霸业的重要合作者。孔子十分称许齐桓公的霸业,《论语·宪问》篇载孔子语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民众从齐桓霸业所受到的恩惠,就在于华夏诸国免遭戎狄过分侵扰,生活相对安定。鲁庄公对此是做出了贡献的。
孔子明确指出他喜欢《猗嗟》一诗。其所喜欢的具体内容可以有多个方面,例如,《猗嗟》诗所写射仪之周全(注:《周礼·乡大夫》曾经言及射礼五物(事也),即“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此五事,在《猗嗟》诗中皆得到印证。)、所写鲁庄公气度轩昂及彬彬有礼之神韵、所写鲁庄公箭术之精湛等,都应当为孔子所喜欢,然而,孔子对于鲁庄公的赞许,最主要的应当在以下两点:一是赞许他重孝道,敬父母;二是赞许他识大体,为国家利益而不汲汲于个人私仇。这两点中又以后者更显得重要。通过竹简《诗论》的相关研讨,我们不仅对于《齐风·猗嗟》可以获得一些新的体会,而且对于齐鲁关系中鲁桓公丧命于齐这桩公案,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