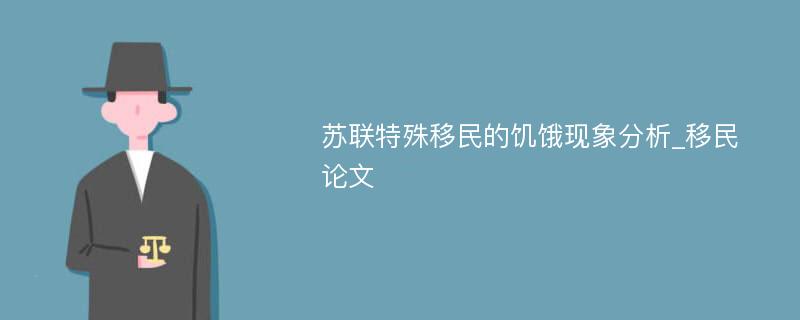
试析苏联特殊移民的饥饿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饥饿论文,移民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斯大林的国策与特殊移民的产生
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苏联20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该理论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它是3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石。斯大林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否能建成的关键放在了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的解决上。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是能够运用国内自身的力量加以解决的,也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能够领导农民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认为,苏联为了消除来自西方主要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复辟的危险,必须要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如果在经济上依赖于西方,苏维埃政权随时都有被颠覆的危险。而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使苏联这样一个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的国家赶上和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自己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因此,工业化是苏联立国之本。苏联领导人也清楚地认识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支撑,工业化也只是空中楼阁。工业化的基础不是建立在个体小农经济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大农业的基础之上。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急需国外设备和技术的投入,加上工业区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对粮食需求与日俱增,所以,如何将国家难以控制的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联合起来,以工业化带动农业从而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中的关键而棘手的问题。
1929年秋,斯大林发表了著名的《大转变的一年》的文章,正式拉开了全盘农业集体化的序幕。然而,全盘集体化不仅没有缓解日益严重的粮食问题,相反还激化了农村中的各种矛盾。斯大林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归结为农村富农阶级的顽强抵抗,认为他们藏匿粮食、逃避税收、转移财产,还拉拢中农,欺骗贫雇农,从事一系列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活动。斯大林认为,事到如今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扫除全盘集体化道路上的最后障碍。
这年冬天当西方经济危机后的第一个圣诞节草草收场的时候,斯大林却雄心勃勃地向苏联社会中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富农发布了进攻的命令,提出了“消灭富农”的口号。
此时正值西方经济危机之时,国际粮食市场的格局变化促使斯大林设想通过倾销的方式大量低价出口粮食,占领国际粮食市场,通过获得更多的外汇以购买工业化所急需的工业设备与技术。与此同时,布哈林等人被逐出政治局为斯大林自上而下在苏联消灭“最后一个资产阶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2月21日是斯大林五十华诞,但他无心祝寿,却认真地准备着即将在全苏马克思主义农业专家会议上的发言。12月27日,斯大林打破约定俗成的惯例,不是在党的会议上,而是在具有学术性的马克思主义农业专家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苏联农业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讲。这次演讲实际上成为了消灭富农的“动员令”。
之后斯大林授意莫洛托夫于1930年1月15日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制定消灭富农的政策。1月26日,特别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草案,并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1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强制迁移被没收富农的决议》。至此,一次剥夺和迁移富农的运动拉开了帷幕。
决议中将富农划分为三类,第一类送进集中营,第二、三类在没收财产之后实行强制迁移,并要求地方在4月15日以前完成规定迁移数量的一半。大规模的迁移从1930年的2月中旬开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个是东部地区,包括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一个是北方边远地区。另外,第三类富农户多被安置在原居住地的偏远地区。运输的方式为铁路运输和畜力运输。被划定为富农的农户其财产被全部没收,并马上被集中起来立即实施迁移。这些被剥夺了财产、失去了选举权、被强制迁移的富农在这时就有了一个新的称谓,即“特殊移民”。到1931年8月,虽然中央已宣布在全盘集体化的地区停止大规模的富农迁移工作,但零星的迁移行动一直持续到了1933年初甚至更晚。
二、食品供应的中断与饥饿现象的产生
要给出饥饿现象出现的准确时间是不现实的。在最初的陆路、铁路的押送过程中特殊移民中的饥饿现象虽已存在,但尚不明显,主要的问题集中在陆路运输缺少马匹、列车车内拥挤不堪、不供开水、卫生条件差、特殊移民情绪低落等方面。但在安置过程中,特殊移民携带的粮食已消耗殆尽,食品等供应已面临十分严峻的境地。以下是1930年一些特殊移民的申诉。
北德文斯克州、科特拉斯市、马卡里哈移民营第45号棚的特殊移民И·В·克雷连科写道:“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检查马卡里哈的富农们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什么也
没有,没有搭棚子用的木柴,没有开水,没有食品,没有澡堂,仅仅是给300克面包,就
这些。”[1](p204)
一位名叫格尔曼的特殊移民,一家五口被迁移到了西伯利亚。他这样写道:“…我们被押送到伊尔比特州塔巴林斯克区的流放地彼得洛夫村。在这里我们正在饿死,孩子们生命垂危,没有面包和食物。”[1](p217)
一些乌克兰的特殊移民向加里宁反映了特殊移民当中儿童死亡增多、住房拥挤、环境恶劣、供应不足等诸多问题:“敬爱的全俄总管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我们乌克兰移民住在沃洛格达。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除了300克面包外,什么粮食也没有,也没有任何热的食物。”[1](p219—220)
一位叶尼塞斯克的居民将自己亲眼所见记录了下来,他在给加里宁的一封信中提到:“在叶尼塞斯克市迁来了几千名带有家眷的农民,房子都被他们占满了,每天给大人300克面包,小孩200克,其他再也没有什么了。甚至连开水也不给。”[1](p222)
一名特殊移民在给加里宁的《瞧,这幅移民营的画面》这封信中称,他不只一次目睹了大批举家迁移的凄惨情景,他写道:“瞧,这就是移民营的现状。……食物糟糕得很,面包干快吃完了。很多人已缺粮了。”[1](p209—211)
在官方的机密文件中,类似的情况也有所反映。乌拉尔州警卫司令部司令员巴拉诺夫在亲自拟定的《乌拉尔州警卫司令部1号调查报告》中较为详细地提供了1930—1931年初乌拉尔州特殊移民食品和日用工业品的供应情况。1930年12月23日的调查记录中提到,“通过对纳杰日金斯克区特居区的调查断定,大多数居住区特殊移民的食品(供应)都有中断,而且往往是长期中断,使特殊移民没有食品。”在对索西瓦区和加林斯基区的调查中,“多数特居区的食品供应中断。特居区由于没有售货亭和商店,移民们为购买食物而不得不从居住区往外走10—13公里。……”在伊夫杰利区,“区内移民食品供应一再中断,日用工业品根本没有。……”在内罗布区,“通过对特居区的调查确认,区消费合作社对特殊移民的食品供应曾一再中断。”
普遍出现的食品供应不断中断的情况使1931年初春特殊移民的处境更加困难。根据1931年1月11日州警卫司令部调查记录,在乌拉尔基泽尔区古巴哈的特居区,“约有50名特殊移民有两个星期没有收到食品”。开春以后正处在青黄不接的时节,这又给食品供应问题增加了新的难度。据“3月7日警卫司令部3/C号报告,(在基泽尔区)乌西瓦工段居住区食品供应没有保障,……”同一时期,州消费合作社联社发出了关于取消无劳力的特殊移民的份粮供应的指示,“特殊移民因吃不饱而生病以及逃跑事件有所增加”。在纳杰日金斯克区,“因食品没有运到边远地点,随着道路泥泞季节的到来,特殊移民的供应面临断绝的威胁。”据3月31日内罗布区区卫生局保健医生的通报,“区内因无面粉,配给特殊移民的面包中掺入锯末达90%”。3月26日切尔登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26/C号的通报中指出,在该区“至今没有拨出专门经费用于特殊移民的食品供应。边远地点在春天联系不上,其食品得不到保障”。[2](p165—167)
1931年4月20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乌拉尔站对萨马林区、杰涅日金林区和马尔夏特林区等若干特居区和其他特殊移民安置地进行了抽样调查。5月13日就调查的分析情况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做了汇报。汇报得出了以下的结论:第一,所抽查地区的特殊移民“确实在挨饿”,一些特殊移民“不得已以死兽肉、苔藓、桦树叶和其它树叶为代食品”;第二,特殊移民饥饿的现象具有普遍性,并且还在不断地蔓延,汇报中特别提到了边远地区特殊移民的情况更为严重。[2](p165—167)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营房管理部主任在《关于特殊移民的政治经济状况(1931年7月20日)》的汇报中,对乌拉尔州特殊移民安置地区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记录进行了概括,并就有关情况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作了汇报。汇报在谈到特殊移民的供应问题时,对发生在特殊移民中间的饥饿现象做了披露。汇报中提到:“在(乌拉尔州的)塔博林卡木材采运企业,连最必需的食品也是供应不足。往往3—4天不发面包,更不说其它食品……尤其糟糕的是对边远地点的食品调运。委员会不得不面对浑身浮肿、无法动弹的儿童饿得奄奄一息的事实。由于饥饿有自杀的事情发生。棚舍附近的所有野草连同树皮一起被用来充饥,……塔夫达区的情况稍好,但也有特殊移民因面包不足而饿上2—3天的事。”[2](p172)调查委员会对纳杰日金斯克木材采运企业的抽查也反映出同样的问题。“在纳杰日金斯克木材采运企业,……特殊移民及其家庭中经常有人吃不饱饭,……各个居住区普遍都有许多特殊移民,特别是没有劳动力的家庭[成员]食用烂木头、各种代粮品、野草和有毒的蘑菇,结果招致疾病甚至完全丧失劳动能力。”[2](p173)
三、饥饿现象的原因分析
联共(布)中央在实施大规模迁移特殊移民行动之前,实际上也考虑到特殊移民的在迁移、安置期间的基本生活的保障问题。在1930年1月30日的决议中已明确地指出,要给特殊移民留下日常生活最必需的物品,包括简单的生产资料、最低限度的粮食储备以及500卢布的现金。2月2日颁布的第4421号命令,更详细地划定了携带物品的种类和总重量,其中还明确规定了特殊移民可带上两个月的粮食。各地方政权机构按照联共(布)中央的指示精神对特殊移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做了相应的规定。
为了统一使特殊移民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的保障,1930年4月24日苏联贸易人民委员部向各联盟组织下发了重要的指示,规定向特殊移民发送以下数目的粮食及生活用品(按吨计):产品的名称北部边疆区
乌拉尔 西伯利亚总计
面粉17403 136589743 40804
米
1647 1363 989 3999
糖 567.7 437.8
313.91319.4
植物油 273.6 166.1
113.6 553.6
鱼
5144 39652844 11953
肥皂 100
100 60
260
燕麦 2160 36002400
816
按照上述标准,每个特殊移民平均每天可以获得:干面包300克;大米20克;蔬菜类产品30克;糖6克;植物油6克;鱼75克。食品的供应标准也有所浮动,如从事移民开垦土地的成年人每天的干面包应为500克或每月10.8公斤的面粉。对于特别遥远地区的特殊移民,供应标准定为每人每天30克;对于未满12周年的儿童,糖的供应标准可提高至12克。植物油要特别供给不满12周岁的儿童。[3](p241)
然而,在初期的迁移、安置过程中,对特殊移民的实际供应是相当有限的,有的地方甚至徒有其名。特殊移民的饥饿现象不是偶然产生的,它是依靠行政手段、大规模、疾速地消灭富农的一个“副产品”。
从特殊移民的社会属性来看,在运动开始之前,他们在本质上属于个体农民。他们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他们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并向国家提供了最多的商品粮。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以及相对封闭的社会生活使他们似乎感到不需要国家的存在。但从1930年春开始,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首先,无限度的剥夺行动使特殊移民的经济基础被彻底击溃,他们已失去了从事简单再生产的物质条件。按照有关的规定,对剥夺的富农户只保留了非常有限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然而这一部分生活和生产资料在迁移之初又遭到了“第二次剥夺”,以充作迁移所需的“实物基金”。因此,有的特殊移民在迁移之前除了自己随身穿戴的衣物之几乎是一无所有,行前所规定的500卢布以及两个月的粮食只是停留在文字上。在安置过程中,由于林业、矿业部门对特殊移民的蔑视政策,特殊移民的劳动所得入不敷出,根本无法供给家庭甚至个人的生活所需。如在乌拉尔州的杰涅日金林区,特种移民在几个月的劳动期间,净挣了83968卢布57戈比,而他们的支取的生活费用则为132927卢布又65戈比,[4](p90)这样算来,特殊移民不仅没有收入反而还倒欠林区的生活费用。拖欠特殊移民劳动报酬的情况也非常普遍,拖欠期限2—3个月不等,最长的达到6个月。特殊移民还要交纳各种形式的款项,如股金、公债、份粮、托儿所维持费及工资提成等等,克扣率达到了25%甚至更高。[4](p95)
其次,在政治上特殊移民失去了选举权,这也就失去了公民权。在迁移过程上他们受到“格别乌”(注:即国家政治保卫局(Госудау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1922年1月6日建立。1923年11月2日建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бьединё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以领导各盟共和国的格别乌。在30年
代消灭富农的运动中,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格别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4年后国家政
治保安总局划归苏联内务部管辖。)人员的押送,没有任何行动自由。随着“特殊移民村
”(注:1930年7月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特殊移民村》的
决议,对特殊移民村的区域选定、管理职能、义务和法规都作了详细的规定。该决议是
正式建立特殊移民村的重要标志。)的建立,特殊移民被集中在特定的区域,由国家政治
保安总局进行专门的管理。“特殊移民村”实际上成了变相的集中营,特殊移民也就成
了变相的“政治犯”。特殊移民在经济、生活和文化上的开销完全自理,凡拒绝强制劳
动或逃跑的特殊移民,轻则被罚款或被拘留,重则送往劳改营。在这种境况下的特殊移
民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他们没有劳动热情,情绪低落,怠工、逃跑的现象已司空见惯。
另一些特殊移民甚至根本不清楚自己为何被迁移,他们对迁移安置抱有幻想,认为迁移
只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他们仍会回到原来的居住地,因此,他们在等待、在观望。
与此同时,特殊移民还将面临来自社会的压力,在苏联全国上下掀起的消灭富农运动几乎渗透各行各业。“富农是苏联社会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必须予以消灭”,这些社会宣传使特殊移民在社会上已无立锥之地。一些医疗部门甚至发出号召,不让医学院毕业生向特殊移民提供医疗求助。
可见,特殊移民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与剥夺、迁移之前的富农已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的社会属性经历着急剧的变化。他们与土地的分离,这使他们失去了维持再生产的基础和手段,也使他们失去了作为农民的社会属性。他们与自己个人财产的分离,使他们再度一贫如洗。他们失去了选举权,政治上受到压制和行动上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生活来源已不是建立在过去的自给自足、市场供给的经济关系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单一渠道、单向供给的配给制基础上的。这种由多样化的生活来源、收入来源的经济关系突然向一种非经济的行政关系的转化,给特殊移民迁移后的生产、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由此不难看到,特殊移民的基本生活来源,在迁移和安置期间只能依靠政府通过行政调拨方式来实现,他们生存的命运已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从实施剥夺、迁移和安置行动的主体——国家各级政权组织来看,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基本的粮食储备,仓促行动、上下关系不协调、地方工作不到位是导致食品供应出现困难的重要因素。
中央在迁移之前没有制定食品供应的专门预算,只是就特殊移民的基本物质保障做了文字上的规定。这些规定是硬性的,并由地方政权组织具体实施。但地方政权组织却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被剥夺的富农很难确保有中央所规定的基本物质保障,特别是粮食和种子;另一方面,地方政权组织也没有用于迁移工作的专门经费,但迫于完成任务,地方政权组织便开始在极短的时间内向特殊移民征收迁移费用,建立所谓“实物基金”。“实物基金”实际上是迁移行动的启动资金,这种基金既包括特殊移民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如粮食等,也包括他们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如劳动工具、种子、马匹、饲料等。这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是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地方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统一看管和发送。因此,“实物基金”是特殊移民迁移过程中食物供应的物质基础,是迁移行动的重要的物质保证。但由于征收“实物基金”的工作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许多区委会、村苏维埃在征收“实物基金”的问题上采取了被认为是“与富农站在一起”的消极态度,因此,绝大多数地方政权组织都没有按照迁移人数的比率征足实物基金。在对西伯利亚15个地区调查统计中只有两个地区即比特科斯克区、切列帕诺夫斯克区完成了“实物基金”的征收任务,仅占所有地区的13.3%,其中瓦新斯克地区仅完成了规定任务的24%;在“各地区迁移中的缺点”一栏中,明确标明“实物基金不足”的地区有4个,有两个地区的区执委会主席因“草率行事”、“不尽职”而送交法庭处置。[3](p237)“实物基金”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得到保障,这就对特殊移民的供应问题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果不其然,在迁移之初一些地方就宣布告急,向中央求助。鉴于财政压力,特别是无力要向迁移的特殊移民提供每天必须的粮食供应,早在1930年2月15日西伯利亚边边疆区执委会就向联共(布)中央就关于特殊移民的粮食供应问题请求中央的援助。[3](p239)在这封直接发给苏联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和俄罗斯联邦贸易人民委员艾斯蒙特的请求信中,西伯利亚边疆区执委会副主席巴佐夫斯基提出,由于西伯利亚边疆区不能组织粮食供应以及没有用于保障迁移工作的粮食基金,要求向西伯利亚边疆区划拨专门的粮食基金,包括粮食4288吨和饲料粮13240吨。粮食的发放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处协同相关组织在安置地区进行。请求信最后强调:“请不要拖延答复,因为迁移已经开始,而粮食的发放也应在现在,即在春季道路泥泞之前进行……”[3](p239)
中央于是进行了紧急调运,以解决西伯利亚等重点特殊移民接受地区的燃眉之急。但由于国家“粮食储备紧张”,[3](p239)以及其他一些客观原因,援助的到位率非常有限。如1930年4月11日西伯利亚边疆区向贸易人民委员部请求援助的3491吨面粉,只下批了1461吨,仅满足了全额的42%。[3](p239)到1931年第三个季度,从喀山运往乌拉尔的食品和工业用品只占应发货物的47.4%。[4](p93)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援助仅仅还是中央向边疆区的划拨情况,这些食品和工业用品再通过州及州以下的行政组织层层下拨,真正落到特殊移民手中粮食和食品仍是一个未知数。
特殊移民的迁移行动是由中央、边疆区、州、区、村专门成立的“三人小组”直接领导的。“三人小组”的成员由格别乌全权代表、各地执委会代表以及各地检查机构的代表组成。格别乌派往各地的全权代表是行动小组的领导核心。各边疆区、州、区以及村苏维埃协助“三人小组”的工作。但事实证明,地方各级政权组织与“三人小组”的行动缺乏有效的协调和配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地方的工作首先面临的是人手严重不足的问题。1929—1930年度,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从肃反委员会的后备工作人员中抽调了800人以扩充各地全权代表的人数,其部队的人数只增加了1100人。[1](p161)很显然要完成如此庞大的迁移、安置工作,这些人员是远远不够的。为此,中央委员会决定从“工业发达州”动员25000名党员工作四个月,帮助地方完成剥夺、迁移富农的工作。但在具体的行动中人员缺乏的问题仍很突出,如在乌拉尔州,30多万户约150—160万特殊移民只配备了328名专职管理人员。鉴于这种情况,该州警卫司令员巴拉诺夫认为,“这个编制极其不足,需要大扩充。”[2](p162)迫于完成任务的压力,一些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地方民警不得不转变角色加入到行动的行动之中。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各级组织几乎包揽了包括押送、迁移、分发食品等各项工作,但由于他们多是临时抽调的工作人员,对地方的情况又不熟悉,这就妨碍了他们的工作进程。
地方各级政权组织在消灭富农问题上认识不清,有的地方还对中央的指令还有抵触情绪。这种情况特别表现在区委和村苏维埃中。一些地区和村苏维埃在剥夺富农的过程中“袖手旁观”,对上级规定的建立实物基金的任务敷衍了事。一些村苏维埃甚至将好的马匹、马车留给自己使用,而将劣马和报废的马车用于迁移富农。作为接受特殊移民的地方组织,按照中央的规定,它们应做好一切接纳特殊移民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勘测土地、土质、水源、统计人数等,并及时向上级部门进行汇报,但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得非常缓慢。在一些地方,特殊移民已被送达目的地,但却找不到负责安置工作的地方工作人员。无奈之下,这些特殊移民只好风餐露宿,等待着相关部门的救助。特殊移民的食品和日用品的供给,主要是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监督下由各地消费合作社进行发放,绝对禁止其它同业组织的参与。由于地方负责供应特殊移民的经济部门和相关合作社工作不到位、管理混乱,不少地方出现了将供应特殊移民的物品积压在仓库里的情况。一些地方的食品发放工作也非常草率,既不进行特殊移民的登记,核实其准确的人数,也不对物品的发放做详细的记录,至于供应的进度和相关的情况更无从查阅。这种在格别乌监督下带有垄断性质的食品供应工作,既没有严密的实施条例,也没有相应的监督措施。最终导致食品供应的渠道不通畅,“粮食和工业品的每次拨付都屡屡中断。”[2](p162—163)
在谈到为何会出现混乱局面的原因时,时任乌拉尔州警卫司令部司令员巴拉诺夫做了非常精道的概括。他认为,粮食及其它物品供应屡屡中断的原因,“不仅中央和州的组织有责任,北方的合作社组织也有责任。”言下之义,中央、地方、基层组织责权不明、缺乏协调、玩忽职守、疏于管理是食品供应出现差错的重要技术原因。针对北方边疆区在安置特殊移民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类似困难,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指导员斯涅特科夫在向中央的汇报中提出,必须加强中央对地方迁移、安置特殊移民工作的统一指导和管理,解决运输问题,做好土地勘察和整理,备足特殊移民迁移之前的粮食储备,建立“代理机构”以协调地方的工作,否则地方政权组织将无力完成“如此宏大的任务”。[1](p228—230)
特殊移民中间出现饥饿的情况,引起了联共(布)中央的注意,中央也采取了相应的应急措施。如加强对各个供应环节的管理,明确责任;逐步改善特殊移民在工业企业中的相关待遇;国家拨出专款向特殊移民划拨土地,提供种子贷款,允许购买农用牲畜和农具,免除特殊移民一年的税赋等,但特殊移民中的饥饿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制止,而是汇入了1932—1933年的大饥荒之中。
四、从殊移民的饥饿现象看稍后苏联的饥荒
“ГОЛОД”一词在俄文中有“饥饿”和“饥荒、饥馑”两层意思。“饥荒”应具有规模性和严重性的特点,它是因大量人口挨饿死亡而严重影响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饥饿现象。对于三十年代初期(特别是指1932—1933年)在苏联一些主要产粮区是否存在饥荒问题,过去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近些年来,对这个问题研究进展表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的促成下,在苏联农村特别是一些粮食生产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居民挨饿或因饥饿而死亡的现象。不仅如此,从不断公开的当时联共(布)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谈话中也反映出,在当时的苏联农村存在饥荒问题。如1940年斯大林曾承认:“我们这里有2500—3000万人挨饿”。[5]莫洛托夫谈到了“饥饿的1933年”,认为“那是充满痛苦的一年。”[6](p453)卡冈诺维奇虽然认为康克维斯特(R.Conguest)(注:美国苏联问题专家,著有《悲哀的收获:苏联集体化运动和令人恐怖的饥荒》等著作。)对乌克兰和全苏联农村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的统计是“谎言”、是“捏造”,但也承认,“饥荒不是由于歉收所致,而是因为播种的差错所致”。[7](p113)因此,三十年代初期在苏联农村曾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已成为了一个得到普遍承认但带有“模糊”特点的结论。
目前争论最大的、意见分歧最多的是这次饥荒导致了多少人员的损失?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规模的饥荒?
对于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问题,学者们提出数字有600万、750万、1000万、1600万。[8](p8)对于这些数字,学者们都提出了自己的理由和相关的依据,但总体而言,这些数字的得出,主要不是依靠精确(实际上也做不到)的统计得出的,而更多是建立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的。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饥荒?多数俄罗斯学者在分析这一问题的时候都把它与全盘集体化运动、斯大林的农村政策联系起来,在一个共同的时代背景下来进行其它具体原因的探讨。总的来说,自然原因与现实原因相比,现实原因为主;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相比,主观原因为主;政治原因与经济原因,政治原因为主。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果多因论。这是一种主流观点,即认为,全盘集体化运动、大规模消灭富农阶级,人为地激化了阶级矛盾,农村社会的动荡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劳动力流失,牲畜锐减,没有节制地增加国家粮食征收计划,是导致饥荒的重要因素。[9]
有计划的饥荒论。这个论点主要是针对部分学者所持的“斯大林本人对下面的情况并不了解”的观点而提出来的。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们认为斯大林有目的、有步骤地组织了这次饥荒;[10]还有的学者是从民族歧视的角度来揭露斯大林大俄罗斯主义倾向提出这一论点的,他们认为乌克兰1932—1933年的饥荒是斯大林执行种族灭绝政策的结果。
收购粮食论。一些学者认为,虽然1931—1932年的粮食产量有所减少,但不是灾难性的。强制性、无节制的粮食征购是导致1932—1933年农村饥荒的主要原因。[11]
粮食出口论。起初,这种观点仅仅在民间流传。[12]而随着一些文献材料的公布,这一观点越来越得到了证实。在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私人信件公布以后,有关不惜任何代价竭力大量出口粮食的事实已真相大白。卡冈诺维奇后来也承认:“出口粮食,这是事实。这是正确的,因为要用钱去买机器、进口设备,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13]
以上这些观点的着眼点虽各不相同,但论点的基本倾向是较为明晰的,即“大转变”是这一时期苏联农村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时代背景,依靠行政手段、快速地完成农业的战略性调整,直接导致了极端的农业政策的出台。农村的饥荒就是执行这些农业政策的直接结果。
因此,特殊移民中的饥饿现象与苏联农村的饥荒,是这一时期极端的农业政策所导致的两个相似的结果。特殊移民的饥饿现象在前,苏联农村的饥荒在后。前者是开端,后者是延伸,是一种面的铺开。特殊移民的饥饿现象主要出现在非全盘农业集体化的边远地区,而饥荒却发生在集体化程度很高的产粮区。截然不同的地区产生相同或相似的结果,这更进一步说明了一种非自然的外力的作用。这种外力作用对于特殊移民而言是专政机关格别乌的力量,对于苏联农民而言则是党的组织、政权组织以及其它社会力量。富农转化为特殊移民,农民则转化为集体农庄的庄员,即农业工人,没有专政力量、行政力量的参与,这一过程是无法完成的。饥饿现象和饥荒的出现,无不透射出近乎相同的导因:第一,剥夺无度。如果说剥夺富农户的财产、强制他们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是威胁他们的生存和生产权利的极端手段的话,那么在同一时期对农民没有节制的粮食征收运动已经把他们推到了绝路,即使这些地区是全苏有名的产粮区。第二,保障无着。如果说特殊移民在安置地无法获得合理的收入,无法得到国家给予的食品配给,那么在广大的农村,那些参加了集体农庄的农民,或者还没有参加集体农庄的个体农民同样面临因新旧生产关系的交替所带来的供需路途的中断和堵塞。第三,生产无望。如果说特殊移民被专政的力量关押在变相的集中营中,他们失去了自主劳动的自由、缺乏劳动热情和主动精神的话,那些被强制参加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同样因为“没有新的工作方法”而缺乏主人翁精神,从而使生产陷入困境。
所以,由消灭富农阶级而在特殊移民中间引发的饥饿现象是苏联农村稍后发生的大规模饥荒的前兆。无度的剥夺,没有成型的社会流通、供给和保障体系,对农业劳动者极度的行政管制是导致特殊移民饥饿现象和苏联农村大规模饥荒的共同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