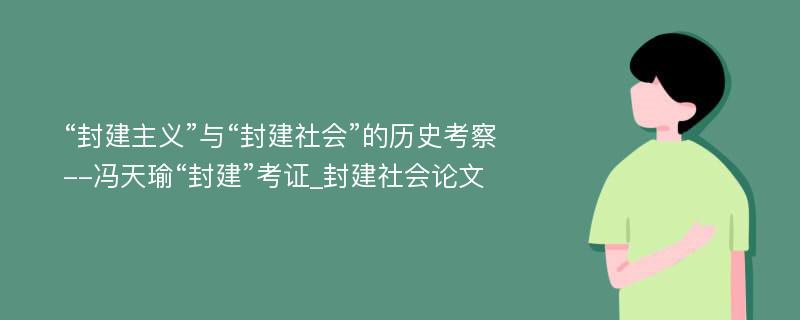
“封建”与“封建社会”的历史考察——评冯天瑜的《“封建”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封建论文,封建社会论文,历史论文,评冯天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①是近年来颇受史学界关注的一部著作。作者认为我国史学界流行大半个世纪的“封建社会”论,乃是一种“泛封建观”,与“封建”的“本义”、“西义”和马克思的“原论”均有悖离。为了纠正这种“偏失”,作者还提出一个包容古今中西词义的历史分期的标准。下面拟就其中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一些商榷意见。
一、关于历史分期的标准
历史是一条变动不居的长河,但历史又是有阶段性的。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对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曾发表过各种不同的意见。孔子关于“天下有道”与“天下无道”之说②,韩非提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的概念③,都反映了他们的历史阶段观。近代以来,受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影响,梁启超、夏曾佑、刘师培等人都曾尝试以新的观念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如夏曾佑编写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就引进了“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等概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唯物史观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逐渐扩大。以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为代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曾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研究和讨论。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时起时伏,史学界迄今未能取得共识,其中得失固然值得认真梳理总结,但不能说讨论没有得出结论就是白费功夫。历史学中有些深层次的问题,是很难得出一致意见的。但各种意见的互相问难和商讨,本身就构成历史学发展的重要篇章。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不同于某个历史人物生平事迹或某个名物制度的考订。不同的历史观对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历史分期会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文化史观的学者大多着眼于文化形态的变动,而唯物史观的学者则注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不仅如此,由于历史现象复杂,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即便是相同历史观的学者,对历史分期也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冯天瑜把分期问题的意见分歧归咎于各家各派在命名标准上没有共识。为此他提出确定历史分期的四条标准:“制名以指实”,“循旧以造新”,“中外义通约”,“形与义切合”。冯天瑜说,按照这四条标准来为历史分期命名,便可以“对词义的古今推演、中西对接,有所会心,易于受用”④。但是这种古今中外兼容并包的“标准”果真合理和管用吗?我们不妨略作分析。
“封建”一词见于《诗经》和《左传》,文献解诂词义为封邦建国,以藩屏西周王室。这一点历来在史学界并没有异议。但西周分封的邦国究竟是什么社会,各家看法却有所不同。问题在于“封建”的历史内涵亦即其“本义”,并不限于建立一种藩屏王室的政制。《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封建”,分封鲁公“殷民六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分封康叔“殷民七族”,“聃季受土,陶叔授民”;分封唐叔“怀姓九宗,职官五正”。鲁公和康叔“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唐叔则“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段史料说明西周分封制度涉及了统治族与被统治族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其“本义”相当丰富和复杂,也留下了值得探讨的空间,远不是所谓“封邦建国”的“政制”所能概括的。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认为周代是奴隶社会,他把西周的“封建”制度称为一种有别于“以封建的经济组织为基础之封建制度”的“殖民制度”⑤。钱穆1940年出版之《国史大纲》,只讲西周是“封建政体”,不讲西周是封建社会。但他又称“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与后世统一政府只以封建制为一种政区与政权之分割者绝然不同”⑥。而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西周封建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既没有把西周的“封建”说成是一种武装殖民,也不把“封邦建国”的政制视为封建社会论的主要依据。范文澜明确说:“封建制度与宗法及土地是分不开的”,“在宗法与婚姻的基础上,整个社会组织贯彻着封建精神,而最下层的真实基础自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⑦。可见,对西周社会性质认识的分歧,关键不在于命“名”标准没有共识,而在于对西周社会经济形态之“实”理解的不同。
“封建”的“本义”,有经解家理解的“古义”,也有近现代史学家理解的“今义”。就历史研究来说,不能片面地拘守“古义”而排除“今义”。对“封建”本义的认识,不是哪一个学者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通过不断的探讨,求同存异,去伪存真,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内涵。在分期问题讨论中,有的学者因为西周实行分封制度,就称之为封建社会,但他们并不考虑西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具有什么性质。也有的学者称西周为封建社会的主要依据不是分封制度,而是西周领主制和农奴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还有的学者则认为西周的分封制实际上是古代的一种氏族殖民制度,其经济基础乃是奴隶制。如果再细分一下,意见就更复杂一些。同样主张西周是封建社会的学者,有的认为当时的主要直接生产者是农奴,有的则认为是农民。同样主张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学者,也有的认为主要直接生产者是奴隶,而有的则认为是农民。西周奴隶制论者和西周封建制论者,对于井田制都既有肯定也有否定的不同认识。诸如此类的意见分歧,显然不是冯天瑜所说的“名实不符”问题,也不是他提出的四条标准所能解决的。
冯天瑜的最大误区,是把语源学的研究和历史学的研究混为一谈。经解家对“封建”一词的解释是“封邦建国”,历史研究必须了解“封建”一词的语源和经解家的解释。但如果把“封建”的“本义”只限于“封邦建国”,并且用它来限制“封建”概念涵义在后代的发展,这就有点近乎“胶柱调瑟”和“削足适履”了。一般说来,“概念”应该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一个名词在语源学上的“本义”,可能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也可能并不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而且,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历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必须从事物的实际内容出发,而不是从词语概念出发。恩格斯在批评杜林的先验主义方法时说:“首先,从对象构成对象的概念,然后颠倒过来,用对象的映象即概念来衡量对象。这时,已经不是概念应当和对象相适应,而是对象应当和概念相适应了。”⑧这种研究方法是我们应该避免的。
冯天瑜试图以他的四条标准来统一人们对“封建社会”概念的认识,但恰恰是他对“封建”和“封建社会”的论述,往往使他陷入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境地。比如严复以“封建之制”翻译西欧中世纪的feudalism,冯天瑜认为这是“沿着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作合理引申”,“从而达成古义与今义的因素互见、中义与西义的交融涵化”⑨,这对严复可说是高度肯定的评价。但是当冯天瑜指责有些学者认为秦汉至明清是封建社会时,他又引用侯外庐先生对严复“中外词汇相混,语乱天下”的批评,说“有学者将新名‘封建’的概念误译严厉批评为‘语乱天下’,并非过分之词”⑩。与冯天瑜反对秦汉是封建社会不同,侯外庐是主张汉代封建社会法典化的。他虽然批评严复误译,但又说“我们倒也不必在此来个正名定分,改易译法”(11)。严复的“封建”译名是否误译,还可以讨论,但冯天瑜前后两种评价,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又如,严复认为夏商周是封建制,冯天瑜也说:“如果把夏商称为氏族封建制,那么西周则可称为‘宗法封建制’。”(12)夏朝历史尚待证明,姑且不论。商朝已进入文明社会,当无问题,但把商朝也说成是“封建制”,似乎已离开了传统文献“封邦建国”的“古义”,与西欧的feudalism更不搭配,这与冯天瑜的四条标准又岂能符合呢?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西周社会性质的判断虽然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主张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作为历史分期的主要标准。正是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指导下,西周史的研究才摆脱了传统的以“封邦建国”为主要线索的旧框架,对西周的生产力水平、土地制度、国野之分、阶级关系等重要问题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一切冯天瑜并不是毫不知晓,他在《“封建”考论》一书中也提到“国-野”对立、“国人-野人”分治“是西周封建制的基本格局”,提到西周的封建制“其根基是井田制度,此制以劳动的自然形态(劳役地租形态)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但是冯天瑜却一再强调“封建”制的“本义”是“封邦建国”、“封爵建藩”,批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着眼于社会经济形态变化的研究是“泛封建观”。他认为“封建”制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封建’特指殷周政制,尤其是指西周盛行的‘封国土,建诸侯’之制”;“广义‘封建’是狭义封建的延伸,指殷周以至明清列朝列代的种种分封形态,包括秦汉以降在郡县制主导下推行的封爵制”。冯天瑜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秦至清的两千余年,政制的主位是郡县制,封建制不过是辅佐性的偏师,郡县制与封建制两者均归于专制君主中央集权政治的总流之下”(13)。也就是说,按照冯天瑜的四条标准的“考论”,“封建”制归结为一种“政制”,而且只能从狭义去理解。这究竟是推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得到解决,还是把问题倒退到传统的“封建制”与“郡县制”政制的讨论呢?
二、封建社会的“中外义”如何“通约”?
冯天瑜在《“封建”考论》中,除了要求封建社会命名“必须遵循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之外,还要求“命名须观照相对应的国际通用术语,其内涵、外延均应与之吻合或接近,以与国际接轨,而不可闭门造车,此谓之‘中外义通约’”(14)。这涉及到中外历史比较研究问题,冯天瑜的意见也是很难令人赞同的。
Feudalism(封建主义、封建制度)的命名,源于欧洲学者对中世纪社会经济形态的概括。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一书的导论中,对feudalism的定名过程曾作了扼要的说明。他指出拉丁文“封建的”(feodalis)早在中世纪就存在,法文“封建主义”(féodalité)可追溯到17世纪。但在相当长的时期,这两个词只是在狭隘的法律意义上使用。1727年,德·布兰维利耶伯爵的《议会历史文书》出版,在标称社会状态的意义上使用了“封建政府”和“封建主义”名词。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法令形式宣布“国民议会彻底废除封建体制”,封建主义这一概念得以在民众当中传播。
欧洲“封建主义”、“封建社会”的命名过程,说明随着中世纪历史研究的深入,它的历史内涵也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例如领主的采邑最初被认为是封建社会的特征,但后来“‘封建主义’和‘封建社会’涵盖了一整套复杂的观念,在这套观念中严格意义上的所谓采邑不再占有突出的地位”(15)孟德斯鸠在谈到法兰克人的封建法律时,曾批评那种认为日耳曼人征服罗马帝国之后就把一切土地都变成采地并建立普遍的奴役制度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有一天,我将用一本专著来证明,东哥特人的君主国的计划和当时其他野蛮民族所建立的一切君主国的计划,是完全不同的;来证明,说‘这一件事情在东哥特人是如此,所以在法兰克人也是如此’,是如何的荒谬。”(16)正是由于“封建社会”的“名”与“实”之间有一个变动不居的磨合过程,所以布洛赫一方面说:“应当承认,封建主义这个前景广阔的词汇,即使在看来有充分理由采用它的时候,也是一种不恰当的选择。”另一方面又说:“假如史学家仅仅把这些词语当作现代用法上认可的标签,来标明他仍须解释的事物,那么他不必有任何顾虑。”(17)他还说:“把‘封建主义’一词应用到这样限定的欧洲历史的一个阶段,有时会被做出极不相同的、几近对立的解释,但是这个词语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人们已经本能地承认了这个词语所表示的这个阶段的独特性质。”(18)
对于使用“封建社会”(feudalism)这一词语的许多欧洲学者来说,他们并非不知道“封建社会”一词并不足以涵盖中世纪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问题是历史研究必须找到足以揭示一个时代与其他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没有代表整个的一组现象的概括性词语,不仅历史学无从谈起,而且一切知识领域的论说都无从进行。”(19)所以布罗代尔才说:“对于封建主义这个经常使用的词,我与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一样感到本能的厌恶。他们和我都认为,由通俗拉丁语‘feodum’(采邑)演化而来的这个新词仅适用于采邑制及其附属物,而与其他东西无关。把十一到十五世纪之间整个欧洲社会置于‘封建主义’之下,正如把十六到二十世纪之间整个欧洲社会置于‘资本主义’之下一样不合逻辑。”(20)但布罗代尔又承认:“所谓封建社会(另一个常用的说法)能够确指欧洲社会史的一个长阶段;我们把封建主义当作一个简便的标签使用,自然也未尝不可。”(21)
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一书中曾经给自己提出一个“令人深感兴趣的问题”:“在其他的时代和世界的其他地区,是否存在其他一些社会形态,其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与我们西欧的封建主义具有充分的相似性,从而使我们可以将‘封建的’这一词语同样地应用于这些社会呢?”(22)在该书的末章“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封建主义”中,他引用了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不同意见。孟德斯鸠认为,“封建法律”的确立是一种独特现象,是“世界上曾经发生过一次,大概永远不会再发生的事件”(23)。而伏尔泰则认为,“封建主义不是一个事件;它是一种有着不同运动形式的古老的社会形态,存在于我们所在半球的四分之三的地区”。布洛赫接着说:“现代学术界总体上接受伏尔泰的观点。埃及封建主义、希腊封建主义、中国封建主义、日本封建主义——所有这些形态和更多的形态如今已是人们熟知的概念。”(24)他认为,“很显然,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所有这些被赋予‘封建’之名的社会,仅仅是因为它们与西欧封建主义具有真正的或假设的——相似性,这个基本社会类型所具有的特点,是所有其他社会必须加以参照的,因此,明确这些特点具有头等重要性”。(25)在布洛赫看来,“就像母系氏族或父系氏族甚或某些类型的经济体,以十分相同的形式出现于非常不同的社会中一样,与我们社会不同的一些社会,会经历很相似于我们所描述的这个时期的一个阶段,这绝非不可能。果真如此,我们就有理由称处于这一阶段的这些社会为封建社会”(26)。
布洛赫和布罗代尔对使用“封建社会”这个词语并不满意但又不得不在自己的著作中继续使用它,实际上是反映了西方历史学家在掌握“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这个方法论要求时的一种无奈心情。他们相信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既有多样性又有统一性,但是他们在多样性中没有能够寻找到反映统一性的科学的切入点。其实,这个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早就解决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对欧洲的封建制度作了深入的研究。可以说,对封建制度的研究,为他们创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他们并没有在资产阶级学者所描述的封君封臣、采邑封土以及农奴制等通常认为是封建制度的特征面前止步,而是深入探讨这些特征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同国家的封建制度其共同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各种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这才有可靠的根据把不同国家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从而使封建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得到合理的解释。
近代中国,最早将欧洲封建社会与西周“封建”制相类比的学者是梁启超。1899年,他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中说:“中国周代国体,与欧洲希腊国体,其相同之点最多,即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是也。”(27)梁启超所说的“欧洲希腊国体”,涵盖了欧洲的古典古代和中世纪,反映他对欧洲“封建时代”的了解其实很有限。1901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把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音译为“拂特之制”。但他随后翻译的爱德华·詹克斯的《社会通诠》,却把feudalism译为“拂特封建制”或“封建制”。其后“封建制”与“feudalism”之对译遂为我国学界广泛接受。严复是饱学之士,他对feudalism的翻译肯定是经过斟酌而不是随意的。起先音译“拂特之制”,想必考虑到中西历史的差异。后来意译为“封建制”,有无受到梁启超意见的影响,不得而知。但可以设想的是,他也看到了feudalism的社会形态与西周的“封建制”有某些相似之处(比如与封君封臣相适应的封土制度等)。Feudalism与“封建”的对译是否准确,史学界是有争议的。前文说过,侯外庐先生早在1956年就对此提出过不同意见。侯外庐是秦汉封建论者,他赞同西周“封建”是部落殖民说,所以对严复把feudalism译为“封建制”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不妨退一步想,如果严复是认为欧洲的feudalism与西周有类似之处,因此把音译“拂特”改为意译“封建制”,似乎也不好就简单地说他是“误译”。
冯天瑜在《“封建”考论》中,对于严复是否误译的问题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当他要批评“封建”概念误植时,他就引用侯外庐关于“中外词汇相混,语乱天下”的批评;而当他要论证中国只有西周以前是“封建时代”时,他就高度评价严复“创制译词‘封建’”,称“严复‘封建’包蕴的概念,兼容该词的古汉语义与feudalism的西义”。冯天瑜还十分赞赏黄遵宪称日本前近代社会为“封建”的用例,认为黄遵宪的语境“古义与近义、中义与西义贯通无碍,实属高明之语用,是清末民初开眼看世界的人士使用新名‘封建’的先导”(28)。冯天瑜称赞严复、黄遵宪对“封建”一词“古今融会、中西通约”,说来说去只是“封建”制有别于“郡县”制的传统政制理念,而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内涵有原则区别。事实上,在严复、黄遵宪的历史观念里,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我们今天包蕴“中义”与“西义”的“封建”概念的,怎么能说他们已创制了“古今融会、中西通约”的“封建”新名呢?
在历史研究中,中外历史可以互相比较和参照。但是统一性只能寓于多样性之中,所谓“中西通约”的提法并不科学。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29)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无论是西周封建论者、春秋战国封建论者或秦汉魏晋封建论者,都着眼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和方法,而不是冯天瑜所强调的与“封建”古义挂钩、与西义“通约”。他们认为,从秦汉至明清,无论是封建国家或封建地主阶级,都占有大量土地,并通过各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超经济强制役使农奴和农民,剥削其剩余劳动乃至一部分必要劳动。正像恩格斯在谈到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剥削”时说的,中国“农民虽然保有自己的土地,但他们是作为农奴或依附农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必须以劳动或产品的形式给地主进贡”(30)。地主阶级的大土地所有制与一家一户的农民个体生产经营的矛盾,以自给性生产为主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封建国家和法律维护贵族和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些封建主义的特征,秦汉以降的中国社会,和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情况都是相似的。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除国有土地之外,无论是地主的土地或自耕农的土地都可以合法地买卖(但并非完全“自由”),不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土地不能合法买卖;中国的地主不像欧洲的领主那样有独立的司法权;中国的封建商品经济比欧洲中世纪的商品经济发达;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大多数时期沿袭秦朝的郡县制,保持了大一统帝国的局面,不像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国家那样分裂割据;中国的封建王朝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欧洲一些封建国家的王权则长期相对软弱,只是到中世纪末期君主专制才得到加强。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秦汉至明清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这些相似之处和不同之点,正是历史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表现。
三、“封建地主制”符合马克思学说的“原论”
冯天瑜认为把秦至清的社会称为“封建社会”不但与“封建”的“本义”和“西义”不合,还有悖于马克思有关封建社会的“原论”。现在就让我们辨析一下这种批评是否能够成立。
“非贵族式土地所有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这是冯天瑜加在马克思头上的一个重要观点。照他说来,土地占有的“贵族性”,“是一个社会是否为封建制的分水岭”。封建领主的地产“是由王者或上级领主封赐而来,不得买卖与转让”。“是否保持土地的‘不可让渡’(或译作‘非让渡性’),是区分封建制与非封建制的重要标准。”(31)
冯天瑜举出马克思主张“非贵族性土地所有制不应列入封建主义”的论据,主要是马克思在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中的一段批注:
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罗马就是证明)和荫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至于说封建主(执行监察官任务的封建主)不仅对非自由农民,而且对自由农民的个人保护作用(参看帕尔格霍夫著作),那么,这一点在印度,除了在教田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罗马-日耳曼封建主义所固有的对土地的崇高颂歌(Boden-Poesie)(见毛勒的著作),在印度正如在罗马一样少见。土地在印度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贵族性的,就是说,土地并非不得出让给农民!]不过柯瓦列夫斯基自己也看到一个基本差别:在大莫卧儿帝国特别是民法方面没有世袭司法权。(32)
柯瓦列夫斯基认为印度的土地关系在阿拉伯人和蒙古人统治时期出现了类似欧洲中世纪封建化的过程,马克思不同意他的意见。马克思指出,柯瓦列夫斯基因为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和“荫庇制”,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但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印度并不存在农奴制。马克思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但是冯天瑜由此引申说,没有农奴制和“非贵族性土地所有制”都不属于“封建主义”,这却是对马克思“原论”的误读,是把“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曲解成“封建主义”的一般形态,忽视了“封建主义”的多样性。其实马克思并没有否认印度的社会也有“封建主义”的成份。他谈到印度“执行监察官任务的封建主”对农民的“保护作用”,尽管“除了在教田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柯瓦列夫斯基在《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的另一处说:印度在穆斯林征服者统治下,“农村居民仍然根据公社所有权或私人所有权照旧占有他们的土地。变动多半只涉及到人,而不是涉及到土地。占有者由自由人变为依附人,同时,他们的占有也由对自主地的占有变为封建的占有”(33)。马克思批注说:“最后这一点仅仅对于领受了第二类或第三类军功田的伊斯兰教徒才有意义,而对于印度教徒至多在下述程度上才有意义,即他们不是向国库,而是向由国库授予权利的人缴纳实物税或货币税。”(34)这也说明,马克思并不完全否认印度也存在封建的土地占有制。
柯瓦列夫斯基所说的印度土地制度,涉及“柴明达尔”领地的性质问题。柴明达尔在印度土地制度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是贵族而是占有地产的田赋征收者(包税人)。柯瓦列夫斯基认为柴明达尔掠夺了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而让后者保留土地的世袭使用权。关于“柴明达尔”的性质应如何看待,以及印度在被英国征服以前是否已进入封建社会,马克思所说的印度和亚洲的农村公社其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又应如何理解,中外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马克思在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的摘要批注中曾几次提到德里的“奴隶王”(或译“奴隶王朝”),这是否代表马克思对古印度社会性质的认识,我们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马克思只是说印度不存在农奴制和“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并没有说西欧中世纪式的“封建主义”是唯一的“封建主义”形态。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谈到欧洲中世纪世袭的长子继承权时说:“长子继承制是‘独立的私有财产’的抽象”,“独立性就是以不可转让的地产为最高表现的私有财产”(35)。马克思是要说明“长子继承制是土地占有制本身的结果,是已经硬化了的私有财产,是最独立和最发达的私有财产”,批评黑格尔倒因为果,倒果为因,把长子继承制描写成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支配权。冯天瑜脱离马克思论述的具体语境,引申说:“是否保持土地的‘不可让渡’(或译作‘非让渡性’),是区分封建制与非封建制的重要标准。”(36)但只要认真阅读马克思的上下文,是得不出冯天瑜所说的这种结论的。马克思说,封建领主的地产由长子继承,“地片和它的主人一起个人化着,它有着主人底阶位,和主人一起是男爵的或伯爵的,它有着他的诸特权,他的审判权、他的政治关系等等”。领主地产的这种政治色彩,决定了它具有“安定的垄断”的性质,但这并不影响封建领主把地产再分割转让出去。因此在欧洲中世纪,就出现了封君和封臣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马克思在说明封建领主的地产具有政治垄断的性质的同时,也指出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是私有制,“安定的垄断之转变为运动的不安定的垄断”是必然的,“土地所有权底转化为商品是旧贵族底最后的颠复和货币贵族底最后的完成”(38)。实证研究表明,欧洲中世纪土地转让虽然受到传统观念和法律的许多限制,但地产的分割和转让在实际生活中却又是常见的现象。恩格斯对于日耳曼人的自主地商品化的历史过程有非常具体的论述。他说:“日耳曼人的自主地,在旧日罗马领土上一出现,就变成了跟它同时并存的罗马人的地产早已变成的那种东西,即变成了商品。财产分配日益不均,贫富矛盾日益扩大,财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是一切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的确定不变的规律;虽然这一规律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中得到了它的充分的发展,但并非一定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才能起作用。所以,从自主地这一可以自由出让的地产,这一作为商品的地产产生的时候起,大地产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39)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时,十分注意不同国家和地区封建化的多样性。他们并没有把封建社会的直接劳动生产者完全归结为农奴。他们多次提到,在中世纪,受封建国王、贵族领主与教会剥削和压迫的不仅是农奴,还有租佃农民、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恩格斯说:“在法兰克人侵占高卢以后,那里仍然留下很多罗马的大土地占有主,他们的田地,大部分由缴纳地租(canon)的自由佃农或依附农耕种。”(40)“日耳曼人在高卢,或者一般地在实行罗马法地区,相当经常地遇到作为佃农的自由的罗马人。但是,他们在占地时所关心的,是他们自己不要变成佃农,而能够在自有地上耕种。”(41)
冯天瑜为论证自己的观点,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生产的特点是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臣属。同一切君主的权力一样,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42)冯天瑜这段引文的删节号耍了一个障眼法,因为正是马克思的这段话否定了冯天瑜所谓的“非贵族式土地所有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的说法。马克思的原话说:“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后者又取决于自耕农的人数。”(43)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封建主的权力并不取决于他的地租(亦即他出租的土地)多少,而是取决于对他有依附关系的臣民(包括自耕农)的人数。因为依附农民的人数大大超过耕种封建主土地的农奴(或农民),而自耕农又往往要沦为封建主的依附农民。冯天瑜删掉了“后者又取决于自耕农的人数”这句至关重要的话,就像马克思根本没有谈到自耕农的问题。马克思在这句话后面还接着说:“虽然英国的土地在诺曼人入侵后分为巨大的男爵领地,往往一个男爵领地就包括九百个盎格鲁撒克逊旧领地,但是小农户仍然遍布全国,只是在有些地方穿插着较大的封建领地。”(44)冯天瑜对这段话显然是更不愿意引用了。马克思在另外的地方还明确指出,在封建社会,“那些完全和封建的生产方式不相适应,完全处于这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生产关系,也被包括在封建关系中。例如英国的tenures in common socage[自由农民保有地](与tenueres on knight's service[骑士保有地]相反就是这样。其实,这种自由农民保有地只包含货币义务,不过在名义上是封建的”(45)。这段话也可以说明,马克思并不认为“非贵族式土地所有制”与封建主义是不可兼容的。
“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这是冯天瑜加在马克思头上的另一个重要观点。他声称马克思“明确主张: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与封建制度是相背离的”(46)。按照他的演绎,“从概念的内涵规定性而言,政权由上而下层层封赐,造成政权分裂,这是‘封建’的‘本义’”;“至于在‘封建社会’的晚期,出现君主专制,分权走向集权,贵族政治走向官僚政治,这正是‘封建’的变性以至衰亡,是‘非封建’乃至‘反封建’的历史走势”(47)。
“君主专制”是一种政体而不是社会经济形态,它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曾在有些国家以不同形式出现过。马克思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君主专制有过不同的评价,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与封建制度是相背离的”这种话。冯天瑜引为论据的是马克思如下的一段话:
现代历史编纂学表明,君主专制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一方。因此构成君主专制的因素绝不能是它的产物……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等级垮台以后,它积极参加过破坏封建等级的活动。(46)
这段话引自马克思批判卡尔·海因岑的文章。海因岑是一名激进的自由派,主张立即建立德意志共和国,宣称君主制是一切贫困和灾难的祸首。马克思批评他实际上是把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工人对雇主的仇恨转移到君主制头上。马克思从“现代历史编纂学表明”展开论述,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讨论的是欧洲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亦即新兴资产阶级崛起时期一些国家的君主专制。冯天瑜用它来论证马克思主张“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显然是混淆了“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的时代性,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在文中说:“德国的君主专制发生较晚、维持较久,这只能从德国资产阶级的畸形发展来解释。”他在指出君主专制“积极参加破坏封建等级的活动”的同时还说:“现在君主专制不实行集权(集权本是它的开明措施)而打算实行分权”;“力图保留哪怕是封建割据的外表”。但冯天瑜在引文中把马克思这些不利于他观点立论的话,都用一个删节号去掉了。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把“基于暴力的所有制”说成是“真正政治性质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式”时明确指出,社会经济形态并不是由“政治形式”所决定的。恩格斯说:
国家和暴力恰好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如果我说——譬如——东方专制制度、古代共和国、马其顿君主国、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都是建立在暴力上的,那末,我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此,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不应该用始终一样的暴力来说明,而必须用被施加暴力的东西,被掠夺的东西来说明——用那个时代的产品和生产力以及从它们自身中产生的它们的分配来说明。(49)
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各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只能用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亦即该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的性质来加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曾经提到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但他们并没有把“东方专制制度”视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一个特殊阶段,也没有说过君主专制制度只能是“封建的变性以至衰亡”的产物这类话。
四、驳“泛封建论”
冯天瑜《“封建”考论》最重要的内容,是他对“泛封建论”的溯源和批判。他说:“在追踪问题的来龙去脉之际,有一点可以预先排除:令‘封建’含义泛化者不通古汉语及中国古史,或不谙西语及西洋史,造成概念误植。事实上,将‘封建’概念泛化的前辈学者,大多饱读诗书,当然明白‘封建’的古义是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他们又多半熟识西文、西史,对feudalism的含义为封土封臣、采邑庄园,并不生疏。故‘封建’泛化,绝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西义,而是另有原因的。”(50)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封建”概念在中国学界乃至社会各界“泛化”呢?冯天瑜认为只有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语汇”输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而广泛使用这一“理论和语汇”,才能得出问题的答案。
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与政治风云的演变诚然有不可忽视的关系。但如果认为对“封建”概念的理解和对“封建社会”的认识完全是由某个政党或某些政治人物的“非学术性因素”决定的,这是对中国史学与政治关系的一种片面性的曲解。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层内部存在着激烈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也影响了当时的理论界。由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论战,又引发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参加这场论战的人,其政治背景和理论倾向非常复杂,绝非像冯天瑜所说的论战各派“多服膺马列”,“竞相表示信从唯物史观”,“不同程度信奉来自苏俄及共产国际的‘社会形态共性论’”(51)。有些人的文章虽然也摘引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词句,但正如论战参加者之一胡秋原后来所说的:不少人“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其实是为了“非共反共”(52)。
中国革命性质和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一个焦点,是关于中国革命是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近代中国是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冯天瑜认为“关于近代中国是‘封建制度’、‘封建主义’的关键性论说”,首见于列宁1912年发表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而列宁的这篇文章,“直接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初展开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应该指出,列宁认为“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53),这个意见并没有错。冯天瑜把列宁关于沙皇俄国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说成是“将泛封建观提升为普世性范式”,这说明他把封建社会看成只是西欧中世纪特有的历史现象,也证明他关于封建社会的“考论”根本是在纠“实”而不是纠“名”。冯天瑜认为,由于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使泛化的‘封建’及‘封建制度’、‘封建主义’、‘封建时代’等史学术语,连同所包蕴的中国历史分期观念,逐步普及开来”。我们承认列宁关于封建社会的论述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意见,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有影响。但就史学界而言,主张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是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而得出历史分期的认识,而不是由于受到列宁和共产国际的什么“泛封建观”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的认识的。以郭沫若为例,他1928年发表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54)认为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但他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却又作出了一种矛盾而不正确的判断。他一方面说“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到最近百年都是很岿然地存在着”,另一方面又把近百年的社会形态说成是“资本制”。郭沫若的这种说法,显然就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流观点并不一致。
冯天瑜的《考论》用了不少篇幅来论述毛泽东对“新名‘封建’的定型”所起的作用。书中说:土地革命期间,毛泽东于戎马倥偬之际,能在多大程度关注中国社会史论战,尚待具体考证,但长征后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很可能阅览、考究了中国社会史论战诸派论著,并作出自己的判断”(55)。毛泽东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封建社会’冠于周秦以下漫长的历史阶段”。冯天瑜猜想该文的“泛化封建观”是王学文、何干之等参与起草而得到毛泽东采纳的。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把周秦以来的中国是‘封建社会’的总体结论,推及‘封建的政治’、‘封建的经济’、‘封建的文化’各分论;又判定现代中国是‘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其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到了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闭幕词《愚公移山》中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以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加上‘官僚资本主义’,共称‘三座大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摧毁的对象。于是‘封建主义’不仅是历史的遗迹,也是现实的存在,现代社会相当一部分腐朽、落后、反动的人与事,都归入此一‘主义’之中,属于打倒之列。”冯天瑜最后说:“毛泽东上述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名论,成为20世纪40年代以后郭沫若等许多史学家的治史依凭,郭老的‘战国封建说’即在此间定型。各种文宣材料有关‘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封建时代’的诠释,也几乎全都以前引《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的那段文字为准绳。”(56)
冯天瑜的这一大段论述,存在许多问题。一些没有根据的猜测之辞姑且不论,主要的是:他把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的时段这个历史研究的问题,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这个现实问题搅在一起,这就使人难于理解他的观点的逻辑起点和终点。《考论》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只限于夏商周三代,秦汉至明清应称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作为一种史学见解,可以百家争鸣。冯天瑜没有谈及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读者也不便追问。但《考论》把毛泽东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的论述,都说成是“泛封建说的广为铺陈”,这就让我们不禁要问,在冯天瑜看来,近代中国又该叫什么社会呢?新民主主义革命究竟有没有反封建的任务呢?至于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提到“周秦以来的中国是封建社会”,众所周知,这种说法并没有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共识。大半个世纪以来,不仅春秋战国封建论、秦汉封建论、魏晋封建论诸说不绝于耳,而且毛泽东本人对于封建社会始于何时也并无定见。他后来在肯定战国封建论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历史分期问题应该由历史学者来讨论。怎么能说20世纪40年代以后,郭沫若等许多历史学家都是以毛泽东“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名论”为“治史依凭”呢?
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冯天瑜一方面说郭沫若等许多历史学家以毛泽东“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名论”为“治史依凭”,另一方面又说,“西方学者多认为,中国学者(如郭沫若、范文澜等)是遵循毛泽东的论述,演绎泛化封建观的。其实,从‘泛化封建观’的形成过程而论,是郭沫若等史学家率先阐发‘泛化封建观’,毛泽东采纳其说,又经过毛著的影响力,使泛化封建观普被中国大陆的”(57)。总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传播,在冯天瑜泛政治化的笔下,不但没有学术的合法性,而且其源流也是说不清的一笔糊涂账。
冯天瑜在批评“泛封建论”时说:“既然是‘地主’,土地便可以自由买卖,怎能加上前 置的‘封建’”?“既然是‘专制帝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为其基本政制,又怎能冠以‘封建’”?如此等等。(58)说来说去,就是他所一再宣称的:“‘封建’义为土地由封赐而来,不得转让、买卖”;“‘封建’义为‘封土建国’,政权分散”(59)。但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对“封建”的这种定义既不符合冯天瑜所说的“西义”,也不符合马克思的“原论”。冯天瑜心目中的“封建”定义,是一种片面而僵化的非历史的概念,而不是多样性统一的历史概念。他对“泛封建观”的批评,实际上是指向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马克思说:“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发展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60)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封建主(领主和地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农奴和农民)。土地是否可以转让和买卖,国家政权的统治方式是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都不会改变封建社会劳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以及他们对封建主人身依附关系的实质,不会改变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与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民个体生产经营的基本矛盾。对于封建社会的这个主要特征,冯天瑜的《考论》是根本不予考虑的。
为了说明秦汉至明清不是封建社会,冯天瑜还“重释‘封建时代’文化精神”,认为“封建抑制自由”的说法“并不一定能够成立”。他以春秋战国为例,赞扬那是一个士人阶层“人性之花美盛”、“个性高扬”的时代,而且说这正合乎“封建”的本义。(61)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反映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这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历史遗产。但是冯天瑜认为这是“‘封建时代’文化精神”的表现,却难以自圆其说。首先,春秋与战国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无论是政治、经济与社会关系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动,不少学者对此已有颇为详尽的论述。冯天瑜主张商周是封建社会,从时代上说东周通常只指春秋而不包括战国。百家争鸣始于春秋末年而盛于战国时期,把它归结为“封建时代”的“文化精神”,在逻辑上就有矛盾。其次,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关系发生激烈变动、形成文化多元化现象的表现,可以说是对商周时代文化精神的一种否定。春秋之前,“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62)。垄断了文化知识的贵族阶级,思想理念都是以王官之学为准绳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63),“士”的成份起了很大变化,“九家之术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64)。冯天瑜无视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说什么“如果还复‘封建’的本义,‘封建时代’(周朝,尤其是东周即春秋战国)……是一个思想较为自由、并不以言定罪的时代”(65)。他这里的说的“封建时代”只提周朝,未提商朝,大概是因为商朝有残酷的人殉、人牲制度,要赞扬其“封建”本义的“人性”、“个性”实在说不过去。但西周和春秋难道就真是“一个思想较为自由、并不以言定罪的时代”吗?周厉王暴虐,杀人“弭谤”,以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66)。西周、春秋以人殉葬之俗犹未绝迹。秦穆公被认为是贤明之君,但他死后,殉葬者177人,包括子舆氏3位“良臣”,“亦在从死之中”(67),这是什么“文化精神”?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68)。实际上是指周天子有无权威的问题。在春秋时代,尽管王权已经衰微,权力已由诸侯而卿大夫而陪臣逐级下移,但君臣名分和人身隶属关系的传统观念仍然还有巨大的影响力。所谓“有君不事,周有常刑”,(69)“臣无二心,天之制也”(70);“事君以死,事主以勤”(71);这些观念在当时的社会精英中还被公认为一种政治准则和道德准则。从春秋到战国,儒墨两家号称显学,但无论是孔子、墨子或孟子、荀子,其实都没有受到当时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各诸侯国的变法和社会改革,是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法家主张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主张严格控制人民的思想,对法家的思想学说既不能片面加以否定,也不能片面加以肯定。对先秦诸子的历史评价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百家争鸣不是什么“封建”本义的体现,也不能归结为对“人性”、“个性”的讴歌。冯天瑜认为“只有在封建时代才可以呈现‘诸子争鸣’的局面”(72),鼓吹“封建时代”的“文化精神”具有“人性之花美盛”、“个性高扬”的品格,这个观点无论是揆之历史实际或在理论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封建社会的命名和时段判断,实际上是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史学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学者无论是西周封建论者、战国封建论者或魏晋封建论者,都是以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为理论指导的。但封建社会时段问题毕竟又是一个学术问题。建国以来,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不正常的情况以外,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各种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和互相诘难。冯天瑜硬要把主张秦汉至明清是封建社会的观点说成是基于政治需要的“泛封建观”,是苏俄及共产国际“以‘封建’指称现实中国”的产物,是毛泽东“泛化封建观”支配史学界的结果,这就把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完全政治化了。冯天瑜的这种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历史研究的百家争鸣,这也正是我们对《“封建”考论》一书不能不加以关注并予以评论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论语·季氏》。
③《韩非子·五蠹》。
④冯天瑜:《“封建”考论》,第380页。
⑤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
⑥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⑧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5页。
⑨冯天瑜:《“封建”考论》,第197页。
⑩冯天瑜:《“封建”考论》,第4、385页。
(11)《论中国封建制的形式及其法典化》,《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3页。
(12)冯天瑜:《“封建”考论》,第22页。
(13)冯天瑜:《“封建”考论》,第90、91、94页。
(14)冯天瑜:《“封建”考论》,第378页。
(15)[法]马克·布洛赫著,张绪山译《封建社会》上册,导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6)[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17页。
(17)[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册,导论。
(18)[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册,导论。
(19)[英]M·M·波斯坦为《封建社会》英译本1961年所写前言。
(20)[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06页。
(21)[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第506页。
(22)[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册,导论。
(23)[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下册,第697页。
(24)[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下册,第697、698页。
(25)[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下册,第697、698页。
(26)[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下册,第705页。
(27)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1册,《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28)冯天瑜:《“封建”考论》,第190页。
(29)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
(30)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9页。
(31)冯天瑜:《“封建”考论》,第317、318、320页。
(32)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3、284页。冯天瑜把马克思文中的“至于说封建主”改为“至于说封建主义”。
(33)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69页。
(34)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69页。
(35)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7、378页。
(36)冯天瑜:《“封建”考论》,第318页。
(37)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6页。
(38)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7、45页。
(39)恩格斯:《法兰克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1页。
(40)恩格斯:《法兰克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2页。
(41)恩格斯:《法兰克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7页。
(42)冯天瑜:《“封建”考论》第317页,注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4页。
(4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5页。
(4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5页。
(4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90—991页。
(46)冯天瑜:《“封建”考论》,第320页。
(47)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0、341页。
(48)参看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0页。
(49)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81页。
(50)冯天瑜:《“封建”考论》,第7页。
(51)冯天瑜:《“封建”考论》,第276、279页。
(52)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第四版序言,台北学术出版社1978年版。
(5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6页。
(5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现代出版社1929年版。
(55)冯天瑜:《“封建”考论》,第291页。
(56)冯天瑜:《“封建”考论》,第293—298页。
(57)冯天瑜:《“封建”考论》,第295页。
(58)冯天瑜:《“封建”考论》,第228页。
(59)冯天瑜:《“封建”考论》,第228页。
(60)马克思:《雇佣劳动和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页。
(61)冯天瑜:《“封建”考论》,第229页。
(62)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
(63)《庄子·天下篇》。
(64)《汉书·艺文志》。
(65)冯天瑜:《“封建”考论》,第229页。
(66)《国语·周语》。
(67)《史记·秦本纪》。
(68)《论语·季氏》。
(69)《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70)《左传》庄公十四年。
(71)《国语·晋语》。
(72)冯天瑜:《“封建”考论》,第2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