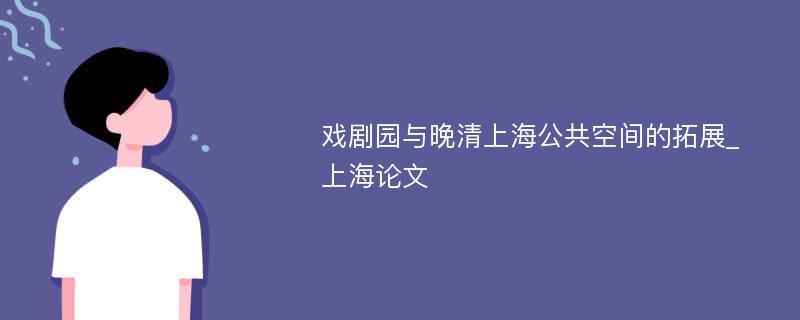
戏园与清末上海公共空间的拓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上海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上海,戏园繁盛。作为提供戏曲演出的公共娱乐机构,戏园是服务于人们休憩娱乐以及文化生活需要的场所。时至20世纪初年,在戏曲改良运动的影响下,上海的戏曲表演从演出宗旨、舞台置景到表演形式、表演剧目等都发生了变化。与之相应,作为演出场所的戏园,其社会功能和空间属性也有所变化,逐渐转变为变相或公开进行社会政治与文化批判的公共空间。①
一、戏园之繁盛
专业性戏园②在上海的出现,是颇为晚近的事情。明清以降,江南地区经济富庶,文教郁盛,人物荟萃,文化生活颇为发达。但上海地处海滨一隅,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人口不超过20万,虽“慕苏扬余风”,然“士文而近浮,农愿而近野”,[1](卷一,“风俗”)“风俗鄙陋”[2](p.10),文物寂寂。除了一些私人堂会和会馆、公所之外,上海也偶有茶楼、茶馆,进行小型戏曲演出,但并未形成专门化的戏园。
开埠以后,上海襟江带海的潜在地理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海舶辐辏,百货阗集,内外贸易突飞猛进,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滨海小城因之迅速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最具生机和活力的商贸中心。随着市面的日趋繁荣,各地商民的大量涌入,上海的戏曲演出也日渐活跃。最初在上海演出的主要剧种是昆戏。昆戏,俗称“文班”,乾嘉道咸时期,盛行以苏州为中心的吴中一带,上至王公大夫,下至贩夫走族,皆酷嗜之。咸丰初年,由于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苏州一带的昆班纷纷转移至上海。“昆腔之在沪者,以鸿福为领袖,其次若宝和新剧,亦高出一筹。荣桂年十五六,丰姿绰约,绝似好女子,聆其音,虽雏燕娇莺不啻也。有三多者,纤腰婀娜,态有余妍。共他诸伶,皆擅绝技,每发诙谐,满座为之头没杯案。”[2](p.9)除了鸿福、宝和之外,尚有大章、大雅诸昆班,也颇著声名。
昆班联翩入沪,带动了上海戏曲演出市场的繁荣,也催生了专门化的戏园。1851年,位于南市四牌楼附近的一家名为三雅园的茶园开张。这是开埠以后上海最早的对外营业性质的戏曲演出场所,也是上海戏曲演出走向商业化的发端,所演仍为昆曲文戏,一度曾吸引“城外人向城内跑”。1854年,三雅园在小刀会战事中毁于兵燹。不过,上海人并没有完全将它从记忆中抹去,后来钱业公会在小东门开设的茶园以及昆曲演员苏人陆吉祥在英租界石路开设的茶园,还一再沿用三雅园的招牌。[3](p.581)昆曲文戏虽为雅音,昆班中也不乏名角,然“皆吴下旧伶,惜知音鲜也”[4](p.33),难以激起人们的持久兴味。咸丰、同治年间,徽班从扬州一带来沪,一些新开办的戏园,如一桂、久乐等,“所演之剧皆系徽调”[5](p.458)。于是,“昔之崇尚昆曲者一变而盛行徽调矣”[6](p.29),向之昆班如大章、大雅等,无复有人问津。不久,京班又接踵而至,燕台雏凤,誉满春江,徽调也日渐式微,上海剧坛因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867年,英籍华人罗逸卿在法租界石路南靖远街创办满庭芳,从天津邀来一批京班艺人演出,是为京剧首次进入上海。沪人初见,趋之若鹜。一时间,“都人士簪裾毕集,几如群蚁附膻”[7](p.116)。同年,浙江定海人刘维忠在租界的商业中心五马路宝善街开办丹桂茶园,特意从北京请来三庆、四喜等著名京班,角色较整齐,有夏奎章、景四宝、王桂芬、王桂喜等[6](p.29),班子健全,行当分工明确,服装鲜明,演出文武唱做俱全,着实令上海人大开眼界,夜夜座无虚席。[8](p.211)
满庭芳与丹桂的成功,揭示了社会娱乐时尚和审美情趣的变化,也极大地促进了上海戏曲演出场所的兴起。此后,各具特色的舞榭歌楼、茶园酒肆,蜂拥而起,连薨接栋,争奇斗胜,生面别开。如金桂园、大观园、天仙园等,皆颇负盛名,与丹桂并称“四大京班”;次之则有宜春园、满春园、富春园、和春园、长春园等。[9](p.33、116、156)尤其是丹桂园,虽因经营盛衰、人事变迁而屡易其主,却历时三十余年而不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人气,堪称戏曲史上的一个奇迹。③据《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的统计,开埠以后至1912年以前,上海先后有大大小小戏园120多家。[10](pp.665-675)所谓“梨园之盛,甲于天下”[7](p.101),洵非虚语。
戏园的大量涌现,使戏曲演出从旧时达官显贵的宅院厅堂、各地商帮的会馆公所走向了市民百姓,也极大地拓展了城市娱乐消费市场,不仅上海本地人经常光顾戏园,就连外地人来沪一般也会到戏园看看。光绪辛卯年(1891年)春,闽人林植斋自福建入都,途径上海之时,就曾应友朋之邀至戏园看戏。据他所记,彼时海上戏园,“戏价三角、或四角。楼上两旁除包厢外,楼中及楼下池座,俱列方桌,被以红缎桌围。每桌排列单靠椅六张,定为六客。客俱盖碗茶,瓜子四碟,戏半并出热点四盆,手巾频频,伺应周到,弥觉舒适。戏价外略付手巾小帐(账)数十文,无他需索也。”[11]戏园的经营状况,于此可见一斑。
晚清时期,上海的戏园大多集中在宝善街、四马路一带。早年的丹桂、天仙等茶园“尚溶化昆、徽、京三班于一园”,而金桂、宜春、满春等“均专演京剧”,丹凤园、同乐园则京、徽并演 。[6](p.29)时至光绪初年,京剧已成为上海最具人气、影响最大的剧种。黄式权《淞南梦影录》如此描绘戏园演出时的场景:“上灯时候,车马纷来。鬓影衣香,丁歌甲舞,如入众香国里,令人目不暇赏。”[7](p.116)池志瀓《沪游梦影》则写道:“钟鸣八下,各戏登场,万头攒动,蚁拥蜂喧……迨至铜龙将尽,玉兔渐低,而青楼之姗姗来迟者,犹复兰麝烟迷,绮罗云集,诚不夜之芳城,鞠部之大观也。”[12](p.157)
日趋繁荣的戏曲娱乐消费,吸引了大批京角纷纷南下,上海的戏园因之也增添了许多亮色。一首海上竹枝词如此咏道:“相传鞠部最豪奢,不待登场万口夸。一样梨园名弟子,来从京国更风华。”梨园豪奢与京国风华,交相辉映,造就了一道绚烂的人文景观。于是,在时人品题的“沪北十景”中,“桂园观剧”便赫然位列榜首。[2](p.112)风气所及,凡官府宴客、士绅聚会、商人社交乃至妓女出局,也无不以演唱“京调”为时髦。更有甚者,一些富室子弟还以学唱京戏而自娱自乐。据王韬《瀛壖杂志》的记载:“沪人喜梨园歌曲,有聚芳、集贤二局,皆富室子弟为之,竞以豪奢相尚。每当熏香剃面,鹄立氍毹,极尽悱恻缠绵之致,令观者目眩神移。尝演《思凡》、《断桥》二剧,尽态极妍。合座为之倾倒。”[2](p.9)设局自娱的毕竟只是少数富室子弟所为,多数人还是到戏园中去领略观剧的乐趣。为了帮助初来乍到的外地游客了解上海的戏园,商务印书馆于宣统元年出版的《上海指南》还专门作了介绍:“沪上戏园,凡经三变,始唱昆曲,继歌二簧,近则专尚京调,燕台雏凤,誉满江南。而向日之文班,已如广陵散矣。南市及英界大新宝善街一带,檀板高歌,行云可遏,而余音袅袅,犹三日绕梁者,无非京都头等名角所唱之戏。”[13](卷八,“游览食宿·戏园”)
戏园里京韵悠长,余音袅袅,确乎令人流连忘返。不过,从戏园排演的剧目来看,还多是些传统戏,“虽尽多忠孝义烈、可歌可哭之类,可以感动观众,激励薄俗”[6](p.32),但其题材无外乎才子佳人、神仙鬼怪、英雄豪杰、历史故事之类,如《蝴蝶梦》、《翠屏山》、《宝莲灯》、《华容道》、《战长沙》、《宁武关》等④,于社会教化或不无裨益,但对于社会现实、特别是对于时事政治则鲜有批判,确也是不争的事实。到戏园观演的当然也有百姓,但这里毕竟是“销金之巨窟”,能够经常出入其中的大多是腰缠万贯的达官贵人、豪商巨富以及家道殷实的地主士绅和一些纨绔子弟。
开埠以后,受商业经济的熏染,上海的社会风气趋于浮华奢靡,而戏园作为公众娱乐场所受影响尤甚。一位客居上海、自名“香鹭生”的人“有感于洋泾风俗之淫靡,人情之浇诈”,特作《海上十空曲》以警世。其中一首《戏馆》描摹当时上海戏园的情景:“锣鼓声中,鬼帜神旗气象雄,奇幻《盘丝洞》,艳冶《描金凤》。咚,异曲同工,京徽争哄。士女纷纷,错座几无缝。君看优孟衣冠总是空。”[2](p.114)因此,如果说一般市民进戏园,目的尚在于看戏和消遣的话,那么对于那些富商巨绅、达官显贵来说,日复一日泡在戏园里,挥金如土,则除了娱乐之外,恐怕还不无寻奇猎艳之意,同时亦以此来夸示身份,炫耀富贵,这实际上是“都市奢华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显示”[14](p.1088)。
毋庸置疑,戏园在清末上海的文化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戏园的戏曲活动超出了一般民间文艺的意义,而同整个城市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成为市民生活的一种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15]但从戏园里表演的剧目内容以及观众的审美情趣来看,它还只是普通的娱乐场所而已,与旧时的书场、茶馆等一样,并不必然具备某种批判性社会功能。
二、戏曲改良运动与戏曲批判功能的彰显
时至20世纪初年,因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戏曲表演在演出宗旨、舞台设计、表演形式、表演剧目等方面都发生了些变化。斯时的戏园仍旧排演戏曲,但其社会功能已不仅仅局限于满足于人们的娱乐需求,而是扩大到对社会现实有所批判。
戏园社会政治批判功能的凸显,是与戏曲改良运动的发展紧密相关的。20世纪初年,主张变革的新派人士,无不以改良戏曲为急务,视之为启迪民智、改良民俗、开通风气、进行政治宣传的有效手段。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两个剧本,揭开了戏曲改良的序幕。1905年,陈独秀以“三爱”的笔名发表《论戏曲》一文,全面论述戏曲的功能以及改良戏曲的方法。他说:“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入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故不入戏园则已,苟其入之,则人之思想权未有不握于演戏曲者之手矣。”在他看来,忧时之士虽多方筹划救国之方,但创办学校“教人少而功缓”,开设报馆、编撰小说亦只能对少数识字的人产生影响,“惟戏曲改良,则可感动全社会,虽聋得见,虽盲可闻,诚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也”。为此,他提出了五条改良戏曲的具体办法,即:多编有益风化之戏;采用西法;不演神仙鬼怪之戏;不演淫戏;革除富贵功名之俗套。[16]天僇生则指出,“欲无老无幼,无上无下,人人能有国家思想,而受其感化力者,舍戏剧末由”。所以,他主张“设剧场,收廉值,以灌输文明思想”。[17]鉴于莎士比亚“能道人心”的“著名之曲”多是些“泣风雨动鬼神”的悲剧,颇为欧洲各国所推重,蒋观云还大声疾呼排演悲剧:“使剧界而果有陶成英雄之力,必在悲剧。”[18]
陈独秀等人所提出的戏曲改良主张,以戏而言事说理,多着眼于戏曲形态、戏曲内容、戏曲表演方式等方面的变革,但种种议论,揆其立意,与其说在于戏曲艺术自身,毋宁说更为注重戏曲的社会功能,即从戏曲的现实功用出发,希望通过改良戏曲,达到开启民智、变革振兴的目的。这些主张,与人们所熟知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等一样,均属于以民族主义为基核的文化革命话语,在致思取径上一脉相承,并无二致,彰显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正所谓理一相殊,而又殊途同归。
1904年10月,陈去病、柳亚子、汪笑侬等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份专门提倡戏曲改良的文艺丛报,明确宣称“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所谓“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其潜台词就是要求反清革命。事实也确乎如此。在《发刊词》中,柳亚子极力主张排演“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法国革命、美国独立等中外历史剧,以激励民众“建独立之阁,撞自由之钟,以演光复旧物、推倒虏朝之壮剧、快剧”。[19]而陈去病则呼吁青年志士积极投身梨园鞠部,“对同族而发表宗旨,登舞台而亲演悲欢”,以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20]从该刊随后发表的几个剧本,如时事剧《安乐窝》、《金谷香》、《新上海》,历史剧《长乐老》、《缕金箱》,西洋剧《拿破仑》等来看,或直刺现实,或借古讽今,或以洋为鉴,较之旧式戏曲,不仅题材有所扩大,而且主题思想也多具革命性。《二十世纪大舞台》刊行两期即被清政府封禁,但它对清末戏曲、戏园的改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正是在戏曲改良思潮的推动下,上海的一些艺人,如汪笑侬、潘月樵、夏月仙、夏月润等,开始排演一些含有政治变革要求的剧目。1904年秋,汪笑侬根据《波兰衰亡史》,改编为《瓜种兰因》,在春仙茶园上演,借波兰亡国之史实,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此为京剧舞台上最早的外国题材剧目。接着,汪笑侬又陆续排演了《党人碑》、《桃花扇》、《缕金乡》、《长乐老》等戏。与此同时,夏月润等人也在丹桂茶园演出《玫瑰花》等新戏。这些戏不仅在表演形式上有所创新,而且在思想内容上或公开或隐讳地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汪笑侬的表演,更是被誉为“独于黑暗世界中灼然放一线之光明”的“梨园革命军”。[19]观众在书函中说:“今笑侬以新戏改良,处处刺激国人之脑,吾知他日有修维新史者,必以笑侬为社会之大改革家,而论功不在禹下也。”[21]
在戏曲改良过程中,一些新派艺术家通过吸收借鉴西洋戏剧的表演形式和风格,培育出一种新的戏剧——新剧。其在上海的诞生,最初是受到教会学校学生课余演出的影响。当时,圣约翰书院、徐汇中学等校常常于圣诞节之际,演出诸如《浪子回头》之类以宣传宗教为主题的短剧。1899年,圣约翰书院的学生还编演过讽刺戏《官场丑史》。受教会学校的影响,南洋公学、育材学堂等学校的学生也开始编演时事剧,如《六君子》、 《义和团》、《张文祥刺马》等。1905年,民立中学学生汪仲贤(后更名汪优游)等组织“文友会”,并假城东昼锦牌坊陈宅举行公演,演出《捉拿安德海》、《江西教案》等“反映社会现实的戏”[22](p.355),反响颇佳。1907年,为了赈济淮海水灾饥民,商部实业学堂与震旦学院学生还两次假座徐家汇李公祠演剧助赈,其间除了演奏西乐外,还穿插演出《璧衣缘》、《伪翻译》等西剧,“一时观者无不同声赞叹”。[23]
对于戏曲改良而言,早期的学校剧只是一种新的尝试,“没有唱腔和舞蹈,也没有锣鼓和乐队伴奏,而仅以台词构成全剧”[24](p.21),在剧目编排、表演技巧等方面都还十分粗糙,而且也没有舞台布景。但它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在表演手法上注意模仿西洋戏剧趋于写实的风格,形式较为新颖;二是贴近现实,“一开始就是同当时人民所关心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结合着的”[25](p.53)。所以,引起了戏曲爱好者的关注。此后,陆续出现了一些新剧团体,并尝试排演新剧。1906年,朱双云、汪优游、王幻身、瞿保年等组织“开明演剧会”,提出六大改良,即政治改良、军事改良、僧道改良、社会改良、家庭改良、教育改良,同时演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等时事剧目,颇受时人关注。不过,应指出的是,1907年以前,新剧大多只在学校以及私人集会场所排演,“仍然是课余或业余消遣活动,并非职业性质”。[26](p.148)
1907年10月,因受李叔同、曾孝谷等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组织“春柳社”,排演《茶花女》片段与《黑奴吁天录》而大获成功的鼓舞,浙江人王钟声、沈仲礼等人在上海组织“春阳社”,并假圆明园路兰心戏院演出《黑奴吁天录》。此为新剧首次在剧场中采取分幕编排、西式布景的大规模演出。继之,春阳社又在辛家花园演出时事剧《张文祥刺马》,还在张园为筹款进行演出。[25](p.50)1908年2月,在浙江旅沪学会因浙路问题而举行的集会上,春阳社社长沈仲礼向与会的2500名来宾以及6000余名浙籍同乡介绍“戏剧改良之作用”,并组织演出《吊郎汤》、《黑奴吁天录》,其“悲歌慷慨之态,令人感愤”。[26]
除了组织春阳社之外,王钟声还与马相伯以及曾在日本参加春柳社的任天知等人合作,于1908年2月创办了通鉴学校。该校位于成都路、白克路之北的一幢小楼内,其经费主要由沈仲礼资助,是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提倡戏曲改良的新剧教育机构。校内设有一个小型舞台,可供排戏。日后成为新剧界名角的汪优游、查天影等均加入其中。[25](p.53)王钟声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宣传,宣传办法,一是办报,二是改良戏剧”。因此,通鉴学校在招生时虽以包念书、包出洋为号召,并开设国文、英文、算术、历史、舞蹈、戏剧等科目,但实际上是以组织学生排演新剧为宗旨。王、任二人还合作在宝善街春仙茶园演出《迦茵小传》。此后,又不断演出如《秋瑾》、《徐锡麟》、《官场现形记》等宣传革命、讽刺权贵的新戏。[22](p.356)
自王钟声创设春阳社与通鉴学校之后,一些新派人士群起而效尤,纷纷组织新剧团体,排演新剧。⑤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任天知于1910年12月成立的进化团。该团组建时,曾登报征招演员,一时爱好新剧者,如汪优游、陈无我、范天声、秦哈哈、陈大悲、王幻身、张治儿、陈天晓、陈镜花等,争相应募。[27](p.130)进化团“可以算中国新剧的第一个职业团体”[25](p.53)。任天知等人以“天知派新剧”相号召,“用化汝演讲那样的方式,反映当时的一些政治问题,为革命作宣传”,曾先后至苏州、南京、芜湖、汉口等地演出,所演剧目大多是时事新剧,如《血蓑衣》、《东亚风云》、《尚武鉴》、《安重根刺伊藤》、 《恨海》、 《血泪碑》、《共和万岁》、《新加官》等。[25](p.54、59)这些剧目极力颂扬民主、自由等革命思想,猛烈抨击清政府统治的黑暗与腐朽,发抒了人们久郁的愤懑与不满,因而颇受欢迎。尤其是台词中时常夹杂着一些极富煽动性的言辞,更是常常赢得一片喝彩之声。芜湖、汉口两地官府曾以该团“鼓吹革命,摇惑人心”为辞,下令严禁演出。然而,愈禁愈演,不仅未能令“天知派新剧”偃旗息鼓,反而使之声名大噪,赢得了“宣传团”的美誉。[26](p.150)
三、新舞台的创建与公共空间的拓展
随着新剧表演的不断推广,上海出现了新型的剧场化的舞台,并将戏曲改良推向大规模的舞台实践阶段。1908年,沈缦云、姚伯欣、张逸槎等士绅联合潘月樵以及夏月珊、夏月润仲昆在南市十六铺创建“新舞台”。新舞台参照西洋和日本剧场的舞台样式,“一切建筑装置多欧化”,废弃旧式茶园三面敞开的带柱方台,改为半月形的镜框形舞台,台中心可以转动,并采用机关、灯光、硬片、软片、附片等布景。[28](pp.200-201)因此,整个舞台不但建筑规模宏敞,而且景象逼真,活泼生动,“既有山林旷野,也有曲院洞房,配合剧情,增加了观众的现实感和优美感”[29](p.28)。在座位安排上,则将以往占地大的方形茶桌、包厢,改为长排的联椅,前低后高,既增加了观众的容量,又保证观众在观演时视线不被阻挡。在剧场管理方面,则废除了旧式茶园的案目制,改为卖票制,同时还取消了抛手巾、递茶水、要小账、招妓陪客等旧习,使戏园里原本嘈杂混乱的秩序有了很大改观,极大地改善了观、演两方面的条件。
新舞台是近代中国第一家近代化的新式剧场。新舞台之“新”,绝非仅仅停留在建筑样式、舞台置景和剧场管理等方面,更重要的还表现在演出剧目与表演方式等方面。潘月樵、夏月珊等人以新剧相号召,在此排演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剧目,如《潘烈士投海》、《黄勋伯》、《赌徒造化》、《新茶花》、《明末遗恨》、《波兰亡国恨》、《黑籍冤魂》等。这些剧目,或警人心之萎靡不振,或策团体之涣散不坚,“或唤起民族主义思想,或讽刺社会现状,取材颇有新意”[30],“演之亦足以鼓励人心、唤醒迷梦”[6](p.32)。如《明末遗恨》,取材明末李自成进京的故事,“其写庸相之误人,奸党之卖国,外戚之赢利罔私,勇士之慷慨激昂,烈女之报仇血恨,莫不绘影绘声,维妙维肖”,使观众在欣赏高水平的戏曲表演的同时,得以抚今追昔,以史为鉴,自然而然生发出“毋使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之慨。[3]而《黑籍冤魂》通过一个封建大家庭因吸食鸦片以致家破人亡的悲剧,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受到鸦片毒害的情况,在观众中更是激起强烈的反响。据说一些鸦片商人对此剧的上演极为仇视,甚至以投寄恐吓信、炸弹等相威胁,但潘、夏等人不为所动,不仅丝毫没有畏怯退缩之意,反而公开登台演说答复恐吓者:“戏要演,毒要抗,决不退让。”[22](p.348)
1911年4月,李平书、叶惠钧、沈缦云等人发起成立全国商团联合会之时,为了帮助筹款,夏月珊、潘月樵等人还在新舞台排演了名为《国民爱国》的新剧,吸引大批观众前来观演,“上中下三层,观者竟不能容膝”。演出前,沈缦云发表演说:“此剧名《国民爱国》,今日诸君购券莅场,如此热心。切盼观剧国民,大家爱国。”拳拳爱国真情,感动了全场观众,“闻者鼓掌雷动”。当剧中“演至外人欺辱国民,士农工商、孤儿寡妇相约寻死之际,台上儿啼妇哭,观者亦多流泪。继由潘月樵假其国皇,与民共讲图强之策,痛哭疾呼,感动多人投资助费”。当日收到的捐助就有900余元,甚至还有观众捐出了金表、金戒指等。[32]
新舞台“乃是旧戏新演的场所,也是新戏旧演的场所,在现代戏剧史上,它是一个重要的场所”。[33](p.191)无论是“旧戏新演”,还是“新戏旧演”,新舞台戏曲表演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突出了社会批判性。实际上,自王钟声组织春阳社起,戏曲表演就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演戏的目的是从爱国思想出发,鼓吹革命,所以在戏里时有长篇演说”。[27](p.127)王钟声“长于言辞,说话很有煽动力,能吸引人的注意,所以他一上台就能引起观众的共鸣”。[25](p.52)其他新派人士在演剧时也时常夹杂煽动性的政治演说,“开口就是‘四万万同胞’、‘手枪’、‘炸弹’、‘革命’、‘流血’”。[34]新舞台创建后,这种夹杂演说的戏曲表演方式,迅速风行开来,甚至还引起了表演角色的变化,即出现了所谓的“言论派正生”、“言论派老生”等角色。
所谓“言论派正生”、“言论派老生”,“顾名思义,就知道他是经常发议论的。这样的角色,多半属于爱国志士一类”。[33](p.201)除此之外,“剧中的主要角色,不管小生花旦也往往会对台下说一大篇道理”[25](p.55)。这类角色虽然后来蜕变为演员在舞台上的自我表现,但在辛亥前初兴时,不仅在形式上较为新颖自由,而且还使演出更具有鼓动性,使剧情的革命主题更突出、鲜明,“颇合当时观众的心理,而潘月樵的议论,夏月珊的讽刺,名旦冯子和、毛韵珂的新装苏白,也是一时无双”[32](p.192),令人回味无穷。尤其是潘月樵,巧舌如簧,每每登台,则慷慨激昂,颇能打动观众。时人将潘月樵与马相伯相比,说“马相伯演说似做戏,潘月樵做戏似演说”。[29](p.30)
毫无疑问,新舞台的出现,标志着戏曲改良运动已从前期的理论探索、舆论宣传和小范围、小规模的演出尝试阶段,转入了规制化、规模化的舞台实践阶段。从旧式茶园到新式舞台,伴随着戏园建筑样式、空间结构、表演方式的变革以及表演剧目的推陈出新,戏园的整体氛围和社会功能都发生了变化。换言之,新舞台作为戏曲改良运动中应运而生的新型戏园,虽然依旧以排演戏曲的方式为社会公众提供休闲娱乐服务,以满足人们的文化生活需求,但它同时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担负了政治宣传和社会批判的功能,甚至于宣传和批判已超越了观众的休闲娱乐需求而成为其主要功能。就此而论,作为公共娱乐场所的新舞台实际上已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化”,并因之转而成为批判性的公共空间。
辛亥前后,在新舞台的带动下,上海的戏园纷纷改造,相继向舞台化剧场方向转变,陆续出现了一批新式剧场,如文明大舞台(1909年)、歌舞台(1910年)、共舞台(1910年)、新新舞台(1912年)等。这些以“舞台”命名的新式剧场与“新舞台”一样,在建筑样式、舞台设计、表演形式等方面不断创新,不遗余力。相形之下,旧式茶园愈加显得陈旧、土气,遂逐渐被淘汰。从各个“舞台”上的演出者来看,不仅有旧艺人,更有一批受西方思想濡染的各界人士,“像春阳社这样的组织,里面有绅士,有买办,有商人,有学生,成员是很复杂的”。[25](p.53)他们把戏曲演出视为一种开启民智、宣传革命的手段,编排演出各种时事新剧、外国剧和有现实借鉴意义的历史剧,“在戏的内容方面都含有民族思想和社会改良观,故事说白比较近于平凡,能使得妇孺皆知”。[35](p.123)
天僇生在论及旧戏曲之弊时曾指出,旧式戏园,“其所演者,则淫亵也,劫杀也,神仙鬼怪也,求其词曲雅驯者,十无一二焉,求其与人心世道有关者,百无一二也”。[17]此语虽不无以偏概全之嫌,但一般而论,旧戏所演,“谋于目者,皆忠孝节义之陈迹,谋于耳者,尽肃雍和蔼之正声”[36](p.122),无论情节如何曲折,内容如何生动,表演如何精彩,大多远离社会现实,缺乏明确的社会政治批判意识,却是不争之事实。诚如姚公鹤所言:“以原有之戏曲,街谈巷议之故实,靡音曼节之淫词,供旧社会之玩物,赏心则有余,谋新社会之移风易俗则不足。”[36](p.122)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欧阳予倩对新旧戏也曾作过一番对比:“旧戏舞台上反映的是历史事件,表演的是历史人物;新戏所反映的是当代的生活,当代的人物;用新的戏剧形式,表现着人民切身的社会问题,和人民自己最熟悉的、体会最深的社会生活;新戏一出来,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是很自然的。”[25](p.56)
因此,较之于旧式戏园,新式舞台已从一般意义上的休闲娱乐场所转变为变相或公开的政治宣传场所,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批判性公共空间。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虽未必通过公共交往和公共批判而直接生产出“公众舆论”,但通过戏曲演出和观、演之间的面对面交流,确乎制造出某种批判性的剧场氛围。其结果,是在潜移默化之中,将观众的目光由狭隘的私人小天地引向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由自足自乐的个体性的娱乐消费引向集体性、大众化、社会化的文化、政治批判,并最终汇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
注释:
①学界对清末上海戏园的研究,虽已积累了一些成果,但以往的研究,多从戏曲史的角度着眼,讨论戏曲改良、海派京剧、戏曲理论革新、戏曲变革的外来影响等问题,较少注意戏园社会功能和空间属性的变化。近年来,以戏园为论题的文字主要有:许敏《晚清上海的戏园与娱乐生活》,《史林》1998年第3期;蓝凡《风云季会的上海戏剧舞台》,《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李菲《近代上海新式剧场的沿革及其影响》,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姚小鸥、陈波《〈申报〉与近代上海剧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②晚清时期,人们对旧式戏剧演出场所的称谓不一,或称茶园,或称戏院、戏园、戏馆等,但以称茶园较为普遍。
③丹桂园后因经营不善而盘与杜蝶云接办,光绪年间复盘与大奎官孙春桓。参见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63页。
④参见池志瀓《沪游梦影》,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157页;曹聚仁《听涛室剧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189页。
⑤这一时期的新剧团体主要有:1908年6月,汪优游、朱双云、任天知合组“一社”,演于天仙茶园;钱绍芬组织“乐社”于沪南;金应谷组织慈善会,演于张园;姚桂生、陈无我合组“天义社”,演于大观园;7月,沈景林、陆申麟合组“仁社”,演于天仙茶园;9月,屠开徵、李廉甫合组馀时学会。1909年1月,一社、天义社、慈善会合组“上海演剧联合会”,演于春桂、张园;6月,袁荩之成立“亦社”,演于张园。1910年6月,陆镜若、王钟声、除半梅等合组“文艺新剧场”,演于张园;8月,汪处庐组织广济社,演于张园。参见徐慕云《中国戏剧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1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