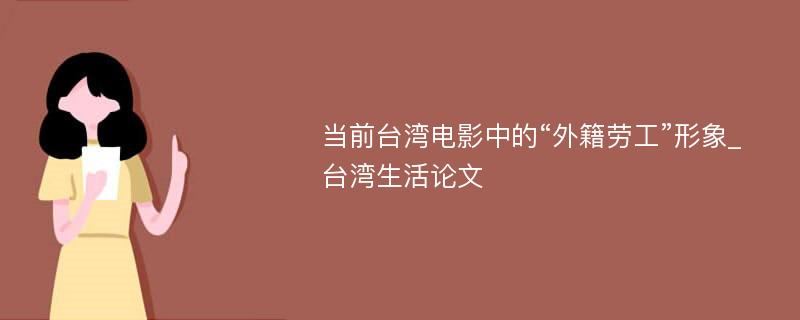
当下台湾电影中的“外籍劳工”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工论文,外籍论文,形象论文,台湾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5)02-124-06 “外籍劳工”问题已经成为台湾社会公众关注的领域之一,根据台湾劳委会2011年9月的统计,台湾外劳人数达417000人,其中最多来自印尼(约占40%),其次是越南(占21%)和菲律宾(20%)。而“外籍劳工”一词本身就具有特定的阶级与种族涵义,在台湾,“外籍劳工”专指来自东南亚欠发达国家的低层次蓝领工人群体。它不包含所有的外国人,而专门指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制造业工人、家庭帮护工等。①在电影创作领域,“外籍劳工”题材也开始出现,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台湾电影人直面这一早已存在的社会问题,站在外籍劳工的立场上去表现真实的劳工生活和塑造劳工形象,试图化解“外劳”问题中的危机和对抗。当然,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表达社会问题时,也容易被看做将社会问题搬演成神话故事②,供社会大众消费的“外籍劳工”的苦难生活,亦可以塑造出温顺谦和卑微的外籍看护工,以人性之美转移族群、阶级差异带来的矛盾和冲突。 外籍移动劳工问题产生于一个提倡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环境中,这种大环境本身为跨国移动工人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让存在于主流社会内部哪怕是角落中的异国劳工文化得以保存它的独特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真的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有尊严地保留跨国劳工文化相当困难。因为文化对话的前提是有人能够真正发声,真诚表达,能够和主流文化形成一种对话,赢得尊重。在这个意义上,长期受压抑的外籍移动工人的“发声权”难以真正打开,强势主流文化所宣扬的多元文化主义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台湾的外籍移动工人,在频繁的流动和短暂的逗留中,也未能形成被台湾主流社会认可的“文化主体”,只是远远的“他者”。 当下台湾电影中,“外籍劳工”的形象屡有出现,但多半是负面的或者零散的。2009年以来,开始出现了专门以外籍劳工为主要角色和探讨重心的台湾电影。这与“外籍劳工”事件频发,日渐成为台湾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直接相关。在台湾近年来的电影作品中,除了《台北星期天》和《歧路天堂》两部以外籍劳工为主角之外,更多的来自电视电影,如《我俩没有明天》(2003,林靖杰导演)、《海边的人》(2007,郑文堂导演)、《移民天堂》(2007,梁修身导演)等,《海边的人》、《移民天堂》、加上《娘惹滋味》构成台湾人生剧展“移民”三部曲。 本文试图选取几部当下台湾电影进行分析,这其中包括剧情影片和公共电视人间剧展放映的电视电影。它们都以台湾“外籍劳工”为表现对象,展示在台湾努力挣钱养家糊口的普通外籍工人的生命故事。这些影片是在台湾社会“外籍劳工”冲突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出现的,影片反映了雇主和雇工的冲突,这些冲突中夹杂着性别差异、种族矛盾、宗教信仰等因素。这些影片中,绝少有执法机构和外籍劳工的冲突,较多的是温和的人性解放、宽容忍让的和解。中心/边缘、离乡/返乡、本岛/岛外成了台湾外籍劳工影片中的诸多主题。 移动工人的情感心理与需求:《台北星期天》《歧路天堂》 《台北星期天》(2010)、《歧路天堂》(2009)、《娘惹滋味》(2007)、《我的强娜威》(2003),这几部作品都是近些年制作发行的剧情电影或电视电影。影片塑造的在台湾的外籍劳工或外籍新娘的形象,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他们在台生存状况的困苦与无奈。这些影片勾勒出一幅以种族矛盾、阶级矛盾为底色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图景。当然,其中大部分影片选择温情、宽厚、体谅来想象性地解决存在的矛盾与冲突。 近些年台湾发生过外籍劳工与本地雇主或政府间的对抗性事件。但在整个社会公共情绪中,某种良知似的同情似乎是基调。在这类台湾电影中,几乎见不到身体性的对抗,连情绪性的反抗都降为委屈和隐忍,幽默和诙谐取代化解了对抗与冲突。《台北星期天》(Pinoy Sunday)是2010年何蔚庭导演的处女作,曾“惊艳”当年的金马影展。这是一部以两位在台湾的菲律宾工人为主人公的幽默喜剧,整部影片可以概括为一个“搬沙发”的故事。一个被人遗落在街头的红色沙发,成了他们二人对于家庭生活、休闲甚至天堂的想象与情感寄托。如何将沙发搬回住所天台成为影片的主线,引发了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搬沙发的举动背后是外籍工人的休假问题。导演说“移工的悲惨故事已经很多人拍了、讲了,但从没有人拍过这些人假日的、快乐的时候。”③这意味着在“外籍劳工”的面前要对他们的真实处境有所回避。然而,导演还是展示了他们遭遇的不平等:公司老板的怠慢、假日休闲的丧失、被盘剥的薪水。 影片片头是刚到台北机场的菲律宾移工Dado,当他憧憬着未来老板的模样时,却在卫生间偶遇工人老乡,这位老乡正手戴镣铐准备遣返故乡。这给影片整体轻松幽默的风格灌注了一层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联的严肃底色。有人憧憬致富的美好前景,有人却触犯了劳工规定被遣返回乡,也许回乡才是更值得盼望的前途呵。剧中的另一主人公是Mauel,一个年轻幽默从事体力劳动的菲律宾单身工人。导演从Dado和Mauel两个背井离乡的男性工人入手,透视着外籍劳工的生活、工作,以及对休假、休闲甚至情感的需求。Dado和Mauel代表了外籍劳工们的休闲方式:教堂、逛街、寻找或者约会女友。《台北星期天》正是围绕着Dado和Mauel休假的一天展开,Mauel梦想将沙发放到宿舍房顶天台就可以夜间聚会。沙发不只是舒服的落脚处,更是一种在烦闷的重体力劳动之后对休闲生活的渴望,躺在沙发上喝酒、唱歌、看异乡夜空。Mauel在影片开头天台的一次闲谈中说“我们这里就缺一张沙发,简单好看的经典款,坐起来又柔软又舒服。收工后,我可以在这儿休息,看着天上的星星,然后畅饮一口冰啤酒。真是太赞了,太完美了。”Mauel没有说出的是他脑中开始的美好想象,电影镜头平移给出了这个“想象性的画面”:霓虹灯装饰下的夜幕中的天台显得柔情浪漫,红色皮质沙发上是Mauel和他梦想的女孩在热情接吻。但这“美梦”很快被Dado叫醒。电影中另一场景更清晰地呈现了这种渴望:一个休息日,Dado和Mauel外出,走在台北街头,突然两人同时被一张巨大的广告牌吸引而停下脚步,摄影机先是虚焦摄影,伴随着两人的专注,再清晰对焦,内心的渴望越发清晰,广告内容恰是红色的皮沙发“只愿,一生一世就这样依偎在你身旁……”美好的白日梦再度浮现,Mauel梦想在红色的沙发上与梦中情人亲昵,Dado则想象着跟妻子女儿相互依偎在沙发上,享受美好的家庭生活。“当你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手里拿着冰凉的台湾啤酒,整个屋顶都是属于你的……然后你不禁问自己,如果上面是天堂?那我身在何处?如果我已经身在天堂,那上面又是哪里?”两人决定将“偶遇的”沙发搬回宿舍。两人搬着耀眼的红色沙发穿梭于台北市区,支撑他们的力量是夏日阳台上的“白日梦”,是工作之余的休闲生活,弹吉他、打鼓、喝酒、聊天,享受劳动之后的休闲娱乐。在影片结尾,夜色下的基隆河水令两人想起在菲律宾组建乐队的日子,失意的Mauel得到Dado的鼓励,镜头给出了一个梦境般的结尾,两人以沙发为舟,徜徉在基隆河水中,谈着吉他打着手鼓,唱着欢快的菲律宾歌曲。天亮之后,两人回到现实,影片给出了那个真实的“现实情境”,晚归迟到,两人丢下沙发落寞地坐着巴士回工厂,接着可能是被处罚、遭遣返,被迫回到家乡。而那个美好的“沙发白日梦”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泡影。 另一部较《台北星期天》更早出现,但不如《台北星期天》博得更多关注的“外籍劳工”影片是2009年4月在台湾上映的《歧路天堂》(Detours to Paradise)。导演李奇是台湾知名的英文教师,他跨进电影界拍摄的处女作即是《歧路天堂》。《歧路天堂》是台湾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外劳题材电影,影片主要描写的是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劳工,小丽Setia是一位来自印尼的女佣,阿勇Supayong是来自泰国的建筑工人;这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不同国籍的工人,在台湾这片异国土地产生了感情,他们在台北和桃园彼此珍惜,享受着爱情的甜蜜。他们在台湾雇主面前的隐忍卑怯与在恋人面前真实自我的展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以小丽故事为核心,延伸出另外的三个角色,在爱情、亲情、友情三个层面去触碰台湾社会对待外籍劳工的问题,促使社会反思如何以更公正的态度来对待外籍劳工。 台湾自1992年正式引进外籍劳工,多元的异域文化涌入台湾社会,间接影响着台湾社会的面貌,相应的社会问题也跟随而来,即社会对于外籍劳工的误解与歧视,外籍劳工被视为低劣、落后、封闭的“他者”。将移动工人视为具有根本差异的异族侵犯者,其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被雇主国认为无法同化相容,甚至应该被完全排除。把文化差异视为自然的本质,将主流社会排斥歧视移动工人的行为合理化,这种种族化不只是建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区分,而是衍生复数的他者,与不同阶层的文化想象相联系。④ 与《台北星期天》相比,《歧路天堂》更清晰地将影片主题指向了外籍劳工在台的情感状态。来自印尼的看护工人小丽,离了婚,带着快上小学的女儿,为个改变经济状况,给女儿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来到台湾“寻找天堂”。然而,小丽在台湾的工作并不顺利,先是她照顾的老人病逝,因担心会被遣送回国,过着担惊受怕、躲躲闪闪的日子。经历了离婚的打击,小丽原本对爱情已经丧失信心,偶然的机会结识了来自泰国的阿勇Supayong,爱情又回到了她的生命中,燃起走向幸福天堂的新希望。泰国工人阿勇Supayong,天性乐观、法律观念淡薄,主张及时行乐,沉湎于当下的欢乐。他和小丽相识后,在每周繁重的工作结束之后,与小丽尽情享受属于彼此的“天堂”世界,他骑着在路边偷来的机车,恣意地载着小丽游荡。但后来阿勇被警察查获,将被遣送回国,这段异国劳工恋情也就此结束。来自泰国的劳工Wonpen婚姻失败,独自挣钱抚养一对儿女。得知患上乳腺癌之后,Wonpen更努力挣钱,她起初做护工照顾按摩店老板父亲,后来开始兼职做色情按摩服务,最后彻底流入色情按摩行业。费曼光则是唯一一个作为主要角色的台湾雇主,一场车祸让本是台湾电影明星的费曼光事业和生活都跌入谷底,剩下的只是忧郁失意与外界隔绝的寂寞生活。直到遇见送外卖的小丽,生活出现了新的气息。失去丈夫与幼子的费曼光和失去在台打工的亲姐姐的小丽,意外地产生了情感联系,台湾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撞、台湾雇主与外籍劳工之间身份地位的差异、人物真实的内心情感需求与外在情绪的发泄构成了整部影片冲突的高潮。 《歧路天堂》重点表现了外籍劳工对情感的渴望、对性的生理需求。每天高强度的工作、严苛的管理制度和极少的休假都压抑了他们的情感。在《歧路天堂》和《台北星期天》中展示了外籍劳工要在台湾寻求爱的港湾,想在台湾创建自己的家庭或者只是谈一场恋爱都是何等困难。 《歧路天堂》和《台北星期天》通过剧中几位主人公的情感故事,显示了因为环境而变异的情感。《台北星期天》中菲律宾工人Dado,为了给家中的妻子和女儿更好的生活独自来到台湾打工,他和也有家庭的打工女Anna保持着临时的男女关系。他在给家中打电话时得知妻子受伤,对妻女的想念让Dado反省自己的行为,于是结束了这段临时关系。外籍劳工因为异地他乡的孤独寂寞可能选择临时“夫妻”关系。这种情感关系如同一场梦一般,带着虚假的面具满足彼此的需求,暂时忘却道德、伦理。⑤在《台北星期天》和《歧路天堂》中,也都对周末假日外籍劳工聚会的场所有所涉及,其中,外籍劳工假日的大型disco pub总是吸引着寻找情感对象的年轻男女,在颇有家乡文化氛围的娱乐场所(比如《台北星期天》中的金万万),沉浸在香水、酒精、音乐声中,男女相追。《台北星期天》里的男主人公Mauel正是借假日舞会的机会追求同是泰国劳工的Cecilia,有台湾社会学者称这种情感关系为“速食式”的情感需求模式。《歧路天堂》的女主人公泰国外籍劳工Wonpen,因经济所迫接受了兼职从事色情按摩的工作,也是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在许多外籍劳工商店中,暗藏着这样的“速食”情感玄机,色情中介和电话成了外籍劳工满足“速食”需求的手段。⑥ 《台北星期天》和《歧路天堂》从不同侧面解读了外籍劳工在台湾生活的种种困境,处在社会底层的外籍劳工有物质困境,有情感压抑,但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被轻松地跨过了,主人公要么回乡找救赎,要么以人性消解敌意,而激烈的矛盾冲突被隐藏了。 理想女佣和跨境婚姻:《娘惹滋味》《我的强娜威》 相较于将男性生产线雇佣工人为主要刻画对象的外籍劳工题材电影,女性外籍劳工角色则更充满戏剧性和建构性。男性外籍劳工形象身上尽管被赋予诙谐、幽默、能干、吃苦的特质,但也总还是含有几分对抗性的力量和一触即发的决心。外籍劳工中更大一部分隐身的“主体”,是女性群体。在台湾社会充当家庭雇佣工的绝大部分是外籍女性劳工,而其中又以菲律宾、印尼、越南、柬埔寨籍为主。女性移民在台湾社会还以外籍新娘的身份存在,这种特殊身份也被诸多电影搬演上映。⑦这些女性角色凸显的问题依然是种族化的“他者”身份。种族界线与阶级位置、世界体系中的阶序高度相关,种族界线的社会建构反映出该社会对于“他者”的文化想象,某些群体被认为具有历史或文化上的亲近性,可以变成“我们”的一部分,而其他群体被看作有根本差异、难以同化的永恒他者。⑧ 2007年上映的台湾公共电视电影《娘惹滋味》(Nyonya's Taste of Life,温知仪导演,2007)关注的正是台湾家庭外籍女佣问题。影片塑造了两位印尼女工西娣和纱丽,她们分别在两户台湾人家做看护工。在和台湾雇主相处中都经历了最初的对立和不了解,但在印尼女工真诚、真心的工作生活中矛盾一点点化解,将心比心换来的是放下敌意与理解接受。“娘惹”(Nyonyah)是专指生活在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的当地人与华人结合所生的女性后代。“娘惹”以勤劳能干著名,将中华传统文化与马来西亚文化融合,擅长著名的“娘惹菜”,形成风格化的中华和南洋风味结合的料理。导演站在外籍女工的立场,看到的是社会新闻“打、偷、逃”之外的另一种温情面相。印尼女工西娣在刚来到雇主家的时候,拿出伊斯兰教祈祷服祈祷,却被雇主一家以为她“装神弄鬼”而一通责骂。纱丽则总是充当着开导者的角色,她看护患有阿兹海默症的雇主老人,比亲生儿女更加用心周到,终于换得了老人和其子女的信任。西娣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雇主的认可,还将自己的娘惹风味菜引进到雇主家的小餐厅而大受欢迎。在《娘惹滋味》等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社会赋予“外籍女劳工”的形象所呈现出的特点,把外籍劳工当作理想的工人或者家庭帮工。这背后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把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劳动工人看作落后、不文明的“他者”,他们适合做危险、肮脏而台湾人不愿做的工作,是天生的廉价劳动力。家务工作本身是高度女性化的,但家庭女工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却高度地去性别化⑨,一般的形象是纯朴贫穷。在台湾电影的“外籍女工”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理想女佣”模式的生产过程:经由招工渠道,温顺的、年轻的农村女性,经过中介或者雇主的“现代化”、“文明化”训练,再加服装、发型与个性化管理,将女性移动劳工呈现出一种去性别化、符合雇主期待的女佣形象。她们性格上的特点是隐忍、谦逊、质朴。《娘惹滋味》理想化地处理了外籍家庭帮佣与雇主之间的矛盾,也给家庭帮佣想象性地勾勒出了一个完美结局,影片中西娣逐渐得到男主人的信任,早年丧妻而门庭冷落的小餐馆被西娣接管,生意大有起色。影片似乎也暗示着西娣通过情感的逐渐建立而取代了女主人的位置,进入台湾雇主的家庭。的确,对待女性家庭移工,另一个游离但相关的角色正是“外籍配偶”。 跨国婚姻中的“外籍新娘”也是外籍劳工女性受到社会压抑或者“污名化”处理的另一个典型领域。在现代社会,婚姻从来就不仅仅是私人事务,它承载了种种公共和政治的因素。在这里妇女流动的性别化与阶级化呈现出与全世界劳动力流动类似的方向与性质。在婚配关系中,跨境婚姻的“外籍新娘”以两个角度呈现,一是被人贩子欺骗的“受害者”,另一是为了摆脱生活困境而嫁给富裕国家男人的“投机分子”。⑩很多台湾电影中的“外籍新娘”角色,多半会涉及道德不端,婚姻生活不幸、理想落空,为了生活出门做妓女等情节设置。确实有学者主张将女性劳工移民与婚姻移民放在一起讨论,这些“外籍新娘”多半是被买卖的婚姻商品。其功能主要是性对象、从事家务劳动的工人甚至是奴隶,也都是当地的穷人。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可以将女性家庭雇佣工和外籍新娘问题互为参照。 《我的强娜威》(My Imported Wife,蔡崇隆导演,2003)作为一部纪录片将镜头对准一对买卖婚姻家庭,丈夫是有先天残疾的台湾小生意人黄乃辉,妻子则是柬埔寨外籍新娘强娜威,两人生活中的矛盾被摄影机镜头一一记录下来,展现了性格倔强、自尊独立的外籍新娘强娜威在婚姻生活里的辛酸和艰辛。夫妻两人争斗的核心是经济问题,享有绝对经济主权的丈夫不愿贴补柬埔寨妻子贫穷的娘家,强娜威则坚持要帮衬娘家并宁愿工作,取得经济的独立。(贫穷地区“外籍新娘”也通常被说成是依靠当地男子以便让自己获得居留在台湾的合法权利,之后便能在台湾工作并满足原生家庭的物质需求。)无论是受骗被卖,还是有心机有目的,“外籍新娘”们无一不被视为急切渴望摆脱贫困的生活状况而来。影片中的黄乃辉在台湾并非“中产阶级”身份,而是从小患有脑、腿残疾的“创业”者,他的创业只是在夜幕降临之后到各个酒吧舞厅贩卖鲜花,被当做自强自立残障人士榜样的黄乃辉有着极强的自尊并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黄乃辉梦想拥有完整的家庭生活,事业有成的同时有妻有子,这样的生活让原本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他获得极大的想象性满足。于是他选择最简单的方式完成这种生活理想,花钱娶来柬埔寨年轻老婆,生孩子。但黄乃辉同他的贫穷妻子一样,在台湾社会是处在经济地位、社会阶层的底层,或者说是未必受欢迎的群体中。这些跨国买卖婚姻的丈夫在影视作品中往往是娶不到条件相当的老婆而酗酒、暴力、坏脾气。黄乃辉更多的是对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财的计较与吝惜,将细碎的生活矛盾放大。他在纪录片中毫不隐讳地表示不希望妻子强娜威出去工作,他担心妻子一旦有钱就不再受他控制,不再听话。花钱买卖的婚姻要找到的无非是温顺、听话、懂事、生孩子做家务的妻子,这就必然决定了丈夫在身体关系上和经济关系上要双重控制。不是雇佣关系但“外籍新娘”一样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在不断冲突对抗中,如强娜威一样自强的“外籍新娘”努力地发声和表达,希望在冲突中实现和丈夫的平等对话,渴求在异乡土地上有真正的家。 这些以外籍劳工为对象的影片当然并非台湾社会主流媒介喜闻乐见的主题,拍摄这些影片要顶着票房和舆论的双重压力。虽然这类影片是绝对的少数,但将摄影机对准弱势群体,带观众进入外籍劳工的内心世界,这也给主流商业温情娱乐电影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力量,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和电影文化的启示:期待更多的人关注全球化移动工人的问题,期待更多的观众通过影像的力量感知社会深处的“移动工人”群体,尤其是“外籍劳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因为这些普通的劳动者背后,是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资本流动带来的最直接的“流动的力量”,这种流动是工人被迫追逐收益的不得已的选择,是受跨国集团资本剥削更多的群体。 这些影片通过镜头追踪或根据外籍劳工真实经历编演,揭示外籍劳工在异国他乡的社会困境,面对艰苦的生存环境和劳动环境,如何满足家乡亲人的期待,如何通过善良与爱的真心付出赢得社会的理解和认可。但影片往往忽略或回避了劳资斗争与冲突,以乐观、积极、隐忍,乃至诙谐、幽默来化解现实矛盾和敌意,多多少少不无粉饰之意。 ①1992年台湾颁布《就业服务法》规定,专业白领外国人的聘用,采取个别许可制,工作许可的取得没有配额管制,契约及工作居留年限无上限。底层移动工人的雇用,采取“客工”(guest worker)的模式,雇主的雇聘资格受到配额管制,移动工人只允许在工作契约期间最长到六年的短暂居留。只能为一个特定雇主工作,不得转换雇主。 ②尼尔·金:《对抗类影片:电影中流离失所工人的祭坛》,李时译,载《世界电影》2010年第1期。 ③放映周报,第255期,放映头条《两个男人与沙发,一种梦想与现实—专访〈台北星期天〉导演何蔚庭》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297。 ④蓝佩嘉,《阶层化的他者:家务移工的招募、训练与种族化》,发表于“跨界流离:全球化时代移民/工与社会文化变迁”研讨会,后收入会议论文集上册,可参见文章第一部分《阶层化的他者:移民分类的种族化》。 ⑤这已经衍生出一种FOR Taiwan Only的情感关系,指男女外劳在其原生国可能各有家庭或伴侣,但在国外移工期间因心理与生理的需求,而意外发展出的情爱关系,但当合约期满后就必须终止关系,互不联系。 ⑥关于台湾社会外籍劳工情感模式的讨论,参见宋法南,《从〈歧路天堂〉探讨外籍劳工的性需求模式》,该文收入巨流图书公司《国族想像离散认同—从电影文本再现移民社会》,2010。 ⑦比如钟孟宏导演的《第四张画》(2010)中郝蕾饰演的大陆新娘,《停车》中大陆来台的妓女等。 ⑧蓝佩嘉,《阶层化的他者:家务移工的招募、训练与种族化》,发表“跨界流离:全球化时代移民/工与社会文化变迁”研讨会,后收入会议论文集上册,可参见文章第一部分《阶层化的他者:移民分类的种族化》。 ⑨同上,蓝佩嘉,《阶层化的他者:家务移工的招募、训练与种族化》第五部分《打造理想女佣》,文中从招募、训练、再现三部分展开对女工“去女性化”的方式。 ⑩Nobue Suzuki,《跨国境婚姻:再现与“国土安全”》,倪世杰译,发表于第三届“跨界流离:国际学术研讨会:治理、生存、运动”,2006年10月,收于研讨会论文集(上册),P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