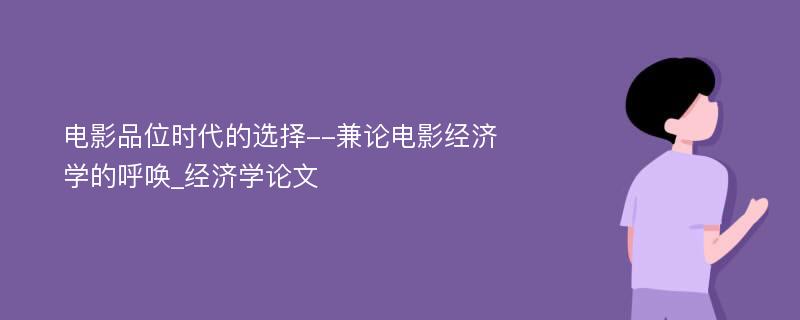
电影品位的时代抉择——兼及电影经济学的呼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影论文,经济学论文,品位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J90
当年轻的电影艺术即将跨入它有生以来第二个世纪之门的时候,面对商品经济的无孔不入,价值观念的迭迭更新,如何调整它的内部结构,重新确立它时代性的定位,以实现其自身价值,该是摆在每个电影艺术工作者面前一个新的时代命题。
回顾电影百年,其艺术品位的纷纭众议,价值取向的斗转星移,无不围绕着商品属性和艺术价值调谐它运作的砝码。在电影刚刚诞生的日子里,虽然爱迪生一时缺乏竞争意识,被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抢了头功——他认为默片的过早公映,无异于“杀死一只会生金蛋的母鸡”——但他很快以艺术上的人为加工和技术上的刻意求精,给自己的影片贴上了厚厚的商品标签;而卢米埃尔兄弟却以纪实风格,满足于现实生活的实录与再现。当电影走向成年以后,由于表现要素的日趋完备和美学追求的各执一端,这两种不同向度的追求便在欧美大地各领风骚数十年。时至今日,应该在更自觉、更清醒的意义上,找到二者之间的种种契合点。
首先,让我们擦亮历史这面镜子:
两极发展的本世纪电影
尽管世界各国的电影标榜着仪态万千的个性,但从它的总体追求上可用“商品性”和“艺术性”作为广义的界定。
人们长期以来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美国电影称霸全球,远销世界各个角落,被称为“装在铁盒里的大使”,而绝大多数国家的电影萧条寂寞,甚至向输入的“十大巨片”乞灵,解决入不敷出的困境;可是很少想到从美国电影中寻求些生存发展的方法,以构造自己的“十大巨片”。既然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切经济行为、文化行为都把金钱效益放在重要地位的时刻,电影也无须自持高雅而甘愿脱离这严酷的现实。
众所周知,美国电影在承认电影诸多属性的同时,始终把商品性放在突出的地位。它早已成为企业家赚取高额利润的手段,成为专门掏取观众钱袋的“扒手”,成为美国政府内外贸易名列前茅的行业。美国电影在种种困扰中持续发展的要义固然很多;但从经济学的思考来看,不外是心中有“上帝”、眼中有“对手”、脚下有“示标”,而且它们又直接左右着电影的创作与制作。
古往今来的生意经都有一个颠扑不破的主题,就是心中有“上帝”。因为一切生产行为——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要通过顾客(受众)的消费才能实现它的真正价值。美国电影不惜重金,通过各种不同渠道向它的观众进行分层次、分行业的调研,把观众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审美追求了解得一清二楚,以便随时调整自己,投其所好。例如,“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发生在本世纪初,他们便针对当前社会上普遍弥漫着的一股“回顾和凭吊逝去年代的悲伤心理”,拍出了带有浓重时代意识的《泰坦尼克号》巨片,“揭示了物质、科技高度发展仍然无法避免因人的贪婪、虚荣、疏离引发的毁灭”(注:(美国)《世界日报》社论,1998年3月26日。), 从而契合了世纪末西方世界大众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感和一种对命运的无奈与无力。至于眼中有“对手”,美国电影更是走在了前面。他们很早就把自己的竞争对手投向了电视,而且把它作为一切创作、制作活动的出发点,举凡足不出户,坐在电视机前所无法领略的图景,都是他们殚精竭虑的追求。试想,反映在银幕上的一场巨大的沉船灾难,通过小小荧光屏去显示会有何等微不足道的效果!要使一双双怠惰惯了的双脚,富有吸引力地从舒适的客厅、居室迈向影院,非有一条咄咄逼人的制片路线和不同凡响的创作思路不可,长期以来,美国电影在题材的选择、结构的营建,制作的精良、耗资的庞大等方面探索出一套足以使电视望而生畏的对策。他们对电视采取一打一拉、亲疏兼济的策略:一方面,把电视作为对手,以高投入、大制作的巨片路线与之抗衡;另一方面,又把电视作为可以依傍的朋友,向电视台出售录像带,借助电视这个媒体宣传电影,以求联手并进,因为这块宣传阵地是任何人都不敢忽视的。所谓脚下有“示标”,就是它每启动一步都有人鸣锣开道。许多影片还没有开拍,一大笔宣传资金就已到位。此后,启用多少明星,投入多大资本,有多少豪华的场面等等讯息早已沸沸扬扬,家喻户晓,在观众中造成一种急切的期待心理。应该说,一切营销之道,美国电影都无所不用其极。
而在欧洲大陆的法国,却对此麻木不仁。他们虽然口头上也承认电影的商品属性,并且拍了一些商业性影片,但与他们自持清高的艺术影片比较起来似有天壤之别。法国著名电影史家乔治·萨杜尔说:“作为结论,我们能为法国电影的相当长远的历史指出它的特征吗?首先,法国电影是最早被组成工业的,并且最早在梅里爱的影片中,随后在1920年左右‘印象主义者’的要求中显示出它是一种艺术。”他从创作实践中毫无避讳地指出:“从它创作作品以来,法国电影当然制造了不少商业性的影片,但是它的影片中最优秀部分总是属于一个因有伏尔泰、狄德罗、卢梭、雨果、巴尔扎克、左拉等这样的名人而获得国际声誉的文化传统。”(注:(法国)乔治·萨杜尔:《法国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55页。)这里所说的“文化传统”, 当然是以文学名著相标榜的作为艺术品的电影了。其实,把电影作为艺术看待,原属理所当然;问题在于将它与商品性绝然隔离,并斥之为媚俗、媚金之作,进而以不受金钱支配而自鸣高雅。在法国,许多电影是要由专家引导才能看懂的。他们要求观众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不像一般的娱乐品那样人人可以接受的,这就把自己的观众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至于电影有多少商业品位,有多大经济价值,似乎不是他们的注意中心。唯其如此,他们专注于文化视角,逐渐走向了曲高和寡的极端,大多数观众是不会买帐的。在百余年的电影历史发展中,为了追求艺术性甚至“纯艺术”,以欧洲大陆为中心兴起了五花八门、此起彼伏的电影艺术探新运动,而其中大多数都策源于法国。从20年代的“先锋派电影”、“实验电影”、“抽象电影”、“印象派电影”,到50年代兴起的“新浪潮电影”、“真实电影”、“左岸派电影”、“黑色影片”等等。法国人同拥有巴尔扎克、莫泊桑、莫里哀、左拉这些文学大师一样,以拥有阿仑·雷乃、罗布·格里叶、让·卢什、法朗索瓦·莱兴巴赫和特台弗、格达尔为法国电影的骄傲,至于他们给法兰西民族带来多少经济效益倒不是那么重要。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看到世界电影两种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
双向综合的Y型流势
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电影形势的激流大潮,必然唤醒一种崭新的电影观念。正是这种价值取向的觉醒,必将迫使各国电影做出影响自身生存和经济发展的时代抉择。这种抉择的主体标识,应是在注重商品性与倾心艺术性的两极发展走向综合的Y型发展趋势带引下, 所有运作环节的大调谐。
首先,电影创作与电影营销亟待接轨,进而产生一门带有跨世纪特点的新的学科——电影经济学。
多年来,电影艺术一直追求着自己的创作个性,这本是一切艺术创作不可逆转的规律。但这种个性如何与大多数观众鉴赏心理的共性沟通,则是商品经济向每一位电影艺术工作者提出的时代课题。著名电影艺术家希区柯克甚至极而言之地说:“电影是观众造成的”。因为没有观众就没有电影,这同没有顾客就没有商品一样,电影是在同观众的双向交流中、在同观众的求同存异中稳步发展的。电影工作者的眼里绝不可没有观众。发行放映者如此,创作、制作者也是如此。长期以来,这两支大军的互相抱怨,其根本原因是缺乏一种必要的沟通。只有营销人员将那些来自广大观众的反馈传输到创作者那里,才能据此调谐影片的内在结构、找准它的时代定位。诸如,各层面观众不断变化着的心理,不断转化着的观众,特别是那些足以使他们离开电视机走向电影院的无形魔力。当然,我们不能像美国电影那样过于迎合观众的口味,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它的艺术品味。法国的德·维尔布瓦说得好:“如果没有枪战,没有床上戏,没有汽车追逐,那就不是美国电影了。”面对当今世界种种社会势力的纽结纷争,人们要惩恶扬善,人们要渲泄那种积郁于心、在现实中又难于表达的某些情感力量,要看枪战;碍于电视节目“大众同一”的种种戒律,一些青年喜欢到电影院去领略现实中一时未能得到的某种满足感,于是有了床上戏;鉴于电影以动态可见的多彩画面在艺术百苑中取得压倒群芳之势,运动是它的存在理由和优势,加之青少年好动的心理,汽车追逐便满足了这些欲求。但是也应看到,任何一种观众心理都不是静止不动、千载不移的,更何况这些东西只能作为艺术创作的参照系,永远不能成为定型化的某种法则。
其次,类型化与独创性的契合,既迎击了商品经济的挑战,又符合其艺术的自身的发展规律。类型电影是美国好莱坞成功经验的某种概括。对此,人们长期以来各执一端、莫衷一是。有的人甚至认为,类型电影是窒息电影发展与活力的桎梏。其实,类型电影的类型本身就是一种富有远见的经济行为。在艺术家的精心探索中,一旦发现某类影片受到观众的热切欢迎,便以此成功的模式再创辉煌,从而大大减少了它的风险与失败的可能。其实,一些改编作品和以历史为题材的影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避风险、免失败的模式化追求。从积极的角度看,它是对人类文化遗产、既成经验的尊重,也是对观众按图索骥、期待心理的满足。但是类型化也不是僵固的模式而一成不变的。严格说来,世上没有绝对的类型化,有的只是类型化的追寻与超越。如果把它与独创性更自觉地结合起来,其前景是不可想象的。在类型电影的创作中,人们会不断发现带有突破性的思想意念和艺术要素,于是要更新,要独创,使之上升为新的模式,新的类型质。我们看中国电影一个不可忽视的类型就是谢晋模式,他从传统美学中承继下来的对人性、对善重于美的追求,到一整套的独特叙事结构,都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所喜闻乐见的;但谢晋电影的发展与独创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要说他跨越几十年的30部电影,单就新时期十多年中的电影创作来看,他也是不断进行自我超越而走向创新的。在《牧马人》中,我们看到的是许灵均从受迫害、在困境中挣扎奋斗,到再次振作而拒绝出国的一个比较单纯的叙事构架和心理发展轨迹。而《芙蓉镇》中的主人公及其人事关系则复杂得多。“女人同时扮演了‘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角色,这种情况就是弗·詹姆森所描述的,一个行动素由两个角色共同承担。”(注:马军骧:《从谢晋电影到新潮电影——两种叙事结构和两种文化构型》,《电影学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9页。) 李国香的复杂性格和心理深度不仅超越了许灵均,也超越了宋薇,而且在叙事与构型诸方面,都代表着谢晋电影的某些独创性,因而也赢得了为数众多的观众和十分可观的票房价值。而某些与之相对的新潮电影,却由于它淡化了传统的叙事结构和蔑视传统伦理观念的若干做法,使它离开了大众欣赏习惯,也削弱了它的商品性。看来类型电影的魅力是不会消失的,问题在于怎样在类型化的操作中,不断推陈出新,构建成符合观众心理,紧跟时代节拍的新的类型质。
第三,在媚俗与附雅中间找到一个既有艺术责任感,又有大众消费性的接合点。无论是电影画面转瞬即逝的“一次过”品性,还是必然要招徕众多观众这一生存使命,都注定了它尽量体现通俗易懂、符合观众口味、清晰流畅的表现特点。这就要求它所负载的信息应以一目了然的单质为主,它所追寻的意趣,也应以大众趋同的意趣为主。但是,这种认同与趋同,决不是消极的迎合,而是积极的疏导。媚俗风习与类型电影一样,往往带有极大的惰性,而历史上的每一发展都是在克服这些惰性中前进的。多数观众需要浅显易解之俗,少数观众则需要较为深厚的蕴藉之雅,这两者在电影艺术家说来应该是矛盾的统一,是一种不断更新再造的雅俗共赏,是一种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连索。因为电影艺术的发展前景,既是受众层面的扩大,又是自身品位的升值;既是外在生存条件的适应与优化,又是内在结构的完美与附雅。如果说,无休止地重复历史与现状是艺术的狭路,那么,一味地媚俗与趋同则是艺术的灭亡。
最后还要看到,电影与生俱来的双重性格,在时代的弃取中也要找准自己的位置。电影产生于上个世纪末社会化大生产的新时代,而它的发明者又不是抒发情感、仰天长叹的诗人和文学家,而是法国一家最大的照相器材厂总经理和摄影师,它从诞生不久就追求观众的有偿欣赏和商品流通;而为了这种流通所必要的市场竞争,又需要它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这就使它既带有商品性,又带有艺术性。一方面,它要遵循艺术规律构建一个完美的艺术符号体系;另一方面,还要按照商品流通规律进入市场销售。在中外文学史上,有人以毕生精力写出鸿篇巨制而没有索取与他的付出等值的酬报;可是没有以巨额的投资拍出电影而不求回收的“傻瓜”。因为没有这种回收,就像《党同伐异》那样,弄得格里菲斯倾家荡产、债台高筑。这就使电影艺术的创作参照标首先放在能否延续生存、扩大再生产的天平上;反过来,电影商业品位的升值,也应首先放在富有无穷形象感染力的艺术砝码上,而不能是一般商品惯有的那种华丽的包装。
凡此种种电影艺术的时代抉择,无不落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挑战上。为了更自觉地将电影艺术与经济行为接轨,迫切需要电影经济学的诞生,以减少电影发展的盲目性与不适应性。那么,电影经济学的总体构架应该怎样呢?我以为它应涵括电影历史中的经济行为追踪,电影创作中的经济学思考,电影制作中的经济学观照,电影鉴赏与评论中的经济学视角等一切方面,从而形成一个既包容电影运作全过程,又具有动态特征的完整体系,成为新世纪电影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航标。
收稿日期:1998—0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