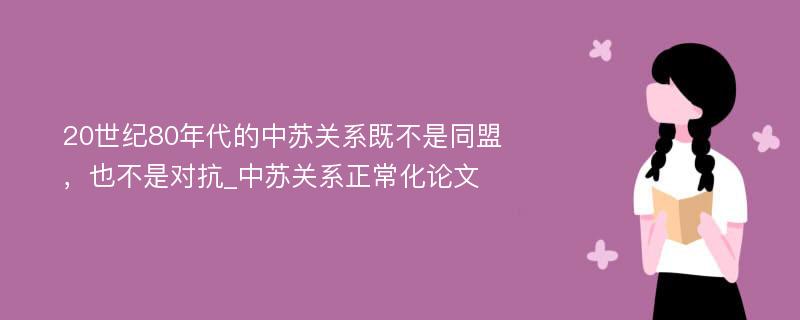
结盟和对抗都不好——八十年代的中苏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苏论文,不好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的全面激烈对抗,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正常、并非不可避免的现象。对抗的形成和发展在不小程度上反映了双方领导人的意志和个性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国家关系中这种逐渐失去客观必要性的紧张不可能长期延续,随着条件的变化、领导人的更替,必定要恢复到自然的发展轨道。因此,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是早一天晚一天的问题。
结束对抗的第一步
1979年初,国内关于中苏关系的讨论出现了高潮。原因是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年后就要到期。按条约规定,期满前一年,如无任何缔约方提出终止,条约自动延长五年。废除还是延续?这是个牵动两国人民心弦和两国政府必须在近期做出决定的重大问题。驻苏使馆对此事格外关心,曾在王幼平大使领导下进行多次讨论,并形成如下观点:中苏条约的军事同盟性质已经过时,但考虑到它的历史作用和具有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意义,最好不采取宣布废止的简单方式。如能以新代旧,既可解除军事同盟关系,又不致引起大的震动,对我稳定周边国际环境和加强我在大三角关系中的地位比较有利。
4月3日,黄华外长通知苏联驻华大使,中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但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苏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为此,中国政府建议,中苏双方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5月5日,余湛副部长又将我方关于谈判的具体建议递交苏方。其主要内容是:一、确定两国关系的准则;二、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三、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四、根据谈判的结果签订相应文件。
我方的谈判总方针和策略是8月29日最后定下来的,中央政治局在这天召开了专门会议,我随王幼平列席。会议由华国锋主持,根据邓小平主旨发言确定的基本精神是:我方在谈判中必须坚持原则,即中国不能同意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同苏联改善关系,核心问题是要求苏从蒙古撤军,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双方都应承担义务:不在对方邻国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不利用邻国威胁对方。会议结束后,邓小平还向王幼平交待了谈判的策略思想:不要急于求成,谈不成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不能示弱;当然不要骂娘,要讲道理。他还说,灵活性是有的,同意谈判就是灵活性,将来如何,要等谈起来再看。可以看出,与原先的方案相比,这次会议决定的方针有所变化,不再把确定国家关系准则和签订文件放在首位。这是个重要的策略安排,因为我方谈判的首要目标是解除苏方对我的实际威胁,搞几条空泛的原则正是苏方所希望的。
中苏国家关系谈判于10月17日在莫斯科开始。中方代表团成员有外交部副部长王幼平及李汇川、邵天任和我。苏方代表团成员有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和部委委员兼远东司司长贾丕才。争论极为激烈,光是谈判日程就用了五次会议。双方在讨论中苏关系的准则的先后问题上出现分歧。我方提出了《关于改善中苏两国关系的建议》,其主要内容是:苏方应首先把部署在中苏边界上的驻军减少到1964年的水平;撤走驻扎在蒙古的武装力量和拆除军事基地,停止支持越南对中国的武装挑衅和对柬埔寨的侵略(即消除三大障碍)。此外,也提到推动边界谈判和扩大经贸等各领域的交流。而苏联只讲空原则,回避两国关系的现实问题。
双方摆明了各自纲领之后,接下来就是针锋相对的辩论战。王幼平一再论证,我们的建议是从中苏关系的现实情况出发,如不能解决两国间妨碍正常化的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只搞几条空泛的“宣言”,是不可能导致关系改善的,“这一点已被历史所证明”。王幼平特别强调了最后这句话。从表情看,对方立即明白了,这里指的是:中苏间虽然签订过一个条约,但关系不还是恶化了吗?我方还指出,苏方拒绝消除障碍,企图在保持武力威胁的压力下谈关系正常化,只能表明其毫无诚意。苏方坚持拒绝讨论消除三大障碍问题,其主要论据是,中苏谈判不可超出双边范围,不能涉及第三国。对此,王幼平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说,苏联利用与中国接壤的第三国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完全属于中苏双边关系范畴。事实上,苏在别国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不止一次成为苏同这些国家之外的第三国谈判题目。此言一出,伊利切夫的脸刷地红到耳根,他立即想到美国迫使苏从古巴撤出导弹那件事。
中苏国家关系第一轮谈判虽然没有结果,但它是中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双方在经历了20年的紧张对峙之后,首次坐到一起,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进行高级别的正式对话,这标志着两大国的长期对抗于1979年10月开始发生转折,从此步入了走向正常化的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对抗与对话并存,对抗逐步降温,对话日益加强。
多条渠道向正常化过渡
双方商定,1980年初在北京举行第二轮谈判,后因苏联出兵阿富汗而搁浅,但持续时间不长,已经起步的过渡进程并未因此而夭折,反而沿着好几条渠道向着缓和和改善的方向一步步迈进。
国家关系磋商 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又有新变化。苏入侵阿富汗后,其国际影响一蹶不振,与美争夺力不从心,不得不搞战略调整,缓和对华关系的需要更加迫切。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对此,钱其琛以我外交部发言人身份做出反应,说中国将“听其言,观其行”。这个表态算是很积极的,蕴含着中国可能有所回应的暗示。果然在四个半月之后,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以视察使馆工作的名义于8月10日到莫斯科,与苏方进行接触。他受权向苏方表示:双方应做出努力,使中苏关系走上正常轨道,并逐步建立起睦邻友好的关系。中国最高领导人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只要双方都有诚意,从解决一两个问题入手,就可以打开新局面。苏方接受我方建议,中苏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于10月在北京开始举行。
这次“磋商”实际上是1979年“谈判”的继续,也是副外长级,我方是钱其琛,对方仍是伊利切夫。内容上也无多大差别,只是我方要求排除的障碍中又增加了一条,即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同时将苏军撤出蒙古和减少中苏边界驻军这两条并为一条,再加上原来的关于停止支持越南侵柬反华一条,仍然是三大障碍。双方在磋商中的立场也无变化。我方继续主张先解决实际问题,排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有一点新意是,我方突出强调要求苏联劝说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苏方仍然是避实就虚,拒绝承认三大障碍的存在,坚持要制定没有实际措施作保证的国家关系原则,重复其关于停止敌对宣传、增进经贸合作、互派留学生等具体建议。对此中方不能同意。
中苏都是大国,虽说双方恢复正常关系的诚意不容置疑,但在重大政治性问题上谁都不肯轻易后退一步。因此,磋商仍旧是马拉松式的,七年间在北京和莫斯科进行了12轮。谈判本身是重要的,因为它在两国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维持了一条权威性的对话渠道。但只靠折冲樽俎难以实现突破,消除三大障碍问题的僵局最终是在双方最高领导人的介入之后才被打破的。
“葬礼外交” 从1982年到1985年,苏联的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逝世,中国曾三次派领导人赴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和正式的政治谈判不同,在哀伤的气氛中人们总是容易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这样,连续的葬礼活动就成了一条特殊而有效的外交接触渠道。
1982年11月10日,勃烈日涅夫去世,中国人大常委会致电吊唁,国务委员兼外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率团前往参加葬礼,我作为苏欧司司长是代表团首席团员。在葛罗米柯与黄华的会见中,双方都强调了中苏关系的重要性。黄华讲了三句话:50年代后期(指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关系开始恶化;60年代后期(指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后达到了严重的地步;对勃列日涅夫不久前关于改善中苏关系的讲话表示赞赏(暗示寄希望于苏联新领导人)。这三句话是邓小平在代表团启程之后提出,由驻苏使馆转达给黄华的。黄华还表示,要使关系得到切实的改善,苏方必须采取实际步骤,两国间那些关键性问题(指三大障碍)如能先解决一两个,就能使关系向前迈进一步。这个姿态也是按小平同志的意见做出的,事先我曾陪同黄华去他家请示过口径。这是我方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首次表现出松动姿态。中国对勃列日涅夫去世的吊唁安排,被当时舆论视做是非同寻常的外交行动。
安德罗波夫逝世时(1984年2月9日),升格为李先念主席致唁电,万里副总理率团赴苏志哀,首席团员是钱其琛副外长。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里耶夫同万副总理举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我方正式邀请另一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当年12月成行)。阿是50年代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我方巧妙地利用他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在促成高层访问方面实现了突破。
对一年后(1985年3月)契尔年科的丧事,中国再次提高规格,由李先念主席和彭真委员长联名致电吊唁,参加葬礼的代表团由李鹏副总理率领。前两次,黄华、万里都曾参加外国吊唁代表团团长与苏新领导人的集体会见,而这次戈尔巴乔夫破例单独会见李鹏,这是他期望与中国修好的第一个姿态。李表示要全面发展中苏关系,戈尔巴乔夫表示希望中苏关系得到重大改善,并提出要提高对话级别。至此(1985年),两国关系中的敌对气氛基本被消除。“葬礼外交”这条渠道所起的特殊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纽约外长会见 多年来,除了治丧这种非正常的场合外,多年来中苏的高级官员即使在第三地也是不接触的。而在1984年,这一僵局开始被突破。9月联大会议期间,两国外长吴学谦和葛罗米柯在纽约正式会见,我作为中国出席联大会议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我记得会见分别在苏代表团驻地和我代表团驻地举行两次,气氛轻松。从此每年都这么做,直到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这无疑是两国关系政治温度升高的表现。每次会见,两位外长总是要全面地讨论双边关系和就国际问题交换看法,有时还达成某种协议,例如,关于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的协议,就是两国外长在纽约谈定的。
边界谈判 中断了九年之久的中苏边界谈判,于1987年得以重开。与1969年~1978年没有结果的九年谈判不同,这一次终于促成了边界问题的基本解决,使中苏关系中这一久拖不决的悬案有望被从历史上抹掉。双方具体讨论了东西两段边界走向问题,取得重大成果,后于1991年签订《中苏国界东段协定》。这次谈判还为后来中哈、中吉、中塔边界(原中苏边界西段)的解决打下了基础。因此,1987年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是促成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又一条重要渠道。
其他领域的交流 和步履蹒跚的政治关系相比,两国间其他领域交流的进展要快些。60年代,两国间除了保留着各自在对方的大使馆外,几乎所有来往均已中断。进入80年代后,贸易、科技、文化、学术、友协等方面的交流,逐步恢复并有所发展。1984年,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发展经贸关系的协定,并决定成立经济科技合作委员会。1986年,重订《中苏领事条约》。这一切均为日后关系的全面正常发展准备了条件。
按邓小平的设计实现了正常化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后,苏联对外政策发生了转折,由对外扩张和对抗逐步转向收缩方针和和解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苏关系的改善随之加快。
10月9日,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时,第一次提出了举行中苏最高级会晤的设想,他请齐奥塞斯库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如果能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他或胡耀邦愿同戈尔巴乔夫会晤,他出国访问的使命虽已完成,但可以破例。23日,戈会见访问东欧回国途经莫斯科的李鹏副总理时表示,苏中举行最高级会晤和恢复党的关系的时机已成熟,建议两国最高领导在苏联的远东地区或中国境内举行会晤,讨论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此后,双方通过外交途径交涉了两个回合,我方认为苏方回避消除三大障碍,因而缺乏举行最高级会晤的政治基础。苏方说会晤不能有先决条件。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说,苏联愿意同中国考虑降低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水平问题,正式宣布苏将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并表示正在讨论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他还说,苏联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划定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中苏边界。这个讲话与以往苏领导人谈中苏关系的言论有所不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是戈氏表示诚意的对华政策声明。
我方对其讲话做出了反应。先由吴学谦外长代表中国政府表示欢迎,并再次对讲话回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表示不满。不久,邓小平同志于9月2日发表讲话,肯定“海参崴讲话”有新的积极的东西,重申如果苏能消除在越柬问题上的障碍,他愿意与戈尔巴乔夫会晤。
1988年底,钱其琛外长访苏。这是1958年以来中国外长首次正式往访。邓小平同志说,这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已开始“半正常化”。双方深入讨论了柬埔寨问题,就最高级会晤问题交换了意见。接着,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于1989年2月来北京同钱外长会谈,中心议题仍旧是柬埔寨问题。经过艰苦谈判,终于取得一致意见,我方最关注的这一大障碍已基本消除。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夕,苏联宣布从5月15日开始从蒙古撤军。至此,举行中苏最高级会晤的条件已全部具备。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会晤,终于在1989年5月16日举行。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从长期激烈敌对转而搞关系正常化,这段历史要不要清理?大论战要不要分清是非?今后的两国关系应如何定位?这些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全世界都在注视着面对这些难题的中苏最高级会晤。
邓小平举重若轻地把一大堆复杂问题处理得非常高明。在与戈尔巴乔夫会晤中,他高度概括地总结了几十年错综复杂的中苏关系史,指出主要问题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邓小平说,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我们也不相信自己全是对的。又说,历史账讲过了,就一风吹了。戈尔巴乔夫喜出望外,对此欣表赞同,双方同意就这样“结束过去”。关于如何“开辟未来”,邓小平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指出,结盟、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声明,中苏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国关系新的定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友好合作的国家关系。
继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中苏关系的这种根本性转变,是8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又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就。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面继承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会晤所确定的新型关系。经过两国领导人的努力,中俄关系现已发展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和互利合作等原则基础上的中俄新型关系,已成为冷战后大国关系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