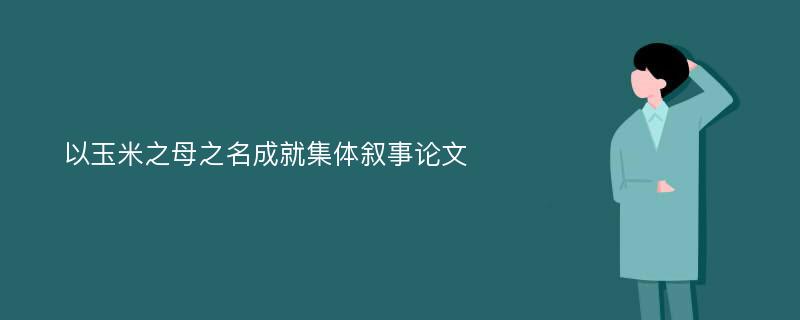
以玉米之母之名成就集体叙事
叶玮玮1,3,解苏亚2译,乔尼·亚当森3著
(1.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 2.河北大学,河北 保定 071002; 3.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英语学院,亚利桑那州 85281)
译者言: 本文是乌苏拉·海瑟、乔恩·克里斯蒂森、米歇尔·奈曼恩主编的《劳特利奇与环境人文》章节之一,指出人类纪时期生态批评呈现出的跨国、跨学科研究趋势,并为未来环境文化研究指明方向,本土世界主义思想是生态批评的重要向度。讲述环境故事的推想小说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对致力于解决生态危机的跨国环境人文组织的构建具有指示作用。种际正义、代际正义、族际正义、“国”际正义主题构成新时期以推想小说和电影为代表的环境叙事题材的四梁八柱。新时期的环境人文研究表现出明显的多元文化行动主义特征:将环境正义文化研究、生态文学批评、生态电影评述及相关美学理论研究等环境人文理论研究与系列促进食品正义、城乡正义等环境人文实践活动相结合。本文表达了乔尼·亚当森主持的美国国家人文中心在研项目“理想未来:世界、经典和环境人文实践”的中心思想:应重视以本土推想文学的观察工具作用;亚当森将本土世界主义和推想小说、电影作为一种“观察工具”,分析新时期生态批评在重视全球与地方、城市与荒野、自然与人工等分野的同时,应避免陷入一元论怪圈。在此基础上,食物正义研究为生态批评走向更跨学科、跨国界的环境人文实践提供了路径。通过十多年的组织和研究,环境人文主义者包括乔尼·亚当森和乌苏拉·海瑟在环境人文研究领域引入生态批评和相关美学理论研究方法,结合系列以促进食物正义、城乡环境正义的环境人文实践活动,从整体视角为生态批评走向环境人文提供了路径。
关键词: 推想小说;环境正义;食物正义;生态批评;环境人文
为学生揭示社会和环境危机的环境人文主义者均对推想小说和电影情有独钟(Perez-Pena)。作为首屈一指的小说家,《马德亚当》(2013)三部曲小说作者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尤善推想小说创作。推想小说在为气候变化等问题发声的同时,也为系列全球生态变革活动提供了可能,阿特伍德称之为“彻底变革”。阿特伍德还大胆设想了未来社会存在或正在通过基因改造而形成的“客观生物体”;无独有偶,其他推想作家也开始关注在人口密集、反乌托邦世界里探索未来世界的食品问题。哈里森的《创造空间!创造空间!》(Make room!Make room,1966)和基于此小说而改编的电影“超世纪谍杀案”(1973)就想象了未来四千万纽约市民生活在由代餐(Soylent)公司搭建的绿色晶片建筑物里,富人一如既往品尝山珍海味,穷人食不果腹的非正义现象。小说最后有个标志性的场景,扮演侦探的查尔顿·赫斯顿在调查公司腐败现象时发现一个恐怖事实:绿色晶片并非浮游生物制成,而是来自回收的人肉。保罗·巴奇加卢比(Paolo Bacigalupi)的推想小说《发条女孩》(The Windup Girl,2009)也是探索未来环境问题;小说中“卡路里公司”的代理商担心地球上搜到的种子会灭绝,于是开始通过基因改造现有种子的基因序列,以求控制世界粮食系统。可以说,在近五十年的推想小说中,食品话题将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黛安.格兰西(切罗基)、莱斯利·马蒙·西尔科(拉古娜)和纳巴·贝克尔等众多北美当代本土小说家的作品和最近的实验电影也展现出对资源获取、利用和基因改造工程等问题的担忧。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法律文书中,涉及此类问题的概念被统称为“粮食主权”,自1940年末以来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旨在保护“人民、家庭、国家和社区支配食物系统的能力”。(参见:Adamson, “Seeking the Corn Mother”,232-234)这些小说以世界性组织数十年如一日地维护世界公民人权及维护文化和粮食主权的活动及声明为背景,如《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UNDRIP)第 31 条:“维护、控制、保护和发展原住民人民的知识产权,包括尊重其“基因资源、种子、药物和动植物特性的传统认知”。(有关跨美洲原住民政治组织的历史,请参阅亚当森,“Todos Somos Indios”!)。
机械生产企业应该加强技术研究,提高机械设备在各个地区的适用性,妥善解决好国产机械设备性能、质量、稳定问题,确保农艺和农机有效适应。农机部门还要结合本地区水稻种植技术,做好育秧、插秧技术的管理研究,对于关键插秧技术要进行反复试验,确定最佳的技术路线和技术要求规范。向农民群众推广适用性和质量过硬的优质插秧机械,进一步完善插秧作业流程。
本章将格兰西、西尔科和贝克尔的作品中的“玉米之母”作为分析重点,探究在“彻底变革”时代,植物、种子和食物的创新适应策略所具备的特点。然而,这些小说和电影归类为历史小说而非推想小说,因为它被判定为“过去”。正如本土研究教授格蕾丝·狄龙(Grace Dillon,Anishinaabe 饰)在《云中漫步》(Walking the Clouds)一书序言中所言,从北美到新西兰的本土小说作家善于运用“时空思维”虚构故事,选取传统文化作为素材,将时间设定在现在或过去。这种“时空思维”是推想小说的一个分支,被称为“本地流派”(3)。本地流派作家把时间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像海洋分流最终汇聚在一起。”(3)。本土推想小说将“科幻”中“科学”视为“本土科学文学”而不是科幻小说或推想小说的焦点—现代或未来的技术(狄龙 7-8)。本土推想小说作家对推想小说作为流派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进化论和人类学”、“与殖民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的方式提出了质疑(狄龙2)。狄龙认为,19 世纪的推想小说可以直接反应帝国主义对“竞争、适应、种族和命运”的担忧(狄龙 2)。本土推想小说作为推想小说的分支关注“时空非线性思考”和直接面对这些帝国主义建构而“颠覆整齐的分类” (狄龙 3)。
我在新西兰做获奖演说时,我讲过“文学是另一种造屋”。写作就是造屋,第一个层面的造屋是使人们有个安居的地方,让心灵有一个安顿的地方,作品就是心灵的屋子;第二个层面的造屋是指每个人都向往自由,自由在哪里能实现?是在文学的这个屋子里实现,因为这个屋子是我的,我可以在这个地方自由地放飞我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你想得到的自由,写作可以满足你。
从物质生态批评角度不难看出,玛丽托尔父亲的遗言表明玉米之母归根结底是一种复杂的固有关联。父亲远离他的小木屋和欣欣向荣的农场,他担心若不能重新获得种子和充足的粮食,他会担心家人的未来。他喊道:“玉米!我们的食物,没有你我们活不下去。你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普韦布洛作家西蒙·奥特茲(Simon Ortiz)提醒他的读者,“土地/玉米”是神圣的,因为当人们食用这种植物时,它能使人体重新获得动力;当人类死亡时,他们的身体重回土壤中,在那里滋养生长的植物[3]。从科学角度,玉米是少数几种能产生四种碳原子化合物的耐旱植物之一,而不是大多数其他植物产生的三种碳原子(Pollan 21)。玉米比其他需要碳的植物吸收更多的同位素 C13和C4在食用了数百年玉米的中美洲人的肌肉和头发中大量存在。如今,大多数现代人也以玉米加工食品和加了植物糖浆形式的玉米制品为主食,就像中美洲种族的人一样,现代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玉米人”。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关于将大多数北美人称为“玉米漫步者”的论断不无道理。(Pollan 23)
根据将波波尔乌翻译成西班牙语的奎奇玛雅文士语言,我将这些变革主体称为“观察工具”,诸如波波尔乌中希腊诸神,均是“超越现实的具有前瞻性和预示性的系统整合”(美国印第安文学 145;波波尔乌 32,71)。从“形体或名字相近的人或动物”角度,这些观察工具的表现的“像人一样,虽不遵世俗陈规,却在一定的宇宙时空布局中以非比寻常的整体性状态存在”(亚当森Why Bears45 n11)。在当代小说中,观察工具存续在过去、现在、未来时空中,自然地评述现实或远古故事遗产或小说新体裁,以便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预测未来。简而言之,它们是人类生存发展中临机应变的一种思维工具,使人类能够生机勃发地存活 (亚当森,Why Bears 36;波波尔乌 236 )。基于对爱德华多·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和玛丽索尔·德·拉·卡德纳作品的分析,我研究在当代本土诗歌、小说和电影中被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称之为“人们”的变革实体,探究这些想象实体如何使地球游刃于不同地缘和生物圈间复杂的掠夺和暴力关系间。这些“人们”提供了“多维视角”;而非“唯一视角”,或者说是“同一”世界(亚当森, Why Bears和Source)。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在2015 年主持会议“盖娅的千种名字”,而关于这些实体的研究正是该次会议的主题。唐娜·哈拉维解释将他们命名“整合物”的原因归结为:“整合物”呈现错综复杂的时间和空间关系,或“实体的集合,其中包括超人类、其他物种、非人类”(哈拉韦160)。
针对数学易错题、典型习题,通过微课程的整合,分门别类整理,或者讲解易错的地方,强调错误点,方便学生进行纠错,或者从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为学生创造一个最近发展区,构建一类问题解决的策略.对于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通过先看具体的解答步骤,或多次重复观看,依据微视频的帮助,掌握解题技能,形成策略性知识,发展数学思维,培养学习兴趣.
阿里低下头,仿佛是想了一想,说:“哦。”然后怏怏地跟着罗爹爹朝外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望望,自语道:“姆妈还在睡。”
“后本土启示录”的概念也源于宇宙学观点;该观点认为地球母亲是一种“集合实体”,她会保留对大规模暴力行为的记忆。2010 年在玻利维亚科查班巴举行的世界人民气候变化会议发表的《地球母亲权利世界宣言》(UDRME)再次重申此观点,该宣言中将原住民民族、国家和组织视为原住民祖先的“宇宙远景”,认为地球是一个“与[所有人]都有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关系的生物体”(第2条)。参会人员指责对地球母亲的侵害行为,说明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我们”自身的攻击,这里的“我们”是指所有人类群体(不局限于原住民)和其他“身体”,包括“土壤、空气、森林、河流和湖泊”。《自然》(Nature)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气候科学家西蒙·刘易斯和马克·A·马斯林提出了人类对其他人类和其他物种侵害的科学证据,表明关于地球留有侵害“记忆”的原住民宇宙论可能不仅仅是浪漫的神话。他们预测公元 1610 年将是北极冰核大气二氧化碳水平历经数年降至冰点的日期。他们推断地球环境的这种变化与欧洲人上世纪美洲有5000多万原住民死亡有关,由于欧洲入侵,“他们携带的疾病,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奴役和饥荒”,导致了大量的美洲原住民死亡。(刘易斯和马斯林 175)。截止至17世纪中期,美国北部和南部大陆原住民居民大量减少,大约只余六百万幸存者,这就意味着农业产出大幅度下降,其他人类活动诸如焚烧等均影响着大气的二氧化碳含量。
刘易斯和马斯林的研究表明,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行为或许真的会被地球母亲以某种形式留下印记。尽管哈拉韦没有使用这一新词,但“后本土启示录”这一说法在“种质、基因组,断层以及部分有机体和去角质植物、动物和人的移置和重组过程”的发展史中均有迹可循(哈拉韦 162)。哈拉维和她的合作者安娜·青(Anna Tsing)提出了全新世过渡时期的另一个新词“种植新世”,这一词也暗示了由殖民统治、种植园制度和奴隶贸易的兴起而导致的大量死伤的地球记忆(Haraway 162N5)。以青(Tsing)的话来讲,全新世是指人类和植物以多种方式共同进化的漫长时代,期间在包括农业在内的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创新。青(Tsing)将这种生态灾难后继续保持丰富的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的某一时空区域定义为“残遗种保护区”。愈万年来,人类致力于创新、杂交、开发数千种新主食作物种子,采集和选择水果和蔬菜的特定特性。随着向“种植新世”的过渡,“代表着全球资本积累和利润的物质符号产生”(哈拉韦162N5) 青(Tsing)补充说明了边界或“临界点”概念,跨越这一界限,地球保护所有物种并为之提供相应的生存条件(有人类或无人类)的能力便会受到威胁(哈拉威 160;青)。这有助于解释《地球母亲世界权利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Mother Earth)生命的所有“肉身”,包括“帕卡妈妈”,这一拉丁美洲本土世界主义论点中的“地球母亲”,均应享有与人类平等的权利。正如人类有“不被杀害的权利”一样,根据《人权宣言》,地球生物和其他物种群体也应通过时间和空间享有“再生……生物承载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权利。(《地球母亲世界权利宣言》)
爱德华的研究初衷并非是“完善人类学”。他带着“目标客户迫切需要的植物清单”,这些客户是“富有的集合者”(西尔科 129)。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他将种子和植物材料从造物者那里窃来。这种行为揭示了殖民、帝国主义、去地方化的农民和被称为生物多样性缺失现象之间的联系,这种概念称之为“生物剽窃现象”(穆希塔和汤普森)。他们并非是借鉴了瓦维洛夫的工作经验,相反,他们所推崇的是美国良种玉米公司(Hi-Bred Corn)创始人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经历。19世纪晚期,华莱士和其他北美玉米育种家收集了数百种玉米品种,将培育的种子在整个中美洲和北美洲大量培育。他们向客户承诺无限的产量,却只选择“原始品种”中的少数作为他们的研究重点。到了20世纪,他们促进精选的“先进或精英”品种的发展,并将其作为私有财产获得专利,赢取利润。华莱士自豪地提出了一种理论,即白人在培育杂交玉米品种上做的比原住民人培育玉米种子要多,而且速度更快。然而,后来当他意识到单一种植优秀的专利品种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流失,玉米品种会失去交叉授粉和恢复活力的机会时,他们开始提出相关警示[5]。1956年,华莱士预测生态单一性灾难即将来临,并警告研究人员要更仔细地考虑到增加产量和利润关系。弗塞尔提出,由于作物“易受一种新的南玉米叶枯病突变株的影响”,这场灾难将在1970年爆发,届时商业杂交玉米的基因单一性将导致美国四分之一的作物损失。(Fussell 93)。
一、集腋成裘:玉米之母
据分子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的观点,玉米是指玉蜀黍属类的农作物,但对于北美的原住民来说,玉米源于“墨西哥类蜀黍”类的一种杂草。在阿兹特克语中,这个词理解为“玉米之母”。如今,这种草植在墨西哥城附近玉米田旁仍然较为常见,当地农民认为它通过杂交授粉方式可以使得现代种子生长的更为茂盛(Nabhan 143,149)。野生品种和培育品种之间的交叉授粉而产生的种子,生动地展示了青对“残遗种重建”能力的描述,这些“残遗种”使某些特征经过巨大的空间和时间跨度获得恢复和再生。黛安·格兰西《推熊》(Pushing the bear,1996)展现了原住民切罗基人在整个全新世期间文化和农业生态方面共同进步取得的经验、创造力和劳动成果。切罗基人及中美洲和北美洲的其他部落群体,将数千种古老的草培育成玉米品种,每一种都以特定的生态位命名:瓦哈卡绿、霍皮蓝、帕尼黑鹰、切罗基白鹰、易洛魁白。这些玉米种子沿着从墨西哥到大湖的古老路线一路被分享、交易,在欧洲人与美洲原住民会面后,玉米种植技术很快在世界各地推广开来(亚当森,Seeking; Kleindienst 228-29)。然而,在“后本土的启示录”中,由于以玉米为主食的人种的消失,很多玉米品种也随之消失。如今,“种子培育者”隐藏的古老品种被重新发现和培育,以便它们继续与不断进化的害虫和不断变化的天气条件改变着特性。
我们可以从以上所述中总结出“玉米之母”的由来:玉米这种被人类培育成世界上最重要的食物的草,一种“肉身”,蕴含着多元宇宙、民族植物学、生物技术、生态、社会、文化和烹饪等与人类发展息息相关的含义。
根据狄龙的观点,“本土未来主义”决定“受殖民影响”的群体如何适应“后原住民时代灾难”的角色 (狄龙10)。正如我在美国印第安文学、环境正义思想和生态批评中解释的那样,原住民长期认为自己生活在后殖民“启示录”中,历经数百年抗争运动,为环境正义概念正了名。据说1980 年代的原住民起义和奴隶起义运动可追溯至15 世纪后期各大洲的奴隶抗争活动。(47-53)。狄龙认为,在本土小说和电影中,英雄人物常被赋予远古神特征,从而代表所有“相互交叉联系的‘身体’”(狄龙7)。在北美本土小说中,“身体”通常是生活在现代社会具有变革意义的人类、熊、鲸鱼、海豚或诡计者。这些“身体”——熊、蛇、土狼、乌鸦、和其他超越人类的客体,频繁出现在北美原住民口口相传的传统文学作品中,阐明了一个“没有明确的界限划分众生”的世界观(亚当森 ,《Why Bears》31)。
透水砖对小雨和中雨有一定的下渗效果,但如果是短历时暴雨,透水砖则来不及下渗。我国北方缺水城市年降水的绝大部分在汛期,一半以上的降水是大雨或者暴雨。所以透水砖有一定效果,但只能起辅助作用。另外,受人为活动等影响,透水砖的透水空隙随着时间的增加会出现堵塞,失去透水性能。
格兰西阐释了原住民与他们所培育的种子间悬于一线的复杂关系,并解释了为什么农业生态知识在《联合国原住民人民权利宣言》(UNDRIP) 和 《地球母亲权利世界宣言》(UDRME) 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推熊》讲述了切罗基人从19世纪30年代被迫离开农场,前往俄克拉荷马州的途中痛失亲人和玉米之种的血泪史。这部小说以 19 世纪为背景,但不完全是历史小说,而是推想小说:对于主人公年轻母亲玛丽托尔来说,这是一部“后本土天启录”,她被迫面对变幻莫测的未来,并要求她学会适应和改变自已以存活并适应所有改变(狄龙 10)在这一过程中,玛丽托尔时刻铭记着自己出生的地方,并将口头传统中的故事称为“观察工具”,它能让我们了解这个角色对周围世界的影响:“玉米杆是我们的源起……玉米穗在空气中授粉”(狄龙 4)。将生物符号学和多物种民族志引入环境人文学科,有助于分析“雄穗”或玉米穗作为“一体”在空气中“授粉”,揭示植物符号学能力和通过化学梯度或光的强度不断感知和解释其环境多元世界的过程。如此,我们可以反观他们与帕卡妈妈(Pachamama)的关系:美洲许多原住民群体将“光源”称之为帕卡妈妈;玉米作为一种“改变地球”的生命形式,“种子扩散过程早在人类开始进行农业生产前的数百万年就已经在默默进行着了”。(哈拉韦159)。玛丽托尔把玉米想象成古老有知觉的生物,玉米作为“母体”唤起了几千年来创造自然历史的过程,这种自然历史造就了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将碳转化为糖,将水转化为氧。在与人类农业生态培育活动的共同演变中,“墨西哥类蜀黍”类的一种杂草终于成为了一种“整合物”,即玉米之母。正如黛博拉·伯德·罗斯所言,关于“玉米穗”和“玉米雄穗在空气中授粉”的论述均是在呼吁环境人文主义者更多地关注“将我们与多个物种群落联系的素来存在的内在关联”(哈拉韦87)。
二、转折点:沙丘花园
西尔科的《沙丘花园》(1999)和《推熊》一样,也是以19世纪为背景的历史小说。然而,主人公英迪戈(Indigo)是一个生活在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边界索诺兰沙漠的年轻原住民女孩,被强制送到美国白人宗教文化控制的白人学校接受教育。对她来说,这是“后本土启示”(狄龙 10)。这使小说从纯粹的历史性小说变成了推想小说,因为它开始探讨类似于哈拉韦提出的关于“种植纪”问题:“当细微变化逐渐产生重大影响,生物文化、生物技术、生物政治、历史人物(不仅限于人类)便开始与其他物种组合和其他生物/非生物力量产生关联或结合?”(狄龙159)。西尔科通过对生物多样性和农业方面进行的另辟蹊径的研究塑造了两个人物,使之为哈拉韦强调范畴化“世界”和“转折点”问题提供了思路。主人公英迪戈的祖母教她用北美西南部的北美原住民部落中很常见的传统雨水灌溉花园里种植的玉米、豆类和南瓜的等作物群,而她的养父爱德华·帕尔默被塑造为一个与华盛顿的美国植物工业局和英国的邱植物园有秘密往来的庄园主和植物学家形象。他在“经济植物学”的实践中探索兰花、香茅和各种玉米的种植方法;而“经济植物学”这一术语出现在 19 世纪,当时欧洲人和美国人正在收集他们在殖民地遇到的原住民民族和少数民族认为有价值的植物(Mushita and Thompson 27)。
英迪戈在当地政府被抓后,进入加利福尼亚的一所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由爱德华和他的妻子收养。在英国,她遇到了养母的英国亲戚布朗温阿姨(Aunt Bronwyn)。布朗温阿姨在她的“厨房菜园”里种了玉米、大豆、南瓜和西红柿。当英迪戈看到这些她熟识的食物时,她开始明白“种子必然是所有旅行者中最伟大的”[4]。以加里·保罗·纳伯汉的“我们的食物从何而来”和基于俄罗斯植物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Nikolay Vavilov, 1897-1943)这一现代作物育种的奠基人之一周游世界寻找“人类养活自己的新种子和新方法”(西尔科9)的行为为背景,英迪戈找到了与自身经历相对应的故事。就像瓦维洛夫一样,英迪戈认真遵循她祖母的建议,尽可能多的将种子收集、保存和“带回家”然后种植并进行试验,观察哪种种子能在新的条件和天气下生长(西尔科 83)。祖母建议英迪戈遵循时间实验的农业生态创新方法,以自由交换、杂交和培育为基础,增加植物生物多样性。
在这一章中,我将重点介绍格兰西、西尔科和贝克尔的推想小说和电影,这些小说和电影丰富了人们对变革主体特征或“整合物”特征的理解。以玉米之母为例,我将探讨原住民是如何运用“观察工具”理解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残遗种保护区关系,以及为什么“世界主义”本质上是在呼吁整合物本源“权利”和其他对维持生命至关重要的多样性集合,保证所有“肉身”——原住民人和非原住民、人类和非人类的食物主权问题(另见亚当森,“Seeking”and “‘Todos Somos Indios!’”)。这种对北美本土小说家和电影制片人紧紧围绕在“玉米之母”的分析也将挑战如下观点:生物多样性发展了自然、纯净、平衡的关系,传统原住民主张“自然”和“纯净”的和谐共生自然文化价值观与转基因和生物研究活动产生了对立和摩擦。以下论述将具体论证本土思想反对“转基因生物(GMOs)并非只是基于平衡自然的概念,而是基于诸如“玉米之母”之类的“整合物”实体所包含的复杂组合关系。随后本文简要论述环境人文的研究方法,包括生物符合学、多物种民族志、和物质生态批评,为本土科学传统和景观想象前瞻研究提供借鉴。
“身体”可以是指动物肉身,亦可以指代人类。通常情况下,这些动物肉身会表现出神奇的能力和特质,例如,以熊冬眠的能力或蛇蜕皮的能力就象征着“生存和死亡”(参见Why Bears,31 - 32)。从克洛德·列维·桑特拉斯到维克多·特纳,从唐娜·哈拉维尔到爱德华多·维韦洛斯·德卡斯特罗,象征人类学家和文化理论家早已确立,“变革主体”代表着“有限的特殊统一: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但又兼而有之”[1]99。他们被单列出来,并非因为他们“容易捕食”或者是说他们“容易禁止”,而是因为他们“善于(激发我们的)思考”(巴布科克 167;亚当森,Why Bears)。唐娜·哈拉韦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她认为之所以说这些变革主体是“整合个体”,是因为像狗和其他生物体具有阈限性质,可与人类“共处”[2]160。
当英迪戈带着她收集的种子从欧洲回到了祖母在索诺兰沙漠的花园。在种满所有种子的花园中央长出了耐旱的“母玉米”。( 西尔科 166)。正如阿特伍德和其他人的想法一样,推想小说常常可以从当前的技术和社会结构到(目前)不存在的形式进行某种程度的推断。在《沙丘花园》里,西尔科运用整合物理念,将玉米粒和其他种子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植物学“当前技术”,来深入研究各个时代之间的变化,并寻求对遗传稳定的进化过程和植物发育过程以及现代农作物生长耐旱所需的空间、时间和规模上有更深入理解。和哈拉韦和青一样,英迪戈的花园及她对新种子“技术”的实验都是在探索是否有可能“重建避难所”(哈拉韦160)。曾经有超过三千种植物被人类用作食物,但今天只有一百五十种被种植,其中只有少数植物,其中还包括占据世界上一半的食物的转基因玉米、大米和大豆等。自19世纪末以来,没有一种新的非转基因食品达到了稳定状态。英迪戈和瓦维洛夫(Vavilov)的故事均呼吁现代读者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食物来自何方,理解当代遗传学家和植物培育家回归到收集现代食物的原生种子植的重要性,譬如古老的蜀黍(母玉米)和现代玉米品种我为例;他们在应对生态变化诸如干旱和疾病方面较之当代的玉米品种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格雷斯·狄龙认为,美国原住民的“推想小说”正在更新、恢复和扩展“第一民族的声音和传统”(狄龙2)。《沙丘花园》加深了人们对《联合国难民救济计划》第5条要求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护土地基地的原因的理解,在这些地方,原住民种植者和农民已经种植了历经百年、具有多样性基因品质的种子,掌握着各种“以适应不断环境的技术”(Nabhan 198)。
三、生物技术伦理质询:第六世界
在《第六世界》(2011年),导演纳瓦霍和编剧纳巴·贝克尔首次推出了一部15分钟的科幻电影,在这部电影中,玉米经过基因改造,可以为宇航员在前往火星时呼吸提供氧气。由珍妮达.贝纳利(纳瓦霍)扮演的主角塔兹巴·雷德豪斯是一名纳瓦霍宇航员,在纳瓦霍民族和一家未来世界公司的共同资助下执行一项任务。雷德豪斯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她关于玉米的实验,并梦想着一片传统的玉米会枯萎死亡。贝克尔指出,影片的创意受到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在《杂食者的困境》(the Omnivore 's Dilemma)一书中的观点启发,认为单一的转基因农业企业会给全球粮食系统(Estrada)的未来带来可怕的影响。塔兹巴的梦想引发了人们对社区粮食主权风险的质疑,这些风险来自于公司专利合同要求在农场上单播获得专利的玉米,以使用正在退化生态系统并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合成肥料和农药化学品。
正如塔兹巴的梦想所预示的那样,当为飞船的氧气系统提供动力的转基因玉米无法茁壮成长时,登陆火星的任务几乎就失败了。然而,在起飞前,指挥官巴赫将军送给雷德豪斯黄色和白色这两种传统的纳瓦霍玉米。利用这两种传统的种子品种,她与由路易斯阿尔达纳(Luis Aldana)饰演的科学家同事史密斯博士(Dr.Smith)一道拯救了飞船的关键系统。传统玉米茁壮成长,氧气系统重新启动,红房子能够进入“冬眠”,度过余下的旅程。考虑到这部电影是以一艘宇宙飞船为背景,且这次任务是由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共同资助的,贝克尔的电影并未简单地反对科技。影片中,宇航员小心翼翼地将传统玉米和转基因玉米用玻璃隔开:玻璃可以避免传统玉米和转基因玉米之间的遗传污染。究其原因,玉米是一种风媒传粉植物,转基因玉米的遗传信息可能通过开放授粉传播,并污染传统品种的自然生存能力。目前还不清楚转基因生物是否真的会导致玉米价值性状(McAfee)的丧失。大多数倡导粮食主权的原住民人“反对将基因工程作为农业战略,不是因为它破坏了理想的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憧憬,以及传统作物土地种族纯净;更由于它带来了生物有机体可以获得专利的威胁,并最终导致种子作物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在冬眠舱里,塔兹巴梦见自己成为了作为纳瓦霍转型实体的变化莫测的玉米之母;她穿着传统的衣服,脸上涂着红色的条纹在唱歌。贝克尔在接受加布里埃尔·埃斯特拉达(Gabriel Estrada)采访时指出,她想把塔兹巴塑造成一个勇士形象,并鼓励她的观众抱有自己独立立场(埃斯特拉达)。作为“整合物”,影片末尾的女性将观众带回对围绕文化和民族主义主权世界主义组织的漫长历史的考量,包括原住民团体和那些联合国在当地设有原住民问题论坛的国家,还包括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关注粮食主权的各种非政府组织(NGO)合作的国家。这些组织代表与小规模的原住民农民、植物育种家、民族植物学家、微生物学家、进步的食品决策者和基因组科学家联合,共同致力于保护食品主权和种子多样性(Adamson,Seeking)。
影片最后一幕,塔兹巴在火星上安全醒来,贝克尔在赤色的火星景观中成功地种植了绿色的纳瓦霍玉米。贝克尔在接受埃斯特拉达采访时说,在纳瓦霍人故事中,“纳瓦霍人和早期先知找到了穿越于几个世界的路,他们穿梭在不同世界的天空,并最终进入下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如果说当今的世界是第五世界,那么影片主人公在火星上的觉醒便预示着进入了想象中的第六世界。正如西尔科小说中所描述的,以“重建遗种避难所”和保持种子多样性来适应生态恢复力是可能的。
第一,关于明朝政府开关互市的历史记忆和真实记录。叙事开篇关于明朝在东北设清原马市、抚顺关马市,马市每个月定期开放两次,以及朝廷征收边关纳税等内容的讲述,是对当时明朝政府开关互市的最生动记录和描述。
环境人文学者和公众开始重视推想小说的主体,不仅由于推向小说关注世界末日主题,而由于它以场景化想象为人类未来注入了可能性和一线生机(Pérez-Peña)。北美本土小说和电影应被解读为一种推想艺术,饱含生物信息、民族植物学和多物种等元素。这些元素激发学生去想象、叙述、设想甚至适应和改造这些推想作家和电影制作者们打造的后天启世界。原住民社区及非原住民社区共同在这个世界中生存、适应并创新,加速完成“彻底变革”。
参考文献:
[1]Turner, V.Betwixt and Between: The Liminal Period in Rites de Passage.The Forest of Symbols:Aspects of Ndembu Ritual[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99.
[2]Haraway,D.Anthropocene, Capitalocene, Plantationocene,Chthulucene: Making Kin[J].Environmental Humanities,2015:159-165.
[3]Ortiz, S.Fight Back: For the Sake of the People, For the Sake of the Land[M].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2:285.
[4] Silko, L.M.Gardens in the Dunes[M].Simon and Schuster,1999:240,291.
[5] Fussell, B.The Story of Corn[M].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92:86.
Collected Things with Names Like Mother Corn
Translator by YE Wei-wei1,3, XIE Su-ya2, Authored by Joni Adamson3
(1.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200092 ,China; 2.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3.English Departmen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Tempe 85281, America)
Translator note: Collected Things with Names Like Mother Corn isone of thebook chapters of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edited by Ursula K.Heise, Jon Christensen and Michelle Niemann.Adamson argues that ecocriticismhas taken a trans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turn in the age of Anthropocene,especially as it takes seriously an emerging indigenous cosmopoliticsthat is influencing understandings of the indigenous literatures.Traditional indigenous oral narratives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 can be considered speculative fiction which addresses historical memory andstories aboutenvironmental problems.Indigenous speculative fiction and filmare concerned withtheissues of multispecies justice,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multi-national justice and international justice,which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four pillars of this genre of environmental narratives.This article directs our attention to this complex question which will be elaborated in detail in Joni Adamson’s forthcoming book titled “Desirable Futures:Cosmovisions, Climate, and New Constellations of Practice in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which is being supported by funding by the 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 in North Carolina.In this book Adamson will explore how indigenous cosmovisions and speculative fictions and film acts as a kind of “seeing instrument” into complex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that cannot be reduced to dualisms: global and local, or city and wilderness.Instead,the studies of food justicewhich are based onthe indigenous cosmovisions Adamson analyzes are providing a path for ecocriticism to move towards a more interdisciplinary and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practice.Through more than a decade of organizing and research by environmental humanists, including Joni Adamson and Ursula K.Heise, we can safely say that there is an emerging synergy among the fields of environmental cultural studies, ecocriticism, and related aesthetic theory studies, with a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humanistic studies which intends to promote food justice, and urban and rural justice.
Key words: speculative fiction;environmental justice;food justice, ecocriticism;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395(2019)04-0068-07
收稿日期: 2019-02-06
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201706260225)。
译者简介: 叶玮玮(1989-),女,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英语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专业英语语言文学,方向比较文学,生态批评,环境人文研究。
标签:推想小说论文; 环境正义论文; 食物正义论文; 生态批评论文; 环境人文论文;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英语学院论文; 河北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