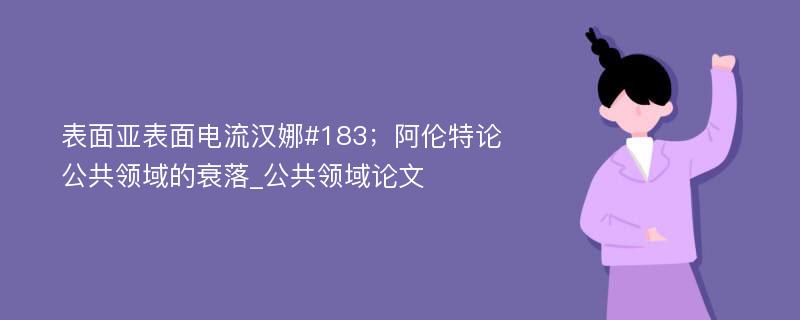
浮上水面的潜流——汉娜#183;阿伦特论公共领域的衰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伦论文,潜流论文,水面论文,领域论文,汉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欧洲的知识分子都亲身经历了欧洲文明的支离破碎,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欧洲仿佛脱轨的火车,成了茨威格无法理解的“昨日的世界”。犹太血统的思想家更直接处在时代风暴的中心,他们在一夜之间无家无国、被迫流亡,无论走到哪里,死亡集中营都象一个可怕的梦魇,向他们拷问着生存的意义和责任。胡塞尔、雅斯贝斯(其妻是犹太人)、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这段悲怆的历史做了哲学的反思。这种历史命运直接影响了汉娜·阿伦特一生思想的起点和方向。她也许是第一个从政治哲学上探索极权主义起源的人,她通过对人类存在条件和现代人类境况的分析,深刻地揭示出极权主义政治的根源在于现代性危机——公共领域的衰落。
汉娜·阿伦特1906年出生在德国一个同化了犹太人家庭,后以德国式的漫游先后师从于三位当代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胡塞尔和雅斯贝斯。跟随雅斯贝斯做完博士论文,纳粹主义的崛起和反犹主义的甚嚣尘上迫使她从象牙塔走向积极的政治生活,并开始思考德国传统和犹太传统之间始终存在的紧张关系,以及她自己同这两种传统的关系,面对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危机苦苦追问“我是谁”?1933年她为躲避纳粹的迫害逃到巴黎,三十年代活跃于反纳粹抵抗运动和犹太人与政治流亡者团体,做了大量营救工作。1940年后她一直生活在美国,战后《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奠定了她作为国际知名学者和思想家的声誉。在混乱空虚的六七十年代,阿伦特坚持不懈地反思现代政治文化,著有《人类境况》、《过去与未来之间》、《黑暗时代的人》、《论革命》、《论暴力》、《共和国的危机》等著作。1975年,阿伦特在写作《精神的生命》时遽然谢世,此书是一本哲学上的三位一体——论思想、意志和判断——是她毕生哲学观的总结。
今年4月23日, 二战期间希特勒集中营的幸存者在波兰最大的集中营旧址奥斯维辛举行了“幸存者大游行”,纪念被纳粹屠杀的600 万犹太人。在人们的心灵和死难者一起哭泣的时候,人们常常会问:为什么犹太人单单被挑选出来作为极权主义发动的借口和牺牲品?为什么他们在被大批赶往集中营时绝少反抗?
在《极权主义起源》中,阿伦特分析了犹太人——这一没有政治共同体而漂泊无根的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生活在他国,犹太人努力使自己同化,但他们一直不被允许进入除商业以外的其它领域,因而商业是他们唯一的同化方式。在民族国家发展的早期,由于国际间金融借贷的需求,大量犹太人以金融掮客的身份在各国政府间发挥影响力,地位迅速上升。但作为整体,犹太人从未培养起政治意识与参与政治事务的能力,结果形成了对政治现实漠不关心和被动反应的习惯。他们要么成为新贵,要么成为贱民,实际上始终处在政治社会之外。随着民族国家的衰落和帝国主义的扩张,犹太人失去了商业上的影响力,分化成一群有钱而无权的个人。拥有财富而无政治行动能力,这是他们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成为仇恨对象的主要原因。同时,在长期隔离于共同世界的状态下,犹太人开始把犹太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思考为自然天性、种族起源,强化了上帝特选的意识。这种自我解释造成一种更加复杂的隔离状态,产生出反犹主义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反犹分子关于种族差异的宣传与犹太历史著作的解释并无不同。因而,二十世纪的政治危机将犹太人驱赶到各种政治风暴的中心并非偶然,犹太人由于自愿隔离于公共世界和缺乏政治行动能力,对自己的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阿伦特的分析激起了她同胞的愤怒,同时也引起他们的深思。
与一般看法不同,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不是专制主义的现代表演或高科技翻版,它与历史上任何专制或暴政不同。专制取消政治现实的自由,但不关心臣民之间非政治的共同联系,而极权主义彻底摧毁任何自由的空间,人们不再有任何行动的能力、形成信念的能力;极权主义从一种虚构的意识形态出发,所有的行为都服从无休止的运动的逻辑,而普通的暴君从未发疯到不顾一切有限的局部利益——经济的、民族的、个人的、军事的——只追求一种无限遥远的将来的虚构目标。这一前所未见的政治体制,能在二十世纪中叶产生并发展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其必要前提是资本主义极端扩张造成的社会政治环境和道德心理基础。
阿伦特首先分析了以经济利益为主旨的扩张运动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破坏。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造成大量的富余资本,破产的贵族、农民和失业的工人等等。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和暴民结合起来向海外殖民地扩张,国家充当了扩张运动的保护人,结果一方面破坏了有一定疆域和宪政结构的现代“民族国家”,摧毁了人权与法治的政治传统,从而一切驱逐、杀戮都成了可能的;另一方面,毁掉了国家间的道义与和平,造成强权及公理、经济利益至上观念。“在帝国主义时代,商人成了政治人,并被承认为政治家;而政治家只有在使用成功的商人语言和‘从全世界角度来思考’时,才会受到认真注意;这时,私人的实践和手段才逐渐转变成为执行公共事务的规则和原则。”(注: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起源》,林骧华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第217 页。)
极权主义的充分展开还有赖于阶级社会崩溃后出现的大众。资本主义无休止的扩张剥夺了个人用于生活需要和确定身份的私产,并把私产转化为无限流动的资产,造成了无阶级无组织的大众。大众和暴民不同,暴民还多少分享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和价值标准,虽然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而大众是完全失去一切阶级联系,纯粹由原子化的个人组成的集合。当代劳动的社会化产生了一大群自感孤独、多余、并跟生活世界日渐疏离的大众。他们缺少正常交往、不关心政治、拼命追求物质满足,成为受消费社会严密组织的机器。因为失去了令生活有意义的共同世界,他们既不能反思事物、也不能反思自身,全无经验能力和思考能力。孤独、恐惧、绝望、无力,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正是极权主义赖以形成的群众心理基础。极权主义自称能解答人类历史意义的意识形态和它“退回到部落社会的运动”(波普语),最终能吸引大众,使他们得到一种追求有意义目标的归属感和最低限度的尊严。
阿伦特认为,经济利益至上的意识形态对于极权主义的发生起了决定作用。她和麦金太尔一样认为,近现代生活的显著特征是生产走出家庭,为非人格的资本服务,政治充当保护经济的手段。(注: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第1版,第286页。)这种变化既破坏了平等自治的政治传统、 破坏了政治之公共领域,又造成个人行动能力和自由的丧失。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一体化,靠的就是不断增长的技术生产力和不断扩大的对自由的剥夺。霍克海默一语中的:“政治不仅成了一种生意,而且生意已经全盘成为政治。”(注:《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24页。)可是我们知道, 政治蜕变为经济利益的工具是近代才发生的事,在西方最早的政治生活——城邦生活中,情形完全相反:那里经济活动被严格限制在家务劳动的私人领域,以保证在城邦之公共领域中,公民能平等对话,共同参与政治事务,在行动中实现自由。自诩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明在近代深刻背离了它的起源,突出表现就是:私人领域的地位日益上升,取代和吞噬了公共领域。阿伦特主张,公共领域是行动,从而自由可能的条件,公共领域的衰落正是现代政治文化的根本危机。
在《人类境况》中,阿伦特以深厚的古典语言文化背景,考察了在古希腊“劳动”和“私人领域”、“行动”和“公共领域”的联系。不同意阿伦特观点的人会提出反对理由,说城邦只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个特例,即使在当时的古希腊社会也属偶然,因而城邦所代表的公共领域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可是阿伦特的思想并不是对古代的浪漫追想,或把现代简单理解为传统的倒退。她分析了“活动”这一人类存在条件,从存在论的角度说明,公共领域对人的生存是根本性的,正是人类错误的自我理解,城邦才成了偶然出现的、遥不可及的高峰。
阿伦特把人类活动区分为三种:劳动、工作和行动。劳动是满足生命必需品的手段和服从于生物本能的活动,劳动的“人类境况”是生命本身。工作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物的世界,人类只有在生生不息的自然之上建立自己“客观的”世界,才能把自己与自然分开,并把后者看成“客观的”,这样人类的自我意识才开始产生。“没有人和自然之间的一个世界,就只有永恒的运动,没有客观性”(注: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 第137页。), 所以工作的“人类境况”就是世界性(worldliness)。持存而稳固的人造物为人类提供了可依持的家园, 其中,艺术品的创制,国家和法律的奠基更是如此。与之相反,劳动留不下任何东西,仅服从于生命物质循环的同一、重复过程,它在现代社会变为生产——消费无限循环的机能。
行动是唯一无须物的中介而直接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活动,是人类最富自我意识的活动。首先,行动凸显着人的多样性。“多样性是人类境况,因为我们之所以是同样的,即都是人,在于没有人和曾经活过、正活着和将要活的任何其他人相同。”(注: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第8页。)行动意味着在人类“多样性”的条件下,通过他人之在场来揭示“我是谁?”我们不可能在人类学或哲学上定义“我是谁?”因为任何定义都是对人的性质、性格的描述,即普遍性的描述。一个人是“谁”只能靠他的言说和行动,在主体间的交互关系中,通过他人的看和听得到承认。人们可以不劳动不工作而照样活着,如寄生者,但失去了言说和行动的条件——公共领域——就不再是人,因为个人认同和自我存在是在公共领域中,通过与他人的持续对话和行动确立的。被迫失去了共同世界的人的存在,在文明当中也被抛回到原始天性和纯粹差异中,象动物属于某一种群一样属于人类,这就是“犹太人”这个称呼所暗示的命运。
“去行动”,在古希腊语言中,就是“去开始”、“去创新”,意味着对机械因果性的打破和对统计学规律的挑战,意味着人的自由。这里,公共领域是行动实现的场所和条件,行动的参与力量又保护了公共领域,由此,人的个性才能形成,自由才能实现。行动不仅揭示着人的多样性和唯一性,而且只有在行动赖以确立和保持的公共领域中,人类才能保有可见世界的真实感。他人在场不仅是自我存在的条件,而且验证着我们关于世界的实在知识。如果我们不同其他人接触,封闭于个人特殊的感觉体验之中而没有共同感觉(commonsense), 我们就不仅失去了对共同世界的经验,甚至不能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因而,“被剥夺了在一个共同世界的表现以及这个共同世界产生作用的行动,这个个体就失去了全部意义。”(注:《极权主义起源》,第425页。)
在阿伦特看来,劳动和行动的对立有根本的意义。古希腊人把劳动归入家务这样一个完全私人的领域,由奴隶担任,以便自由人从本能的必需性活动中摆脱出来而自由地参与城邦事务。实际上,古代的奴隶制并非处于廉价劳动和利益剥削的目的,毋宁是试图把劳动排除到人的生活之外。这种对劳动根深蒂固的轻蔑源于古希腊人努力摆脱本能活动,追求自由和不朽的强烈渴望。古希腊人对于“人”理念,可以简单地用“观照至高存在并据之以行动者”来表达。(注:洪涛《逻各斯与空间——古希腊政治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4页。 )言作为对神的观照同时是一种实践,人必须依观照而行动,言行一致就是古希腊最重视的政治品格——“勇敢”的体现。城邦是公民对话和行动的场所,参与和共享的空间,人只有在城邦中才成其为人,人的生活就是在城邦中的公共生活。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人是政治的动物”,“城邦外的人,非神即兽”的含义。劳动和行动的对立在现代社会却表现为一种绝然不同的方式,即劳动的社会化和劳动地位的上升。洛克首先把劳动看做私有财产的证明,进而斯密把它看作国民财富的源泉,后来马克思把它看作一切价值甚至人类文明的基础,劳动一步步获得了绝对的重要性。但是劳动因此就获得了崇高意义吗?不,因为劳动不仅是痛苦、不自由的,而且是私人化、无世界性的。劳动的痛苦和不自由属于人类境况本身。虽然近代以来工具和机器的发明减轻了劳动的痛苦,这确实意味着非暴力方面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自由方面的进步,因为没有一种奴役比得上受生存必需性所胁迫的自然强力。劳动的社会化没有造成这一活动与其它活动的平等,而是造成它无可争辩的统治。它第一次让人类全体缚于生存之轭下,让所有与谋生无关的活动都成了娱乐。劳动的私人化和无世界性在于劳动者不和世界、他人在一起而单独面对生命必需性的事实。当然现代大生产中劳动者必须和他人在一起,但这种“在一起”不是真正“多样性”的标志,而是单纯种群繁衍的特征。它产生的不是公共领域内有差异的个体的平等,而是弥漫于生产——消费社会中的单面性、原子化,日益发达的消费社会把一切都卷入生产和消费的巨大循环:工作的产品变成消费品,不再具有保持世界持存性的特征;政治蜕化为劳动无限扩张的手段,因此它不再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靠沉默的暴力更易达到目的。劳动的解放实际上变成劳动占绝对支配地位,变成私人领域的公开展现和真正公共领域的萎缩。阿伦特认为,如果工作是非政治的,劳动就是反政治的,现代性的困境——公共领域的衰落和人的异化——在劳动社会达到空前的程度。
阿伦特从劳动和行动的基本区分出发,进而区分了“社会性”和“政治性”,“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组概念。社会性在古希腊指示满足需求的活动,属于家务劳动的范围(亚氏的经济学是家务活动的学问)。从事劳动的奴隶不是公民,因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但他们的劳动是公民成为政治的、即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的前提条件(古代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必需以家务中的不平等来保证自由人在城邦政治里享有平等)。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因为政治的交往把我们带向世界和与我们共同拥有世界的他人,而在社会性交往中我们仅仅表现自己的欲望。近代劳动分工和技术发明的“进步”,却导致了私人经济成为全社会最为关心的问题。政治不再是独立自主的领域,不再是以行动揭示人之为人的场所,反而蜕变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和保护私人利益不受侵害的必要之邪恶,只具有最低限度的约束作用。阿伦特认为,“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术语鲜明地体现了“生意全盘成为政治”,只不过在把握时代特征上后者“更科学”一些。亚氏早已告诉我们,城邦存在的目的是追求“优良的生活”,如果仅为生活的自给自足,城邦之外的其它社会团体更易于达到这个目的。(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一章二1252b30,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第1版。 )对于追求生活质量的提升,给出人之为人极高标准的古希腊人来说,近代以“需要体系”、“利益集团”为模式的国家观念不仅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是可鄙的。
当然,阿伦特也同意社会问题不是与政治毫无关系,她认为,“自由只会降临到需求已得到满足的人身上,同样自由会逃避只为欲望生存的人。 ”(注: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Zndend 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3,第139页。)问题在于, 局限于私人领域不可能有自由,因为自由作为一种内在能力,与开始行动的能力一致。公共领域是人们相互对话、辩论、参与行动和达成共识的政治共同体,既是个体自我和世界实在性的保障,也是政治行动从而自由可能的条件。古希腊城邦、古罗马共和国和近代的民族国家都提供了共同世界和文明的基础。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导致私人领域取代和吞噬了公共领域,大众社会就是私人领域极端社会化的产物,就是人类不知公共领域为何而群体从事家务劳动的产物,在其中人类的平庸、单面、无自主性和无批判性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公共领域衰落对人的戕害在极权主义中暴露得最为彻底: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个人”,所有的行动都旨在加速虚构的自然或历史运动。其中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不是自由的,前者一方面相信人无所不能、无比狂妄,一方面自认为是执行历史或自然法则的工具;后者生命中的主要经验是无力感和绝对顺从,所有人都丧失了政治责任的判断和承担。在引起争议的《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她使人们不得不正视一个可怕的事实:艾克曼不止是“欠下五百万条人命”的杀人魔,不止是一个官僚机器的体制化产物,更在于他是个毫无思想力和判断力的普通人。
“西方历史的潜流终于浮上水面,取代传统的尊严”(注:《极权主义起源》,初版序。),阿伦特鞭辟入里的分析表明,奥斯维辛的苦难不是一段与现代人无关的苦难,极权主义不是一个杀人恶魔偶然发明的政体,而是西方社会在现代性进展中潜伏的暗流终于浮上水面的结果。她警告,如果不根本诊治现代性的痼疾,极权主义仍可能以一种强烈诱惑人的方式,以解救种种悲苦的姿态出现。
阿伦特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作出明确界定,既非出于知识考古学的兴趣,亦非从事单纯概念的游戏,因为这一区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由此阿伦特唤回了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对“政治”的理解——政治是一种内在目的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发展经济的手段,政治之公共领域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条件,而不是私人领域社会化的派生物。这一与近现代普遍接受的自由主义不同的政治观,为当代政治提供了深刻的批评和反思的源泉。我们知道,东亚的经济奇迹靠的就是单纯追求GNP的高速增长,实行高度的集权统治, 以自由的代价换来物质的丰裕。在人们赞美“亚洲龙”的时候,很少想到这种功利的道路不是每个个体生命应有的理想。我们在这些国家看到了严重的腐败和两极分化,人们丧失尊严、道德恶化,社会矛盾激增。终于,97年下半年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震惊了世界。这一严峻的现实恰恰证实了阿伦特的观点:如果政治行动只是为了达到某些经济目标,如果政治自由为经济增长牺牲掉,我们就既失去了自由,同时也不必然能消除贫穷。进而言之,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颠倒,不仅是现代政治危机的表现,而且也是现代性的根本危机:近代主体主义形而上学的表现。这一颠倒表明人们不是从人和他人、和世界共存的关系来理解人,不是从以言说和行动来体验存在方面理解人,而是把人理解为原子主义的个人,自我中心的主体,把世界理解为必须加以征服和消灭的客体和对象,这实际是劳动社会的人的自我理解。失去了公共领域的自由的人从“行动”退回到自我意识的内心,反而导致人内在的无力感和外在的贪欲性、侵略性。作为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更为关心的是使政治行动、从而自由可能的条件。她接受了古希腊的政治传统,认为人既非天生自由,亦非天生不自由,而是在政治共同体中并以之为条件创造和确立着自由。没有政治的公共领域,自由就缺乏实现的空间。她说:“根本剥夺人权,首先表现为人被剥夺了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一个能使言论产生意义、行动产生效果的位置”,她石破天惊地指出,“比自由与正义远更重要的人权是公民权。”(注:《极权主义起源》,初版序。第418页。 )这不仅是对当代政治哲学主流的批评,也是对空洞抽象的启蒙理念的批评,表现出了人们无法拒绝的智慧和勇气。
来稿日期:1998年6月10日。
标签:公共领域论文; 政治论文; 阿伦特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古希腊论文; 经济学论文; 犹太民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