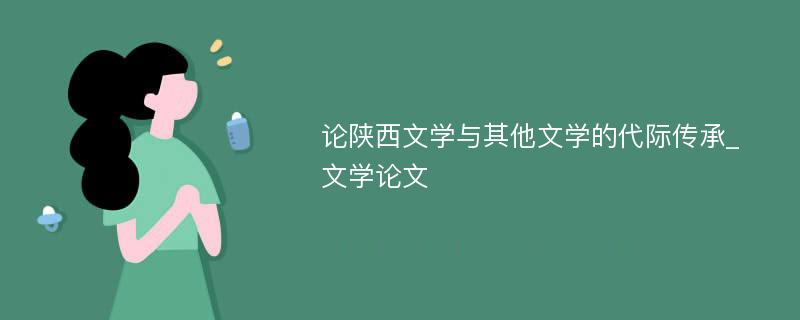
论陕西文学的代际传承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陕西论文,及其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11月17日,陕西文学界在延安举办了纪念路遥逝世十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随后,又在西安召开了“陕西文学三十年研讨会”。在这两次会上,我听到了人们对路遥创作成就的高度评价,也感受到了人们对陕西文学现状和未来的焦虑,对陕西文学的殷切期待——这也引发了我对陕西文学的一些思考。陕西是我的“父母之邦”,“野人怀土,小草恋山”,我对它有着无边的眷恋,而对于陕西文学,我更是愿它飞英藤茂,龙跃凤鸣,“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上,陕西文学无疑是一个重要而醒目的构成部分。不仅现在是这样,半个多世纪来,一直是这样。20世纪50年代的《延河》,乃是一份具有全国影响的杂志,曾经发表过《百合花》、《新结识的伙伴》、《飞跃》、《忆》和《创业史》等引起关注的作品;而陕西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和批评家,也都是人材济济,不可小觑的。
如果历史地考察,我们便会发现,陕西文学是只有“当代史”而没有“现代史”的。由于远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由于经济的落后和文化上的封闭,所以,陕西文学的“现代”阶段,几乎是一片空白:既没有成立有影响的文学社团,也没有创办有影响的文学杂志,更没有产生有影响的文学家。
20世纪的陕西文学,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准确地说,形成于陕北红色根据地政权稳固以后。正是借助“解放区文学”的资源和助力,陕西文学才得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
这样,对陕西当代文学的全面研究,就应该把至少“五十年”的历程作为一个整体。如果将考察的内容,仅仅限定在最近的“三十年”,那么,我们对陕西文学的研究,就是不完整的,就必然要把第一代的陕西作家排除在外,就无法完整地描述陕西文学的发展过程和代际传承。
从代际构成来看,陕西文学五十年,薪火相传三四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胡采、魏钢焰等人为第一代;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李天芳、高建群、程海、晓雷、王蓬、京夫、文兰、叶广芩、谷溪等为第二代;冯积岐、朱鸿、寇辉、杨争光、方英文、红柯、爱琴海、邢小利、张虹等为第三代。陕西的第四代,即“70后”和“80后”,我了解不多,也就不好判断,不知是否仍然盘龙卧虎,蓄势待发,据说,似乎有些后继乏人,青黄不接。
在我看来,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陕西作家之间,有着较为正常、积极的代际影响。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属于很难继武其后的军事文学,但是,他的工业题材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却充满了一种别样的激情和格调,对莫伸等人的工业题材写作有过不小的影响。王汶石的结构精致、巧妙的短篇小说,对第二代作家的结构意识和叙事经验的成熟,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比较起来,柳青的《创业史》对陕西小说写作的影响,远比别的作家要大、要深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柳青,陕西文学就是另外一种样子。没有柳青,陈忠实和路遥的创作,就很难达到现在这个水平。就文学性来看,柳青所达到的境界,也是不容低估的:通过细节和对话来描写人物心理和性格的技巧,朴素、省净而不乏诗意的语言,从容不迫、疾徐有度的叙事态度——这些,今天小说家比得上的恐怕还不是很多呢。
但是,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具体地说,由于争取战争胜利和夺取政权的现实需要,陕西文学一开始就是政治的文学,甚至可以说是战争的文学,一开始就自觉地服从于形势的需要和政治的需要。柳青的《地雷》、《种谷记》、《铜墙铁壁》和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小说,都属于这样的作品。这个时期的陕西文学虽然表现出记录时代风云的政治热情,虽然具有很强的完成时代使命的责任感,甚至不乏朴素的才华和令人觉得亲切的生活气息,但是,从整体上看,它还没有在文学的意义上形成自己的文学精神和文学传统,还没有确立稳定的具有现代性的价值理念。
从积极的方面看,从第一代作家开始,陕西文学就强调切切实实地“深入生活”,就充满热情地刻画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崭新的人物形象,从而形成这样一些值得肯定的成就和经验:
一是强调体验生活,强调从生活实感出发展开写作,这使陕西文学充满鲜活的生活气息。二是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写实经验,柳青和路遥、陈忠实的小说都体现出一种追求细节真实和描写生动的自觉意识,分别代表了自己时AI写作实主义写作的最高水平。三是充满责任意识、道德激情和利他倾向,力求有益于世道人心,尤其路遥的小说,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在激情、理想和诗意表现上最有力量的作品,已经极大地影响了无数青年读者。这是陕西文学的骄傲和光荣。
其实,陕西第二代作家在代际超越上的经验和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文学发展既是一种“前喻文化”现象,即前代作家对后代作家发生影响的过程,也是一种“后喻文化”现象,即后代作家摆脱前代作家的“影响”而另辟蹊径的过程。如果说,在创作的开始阶段,陕西第二代作家像第一代作家一样,都无一例外地写过一些“紧跟形势”的应景之作,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他们便开始艰难地超越第一代作家的局限,开始了对第一代作家的缺乏个人视境的写作模式的超越。
路遥是一个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作家。他不仅在第二代陕西作家中读书最多、学养最好,而且是他们中间最会思考问题、最有哲人气质的人。虽然路遥具有自觉地接受一切优秀文学影响的开放态度,但是,俄罗斯文学对他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可以说,他的作品里的道德诗意和利他精神,他对底层“平凡的世界”和“小人物”的关注,都与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是相通的。他固然虔诚地学习柳青的文学经验,乐于做“柳青的遗产”的继承者,但是,他也在清醒地克服柳青的局限。在柳青笔下,人物的个性和情感的丰富性,常常被时代性和阶级性约减到苍白的程度,《创业史》里的许多人物,如梁生宝、郭振山、高增福、徐改霞等,大都呈现出一种简单的性格特征,缺乏成熟的性格和充分发展的内心生活。例如,在《创业史》里,梁生宝从来不曾有过自己的思想、愿望,从始至终都是按照外在的社会指令来生活和行动。比如,梁生宝接受当时流行的观念,认为“私有制”乃是万恶之源,一切与“私”沾边的情感和行为,都是丑恶和不道德的:“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使继父和他别扭,使这两兄弟不相亲,使有能力的郭振山没有积极性,使蛤蟆滩的土地不能尽量发挥作用。快!快!快!尽快地革掉这私有财产制度的命吧!共产党人是世界上最有人类自尊心的人,生宝要把这当做崇高的责任。”①这种对“私有财产”的理解显然是简单的,有害的,甚至是反人性的,它所导致的后果,便是对人的自由的限制,是对人的合理要求的剥夺,是对人的内心世界的严重扭曲和伤害,因为,“私有财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在生活和行动上享有多大的独立性和自由度,也与个人的幸福感密切相关。同时,反对“私有财产”必然要求限制个人的权利,把一切谋求个人发展和个人利益的努力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个人与集体、自由与服从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如,徐改霞想到城里当工人,也算是积极响应“工业化”的号召,但是,尽管如此,她的内心却仍然觉得不安,仍然产生了强烈的内疚感甚至负罪感:“啊啊!分配给渭原县的名额只有二百八十个女工,报名的突破三千了。光城关区就有一千多报名的。根本没上过正式学校的,都拥进城来了嘛!有些闺女,父母挡也挡不住。有些是偷跑来的!”②站在这千百个报名的女孩中间,徐改霞深深地自责起来,觉得自己进城当工人的想法是自私的、可耻的,甚至因此怪罪起一直在这件事上帮助她的郭振山。最后,当“穿灰制服的女干部”王亚梅告诉她“工人比农民挣得多,所以才会有盲目流入城市的想象”时,可怜的改霞简直羞愧到了无地自容的程度,痛苦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她想哭。自己多没意思!难怪那天在黄堡大桥左近菜地草庵跟前,她一提想考工厂,生宝就冷淡她了。她是该被冷淡的,甚至是该被鄙视的!……唉亥!俗气!真个俗气!两年前五一节在黄堡镇万人大会上代表全区妇女声讨美帝的徐改霞,竟给人这样的印象!在城里能找到一个没人的僻静地点吗?改霞要认真地哭它一场!③
但是,在路遥那里,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生》中的高加林无疑可以被看做另一个时代的徐改霞。他面对的同样是农民的后代进城的问题,同样面临着进退去留的抉择,同样面临着忍受给予的生活还是与命运抗争的抉择,同样承受着巨大的道德考验和尖锐的心灵痛苦。然而,路遥极大地摆脱了那种僵硬的道德律令的压抑和拘执,而是站在同情的立场,来处理一个悲剧性的冲突:个人自我发展的合理要求与这种要求的时代性压抑之间的尖锐冲突。同时,路遥还真实而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被长期忽略的问题:在反对、消灭“私有财产”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让农民承受了太多的痛苦?是不是让他们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是不是让他们放弃了太多的自由?
虽然,有时候,路遥也从道德上批评高加林,但是,他又是多么爱他和同情他啊!如果说徐改霞是一个简单而苍白的人物,那么,高加林却是一个复杂而真实的人物,用路遥自己的话说,就是“要给文学界、批评界,给习惯于看好人与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④。如果说,我们从徐改霞身上看到了柳青对于时代的过度顺从和盲从,那么,我们从高加林身上看到的就是路遥对于变化中的“城乡交叉地带”生活的独立观察和深刻思考。如果说,柳青的着眼点在抽象的时代经验,而且几乎只是根据“时代”的“宏大”经验和权威指令的严格规约来写作,那么,路遥的着眼点就在具体的个人经验,而且主要根据包括自己在内的具体的未被“时代”阴影遮蔽的个人的经验来展开叙事。
当然,毋庸讳言,路遥的写作还没有达到成熟和深刻的高度。他还没有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仍然缺乏彻底的批判精神,所以,他的写作就更多地停留在经验的层面,而没有进入真正思想家和批判者的高度。路遥一方面在写具体的人,写他们的艰难和坚韧,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想对那个抽象的“时代”唱赞歌,所以,最后,他便在某种程度上把柳青的局限也“继承”了下来。总之,直到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路遥还仍然是一个处于成长和展开过程的作家,无奈天不假年,使英才早逝:“如何灵祗,歼我吉士?谁谓不痛,早逝即冥;谁谓不伤,华繁中零。”(曹植:《王仲宣诔》)这不仅是陕西文学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大损失。
陈忠实的写作模式转换意识的觉醒,来得比较晚些。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的写作基本上还是在一种随顺时代的惯性推动下进行的。不同的是,与第一代作家比起来,他稍微多了些问题意识,而这种问题意识,决不比“时代”提供给他的更多、更尖锐、更深刻。但是,虔诚的态度和广泛的阅读拯救了他。据他自己在《创作经验谈》里说,为了学习写作的经验,他曾经花了很多时间细致地阅读莫泊桑和契诃夫的小说。而到了80年代中期,对于自己写作的强烈的危机感,使他产生了彻底改变写作模式的强烈冲动。他说:“到了1985年,当我比较自觉地回顾包括检讨以往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必须摆脱柳青和王汶石。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这段经历,概括为一句话说,一个业已长大的孩子,还抓着大人的手走路是不可思议的。……但有一点我还舍弃不了,这就是柳青以‘人物角度’去写人物的方法。”④他读了大量的书,深入地阅读了涉及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犯罪学等内容的著作,尤其细致地研究了包括《百年孤独》在内的优秀作品的结构方式和叙述技巧。他坦率承认《古船》和《活动变人形》对自己的影响。他接受“文化心理结构”的理论,把这当做使他“获得了描写和叙述自由”的关键。他终于实现了对第一代作家写作模式的超越,实现了对自己的写作困境的超越,终于写出了一部厚重的可以做“枕头”的小说。
《白鹿原》的成功在于它很好地解决了“可读性”的问题,在于它塑造了许多足以不朽的人物形象,在于它所包含的对民族命运的危惧悲呻的忧患,在于它对中国文化前途的凄凉在念的关怀。但是,陈忠实的超越,也是未臻至善之境的。《白鹿原》无疑是20世纪后五十年中国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收获,但是,如果放在整个世界文学的比较视境里,我们就可以发现陈忠实这部作品的问题:狭隘的民族意识,缺乏更为深刻的思想,缺乏更为超越的批判精神,缺乏现代性的价值建构。
贾平凹写作模式转换的经验支持,来源于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民间文化,主要是民间的逸闻、传说、野史,以及当下的“段子”和民谣等等;一是中国古代的小品、笔记小说和包括《金瓶梅》在内的着重于表现世态和风情的小说;一是包括沈从文、孙犁在内的“南方气质”的写作。他早期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比较清纯的意境和比较雅秀的文体,大多得益于对沈从文和孙犁等“水性气质”写作的模仿和学习。但我们在他的作品里看不到现代性的启蒙精神,看不到对中国旧传统的理性的批判态度。
从文化气质来看,陕西文学可以分成三种形态,即高原型精神气质、平原型精神气质和山地型精神气质。路遥所代表的高原型精神气质的文化,具有雄浑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难感、淳朴的道德感和浪漫的诗意感,但也有价值视野不够开阔的问题。它与陈忠实受其影响的关中平原型精神气质的文化不同,后者具有宽平中正的气度、沉稳舒缓的从容,但在道德上却显得僵硬板滞,缺乏必要的宽容和亲切感;它也与贾平凹等陕南作家受其影响的山地型精神气质的文化迥然相异,后者属于这样一种气质类型:轻飏、灵脱、善变,但也每显迷乱、淫丽、狂放,有鬼巫气和浪子气,缺乏精神上的力量感及价值上的稳定感和重心感。
现在来看,随着路遥的去世,陕北高原型精神气质的写作显然已渐趋消歇;以陈忠实为代表的关中平原型精神气质的写作,似乎也处在一个停滞阶段或者说转型过程;而比较活跃的,是陕南山地型精神气质的写作,只是这种写作声势不小,但成绩不大,不仅如此,这种模式的写作,甚至还有很多的问题,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研究。
就整体的情况来看,陕西文学既是辉煌的,但也是残缺的。它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但是,种种的问题,也应该引起批评家的注意和分析。一味地唱赞歌,而不注意研究问题,其结果最终会把陕西文学导入歧途。
是的,如果用更为严格的尺度来衡量,我们就会发现在陕西文学中曾经长期而普遍地存在的一些问题,那就是,依附性大于主体性,“时代性”大于“现代性”,服务性大于启蒙性,肯定性大于否定性。换句话说,陕西文学普遍缺乏启蒙意识,缺乏批判精神,缺乏独立的价值立场,缺乏对“现代性”的探索热情。他们要么满足于亦步亦趋地做自己时代的“歌手”和“书记官”,要么彻底退回到纯粹私人的生活领域,满足于自哀自恋的“私有形态写作”。更为严重的情形是,有些陕西作家,始终没有彻底摆脱“小农”的狭隘性,心胸褊狭,目光短浅,对于现代的都市文明,充满偏见和敌意。
具体地说,陕西文学的问题,较为严重地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是缺乏完全独立的人格精神和高度自觉的批判精神。从与现实和权力的关系来看,陕西作家整体上表现出一种随顺的姿态。面对现实,他们往往倾向于选择简单地认同甚至赞美的态度,而不是做生活的冷静的观察者和批判者。柳青、王汶石的写作,终其一生,没有摆脱这样的局限;陈忠实《白鹿原》以前的作品,大半是顺应现实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则分裂为两个世界: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虚假的;一个是“平凡的”,一个是“非凡的”;一个是让人觉得亲切的,一个是令人觉得隔膜的。而正是后面的这些部分,减损了他这部小说的影响力,破坏了小说的内在的完整性。
第二个问题,是缺乏距离感。这既指时间的距离,也指情感的距离;既指与外部世界的距离,也指与自我的距离。距离是产生美的前提条件。对于试图包含复杂的生活内容的史诗性作品来讲,作者与自己将要处理的对象和题材内容保持适当的距离,实在是一件必要的事情。司马迁就与他深受其害的冷酷的刘汉政权,保持了足够大的情感距离,否则,我们就看不到“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了,就看不到对无赖刘邦的摘心取肝的刻画了。但是,很多时候,陕西作家似乎倾向于缩短与外部世界的距离,缩短与自我的距离。像《创业史》、《新结识的伙伴》、《信任》、《满月儿》、《秦腔》都是与外部世界距离太近的作品,《废都》则是与自我距离过近的作品,这些作品的问题最终都表现为缺乏叙事作品所必不可少的真实和准确、客观和公正。
第三个问题,是缺乏理想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启蒙精神。没有理想之光的照亮,就没有文学的灿烂辉煌。伟大的文学不仅写出了生活所是的样子,它还致力于写出生活当是的样子。文学既是人类克服生活的无意义感的手段,也是人类通往精神上的理想世界的途径。一切伟大的文学,都有一个自己的乌托邦,或者说,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理想图景。理想主义和科学主义必然指向启蒙主义,指向对现实中存在的庸人主义和愚昧现象的反思和批判。所谓启蒙,就是揭开一层层的遮蔽物,使人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必须拒绝和告别的,什么是应该向往和追求的。所以,启蒙最终指向光明、美好,指向一个更为理想的世界。启蒙精神是一种现代精神,具有灯与火的作用,是可以照亮世界和温暖人心的。它要求作家,既要勇于面对黑暗,面对外部世界的黑暗和自己内心的黑暗,又要创造光明,要像鲁迅那样充满破毁“铁屋子”的激情,要“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别人到光明的地方去,让他们“合理地度日”,“幸福地做人”。它要求作家要有科学精神,而不是做迷信和无知的奴隶。
然而,遗憾的是,陕西作家中,除了朱鸿、寇辉等少数第三代作家,似乎普遍缺乏这种启蒙精神。有的作家丧失了最起码的科学精神,缺乏最起码的理性精神,因此,在作品中津津有味地渲染反科学的事象,不遗余力地渲染神神道道的怪异事象。甚至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作家也倾向于用神秘主义的方法来解释生活。西方有句话:over simplification is always an insult to intellect.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过分的简单化是对人类智力的羞辱。充满迷信色彩的神秘主义,就是对世界的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认识,因而,是对人类智力的羞辱。用迷信的方式解释一切,是认识领域的典型的懒汉主义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因而是要不得的。最近,读到贾平凹的长篇新作《高兴》,发现小说在描写人物、叙述情节上的虚假和随意,就与这种严重的“简单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如果想克服这些创作上的问题,就必须在内心培养科学主义的精神,点燃理想主义的火焰,从而使作品成为能够照亮人心的启蒙性质的作品。
第四个问题,是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大于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是一切伟大文学的精神基础。真正的文学总是充满对人类的挚爱,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一切人的热切的同情,对人类平等和最终解放的追求。按照简单的阶级斗争理念展开叙事的人,是不可能具有博大的人道精神的,因而就不可能对所有不幸者都给予温柔的怜悯和同情。例如,柳青不仅对姚士杰这样的“阶级敌人”缺乏起码的平等态度,而且对素芳这样的“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也显得很冷漠,甚至多多少少还有点歧视。寇辉的《黑夜孩魂》⑥就极大地超越了柳青,他像叶赛宁在《狗之歌》中一样,表现出一种极其富有人性内容的态度,从而使他的这篇小说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优秀之作。陈忠实的《白鹿原》则将民族情感置于人道主义之上,在叙述民族冲突的时候表现出一种简单化的态度和立场。如果与萧洛霍夫和罗曼·罗兰比起来,陈忠实在这一问题上的残缺,就显得更加明显和严重。在缺乏人道主义精神上,贾平凹在《废都》中出于发泄压抑情绪的消极需要,将几乎所有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都置于一种被羞辱、被伤害的境地,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⑦
第五个问题,是反都市文明成为一种顽固的精神姿态。对现代都市文明充满误解、恐惧和敌意,乃是很长时间里陕西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倾向。对于城市,这些“农裔城籍”的作家,充满一种既爱又恨的复杂心理。他们通过写作进入城市,但是,又觉得自己与城市很隔膜,所以,便以农村做参照来打量城市和城里人,觉得城里人并不像农村人那样活得自由和自在、健康和真实。这样,虽然已经定居在城市,做了城里人,但是,这些农村出身的作家,却乐意把“我是农民”挂在嘴上。他们借此显示自己对城市的排斥态度。然而,这与其说显示着一种虚妄的傲慢,毋宁说是表现着对于自己的“农民”身份的强烈的焦虑和自卑。于是,贬低和否定城市,在某些作家那里,便成了一种捍卫内心“尊严”的策略和方式,进而成了一种坚定不移的文化立场。他们甚至常常用动物主义原则,来贬低、羞辱和对抗城市。例如,在《废都》里,都市里的人连动植物都不如,因为他们跑不过一只“普通的羚羊”,也不如“一棵草耐活”,而“只有西京半坡人,这是人的老祖宗,这才是真正的人”⑧。
创作伟大的作品当然需要勇气,但更需要克制,需要达到较高境界的教养、深刻的思想和丰饶的诗意,尤其需要开阔的精神视野和追求现代文明的激情。不然,就像鲁迅所说:“所感觉的范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小的悲欢为全世界”,从艺术层面来看,它的“技术是幼稚的,往往存留着旧小说的写法和情调”⑨。
第六个问题,是文学批评严重缺席。我曾在《真正的批评及我们需要的批评家》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从功能和作用上看,文学批评通过对作家、作品及思潮现象的分析和评价,积极地影响着读者的阅读和作者的写作,维护文学肌体和社会精神环境的健康。批评会潜在而有力地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和精神气候。”⑩是的,没有真正的批评,没有尖锐的质疑和不满,作家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就不会被揭示出来。如果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友谊,被降低为低俗的互相吹捧,被等同于文过饰非的话语交换,那对文学来讲,简直是糟透了!
无疑,陕西的文学批评在对陕西作家的研究和评论上是做出过成绩的,但是,陕西第二代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太好了,太亲密了,常常好到了可以把文学放在一边的程度,亲密到了再拙劣的作品批评家都能看见“突破”、“超越”和“杰作”的程度。长此以往,面对陕西作家的问题,陕西的批评家基本上处于失语的状态——与第二代作家同代的批评家不便批评他们,比第二代作家晚一代的批评家则不敢批评他们。不仅如此,有的批评家甚至通过虚假的传记写作等方式,制造神话,纵容作者,遮蔽真相,误导读者,造成极为消极、有害的后果——这是极为严重的失职,甚至是不能容忍的渎职。
我希望陕西的批评家尤其第三代批评家,能够切切实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即通过认真的、冷静的批评,揭示陕西作家的经验,剖析他们创作中的问题。这样的批评,才是有尊严的批评,才是有价值的批评,才能使陕西文学配得上它所享有的盛名,才能对得起读者对它的尊敬和信任。
关中大儒张载有几句非常著名的话,冯友兰先生在几篇文章中五体投地地三复其言,称之为“横渠四句”:“替天地立心,替生民立命,替往圣继绝学,替万世开太平。”元好问则在《送秦中诸人引》中说:“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的确,陕西是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陕西的文学之树,如何才能植根于传统的厚土,开放出现代文明的灿烂花朵,结出可以被人类共享的丰硕果实,这既是陕西文学的研究者应该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对陕西作家的殷切期待。
注释:
①②③柳青:《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6月版,第264页,第440页,第447-448页。
④《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广州出版社、太白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9页。
⑤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小说评论》2007年第6期。
⑥寇辉:《黑夜孩魂》,《延河》2002年第4期。
⑦⑩详见拙著《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39-75页,第315页。
⑧《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53页。
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标签:文学论文; 陈忠实论文; 陕西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陕西经济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创业史论文; 柳青论文; 废都论文; 路遥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