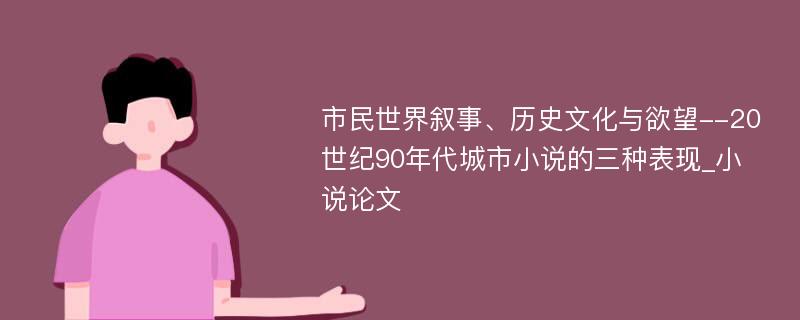
市民世态,历史文化,欲望叙事——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的三种表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态论文,三种论文,历史文化论文,欲望论文,市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6)05-0091-05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动。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巨变主要不是通过乡村而更多是通过城市体现出来的,城市内部多重意识形态交互作用所造成的复杂变局以及这种变局带来的多重不确定性使城市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中的各阶层的矛盾及不同阶层的人关于城市的观念的变化,成了中国社会变化最重要的现象之一。
居住在城中的作家,自然会关注这一重大变化,并通过这种关注探寻自己的精神出路。他们的探寻,一方面透露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市变化的状态以及不同阶层市民的生存策略。从新写实小说到城市文化小说,再到城市欲望化的叙事,尽管不是一个呈递进状态的写作探索过程,但的确是一个诗意逐渐消解,欲望逐渐膨胀,精神渐渐隐去,肉身慢慢凸现的过程,这是一个城市和作家互为镜像的过程。从这一过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的变迁,也可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此一时期的心路历程。这是一份内容丰富、意味深长的历史文化档案。
一、回归市民世态
描绘世态人情的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小说大都有着较鲜明的“新写实”风格,这也许是因为生活的丰富性大大超越了文学的想像力吧。这些小说,或越过层层叠叠的屋顶,或穿过或宽或窄的街巷,驻足于底层市民的群居地带,细细刻绘远离庙堂的城市世情生态,将素不被人关注的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三教九流的众生相和纷纭杂陈的世俗景观最真实的裸呈出来,让人清晰看见隐藏在高楼大厦之后的窄街背巷的市井民间的世态、人情和事理。
底层市民的生存状态历来是当代作家挖掘的富矿,因为这里的人情世相比纯粹的乡村和纯粹的都市都要丰富复杂得多,生活在窄街背巷的小市民们大都有着发达国家市民所没有的或远或近的乡村背景,尽管他们已经远离土地谋生和生活于城市的底层,但他们的农民血缘和庞大的人数,总使得中国每一个城市都带有极深厚的乡村背景,他们是过着城市生活的农民。
在他们身上交汇着当代都市文明与传统的农业文明的痕迹,既有经过市场经济大潮的浸染洗礼的经济头脑,也留有几千年来自然经济的农业文明的基因。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些生活于街巷和市井之中物质上的相对贫困和精神上相对庸俗逆来顺受的人们,并不足以构成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然而在一些作家那里,这些市民们知足常乐式的生存方式,是非莫辨的道德态度,在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生活空间里对政治权力话语和思想启蒙话语的拒绝和嘲弄,都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甚至赞赏。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就是这样一篇标志性的小说:市民的精神气质不再被当成批判改造的对象,而成了被歌颂的力量。燕华们锦簇一团的走在汉口街头的美丽风景,就成为这种文化精神的象征。美丽的一面被强调性地加以表现,而武汉小市民身上的另一些精神现象如粗鄙、庸俗、势利的一面却被隐匿起来。“精英文化”的命运在小说里则恰恰相反:市民们对新闻联播普遍排斥,当有着作家梦想的“四”给药店店员“猫子”讲令自己激动不已以为也能把“猫子”感动得随自己心动神驰的小说灵感时,“猫子”却早已经神游酣梦了。这些场景都暗喻着启蒙话语或意识形态话语在“民间”的普遍失效,只有在有限视域的经验范围内生成的能让市民们切实感觉到的民间知性和集体无意识的习俗才可能在他们中间产生作用。在这类小说中,精英话语和启蒙话语是普遍失效的,而民间性的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停滞的日常市民生活或精神状态,则被精心梳妆打扮起来成为小说的主体。
这一类的城市小说主要有范小青的《城市民谣》、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你以为你是谁》、苏童的《城北地带》、鲁彦周的《双凤楼》、缪永的《驶出欲望街》等等。范小青的《城市民谣》写得算是比较有诗意的了。至少,江南小城的情韵依旧构成小说的言说背景,小说的主人公钱梅子也给诗意的语言刻绘得如暗香的米兰、青青的小草一般美丽。在这里,生活的苦难感被完全过滤掉了,“下岗”、待业、创业不再成为承载这一时代或喜或悲的市民生活的习惯性文本内容。生活如小河一般静静流淌,无论是下岗、炒股还是经商,这些人们赖以制作热门话题的生活内容,都无法在这里掀起大的波澜。时代隐去,而历史呈现,如果说以前城市小说惯于表现的是白天的喧闹的话,那么范小青的城市小说表现的则是月夜的寂静。于是一切喧嚣都融化在夜的沉静里,古老长街上的雕栏玉砌呈现出来,乾隆下江南的传说中的石狮子浮现出来,静静流淌的小河也出现了,现实的喧嚣与浮躁都稀释、化解在这“历史性的”人文气息浓厚的小河之中。这种小说与其说是在写实,还不如说是在写梦,是越过下岗、待业、炒股、经商的和谐优雅、韵致柔婉的江南梦。
如果说范小青的小说具有诗性的话,池莉的小说则是世俗性的;如果说范小青的小说是历史性的表述的话,池莉小说的时代性则是非常强的。池莉曾在《我坦率说》中对“小市民”作了重新解释:“我自称为‘小市民’,丝毫没有自嘲的意思,更没有自贬的意思,今天这个‘小市民’之流不是从前概念中的‘市井小民’之流,而是普通一市民,就像我许多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池莉的解释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和她的叙说立场密切相关的,比起那些启蒙欲极强的精英分子,那些每天为衣食奔忙的“市井小民”一类的人物显然让池莉觉得亲切可信得多,也许在民间从来就存在着一种对精英文化的不信任的敌视态度。在池莉那里,启蒙立场未必就不是一种虚伪、欺骗、令人厌恶和鄙视的立场。相对而言,“小市民”的、平民化的、经验性的、“日常现实主义”的世俗性关怀则要真实可信得多,所以池莉说:“我用我的目光,用我的感觉,用我的语言,从我的角度去写芸芸众生”(《关于汉味》)。这样,池莉的小说未尝不可以叫作“反启蒙小说”,她企图用这种反启蒙的态度来嘲笑启蒙的虚假、虚伪、欺骗和无力。可问题在于,池莉精心构设的诸如“沔水镇”、“江汉路”之类的民间性城镇社会、生活在其间的“市井小民”以及市民们的那种坚忍达观、平淡自如的生活状态,未必就是那么美好,也未必比生活真实,比启蒙小说真实。那些无痛苦的世俗人生中的芸芸众生其乐融融的鲜活日子,与其说是池莉所言的不屈不挠的活法,还不如说是当生活的残酷被滤去后又一种虚伪的表达。如果痛苦消失,小说的深度就自然消失,于是“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自我麻醉和大武汉长江北岸被江堤围出的真实的散发着种种城市异味的“江汉路生活圈”疏离的表达未必就不是虚伪的虚构。池莉也好范小青也好,都是滤去变革现实残酷之后的写实,她们的写实与其说是在对生活做真实的触摸,还不如说是面对生活无奈的逃避,这种逃避的虚构尽管不可能比生活更真实,但也许比真实更能给人以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二、玩味历史文化
对启蒙表达拒绝和防范的还有一类小说。这类小说的内蕴和立意仍采取历史性的民间立场。它们穿透即时性、时代性、现代性的云雾,驻足于传统文化的风流余韵中,将时代行进的脚步挡在门外,其文本的叙述格调和作品中人物的存在方式、活动范畴都是通过对传统文化趣味的坚守来与门外的喧嚣保持着距离的。这类小说不妨称作“城市文化小说”。与描绘市井生态的小说相比,“城市文化”小说涵盖的生活面不仅要宽广一些,而且精神层面的内容也要丰富复杂得多,然其精神基点依然是回到传统农业文明的深处,体现的是被“文革”从表层阻断的传统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这就不自觉地体现出对政治权力话语和启蒙话语有意或无意的疏离。彭见明的《玩古》、贾平凹的《白夜》、王小鹰的《丹青引》等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都体现出相当老旧的文化趣味。特别是《玩古》,以“玩古”这一历史久远的文化风习为本事,串联起散落在鹤了城各个角落集古玩古者的鲜活故事。市长高安用玩古品尝生活的趣味,柳三生和洪伟达靠集古玩古打发时光,谷定坤与周顺清靠贩古来摆脱生存困境,谷家大院的人用护古来守持自己经年历久的心理优势。众多市民参与其间,乐此不疲,炒古成为一时风尚。显然,当彭见明用和茅盾文学奖评委们宏大叙事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的叙事视角去玩味生活的细枝末节的时候,意识形态化的、启蒙性的话语自然就被消解得了无痕迹,经济性的和政治性的生活内容便化成淡淡的无足轻重的背景,而人心灵深处的细微、世故人情的复杂和南方小镇的秘密便在娓娓道来的情韵笔墨中凸现出来。在这里,彭见明的小说似乎是在有意摆脱政治经济性的生活内容而上升到更高的文化性的生活境界之上的。在蛰伏于纷扰小城的“玩古”高手们那里,“玩古”即是“玩世”,即从“玩物”状态中超脱出来,从喧嚣的利益纷扰中超脱出来,进入自在自适、精致高雅、通脱练达的宁静人生,即彭见明所说的:“玩古者,玩世也。这‘玩’因此就不是通常概念的闲耍了。是优雅的沉重,时髦的苍古。”
贾平凹的《白夜》则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浸染了极浓厚的旧文化趣味,虞白的贵族品格、夜郎的游侠精神和小说散点透视的笔法无不是旧的文化传统在新小说中的成功复活。贵族和游侠的苦恋其实是贾平凹自己对旧文化的苦恋,然而这种苦恋显然和小说中那些乘风追逐却又一无所得的活在城市的各色人等一样,是没有结果的。虞白心比天高,一尘不染,可城市已经抹杀了白天和黑夜的界线,就像丑女颜铭用美容手术变成美女一样,城市的化妆术也抹杀了本真和虚假的界限,虞白的坚守永远也无法落到实处,只能是一个姿态而已。如果说已经变成西京民间博物馆的虞家旧时的园林和宅第是历尽风雨而残存下来能较为完整地体现贾平凹的文化旧梦的实境的话,那贾平凹也只能像居于院中的虞白一样感叹时光飞逝、物是人非了。与静而传统的虞白相反,夜郎则是动和现实的,但他的现实的积极姿态却不过是传统理念崩塌后略带玩世意味的侠的心态,当夜郎正义的努力换来的只是冰冷的镣铐的时候,表明传统的侠的精神在现实中是完全行不通的,这又何尝不是有着浓厚传统文化心结的贾平凹自己的悲叹。如果说虞白和夜郎身上充满想象地折射着旧文化的气韵的话,散点透视的叙述手法更显示出传统山水画般的魅力。贾平凹对散点透视的言说方式的选用源自他血脉中天然的文化自觉。早在1986年他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浮躁》的时候,他就觉得《浮躁》式的如上帝俯瞰人间的全知全能式的西化的写实手法让他实在痛苦,而他的阅读经验又告诉他,源自唐宋“说话”、到《金瓶梅》、《红楼梦》趋于成熟的非史诗非传奇的、平常聊天式的“散点透视”的言说方式,才能让他内心感到放松、有趣和自由。于是便有了使贾平凹才情智慧得到最充分发挥的“散点透视”的浸染着极浓厚文人气的《废都》,它和《白夜》一样是一部汉字和小说叙述相得益彰的作品,也许汉语只有在这种言说方式中才能获得最充分的自由。它照亮了作家的回家之路,当然这样的言说是需要深厚的语言功力和立足于当下的时代精神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写的。《白夜》的文人意趣之所以能通过这种纯熟的言说方式传递出来,不仅在于贾平凹是在当代复活了旧小说,更在于贾平凹和当下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然,真正的创造资源不是来自过去,而是来自现在。只有立足于现实才能创造一种新的现实,和西方伟大的现代作家比起来,贾平凹创造的欲望显然要弱一些。
王小鹰1977年的《丹青引》也是远离浮躁和喧嚣的产物,是上海作家中少受时代情绪干扰、潜心创作的精神素质的体现。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功需要和时代保持一定距离。这种距离让王小鹰在小说中使用了一种和《白夜》极相似的散点透视般的长卷式的叙事结构方式。丹青是传统的,叙述方式也是传统的,这使得《丹青引》洋溢着极浓厚的传统文化的气息。而透过无极画派的兴衰所传递出来的名利场中的让人无法置身事外的争斗和算计又是当下的。画家画商关系、夫妻关系、恋人关系、师徒关系、师姐师兄关系,各种社会矛盾的深层次的表现,都被作家的散点透视法裸露出来,卑微欲念的烧炽让艺术暗淡无光,留给人的只有莫名的恐惧和焦虑。如果说现实是浮躁和焦虑的话,传统的文化趣味则是沉着和有魅力的,这需要拉开距离来看。《丹青引》之所以让人着迷,就在于它和现实拉开的距离,就在于它的传统文化趣味和言说方式,正是这种内在的既传统又新鲜的文化趣味和言说方式,才使《丹青引》成为这一时期上海作家自我突破而获得成功的标志性作品,和竹林的《女巫》、王安忆的《长恨歌》一起成为1990年代上海文坛乃至中国文学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都市一样,中国的那些靠侵占农村土地、用一幢幢水泥房子迅速栽种起来的都市都带有极浓厚的乡土色彩,而且几乎所有的城市,即使是上海,构成大都市的现代元素都极其缺乏。找遍地图,你将发现没有一座城市有着个性化的和影响力足以辐射全国的金融、商业、时尚、艺术、文化等现代大都市的必备元素,即使是以高层建筑自豪的上海的建筑设计及色调,在从东京回国的“海归”眼里也是不堪入目。所以中国的大都市往往是人口的大都市而不是现代意味的大都市。居住在这些大都市里的作家们又多是移民而非土著,往往是客者和主人的心态兼而有之,且不能深入城市的最本真地带,所以他们笔下的城市往往带有相当浓厚的个人化色彩。像贾平凹的《废都》,乡村的生活趣味和文化趣味溢满纸间,他笔下的西京与其说是“西京”还不如说是“西村”。
当作家的乡土文化情结和都市市民本来就有的乡村文化习惯一拍即合之后,自然就使相当多的中国作家笔下的城市带有极浓厚的乡土气息。而作家本身的乡土思维定势和对城市本真生活状态的疏离,又使这一类小说被纳入传统叙事话语之内而带有较浓厚的古典主义的想象虚构性质和平民性的理想主义色彩。
三、欲望化的叙事
如果说前邓小平时代的城市像一坐巨型城堡的话(中国务大小城市在城墙尚未被拆除的时代就是以城堡的形式而存在的),邓小平时代对人的欲望的肯定,则使旧城堡的城墙逐渐瓦解而渐具城市的品格。因为在城市里,人与人的关系决不会如城堡那样建立在政治关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新的商品化原则支配下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由于中国并没有完全建立起使商品化原则贯彻得相对彻底的公平的体制和制度,城堡瓦解为城市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城市小说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既无法摆脱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叙事母题,又因为和巴尔扎克截然相反的金钱观和卡夫卡式超越金钱罪恶的对人的物化、异化的关注而不再坚持巴尔扎克式的批判。当中国的文学超越道德标准从城市里嗅出物化和欲望的味道而进入到人心灵的最隐秘处时才离真正意味的都市小说近了。
由于哲学原点定位的通俗和批判否定精神及原创力的匮乏,中国作家即使急功近利也难以如巴尔扎克般汪洋恣肆,即使上下求索也难如卡夫卡般入木三分。因此当中国作家们将商业文明即都市文明作为小说的主体性内容进行放大性表述的时候,更多地描述的是商风吹拂下城市景观改变后的人欲横流的直观印象和体制与市场错位中人的无奈与挣扎。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初对市场经济的合法定位,从某种角度上说其实是在将人的欲望合法化。当聚居于都市的千百万人的欲望膨胀爆炸的时候,其冲击波之强大将是难以限量的,于是城堡色彩浓重的城市迅速波动起来,人们唯恐挤不进新富群类,暴发户式的和末世般的“十亿人民九亿倒”的飓风全面扩散,既垃圾飞扬又五色迷离。
最易点燃人暴富欲望而又最便于操作的致富手段自然就是炒股了。股票是都市的标签,是时代的徽记,是将复杂的商品化规则简化为几根曲线的心电图,是看不见的商海之风吹动起的欲望旗帜。然而在有着漫长的赌博史的中国人面前,炒股毕竟算不上什么新鲜玩艺。因此当股潮在都市拍打着无数窗口而翻起浪花的时候,它不可能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影响、改变并重新塑造都市人的生活方式、欲望结构和价值观念,毕竟它是已经深藏于许多人内心的东西。但旧的赌博方式一旦和大众广泛参与的现代性的投资活动相联系,必然会成为旧城堡的颠覆性力量,这对在道德净化的非商品经济环境下生活多年的人来说毕竟是一种未知的恐惧。李其纲的小说《股潮》给我们描绘的就是这种恐惧,它告诉我们合法性赌博是怎样破坏原有生态平衡而损害家庭的。小说虚构了董吉夫妇的故事,董吉夫妇因不甘心大学的清贫而双双下海。然而两个下海者的命运又是如此不同,一边是董吉在股市里被套牢,一边是秦玫在商界的如鱼得水。于是,为了弥合双方的心理落差和经济落差所造成的地位落差,秦玫不得不过着在公司奢华、在家里清贫的“双面人”生活。然而无论秦玫如何努力,董吉也知道他们已经是无法缩短貌合神离、日益疏远的情感距离了。在商品经济的丛林法则里,从来都是物质至上的。一辆不算高级的“桑塔纳”、几瓶不算顶尖的“高级化妆品”就足以解构多年的夫妻感情,于是物质力量的消长和货币关系的变动取代情感而成为人与人关系的新的纽带和人活着的原动力。
然而只有在都市小说进入人的更深层次的欲望化层面时才真正具备了“城市文学”叙事的穿透力,当作家们穿过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抵达个人欲望化的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时,现代品格的城市小说的叙事模式才算搭建完成,都市小说所呈现的城市景观才真正成为一个时代的镜像。
操练这种“欲望化”话语的大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和90年代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同步成长的生活在年轻都市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把脑袋连同身体一起变成感官去感受周围的一切,把触觉当作获取现代都市生活病态的快感和自身躁动的欲望和情绪的唯一方式。他们总是将自己的身体挪到城市中那些在他们心目中真正算作都市的部位,用他们自以为更真实的相对主义观念,即用当下而非历史的、实在而非真理的、欲望而非心智的、游戏而非严肃的、存在的而非抽象的价值尺度,去寻求彻底的快感和真实,他们认为这就是“现代化”城市的本质和魅力之所在。于是历史性思索的沉重被置之脑后,消费城市魅力的快感溢满纸间。对他们而言,都市只是一个穿越人生的通道,一个寻欢作乐的舞台,城市不是“家园”,他们从来就没有寻根的打算,也没有追问终极价值的诉求,更没有寻找家园的能力,所以他们所写的世相更多的是“正在进行时”的即时的焦虑、冲动和挣扎。他们只能在和城市欲望互为镜相的描述中捕捉物化的现实,他们没有理性的力量,只有燃烧的青春。在权和利操控下的现代都市消费性的物化空间是他们青春的燃料,消费性的物化空间又需要他们青春的火焰去照亮,或者说他们在互相消费,他们的小说就是对这种互相消费的欲望空间的表达。或者说这就是小说写作的“城市化”,一种城市化的文字行为,它们的出现构成城市化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尽管邱华栋曾经跟刘心武说过他是为了实现现世的世俗欲望而创作的,但邱幼稚的世俗欲望之于一个心智成熟的人显然是极其可笑的。在邱华栋那里,欲望不仅是文本写作的原动力,也是文本内真正的第一主角。邱华栋执拗的笔下,都市又开始重复几十年前新感觉派的老调,声、光、色、电又成了组合城市的最重要元素:装饰华丽的星级大酒店,琳琅满目的购物中心,横贯市区的丑陋的立交桥,熠熠生辉的豪华房车,散落于城市各处的酒吧、歌厅、舞厅,一切让人望而生厌而联想起低俗和罪恶的元素都被邱从城市的各个角落里挖掘出来,成了现代都市的新景观。一方面邱华栋对新的城市景观做着渲染,另一方面他又重复着巴尔扎克式的古老的批判,说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细菌培养基,只要有一点水和阳光之类的玩意儿,那些各种活跃的东西就呈放射状开始繁殖。”(《哭泣游戏》)城市“是一座欲望之都”(《手上的星光》)。在以欲望为原动力和小说叙述主体的邱华栋的小说中,占都市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市民是隐匿不见的,旋转在城市这个轮盘赌上的多是体制外彻底贯彻利益原则和快感原则的崭新人类:歌星、影星、画家、作家、制片人、公关人、时装人、直销人等。在这些人心里,物欲价值观似乎是唯一的,他们通过物欲的满足来把握世界,也通过物欲的满足来证明自己。利益优先或利益唯一的处世原则,意味着抛弃道德规范的物质主义的终极陶醉,这使得他们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成了一种只遵循丛林法则而后果殊难预料、追逐偶然或必然稍纵即逝和变幻莫测机会的博弈和冒险。这样,生活本真的意义自然被抽空,剩下的只是不可捉摸、充满戏剧性玄机的刺激性快感,这也就有效地转移了他们对自身行为意义的追问,将一切归结为行为本身单纯的当下体验。
如果说邱华栋小说的“欲望”化表达是体制外白领们将自己变成一颗色子在轮盘赌上掷得丁当作响的白日梦的话,那么何顿的小说写的则是同处体制之外的城市底层无业游民不甘人后,也欲从社会变革中抢一瓢羹的赤裸的疯狂。
在何顿的小说世界里,那些往日潜行在都市暗处的“个体户”、“自由民”被利益再分配变革的浪涌推上水面,在欲望的旗帜下用粗鄙的人生方式和商业方式重塑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新都市神话。和邱的小说比起来,何的小说无疑要更真实一些,因为它反映的是人被抽空一切内在意义只剩下金钱这一唯一价值取向时的显在事实。一旦理想成为虚幻,物质性的欲望就会轻而易举地突破肉身而进入心灵深处,而心灵层次的需求与满足是无边界的,这样物质化的欲望会迅速取代旧有的一切非功利性的人生理想而成为一个时代主导性的精神内容。因此《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中的何军的“现在这个社会只谈两件事,谈钱玩钱,人玩人”的人生信条就成为主导性的社会箴言。这样一来,何顿笔底的这些有着“案底”的“政治贱民”、“无业游民”和城市“自由民”,自然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一个时代极具代表性的精神画像。《太阳很好》中的龙百万、《我们像葵花》中的冯建国也就走上前台,有效地遮蔽了既往的工农兵、干部、知识分子等中心性的人物形象,又一次顺利地实现了小说主人公形象的大转换。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又是一个老旧的时代,因为这是知识分子头一次在公众面前失去思想力量和话语力量的时代,而物欲横流、道德崩坏的景象又似乎能在许多发黄的和不发黄的历史书页里看得到。于是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只有铜钿才能在人们的心头压出沉甸甸的分量;于是何顿笔下的小混混的“要心怀大财,发狠搞”(《我们像葵花》)就成为许多人心头最有力量的语言,于是末世般的景象出现了:到处都散落着混乱无序地寻找财富和捞取财富的人们,人消失掉了,只剩下金子在那里发光,每一个轻度污染的城市暧昧不明的上空都弥散着人形生物身上散发出的质量低劣的精神欲望。因为欲望并不能自由实现,所以无论对成功者来说还是对失意者来说,追求身外之物的行为过程,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能获得认同的行为过程,也同时成为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精神方式。这种拜金主义的理想显然已经代替原有的乌托邦色彩的理想。既然灵魂无需救赎也无从救赎,当何顿笔下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口袋扁扁的教师何夫沦落为一个腰包略鼓的票贩子时,无论是我们还是他自己,也还是能对这样的社会角色转换较为心安理得的。
在欲望化表达的城市小说里,作家笔下的世界跟现实世界是无分别的,是没有界限的。因为在这样的小说里,“有了快感你就喊”,快感取代了美感,痛苦消失,深度自然消失,平面化的叙事不再寻找新的精神出路,只剩下即时性和随机性的身体在那里翩翩起舞,小说和生活在那里作共时性的梦游。小说的制作更像是在生产物质产品而非精神产品,作为物质性的精神产品到底能走多远,则是有待大家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