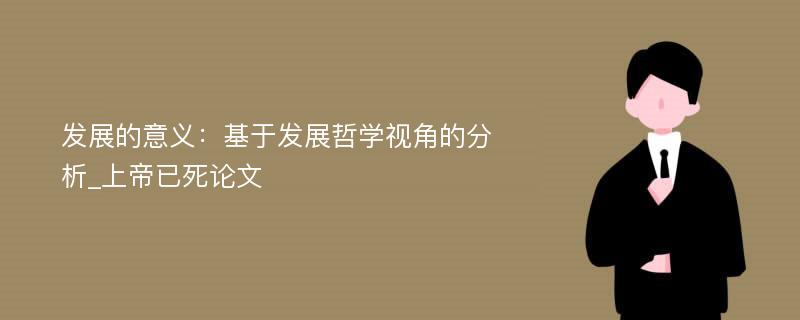
发展的意义:基于发展哲学视域的一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是一种追寻意义的社会性生物。人对意义的追寻直接体现在他所从事的发展活动中。当前,随着发展危机的加深和以人为本理念的确立,发展的意义问题日益突出。发展的意义是什么?发展的意义从何而来?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今天,为什么会出现意义危机?人们应当怎样追求一种有意义的发展?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正在埋头于发展实践的人们的思索和探究。
一、发展的意义
波兰哲学家沙夫在《语义学引论》中曾指出:关于意义的问题,的确是今天最重要的和在哲学上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不错,自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界对意义问题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如洛克、休谟、穆勒等人都曾专门论述过概念的意义,而自20世纪初以来,对意义的探究更是成了现代西方众多哲学流派所关注的一个中心课题。如分析哲学家把实用主义者提出的意义狭隘化为语词或命题的意义,而存在主义者则直接把人的生存意义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总之,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家对意义问题的普遍重视表明,以寻求真知为出发点的知识论哲学,已为以寻求意义为出发点的价值哲学所取代”①。
意义的传达和交流尽管要以语言为中介或载体,但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语言意义的来源和基础。也就是说,其一,相对于人的实践活动而言,语言意义还是第二位的。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②其二,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和蕴含着意义的社会性活动,它具有意义的自明性,这种意义人们可以不必借助语言的载体,而通过反思和领悟等的方式加以掌握,并通过观摩、欣赏等的方式进行交流。
发展哲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人的发展活动的“部门哲学”。人们对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变化这一特殊物质运动形式的探究,最后不能不归结到发展的意义问题上。发展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解读:“是什么”的事实性意义和“会怎样”的价值性意义。关于发展的事实性意义,是人们对社会发展包括某一具体的发展活动或发展模式的结构、规律、本质、属性等的一种事实性认识,这种认识是人们对发展进行价值评价和选择的前提。就发展的价值性意义而言,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细分。在形式上可分为两种:一是对从事或拥有该发展活动或发展模式的发展主体“自我”(“小我”)的价值意义;二是某一具体的发展活动或发展模式,在宏大的社会时空背景下,对“他人”即代内发展主体和代际发展主体(“大我”)的发展活动的价值意义。在内容上,发展的价值性意义也分为两种:一是发展的物的意义;二是发展的人的意义。发展的物的意义,主要是指发展所具有的创造物质财富、满足人的物质文化需求、改变人们所处的发展环境的贫穷落后面貌等的价值功能。发展的人的意义,是指社会发展在实现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平等发展方面的作用和价值,它是关于人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的意义。本文正是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谈论发展的意义问题的。
在关于“发展的意义”问题上,我们应该在认识上进行这样三种提升或超越:第一种提升要从发展的事实性意义上升到发展的价值性意义上;第二种提升要从“小我”的价值意义上升到“大我”的价值意义上;第三种提升要从发展的物的意义上升到发展的人的意义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发展的意义问题获得一种完整、准确和深刻的体认。
意义既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观当然要从人的角度探讨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及世界对人的意义等问题,同时它也是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发展观而言,传统的发展观的定义是这样的:发展观是人们关于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等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根本观点。这样的发展观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它所关注的只是发展观中的事实意义或真理意义,而没有交代发展观中的价值意义。因而真正的发展观应当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意义等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根本观点。没有意义内容的支撑,发展观无疑是不完整的。同样,没有意义的支撑和推动,社会发展将不成其为由人所主导的社会运动过程。如果说,发展观中既要探究社会发展的真理性内容,更要探究社会发展的价值性内容的话,那么,发展实践既要创造物的意义,更要创造和突出人的意义。
二、发展意义的陷落:一种最严重的发展代价
当前,人类正处于深刻的危机当中。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器物结构层面的危机,如日益严重的自然危机、社会危机等——包括生态环境问题、社会结构的失调、社会关系的不和谐等等;二是内在的精神层面上的危机——主要表现为发展价值的错位、发展方向的迷失、人在发展中的异化等。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固然积累了巨量的物质财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也有了巨大的进步,但精神意义上的空虚感和失落感却日趋严重。人类掌握了强大的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能“上天、入地、下海”,却不知如何善待同类甚至自身;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和丰富的影视作品在对人们进行着视听轰炸,却不清楚应该把社会和人的发展轨迹引向哪里?发达的通讯和交通工具在日益拉近着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却日趋隔阂和疏远;人们在卖力地营造和美化着自己的“物质家园”,但面对“精神园地”的荒芜却束手无策。总之,当代人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问题,都与意义危机有关,可以说,当代人所遭受的最大的危机,正是发展意义的危机。
自近代以来,人类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的两次重大的意义危机:第一次意义危机——“上帝死了”。在古希伯莱语中,上帝这个名词的意思是“来自天堂的人类”。从耶稣在巴勒斯坦创立基督教以来,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便持续了两千多年。但自近代以来,随着理性的复苏和人的主体性地位的进一步确立,这种信仰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于是尼采以振聋发聩的声音宣布:“上帝死了!”“上帝曾被认为是意义世界中的最高主体,它使一切事物都具有意义,人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用上帝的目光来理解事物的意义。”③人格主义者就曾认为,上帝是宇宙的人格,是“最高的创造理性”,上帝的意志是宇宙的基本法则,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以上帝为顶点的精神价值体系。现在,“上帝死了”,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崩溃了,而以这种信仰为基础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那些东西也随之坍塌,于是人们似乎陷入了可怕的信仰虚无之中,感到了焦虑、迷惘、荒诞、绝望和无意义。当然,尼采主张以超人来取代上帝。所谓超人,即具有“强力意志”而能将这种意志变成现实的人。“上帝已死:现在我们热望着——超人生存!”④尼采要通过超人这个拯救者,赋予这个世界以目标,通过超人战胜上帝与虚无。在他看来,那些“连上帝也没有解决的难题”,就让超人来解决吧,因为“超人是世界的意义”。于是,当人们把目光从“天堂”收回到大地上时,在日益强大的发展力量的支配下,人类逐步走上了一条睥睨万物、傲立尘世的“主宰者”、“征服者”的“超人”之路,这样,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又遭遇了第二次重大的意义危机。
第二次意义危机——“增长的极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以“自我”为中心,通过对生命规则和价值的重新立法与创造,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基础上,开启了一个张扬人的生命强力的自足自立的新时代。在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二战之后人类经历了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这也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时期”,人们普遍陶醉于经济增长的成就之中。正当越来越多的人沉浸于辉煌的物质文明成就之中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却发现了繁荣背后的隐忧、成就背后的问题。1972年,米都斯等人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在这本“70年代的爆炸性杰作”中,一些人对无视生态代价的“指数式增长”的旧有发展观念提出了挑战。米都斯等人认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⑤尽管“增长的极限”带有悲观论的色彩,但它对世人的警醒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面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及其加剧所导致的“增长的极限”的事实,人们终于发现了单纯的经济增长之路是一条走不通的“不归之路”。如果说,上帝之死,还只是人的精神信仰上的空虚化、无助化、恐惧化的话,那么“增长的极限”的出现,则有可能导致这样两种毁灭: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灭亡和人的生存与发展意义的毁灭。
当今人类正处于深刻的意义“毁灭”的危机之中。何以如此,因为发展中的人的意义已陷没于发展中的物的意义之中,“小我”的发展意义在严重排斥着“大我”的发展意义,而且,创造意义的方式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当今发展意义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们在发展实践中一味追求发展的物的意义,从而遮蔽了发展的人的意义。发展的意义何在?它在于物的创造和积累吗?或者说发展的意义是其创造物质财富的功利性意义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生产力不断进步、物质财富不断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为什么我们还面临着那么严重的精神信仰方面的问题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感觉不到人生的快乐和意义呢?可见,发展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或主要是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创造物质财富的价值。因为,发展中的物的价值并不是发展的最核心的价值,物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只是一种中介性、服务性的价值,在其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东西。这种更深层次的东西就是物的创造背后所体现的人的自由全面平等发展的意义,是人对自身自由和幸福的追寻,是人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或者说,发展的人的意义才是发展的本真意义、核心意义。在发展中,人的意义支配着物的意义,即支配着对物的意义的创造、评价和选择。但不幸的是,在现实中,人们选择了一条唯物质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使得人在现实的发展活动中被大大地异化和“矮化”,即在发展手段上人被异化为一种“工具人”,在发展目的上人被异化为一种“经济人”,同时,社会发展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冰冷、枯燥,甚至残酷追逐功利、满足人的本能欲望的过程。人们创造了财富,却感受不到创造的乐趣;人们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却体验不到进步的欢乐;人们“寻寻觅觅”,却发现自己被“冷冷清清”的压抑所包围,于是大发“凄凄惨惨戚戚”的感慨。当人的意义被物的价值所遮蔽,人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被发展的物化追求所销蚀的时候,这无疑是一种最大的发展意义的危机。
第二,将追求“小我”发展的意义凌驾于追求“大我”发展的意义之上,从而造成了“小我”发展的意义与“大我”发展的意义的严重对立和冲突。“小我”是局部的,“大我”是全局的;“小我”是具体的,“大我”是整体的;“小我”是眼前的或今天的,“大我”是长远的或明天的。我们既要关注和尊重“小我”的发展意义,更要关注和尊重“大我”的发展意义。由于发展主体是一种多样性的社会存在,发展活动具有横向的局域性和纵向的阶段性的特征,因而,对特定的“当事性”发展主体有意义的发展活动或发展模式,则不一定对其他的发展主体有意义;对今天的发展有意义的,也不一定对明天的发展有意义。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如源于西方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如果从世界范围内来考量,则不具有其价值意义的普适性。还有在当今发展实践中依然相当盛行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显然不能适应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遗憾的是,在现实的发展活动中,时常存在着为了追求“小我”的发展意义而损害了“大我”的发展意义的情况。例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发展模式之所以在当今世界不受欢迎,是因为这种模式将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价值利益置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利益之上,其弊端不仅在于实现利益的手段往往是对抗性的,更在于其意义的追求是极端利己性或自私性的。再以目下我们谈论较多的“大国崛起”为例,一个成功崛起的国家,应当是指成功地解决了自身和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国家。对于谋求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一个令人羡慕位置并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而言,这意味着置于国家战略首位的,不仅仅是对硬实力的追求,而主要是对软实力的追求,是对解决问题智慧的追求,一句话,是对自身所进行的发展的世界性意义的追求。“竞争着的国家,不仅仅是在进行一场实力的竞赛,更重要的是一场看谁能提出解决世界所面临重大问题的‘方案’的竞赛……所以说,一个追求领导地位的国家,一个追求崛起的国家,应当把创造性地解决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作为第一位的战略目标——为世界指出一条出路,为人类指出前行的方向,为国家找到和平共赢的战略”⑥。可见,只有既对“小我”同时也对“大我”有价值意义的发展模式或发展活动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也是值得提倡、普及和传承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平发展的主张等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较大的反响或广泛的响应、追求,是因为它们对“小我”和“大我”都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蕴含着解决世界性重大发展难题的独特智慧。
第三,人们对发展意义特别是对发展的物的意义的创造采取了一种不合理的高代价的发展模式,从而加剧了发展的意义危机。迄今为止,人类的发展模式在总体上讲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尽管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进步,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实现了人的阶段性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发展代价问题,而一系列代价的频繁发生,不仅加剧了社会发展物化追求的消极后果,更使人们在日益严重的发展代价的重压下,对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正当性产生了疑问:人们孜孜以求的发展活动,会是这样一种状况吗?社会发展的真正希望和出路在哪里?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发展代价和步履维艰的发展进程,人们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这其实正是一种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支撑的表现,是一种找不到应有的方向感的表现。物欲横流的社会似乎变成了一架发了疯的钢琴,而人们则在混乱嘈杂的音响的冲击下晕头转向。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有疑问的;他不再知道他是什么并知道自己不知道。由于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由于自己有疑问,因此,他以无比的忧虑研究他自己的意义和实在,研究自己来自何方、走向何方”⑦。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世界“唯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⑧。
三、追求一种有意义的发展
总之,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所谓意义危机,既是旧发展阶段所固有的局限性的显现,也是人们谋求新的发展的一种转机和起点。或者说,意义危机的出现,表明人类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转折点上。
寻求和创造发展的“意义”,对人类的发展活动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第一,是否有意义,是社会运动区别于自然运动的根本所在。在物质世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发展形式,即自在形式和自为形式。“客观过程的两个形式:自然界(机械的和化学的)和人的有目的的活动”⑨。列宁的论断表明,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属于两个不同系列的发展形式:自然运动是一种自在形式,社会运动属于自为形式。所谓自然运动的自在性,即自然运动按照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在进行着一种无意义的自发的、盲目的过程。而社会运动的自为性即表现为一种“意义性”。“意义”只能是属人的概念。美籍著名犹太教哲学家赫舍尔指出:“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做人所固有的。正如空间的向度对于恒星和石头来说是固有的一样。正像人占有空间位置一样,他在可以被称作意义的向度中也占据位置。人甚至在尚未认识到意义之前就同意义有牵连。他可能创造意义,也可能破坏意义;但他不能脱离意义而生存。人的存在要么获得意义,要么叛离意义。对意义的关注,即全部创造性活动的目的,不是自我输入法的;它是人的存在的必然性。”⑩这就是说,在社会领域由人所主导或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活动,当然也是一个追求和创造意义的历史过程。正因为有了人并为了人,社会发展才恒久地闪耀着意义的光辉。换言之,人们在发展实践中所创造和追求的东西,绝不仅仅是物质功利性的东西,而是物质功利性的东西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提升和人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可见,从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相区别的角度分析是否有意义,应当是区分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根本标志。
第二,是否有意义,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或标准。“意义”是发展的“灵魂”,是一切发展活动何以进行或为何进行的根本所在。对意义的追求和创造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离开了意义世界作参照,人们的发展活动就无法被准确地评价和理解。而一旦以意义世界作参照来进行考评,人的发展活动立即会显现出其完美性或不足性。换言之,意义世界为人们认识和评价社会的进步程度、文明程度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平台”和“视窗”,人们能通过这个“视窗”发现社会发展的完美与否、先进与否。以往人们总是从物的进步程度来衡量社会的进步程度,这固然不错,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物的标准只是一种非常狭隘和低层次的标准,它无法真正担当起衡量社会是否进步的刻度的重任。如前所述,即使在社会产品有了极大丰富、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的情况下,依然发生了严重的意义危机。可见,物的创造只能给意义的生成提供物质基础,但它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的意义性。只有发展中的人的因素——具体说是社会发展所实现的人的意义的因素,才能真正成为衡量社会是否进步、社会发展是否正当或合理的根本标准。
第三,追求意义,是人们进行发展选择和发展创造的深层根据和最高目的。在发展中,人们会经常反思和追问,什么样的发展活动是人们应该追求的,而什么样的发展活动是应该予以拒绝和回避的。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必然要涉及意义问题。饥饿的动物看见食物当然只知道吃,而人则往往要在弄清食物的意义之后才做出选择。在社会发展领域,人正是通过意义或依据意义来从事发展活动的。人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发展活动而不选择那样的发展活动,完全是不同的发展意义使然。换言之,人们在发展实践中所进行的选择活动,如选择新的发展观、新的发展战略、新的发展模式、新的发展道路等,其背后的根据就是发展的意义,即人们是根据不同的发展意义或基于不同的发展意义来进行选择的。旧的发展模式包括发展观具有物本论的意义,这样的发展意义非但不足以支撑新的发展活动,而且造成了发展的困境和危机。新的发展模式包括科学发展观等具有新的价值和意义,它的宗旨是以人为本的,是为了人、实现人、从人的发展目的和需要出发的,因而具有了新的意义。这样一种具有着新质或新的意义的发展模式,能真正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因如此,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发展,已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人不可能长久地容忍发展意义的陷落。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在发展领域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和创新,都与对发展意义的拯救有关。总体而言,对发展意义的拯救,应沿着这样两条逻辑进路展开:一是实践创造方面的,一是审美观照方面的。
在实践创造方面,要求人们所从事的发展活动,在价值论的视域要倡导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突出人的意义在发展意义创造中的主导性作用和主体性地位;在实践论的视域要走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的道路;在代价论的视域要将发展意义的创造和发展代价的克服有机地统一起来。为此,必须要实现由高代价的发展模式向低代价的发展模式的转变。高代价的发展模式是指代价的付出大于或等于社会之进步,从而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发展问题,包括发展意义危机的发展模式。高代价的发展模式奉行和实施的是物本论的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从而将人的意义陷没于物的意义之中;它把“小我”的发展意义的追求绝对化、极端化,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当代人与未来人的发展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高代价的发展模式,才造成了当今发展意义的危机。因而,从发展意义的角度分析,这样的发展模式是没有生命力的,是不可能适应人类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的,因此也是必须予以摒弃的。低代价的发展模式,是一种以最少的投入和付出,最小的风险和危害,以及适宜的发展速度,而获得最大发展收益的一种发展模式。低代价发展模式高扬“以人为本”的发展大旗,它将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将“小我”的发展与“大我”的发展统一起来,将创造发展的意义和消除发展的危机统一起来,从而蕴含着解决发展难题和升华发展意义的价值功能。这样的发展模式为我们消除发展的各种危机,特别是发展的意义危机提供了可贵并有效的实践路径。
发展意义不仅在创造中生成,而且要在审美体验中发现和领悟。从审美的角度分析发展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物质财富、改变落后面貌的功利价值,更具有促进人的身心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审美价值。因而,对发展意义的发掘和领会,离不开审美观照的途径。
对发展的审美观照是以发展中所潜藏的审美意蕴为基础的。审美活动存在的理由在于,发展实践深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而表现出的直接有限目的性与发展理论活动的间接有限目的性,同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之间的巨大差异。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平等的发展,使人过上一种自由幸福自主的生活。在根本的价值追求上,人类的全部发展活动都是为了这一终极目的而进行的。但这种终极目的的实现,总是表现为一种客观、渐进的具体历史过程。发展实践是以实在的、基本上是“经济化”的方式去实现这一目的的,这就使得发展实践因其客观性、受动性从而表现为一种有限性的活动,即它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实现在本质上具有无限性的终极目的。人的全面自由平等发展的无限性和发展活动的有限性是发展实践中的一个巨大的矛盾。社会发展的理论建设活动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发展实践的直接有限性,但这种超越是以抽象化的方式进行的,而且,在发展实践中,发展理论只是作为一种实现发展目的的手段或工具而起作用的。这表明,发展的理论认知活动本质上作为一种“工具理性”之运作,也是与社会发展所追求的具有无限性的终极目的相矛盾的。
笔者认为,如果说发展理论属于一种“工具理性”的话,那么,发展的审美观照就是一种“意义理性”,它主要是作为一种发现、体验、审视发展之价值、意义而起作用的。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发展中的审美活动象征性地消除了人类发展的无限目的性同发展实践与发展理论建设活动之间的巨大差距,消解了有限目的和无限目的之间的矛盾,使人由追求物质需要满足转向了追求人自身才能的自由发展,使人在现实的发展实践中未能充分发挥的自身才能象征性地发挥出来。在这里,发展的审美活动,除了具有对人的审美需要的直接满足的功能以外,还具有将人从繁重的“物役”和沉重的“肉身”中解脱出来的功能,体现了“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黑格尔语)。它能使整个发展进程更多地向人的心灵感悟和精神享受层面倾斜,表现为在创造丰盛、繁华的物质世界的同时,也更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其二,社会发展的真谛、价值、意义只能通过审美活动才能捕捉和掌握。当我们凝视或端详着我们的发展创造及其成果时,看到发展客体在我们的发展实践中变成了我们所希望的一种理想的发展存在,那么,我们就会油然生出一种意义感、自豪感。这种意义感既是针对发展实践的——是对人的发展活动的一种肯定和赞美,更是针对发展主体的——它使我们感受到了作为发展主体的价值和意义。在这里,发展的审美活动具有挖掘和显示社会发展之价值和意义的功能。长久以来,由于高速前进的历史列车没有被凝视、欣赏、品味,社会发展的愉悦性没有被充分地感受到,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也没有充分地展示出来,因而,当今的人们尽管做了很多事,尽管在物质上很丰裕,却常常感到没有意义,感到空虚和无聊,感到迷茫和痛苦。为此,在创造历史的舞台上忙忙碌碌的人们,应当从纯功利化的追求中解脱出来,通过休闲审美等的活动,以一种闲情逸致,感受和认识正在从事着的历史创造活动。“慢慢走,欣赏啊!”人们只有驻足观赏和细细品味时,才能真正窥见和领会社会发展的美妙和真谛,领略到人作为发展主体自身所具有的本真价值。
注释:
①俞吾金:《迈向意义的世界》,《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③秦光涛:《意义世界》,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④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尹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页。
⑤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李宝恒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⑥张剑荆:《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⑦米夏埃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张乐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⑧维克多·奥辛廷斯:《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徐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
⑨《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⑩赫舍尔:《人是谁》,隗仁莲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