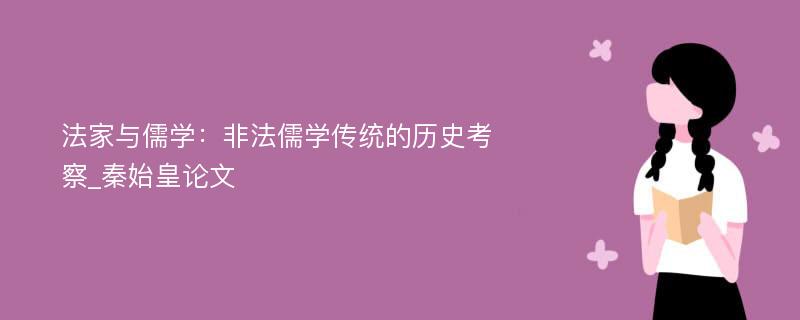
法主儒從:韓非法儒思想傳統的歷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法主儒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是針對會議論題之一“韓非子思想的政治實踐及歷史命運”而提出的。韓非的法治思想提出了一個法主儒從的框架,而形成後世政治結構以及法典編纂的思想傳統。然而,歷史没有給韓非法治思想公允的評議,從李斯、秦始皇到漢武帝以至歷代黄帝,都没有尊重韓非的知識産權。正如明趙用賢《韓非子書序》:“三代而後,申韓之說常勝;世之言治者,操其術而恒諱其迹。”①世人多以儒評法,或間有肯定其實用處,但多是偏頗不全。
韓非集商鞅、申不害、慎到之法、術、勢的優點,對其短處加以批評、增益,而成爲法家的集大成者。這是没有疑問的。
本文要提出的是,集法家大成的韓非,其法治思想是容儒的。我是從法主儒從的法儒融合的角度來探討韓非思想,這和一般單純把韓非作爲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或認爲《韓非子》書中有儒家思想的篇章即非韓非所作的論點,有所不同。
由于容儒,韓非法治思想可以定位爲“法主儒從”。而這一“法主儒從”的容儒思想格局對中國以後的政治結構、甚至法律有深遠的歷史意義。這“法主儒從”的思想格局因爲其策略符合中國歷代專制政權帝王、甚至當今政治家的需要,成爲中國政治、法律思想的傳統。
“法主”是統治、治國、制民的不變道理,“儒從”則可以利用儒家在中國文化的深厚歷史根基,標榜其正統性。處理得好,可以中和法的嚴厲、無情甚至苛酷,我所來自的國家新加坡曾經如此。新加坡的法律嚴明,治安良好,這是衆所周知的。新加坡的法律思想與韓非絶無任何關係,但是政府在八十年代曾經推行的儒學運動,以及民間細水長流、一步一脚印的堅持下,“儒從”的角色,有助于優雅、關懷的社會。
在歷史的考察上,本文是以秦政和《唐律》作對照,以見兩者都以“法主”爲主調,不同在于“儒從”的角色:秦政是“法主深刻,儒從不顯”,《唐律》則充分利用“儒從”的地位,粉飾“法主”,讓作爲帝王之具的“《唐律》冠上“德禮爲政教之本,刑罰爲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②和“仁恩以爲情性,禮義以爲綱紀,養化以爲本,明刑以爲助”③的美名。
一、反儒的歷史階段
反儒是被認爲韓非思想的特色之一,這是正確的;論者有以儒的成分作爲辨別《韓非子》篇章真僞的根據。我認爲,韓非的反儒,是有其一定的局限,歷史階段是其中一個必須考察的環節。
韓非本著他對歷史的洞察,將歷史分成上古、中世與當今三個歷史階段④,並在“争于力”的“當今”這個歷史階段,提出了反儒論證。這就是他的异變機制:韓非的异變機制是“世异則事异”、“事异則備變”。⑤事是時代的事件、事實,備是指應對事件、事實的方法、設施。事是因世而生,應對事的方法、設施必須適合于所應對的事;由于事件的不同,措施與應對的方法必然隨之而變,所以韓非又說:“事因于世,而備適于事。”⑥所以他認爲“當大争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⑦由于“古今异俗,新故异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⑧
韓非直接指出“當今”所處的歷史階段的內容是“争于力”,在這個争于力的歷史階段裏,韓非有生之年一直目睹祖國韓國受到侵略的殘酷事實,對“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于人,故明君務力”⑨有深切的體會,而有以下的論點。《八奸》:“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强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⑩《五蠹》:“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强者能攻人者也,而治則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責于外,內政之有也。”(11)
不論是國際關係或是治理人民,都不能用不適合于這一歷史階段的德治的方法與措施來處理,《顯學》指出:在國際關係上,“當今争于氣力”之世,强者能攻人雖然不義,只要國强力多必能使他國入朝。對內治民方面,道德已經失去止亂的作用,必須代之以威勢來禁暴,使人不得爲非。人民之中雖然有不恃賞罰而自善之民,但是人數畢竟太少。治民所考慮的是使全體人民不得爲非犯法,而不是少數的自善之民所以韓非主張不行德治而行法治。(12)
處于“争于力”的“當今”的歷史階段的韓非,儘管承認在上古競于道德的時代,曾經有過德治即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禹修教服有苗的事實。(13)但那不是“當今”的事。面對“當今”的歷史階段,韓非的异變機制所提供的應對方法是實行法治,不能實行與這歷史階段的內容不符合的德治。
二、反儒的局限
在韓非反儒的“當今”歷史階段裏,我們也必須留意韓非爲何反儒?所反何儒?可以肯定的是韓非不是從學理上反儒,也不是從純道德意義上反儒。他是從儒在“當今”這個歷史階段的對治效用太小、“當今”儒者的妨礙法治的推行以及儒者對法治的挑戰而論。這即是韓非反儒的局限。
(一)德治在“當今”歷史階段的對治效用太小
德治之所以不能用于“當今”之世,是由于它的效用極其有限;而法治的效用則是無限的。韓非在《難一》指出:在不屬于“當今”的歷史階段的舜的時代,舜行德化,花了三年的時間,只糾正了三項過錯,效果何其有限,更何况是在“當今”的歷史階段。如果,在“當今”的歷史階段實行法治,利用“賞罰使天下必行之”,“十日而海內畢矣”(14),就能够達到必然與普遍的强制效果。兩者相比,真是天淵之別。《五蠹》也說:在“當今”之世,人民絶大多數是“固服于勢,寡能懷于義”與“驕于愛,聽于威”(15),所以不能實行仁義德治。因此,《顯學》在指出在當世“力多則人朝”、“明君務力”、“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厚德不足以止亂”後,又從重視在“當今”之世的治國功用上指出“言先王之仁義,無益于治”(16),要“明主舉事實,去無用,不道仁義”,“不聽學者之言”。(17)不道仁義、不聽學者之言即是從洞察争于力的當世之事實而言。
(二)反對當世之儒者
在“當今”争于力的歷史階段裏,韓非所反之儒是當世之儒者。他把當世之儒者視爲五蠹之一,以下引文都是以當世的儒者爲反對對象的。《顯學》指出:不面對現實的當世儒者,在游說人主時,不針對“當今”治國所應實行的方法,只是儘量誇大過去的治國功績、遠古流傳的美譽及先王所成就的功業,並吹噓以此可使人主王霸天下。(18)《奸劫弑臣》則說:假如人主不依憑必勝的權勢,聽信當世儒者的游說實行仁義惠愛,則不但不能王天下,甚至小者地削主卑,大者國亡身死。韓非所强調的是“察其實”,即要人主洞察“當今”争于力的事實,而實行法治,不要爲仁義的美名所迷惑。(19)《六反》再次指出:“當今”之儒者不瞭解當世的實際情况,稱引典籍中歌功頌德的言語,主張輕稅賦、輕刑以治國。韓非重視當世的實事,直指“當今”學者的錯誤。“當今”的明主,必須要明察當世之實事,根據“當今”异變的事物采取適當的應對方法,“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禄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20)這即是韓非的“事因于世,而備適于事”的异變應對原則的具體做法。
(三)儒者擾亂與挑戰法治
從韓非的反儒言論中,可以明顯看出他之所以反儒是因爲當時儒者的言行妨礙了法治的推行。法治的實行是“當今”務力的君主治國、富國與强國的必然途徑。當世之儒者不知世務、不面對現實,妨礙法治的推行,疑惑君主推行法治的决心,必然是韓非攻擊的對象。當世之儒者游說人主,固然可以動搖他推行法治的决心;然而,儒者最爲韓非所抨擊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擾亂法治。《五蠹》指出:儒、俠都是法禁的破壞者,都是韓非所反對的。在此,韓非雖然兼反儒、俠,但以反儒爲主。對于犯罪而應受罪者,儒者卻以文學而加以取用;儒者雖有這種以文亂法的做法,但卻爲人主所禮遇。儒者以文亂法,即是對法治的直接挑戰,所以韓非以“害功”與“亂法”反對人主稱譽修行仁義者及録用工于文學者。(21)《問辨》强調:在明主治下,法令應該是最具權威性的;然而處于亂世,法令卻受到人民以文學與私行給予挑戰。韓非認爲法令具有最高權威,不容人民以言行非議與違反,人民以文學非議、反對法令,必然不爲韓非所容。(22)《五蠹》以“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積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23),列爲亂國之俗的首位。學者以儒家仁義與先王之道質疑當今之法令,並動搖人主實行法治的决心,必爲韓非所大力反對。
韓非從現實的功利立場,認爲儒者不參與耕戰,無益于富國强兵。實行法治是爲了達致國富兵强,然而儒者的言行以及人主禮遇儒者的後果與法治所欲達致的目標相違背。《外儲說左上》記載王登薦用儒者爲中大夫,以致中牟地方有一半人民放弃農耕,嚴重影響農業生産力,而爲韓非所反對。(24)凡是無利于農戰者,韓非一概加以攻擊。《顯學》(25)、《八說》(26)認爲即使是儒墨的創始人孔子與墨翟,以孝稱著的孔門曾參,或是作爲正直典範的史魚,由于他們不參與耕戰,便對國家無得、無利,而不符合人主的公利。
法治的實施與所要達到的目的,正如《五蠹》所述:“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以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于法,動作者歸之于功,爲勇者盡之于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强,此之謂王資。”(27)
以上是對韓非反儒的歷史階段與內容加以規定說明,這也是韓非反儒的局限。在這個局限之外,如上古的德治,作爲純道德概念的儒之道德,不妨礙法治的儒者以及可以被法治思想所利用的德目,都不是韓非所反對的。更重要的是,儒思想的産生是春秋以前歷史文化長期積累的結果,它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深厚的社會基礎。韓非自己也指出儒學即是當時顯學(28)之一,他的反儒即是在傳統的主儒思想的社會背景中提出的。
三、韓非歷史哲學所隱藏的下一個歷史階段
韓非認爲歷史有不同的階段,是可變化的,所以從他所說的三個歷史階段來看,應該還有一個未來的階段。這個未來階段韓非没有說出,我們從他以“争于氣力”作爲“當今”這一歷史階段的特徵看,下一個階段應該是在“務力”、“務法”,實行法治,達致富國强兵,甚至稱霸天下之後的階段。這應該是無人與争的時代。
然而,韓非主張法治,要確保絶對君勢的鞏固、持續,如何處勢、行法、用術,都不可能以德治或是仁義來達成。即使是在天下統一,在不必“争于氣力”的時代裏,也不可能完全實行德治。根據“古今异俗,新故异備”(29)的原則,統治者在下一個歷史階段所應采取的措施將根據其歷史內容與特徵而定。這便爲儒在韓非思想中提供回流的餘地,也爲法儒的進一步兼容提供空間。
在“當今”之世的歷史階段裏,韓非一方面肯定上古有德治的時代,另一方面又在不涉及政治的純道德概念上,對儒的道德有深切的掌握,同時也將儒的德目運用到他的法治思想中。由此,我們推論在天下統一的歷史階段裏,儒的一些不違反法治的內容,將更有發揮政治功效的餘地。《安危》云:
使天下皆極智能于儀表,盡力于權衡,以動則勝,以静則安。治世使人樂生于爲是,愛身于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争鄙起。(30)
周勛初從韓非對孔丘的不同評價來推斷韓非作品的年代,認爲《安危》把孔丘作爲智者的典型而加以肯定,或是韓非早年的作品。(31)鄭良樹也贊同周氏的推斷,認爲《安危》是韓非尚未獨立門戶、尚且崇敬儒家的早期階段的作品。(32)如果我們瞭解韓非法治思想可以容儒,只要屬于儒的人物不違反法治,或能爲其法治思想所利用,當爲韓非所容;那麽,《安危》可以是韓非的作品,而且不必是韓非早年的作品。《安危》裏所謂的天下是天下統一的構架,韓非在此描繪了一幅“社稷常立,國家久安”的治世美景。天下百姓都在國家法令的規定範圍內充份地發揮智慧、才能和力量。對外有戰事則能得勝,對內治國則能使國家安定。在這樣的法治社會裏,人民樂生于爲是,愛惜自身而不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國家長久存在,永遠安定。韓非由此歸結到行法令而使國家安定,然後纔有道德可言,而危亂則産生争奪與貪鄙。“奔車”與“覆舟”都是國家危亂的比喻,孔子、伯夷則代表智廉,危亂與智廉兩者不會同時存在。
在這樣一個時代裏,儘管是法主儒從,“儒從”絶對可以顯出。
四、秦政:法主深刻,儒從不顯
根據韓非的歷史變化論,秦始皇的統一天下應該是“争于力”之後的另一個歷史階段。這是在“争于力”階段之後的大一統。以韓非的歷史哲學來說,世异則事异,事异則備變,應對統一的國家的新時代與新事物,其處理與應對的方法必然有所不同。從韓非在《安危》所勾畫出的法治之後的美景來說,應該是“儒從”顯出。
然而,秦自孝公起力行法治,秦政在秦始皇對韓非思想的偏好、竊取韓非思想而不知异變的李斯和通于獄法的趙高的主理下,對于韓非的容儒,特別是韓非的异變機制與容儒的配合,並没有體現,而造成主法深刻,容儒不顯的傾向。秦是以韓非思想作爲政治指導的,李斯作爲學習比韓非差的同學,在以韓非思想實行于“争于力”的秦統一戰争中是成功的,因此,Derk Bodde稱李斯爲中國第一位統一者。(33)秦政的措施,是歷史階段的錯位,即秦始皇、李斯將韓非在“争于力”時代所創建的思想用于統一的秦朝。
(一)法主深刻
秦始皇自稱爲皇帝之後,把國君獨尊的地位提高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命爲制,令爲詔”(34),皇帝的命令成爲國家的法律。他把相權與國家的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都集中到自己手裏,形成一種君主一個人所全部擁有的絶對權力,不能與臣下共有,這即是李斯所說的“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35)在另一方面,君權却不受任何約束與限制,正如李斯對二世所說的“主獨制于天下,而無所制也”。(36)
《史記·秦始皇本紀》:“聽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陽宮。”(37)又記載侯生、盧生語對秦始皇的批評:“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天下之事無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38)《漢書·刑法志》:“秦始皇…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决事,日懸石之一。”(39)
這是對于韓非的法與術的運用,也與韓非的權勢不可借人、威勢不可與臣下共同使用、不與臣下共賞罰及獨斷的理論是不謀而合的。
秦始皇,甚至秦二世,都是以韓非的法治思想作爲政治指導以完成其法治。在本文所說的主法容儒的架構中,絶對屬于主法。其主法深刻是從秦始皇以韓非絶對君勢論完成其徹底的中央集權與君主專制而言,秦始皇的法治與獨斷,也即是用法術作爲工具以鞏固君勢的實際應用。至于專任刑罰,只是韓非嚴刑義的極端應用,更見其主法深刻。
(二)秦儒不顯
秦始皇治下儒學不顯,究其原因,有其歷史傳統的因素,也有其現實政治的考量。從歷史傳統而言,又與其地理環境有關。秦國地處西陲,相鄰多是戎狄政權。秦長期在戎狄的影響下,形成不同于中原的文化傳統。在傳統上,秦没有嚴格的宗法制,君位繼承不分嫡庶,道德觀念相對薄弱。到商鞅變法之時,猶行“戎狄之教”(40),商鞅變法使國力富强,但卻没有徹底提高倫理水平。
歷史固然如此,更重要的是在環境現實政治環境中失去使儒顯出的契機。
先是《呂氏春秋》不爲秦王所用。《呂氏春秋》中的某些儒家思想原本是可以作爲秦始皇以法家,尤其是韓非思想爲基調下的治國參考;果真如此,則儒在秦治下,當有顯發的空間;問題是《呂氏春秋》不爲秦始皇所用。《呂氏春秋》不爲秦王所接受,呂不韋的個人因素最爲重要。他是秦始皇父親莊襄王時的丞相,封文信侯。秦王政即位後,呂不韋被尊爲相國,號稱仲父。在公方面,他是相國,秦王親政前權勢是操縱在呂不韋手中;在私方面,他是秦王的仲父,又與母后私通不絶;呂不韋安排嫪毐與母后淫亂,又幾乎釀成奪權政變。對于呂不韋這個“生害事,死傷名”(41)的人來說,秦王是不可能用他所編纂的書的。在實際政治環境中,因人廢書是不變的真理。
李斯將分封制與師古錯誤對等。秦始皇二十六年(42)和秦始皇三十四年(43)的兩次廷議,尤其是第二次廷議,儒者博士所提出的分封制,被李斯誇大,推至極端,導致焚書的文化浩劫,使秦儒没有了回轉路。從廷尉晋升至丞相的李斯,利用秦始皇反對分封的前例,在廷議上通過焚書令,以作爲焚書、禁私學的法律根據。李斯從歷史的發展來否定分封制是正確的;但是,他的推論則是錯誤的。李斯以三代之事不足效法,是以分封制偏蓋三代之事;他將古時亂的根源歸咎于私學,是牽强的說法;他認爲學古即是非議當世與疑惑人民,聯繫薄弱;他以私學與法教(44)相違背而將兩者提到對立的層面,危言聳聽地指出私學危害君勢,更是片面的說法。就是這一切導致一個簡單的師古分封的建議竟然引起焚書的文化浩劫,也斷絶了使儒在秦政顯出的契機。
任用博士,但不重用。據《史記》記載,秦始皇時有博士七十人(45),二世時有博士三十人。雖然秦博士不全是儒生,但是如伏生、叔孫通是必然屬于儒者。儒生博士在秦朝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議政,二是文化、禮儀諮詢。儘管如此,儒者所扮演的不是重要的角色。秦始皇及二世對于儒者的意見,不論是議政或是禮儀,大多是不被采納的。這是另一個秦儒不顯的事實。
五、《唐律》儒從顯出,標榜義勝
韓非之書,是歷代政治家所樂讀,其術更是他們所樂用。韓非之術,應用之妙,存乎一心,歷代專制皇帝自有其獨特的領會。
韓非說:君無術則蔽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46)從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所看到的《秦律》、漢承秦制的《漢律》,到體制完整的《唐律》,以及其後延續、擴充的《明律》、《清律》等,可以明顯看出韓非“法主儒從”的思想格局所體現的本質與特點,一直被承繼著。帝王爲了掌握這帝王之具,都致力于編纂法典。無它,因爲法典不但包涵了韓非的“法”和“術”這兩種控制臣民的工具,爲這兩種工具的唯一服務對象――帝皇的權勢、權位與權力,提供了絶對的保護、保障與擴張;尤爲絶妙的是,在“儒從”顯出的操縱下,作爲帝王統治工具、保障帝王至尊地位、嚴苛無情的法典,在德、禮的標榜下,至少以《唐律》而言,被視爲是體現儒家思想的法典。因此,《四庫全書》說:“論者謂唐律一準乎禮,以爲出入得古今之平”(47),研究《唐律》者都遵循這點,認爲禮是《唐律》的真髓。(48)
《唐律》的法主,表現在它以維護君勢爲中心,屬于韓非的法與術的內容都以法典的形式,統二爲一,爲國君的統治臣民,提供工具性的服務。法典的內容不但包括了屬于法的部份,如罪行與刑罰,更包括了韓非的術的內容,尤其是應用了他的治吏與禁奸術。所以說,《唐律》所體現的正是韓非以勢爲中心,以法術爲工具的思想。《唐律》的內容雖有儒家思想成份,却是屬于從屬的地位。(49)
《唐律》在維護君勢表現在將皇權法律化、嚴厲制止危害皇權統治的行爲及保護皇帝人身安全上。其中,“十惡”中的首三大罪謀反、謀大逆、謀叛都以“謀”爲名。單說謀反,是預謀危及皇權統治的罪行,律文對謀反罪的刑罰適用于“其事未行”及“不能爲害者”,刑罰最爲嚴厲,都是斬,還有廣泛的連坐。正如《唐律疏義》對于謀反的刑罰適用的說明是:“謀危社稷,始興狂計,其事未行,將而必誅,即同真反”。(50)這是將還未付諸實施的準備階段的預謀與真反一並定罪,即是也要在犯罪實施階段之前將罪行禁止的表現。這三大罪行都以“謀”爲名。從刑罰適用來說,三者都包括“未行”的罪行。《韓非子·難三》說:“明君見小奸于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于細,故民無大亂”。(51)大謀、大亂都是指著對君主叛變而說的,能够在細微處見到犯罪的苗頭,並在犯罪實施的階段前加以禁止,人們便無法進行危害皇權統治的罪行。從維護皇權統治的法典而言,謀反、謀大逆和謀叛,都是大謀、大亂的罪行。從《唐律》對這三大謀罪所規定的刑罪及其刑罰適用來看,其主要目的是要在犯罪實施的階段之前,包括犯罪的準備階段,甚至犯罪的動機上,加以禁止。韓非的禁奸理論與法典中的謀罪的確有內在的理論關連。
(一)以禮顯出“儒從”
儘管《唐律》是以維護、保護君勢爲最高目的和主要內容,是本文所謂“法主”的要點。然而,“儒從”的顯出,却發揮積極的作用。
《唐律》和其他法典一樣,總是把謀反總是第一大罪,刑罰是最爲嚴厲的。在說明謀反罪行時,是引用儒家經傳,將皇帝置于至尊地位,有君權天受的用意,以使謀反罪所定下最高的刑罰有其合理性。《唐律疏議》在解釋謀反罪時,律疏引用《公羊傳》的“君親無將”作爲理論基礎,認爲皇帝奉天寶命,爲人民之天地父母,作爲子臣者,只能以忠孝事君,絶不能起逆心;否則,既背天常,又反人理。(52)在這樣的論述下,國君的地位自然高高在上,與臣民间有一不可逾越的界限。從皇帝的至尊地位,以說明即使是“將”也須科以極刑的合理性。
在此,禮在法典中就發揮了維護君主的至尊地位的積極作用,這是禮爲韓非的“勢”用。而這貌似儒家的禮其實只是韓非的禮。韓非的法治思想以君勢爲中心,他所重的禮是君臣之禮,這君臣之禮是單向的,是嚴格區分君臣之別,要求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53),只規定臣下對君上的責任,而没有君主對臣子的義務;這與儒家對君臣關係的雙向規定所不同。我們這樣來對比法典中以禮尊君的內容,就可以斷定法典以禮維護國君的至尊等級是主法容儒的格局。
禮作爲加强維護皇權的理論,更見于《唐律》。《唐律疏義》在“十惡”的“謀反”條下引“《周禮》云左祖右社,人君所尊也”;其目的是爲瞭解釋律注稱“謀危社稷”,因爲“不敢指斥尊號,故托云社稷”。(54)在謀大逆條下也引“《周禮·秋官》正月之吉,懸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人觀之,故謂之觀”。其實,這只是要解釋《爾雅·釋宮》所說“觀謂之闕”。《爾雅》釋“闕”只是適用于律注對“謀大逆”條下“謂謀毁宗廟、山陵及宮闕”中的“闕”字的解釋。(55)《唐律疏義》迂迴曲折,引禮以加强維護皇權的理論,可謂用心良苦。法典以禮維護國君的至尊等級,可見一斑。
禮成爲尊君的工具在法典的“大不敬”罪名中最能表現。《唐律·名例》“十惡”條有“不大敬”,是七種罪名的總稱,這七種罪名是:盗大祀神御之物、乘輿服御物;盗及僞造御寶;和合御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誤;若造御膳,誤犯食禁;御幸舟船,誤不牢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對悍制使,而無人臣之禮。由于這些罪行都是對皇帝尊嚴的嚴重侵犯,或對皇帝的人身安全有所威脅,《唐律疏義》即引禮書加以說明:“禮者,敬之本,敬者禮之輿,故禮運云:禮者,君之柄,所以別嫌明微、考制度、別仁義。責其所犯既大,皆無肅敬之心,故曰大不敬。”(56)這裏引用了《禮運》的“禮者,君之柄”作爲立論根據,禮爲君勢所用的意義甚明。這不但顯示了禮在法典中的工具意義,也指明作爲敬之本的禮所涵攝的範圍包括維護皇帝的尊嚴與人身安全。正因此,以禮爲標榜的《唐律》以維護皇帝尊嚴和保護皇帝人身安全爲重要內容,就有其堂皇的理論根據。
這是以禮來顯出“儒從”。
(二)符合儒家思想的律文
《唐律》確實有一些至少在表面上看是符合儒家思想的內容。如容隱、事親易、老人的律文。
最爲稱引的是“同居相爲隱”(57),這是規定親屬相容隱之法。如果違犯此法,《唐律·鬥訟》“告祖父母父母”條規定:“諸告祖父母父母者絞。”(58)這是符合儒家父子相隱的思想。然而,親屬容隱的最重要原則是:謀反、謀大逆、謀叛這三大危害皇權統治的大罪,並不能相隱,一定要密告。《唐律疏議》明確地指出:“謂謀反、謀大逆、謀叛,此等三事,並不得相隱,故不用相隱之律,各從本條科斷。”(59)《唐律疏議·鬥訟》“密告謀反大逆”條這是嚴格與詳細規定知謀反、逆叛,不告與承告不捕的刑罰。(60)親屬容隱在這些罪行上都失去作用。《唐律疏義》“告祖父母父母條”爲此作瞭解釋,認爲:不臣遠比不孝爲大,子對父必須孝敬,不能忘情弃禮,但是對于謀反、大逆與謀叛等不臣罪,即可忘情弃禮。情與禮的重要性隨所涉的對象是君、是父而异。只要一句“不臣”(61),什麽忘情弃禮的大道理都消失了。
再看《唐律》中的侍親緩刑和侍親易刑的律文,《唐律·名例》“犯死罪非十惡”(62)條規定侍親緩刑之法。看來這也是以儒家的親親、盡孝爲考量;然而,符合這種緩行的只限于犯十惡以外的死刑罪或流刑罪的罪犯,這些罪行與直接危害皇權統治與皇帝人身安全無關。而且,犯死罪者必須上請皇帝批准,皇帝有絶對的决定權。同時,還得具備兩個條件:一、犯人的祖父母、父母,包括曾、高祖父母,必須是“老疾應侍”;所謂老是年紀八十以上,所謂疾是篤疾以上。二、犯人家中無期親成丁;期親是在期以上的親屬,所謂成丁是指年二十一以上、五十九以下之男丁。
這些只限于非十惡之死罪及流罪的養親緩刑以及徒刑改易仗刑的規定,確有從孝與親親加以考量。從孝仁出發,以完成親親之義,確是法典儒家化的一種表現,但畢竟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以此否定儒家思想在法典中僅是從屬角色。
此外,《唐律》有“老小廢疾”(63)條,是減免老、小、疾刑事責任的規定。這是本于《周禮·秋官·司刺》的“三赦”(64)原則和《禮記·曲禮》的“悼老不刑”(65)的原則,是律之禮教化的表現。但是,這種刑事責任的減免是有附帶條件的,在實行上只要觸及危害皇權統治的事件,就是篤疾者、八九十歲的老人及七歲以下的小孩,都不可能完全免除刑事責任。因此,這些怎能用以作爲法典寬仁的說明。儘管《唐律》如何以禮爲依據,律文內容與禮何其密切,其禮是統攝在法下的,屬于主法容儒的格局。
(三)不涉皇權的親等與尊等
《唐律》有親等、尊等的制定,用于對親屬間相犯時的規定及保障家族尊長特權。這些以親屬親疏及家族尊卑作爲定罪量刑的規定主要是用于家族犯罪事件,不涉皇權統治。
親屬範圍的劃定固然有其家族的必然的血緣意義,但是對法典的實際作用而言,主要是在親屬容隱及連株上。在親屬的範圍內,親屬對于犯謀反、逆、叛以外的親屬罪犯有庇護的責任,没有告發的義務。另一方面,親屬範圍更適用于連坐,即是在犯一些重大罪行,尤其是與謀反、叛、逆有關的罪行,親屬是要連坐的。罪刑越重,所誅連的親屬範圍就越廣,而親屬關係越近,被誅連的可能性就越大。
《唐律》對于儒家所贊成的容隱,却在絶對尊君的原則下排除在謀反、逆、叛之外,而對于儒家所反對,而韓非從商鞅所繼承的連坐,也在絶對尊君原則下無限的應用在危害皇權統治的反、逆、叛罪(及其他重大罪行)上,是最典型的主法容儒的格局。
尊等保證尊長特權,如財産權及主婚權等以及卑幼相犯時,保障尊長優于卑幼。但是,尊長的這些特權也並無損于君權。相反的,給予尊長的特權,换來家族尊長對皇權的忠心,確保家族的安寧與社會的安定,對皇權的統治是有益的。
由于宗法家族始終是國家的社會基礎,法典中穩定家庭秩序的律文與韓非的絶對君權並無矛盾,家族的安寧對國家的安全有著重要的意義,家族首長的特權也絶不涉及與侵害君權。法典在維護皇權的同時也確認家族首長的一系列特權,這是屬于儒家禮治的範圍,它與維護集權專制的韓非法治思想配合,在法的統屬下,仍是法主儒從的格局。
總之,法典是統治臣民的工具,皇帝爲了要全面地掌握這一有效工具,重視編纂法,甚至親身參與。內容包括韓非的法與術的法典,以維護絶對君權爲最重要目的,其所體現的確實是韓非那以勢爲優先、以法術爲工具的法治思想。《唐律》以禮爲依歸,與禮的關係密切;然而《唐律》用以尊君的禮是韓非單向的禮,禮所尊的君是韓非絶對君勢的君。法典雖有標榜儒家的理想,尤其是德與禮,然而法典標榜儒家的理想只是處于從屬的地位,但是這處于從屬地位的德與禮不但發揮了維護君勢的積極作用,也在加强法治的效用上扮演一定的角色。在完全以禮爲依歸的家族制的律文中,儒家的禮還是被統攝在法之下的。如果說法典中儒法兼容,應該是主法容儒、儒攝容于法的格局。這是中國古代法典的傳統,這傳統正是韓非法治思想“主法容儒”的兼容模式在法律條文上的實際反映。
注释:
①陳奇猷:《韓非子集釋》下册,附録引《非子書序》,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1197。
②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卷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第672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頁672-142。
③魏徵等:《隋書·刑法志》卷二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695。
④陳啓天:《增訂韓非子校釋》,《五蠹》、《八說》,臺北:商務印書館,1994年,頁33、14。
⑤同上,頁33。
⑥同上,頁29。
⑦同上,頁138。
⑧同上,頁36。
⑨同上,頁16。
⑩同上,頁187。
(11)同上,頁54。
(12)同上,頁16。
(13)同上,頁33。
(14)《增訂韓非子校釋》,頁317。
(15)同上,《五蠹》、《八說》,頁33、36。
(16)同上,頁18。
(17)同上。
(18)同上,頁20。
(19)同上,頁224。
(20)同上,頁99~100。
(21)同上,頁43。
(22)同上,頁84~85。
(23)《增訂韓非子校釋》,頁58。
(24)同上,頁506。
(25)同上,頁15。
(26)同上,頁136。
(27)同上,頁50、51。
(28)《韓非子·顯學》:“世之顯學,儒、墨也。”同上,第一卷,頁1。
(29)同上,第一卷,頁36。
(30)同上,頁809。
(31)周勛初:《韓非作品寫作年代的推斷》,見《韓非子札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26~133。
(32)鄭良樹:《韓非之著述及思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頁262~275。
(33)見Derk Bodde:China's First Unifier: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Leiden:E.J.Brill,1938。
(34)《史記·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36。
(35)《史記·李斯列傳》,頁2557。
(36)同上,頁2554。
(37)見《史記·秦始皇本紀》,頁257。
(38)同上,頁258。
(39)《漢書》卷二十三,香港:中華書局,1970年,頁1096。
(40)見《史記·商君列傳》,頁2234.
(41)見《韓非子·八經》,《增訂韓非子校釋》,頁156。
(42)見《史記·秦始皇本紀》,頁238~239。
(43)同上,頁254~255。
(44)見《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頁2715。
(45)見《史記·秦始皇本紀》,頁254。
(46)《增訂韓非子校釋》,頁77。
(47)《唐律疏議》,頁672-142。
(48)見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36~64。
(49)林緯毅:《法儒兼容:韓非子的歷史考察》,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年,頁264~265。
(50)《唐律疏議》,頁672-217。
(51)《增訂韓非子校釋》,頁353。
(52)見《唐律疏議》卷一,頁672-31。
(53)見《增訂韓非子校釋·難一》,頁325。
(54)見《唐律疏議》卷一,頁672-31。
(55)同上,672-31~32。
(56)同上,卷一,頁672-33。
(57)同上,卷六,頁672-99。
(58)同上,卷二十三,頁672-287。
(59)同上,卷六,頁672-99。
(60)同上,卷二十三,頁672-284。
(61)同上,卷二十三,頁672-287。
(62)同上,卷二十八,頁672-349。
(63)同上,卷四,頁672-68~70。
(64)《周禮·秋官·司刺》有“三赦”之法: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蠢愚。見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禮類》第90册,卷三十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頁90-646~647。
(65)《禮記·曲禮》:“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死罪不加刑”。見《禮記注疏》卷一,頁115-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