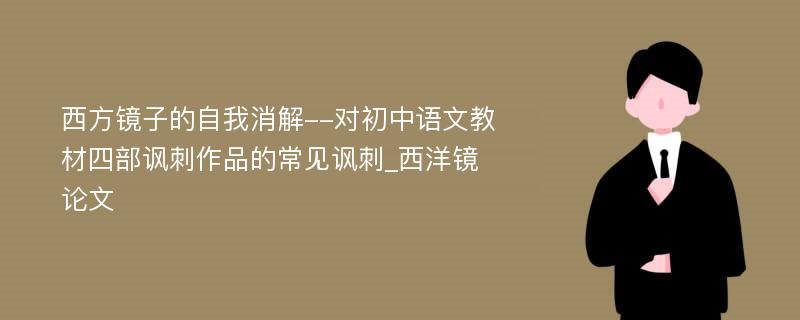
自拆西洋镜——初中语文课本中四篇讽刺作品的一种共同讽剌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洋镜论文,课本论文,手法论文,初中语文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初中语文课本中的讽刺作品,包括小说、童话、寓言、笑话,篇数不少,无不“慼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小说史略·清之讽刺小说》);而《范进中举》《制台见洋人》《皇帝的新装》《变色龙》等,更是“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同上)。这几篇作品之所以能有此收效,细析之,笔者以为,与它们采取了一种共同的讽刺手法──自拆西洋镜,密不可分。
所谓自拆西洋镜,就是通过情节的提练与典型化,让被讽刺的对象去自我暴露本身的矛盾与荒谬,从而揭示出他的本来面目。
首先,作者通过被讽刺的对象自身语言的前后矛盾,自拆西洋镜,露出真面目。《范进中举》中的胡屠户,当女婿范进才中了秀才时,他去贺喜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然后当范进中了举人后,在同一地点,他却说:“我自己觉得女儿象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未中举人前,胡屠户骂范进“痴心想中起老爷来”,是“癞虾蟆想吃天鹅肉”,“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一个个方面大耳?象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待中举人后,胡屠户又百般奉承范进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在同一地点,同样对待女婿范进,胡屠户为什么会说出这般自相矛盾的话?无非胡屠户是个势利小人。《制台见洋人》中的制台文明,平时在下属面前,是一幅凶相,八面威风。他曾再三交代:“凡是我吃着饭,无论什么客来,不准上来回。”然而一听是洋人来了,他却又喝斥道:“我当是谁,原来是洋人!洋人来了,为什么不早回,叫他在外头等了这半天?”试问,同一地点,同样对待来客,文明这话能自圆其说吗?本来,一句“无论什么客来”,就应包括了本国来客与外国来客,然而一听是洋人,他的话又变了,变得与前边的话大相牴牾起来,而正是在这个性化的矛盾语言中,自拆了“大帅”这西洋镜,露出了洋奴的脸孔。
其次,作者通过被讽刺对象自身言与行、表与里的矛盾,自拆西洋镜,露出真面目。仍如《制台见洋人》,作者在写到文明吃饭时,巡捕因说了声“回大帅的话,有客来拜”,挨了文明一个耳刮子后,便“索性泼出胆子来”,说“这个客是要紧的,与别的客不同”,文明道:“他要紧,我不要紧!你说他与别的客不同,随你是谁,总不能盖过我!”真个不可一世。可当一听“洋人”二字,“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蓦地起来,拍挞一声响 ,”“又打了巡捕一个耳刮子”,“举起腿来,又是一脚”,大怪巡捕回迟了。弄得个巡捕“回也不好,不回又不好”,只落得“掉过去一个巴掌翻过来又是一个巴掌;东边一条腿,西边一条腿!”这样一来,就使得文明在同一地点对待同一事情上的自身言与行的矛盾,自我“揭穿假面”,“指出了实际来”(最后两小节引语见鲁迅《招贴即扯》)──文明自身真实的洋奴面目。
至于《皇帝的新装》又略有异,它则是利用被讽对象在同一地点对待有无漂亮布料与衣服这件事上的内心与外表的矛盾来自我暴露的。内中那两个骗子,内心是要骗取皇帝的“生丝”和“金子”,但外表上,他俩还是不得不装出一幅煞有介事的样子:“在那两架空织布机上忙忙碌碌,直到深夜”;当老大臣来查看时,他俩是“指着那两架空织布机问他花纹是不是很美丽,色彩是不是很漂亮”;当皇帝亲临时,他俩便叫皇帝脱下衣服,说“好让我们在这个大镜子面前为您换上新衣”。这就以其内心与外表的矛盾,把个骗子面目摆到了读者面前。如果有人说,写骗子,当然只能这么写,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老大臣”和“皇帝”。那个被皇帝视为最“有理智”,最“称职”的人派去查看两个骗子的织布情况的老大臣,明明内心十分清楚,空“把眼睛睁得特别大”,“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但他担心人家说他“是最愚蠢的”,“是不称职的”,于是便装出看见那布料的样子说:“哎呀,美极了!”“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皇帝自己呢,内心深处明白自己“什么也没有看见”,但生怕被臣民认为是一个最愚蠢的人,不够资格当皇帝,也就自欺欺人地说:“哎呀,真是美极了,”“我十分满意!”并乐意的脱下原有的衣服,去穿上这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最漂亮的衣服──“什么衣服也没穿”,而去参加游行大典。至此,读者便可明白:所谓称职、诚实的老大臣,其实是最不称职最不老实的人,皇帝也不过是一个崇尚虚荣、无知愚蠢的家伙;朝廷上下,完全是你骗我,我骗你,全是骗子。
鲁迅先生在《什么是讽刺》中说得好,“一个作者,用了精练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而“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中,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他特别一提,就动人。”正是如此。只要读者留心现实,象大臣、皇帝这种表里不一、自欺欺人的人能少见吗?
再次,作者通过被讽刺对象自身前后行动上的矛盾,自拆西洋镜,露出真面目。《变色龙》中的奥楚蔑洛夫在同一地点,对待同一只狗,他是“变”来“变”去,来了个彻底自我暴露:穿着军大衣的他── 一条沙皇警犬,来到木柴厂门口,听说那只狗咬伤了赫留金时,就威风凛凛,骂那只狗是“疯狗”,要“把它弄死”,当有人说那狗是将军的狗时,他急了,吓出了汗,忙叫脱去大衣,并说那狗是“名贵的狗”,骂赫留金是想诈钱;当有人怀疑不是将军的狗时,他又盛气凌人起来,骂那只狗是“下流胚子”;当巡警说出“也说不定就是将军家的狗时”,他又一被吓坏了,心冷胆寒,忙叫给穿上大衣,说那只狗是“娇贵的动物”,大骂赫留金是“混蛋”;当一从将军的厨师口里听到“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这样的狗”时,他又骂这条狗是“野狗”,“弄死它算了”;然而当厨师说是将军的哥哥的狗时,他又吓得“裹紧大衣”,奴颜婢膝地奉承那狗“还不赖,怪伶俐的,一口就咬破了这家伙的手指”,并对赫留金斥道:“我早晚要收拾你!”──就在这“变”的过程中,奥楚蔑洛夫自拆了警官这个西洋镜,露出了他那媚上欺下,看风使舵,趋炎附势,奴颜婢膝的庐山面目。再如《范进中举》中的胡屠户,当范进只中了秀才时,他是“吩咐女婿”要怎么干,不怎么干,“立起个体统来”,“免得惹人笑话”;可当他一旦中了举人,即使是为了替女婿治病,他也只是“大着胆子打了一下”,“手早颤起来”,“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着:‘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并且,当看到范进的衣滚皱了后,是“一路的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这么前后比照,这胡屠户是判若二人。
总之,这四篇作品的作者,没有用只言片字去直接表露观点,而是通过情节的提练与典型化,从而使被讽刺对象自身在同一地点对待同一事物的不同态度所形成的比照中以暴露矛盾或荒谬,自动去拆穿自己的西洋镜,把自己的脸孔彻底表露出来,供读者在讽笑中予以抨击或诅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