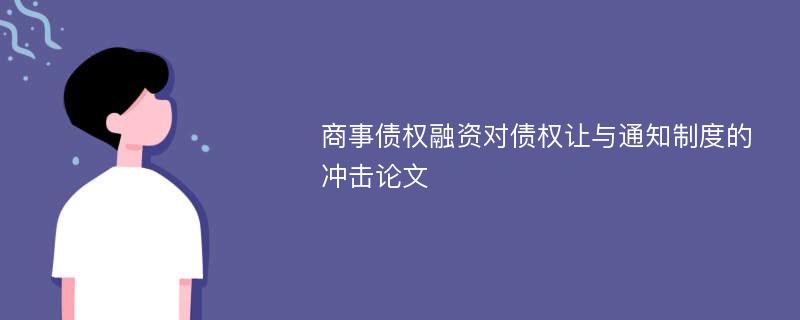
商事债权融资对债权让与通知制度的冲击
虞政平 陈辛迪
(辽宁大学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内容摘要】 对于民事债权转让而言,让与通知制度的合理性在于遵循“形式主义”的债权移转理论。但面对未来收益权、集合应收账款等新型融资标的,固守让与通知制度将动摇商事债权融资的法律基础。完善让与通知制度,一方面要强调债权移转需以履行债权转让合同义务为条件,另一方面又当允许当事人对合同义务的履行方式进行意思自治。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中,未来《民法典》应将商事债权融资一并纳入债权让与制度的规制范围。对于债权移转的生效要件,仍应以让与通知为原则,但也应允许当事人对债权移转条件和方式的意思自治。而对于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应以登记时间的先后作为确定多重让与中债权归属的标准。
【关 键 词】 商事债权融资 债权让与 让与通知 集合债权
债权所蕴含的价值逐渐被商品经济社会发现并认可,其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商事融资领域。为契合于商事融资的利益追求和流动性需要,作为融资标的的债权就需具备高附加价值和易流转性,这就将因侵权、继承等行为所产生的价值较低且人身附属性较强的债权排除在外。实践中,最常见的商事债权融资标的是应收账款债权。而就商事债权的融资模式而言,其又可分为担保型债权融资和转让型债权融资,本文主要关注以债权让与为法律制度基础的转让型债权融资模式,典型的就是保理和以债权为基础资产的资产证券化业务。
在现有关于债权让与制度的研究中,学者曾就债权移转依据和债权多重让与中优先顺位标准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但其视角基本局限于传统的个体、现实债权让与的情形中。在此种情形下,将通知债务人作为债权的移转依据和债权多重让与中的权利归属标准,其与合同相对性理论更为匹配,也更符合债权让与的制度逻辑。但在商事债权融资领域,利益和效率是最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对于渐获认可的未来收益权融资,因其指向的债务人尚不能确定,让与通知将无从着手。此外,让与通知对于集合应收账款融资也显得尤其困难。但与之对应的疑问却是——在债务人并不知悉债权让与时,受让人如何向债务人求偿?其所受让债权的法律效力又当如何体现?在法律问题越发复杂的今天,整合性、多维度和一体化的研究范式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1]本文通过将让与通知制度对民事债权让与和商事债权融资的适配性进行比较,分析出商事债权融资语境下的债权移转依据和债权多重让与中的权利归属标准,为传统的民事债权让与制度提出一种商事角度的思考。
一、让与通知制度对民事债权让与的适用性
(一)通知作为债权移转依据的正当性
债权让与是“不改变债的内容,债权人将其债权移转于第三人享有”[2]P69的过程。债权作为“特定的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3]P98,债权让与的直接效果当是该请求权归属主体的移转。因此,确定债权移转的依据对于研究债权让与制度意义重大。以大陆法系惯常的要件主义思维模式观之,界定债权移转的依据就相当于在确定债权让与的生效要件。但对于债权让与生效要件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却语焉不详。其第80条“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是现今立法关于债权让与法律效力最直接的规定。对该条规定意涵的解读和判断,也成为学界关于债权移转依据争论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学者们分别依据“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权利变动模式,提出以“债权让与合同生效”或“通知债务人”作为债权移转的依据,并形成“债权让与合同说”和“债权让与通知说”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但相较而言,遵循“形式主义”的债权移转模式,将让与通知作为债权移转的生效要件更具合理性,且更贴合我国《合同法》第80条的立法原意。原因在于:
第一,唯有让与通知,方符合债的本质。作为一种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权利,萨维尼认为债务人的履行行为构成债的真正本质。[4]债权关系成立后,债权人的利益完全依赖债务人对于债的履行方能实现。根据合同效力相对性的原理,债权让与合同的生效只是使得出让人负有向受让人转让一项债权的债务。况且根据《合同法》第80条的规定,在让与通知前,该债权让与不能对债务人生效。换言之,债权让与合同生效并不能为受让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提供充分的法律支持。如果将债权让与合同生效作为债权移转的依据,此种不能对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债权继受将是对债权法律效果的根本背离。有支持“债权让与合同说”的学者认为,“即使债务人不知悉债权让与的事实,受让人也只对其受让的债权不享有诉请履行力、强制执行力和私力实现力,但依然享有处分力和保有力。”[5]但此种说法仍不免留人疑问:受让人在不能对债务人诉请履行、强制执行和私力实现时,其债权又剩余何种效力?此等债权的保有力如何体现?若债权仅具有处分力,且债权继受人的权利范围必然不超过出让人的权利范围,由此之后的所有继受人当然也不具有请求债务人履行的权利,这无疑将陷入对债权定义和本质的根本违反。
第二,唯有让与通知,才使得债权让与的逻辑得以自洽。在条文的表述方式上,台湾地区“民法”第297条第1款与我国《合同法》第80条的内容类似,以让与通知作为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生效要件。①根据台湾地区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让与通知是受让人请求债务人履行和接受债务人履行的依据,甚或可以不论债务人是否通过其他方式知悉债权让与。②若依“债权让与合同说”的理论,自让与合同生效后,受让人即已取代出让人成为债权人。但在让与通知前,债务人却只能向出让人履行,且此种履行可产生债之清偿的法律效果。但于出让人而言,接受债务人的清偿却构成对受让人的不当得利。而受让人作为真正的债权人,却在通知债务人之前不能对其主张债权。由此可见,将“债权让与合同说”的理论嵌入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债权让与制度,将人为地使得债权让与中三方当事人的权利行使模式复杂化。比较法上,虽然秉持意思主义债权移转理论的《德国民法典》第407条第1款也规定,“对于债务人在债权让与后向原债权人履行的给付,及其在债权让与后与原债权人之间就债权所实施的一切法律行为,新债权人必须承认其效力”。但该条之规定与我国《合同法》第80条却有着本质的不同。依德国意思主义的债权移转模式,自债权让与合意达成时,无论是否通知债务人,其都应向受让人履行。故而,第407条是为保护债务人的利益而设,避免对债权让与不知情的债务人二次履行债务而损害其合法权益。换言之,对于第407条的保护,债务人是可以放弃的。债务人选择再次向受让人履行债务或在通知前直接凭反对债权向受让人主张抵消,并与此同时向出让人提出不当得利的诉请,其行为也同样可以获得德国法律的支持。但依我国《合同法》第80条的规定,通知是债权让与对债务人产生效力的条件。只有在让与通知后,受让人才与债务人构建起真正的债权债务关系,其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才能获得法律的支持。
第三,唯有让与通知,才符合为第三人设定义务之法理;债权让与的实质是为债务人设立一项新的义务。而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只能为自己设定权利或增加负担,即使为第三人增加纯粹的利益,也必须获得第三人的同意。[6]P156根据该原则,为第三人设立义务需有该第三人的同意。即便出于鼓励债权自由流转的实际需要,也只有在债务人获知债权让与的情况下,方可为其设定向受让人履行的义务。但若依“债权让与合同说”,出让人和受让人所达成的债权让与合同就使得债务人负担了一个向受让人履行的新债务,这实质上混淆了两个并不能同时发生的法律关系。法律关系作为被民法摄入自己调整范围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7]P60,其应充当抽象法律逻辑与现实社会生活之间的连接点。对于债权让与而言,其包含了债权人(出让人)与债务人和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两个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凭借债权让与合同,受让人只是进入了第一层次的法律关系。换言之,受让人只是获得了替代出让人成为新债权人的“可能性”。而在出让人将债权转让的情况通知债务人后,受让人才进入第二层次的法律关系。出让人通过履行债权让与合同的义务,才使得受让人成为新债权人的“可能性”升格为“确定性”。“债权让与合同说”遵循意思主义的权利变动理论,但该理论模糊了“合同生效和合同履行之间的界限,把‘当事人应当履行义务’视为是‘当事人已经履行了义务’。”[8]P290
(二)通知比合同更适宜作为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
相较而言,若将通知债务人作为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能够较好地适用于传统的民事债权让与。一方面,让与通知使得与债权有利益关涉的债务人可以监督债权人的债权转让情况,降低出让人将债权待价而沽抑或自行篡改让与合同时间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作为民事主体参与债权让与,其从事该项活动的经验和精力都有限。如果参照《物权法》第24条将登记作为对抗要件,在登记系统尚未普及和成熟的条件下,可能会使得偶然的、小额的债权让与成本增加,进而挫伤民事主体出让、受让债权的积极性,长此以往也不利于债权的流转和其经济价值的体现。将让与通知作为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也可与依让与通知实现债权移转的制度设计更好地适配,适当兼顾债权让与的安全性与便捷性。
就债权让与对抗要件的法律效果,有学者认为其表征的是对债务人的对抗效力,并援引《日本民法典》第467条第1款的立法例,将让与通知作为债权让与对抗债务人的要件。[5]但笔者认为此说是对债权让与对抗要件的误读。所谓“对抗”,是就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冲突而言的。对于满足对抗要件的当事人,其权利可以获得法律的优先保障。而反观债权让与中的债务人,出让人和受让人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存在与其就标的债权的权利冲突。相反,对于债务人而言,债权让与只决定了谁有权向其行使债权,抑或是其向何者履行可获得债之清偿的法律效果。因此,债权让与对债务人体现的是权利主体移转的法律效果,而非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竞争。我国《合同法》第80条“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用词是准确的。所谓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应体现为债权多重让与中的权利归属标准。
而对于如何设置债权多重中的权利归属标准,其必然受到债权移转依据的影响。持“债权让与合同说”的学者认为,既然自让与合同生效就已实现债权移转,则出让人再行与第三人签订债权让与合同属于对该债权的无权处分。鉴于债权让与本身缺少有效的公示手段,后续签订让与合同的受让人不能依据善意取得制度而获得比在先受让人更优位的权利。[9]而对于出让人将在后签订的债权让与合同通知债务人的情况,持此论的学者则认为债务人可依让与通知的内容为清偿,且此种清偿受表见让与制度的保护。但就二受让人之间的权利归属,其认为在后受让人即便已经获得债务人的偿债履行,其仍不能对抗在先受让人对其主张的不当得利诉请。[10]P570换言之,此种观点贯彻了“成立在先,权利在先”的逻辑,将债权让与合同作为债权让与的生效要件和对抗要件。但笔者认为此说虽保证了逻辑上的一致性,却与债权让与对抗要件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
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既是为了解决债权多重让与中的权利归属,其标准设计上必然要考虑多个竞争性受让人之间的权利比较。既然已经承认债权让与欠缺公示手段,则在先、在后的债权让与在公示性上并无差别。如果后签订的债权让与已经通知了债务人,其反而具备较在先的债权让与更强的公示性。况且如果在后受让人已经接受了债务人的履行,强行保护在先受让人的利益反而会造成债权流转成本的增加。最重要的是,在对债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时间缺少有效手段加以固定的条件下,如何能保证出让人不会因利益诱惑而肆意篡改债权让与合同的签订、生效时间?诚然,依诚实信用原则观之,遵循“成立在先、权利在先”的规则对第一受让人的权利保护可谓周全,但因债权让与缺乏有效公示手段,受让人又如何确认自己处于何等受让顺位?在不能对受让顺位进行可靠的知悉和固定时,探讨如何对第一受让人为周全保护不过是一厢情愿。
如果说《合同法》对作为债权移转依据的债权让与生效要件语焉不详,而对于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合同法》可谓“讳莫如深”。在《合同法》有关债权让与制度的规定中,完全没有提及债权让与对抗要件的法律效果和设置标准,学理上对此争议不断。
而金属空气电池,由于正极与空气连接,不会积聚压力,所以爆炸的危险比较小。另外,由于多数的金属空气电池采用的材料与空气接触反应剧烈程度较小,其燃烧的风险也非常小,故金属空气电池一般不会自燃或爆炸,除了锂空气电池。
二、让与通知制度对商事债权融资的适用困境
(一) 通知对于收益权融资的不适用性
1.收益权从性质上属于纯粹未来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97条肯定了“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公路渡口等不动产收益权”的可质押性,这也从制度层面为收益权融资开辟了道路。虽然对收益权属于用益物权还是债权在学界尚有争论③,但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在《物权法》未明确将其归为物权范属时,尚应将其归于债权的范围。此类收益权是一系列单个债权组成的权利束,其在出质时无法确定最终形成的数量和数额,更无法确定债权指向的具体债务人,学界将此类收益权定义为未来债权。又因该类未来债权缺少基础法律关系的支撑,故其又被称为纯粹未来债权。[11]P616在公路、桥梁、隧道等不动产建造之初,其未来获取收益的高概率可能性就可被合理预期,但在债权真实发生前,此类收益权的数额和指向的债务人根本无法确定。换言之,不动产的收益权是一个债权的集合,在每一个债权真实发生前,此等债权均属于无基础法律关系的纯粹未来债权,而作为集合概念,收益权的法律属性也当归于纯粹未来债权。
2.纯粹未来债权的可让与性逐渐被承认。出于保障债权流动性的目的,不应将可让与债权的范围限于已到期债权。对于有基础法律关系的未到期债权,其可转让性已被学界基本接受。有关未来债权可否被让与的争论焦点,集中于纯粹未来债权上。而对其可让与性,无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经历了从拒绝到接受的过程。英国普通法法谚“自己无有者,不得与人”[6]P178,表明其早期对未来债权让与的否定态度。但这一具备逻辑合理性的限制被衡平法所打破。1842年,美国Story法官在“Mitchell v. Winslow”案中承认了衡平法上的“未来担保权益”。[6]P124此后,随着《统一商法典》的颁布,美国正式承认了未来债权的可让与性。[6]P127而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在2003年和2004年分别颁布了《金融安全法》和《新证券化指令》,从原对未来债权可转让性的否定转变为肯定态度。[6]P119德国则通过其《民事诉讼法》第259条,支持对“将来之给付”提出的权利主张。[12]P57德国最高法院也在应收账款“浮动质押”的案件中,承认“让与的权利不必在让与时能够确定”。[6]P121至此,两大法系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均对纯粹未来债权的可让与性做出肯定。受此影响,有关债权让与的国际公约,如《国际保理公约》、《联合国国际贸易应收账款转让公约》都承认了纯粹未来债权的可让与性。④
前段日子,关注腕表的“老客”们都注意到了真力时(Zenith)推出的DEFY系列的自动上链机芯表。以每小时36000振次,1/100秒的精准度,将计时功能推到了腕表界前所未有的高度。
解志熙《“青春·美·恶魔·艺术……”唯美—颓废主义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戏剧(上、下)》[5-6]选取了众多作家及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苏雪林及其剧作亦在其中。在苏雪林部分,解志熙首先指出,苏雪林的《玫瑰与春》运用了童话与象征的手法,可能受到王尔德的《玫瑰与莺》《自私的巨人》等童话的影响。其次,作者认为在中国现代戏剧中,受唯美—颓废主义影响最深的剧作之一就是苏雪林的《鸠那罗的眼睛》,并从戏剧主题和人物性格两个方面,将《鸠那罗的眼睛》和王尔德的《莎乐美》进行了比较,虽然二者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雪林也并非完全模仿,而是有所创新。
有学者将债权让与合同的履行行为比作动产物权变动中的“交付”[6]P155,那么让与通知只能是最基础、最原始的交付方式。对于动产物权变动,除《物权法》第24条规定的“现实交付”,还有第25、26、27条规定的三种“观念交付”方式。⑩在债权让与中,让与通知更接近对债权的“现实交付”,而委托出让人代为收款则可被类比为“观念交付”。具体而言,应当更接近《物权法》第27条规定的“占有改定”方式。自委托收款合意达成时,出让人成为受让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媒介。然而,对于债权的“观念交付”可能产生两个质疑,笔者在此分述并予以回应。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遵循教学大纲的基本指示,还要鼓励学生走出教室,走出校园,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开阔视野,激发创造性思维。如果一个学生每天只沉浸在艰苦的学习中,他的思维就会受限制,并且他的大脑使用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会逐渐退化。随着素质教育的实施和发展,学生的能力需求更倾向于全面和实用。因此,教师可以通过实地观察,主题调查和访问,引导学生关注当地的自然风光、文物、风俗习惯以及国内外重要事件。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世界中,让学生在情境中充分感受到语文知识运用的喜悦并由此热爱学校生活,热爱语文学习。同时,使他们不断领悟人生的意义。
3.通知对于收益权融资的制度障碍。在承认纯粹未来债权具备可让与性的前提下,若固守让与通知要件,将造成债权让与制度对收益权融资实践极大的不适用性。在以收益权为基础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时,收益权出让给特殊目的机构(SPV)不会以通知债务人为必要,这在国际和国内的融资实践中已成共识。早在1996年,珠海市政府就通过其注册在开曼群岛的珠海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珠海当地的机动车管理费和外地过境车辆的过路费为基础资产,在美国发行了2亿美元的资产支持证券。广州机场高速公路通行收费权的资产证券化项目也同样如此。广州快速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将其对广州机场高速自2015年10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的通行收益权,出让给由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的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作为该专项计划的基础资产——为期近6年的高速公路通行收费权,是典型的纯粹未来债权。⑤在基础资产出让时,根本无法确定此种债权最终指向的债务人。但既然允许其转让,当认为此种未来债权的转让不再以通知债务人为必要。若以让与通知作为债权移转要件,将从根本上否定未来收益权的可让与性,进而导致现有收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法律基础彻底瓦解。从现实角度出发,承认未来债权的可让与性已为国际共识,固守让与通知要件,其结果无异于削足适履。
(二)通知对于集合债权融资的不便利性
1.提高集合债权融资成本。所谓集合债权融资,是指出让人通过将其对不同债务人享有的多个债权打包为一个整体,一次性转让给受让人并进行融资的行为。对于由若干子债权组成的债权包,其将被视作一个整体而进行估值和转让。因此,对于集合债权融资,出让人和受让人达成的合意均是以债权包整体为标的,而非对单个债权分别达成合意。但如果将让与通知视为债权移转的生效要件,则有必要对全部债务人分别进行通知,方可实现受让人对债权的顺利继受。鉴于进行融资的债权价值巨大,组成债权包的分项子债权个数也绝非一二。若对债务人分别进行通知将使得出让人不堪其扰,此种债权让与也将耗费甚巨。保理行业中出现保理与融资租赁结合的趋势。例如,长安银科以池保理的形式为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融资,而融资租赁公司则将其一定时期内的多笔租赁债权打包转让给保理公司。由此,对多个债务人的集合债权成为了融资标的。⑥另如于2015年10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京东白条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其首期融资额度就达到8亿元人民币。作为该项目的基础资产——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公司”)所持有的应收账款债权是典型的集合债权,囊括了无数笔消费者在京东商贸体系中购买商品、服务所形成的分期付款债权。在京东公司将该集合债权出让给由华泰证券担任管理人的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过程中,若对每一个子债权的债务人分别进行通知,其转让债权所需的经济和时间成本将超出融资主体所能承受的限度。由此可见,若僵化地坚持以让与通知作为债权移转的依据,将人为地提高债权让与成本,不利于最大程度地发挥债权的经济价值,并最终与债权让与的制度初衷相背离。
2.不符合融资参与主体的实际需要。如果说收益权融资导致让与通知无法进行,集合债权融资更多地表现在融资参与者对让与通知的抗拒。导致此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债权让与通知违背了集合债权融资参与者——融资人和出资人的实际需要。从出让债权的融资人角度看,其面对的债务人几乎全部是其主营业务的交易对象,若将其出让债权以获取融资的情况告知各债务人,势必造成债务人对于其现金流稳定性的质疑,影响债权融资主体的商业信誉。更严重的可能是债务人趁机“敲竹杠”,以缓解债权人短期资金压力为条件换取债务减免,由此导致融资人的合法权益受损。而作为出资方的债权受让人(或受让人的代理人)又多为从事金融行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其本身并无从事非金融业务的利益激励,也无暇完成对不特定多数债务人的债权催收。借助目前较为完善的银行信用体系和银行账户监管技术,此类机构受让人更乐于委托出让人去从事债权催收,并将所得款项汇入银行监管账户。仍以“京东白条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为例,在华泰证券担任计划管理人的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受让集合债权之后,其又委托原始权益人——京东公司担任资产服务机构,并委托兴业银行作为资产托管人。此举让熟悉具体应收账款债权情况的京东公司在其原有业务领域继续开展工作,这显然更有助于保证债权催收的效率和效果,进而实现融资参与方的共赢。至于对京东公司私自截留应收账款的担心,则由托管人兴业银行负责监督,计划管理人当然也可与京东公司约定外部审计的时间频段,以确保京东公司审慎履行代为收款的义务。
(三)通知与企业资产证券化所依托的法律关系不匹配
鉴于资产证券化业务中的SPV尚未被法律认可为适格的商事主体,对投资者与SPV管理人之间是委托关系还是信托关系仍旧存在争论。[14]在“一行两会”的金融监管政治格局下,我国的金融立法和监管也出现各自为政的情况。我国将信托作为金融牌照业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授权银(保)监会专门负责牌照发放与业务监管。在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模式中,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资产证券化被归入由不同监管机关所监管的交易市场。由银监会所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可以充分利用信托制度构建SPV的法律关系,但企业的应收账款融资却只能以由证监会监管的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来进行。因以公司形式构建SPV存在税务负担和法律障碍⑦,另受限于信托制度的专属性,企业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只能借助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来进行体系架构。[15]
在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中,作为委托人的投资人是债权的真正受让人。若在此种法律关系中嵌入让与通知制度,受托人需告知投资人(委托人)其代为受让的债权所指向的具体债务人。但资产证券化的过程必然打破作为基础资产的债权与收益权份额之间的联系,难以实现投资人与具体债权的一一对应。投资人只握有对应一定份额的收益性证券,其收益权份额是对作为基础资产的全体债权而言的,并不能依具体债权进行区分。申言之,在集合债权的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中,一旦个体债权发生无法清偿的情况,投资人作为权利义务的最终承担者,应由其中一人还是全体投资人按份额负担这一损失?在企业资产证券化尚不能应用信托法律关系的条件下,个体债权又难以与投资权益实现对应,让与通知制度对企业资产证券化模式的债权融资更显不合时宜。
(四)以通知作为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并不绝对可靠
将让与通知作为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其理论根源在于对债务人“信息中心”[12]P133地位的强调,且此种制度设计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承认。⑧但将让与通知作为转让型商事债权融资的对抗要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漏洞,具体表现在:
其一,以通知作为债权转让的对抗性要件,其实质与以债权让与合同作为对抗要件区别不大,都是依赖于私主体的信用。无非“通知主义”⑨依赖的是债务人信用,而“让与主义”依赖的是出让人信用。批评“让与主义”的观点认为,“仅凭一纸让与合同即可对抗第三人的制度,无异于纵容乃至鼓励欺诈。”[16]但若依“通知主义”的制度设计,在未改变依赖私主体信用的条件下,商事债权融资还可能为债务人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最终使得通知债务人的对抗效力越发薄弱。债务人本不负担对受让人的告知义务,且债权让与越频繁,债务人的告知负担越重。由此有学者批评道,“法律既不能以利相诱,又不能以力相逼,则债务人实不堪当信息供应的大任。”[16]
其二,以通知作为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对于集合债权转让具有极大的不适用性。面对债务人众多的集合债权转让,若将让与通知作为对抗要件,则必然要对全部债务人进行通知。撇开通知成本不论,对多数债务人的通知本身就需要时间。在同一集合债权被多次让与的情况下,对债务人通知所需的时间段一旦出现重合,将导致对整体集合债权受让人之间的优先顺位无法评价。如果延伸到对个体债务人的通知时间来分别确认子债权的受让顺位,则割裂了集合债权转让所应具备的突出的整体性,也不符合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原本合意。
其三,以通知作为对抗要件,可能引起债务人支配债权受让顺位的问题。对于该问题,实行通知对抗主义的国家已经注意到。根据《日本民法典》第467条第2款规定,能够产生对抗效力的通知或承诺,需以附有确定日期的证书为之。而此处的“确定日期”,是指通过公的手段确定、当事人事后不可能涂改变更的日期。[12]P134然而,通知自作成至到达债务人必然需要时间,日本学界对于以通知“作成时间”还是“到达时间”何者为产生对抗效力的时间节点始终存在争议,但“到达时间”最终获得多数认可。[12]P135“确定日期”制度设计的初衷,是通过公主体的介入,使债权受让顺位的确定转向对公主体信用的依赖。但证明“到达时间”本身仍有赖于作为私主体的债务人如实报告或遵守诚信义务,故而“到达时间”的标准似乎又违背了这一制度初衷。由此可见,以通知作为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终究难以摆脱对私主体信用的依赖,而这与商事债权融资高效、可靠的利益诉求是难以兼容的。
在商事领域,以未来收益权、集合债权等作为标的资产来开展融资业务已越发普遍,这也使得其遵循的制度和逻辑必然有别于传统民事上的现实、个体债权的转让。在保理、资产证券化等典型的转让型商事债权融资模式中,标的债权作为进行融资的基础资产必须完成真实出让。但对于此类债权融资的出资方而言,其并无意对不特定多数债务人直接主张权利,或者其根本就不能确定所受让债权具体指向的债务人。而出于商业信誉考量,有融资需求的债权出让人也不希望债务人知晓其转让债权以换取资金的事实。以应收账款账户可被监管为条件,参与债权融资各方的利益诉求可以实现契合。但反观让与通知的制度设计,其本意是以建立受让人与债务人直接联系的方式来实现对受让人权利的保护,而在债权受让人不想、不能或不需要对债务人直接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其制度设计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也自然值得被怀疑。
三、商事债权融资对让与通知制度的扬弃
(一)债权让与应遵循形式主义的债权移转模式
首先,从比较法的视角观察,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债权让与制度不同于典型意思主义债权移转模式国家的立法例。对于债权移转问题,《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都明确规定自出让人与受让人达成合意时债权发生移转。但我国《合同法》第80条却将通知作为债权让与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的要件。而让与通知前,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究竟产生何种法律效果?对此问题的回答,将成为解释和判断我国现行立法对债权移转依据认识的重中之重。就债权让与在通知前对债务人的法律效果,应该从以下两方面观察:其一,在债务人不知悉债权让与的情况下,其向出让人履行债务是否可以发生清偿的法律效果?其二,债务人非经通知而知悉债权让与,其自行向受让人履行债务是否能产生清偿的法律效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已成共识,债务人在让与通知前对出让人的履行能够实现债之清偿,以此认为未经通知的债权让与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没有问题。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国法律上没有规定,只能通过比较法来对照性地寻找答案。《德国民法典》有关债权让与的规定,淡化了让与通知的法律效力,转而强调债务人对债权让与的知悉。依据《德国民法典》第404条和406条的规定,无论债务人以何种方式知悉债权让与,自知悉时即应向受让人履行,且可同时向受让人主张抗辩权和抵消权。《日本民法典》第467条虽采用通知对抗债务人的模式,但其国学界和司法审判均认可债务人非经通知而知悉债权让与时,其有权选择向出让人或受让人一方履行债务或行使抗辩权,且此种行为可产生债之清偿的法律效果。[5]就此,应当认为比较法上认同债权移转同债务人对新债权人的抗辩权、抵消权同步发生。德国和日本均遵循意思主义的债权移转模式,故只要让与合同生效,受让人即成为新的债权人。无论是否得到通知,只要债务人知悉债权让与,其就应当向受让人履行债务,与此同时也可以向受让人行使合法的抗辩权和抵消权。但依《合同法》第82、83条的规定,债务人若想对受让人行使抗辩权和抵消权,均需在获得让与通知之后为之。在债务人可能享有对受让人的抗辩权、抵消权的情况下,若不允许其向受让人行使上述权利,其自然也不会向受让人履行债务。况且依《合同法》第80条之规定,获得通知前债务人可以拒绝受让人对其主张的权利请求。概言之,《合同法》第80、82、83条将让与通知作为债权让与中权利移转的条件,其规定虽颇具中国特色,但其条文之间的制度逻辑却是一以贯之的。
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为城轨票务云支付的改革创新发展提供广阔平台,使用电子虚拟票取代实体票已成为业内共识,也是城轨票务发展的必经之路。
1.形式主义的债权移转更贴近《合同法》的立法原意。之所以说遵循意思主义的“债权让与合同说”是对我国《合同法》中债权让与制度的曲解,其原因在于《合同法》有关债权让与的规定,既不同于比较法上遵循意思主义债权转让模式国家的相关规定,也不同于其他部门法上所规定的意思主义的权利设立、变动模式。
债权的价值在于请求债务人为偿债履行,不论是传统民事债权让与还是转让型商事债权融资,只要以债权让与制度为基础来开展业务,就必须关注受让人向债务人为权利请求的方式和时间始点。基于前文分析,遵循意思主义模式的“债权让与合同说”混淆了债权让与合同生效和债权让与合同的义务已经履行的概念。易言之,债权让与合同的生效不意味着其合同义务必然得到履行,受让人要想真正继受债权,必然要依赖出让人对让与合同义务的忠实履行。就传统的民事债权让与而言,履行让与合同义务最典型且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知债务人。据此分析,引发债权移转的条件有二:一者为让与合意的成立且生效,二者为出让人履行合同义务。这种“合意+履行=权利变动”的模式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权利变动模式。债权让与应遵循形式主义的权利变动模式,这一结论的得出并非凭空捏造,从对现行立法的解释和司法审判实践中都可找到依据。
将让与通知作为债权让与的生效要件和对抗要件,能够较好地适用于传统的民事债权让与。当出让人履行债权让与合同的义务——通知债务人时,债务人便也清楚地认识到其所负担债务对象的变更。受让人依据让与通知对债务人行使请求权,并依据让与通知的时间先后来确定各受让人之间的顺位排序。但进一步观察可知,债权让与通知说的立论基点在于:债权人需直接向债务人为权利请求,方可实现其债权的价值。但正因让与通知制度强调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权利联系的直接性,其造成债权让与制度的僵化,难以适用于商事债权融资的新型实践。
① 台湾地区“民法”第297条:债权之让与,非经让与人或受让人通知债务人,对于债务人不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2.审判实践支持形式主义的债权移转模式。在审理李敬堂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苏建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时,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97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将让与通知视为债权移转的生效要件。该案随后经审判监督程序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该院在(2017)粤民再300号民事判决书中进一步明确,“在债权人签订多份债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应当将债务人是否知晓以及能否确认债权转让事实作为认定债权通知效力的关键。”申言之,该判决表明在债权多重让与的情况下,未获通知的在先受让人不能对抗已经过让与通知的在后受让人。该两份判决书遵循形式主义的债权移转模式,将让与通知作为债权让与的生效要件和对抗要件。无独有偶,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遵义渝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保理合同纠纷一案时,其所作的(2016)最高法民申7号民事裁定书也认为,“债权转让通知义务是债权人在债权转让协议项下对受让人负有的一项合同义务,以使受让人获得向债务人主张债权的权利。”以此为基础,该民事裁定书强化了让与通知的法律效力。其认为在让与通知前,不仅受让人不能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债务人擅自向受让人履行债务都不能实现免责性债务清偿的法律效果。上述司法裁判认可了让与通知是债权转让合同的义务,并将让与通知作为受让人对债务人受偿的依据。且不论让与通知是否为债权让与合同义务的唯一履行方式,但履行让与合同的义务对于债权移转却是必不可少的。反之,若仅依债权让与合意就可实现债权的移转,又何需履行债权让与合同的作为义务呢?确认履行行为对债权移转的必要性,正是形式主义债权移转模式的合理性所在。但面对商事债权融资的新型实践,将让与通知作为债权移转的绝对依据似乎也不可行。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对债权让与合同义务的履行方式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允许对债权让与合同履行方式的意思自治
在债权让与合同中,出让人向受让人转让的是向债务人求偿的权利,商事债权融资也不例外。但银行信用体系的日益健全和特定账户监管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商事应收账款融资实践中受让人对债务人的求偿和受偿模式。作为出资方的受让人不再必须对债务人直接主张权利。在更为熟悉金融业务的受让人看来,其完全可以接受更为灵活的债权受让方式,立法和司法也对债权让与合同履行方式的创新做出了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的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公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合同法》规定的通知义务。”2004年第4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何荣兰诉海科公司等清偿债务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一终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也承认了登报通知的合法性。该判决认为国家法律并未对让与通知的方式进行强制规定,登报通知“更具时间性、公开性和广泛性,与单个书面通知具有同等的作用和效力。”但此类债权让与合同的履行方式还未脱离通知的框架,直至受让人委托出让人代为收款方式的出现。例如前述京东白条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模式,京东公司一方面作为原始权益人出让其集合债权,另一方面又以服务机构的身份代替出资方(受让人)对债权先行受偿。此种当事人之间的委托收款合意作为债权让与合同的履行方式,很难将其解释为“通知”的一种。
我国立法层面虽并未对纯粹未来债权是否可被让与做出明确规定,但《担保法解释》第97条率先承认了不动产收益权的可质押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2条第1款更是将应收账款界定为“现有的和未来的金钱债权”。对于此类收益权,其可被质押的前提必然是其具备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就体现在可转让性之中。在保理领域中,《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3条虽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对未来债权开展保理业务,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2017)京03民终9853号判决中,仍确认了针对未来债权所签订保理合同的法律效力。统而观之,对纯粹未来债权让与予以认可的路径是以实践为导向的。正如海因·克茨评价的那样,“面对商业尤其是银行业压倒一切的实际需要,对未来债权让与的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反对终于全部消失了。”[13]P395
其一,如果将另行达成委托收款合意作为债权让与合同义务的履行方式,此种债权移转模式岂非与“债权让与合同说”的外观相同?诚然,对于债务人和债权让与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而言,委托出让人代为收款并不能将债权让与的情况向外界予以公示。但就制度运行逻辑和对受让人权利的保护程度而言,此二者却截然不同。委托出让人代为收款的合意是在债权让与合意之外,出让人与受让人就债权让与合同履行方式单独达成的合意,这一合意具备独立的合同效力。以当事人对履行方式另行达成合意的形式替代传统的让与通知,从而使得债权移转在制度逻辑上符合“让与合意+履行”的形式主义模式。简言之,债权让与合同说认为一个让与合同即可实现债权移转,代为收款的模式却是两个合意才能实现债权移转。虽然明确了债权的“观念交付”与意思主义债权移转的区别,仍有质疑认为允许对让与合同履行方式进行合意是制度的自我设限,除人为地匹配形式主义债权移转的逻辑外没有实践意义。但从保护受让人权利的视角来看,此种制度设计的优越性非常明显。以出让人截留应收账款债权为假设情景,若依意思主义的债权移转模式,受让人只能向出让人主张不当得利。当债权仅凭让与合意即告移转而不需借助其他的履行行为时,截留账款也就不构成对债权让与合同义务的违反,自然就没有违约责任适用的空间。但作为债权“观念交付”的委托出让人代为收款模式则不同,此种委托收款的合意,是受让人与出让人就债权让与合同义务的履行方式达成的一个新的、独立的合同,其当然可以设置违约金条款。一旦出让人截留账款,受让人除向出让人主张不当得利之外,还可向其主张违约金赔偿。后者两种请求权的救济显然强于前者单一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救济。
其二,委托出让人代为收款不能将债权让与的事实向外部公示,此当如何满足形式主义权利变动模式对于公示性的要求?对此种质疑的回应需回溯到物权变动理论本身。对于动产物权变动,除现实交付外,物权理论已经接受了“观念交付”所具备的法律效力。而对于“观念交付”本身,特别是将“占有改定”作为交付方式之一,其能表现出的公示性本就不明显。刘家安教授甚至认为,所谓“观念交付”,实则起到替代交付之功能,其制度设计本身就不以“公示”为必要。[17]庄加园博士引用德国法学家黑克之言来评论交付和意思自治的关系,“交付原则只是历史上的道具,由此进入现行法的却是合意原则”,他进而认为交付的公示功能只是与其真正目的难以分离的副作用。[18]退而言之,即使此类“观念交付”公示性较弱,但其尚可支撑动产物权的变动。债权作为典型相对权,其权利变动又何须以“公示”为必要?
对于转让型商事债权融资而言,其债权移转虽需让与合意之外的履行行为,但履行方式却绝不局限于让与通知一种。动产物权变动的理论尚且接受除直接交付外的多种“观念交付”方式,且允许对物权变动方式、时点进行意思自治(如保留所有权的买卖合同),债权让与中的权利变动又何须奉让与通知为金科玉律?在对债权让与合同履行方式进行完全立法列举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为出让人与受让人就债权让与合同的履行方式留出意思自治的空间,特别是承认委托出让人代为收款方式的法律效力,能够实现受让人对标的债权的间接受偿,而这也是商事债权融资实践对于让与通知制度最核心的突破。
小学阶段的学生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具有很强的求知欲,教师积极培养学生的兴趣,可以使学生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扩大视野,提高创新能力。传统的教学模式单一的向学生,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利于教学的有效开展。如果利用教学情境法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注重参与到科学探索中,可以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例如在教学《生活中的静电现象》时,让学生先说一说生活中产生的静电,在向学生展示相关的图片,在带领学生做一些有趣的小实验,如用梳子梳干燥的头发或者用经过摩擦的塑料棒靠近纸屑,让学生仔细观察教学现象,营造良好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进行探索,可以有效开展小学科学教学课堂。
(三)以登记作为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
对于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也即债权多重让与中的权利归属问题,理论研究和审判实践分别提出以让与合意生效时间、通知债务人时间、在债权转让登记系统登记的时间等作为确定债权多重让与中权利归属标准的不同主张。对此问题,笔者提出两点看法,分述如下:
早晨起床,杜思雨觉得头昏昏沉沉的。他想,妻子田歌睡一宿觉也许就消气了,一切都会烟消云散的。过去和妻子吵架赌气,妻子大多数都是这样,自己睡一宿,消化消化,也就啥事都没了。但这一次思雨可想错了。思雨来到客厅,发现妻子坐在沙发上好像在等他,身边放着一个大旅行袋。妻子的眼睛红肿,眼圈发黑。妻子一说话,嗓子也变得沙哑。
其一,债权让与对抗要件的设置要以作为生效要件的债权移转依据为大前提,而且应注意协调该对抗要件与生效要件的关系。准确界定债权移转的依据,对于债权让与对抗要件的设置意义重大。潘运华教授曾主张遵循“让与在先,权利在先”的权利归属模式,但其论证的前提是将让与合意作为债权移转的依据。[19]根据本文以上的分析,以债权让与合意作为债权移转的依据绝非是不证自明的,甚或其作为前提的正当性本就可被质疑。此外,通过比较债权让与生效要件和对抗要件的功能可以发现,债权让与的生效要件只需要搭建起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联系,故而生效要件的公示性只需覆盖出让人、受让人和债务人的范围即可。但债权多重让与中的对抗要件则不然,其已涉及债权让与合同之外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由此也必然要求对抗要件具有更强的公示性。就解决多个竞争债权顺位排列问题的对抗要件而言,应当优先考虑各竞争债权所具备的公示性,依其所能表现出的公示性强弱来排列其先后顺序当是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20]
其二,就标的债权的属性和数量而言,民事债权让与和商事债权融资虽呈现不同特征,但二者的对抗要件设置可向债权转让登记的模式统一。曾有学者在考察美国债权让与优先顺序制度的发展历史后,提出美国现今适用的通知登记制当为我国未来债权让与制度改革之方向。[16]相较于将债权让与合同或通知债务人作为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通知登记制彻底摆脱了对于私主体信用的依赖,凸显对抗要件所应具备的公示性,也便于在债权多重让与的情况下对权利归属准确判断。根据《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编的规定,有关债权融资的登记,无需当事人登记让与或担保合同,仅须登记一份融资声明,载明让与人、受让人的名称并指明担保财产,且对担保财产的描述只要可合理地识别描述对象,无论是否特定化。[16]此种登记模式无疑为集合债权的转让提供了莫大的便利。而对于未来收益权转让以及债权秘密让与(如暗保理业务),通知登记制也可以通过变更登记内容及审查标准做以灵活协调。而对于普通民事债权的转让,现有数据技术使得债权交易统一登记平台的建立成为可能。电子登记替代传统的纸质登记,使得成本较往日已大幅降低,原有批评将登记作为债权让与对抗要件的论据多以消弭。登记所能表现出的公示性当无质疑,且将债权让与纳入统一登记平台,便于实现与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制度的衔接,扭转债权融资中“逃离合同法、投靠物权法”[16]的趋势。此外,也无需过分担心登记可能给民事债权让与带来的不便利性。一方面,对抗要件本身更多地体现为对债权受让效力的补强,是否进行登记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即使不登记也不碍于民事主体依让与通知取得债权。另一方面,数据技术的不断进步必然使得债权转让登记系统的操作难度日益降低。凭借数据技术的进步,原有需要去行政管理机关查询、登记的诸如工商登记信息等,现今已可在网络平台自行注册、查询。“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域名为:www.zhongdengwang.org.cn)也将不再是商主体的专属。
事实上,我国已经对债权转让登记做了诸多有益的尝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操作规则》第26条的规定,“登记公示系统为应收账款的转让交易提供信息平台服务。应收账款转让的,受让方可以将应收账款转让的信息记载于登记公示系统。”但遗憾的是,即便搭建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的统一平台,此种登记仍被定位于一种“公示服务”,与《物权法》中规定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分属不同效力位阶。但另一方面,在立法和司法实践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对债权转让登记的积极回应。《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审判委员会纪要(一)》在“登记公示和查询的效力”部分规定,“受让应收账款时,应当……对应收账款的权属状态进行查询,未经查询的,不构成善意。”此外,2018年8月27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草案)》第336条规定“债权人将同一债权转让给数人的,债权转让可以登记的,最先登记的受让人优先于其他受让人。”此二者虽未上升为国家性的正式法律文件,但由此我们可以推测,立法上已经有将登记作为债权受让顺位标准的倾向。
结语:为债权让与制度注入商事思考
富于创新精神的商事债权融资实践为其所依托的债权让与制度提出了很多挑战,且这种挑战集中于债权让与通知制度。对于传统的民事债权让与,让与通知制度不仅符合其制度运行逻辑,也便于一般民事主体的理解和操作。但若将视角转向商事债权融资领域,因标的债权性质、数量的变化,固守让与通知制度就显得不那么恰如其分。依笔者所见,即便商事债权融资对让与通知制度构成冲击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冲击也不意味着对让与通知制度的彻底否定。一方面,让与通知制度对于民事债权让与仍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债权让与合同的履行方式仍需以让与通知为原则。将让与通知作为债权移转的依据,严格遵守了合同效力的相对性,并将债权转让合同的成立和履行准确地区分开来。但另一方面,若僵化地认为让与通知是履行债权转让合同的唯一方式,将彻底动摇转让型商事债权融资所依据的法律基础。
从女人们的命运结局方面比较,《甄嬛传》和《红楼梦》中的女人们都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但是她们悲剧命运的表现形式还是有所不同的。
让与通知制度所遵循的形式主义债权移转模式是其制度正当性的根基所在,将其移植并适用于商事债权融资领域,则需对让与通知制度“去其形而取其神”。对于转让型商事债权融资业务而言,既然以债权让与制度为法律基础,则同样需遵守形式主义的债权移转模式。无论是保理、资产证券化抑或他种融资模式,在其标的债权真实出让的阶段,其债权的移转仍需以对债权转让合同的履行为依据。但在商事债权融资实践中,债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方式可以更多地体现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且应允许作为出资方的受让人间接性地对债务人受偿。诚然,委托出让人代为收款的模式也未必是转让型商事债权融资的最佳选择。但无论采用何种履行方式,以此当可窥见商事债权融资与民事债权让与在行为模式、所遵循法律理念等方面的区别之一斑。我国虽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但不可否认“实质商法”作为一个有机体系始终独立而客观的存在。[21]在未来《民法典》的编纂中,有必要对债权让与制度融进商事化的思考,以拓展其制度对新型债权融资的适用性。基于本文以上分析,笔者对未来《民法典》中的债权让与制度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其一,对于债权让与中的债权移转依据问题,应确立以让与通知为原则,并允许当事人对债权移转的方式和时间进行意思自治。建议将现有《合同法》第80条修改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债权自通知债务人时发生移转,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出让人与受让人另行约定债权移转条件的,不得损害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其二,对于债权多重让与中的权利归属问题,应以登记作为债权让与的对抗要件。《民法典(草案)》第336条“债权人将同一债权转让给数人的,债权转让可以登记的,最先登记的受让人优先于其他受让人”,体现了对债权转让登记制度所蕴含的“公”信用的信赖,也进一步与《物权法》第228条应收账款债权质押制度相匹配,当属较为合适的制度选择。
注释:
在河(沟)道生态修复目标上,综合考虑河(沟)道的防洪、水质、生态和休闲娱乐四个方面的分目标。其中生态目标又包括河(沟)道最小生态流量、水文地貌、河流纵横断面的连续性和生境条件等关键指标的要求;在防洪目标上,主要是要有足够的防洪空间,能安全排泄洪水。该项目制定的6条示范小流域河(沟)道生态修复目标包括:径流流水水质不低于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塘坝水质不低于地表水Ⅳ类水质标准;治理后的生物多样性、水文地貌等级和防洪空间均比治理前提高;生态景观恢复;防洪能力提高。
其次,《合同法》有关债权让与的规定明显区别于其他部门法所确立的意思主义权利变动模式。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对意思主义权利设立、变动模式最典型的规定当属《物权法》第127条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以及《物权法》第158条有关地役权的规定。按照《物权法》中意思主义的权利变动模式,在权利设立或出让的合意达成后,出让人不需对受让人负有移交权利的作为义务,受让人仅凭合意即可获得权利。此后,出让人仅负有不侵害权利、不将同一权利转让给第三人等不作为义务。但《合同法》有关债权让与的制度模式却与此完全不同。为保证受让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有效性,出让人需在让与合意达成后将债权让与的情况通知债务人。此种通知无疑是作为义务的体现,这便从另一角度证明债权让与中的权利移转与意思主义权利变动模式的不同。此外,《物权法》第224、228条对于债券、应收账款的质权设立,规定了质权设立合意之外的交付、登记要件,显然属于形式主义的权利变动模式。债券只是一种证券化的债权,而应收账款债权本就隶属于普通债权的范畴。以此二者为标的设立质权,一旦其所担保的债权不能清偿,对担保物的拍卖必然导致此二者归属主体的变动。申言之,以债券和应收账款为标的设立质权,其本质上应和债权让与遵循同样的制度规则。此外,债权让与本就可被解释为包括债权的完全让与和担保性的债权让与,(如债权质押、债权的让与担保等)。[16]从理论上讲,债权的完全让与将导致债权立时的移转,就权利变动要件的严格程度而言,其要求应高于担保性的债权让与。既然《物权法》就担保性的债权让与(应收账款质权、债券质权)都规定了形式主义的权利变动模式,债权的完全让与也不应坚持意思主义的移转模式,否则将造成制度的失衡和错位。
② 台湾地区民法学界较为通行的观点认为:在为让与通知前,债务人仍可认为债权归属于出让人,甚至在债务人明知债权让与的条件下亦同,因而债务人有权对受让人拒绝清偿。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91页、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2页。转引自申建平:《债权让与制度研究——以让与通知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
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安康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逐渐偏高;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且严重失衡,不仅高于全国和陕西省的比值,甚至高于同属陕南的商洛和汉中两市(表1)。
因了一个“怹”,因了满目深情跃然的“怹”,那篇貌似寻常的怀念师长的文章不再寻常,而那个“怹”——常驻于心上的他,一个与“您”同样厚重的字眼,成为牢牢攫住我心的罗盘。
③ 对于不动产收益权的法律属性,目前学界仍有争议。王利明教授主张将其定性为用益物权,何勤华教授倾向于将其定性为集合债权。参见王利明:“收费权质押的若干问题探讨”,《法学杂志》2007年第21期。何勤华:《日本法律发达史》,王海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④ 《国际保理公约》第5条“(a)保理合同关于转让已经或将要产生的应收账款债权的规定,不应由于该合同没有单独指明这些应收账款债权的事实而失去效力,只要在该合同订立时或这些应收账款债权产生时,上述应收账款可以被确定在该合同项;(b)保理合同中关于转让将来所有产生应收账款的规定可以使这些应收账款债权在其发生时转让给保理商,而不需要任何新的转让行为。”
《联合国国际贸易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8条第1款第(2)项规定,“如果在原始合同订立时,未来债权可被识别是与转让相关的债权,该转让对于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对债务人或对于竟合求偿人而言都是有效的,并且受让人取得优先权。”
⑤ 参见:广州机场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书),http://abs.seid.com.cn/plxx/s_zqjys/2016/01/194563.sht;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729/125065484.shtm,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月21日。
弥散度室内测定值不适用于大范围的研究区污染物弥散数值模拟[9],因此,纵向弥散度应参考前人在该场地得出的研究成果[10],根据研究区附近试验资料,计算纵向弥散度与观测尺度的统计关系,并按照偏保守评价原则取值,纵向弥散度取值48.375 m,横向弥散度为纵向弥散度的10%。查阅已有的研究区研究成果资料,确定研究区岩体平均孔隙度为0.30。
⑥ 参见长安银科:以“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让资产流动起来,http://www.cfec.org.cn/view.php?aid=1882,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1月21日。
⑦ 按照我国现有税收制度,以公司形式构建SPV,公司本身需要缴纳所得税,比照信托制度存在双重纳税的劣势。另外,《公司法》规定了公司设立、管理和注销的一系列强制性规定,SPV作为一个特殊目的的暂时性存续机构,以公司法人作为其制度建构,将造成后续运营的一系列不便利性。
(1)薇甘菊颈盲蝽PmGSTd1是属于GST delta家族的一个分泌蛋白,与温带臭虫(Cimex lectularius)GST的亲缘关系最近。
⑧ 法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其《民法典》第1690条规定,“债权受让人仅依其向债务人送达权利让与的通知,始对第三人发生占有权利之效力。”与此类似,具有判例法传统的英国在Dearle V. Hall案中确立的“英格兰规则”,也同样承认先行对债务人进行通知者优先受让债权。
⑨ 李宇在《债权让与的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一文中,将学界对于债权让与对抗要件的观点分别归纳为“让与主义”、“通知主义”和“登记主义”。其中,“让与主义”的观点认为让与合同成立在先,受让人的权利优先;“通知主义”的观点认为先通知债务人的受让人权利优先。“登记主义”的观点认为已登记的债权受让人优于未登记的受让人,先登记的受让人优于后登记的受让人。本文借用该文的概括方法。参见李宇:《债权让与的优先顺位与公示制度》,《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101页。
⑩ 理论上将《物权法》第25、26、27条所规定的交付方式称为“观念交付”。参见王利明:《物权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2页。
参考文献:
[1] 刘建文.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型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J].政法论丛,2016,5.
[2] 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3] 王利明.民法总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4] 龙卫球.债的本质研究:以债务人关系为起点[J].中国法学,1995,6.
[5] 潘运华.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法律效力——从(2016)最高法民申8号民事裁定书切入[J].法学,2018,5.
[6] 申建平.债权让与制度研究——以让与通知为中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7] 李永军.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坚持规范属性[J].政法论丛,2016,1.
[8] 于海涌.法国不动产担保物权研究——兼论法国的物权变动模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9] 庄加园.《合同法》第79条(债权让与)评注[J].法学家,2017,3.
[10]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1] 黄立.民法债编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 王勤劳.债权让与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12.
[13] [德]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卷)[M],周忠海,等云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14] 刘燕,楼建波.企业并购中的资管计划——以SPV为中心的法律分析框架[J].清华法学,2016,6.
[15] 沈朝晖.企业资产证券化法律结构的脆弱性[J].清华法学,2017,6.
[16] 李宇.债权让与的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J].法学研究,2012.6.
[17] 刘家安.论通过返还请求权让与方式实现动产所有权移转[J].比较法研究,2017,4.
[18] 庄加园.交付原则框架下的意思自治[J].法学,2017,3.
[19] 潘运华.债权二重让与中的权利归属[J].法学家,2018,5.
[20] 程啸.论动产多重买卖中标的物的所有权归属的确定标准——评最高法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9、10条[J].清华法学,2012,6.
[21] 范健.论我国商事立法的体系化——制定《商事通则》之理论思考[J].清华法学,2008,2.
The Impact of Commercial Debt Financing on the Credit Assignment Notification System
Yu Zheng -ping Chen Xin -di
(Law School of 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 110036)
【Abstract 】For the assignment of creditor’s rights , the rationality of the transfer notification system is to follow the “formalism” of credit assignment. However, faced with new financing targets such as future income rights and collective accounts receivable, the notification system will shake the legal basis of commercial debt financing.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transfer notification,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at the assignment of creditor’s rights is subject to the obligation to perform the contractual assignment of creditor's right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to allow the parties to autonomy in the manners of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In the legislative system of “combination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the future “Civil Code” should incorporate commercial debt financing into the scope of regulation of the credit assignment system. For the effective elements of the assignment of creditor’s rights, the principle of giving notice should still be used, but the parties should also be allowed to autonomy on the conditions and means of transferring claims. For the confrontational elements of creditor’s rights, the order of registration time should be used as the criterion for determining the attribution of multiple credits.
【Key words 】commercial delit financing;the assignment of creditor’s rights; transfer notification system;collective debt rights
【中图分类号】 DF438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虞政平(1968-),男,江西余干人,法学博士,最高人民法院一级高级法官,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辽宁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陈辛迪(1991-),男,辽宁辽阳人,辽宁大学民商法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文章编号】 1002— 6274( 2019) 03— 084— 12
(责任编辑:唐艳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