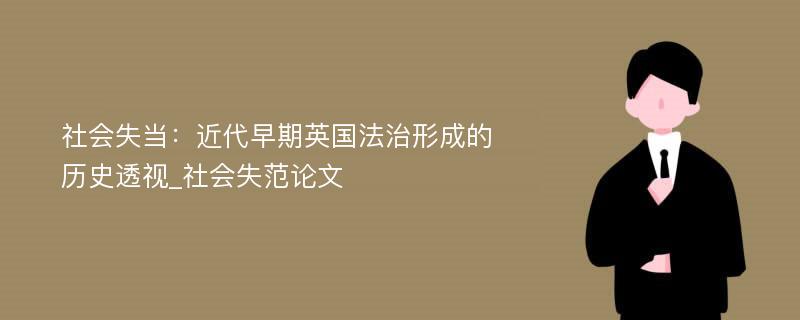
社会失范视域下:近代早期英国法治秩序形成的历史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英国论文,近代论文,法治论文,透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5)03-0105-05
社会失范概念,最初是由法国社会学家杜克凯姆(Emile Durkheim)所使用。他曾指出,在一个高度失范的社会中,由于社会成员没有共同的生活目标与价值标准,缺少行为的指南与约束,因而这个社会有解体的危险[1](P246-247)。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杜克凯姆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社会失范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同决定着达到这些目标的规范不一致。即当社会所规定的目标与用以达到这种目标的手段不一致时,社会出现失范[2](P12)。近代早期英国,伴随着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社会结构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的转型,新旧社会价值构成、制度规范难免处于剧烈的冲突和碰撞之中,社会曾一度失范。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莎士比亚借《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俄底修斯之口表达了对英国这一时期社会失范的洞察:由于旧的社会价值观和秩序正在式微,而新的社会价值观和秩序又没有得到认可和确立,社会难免处于动荡之中[3](P11)。本文拟通过对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失范的发生机制及法治秩序的形成,作一简要历史透视,以求加深和丰富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失范现象认识。同时也希望能对当下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法制建设有所启示,因为提供经验智慧的钥匙存在于历史之中。
一、个体本位:新的社会价值构成
近代早期英国,发生了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在中世纪英国文明史上,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只是到了近代早期才开始出现新的转机。近代早期英国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较高,其表现也较明显。克拉潘曾指出:“‘历史是一件无缝的天衣’,而在它的经济和社会方面往往更难发现类似接缝那样的痕迹。这件历史的天衣的变化往往是极其缓慢而难于觉察的。可是,十六世纪初叶所能追溯到的那些变化却没有被忽略,这些变化几乎暗示出一条接缝和一块新的材料。”[4](P257)这一接缝和新材料就是英国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此时,英国货币经济的发展已由城市开始拓展到整个英国社会,正像米歇尔·博德所指出的:“在这个时候,谁会想到一个新的上帝——资本,正在准备统治世界呢?或许,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写《乌托邦》时,已感觉到这一情况的到来。在此书中,葡萄牙海员希尔斯拉德宣布:‘不过,莫尔先生,把我内心的感想坦率地对你说吧:只要私有财产存在,只要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我以为一个国家就不会得到公平恰当的统治。’”[5](P12)也就是说,对于货币经济引发的社会失范,“对于伴随这政治和经济发展而来的旧有价值准则和典章制度之摧毁,有许多人是激烈反对、甚至感到震骇的。托马斯·摩尔就曾用讽刺和忠告,最后用他的生命,反对都铎王朝的经济和社会政策”[6](P177-178)。
个体本位的出现是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近代早期英国货币经济的发展,从根基上瓦解了传统社会结构。它斩断了传统群体本位的“共同体”纽带,将“共同体”分解成原子式的个人。对于近代早期英国货币经济对原子式个人生成的事实,霍布斯已有深刻认识。尽管在17世纪货币逻辑还处在襁褓之中,但是他已经很有预见地指出,货币的逻辑将导致人类社会的原子裂变。假如说前现代化社会将个人以及他们为了生存而从事的劳动纳入一个即使经常有点粗糙和不完善的“宇宙”之中,即纳入一个集社会监控和一定程度上的安全保护于一身的文化整体之中,那么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则是彻底解散所有的集体,以纯粹的金钱关系取代由文化决定的共性和相互的责任。由此,麦克弗森指出,霍布斯的《利维坦》描述的正是霍自己生活的时代里,归属感不断衰落的英国状况[7](P15)。用麦克弗森的话来说,近代早期英国个人自由的根源在于承认占有财产的分离的人,承认人归根到底是他的人格或能力的拥有者,而不能将它们归属于社会,人是占有财产和渴望获得财产的经济动物[7](P263-264)。也正像马克思形象地说:“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能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8](P103-104)所以,英国宪政史家米勒指出:“自由的途径是物质的进步,在英国,自由权起源于近代,而不是在古代。”[8](P100)即“通过财富的增长和分散,商业社会的发展可以在民众中培育一种独立感和自由感”[9](P100)。
在货币经济社会,货币是私人财产和个人利益形成的形式手段。马克思指出:“货币是把财产分割成无数小块,并通过交换把它一块一块吃掉的一种手段。”[10](P447)货币是最典型的可分割且具有多种用途的物品,货币对任何财产具有分割和同化作用。韦伯也认为:“从进化的观点看,货币是私有财产之父;它自始就具有这种性质,反之,没有一种具有货币性质的东西而不带有私人所有权的性质。”[11](P200)个人通过货币占有,实现了对社会财富的分割和个体化占有。“mutuum”(货币)这个词是从meum(我的)和tuum(你的)演变而来的。货币也是加深“我”与“你”之间差别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货币的占有,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与别人不同的、分离的个体。货币性占有,为个人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现实基础。而近代早期英国个人自由的唯物主义因素,就是个人对货币财富的占有。用麦克弗森(Macpherson)的话来说,就是财产积累个人主义,或者再确切地些,是货币占有性个人主义[7](P341)。这也说明了私人财产,不是国家乃至社会创造的,它首先是一种事实,是一种经验的存在。而国家和社会所要做的只是对其给予道德和法律社会认可。也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利益不仅仅作为一种个人的东西或众人的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12](P27)所以,恩格斯指出:“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13](P539)
二、法治秩序:新的社会制度规范
近代早期的英国,伴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正经历着一个愈发显著的利益分化。从传统共同体下分化出来的个体开始有其自身个人利益,从而使英国进入了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货币经济对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影响,麦克弗森的观点要旨非常简单:以财产为基础的、实际上是依附于货币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并产生了一个“占有性市场社会”。占有性市场社会“使人与人之间充斥着竞争性和侵略性关系”[7](P271)。在此情况下,诉讼的增多,对普通法的普遍崇尚,特别是对法治的崇尚,成为近代早期英国给世人留下的最为醒目的历史景象之一。15世纪末,威斯敏斯特的中央法庭每年处理的新案件达到3000件,这在当时人口可能不超过200万的英格兰是一个颇为令人注目的数字。在1560年至1640年之间,位于威斯敏斯特的两个主要普通法法庭——王座法庭与高等民事法庭,所受理的案件有了巨大的而且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增长。在1580年,这两个尚处于发展阶段的主要法庭共处理了13300件案件;到1606年,处理的案件的总数已增至23453件;到1640年达到29162件。随着诉讼的增多,涉及契约和法律的事务增加,律师行业日渐兴旺起来。在16世纪末的英国,没有一个郡、城、镇,甚至没有一个村没有律师,其中最富的年收入高达二三万镑,差的也能达到1.2万至1.4万镑[14](P23)。
诉讼增多,是传统社会秩序向现代社会秩序变革的表现。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形成,日益确立的个体本位社会价值构成,已经与传统的宗法的伦理秩序不能相容了。斯通把近代早期英格兰诉讼的激增解释为乡村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裂缝扩大,邻里间的冲突日益加剧的结果[15](P32)。由于个人利益的出现和社会利益的分化与冲突的增多,传统的社会伦理秩序必然日渐失效。于是,法治秩序开始成为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主导模式。人们开始将打官司作为解决冲突的一个手段。由于起诉能使案件公开,并以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解决,最重要的是,诉讼比暴力更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日益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化解社会矛盾的方式。如恩格伦指出:“各种不同意见与冲突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但重要的是,法治的存在……法律诉讼的增加平衡了社会对暴力的承受能力,减少了发案率,它标志着英国向一个以更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文明社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6](P116)此后,法律在近代早期英国,日渐成为一种新的、强有力的社会粘合剂,在社会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方式。
近代早期英国的法治秩序主要是用来维护和保障个人的私有财产、契约自由的。从17世纪早期开始,英国普通法已持有这样的观点:财产是自由的本质[17](P147)。1641年,当一个议员在解释他对“自由”的理解时曾说:自由是“根据一定的法律,我们得以知道,我们的妻子、儿女,我们的奴仆和我们的财产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建造,我们耕作,我们播种,我们收获,是为了我们自己”[18](P44)。戴维斯警官1620年开始主管约克巡回法庭时就曾提出了这一点。他指出,若没有司法,“陆地上窃贼横行,大海中海盗猖獗,平民起来反抗贵族,而贵族则会起来反抗国王,我们将茫然失措,我们将不知道什么是属于自己的,什么是属于别人的……总之,万事难料,没有契约,没有贸易,没有交往,所有的王国与财富都将毁灭,整个人类社会都将解体。”历史学家廉姆·坎登(William Camden)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也写道:“明确我的(meum)和你的(tuum)……正是英国法律的目的。”[19](P107)法学史家阿业如实地记录了当时英国的情况:“法官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财产权利、执行与财产有关的契约、惩罚犯罪行为。其中绝大多数犯罪行为被视为对财产权利的危害。”[20](P95)一言以蔽之,在英国近代早期的英国,“法律规则的首要目标是使社会中各个成员的人身财产得到保障,使他们的精力不必因操心自我保护而消耗怠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法律规则中必须包括和平解决纠纷的手段,不论纠纷是产生于个人与社会之间,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21](P41)。
总而言之,英国伴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的分化,旧的社会秩序出现了危机。同时,由于经济利益私人化、主体多元化而出现的利益个体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矛盾的复杂化,引发和强化了人们的诉讼意识,并扩大了司法机构在经济生活中的影响,为树立司法权威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根本可能。事实上,人的多样性及其社会关系中所表现出的利益多元化最能符合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但不同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对这种多样性和多元化所能容纳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简单地因为利益冲突的产生而否定利益多元化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创造力和破坏力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利益的多元化、多元利益主体间的公平自由竞争最能促进社会进步,最能带来高效率和增加社会福利。同时,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混乱,关键的是采取何种秩序来协调和解决这些利益冲突。法治秩序正是这种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法治秩序正是协调和解决多元利益冲突的最佳秩序,它通过和平的而非暴力的方式将社会矛盾进行化解和吸纳。法治秩序在保证人们自由和创新精神的同时,也限制了人们行为的盲目性和破坏性。以保证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个人的公平追逐私利从而不致于发生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的“狼与狼”的战争,并且最终每个人追逐私利整合到增加、提高社会福利的道路上。
近代早期英国法治秩序确立的标识,是在16世纪末从意大利直接引入了isonomia术语,意指“法律平等适用于各种人等”,稍后翻译李维(Livy)著作的学者以英语形式isonomy替之,意指法律对所有人平等地适用以及行政官员也负有责任的状况。此一意义上的法治在17世纪得到了普遍使用。直到最后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法律之治”(government of law)或“法治”(rule of law)等术语取而代之[22](P206)。此后,法治秩序,在英国开始成为消弭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冲突的重要理性化技术,成为社会的减压阀与利益平衡器。当地位平等的多元利益主体间发生纠纷时,便开始诉诸司法裁判,司法站在中立的立场上,通过正当程序对纠纷给予公正处理。它通过程序所保障的中立性,对社会矛盾、冲突、利益磨擦与利益对抗进行协调和裁决,无论在过程上和结果上很容易得到社会普遍性和正统性的认同。它能将社会冲突在真正意义上纳入程序裁判之中,通过程序公正使得正义看得见。从而也使得人们对法治秩序产生了信仰,因为现代信仰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的利益感知和理性认同。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近代早期英国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货币经济社会中,法治秩序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近代早期英国的个人自由,是以竞争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由。货币经济下,既然私有财产是事实存在的,那么合理谋利便成为人的正当权利。这里的“合理”是倾向于对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形式意义理解,即将每个人权利的平等归结为机会的平等。于是,保护和鼓励自由竞争的放任主义便成为自由实现惟一可取的形式选择。这也正是我们认知近代早期英国法治秩序形成的落脚点。
首先,引发英国社会失范的深层机制是货币经济的发展。究其深层原因如下:在传统社会下,由于自然经济的自足性,农业社会缺乏横向交流和纵向社会流动,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等级的社会。人的社会活动空间狭小,人与人之间的简单交往体现在自然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中。自然经济产生的是亲族共同体社会,人们之间大都相识。人们持有相同的价值观念和标准,对社会行为的规范主要采用非正常的手段血缘纽带,如风俗习惯、特权等级、宗教神谕等等一些源于经验思维的“自然”方式。而货币经济社会中的人开始由从等级身份和血缘纽带的集团本位走出来而成为独立、平等的“原子式”经济人。人们之间大多不相识,社会交往常面对陌生人而非熟人。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基于亲缘的联结,而是基于对对方商品的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自愿性的而非义务性的,体现的是一种契约关系。在此情势下,传统的秩序规范必然失效。
其次,货币经济社会运行,只能由法治秩序来维持。在货币经济社会中,人们在通过货币剪断传统纽带而获得独立自主后,也丧失了传统的群体归属纽带,相互之间产生了陌生感和不信任感。激烈的竞争更强化了这种疏离感,并几乎发展为对立和冲突。同时由于货币的中介和抽象还原作用,人们之间的交换和互认模式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商业”。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合作变得可能并有效,惟一的选择是通过约束性协约,即通过契约的方式来实现新的社会性合作。几乎所有的契约论者都强调,正是为抵御暴方冲突的风险,或克服无序的利益追逐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人们才在求共处、求互惠的愿望驱使下,收敛自己的任性妄为,而缔结契约。而契约的维护需要法治秩序来保障。因为,以货币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是一个为个人私欲推动的社会,它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保护现代个体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又要保证那些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自由个体能够在交往中形成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而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只要他能从不诚信的行为中得到的好处大于他要为此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违背诚信。这就需要一个维护社会诚信的契约法治秩序,来为社会提供一个平等竞争的发展氛围和制度环境,从而实现社会竞争与和谐的统一;从而使得社会关系的调控不再是以人情、血缘的方式,而是通过理性和法律形式来实现。亦即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这个自私自利的世界,人的最高关系也是法律规定的关系,是人和法律的关系。”[23](P449)也就是说,货币经济社会只能通过理性的、正式的制裁手段——法治秩序来规范社会关系。
最后,通过货币的分割作用,社会财富分化为无数个体所有,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权利与义务观念和社会网状结构加强,从而为法治秩序的建构提供契约基础和社会关系结构。在此过程中,货币经济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权利与义务关系模式——这正是法治秩序所必需的社会关系模式。即“我给,为了你给;我给,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给;我做,为了你做”[24](P591)。“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8](P196)。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由于商品实际上只能是自己劳动的物化,并且正像自己的劳动实际上是对自然产品的实际占有过程一样,自己的劳动同样表现为法律上的所有权依据。“法律的精神就是所有权”[25](P368),而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是通过自己劳动的所有权取得的。在此情况下,“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反过来也一样,相反地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是自愿地出让财产”[8](P195-196)。这实质上是以契约为媒介,通过互相转让而互相占有。在这里,契约代表着是—种利益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利益交换,契约是一种讲究互惠合作与合理谋利的理性制度。共同获利是契约发生的原初动因和基本前提。于是,维护契约的“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性、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23](P71)。
总之,近代早期英国,正是通过对法治秩序的不懈追求,才最终跨越了由传统到现代带来的“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社会失范瓶颈而进入现代契约文明的。现代文明在本质上是一种契约文明。并且,近代早期英国法治秩序形成的历史,也经验地证明:缩短和降低自然经济社会向货币经济社会的社会失范的时间和危害的惟一手段,就是加速构建法治秩序。根本说来,现代市场秩序和契约文明的形成,是法治而非德治的结果。
[收稿日期]2005-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