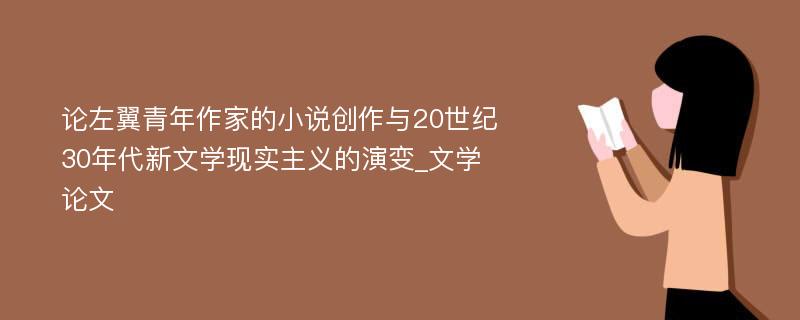
论30年代左翼青年作家群的小说创作与新文学现实主义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左翼论文,现实主义论文,作家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系作者《论30年代左翼青年作家群崛起的社会历史原因》、《论30年代左翼青年作家群小说创作的基本特质》(见本刊1992年1、3期)的姊妹篇。于前文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左翼青年作家群的小说创作与新文学现实主义流变,指出:左翼青年作家群的小说创作不仅克服了早期“革命文学”创作中的种种失误,实现了对“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复归,而且对“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作出了拓展和超越,使新文学现实主义具有更为丰富、生动的内涵,推动了现实主义文学走向成熟。
一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学思潮,在我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出现的现代文化意识的一部分,它伴随着“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而走上中国文坛,与浪漫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创作领域中并驾齐驱的两大文学潮流。然而到了3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却出现了令人难忘的历史沉重感,大革命的失败以及接踵而至的一连串政治事变所产生的强大反作用力,使“五四”所开启的有相对思想自由的时期宣告结束,新文学创作也出现了急遽地整体性嬗变:一方面,严峻的社会现实迫使作家们的创作由个人感情生活的狭小天地转向集体社会生活的广阔世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分道扬镳,崇尚客观再现成为30年代据主导地位的文学风气;中一方面,为顺应社会和政治形势的需要,在“文学要成为无产阶级最高的政治斗争之一翼”①的主张下,新文学创作更加峻急地参与现实生活,并显示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左翼文学被紧紧地连接在政治斗争的脐带上。上述变化的结果使原来仅仅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与其他各种社会思潮交织一体,呈现出与“五四”时期多元统一格局迥异的单元划一的固定模式。新文学创作在艺术与政治、真实性与倾向性、非审美的功利观与审美意识等一系列问题上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双重的困惑和两难的选择。
正是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为了适应无产阶级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需要,1928年爆发的“革命文学”运动就成为现实主义发展历史中的必然产物应运而生。但是,作为“革命文学”运动主要倡导者的创造社、太阳社作家中,除一部分是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家是刚从大革命前线撤下来转移到文学阵地上的,政治上的失落感伴和着激烈愤懑与痛苦狂热的情绪,使他们急于把在武装斗争中失去的东西借用文学的形式来获得,把急迫的政治斗争要求在文学中表现出来,以发泄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加之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缺乏深刻的理解,理论的根底很浅,这一切必然导致了“革命文学”在创作上的缺陷:阶级对抗的严重和文化准备的不足,以及过分强调革命的功利而忽略了文学的独特性。因而“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在理论上偏颇地认为“文学是宣传”、“文学,与其说是社会生活的表现,毋宁说是反映阶级斗争的实践和意欲”,因此“革命文学”就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②他们还把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五四”新文学统统作为批判对象,否认左翼文学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联系,把“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作为“过时的文学”进行批判。在创作上则提倡集体意识、阶级意识而否定个性意识,否定创作中的“自我”和艺术个性,将文学作品仅仅作为阶级意识的“留声机”。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以“革命浪漫谛克”为特征的文学创作取替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并产生了两种类型的普罗小说。一种类型是被称为“革命+恋爱”的革命小说,以蒋光慈的创作为代表,如《少年漂泊者》、《短裤党》等。这类作品多数能及时反映革命的重大题材,有某些真实的事件和报告性的材料,兼有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双重特点,为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摄下了历史性的场面,并且展现了知识者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心理历程,因而自有它的历史功绩和存在价值。但是,这类作品的弱点也极为突出:这些作品往往过分渲染爱情的力量,把爱情作为调料,任意加进一些脱离作品发展的“革命+恋爱”的情节,于是就产生了“恋爱使‘革命’显得浪漫,革命使‘恋爱’找到出路”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和不健康的“革命罗漫谛克”情绪。另一类作品是正面描写工农觉醒和革命斗争的小说,如钱杏邨的《义冢》、阳翰笙的《地泉》等,这些作品一般都离不开“工农受压迫——逐渐觉醒——奋起反抗——取得胜利”这一情节模式,并且明显表现出作者对工农生活的隔膜,他们只是为了宣传某些政治道理而去演绎、图解政治概念,其作品必然存在严重的标语化、口号化倾向,破坏了作品的艺术与审美价值。因此,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和斗争形势的深入,这两类“革命文学”作品引起了人们越来越甚的不满和厌倦,并导致了创作上的萧条,人们意识到即使是把文艺作为斗争的武器,那末也需要更为称手、更为有力的武器。这一切清楚地告诉人们,新文学现实主义流向正面临着一场如何跟上时代发展,适应新的形势的严峻考验。
也许要稍稍推开一段距离,才能更深切地感到历史前进的脚印。历史选择了现实主义并把它推向首座的地位,同样,现实主义也是以极大的自强精神,通过对内对外的自我调节,寻找自我发展的途径。广大左翼作家在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创作实践后,从自身的弱点与错误中意识到要使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得以继续和发展,必须寻找新的方向。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国内文艺界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于是,人们把目光转向国外。1929年,由“拉普”提出并得到“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大会”认可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被引入中国,成为左翼文艺运动“法定”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得到提倡。这种创作方法的提倡,在左翼文坛形成了一种新的创作风气:即作家们注意摆脱“革命文学”初期那种激情的浪漫主义,转向社会性题材的开拓,进而注重对社会现象作阶级剖析,由此创作出一些与前一阶段作品明显不同的小说,最突出的标志是1931年丁玲的中篇小说《水》的创作与发表。《水》以同年16省水灾为题材,表现一群灾民同洪水、饥饿搏斗,与官绅斗争而觉悟的过程。这篇小说是丁玲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转向:从表现狭隘的小资产阶级男女青年的幻灭、动摇,转向表现农村阶级斗争的重大题材,并且克服了以前的小资产阶级的浮浅热情和对革命不切实际的幻想,创作方法开始由主观表现转向客观再现,在注意社会剖析的同时,注重描写现实。这样,她就把新写实主义所需求的“写实”和“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世界观要求在创作实际中结合起来了,从而使当时在理论上对现实主义还无法作出准确界定的左翼理论家,以及在创作实践中一时还把握不准现实主义路子的作家们,立时似乎都看到了一个“范本”,因而被公认为是一篇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小说。冯雪峰把这篇艺术上仍比较粗糙的速写式小说看成是“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初步兑现”,是丁玲从“离社会到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从浪漫谛克走到现实主义;从旧的写实主义走到新的写实主义的一个路标”;并宣告了“一种新小说的诞生”。③茅盾也把《水》的发表看作“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是文坛全体,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的界碑。④在这种导向和趋势之下,30年代初,左翼青年作家们创作了一批以重大社会问题为题材,表现工农觉醒斗争的作品,例如葛琴的《总退却》、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楼适夷的《活路》等。这些作品大都注意用阶级分析的眼光去观察和表现社会,反映群众中革命意识的增长,又比较写实,较以前的创作有更多的生活气息和更真切的人物刻画,基本上褪尽了前一段“革命文学”中的那种浪漫谛克气味,标志着左翼现实主义文学在这一阶段所实际达到的程度。
然而,当时左翼作家所主张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毕竟是左倾机械论的口号,它虽然在促进作家注重现实题材与社会分析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根本的弱点在于只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直线式的决定作用,却没有提出具体的艺术方法论的内涵,将世界观混同于创作方法,似乎只须掌握唯物辩证法,就可以直接进入创作,而且能够写出好作品。这种貌似全面实则刻板的创作观念必然导致从另一个方面脱离生活的概念化创作。可见,这一阶段的现实主义创作在某些方面比前一阶段有进步,也更成熟了,但是还存在着许多混乱、模糊的观念,左翼文学在理论和实践上要达到真正的现实主义高度,无疑还需经过艰苦的努力。
幼稚可以成熟,胜利之路是踏过一次次的挫折和失败之后形成的,每克服一个错误,就在通向胜利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客观地说,1928至1929年的“革命文学”运动和1929至1932年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提倡,都是无产阶级政治力量要求在现实主义文学领域中表现自己的努力,也是现实主义思潮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几次不太成功但又不可缺少的尝试,这种尝试虽然是粗浅而且幼稚的,但它使广大左翼作家从一次次的失误中认识到现实主义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和文学发展的需要。因此,当历史进入30年代中期(即1933年前后)时,左翼现实主义文学终于突破了重重障碍,真正地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
这种转变首先是从理论上取得突破的。1933年1月,周扬发表于《现代》杂志4卷1期上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在左翼文坛激起巨大反响,这篇文章奠定了30年代左翼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理论基础。它首先认真地从哲学层次的高度批判了“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机械论,指出:“‘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忽视了艺术的特殊性,把艺术对于政治、对于意识形态的复杂而曲折的关系看成是直线的、单纯的。换句话说,就是把创作方法问题直线地还原为全部世界观的问题,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错误。”这个观点对“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无疑是有力的一击。同时,文章还介绍了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典型的论点,提醒人们注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之正确传达,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有怎样重大的意义。”尽管周扬的文章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介绍和解释还有不够准确、全面的地方,但它代表了中国革命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要求,强调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必须从本质上反映社会动向和历史趋势,这对于引导当时的左翼作家正确观察和反映生活,无疑是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的,在相当一个时期里成为指导我国左翼现实主义文学的权威性论点。
创作不完全受制于理论,但理论对于它的指导还是较清晰地反映出来了。在理论的指导下,创作上的转变与突破则首先是由一批左翼青年作家实现的。1933年前后,丁玲、张天翼、沙汀、吴组缃、罗淑、艾芜、周文、端木蕻良、叶紫、蒋牧良、葛琴、肖红、肖军等一批青年作家,作为现实主义创作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涌现于文坛。比起前一辈从国外归来的“革命文学”倡导者来,这批青年作家的生活底子更丰厚,受左倾机械论的影响也更少一点,其中许多人还直接在鲁迅的指导下从事创作,所以他们能够比较自觉地实践现实主义,注重在再现生活时,运用社会剖析和典型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既深入剖析各种社会关系,提出并讨论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又十分重视对人物个性独特命运的描写,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揭示现实的某些本质,并显露出各自的艺术风格,在不同的写实取向中有突出的建树,从而写出了一批坚实的作品,如丁玲的《母亲》,张天翼的《包氏父子》、《清明时节》,沙汀的《代理县长》,艾芜的《南行记》,周文的《雪地》,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叶紫的《丰收》等等。可以说,恩格斯所要求的现实主义文学,在我国是到了30年代这一批左翼青年作家手里才比较广泛地实现的,他们的涌现标志着新文学现实主义真正结束了“革命文学”的时代并迈入一个新的阶段,而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潮流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支新生力量,才能够以浩大声势继续向前发展。
二
在从理论角度对3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脉络作一番清理之后,再从创作方面看看由于左翼青年作家们的介入,新文学现实主义潮流呈现出哪些新的特色。因为只有最终考诸创作,才能更完整地显现出左翼青年作家们的创作对整个现实主义思潮发展作出的促进与推动。
如果说新文学第一个10年的现实主义使命感主要是抒发个性解放的心声,以表现自我生活(特别是爱情婚姻生活)遭遇及心理变迁为特色。那么,在第二个10年中,由于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人们所关心的已不再是个性的解放,而是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这一现实必然使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左翼青年作家们,把自己的艺术目光更多地倾注于多难的民族和人民,用文学作品去反映并剖析造成这种状况的阶级和社会原因。因此,3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科学的世界观指导下深刻地剖析中国社会,并通过生活断面再现社会真实面貌,揭示中国社会本质的社会剖析小说的产生和兴旺。对此,严家炎先生认为:“应该说,社会剖析派在中国产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只要以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为代表的重视社会剖析的欧洲现实主义能够传入中国并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只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科学能够传入中国并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只要这两种思潮能够在文学实践过程中相互结合并确实造就出一批社会科学家气质的作家;那么,社会剖析的形成就是不可避免的。”⑤毫无疑问,在这里“社会剖析”并不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或手法,而是被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精神和原则得到普遍的重视。左翼青年作家中就产生了这样一批具有社会科学家气质,并试图以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方法来对中国社会的人生世相加以冷峻剖析的作家,他们继承了“五四”乡土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农村——这个原本就为自己所熟悉并早就孕育在心灵深处的审美世界——为创作题材,写出了一批充实、成熟的乡土小说,显示了30年代左翼文学向现实主义深化的实绩。然而,与“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明显不同的是,左翼青年作家们的乡土小说具有更为鲜明、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剖析色彩,能够以逼近时代的自觉来关注、反映“全盘的社会现象”,尤其对关涉社会动向与阶级关系的重大事件更为关注,从而把作品的思想倾向由“五四”的启蒙主义推进到以阶级论为中心的历史意识,并使“五四”乡土小说纯情的浪漫主义回归到现实主义主流之中。这一点我们可以从30年代中期许多青年作家的以“丰收成灾”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得到实证:
1933年前后,围绕“谷贱伤农”、“丰收成灾”的社会问题,包括茅盾、叶圣陶等老一辈作家在内的许多进步作家写了大批小说,企图以文学手段去揭示与探讨农村破产及阶级变动的状况。在这类作品中,左翼青年作家叶紫的《丰收》、夏征农的《禾场上》和蒋牧良的《高定祥》是其中的佼佼者,具有较高的代表性。《丰收》中的云普叔在灾荒、饥饿中苦苦挣扎,终于获得丰收,然而,金黄的“救命宝”并没有为这个受尽煎熬的贫苦老农打开一条活路,“他辛苦一年种下的谷子,都一担担被人挑走”,儿子立秋也因抗租被地主团防局杀害,丰收反而把他一家推入更黑暗的深渊。《禾场上》的佃农泰生熬过了几年的水灾、旱灾、虫灾,好不容易得到晚稻“十足的收成”,但谷子刚上场就被地主掳掠一空,“整年的辛苦完全为了别人”。蒋牧良笔下的“高定祥”则把还债的希望寄托在年成丰收上,结果他虽然得到了丰收,但“洋米洋面”潮水般涌来,米价不断暴跌,即使把谷子全部卖掉,也无法还清债务,丰收的欢乐登时被绝望的现实击得粉碎,高定祥终于被迫在丰收的年景中走上了逃荒的路。
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丰收成灾”的社会和阶级根源,它不象过去同类题材小说那样,满足于直接描写贫苦农民的悲惨境遇,或以浓郁的伦理批判色彩表达反封建的主题,而是从社会经济变动的角度去发掘和表现农民日益贫困的根本原因,以及农民反抗意识的觉醒。由于作家将笔力用在社会剖析上,概括了更丰富的社会矛盾,因此他们的小说呈现出反帝与反封建相交融的深刻内蕴,不仅在现实主义深度上比20年代的乡土小说有明显进展,而且使作品带上了格外鲜明的时代色彩。同时,注重社会剖析成为左翼青年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品格,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五四”现实主义关注现实的传统,在左翼青年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更高层次的发展,文学更加贴近社会生活,作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去观察和表现生活,深入分析各种社会关系,提出并讨论重大社会问题,这就使30年代左翼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大大增强了时代所要求的社会性与思想性。吴组缃30年代的小说创作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一个具有社会科学家气质并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左翼青年作家,吴组缃在“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文学是否可以拿来当作解剖社会的工具”等问题上,是持肯定态度并主张功利主义文学观的。他认为“文学决不是艺术象牙塔中的神秘的娱玩品”,而应该“站在时代思潮的前面,真实地反映当前社会与时代的‘内在’与‘外在’,指示着我们应该怎样做、怎样生活”。尤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文学更应该对社会负有严正重大的使命。”⑥但是,将现实主义仅仅概括为功利性和战斗性是不全面的,所以在强调时代需要和功利价值的同时,吴组缃也反对以“工具论”而否定文学的审美功用的极端观点,主张文学的功利价值与审美需要相统一的观点。因此,他的作品善于从总体上去把握社会,再现社会,把小说艺术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运用横断面的写法,缩影式地反映“整个的时代与社会”。⑦他的《官官的补品》、《栀子花》、《金姑娘与雪小姐》等小说,即显示出作家以科学的社会观点来观察和剖析社会的现实主义特征。在《官官的补品》中,作家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运用“反讽”的笔调叙写了一个地主大少爷将人奶当补品吃并残杀奶妈丈夫的故事,反映了农民和地主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刻画了农民阶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悲凉情景。《栀子花》在描写失业店员祥发家破人亡的悲剧时,通过小说人物的认识,揭示出产生这种悲剧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在中国“经济完全踹在帝国主义脚下,政治是如此的紊乱;内地的农村社会加速崩溃”。而要改变这混乱黑暗的社会,就只有“彻底革一次命”。即使是描写妇女题材的《金姑娘与雪小姐》,作家也同样深刻地揭示出社会制度是造成妇女悲剧命运的根源,说明“金小姐是被这社会用封建统治的毒害给沦落了的,雪姑娘则是被这社会用资本主义的方式给蹂躏践踏成污泥的”。并启示人们:妇女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就只有拿出力量来摧毁“这杀人的社会”!上述作品中人物的种种认识,其实就是作家自己的观点,反映出吴组缃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剖析和对社会前途的思考。这种剖析和思考正是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所必须具备的基础。以后他陆续发表的《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小说,分别从地主阶级的凶残堕落、农村商业经济的崩溃瓦解和农民被迫起而反抗等方面,剖析了皖南农村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广大农民崛起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成为30年代社会剖析派小说创作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基础,但真实性并不等于现实主义。因而作为以社会剖析为主要目的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不仅是要真实地反映生活,而且要求通过典型环境的创造,揭开生活的底蕴,探出社会的本质。在“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作家们的文化思考几乎都集中于对正统的儒家文化的批判这一单一的范式上,而忽略了对处于下层文化地位的民俗风习的揭示与批判。左翼青年作家们的乡土小说创作,则以带有乡土气息和民俗风习的刻绘与描画,为现实主义小说中典型环境的创造拓开了新的视界和领域,并通过这一现实主义独有的审美创造,赋予作品以新的镜角与内涵。它既是“五四”现实主义文化批判的延伸,又是对它的必要补充。在这方面成就最大的无疑是沙汀。
在沙汀的小说中,作家独具个性的现实主义审美观与民俗文化意识是相互渗透的。他的作品对乡土气息和民俗特征的刻画,既不是简单地从现实政治功利出发,去选取形象的素材,提炼和概括形象的意义,用乡土民俗现象去直接映证主题需要,也不是将人物完全置于作品中社会民俗环境的支配之下,从而使人物失去个性。而是以乡土民俗环境为依据,通过对能够体示生活底蕴,探出社会本质的大量民俗态生活的艺术勾画来反映社会本质,甚至触及重大的政治时弊,达到剖析、鞭挞现实的目的。在他的小说中,乡土气息和民俗风习的刻画主要体现在作家对场面的描写之中。他的作品往往选用一个固定的然而又最能体现民俗风情的特定环境作“风俗画面”的载体,这种“载体”本身就包孕了丰富的风俗画场景内涵。茶馆这一极有风俗文化色彩的场所,就是他许多小说的故事发生的“背景”和情节发展的“载体”。因此,出现在沙汀笔下的既不是华老栓经营的茶馆(鲁迅《药》),也不是北京的裕泰茶馆(老舍《茶馆》),而是川西北僻远乡镇上的“者者居”、“畅和轩”和“其香居”。作为一个在川西北农村和小城镇土生土长的“原乡人”,他对乡土生活的熟悉达到了连本地人“打一个喷嚏,都能猜到他是啥子意思”⑧的程度,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对茶馆的刻画也达到了入木三分的地步。作家通过茶馆这一典型环境,把四川独有的闭塞、落后,官绅各派势力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三教九流各种人物“吃讲茶”的特有风俗等等,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其现出本来面目。可以说,如果没有茶馆,沙汀最重要的小说如《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等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戏”。著名的讽刺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便是通过茶馆里一台富有世俗画色彩的“吃讲茶”的闹剧,从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一件小事中,剖析了国统区腐败的兵役制内幕,揭露了国民党官场的黑暗与腐败,达到既能世态毕现,又能韵味深藏的艺术境界。正是在茶馆这个特定的环境里,邢幺吵吵的粗鄙蛮横和方治国的圆滑狡诈(《在其香居茶馆里》),龙哥的恣肆抢掠与烈士遗孀的孤苦无告(《公道》),魏老婆子的屈辱含愤及乡下人的无知落后(《兽道》),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由于多数左翼青年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在描写风俗民习时,是从批判角度来观照其落后面的,并且将民俗风习的描写运用于典型环境的创造,形成他们的乡土小说大都有明晰的地域指认性,这种指认性必然使他们的作品具有更为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例如,都是暴露和抨击残酷的典妻制度,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与罗淑的《生人妻》相比,就明显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地域文化意识。浙江作家柔石所观照的沿海风俗,更多儒家文化的沉积:那个秀才典用别人的妻室,还吟诵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诗句,生儿子起名“秋宝”,还援引《书经》“乃亦有秋”的典故以证明其高妙。这里描写的是沿海书香人家在礼仪文化的纱幕下对人性的摧残。而罗淑所描写的则是内陆僻地的四川沱江上游山坳里赤裸裸的带有巴蜀风俗印记和初民文化色彩的野蛮风习:夫卖其妻、弟奸其嫂、买妻者构陷卖妻者。它揭示了旧制度下民不聊生、家室难圆的惨痛现实,这种现实惨状是在卖妻陋俗和猪圈里“洗晦气”、强喝“对杯酒”等恶俗粗鄙的婚宴礼俗中展示的,它不同于《为奴隶的母亲》以三年的典卖期寸寸磨碎受侮辱者的肝肠,而是两昼夜的奇灾异祸摧毁了一对老实夫妇的家室。从这两位作家同一题材的小说中,读者看到的不仅仅是两个家庭的悲剧,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和形成这种悲剧的深层原因——宗法制社会重血缘承续的观念。这就不仅揭露了民俗文化中野蛮落后的一面,而且把对封建正统文化观念的批判引向深入。它是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对中国乡村生活真正楔入的一个标志。
总之,以对社会进行理性分析为特征的社会剖析小说的创作,以及将民俗风习渗透到典型环境创造中的乡土小说创作,是30年代左翼文学向现实主义深化的重要成果,它使左翼青年作家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艺术思维空间更为开阔,并且从人生命运、情感心灵等不同的角度把捉到历史意向和时代精神,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封建腐朽伦理道德的丑恶,听到旧中国拆裂的沉重声音,感受到劳动人民人性的美好和人民革命伟大时代到来的历史趋势。
(待续)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作家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描写方法论文; 环境描写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乡土小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