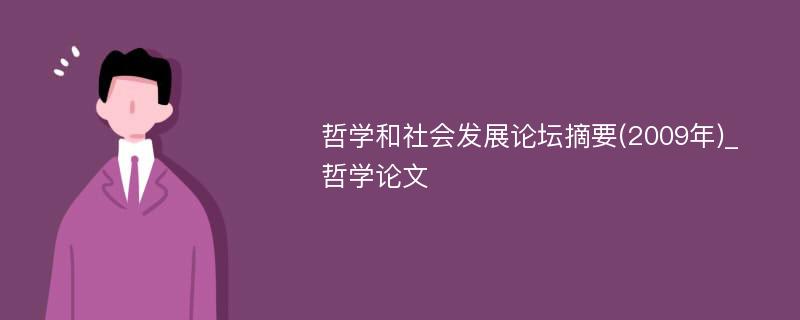
“哲学与社会发展论坛(2009)”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哲学论文,论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12月18日,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哲学与社会发展论坛(2009),在中央党校举行。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近8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峰出席论坛并讲话。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哲学教研部主任、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贾高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周炳成分别致辞。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晓兵、董德刚参加了论坛。论坛由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才主持。论坛的主题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背景下的哲学:现状、机遇和挑战”。校内外10位专家学者代表先后发言,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一、关于哲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
与会学者对哲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普遍认为哲学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社会实践对于哲学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二者具有密切的关系。
石泰峰教授认为,当前,无论是就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而言,还是就我国社会的科学发展而言,哲学的发展和哲学作用的发挥都是亟待解决的一项任务:第一,要充分发挥哲学对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引,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必须进一步发挥哲学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第二,要充分重视社会实践这一哲学发展的根本源泉和动力。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之所以能够引领社会进步,就在于哲学能够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站在时代的高度,回答和解决时代所提出的重大实践课题。第三,要切实担负起哲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推进哲学和社会的结合,促进哲学与社会的各自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哲学理论工作者的作用,以哲学的思维方式研究和把握社会发展,引导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同时推进哲学理论自身的创新,这是对哲学理论工作者的要求,也是时代赋予哲学理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贾高建教授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特殊重要的历史阶段,新的实践对我们的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我们作出回应。如何在梳理和整合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方向,使哲学理论研究更好地向前推进,从而更有效地指导实践,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中央党校作为我们党培训、轮训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肩负着特殊的职责,同时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定位,这便是正好处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部。我们背靠整个理论界,而面对着来自各个实践领域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以及他们带来的各种重大现实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理论高度研究这些现实问题,同时从这些问题着眼对理论本身进行反思,不仅仅是党校工作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党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有利的生长点。
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教授认为,哲学和社会发展有什么关系,当代中国的哲学与当代世界的发展有什么关系,这很值得我们思考。不要只是强调哲学的引领作用和指导作用,哲学不要追求什么繁华,不要追求什么显学。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灵魂,这种精华和灵魂需要沉淀、需要提炼、需要在一种平静深刻的思考中去体会和把握。
二、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反思
与会专家学者对于当前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抽象、概括、提炼和总结。
董德刚教授提出,研究当代中国的基本走向,要有宽广的世界历史眼光,有一个基本坐标或参照系,这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轨迹。对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史,可以作出“四大领域、四个阶段”的简要概括:经济领域:渔猎化→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政治领域:神权→君权→少数人特权→民权;文化领域:神学→玄学→经典科学→现代科学;人的发展状况:原始蒙昧人→关系人→自立的单面人→健全人。这四大领域的四个阶段之间大体上是上下对应的关系。依据这个参照系分析,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既有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化的成分,也有从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转变的因素,处于亦此亦彼的混合型的过渡态。当代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中,总体上是从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其主要内容,在经济上,是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和信息化转化;在政治上,是从君权、少数人特权向民权转化;在文化上,是从封闭、愚昧、单一向开放、理性、多样转化;在人的发展方面,是从人身依赖的“臣民”、“奴性”、单面人向独立自由的公民、个性、健全人转化。如何实现这些转化?从社会客体角度看,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社会主体角度看,根本机制是激发个体活力,并与改善社会调控相结合。
中央党校段培君教授认为,从当代发展的视野看,随着全球系统化方面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系统哲学的社会意义有了新内涵,在社会实践与哲学理论方面提出了新的重大课题。第一,人类实践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新系统,社会系统性大大增强,社会大系统的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第二,与上述系统大变化相一致,社会系统规律,特别是结构性规律的地位上升,系统的复杂性增强,不确定性增强,形成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新态势。第三,上述全球系统的变化与结构性规律地位的上升,既需要在系统哲学乃至整个哲学视野中反思和提升,开创哲学发展的新空间;也需要在实践中根据这一变化趋势提出解决经济社会与环境发展问题的新思路。全球系统性变化的趋势表明: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发展问题,可以说是系统哲学的问题。在当代,系统哲学显示了极为重要的社会意义。
中央党校赵建军教授对工程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工程实践与哲学研究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工程实践需要哲学指导,哲学也需要面向工程实践,需要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由于工程哲学以工程为研究对象,把现代人类的主要实践方式之一的工程活动,提升到了哲学理论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和研究。通过对现代工程与工程活动的哲学研究,来透视人的本性和工程活动的本质,研究工程的发展规律,研究工程对自然、对经济、对人类和社会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工程对文明进程、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状态的作用和影响。因此,研究和普及工程哲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价值,可使人们在活动中提高效率,少走弯路。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与会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清华大学陈来教授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对于我们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今天,我们重新研究学习这些精神,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自强不息、以民为本、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为核心。自觉地汲取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资源,正面宣示对中国文明的承继,更充分的中国化,以应对内外现实的复杂挑战。这种再中国化,它重在表示与“和传统决裂”的不同态度,肯定了现代中国必须是根于中华文明原有根基的发展,表现出复兴中国文明、发展中国文明的文化意识。
中央党校王杰教授认为,中国文化中那种主张“以义制利”、“见利思义”、“义以为上”的道德价值优先的观点完全有可能成为人类构建共同价值观、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有鉴于此,当前我们的领导干部教育存在一个偏差或者说是误区,就是忽视了道德素养和人文素养的教育。我们强调党性修养,这非常必要,但没有人性修养、道德修养,党性修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是一句空话。在重视道德修养问题上,中国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丝毫不矛盾,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儒家思想,都把道德修养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四、我国哲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我们总结新中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哲学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国哲学研究中也存在突出的问题,甚至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侯才教授认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仍面临着某种困境和危机。集中地表现在,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在国际社会地位的空前提高,当代中国哲学正愈益紧迫和突出地面临世界化的任务,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但是,哲学自身却尚未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性转换工作还大大滞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要思想前提,显然,没有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是不可能完成的。
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教授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来说,存在三多三少的现象:第一,体系意识、文本意识比较多,而问题意识、现实意识比较少;第二,行动、实践研究比较多,制度层面研究比较少;第三,解释的多,批判的少。
李德顺教授认为,整个文化界的浮躁,使得文化面临着沙漠化的危险。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需要提出真正凝练的哲学理论,来体现时代精神,而不是急功近利,让我们只是看眼前的东西。我们的哲学工作者真正能够坐下来,依据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来进行概括和提炼的很少,哲学研究失去了科学研究的自觉的、批判的性质,就沦落成了宣传工具。
中国社会科学院谢地坤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哲学具有被社会边缘化的倾向和自我放逐的问题,原因在于哲学研究脱离中国的现实。我们的一些哲学工作者,无视社会现实,一方面是食古不化,什么事情都要从老祖宗那里去找药方;另一方面,是食洋不化,有一些学者自娱自乐,他们翻译的东西和写的东西别人都看不懂,脱离了哲学本有的意义。这实际上是哲学界的自我放逐。
中央党校胡为雄教授认为,我们的哲学研究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话语权危机,即话语与研究兴趣大多以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话语为转移;第二,翻译的挑战,即翻译缺少推敲,有些浮躁,令读者犯惑;第三,治学方式的危机,即不注重本文研究,以“原理”为中心;第四,哲学教科书存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误解、遮蔽乃至附加的问题。
五、关于我国哲学发展的出路
针对我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所面临的危机,与会学者探讨了相应的对策,提出了当代我国哲学发展的出路。
侯才教授以为,要使当代中国哲学摆脱困境,有一个大的发展,必须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认识和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哲学的科学性与哲学的价值性的关系;二是外国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的关系;三是外国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的世界化的关系。只有解决好这三个方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各个方面关系的有机统一,当代中国哲学才能够以应有的地位和姿态立足于世界哲学之林,才能够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郝立新教授认为,哲学研究的出路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哲学既要上天,又要落地,既要有理论高度,又要关注现实;第二,哲学既要关注外部世界,又要关注内部世界。外部世界就是环境、制度、条件,内部世界就是精神世界、价值诉求、信仰追求;第三,哲学要努力探索和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批判理论,以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为中心的,充分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社会发展理念。
谢地坤教授认为,哲学研究:第一,必须从现实出发,立足于现实问题,要由体系意识转化为问题意识,真正实现哲学范式的改变;第二,必须从本土视域转向实践视域,扩大哲学视野,中国哲学家要具有全球性思维,在回答中国问题的同时,也要回答全球性问题。
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认为,哲学研究中要解决好学习和创新的关系。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就是我们引进、学习、消化、吸收方面做得不错。但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学习还不够。因此,哲学研究要大胆学习,小心创新。在大胆学习的基础上创新。能否大胆开放而又深入细致地研究哲学经典,这需要更多关注我们学风的问题、学术规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