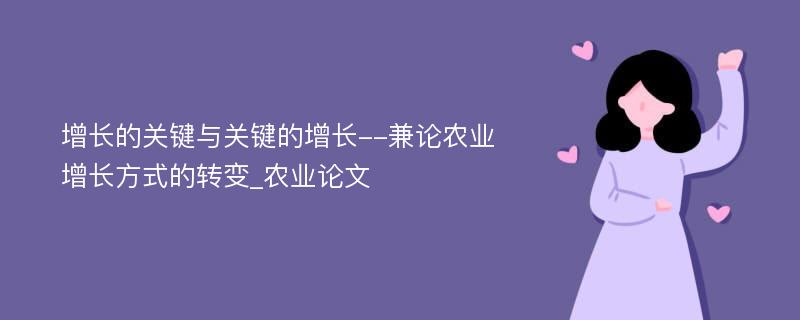
增长的关键与关键的增长——也谈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键论文,增长方式论文,也谈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十多年来,我国的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仅占有世界7%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世界22%强的人口, 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以致于人们用颇带自豪的口吻声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但中国农业的增长基本属于“投入增长型”,高速的农业增长是以更高速的资源耗费为代价所获得。而资源的有限性和农业资源环境的恶化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种增长的经济性。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业增长?答案是唯一的。在农业生产资源的高度约束下,我们需要从要素效率提高中获得有效的增长。这样,转变我国农业的增长方式,使我国的农业从“投入增长型”向“效率提高型”引导和转变,就自然而然地摆在政府和农业经济工作者面前,而且成为历史的必然。
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作为一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似乎已不需要再去喋喋不休地讨论这种转变的伟大历史意义,而应该着重并深入地研究加速这一转变过程所需要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一转变过程所涉及的关键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关键问题的可操作的办法和政策措施。
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实质上是一个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优化的实现过程,制度这一对经济增长影响重大的因素,就将决定人们的行为、资源配置和经济效率。因此,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顺利与否的关键就在于农业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以适应农业由数量型增长向效率型增长变革的要求。同时这一过程的实现又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条件下进行。促使这种变革所需要的关键增长,则在于从现在开始,使改造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的相关投入获得迅速地增长,以提高农业对于转变增长方式的承载能力。
农业资本:需要高速增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农业获得了巨大的增长,1952—1993年间,农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91%。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增长率得到了迅速提高,1978—1994年间,达到5.69%,199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4.65亿吨以上,棉花总产450万吨,油料总产250万吨,粮料总产7800万吨,肉类5000万吨,基本满足了国内的需要。然而,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所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的粮食生产。1995年全国粮食的净进口量已接近2000万吨,据预测(黄季焜,1996)到2000年全国的粮食净进口量将达到4000万吨,净进口量将以每年14.87%的速率增长, 同时将由大米净出口国变为世界大米的主要进口国。2010年全国粮食总需求量达到5.13亿吨,2020年将达到5.94亿吨,到2000年猪肉的需求量(梁振华,1996)约4200万吨(1995年全国猪肉产量为3500万吨)。然而,短缺的农业资源状况和相对脆弱的农业基础却制约着农业的增长步伐。首先,土地资源匮乏并伴随耕地减少给进一步增长带来巨大影响。1978—1995年间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271万公顷。每年平均减少近75万公顷,人均耕地面积已由1949年的0.21公顷降到1994年的0.08公顷,虽然近几年耕地减少的速度有所放慢,净减为30—40万公顷左右,但如果耕地减少的速度不能再度放慢,到2000年,我国耕地面积将净减少150—200万公顷, 到2010 年我国耕地将不足9000万公顷,人均耕地占有量将不足0.06公顷。另外,耕地减少面积大大高于耕地净增面积,例如1995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50万公顷,新垦荒地20万公顷,净减30万公顷,被占用的耕地大都是高产良田,因而将使土地生产率大为下降。第二,农业投入品的边际效率下降,使农业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投入品的高速增长,1978—1994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5.69%,而农业投入品年平均递增9.44%,化肥使用量年平均递增8.09%,农机总动力年平均递增6.41%。以化肥为例,50年代,每千克氮素可生产16.5千克稻谷,而到80年代已下降到10千克左右。投入的报酬递减的状况日趋严重。第三,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将成为农业增长的重大制约因素。根据1990年调查(胡鞍钢,1990),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16.7%,达160.3万平方公里,比50年代初增长了38 %;草场面积不断退化,全国退化草原面积已达0.87亿公顷,而且以每年133万公顷的退化率扩大;水资源短缺和污染严重,与50 年代初相比湖泊面积缩小约1.86万平方公里,占现有湖泊面积的26.3%;水体污染情况严重,82%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农村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全国1/3以上的水库带病运行,灌区工程基本完好的仅占30%;自然灾害频度加快,受灾和成灾面积不断扩大。全国年平均成灾面积,80年代是50年代的2.1倍,是70年代的1.7倍。而90年代又比80年代增加了近20%。据测算(胡鞍钢,1990),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数量:1975—1979年间,年平均89万吨,1980—1984年间,年平均1300吨,1985—1987年间,年平均1800万吨,1995年自然灾害损失的粮食达到3000多万吨。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灾害的能力下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第四,劳动力素低下,技术扩散力量薄弱。农户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不到5年,小学以下文化的农业劳动者占60%,文盲半文盲占20% 以上。农业人力资本素质的低下,将有可能成为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瓶颈。由于近年来国家投入的不足,农业科技和农技推广部门和技术服务网络出现“线断、网破、人散”的局面。全国40%以上县、乡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机构被撤并,建国后培养的农业专业技术人员近一半离开了农业系统(贾大明,1995),农业技术的推广率只有30%—40%,形成规模的尚不足20%。
因此,要使中国农业稳定地获得增长,改善农业基础条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目前全国中低产农田占全国农田的2/3,近6000万公顷。根据经验,改造后的中低产田每公顷产量可提高3 吨左右。 1988 —1994年间,国家共投入328亿元,改造3986万公顷中低产田, 平均每公顷约3300元,如果全国中低产田全部得到改造,每年可增产粮食1.8 亿吨。但需投入2000亿元改造资金。据测算(周一行,1991),我国粮食从3亿吨到4亿吨的递增过程中,固定资产、支农资金和化肥投入的年平均递增率为5.55%、6.48%和8.45%,而从4亿吨到5亿吨的递增过程中,将分别为6.74%、15.53%和5.94%。
从增长方式的一般概念出发,我们将以要素增量为主所获得的增长定义为粗放型的增长,而把以要素效率提高为主所获得的增长定义为集约型的增长。由此可见,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技术进步的过程,而技术进步则更普遍地表现为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粗放型的增长将遭遇“极限”,当增长趋于“极限”或人们意识到这种“极限”的存在,要使增长突破这种“极限”,就必然去改变这种增长的方式,而着眼于从提高要素的效率来获得有效增长。然而,技术进步的渐进性又要求在一定的技术和物质基础上进行,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准备,要转变增长方式是极其困难的。特别是对于农业这一取决于土地和自然条件的特殊行业,要素效率(如土地生产率,其他投入要素的效率等)的提高,不仅取决于技术进步,更取决于技术载体(如土地、劳动等)基础物质条件的提高与进步,这种基础物质条件将决定农业对于技术进步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承载能力。所以要使我国农业的增长方式获得转变,当务之急是加大投入力度,强化和改革农业物质要素效率提高的基础条件,以提高农业适应增长方式转变的承载能力,而不是简单地讨论农业技术进步的问题。当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缺乏必要的载体和制度保证时,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就将无法实现,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率较低,在实证上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根据钱纳里(1986)等人的研究,农业要素生产率的年递增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当人均收入为100—140美元时,全要素生产率年递增率为0,当人均收入为560—1120美元时,全要素生产率年递增率为0.86,同时,资本对产出增加的贡献由39%提高到68%,劳动的贡献则由47%下降至8%,这表明, 要素效率的提高与资本的密集程度具有紧密的关联。所以,要从现在开始转变我国的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必需加强农业资本的投入,可以预计,从现在到2010年我国农业资本将进入一个高速成长期。
制度改革:增长方式转变的保证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端于农业,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农民获得了部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这种制度的变革解放了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的效率和资源的配置效率,加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其他各业的生产就业门路尚未得到充分的拓展,农业就当然地成为农民资源的主要投向和生计的主要源泉,农业生产和农户收入都由此获得迅速增长。林毅夫(1994)的研究发现:1978—1984年间,中国农业总产出增长42.23%, 年平均递增5.93%,这一增长中45.79%来源于投入的增加,46.89%来源于联产承包责任制。黄季焜(1996)对于水稻生产的研究也映证了这一点,1978—1984年间,生产责任制对于水稻生产增长的贡献为34%。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辅开,农民的就业门路进一步拓宽,随之而来的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和资源的机会成本逐步上升,责任制对于农业增长的激励作用逐步降低。1984—1987年间农业年均增长率降到2.97%。林毅夫(1994)认为1984年后产出增长放慢的一个原因就是责任制产生的一次性突发效应在1984年已释放完毕。黄季焜(1996)对水稻生产的研究也表明了相同的观点,据他测算,1984—1992年间,责任制对水稻生产增长的贡献为0, 此间水稻生产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
以现在的观点客观地来看,责任制在80年代初中期对中国的农业增长起到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调动了农民被长期抑制了的生产积极性,适应了在长期计划经济下农民占有自己生产成果的渴望,也适应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对地权追求。然而,长期不变的土地承包制度却给土地这一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资源在合理配置和规模经营上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土地的过分细化,不仅提高了技术的采用和管理成本,也无法使得绝大多数农民的生计完全依赖于农业生产。农民一旦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当其他各业的发展使得农业生产的劳动与资源机会成本增加以后,农民对于农业的投入强度就必然降低。另外,责任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促进农业生产的市场化进程和提高行业内部的竞争氛围,两田制和土地规模的不可变动,根本无法使农业生产者在生产中真正感受到追求利润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在压力,自觉地不断提高生产的效率,而仅仅将农业生产作为一种生存的基本保障。从1995年和1996年全国农户生产意向调查可以发现,多数农户将家庭消费的增减作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动的第一位原因,而价格的变动则是第二位……尽管农产品已经历了几次大幅度调价。这说明农业生产并没有真正走入市场,而仍处于一种变相的自然经济之中。众所周知,市场化和激烈的竞争是使得生产效率提高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当制度因素阻碍这种推动力的形成和作用时,效率的提高将很难成为可能。
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包括生产要素自身效率的提高和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组合效率的提高,而制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效率提高内在性。要使我国的农业增长方式得以从资源增长型向效率增长型转变,建立一套适合增长方式转变的农业制度是这种转变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就当前而言,为了适应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我们对责任制加以重新考虑和完善,建立一套可行的资源流转和土地资源集中制度,以及进一步将市场机制导入农业的相应制度。
政府作用:将更为重要
在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资源合理配置和市场导入方面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成败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动员经济的能力。福克纳指出:在美国“农业已基本上变成一个‘被管理的部门’,制定价格和分配资源的决定因素,已不再是市场力量,而是政府”。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发展状况,政府在农业增长与发展中的作用似乎有逐步削弱的趋势。表现在:
第一,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导入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起到巨大推动以后,随着产生这种制度的经济环境的改变,后续的改革措施显然没有跟上,农业经济体制的改革落后于国民经济体制和企业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在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已经导入了股份制、合作制、破产制度等适合于资本与资源重组与合理配置的产权制度并建立了相应的保障制度,为企业增长方式的转变铺平了道路。而农业制度如土地制度、经营制度等的改革方面却迟迟未见动静,并未根据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加以调整和完善,至今没有找到一套能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办法,为了保证粮食的生产反而实施了一套变相的计划经济办法,如“米袋子”省长制,计划任务层层分解,层层自我平衡,层层自我封锁(当然这一作法并非一无是处)。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而言,这种作法显然不利于资源的合理有效的配置,只是一种暂时和短期的行为,也表现出是农业在增长和制度保证之间无法适应所作出的一种无奈选择。
第二,对于农业的投资与投资导向缺乏力度。自1978年以来,政府对于农业投资的力度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例如,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13.6%下降到1994年的9.2%, 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由“五五”期间的10.5%降到“七五”期间的3%,而1994年进一步下降至2.41%, 政府农业投入力度的削弱,造成农业基础脆弱,生态环境恶化,抗灾能力下降。例如1978年成灾率为42%,而1995年上升至51%,且绝收面积扩大。同时国家对农业科研及推广的投入的力度也不断下降,1979年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8.8%,而1993年下降至1.9%,停止或减少经费供应的县、乡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已达约2.2万个,占总数的40%以上。
第三,政府对农业的保护不够。作为一个弱质型的产业,政府对于农业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政府和专业人士普遍认识到这一点,但在实际过程中农业的保护问题始终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甚至出现恶化趋势,除了投资向非农产业倾斜外,还表现在:
1.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例如1989 —1992年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5.3%, 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却上涨33.59%,而1995年农业生产资料上涨更创了历史记录, 一季度涨幅高达30.4%,而同期一些农产品价格,如油菜籽、生猪的价格却下降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100:42扩大到1993年的100:35.7。农民收入的增长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
2.农产品流通渠道仍然不畅,农民利益流失严重。据统计(江观伙1995)1985—1993年物价的放开,使得农民人均利益损失达171.76元。在农业财政与信贷方面,国家一直处于“取大于予”的状况, 1991 —1995年间,农业税金与支农资金相抵,农民净资金流出为3598 亿元, 1995年农业存贷款相抵,农民净流出资金2574亿元。
3.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农村乱收费、乱摊派等基本没有得到很好治理,农户税金和费用上交占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的比重由 1980年的不足1%上升到1993年的占12.74%。
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源重组以提高要素效率的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导向和调控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应强化对于农业的宏观调控能力,在资源配置、制度变革、投入引导等方面制定出适合增长方式变革的相应经济政策并加以实施,不能只说不做,如果我们不能真正地重视农业及其增长方式的转变而切实地做一些事情的话,布朗的预言也许真有实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