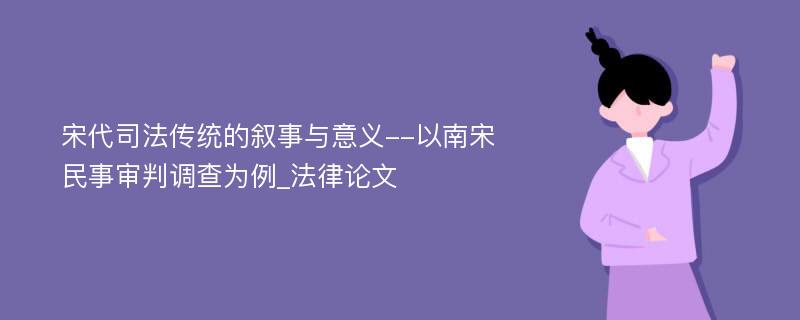
宋代司法传统的叙事及其意义——立足于南宋民事审判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宋论文,宋代论文,立足于论文,民事论文,司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既是中国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如何改造自己的传统,建立和谐社会的现代化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学界长期聚讼纷纭的学术理论问题。法学界对中国传统法制——即中国古代司法传统的看法及其评价,也因视野及价值观念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历史叙事及其结论。多维视角下的不同叙事,既反映出了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司法传统的浓厚兴趣,也使争论的焦点更加突出,这就是:到底如何看待中国古代司法传统,中国传统法制,亦即中国司法传统是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非理性的“卡迪司法”。①
就中国的文明形态而言,儒家人伦文化的核心价值是“远神敬人,以人为本”,因此,中国古代文明早在西周时期就开始摆脱了宗教神鬼思想的羁绊,“卡迪司法”的宗教神秘性很难在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下找到生存的空间,再加上,古代中国是一个成文法传统的国家,成文法传统的典型特征是:法官断案原则上必须引用法律条文。尽管在儒家人伦文明形态下,好的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融“天理”、“国法”、“人情”于一炉,绝不可能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单纯机械地适用法律条文,但“援情入法”的基础是国家的基本法典必须在司法中贯彻落实,否则法官就要担负法律责任。中国至迟在唐代就已确定了这一原则,《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诸断罪皆须引律令格式,违者笞三十。
故本人以为,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有违中国历史实际。鉴于学界已有黄宗智、林端二位教授以明清时期的司法为例,对韦伯的学术观点进行厚重而缜密的分析与批评,②因此,本文的研讨只以宋代的司法审判为限。之所以如此选择还基于以下两个理由:首先,也即最根本的原因是,现在能见到最早的中国古代的法官判词,亦即司法过程中以真实案例为基础而记录下的判决书便是宋代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学界又简称《清明集》),这是说明中国古代司法传统不是“卡迪司法”,而是依法断案的最为确凿的证据;其次,宋代的判词中,有关婚姻、田宅、财产继承方面的民事审判案件占有极大的比重,而学界对中国古代在刑事审判方面的认识基本达成一致,那就是依法判决。唯有民事审判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论。因此,以宋代为背景,选取《清明集》中的民事案例为素材,分析认识中国古代的司法传统,也于学界起着补其罅漏的作用。本文从语用学的角度出发,用历史叙事的方式,首先分析梳理概念,然后对宋代司法的理念、运作机制、审判原则、语用环境进行研讨,从而揭示宋代司法传统的典型特征及其现代意义。
一、概念与方法
欲言宋代司法传统,必先对其涉及的概念与方法进行交代,即何谓司法、宋代司法传统、叙事?
“司法”一词,并非现代的法律用语,早在宋代,这一词汇便已成为社会生活及审判活动中的日常用语。在宋人的话语及社会生活中,“司法”一词大约有两种含义:一是泛指司法机构与司法官员。如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朱熹就曾说过:“今所在常平仓,都教司法管,此最不是。少间太守要侵支,司法如何敢拗?通判虽管常平,而其职实管于司法。”③宋代用以平准粮价的粮仓叫常平仓。太宗淳化三年(992)始置于京畿,景德三年(1006),除沿边州郡外,全国普遍建立。显然朱熹此处所说的“司法”,是指州里设置的司法机构及司法官员。二是专指检法议刑的司法参军。为了保障司法的公平,在宋代司法审判中,专门实行调查审讯与司法判决互不隶属的分立制度,史称“鞠谳分司”制。④也就是审讯的官员与判决的官员原则上既不能由同一人员担任,也不能隶属于同一机构。在宋代,负责调查审讯的官员在州一级叫“司理参军”,隶属于“推司”,又称“狱司”;⑤负责判决的叫“司法参军”,隶属于“法司”。⑥司法参军是知州的幕职官员,专门负责判决前的“检法议刑”工作。所谓“检法议刑”,就是针对案件,检出适用的法律条文,向州长官提出建议,但其不得参与决断。
“司法”泛指司法机构及司法官员,就此义而言,宋代与现代广义的“司法”一词并无实质性差异,只不过宋代的“司法”专指州一级“检法议刑”的“司法参军”一义,已化作历史的陈迹,不复存在。而现代社会中狭义的司法一词所包含的“仅指民主宪政基础上,法院独立行使的审判裁断活动”之义,宋代的“司法”一词也不能包含。
所谓“传统”,学界通常认为,它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它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及其社会行为有着无形的影响及控制作用。就此而言,传统大约可指一个民族代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及其行为方式。如风俗、习惯、思维、语言、文化等。因此,“宋代司法传统”这个概念是指赵宋王朝所具有的、极富时代特征的、代代相传的司法机关及其官员处理诉讼纠纷、审理民刑案件的活动及其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司法理念、运作机制、审判原则、行为方式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至于“叙事”,原本指叙述故事。这个词首先在文学界使用,它是用来讲故事。按理说,文学的讲故事不能直接用于历史研究,因为历史学的核心价值是求真求实。文学重形象思维,史学尚客观真实,领域不同,标准不同。何以史学研究乃至法律史研究亦可用叙事的手法呢?换言之,本文使用“叙事”的方法与传统法律史研究有哪些不同呢?这里可以分三个层次来回答此问题:首先,随着语言学与解释学的兴起,社会学的研究中广泛使用叙事的概念与方法,来对同一时期的同一重大历史事件作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从而突显了多元价值主体对同一历史文本所具有的不同视域与兴趣。这样的多元视觉叙事也同样引发了历史学家的兴趣,史学界也在近些年来广泛应用这一方法。其次,后现代主义者公开否定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认为史书与小说没有什么区别。⑦此种思潮下,多元视觉的叙事风格不去追求历史之真而去追求历史之新也成为现代人的一种时尚。最后,叙事的方式借用到历史学研究中,在尊重历史资料所彰显的客观真实性基础上,强调语言在历史解释中的向度及解释艺术在历史文本中的不可或缺功用,这也确与历史学的本质暗合。所谓历史学的本质是说单纯的史料堆积并非历史的真实与客观,历史已经过去,因此任何历史研究之真,固然离不开史料的基础,但历史学不同于史料学,史料如砖石、水泥、木材,它要成为美轮美奂的建筑物,尚需图纸设计与能工巧匠,故此,历史学又是一门艺术。而叙事方法下的语言向度及解释艺术恰恰是历史学研究中的两大法宝,故本文在首重历史客观之真实的基础上,强调对宋代司法传统的叙事必须放在历史语言的向度下,借用史料载体,作出符合中国古代成文法传统典型特征的解释,而不是盲从马克斯·韦伯之结论。
二、“为政者皆以民事为急”——宋代民事审判中的司法理念
理念即认知。所谓司法理念就是指司法主体对司法活动本身及其司法对象所持的情感、态度与认同方式。就宋代而言,司法活动的主体是经过科举考试及法律专业考试合格后,进入中央及其地方各级司法机构,担任司法审判职责,或者辅助司法审判的各类官员,他们有一通称——士大夫。有关士大夫的司法理念,本人曾在近几年的著文中研讨过,但过去关注的重点是刑事审判,而对民事审判中的司法理念的研究则用力不多。尽管宋代仍像其他朝代一样,在审判活动中对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审理并无现代意义上的民刑之分,但是由于宋代土地私有制的深化及财富流转关系的加快,百姓日常生活中有关婚姻、田宅、财产继承、赁房租屋的活动与纠纷,确实是空前活跃、日繁一日。对此,宋代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及其各级司法官员也确实给予了高度关注。尤其是宋廷左迁之后,江南地区一方面经济进一步活跃,一方面因人稠地稀而引起的“田宅纷争”更是日见千状。南宋的统治者们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不仅在民事审判方面创建了独特的“断由”制度,还开创了允许卑幼告尊长的历史先河。在民事案件的受理及审判中,以传统的“民本”思想为基础,提出了“执政者务以民事为急”⑧、“此其有关于朝廷上下之纪纲,不可以细故视之”⑨的司法理念。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司法理念首先包括对司法的整体认知,其次是对法官素质的要求,再次是法官群体在审判活动中对刑民诉讼案件的态度。本文虽然是重点研讨民事审判中的司法理念,但若不从刑事审判理念说起,我们就很难对宋代的司法理念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更无法彰显民事审判理念的时代特征。
首先,从开国之初视“庶政之中,狱讼为切”⑩到南宋初期的“执政者务以民事为急”,标志着民事诉讼与民事审判成为南宋统治者所关注的头等大事。由于“狱讼”或“民讼”事关百姓的生命、财产、名誉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故视“狱讼”、尤其是事关百姓生命的“刑辟”大狱为政务之首,是宋朝皇帝与士大夫的共识。开国之初,太祖、太宗兄弟历经战乱,亲眼目睹了五代十国烟云兵燹中,悍兵骄卒率意司法、滥杀无辜的血腥事实,一革前代草菅人命、轻视狱讼的弊政,特别重视对刑事案件的审理。这种重视有多重表现:一是太祖、太宗皇帝亲自录囚,专事钦恤,这在《宋史·刑法志》中有明确记载;二是宋朝中期之前,本司监察之职的御史台及其官员们,其主要的职责与精力不是用在监察百官、振肃纲纪上,而是专门负责审理刑事大案,这在宋代也是一奇观,已为宋史学界所注目;(11)三是注意从儒家知识分子之中选拔司法官吏,且皆以律书试判,即进行司法考试。然而,就其理念而言,以宋太宗的认识最为到位。他对群臣说:“朕以庶政之中狱讼为切。钦恤之意,何尝暂忘。”(12)
学界一般认为,由于中国古代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司法审判中,绝大多数朝代与开明的君主都对“强盗”或“人命”大案十分重视,制定专门的法典予以惩处那些伤害人身及抢夺、盗窃财产的犯罪行为,稳定社会秩序,而对“民间细故”,即有关婚姻、田宅、财产继承的民事案件,历来不予重视。其实,这是对历史的误解,更是不深入断代研究、好下宏观之论的现代偏见。
中国古代至迟在北宋末期,已出现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这就是从北宋末至南宋之际,出现了一批特别关注州县民事案件受理及审判的政书。最为著名的:一是北宋末徽宗政和年间李元弼撰写的《作邑自箴》;二是托号北宋陈襄实为南宋人所撰的《州县提纲》;三是南宋初年胡太初的《昼帘绪论》。这些书虽然还不能视为是法学专著,但其中有关民事案件受理、审理乃至民事诉状的格式等,的确占有丰富的内容。
这些著作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现实,即南宋的社会与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种需求,这就是如何处理民间的社会纠纷,而在这些纠纷中民事诉讼是其主要类型。事实也正是如此,南宋于高宗到孝宗朝,最高统治者已开始认识到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民事诉讼,不再是民间细故,而是有关朝廷上下纲纪的大事,凡“为政者皆知以民事为急”。(13)对此,南宋皇帝自高宗到宁宗屡发诏书,我们仅以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公元1140年)为例,仅此一年,朝廷就连发三道诏令,说明宋朝最高统治者对此十分重视。绍兴十九年,乙亥诏:自今监司守臣代还入见,并令以民事奏陈,先是上谕大臣曰“监司郡守得替上殿,本欲知民间利病,近来所奏,姑应文书,多不及民事,宜行告谕,故有是旨。”(14)庚戌,叶綝言:“自祖宗以来,定公私赃三等之罪,其意未尝不重于保护斯民而已,向缘官吏率多不定罪,而民被其害,是以又标立民事一罪以戒惧之。”(15)……己卯,上曰:“治道以民事为急。”(16)这里的所谓“以民事为急”,其中的“民事”二字非确指民事诉讼与民事审判,因为当时的宋代还没有现代意义的部门法观念,但“民事”一词包含有民事诉讼的内容则是确定无疑的,这从《宋会要辑稿·刑法》之《诉讼·田讼》所载的大臣奏议及皇帝的诏令中可以得到验证。史称,宋宁宗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十月二十六日,权户部侍郎李珏言:
窃惟今日中外之弊,莫甚于按牍积滞,吏习因循,视民政为不切之务。近因置籍稽考,诸路监司并州郡承受本部妥送民讼,截至九月终未结绝,共一千三百三十四件,其间盖有经数年尚未结绝。近而两浙转运司未结绝者亦二百四十余件,是致人户不住经部经台催趣。(17)
户部是宋代民事诉讼的上诉机构。依《宋史》卷163《职官三》记载,元丰改制前,户部只是一闲置机构,神宗改制后,户部的事权与机构扩充,设户部左右曹,左曹负有审理户婚、田债等民事上诉的职能。南宋时,户部左曹分设三案,即户口案、农田案、检法案。户口案专门受理民间因立户、分财、典卖屋业、陈告户绝、索取妻男之讼;农田案则专门掌管因“务限法”而引起的关于田宅典卖方面的务限之讼,“务限”即官府受理民事案件的期限。检法案则负责检出户部受理民事上诉时所适用的法条。由于户部受理民事上诉案后,并不直接审理,而是检出法条后,指导监察原审地方州县、监司的审判活动,故户部经常把这些上诉案件转送原审机构,并负责稽考、催办。故上引史料中,李珏才说,近来依据档案稽查考核,全国上诉至户部并由户部转送到各路州县、监司应当按时审结而没有审结的案子多达1334件,两浙路240余件。应结案而不结案,当然会引起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不满,他们便不断地向户部与御史台催促,这才引发李珏向朝廷建议,凡各路及时理诉并审理公平者,应提名嘉奖,反之就予以惩罚,“庶使为政者皆以民事为急”,这里的以民事为急,便是指及时处理民事诉讼案件为各级地方官员的首要任务。
其次,再看宋代如何看待法官的地位及怎样选拔法官。依据现代法治理念,法官的地位与素养直接关涉到政治的清明和社会正义的实现,一向为现代法治国家所重视。一般而言,现代社会中,法治程度越高的国家,其法官的地位和素养也就越高。当然古代不同于现代,但饶有趣味的是,宋代的皇帝和士大夫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法官地位的高下与素质的良窳与国家的命运以及司法的公正休戚相关。宋真宗说:“法官之任,人命所悬。太宗常降诏书,诸州司理、司法峻其秩、益其俸。”(18)这里的意思是说法官的司法审判之职责与百姓的生命攸切相关,百姓的生杀之权系于法官之手。太宗时就经常发布诏令,各州辅助长官审理案件的“司理参军”及“检法议刑”的“司法参军”,都要慎重挑选,以严肃其地位,并给其较高的俸禄。这样的认识也是北宋时期士大夫的共识。(19)宋代编纂审判案例的桂万荣甚至说:“凡典狱之官,实生民司命,人心向背,国祚修短系焉。”(20)法官的职责如此重要,该怎样选拔,即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保证法官具有良好的素质呢?宋代皇帝认为:第一,从事司法活动的官员必须是儒家知识分子,只有他们才明白法中之理;第二,光懂儒家义理还不行,还要有法律知识,熟悉政府管理,即谙法律、晓吏事;第三,要保证司法官员明义理、谙法律、晓吏事,做到三者合一,只有在科举考试的基础上,再进行专门的法律考试——即今日的司法考试,才能保证法官的素质是好而不是坏。北宋时太宗常对群臣说:“法律之书,甚资政理。人臣若不知法,举动是过,苟能读之,益人知识。”(21)太宗的儿子宋真宗也对宰相意味深长地说:“刑狱之官犹须遴择。朕常念四方狱讼,若官非其人,宁无枉滥!”(22)
正是在这种理念下,宋代的司法考试在规模和种类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按照宋代的诏令要求,中央各级官员以及地方州县长官、监司官员及辅助司法审判的幕职官员,要想从事司法审判工作,都必须通过法律考试。(23)宋时法律考试的名目有明法科、出官试、试刑法(又称试法官、试刑名)等。(24)以至于著名法史学者徐道邻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中国的考试制度,从唐朝起就有‘明法’一科,专门用来选拔法律人才。到了宋朝——这是中国过去最讲究法律的一个朝代——法律考试便进入了鼎盛时期。”(25)
其三,怎样看待司法的对象——百姓呢?中国古代没有权利主体意识,只有民本思想。我国古代法典《唐六典》明确要求,亲政抚民的县令“务知百姓之疾苦”,躬亲狱讼,审察冤屈。宋继唐后,州县官员于民事听讼中当然仍会秉持这种理念与传统,问题在于:历史发展到宋朝,尤其是到了南宋,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型,以“均田制”为基础的中古田制结束,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租佃制”成为宋代土地所有制的主导形态,这导致宋代社会生活中的两种现象异常突出:一是大部分土地集中于主户之手;二是四五等主户中,拥有三五亩至二三十亩土地的小农户异常增多。土地与房屋是百姓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财富,也是借以生财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因此在田宅流转过程中,因典当、抵当、倚当或买卖而引起的诉讼纠纷就格外突出,这是唐以前所没有的。这样一来,儒家民本思想的传统,反映在宋代州县司法官员的审判活动中,就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特征,那就是依法判决,保护下层民众及卑幼的利益,允许卑幼在尊长侵夺财物或殴打其身时,依法起诉,(26)并放开了民事诉讼中的越诉大门,(27)由此形成了两宋,特别是南宋时期民事诉讼中两大凸现时代特征的司法机制:一是为了实现司法公平、疏理滞讼、保障司法秩序的正常运转,实行民事结案必给“断由”的制度;二是开创了民事诉讼中的“越诉”制度。
三、司法运作机制:首创民事诉讼中的“断由”与“越诉”制度
司法机制落实到宋代,就是指宋王朝司法审判活动中是怎样启动受理程序、如何规定诉讼程序的运作、在什么样的精神下运作、有什么特征等等。机制与程序相关,就宋代而言,刑民案件的诉讼程序作为常识已经在学界出版的教科书及宋代法史研究的成果中大量反映,(28)本文不拟赘述,就是宋代的刑事审判运作机制,本人也有论及。(29)故本文研讨的重点在于民事诉讼受理中的“断由”与“越诉”制度。
何为“断由”?断由是判决书,还是其他法律凭证?为什么要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给当事人发放“断由”?这些问题虽有论著涉及,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更鲜有论者对它深入研论。我们先看史料的记载,南宋高宗时期,亦即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3年),宋朝首创了发给民事诉讼当事人“断由”的制度。史称:
绍兴二十二年辛丑,右谏议大夫林大鼐言:“比来遐方多有健讼之人,欺绐良民,舞玩文法。州县漕宪未结绝,则申冤于部、于台、于省,官司眩于偏词,必与之移送重定,外方往往观望,为之变易曲直。欲今后所送,如婚田、差役之类,曾经结绝,官司须具情与法叙述定夺因依,谓之断由。人给一本,厥有翻异,仰缴所结断由于状首,不然不受理,使官司得以参照批判,不失轻重,而小人之情状不可掩矣。将来事符前断,即痛与惩治。可使户婚讼简,台省事稀,亦无讼之一策也。”上曰:“自来应人户陈诉,自县结绝,不当,然后经州、经监司,以至于经台,然后到省。今三吴人,多是径至省,如此则朝廷事多,可从所奏。”(30)
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宋代最早也是最详实的有关婚田诉讼给当事人“断由”制度的原始资料。这段资料通过右谏议大夫林大鼐与宋高宗之间的对话,清晰地说明了为什么要给断由、何谓断由、由谁来给、目的是什么,简直就是南宋高宗时期官府受理民诉案件及其运作的生动图画,现笔者试分析解说如下:
其一,就时间、地点而言,文中所说的高宗绍兴二十二年辛丑,印证于《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二八《诉讼·田讼》,知是公元1153年5月7日,而事情发生的原委是,三吴之地的百姓因为婚田诉讼纠纷在地方得不到及时处理,不遵循诉讼管辖之规定,径直上诉到中央,引起司法秩序的混乱,给朝廷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从而才有了上述对话。文中的“三吴之地”,大概指现代的江苏与浙江一带。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实际上,南宋江南各路都有这些现象,这从宋代各类史料记载的时人“健讼”、“兴讼”、“缠讼”的世风中可以得到印证。(31)
其二,“断由”既非以往所说的判决书,也不是学者所说的“官府不予受理的判状”,据上引林大鼐之言,似是记载着判决理由的官府用以结案的法律文书。该文书的内容主要是:判案时所适用的法条、案情事实、结案的理由三大内容。今天,宋代“断由”之原件已不可复得,要弄清此种法律文书的原貌,已非易事。唯有上述文字资料可使得我们得以知“断由”之概貌。我们在此再引《清明集》法官范应铃所断的真实案例,加深对此一法律文书的印象。范应铃的判决原文是:
王九诉伯王四占去田产。王九状论王四擅卖本户田产,欺谩卑幼。今索到游旦元买契,系是王九父王昕着押,开禧元年交易,次年投印分明。准法:诸理诉田宅,而契要不明,过二十年,钱主或业主死者,不得受理。今业主已亡,而印契亦经十五年,纵日交易不明,亦不在受理之数。田照元契为业,余人并放。(32)
判词中所说的业主就是土地的所有者王九的父亲王昕,而钱主则是土地的买者游旦。这应是一块王昕与王四——即诉者王九之伯共有的土地。土地交易已过十五年,且卖者王昕已死。故法官的裁决是:此诉讼不合法律规定,不予受理。现在的土地仍归现所有人游旦,由游依契约占有、使用、受益。涉案人员放回原籍。古代不同于现代,民事诉讼当事人乃至证人,一旦涉讼,都会被官府关押,结案后,方才放回。这显然是一件法官裁决不予受理的法律文书——即断由。
南宋之所以在民事诉讼结案时,要求官府发给当事人“断由”,其原因有三:一是南宋时婚田诉讼纠纷日益繁多,史称“讼牒纷纭,至有一二十年不决者”(33),这势必给官府造成压力,也严重影响了宋代的司法秩序;二是宋代民事诉讼没有严格的终审制度,依宋制,民事诉讼须先经县受理,县审理后不服,可以申诉到州,州断决不服,可向路的监司机构申诉,再不服可向中央御史台直至户部申诉。这样的制度本身就为缠讼者提供了方便,若是初审者不在审结案件后,给当事人一个法律文书,说明理由与案情,以后从州至路,再到中央的复核审理,就难免成为一笔糊涂账。故此,发给当事人断由,也是为了方便上级官府的审理,使之有案可据、有理可依;三是为了保障交易的安全。田宅交易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也是百姓生活所需。发放断由可使田宅交易在繁杂的纠纷审理中有稳定的预期。
“断由”的发放,先由初审的县级官府进行,此后各级上诉审的州、路监司机构均应发给当事人。断由是在结案的什么时间发给当事人,宁宗庆元三年的规定是“限三日内出给断由,如过限不给,许人户陈诉”(34)。依《清明集》法官范应铃断案的实例,“断由”也可于结案日当厅发给。范在判决“吕文定诉吕宾占据田产”一案时,援笔说道:
吕文定、吕文先兄弟两人,父母服阙,已行均分。文先身故,并无后嗣,其兄文定讼堂叔吕宾占据田产。今索到干照(宋代,土地典卖一应契约文书及纳税凭证,皆统称为干照——引者按),系吕文先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典与吕宾,十三年八月投印(即办理过割纳税手续——引者按),契要分明,难以作占据昏赖。傥果是假伪,自立卖契,岂应更典。县尉所断,已得允当。但所典田产,吕文定系是连分人,未曾着押,合听收赎为业,当元未曾开说,所以有词。当厅读示,给断由为据,仍申照会。(35)
如果说给“断由”的机制是南宋官府为了在程序上保障田宅交易的安全及提高官府的司法效率的话,那么民事诉讼中“越诉之门”的洞开,其主旨则在于保护下层民众在田宅交易中的利益。
宋之前,中国古代的诉讼程序中有两条不可逾越的原则:一是不允许卑幼告尊长,除非是“三谋”大罪;二是除非有特大冤屈,可邀车驾及击“登闻鼓”外,一般必须逐级告诉,不得越诉。宋代则打破了这两项原则。对于前者,上文已有研讨,现在再来看“越诉”机制在民事诉讼中的运行,这也是宋代特有的制度。
宋代越诉机制的创立,大约是在北宋徽宗政和年间。(36)南宋时期,越诉之门洞开,允许越诉的法令与法规也有十数条增为百种之多(37),越诉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对此郭东旭先生已有专文论述。(38)由于本文论述的主旨在于民事诉讼中“越诉”机制的运行,故把研讨的重点放在与民事案件相关的诉讼程序上。宋王朝从北宋到南宋都对民事诉讼的受理与审结非常重视,制定了专门的法规——“务限法”来加以调整。北宋时,“务限法”规定于《宋刑统》的“户婚律”中,南宋则在高宗时颁布了“绍兴务限条法”。(39)
依据此法令,宋代民事案件的受理时间分别是:北宋的时间为每年的十月一日至正月三十日,三十日以前审理完毕;南宋的时间则是每年的十月一日至二月一日,其受理的时间与北宋一样,而审理结案的时间则做了调整。依据宋宁宗《庆元令》之规定:县级司法机关受理简单的民事案件,限当日结案;须追索证人的,限五日,州郡十日,监司半月。(40)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国家,农务是各级官府的大事,现在也还有“农民的事,件件是政府的大事”之说法。因此,“务限法”之本意,旨在不使官府因受理民事案件而妨碍农务。因为古代的民事诉讼与现代有别:现代的民事案件,受理查证时,不会拘禁当事人,更不会关押证人;宋代则不然,证人及当事人若不到厅,会被强制拘禁。故民事诉讼一经涉案,则“追证会对”必牵涉数人,由此妨碍农务是必然的,故法令才规定农忙季节不受理民事案件,更不会进行审理。但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地方的豪强及地主往往假借“务限法”之规定,侵占下层民户的田宅。
依照宋代法令之规定,土地与房屋可以典,也可以买。典不丧失所有权,可在一定限期内回赎。社会生活中,有小块土地三五亩、房屋三两间的贫民下户,常因生活窘迫而典卖田宅,此时豪强之家往往借“务限法”之规定,在务开之前百般拖延,以各种理由不让出典的贫户业主赎回田地或房屋,待务开后,即农忙季节到来、官府不再受理田宅之讼时,便图侵吞。这在南宋社会的乡村生活中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对此,南宋高宗时即已有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故特向朝廷建议,即使务开之时,若业主回赎田宅的期限已到,钱也备齐,出典契约文字分明,别无牵涉,也应该允许业主赎回产业,由此引起诉讼,官府也应受理。(41)这还没涉及越诉,只是特殊情况下的例外,对此,官府予以采纳。可是,孝宗时,一些地方官员因循苟且,对此类规定不予执行,于是大理寺卿李洪向朝廷建言,当官员苟且不予受理上述情况下的民事诉讼案件时,诉讼当事人可以越诉,由此洞开了贫民下户因田宅遭受侵吞,官府以务限为由不予受理时,可越级上诉的大门。史称:
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四月二十四日大理寺卿李洪言:“务限之法大要,欲民不违农时。故凡入务而诉婚田之事者,州县均不得受理。然虑富强之家,乘时恣横,豪夺贫弱,于是又为之制,使交相侵夺者,受理不拘务限。比年以来,州县之官,务为苟且,往往借令文为说,入务之后,一切不问。遂使贫民横被豪夺者,无所申诉。欲望明饰州县,应婚田之讼,有下户为豪强侵夺者,不得以务限为拘,如违,许人户越诉。”从之。(42)
四、民事审判中的三大原则
宋代民事审判颇具时代色彩,尤其是南宋民事审判有着鲜明的三大原则:第一,田宅纠纷诉讼中以书证为凭据的原则;第二,同一类案情适用同一类法律的原则;第三,依法判决的原则。
先看第一条原则。中国古代司法自秦王朝开始,就建立了以物证为首要证据的原则,这也是符合成文法传统之特色的。书证既是物证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反映民事法律关系真实情况的最为有效的证据,其内容主要包括:(1)干照,即田宅交易中的一应契约及向官府过割、投印交税的法律凭证等;(2)有文字记载的遗嘱;(3)田宅交易中邻人与证人的陈述笔录;(4)官府的砧基薄;(5)书铺对书证之真伪所作的检验报告等。由于书证具有客观性与真实性的特质,故其地位受到南宋各级司法官员的高度重视。我们来看《清明集》一书中法官对书证的认识,再以个案为例,看一看南宋的官员们在司法实践中,是怎样辨别书证——即物证真伪,并依法作出判决的。
著名法官范应铃在“吴肃、吴镕、吴桧互争田产”一案中说:“夫岂知民讼各具道理,交易各凭干照。”(43)南宋时期的临安知府吴恕斋在审理发生在富阳、昌化等地的田宅交易案中多次说:“理诉田产,公私惟凭干照”(44)。又在“孤女赎父田”一案中深切地说:“切惟官司理断典卖田地之讼,法当以契书为主,而所执契书则又当明辨其真伪,则无遁情。”(45)南宋时另一著名法官胡颖则说:“大凡官厅财物勾加之讼,考察虚实,则凭文书,剖判曲直,则依条法。舍此而臆决焉,则难乎片言折狱矣。”(46)
书证虽具有客观性与真实性,但现实生活中,出于私欲及利益之所在,田宅交易中,当事人往往在契书上涂改作伪,以制造假象,蒙骗法官,获取不当利益。其中典主蓄意改典契为卖契,从而达到侵吞出典人产业的贪婪行为,便是常见的社会现象。契书虽可涂改作伪,但殊不知,作伪便会留下痕迹,一旦法官通过书铺验明真伪后,真相便会暴露,契书作为书证仍具有极高的证据效力。法官吴恕斋在审理“孤女赎父田”一案中,不仅重视书证——契约,而且还亲自调查,并唤上书铺,对有作伪嫌疑的契约文书进行查验,终于弄清了案情,并依法作出了公正的判决。依据《清明集》卷9的记载,此案的案情是:争讼双方为戴士壬与俞百六娘及其丈夫陈应龙,争讼的标的是俞百六娘之父俞梁留下的田产,故为田产交易之诉。双方因田产之争互诉于官府,俞百六娘一方诉求赎回本应属于自己(继承其父)的田产;戴士壬则诉求官府应把这块争执的田产判给自己所有,因为他声称这块土地是从俞百六娘之父俞梁手中买来的,并非如俞百六娘所言是典不是卖,并有文书——契约为凭。(47)
这个案情在《清明集》所载的案例中,情节虽不十分复杂,但由于俞梁已死——死于公元1229年(即绍定二年),而田产的交易是在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双方争讼发生在1240年之后。从1206年至1240年,时间过去了三十余年,已是陈年旧账,又加上陈应龙从中作伪,改典为卖,俞百六娘又是招的赘夫,即民间所说的“倒插门女婿”,故涉及宋代法条极多,理清此案并非易事。好在吴恕斋是个判案能手,他在此案中既重书证,又通过书铺辨别了陈应龙手上契书的真伪,查证后,知是典,不是卖,故依法判决俞百六娘夫妇有权赎回田产。这既还原了历史真相,又显示了书证在田宅交易诉讼的审理中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坚持了“官司理断典卖田地之讼,法当以契书为主”的原则。
再说第二条原则。民事审判中,同一类案情适用同一规则,是现代司法最为重要的法治原则之一。在中国古代,由于没有制定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故民事审判之传统一向为学界所诟病,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之司法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不可预期的,是“卡迪司法”。法官可从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48)其实,这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简单化,也是对中国古代司法,尤其是民事审判传统的误解。没有民法典,并不意味着没有单行的民事法规,更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就没有民事法律关系。若说中国古代没有婚姻、没有田宅之交易,这是不可想象的。最起码,在商品经济十分繁荣的宋朝,就有单行的民事财产继承法——即宋仁宗时期《户绝条贯》的颁布。到了南宋,民事纠纷日益增多,如何审理民事案件,南宋政府还在《宋刑统》的基础上颁行了《庆元条法事类》,其中规范民事诉讼程序的就有数十条。由于《庆元条法事类》留下来的是个残卷,这就使得我们难以看见其全貌,值得庆幸的是,《清明集》一书保留了不少法官引用的民事诉讼法令,从而我们可以确认,宋代的民事诉讼及其审判也是奉行的“同一类案情适用同一类规则”之原则的。现笔者从两个方面叙述之:
首先,我们从《清明集》记录的民事案例看,其中户婚门涉及的争业(即田宅交易引起的诉讼)、立继、检校、户绝、女承分(即财产继承)、取赎、雇赁之七大类案件都是适用同一规则的。我们仅以田宅交易中的“取赎”类而言,这在宋代的民间生活中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纠纷类型。按照宋代法令,土地与房屋均可交易,既可买卖,也可典当,还可以抵当、倚当(即以田宅为抵押而借钱)。典与抵当,皆可在一定期限备钱取赎,这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制度。但在田宅交易中,因典或抵当而取赎时,发生的纠纷也最多,这是因为“典”这项交易既涉及出典人的资格,譬如寡妇、卑幼就无权出典,又涉及交易时当事人的亲邻,还涉及到交易过程的中途变化,如先典后卖,典后出租等。此类纠纷的处理如不适用同一规则,必然使当事人无所适从,正常的田宅交易秩序将无法维持,社会生活因此而引起混乱。对此,司法官员格外重视,此类案件的审理适用的同一法规有:亲邻之法、典主故作迁延之法等。
所谓“亲邻之法”,是宋代颁布的专门用以规范田宅交易中当事人之亲邻行为的专门法规。因为此法令既关涉田宅交易中卖者一方的行为,也关涉到田宅取赎时亲邻的优先权问题,故在田宅交易中十分重要。依据宋代法令,田宅交易中,不论是卖,还是典,都要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即田宅出卖人的房亲与四邻有优先购买权。如田宅出典,业主已死,又无子女,亲邻可优先赎回。之所以如此规定,是为了维持家族之间的和睦、邻里之间的融洽,当然也是出于保护交易的安全。南宋时,亲邻之法的法意有所变化,依《清明集》卷9中胡石壁(即胡颖)之解释,亲邻之法的意思是:
照得(即勘会案卷后得知——引者注)所在百姓多不晓亲邻之法,往往以为亲自亲,邻自邻。执亲之说者,则凡是同关典卖之业,不问有邻无邻,皆欲收赎;执邻之说者,则凡是南北东西之邻,不问有亲无亲,亦欲取赎。殊不知在法:所谓应问所亲邻者,止是问本宗有服纪亲之有邻至者。如有亲而无邻,与有邻而无亲,皆不在问限。见于庆元重修田令与嘉定十三年刑部颁降条册,昭然可考也。今谭亨所欲执赎堂弟出典之田,既是有亲无邻,则是于法有碍,合照佥厅所拟行。
于此判中可知“亲邻之法”中亲邻的界定,也可见同一类纠纷中,皆适用同一规则。
在田宅的出典中,典主(即典权人)经常假“务限法”之规定,当业主备钱收赎时,迁延拖沓,至务开时,不予还业。故此,朝廷颁布法令专门惩治此类行为。由于此类行为具有普遍性,故同一类案情中皆适用此一规则。胡颖在审理“典主迁延入务”一案中说:“‘在法:诸典卖田产,年限已满,业主于务限前收赎,而典主故作迁延占据者,杖一百。’赵端合照本条勘断。”(49)
其次,为了维护田宅交易的安全,南宋的法官们在民事审判中总结了五种“不予受理“案件的类型,现据台湾学者刘馨珺之研究,条例总结如下,以证宋代民事审判遵循同一案情同一处理之准则。这五条法令是:(1)“交易典卖田宅满三年,而诉以准折债负,官司不受理”;(2)“诸典卖田宅满三年,而诉以应问邻而不问者,不得受理”;(3)“诸理诉田宅,而契要不明,过二十年,钱主或业主死者,不受理”;(4)“典产契头亡没,经三十年者,不许受理”;(5)“已分财产满三年而诉不平,及满五年而诉无分违法者,又遗嘱满十年而诉者,各不得受理”。(50)
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即依法判决的原则。中国古代的司法审判,无论是刑事,或者是民事,都是依据法条判决,这本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可是为何学界既有前几年的日本学者滋贺秀三与华裔美籍学者黄宗智之间的大辩论(51),也有台湾学者张伟仁与北京大学贺卫方、清华大学高鸿钧先生之间的学术争鸣呢?争论的原因固然有多种,如立场不同、视域不同、方法不同等等,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持中国古代司法审判是“卡迪司法”、诉讼是“父母官型”诉讼的学者,大都被中国古代的“法意”与“人情”互相融合所带来的假象所迷惑,故执意认为中国古代的司法判决,尤其是民事审判主要以“情理”为主,没有法的生长空间,其实,这是误解。就宋代的民事审判而言,根据现代能够看到的案例,台湾学者刘馨珺、河南大学孔学先生均依《清明集》之统计,得出了称引法条53%以上及引用法条占判案篇数1/5以上的结论。(52)
窃心以为,用引用法条的实证性结论,固然是对宋代民事审判基本上是依法判决的肯定,但却无意中回避了一个颇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即中国古代,宋代也是一样,民事判决中的确在遵循依法判决的原则时,还有着一个“法意”与“人情”融合的问题。怎样理解这个问题?法意与人情的协调是否就是对“依法判决原则”的颠覆?我的看法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第一,宋代的民事审判案例中,虽然依然保留着道德伦理的说教,道德伦理即是情理中的重要内容,但若从宋代的历史语境出发,把这些道德教化的说辞放至宋代私有制深入发展、“争财尚利”已成为宋代时尚的大背景中考察,便可看出,儒家的道德防线已在“民事纠纷”的汹涌大潮中溃退,法官们使用道德伦理说词时,与其说是坚守人伦道德防线,不如说是在说词的表象背后,表达着时代的新内容,这个新内容就是正视发生在兄弟、父母子女及家族内的财产纠纷,以说教为幌子,行依法判决、维护当事人(不论他是卑还是幼,只要法律允许)合法利益之实。我对《清明集》一书所载案例的统计是:民事案件共226件,依法判决的占75.22%;表面息讼,实为判决的有10件,占4.4%;息讼教化的占17.2%。这个数字说明,在儒家人伦文明形态的大背景下,读儒家之书的法官们完全摆脱道德说词的束缚是不现实的,但其司法理念又确实在新的社会结构面前发生着裂变,这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
第二,从法官审理的个案来看,考虑情理,依然是在依法条之规定的基础上,作出判决的,故依法给断仍是其判案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不可动摇的。
再以吴恕斋审理的“孤女赎父田”一案略加分析,以证其实。判词称:
俞梁有田九亩三步,开禧二年(1206年)典与戴士壬,计钱八十七贯。俞梁死于绍定二年(1229年),并无子孙,仅有女俞百六娘,赘陈应龙为夫,当是之时,阿俞夫妇亦未知此田为或典或卖。至嘉熙二年(1238年)三月,始经县陈诉取赎。而戴士壬者称:于绍定元年内,俞梁续将上件田作价钱四十五贯,已行断卖,坚不伏退赎。展转五年,互诉于县,两经县判,谓士壬执出俞梁典卖契字分明,应龙夫妇不应取赎。今应龙复经府番诉不已,准台判,佥厅点对,寻引两词盘问,及索俞梁先典卖契字辨验看详。切惟官司理断典卖田地之讼,法当以契书为主,而所执契书又当明辨其真伪,则无遁情。惟本县但以契书为可凭,而不知契之真伪尤当辨,此所以固士壬执留之心,而激应龙纷纭之争也。今索到戴士壬原典卖俞梁田契,唤上书铺,当厅辨验,典于开禧,卖于绍定,俞梁手押,夐出两手,笔迹显然,典契是真,卖契是伪,三尺童子不可欺也。作伪心劳,手足俱露,又有可证者,俞百六娘诉:取赎于嘉熙二年(1238年)二月,而士壬乃旋印卖契于嘉熙三年(1239年)十二月,又尝于嘉熙三年三月内,将钱说诱应龙立契断卖四亩,以俞百六娘不从,而牙保人骆元圭者,尝献其钱于官。使其委曾断买,契字真实,何必再令应龙立断卖契,又何为旋投印卖契于俞百六娘有词一年之后耶?此其因阿俞有词取赎,旋造伪契,以为欺罔昏赖之计,益不容掩。切原士壬之心,自得此田,历年已深,盖已认为己物,一旦退赎与业主之婿,有所不甘,故出此计。照得诸妇人随嫁资及承户绝财产,并同夫为主。准令:户绝财产尽给在室诸女,而归宗女减半。今俞梁身后既别无男女,仅有俞百六娘一人在家,坐当招应龙为夫,此外又别无财产,此田合听俞百六娘夫妇照典契取赎,庶合理法。所有假伪卖契,当官毁抹。但应龙既欲取赎此田,当念士壬培壅之功,盖已年深,亦有当参酌人情者。开禧田价,律今倍有所增;开禧会价较今不无所损。观应龙为人,破落浇浮,亦岂真有钱赎田,必有一等欲炙之徒资给之,所以兴连年之讼。欲监陈应龙当官备十八界官会八十七贯,还戴士壬,却与给还一宗契字照业。俞梁既别无子孙,仰以续祭祀者惟俞百六娘而已,赎回此田,所当永远存留,充岁时祭祀之用,责状在官,不许卖于外人。如应龙辄敢出卖,许士壬陈首,即与拘籍入官,庶可存继绝之美意,又可杜应龙贱赎贵卖之私谋,士壬愤嫉之心,亦少平矣!(53)
这篇判词叙述的案情并不十分复杂,前文已经叙述,争讼的焦点为:俞梁——即俞百六娘之父的一块田产,到底是典给了戴士壬,还是卖给了戴士壬。若是卖,俞百六娘无权可赎,是典则依继绝法当赎父田。戴诉说是卖,俞百六娘夫妇诉称是典,二者争诉不已。
现查明,此田产是典,不是卖。戴所执卖契,经书铺辨验为伪造。故俞百六娘夫妇于法可赎。依据的法条有二:一是在室女继绝法令,文中所谓准令,即依此;二是法官查出来的法条——即“诸妇人随嫁资及承户绝财产,并同夫为主”,依此法条,俞百六娘与丈夫陈应龙共有赎回权,只不过当以丈夫之名起诉。故吴恕斋作为法官在查明案情后,依法判决俞百六娘夫妇可赎回父田。不过判词中又提到“当参酌人情”,这是必须引起我们关注的,因为法意与人情的平衡,或叫融合,是南宋法官在民事审判中必须面对的话题。在他们看来,二者并不矛盾,所谓“殊不知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循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54)。此为胡颖之语,他代表了南宋法官乃至中国古代法官的共同理念。以此来看此案中吴恕斋的处理,所谓的“参酌人情”在本案中所指有二:一是戴士壬对所典之田有“培壅之功”,二是陈应龙为人破落浇浮,不是勤苦持家之人,其背后说不定有人指使。故法官在判决其有权赎回田产的同时,还特意要求陈应龙向官府写状担保,不许赎回后,卖与他人。应当说,这样的“参酌人情”完全合乎情理,也没有从根本上破坏“依法给断”的原则。
第三,宋代于地方州一级机关设有专门的检法机构——即法司,还配有专门的检法官员,史称司法参军。他们负责保管皇帝新颁的法令,并在长官判决时,检出适用的法条,这也就保证了法官——即地方长官依法判决的可行性。从现存的史料来看,不但《江苏金石志》第13册第32页中保留了宋代法司检出来的法令,(55)《清明集》一书也载有法官依法断决民事案件的典型案例,现再具引一例如下,以示宋代的司法具有典型的成文法传统之特色,客观性与确定性才是其本质,这样的判决引用法条分明,与“卡迪司法”格格不入。
案例一:游成讼游洪父抵当田产
判案法官范应铃
准法:应交易田宅,过三年而论有利债负准折,官司并不得受理。(56)又准法:应交易田宅,并要离业,虽割零典卖,亦不得自佃赁。游朝将田一亩、住基五十九步出卖于游洪父,价钱十贯,系在嘉定十年,印契亦隔一年有半。今朝已死,其子游成辄以当来抵当为词,契头亡没,又在三年之外,岂应更有受理。且乡人违法抵当,亦诚有之,皆做典契立文。今游朝之契系是永卖,游成供状亦谓元作卖契抵当,安有既立卖契,而谓之抵当之理。只缘当来不曾交业,彼此违法,以至互争。今岁收禾,且随宜均分,当厅就勒游成退佃,仰游洪父照契为业,别召人耕作。(57)
两宋之际,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转型,以土地私有制为核心的财产流转关系加快,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了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在人们生活世俗化的大潮下,社会各阶层的物质欲望空前膨胀,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构筑的处理社会纠纷的道德防线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一个由“伦理型”向“知识型”转化的司法机制与传统应运而生。宋代的“法官”在处理社会各阶层无所不在的诉讼纠纷时,尽管还要在儒家的语境内参酌“人情”,但是以法律为依据则是处理刑民案件的首要原则。法的客观性进入了宋代“法官”的视野,以“法”的功能确定人的财产利益边界是宋代司法的基本原则。宋代“法官”依法判决,重视物证,已非汉代以来司法官员“援情入法,法随情断”的传统司法模式所能涵盖,而是具有了法律作为知识与客观准则得以在民事纠纷的审判中发挥重要作用,且滋生了成长的空间。故宋代法官是依法判案,而不是随心所欲;宋代的司法传统是成文法传统,判决具有客观性与确定性,而不是“卡迪司法”。
注释:
①2006年11月,在中国的法律史学界发生了一场饶有趣味的学术辩论,论辩的双方均是活跃在现今法学界的著名学者,引起了业内人士对“中国传统法制与现代法治”关系的深层思考。论辩的焦点是:中国古代司法传统是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卡迪司法”(Khadi Justice)。以北京大学贺卫方及清华大学高鸿钧二位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同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认为中国传统的纠纷处理犹如“卡迪司法”,其过程不注重同样的事情同样对待,而是就事论事,完全不考虑规则以及依据规则的判决的确定性,将天理人情置于国法之上;天理人情的不确定性导致判决者可以翻云覆雨;人民无法通过这种司法制度伸张正义。而持相反观点的则是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张伟仁及林端教授(有关对韦伯“卡迪司法”命题的深入研讨,可以参见张伟仁:《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现代法学》2006年5期;林端:《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林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卡迪审判”或“第三领域”》,范忠信、陈景良主编:《中西法律传统》第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贺卫方:《中国古代司法的三大传统及其对当代的影响》,《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高鸿钧:《无话可说与有话可说之间——评张伟仁先生的〈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政法论坛》2006年5期)。
②参见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2007年;林端:《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
③《朱文公政训》,陈生尔辑:《政书集成》第4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36页。
④参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6年,第115-127页。
⑤台湾学者徐道邻先生说:“专门管审问刑事案件的官吏,宋朝官文书称之为‘推司’”(参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集》,第116页)。
⑥宋朝官文书所称的“法司”,包括内外各种机关里的“检查”、各州的“司法参军”和各县的“编录司”(参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集》,第119页)。
⑦参见汪荣祖:《史学九章》导言,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⑧《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四一。
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9页。
⑩《宋会要辑稿·刑法》五之十六。
(11)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请参见刁忠民:《宋代台谏制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
(12)《宋会要辑稿·刑法》五之十六。
(13)参见《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四十二。
(1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9,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576页。
(1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9,第2580页。
(1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9,第2581页。
(17)《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四一。
(1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真宗咸平三年五月丙寅记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第2册,第1021页。
(19)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第1020页。
(20)桂万荣:《棠阴比事序》,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年。
(21)李攸:《宋朝事实》卷16《兵刑》,《丛书集成初编》。
(2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第3册,第1659-1660页。
(23)参见《宋大诏令集》卷200,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42页。
(24)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3,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0年,第268-269页。
(25)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集》,第188页。
(26)中国古代依据儒家礼制思想,严禁卑幼告尊长,告者有罪。然而,到了宋代,随着土地私有制的深入发展,财富越来越受时人重视,《宋刑统》首先突破传统礼制的束缚,允许卑幼于尊长侵夺财物与殴打其身时,可以向官府起诉(参见《宋刑统》卷24《斗讼律·告论周亲》条及其疏议)。南宋时,卑幼因尊长侵夺财物而相告已成为时代风尚,这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绝非个案。如其卷5的“侄与出继叔争业”、卷6的“叔侄争”、“舅甥争”等。
(27)越诉的研究可参见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
(28)有关成果可以参见各类《中国法制史》教材,专著则有刘馨珺:《明镜高悬:南宋县衙的狱讼》(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这是宋史及法史学界近几年最有代表性的成果;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戴建国:《宋代法制初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张晋藩主编:《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等。
(29)参见陈景良:《宋代司法传统的现代解读》,《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
(3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3,第2658页。
(31)参见陈景良:《讼学、讼师与士大夫》,《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32)《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第106-107页。
(33)《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三○。
(34)《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三八。
(35)《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第106页。
(36)参见《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九一。
(37)参见《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二十九。
(38)参见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
(39)参见《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四十六。
(40)参见《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四十至四十一。
(41)《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四十六载:“高宗绍兴二年三月十七日两浙转运司言:准绍兴令,‘诸乡村以二月一日后为入务。应诉田宅、婚姻、负债者,勿受理。十月一日后,为务开。’窃详上条,入务不受理田宅等词诉,为恐追人理对,妨废农业。其人户典过田宅,限满备赎,官司自合受理交还。缘形势豪右之家交易故为拖延,至务限便引条法,又贪取一年租课,致细民受害。诏应人户典过田产,如于入务限内,年限已满,备到元钱收赎,别无交互不明,并许收赎。如有词诉,也许官司受理,余依条施行。”
(42)《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四十八。
(43)《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第112页。
(44)《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第313页。
(45)《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第315页。
(46)《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第336页。
(47)案例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孤女赎父田》,第315—317页。
(48)参见贺卫方:《中国古代司法的三大传统及其对当代的影响》,《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49)《名公书判清明集》上册,第138页。
(50)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第104页、第106页、第136页、第309页、第319页、第373页。
(51)参见易平:《日美学者关于清代民事审判制度的论争》,《中外法学》1999年第3期。
(52)参见刘馨珺:《明镜高悬:南宋县衙的狱讼》,第357页;孔学:《〈名公书判清明集〉所引宋代法律条文述论》,《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孔学把引用律条分两类情况:一是明确引用;二是法意暗含,没有明确引用。
(53)《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上册,第315-317页。
(54)《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上册,第311页。
(55)《江苏金石志》所引的法令是:“律:诸盗耕种公私田者,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敕:诸盗耕种及贸易官田、泥田、沙田、逃田,退复田同公田,虽不籍系也是,各论如律。”
(56)按照台湾学者刘馨珺之解释,此法条的意思是:典卖田宅完成交易满三年,业主到官府投词诉讼时,论诉钱主强迫业主将本意为抵当的田宅转变为典卖给钱主,则官方不予受理(参见刘馨珺:《明镜高悬:南宋县衙的狱讼》,第331-332页)。
(57)《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上册,第104-1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