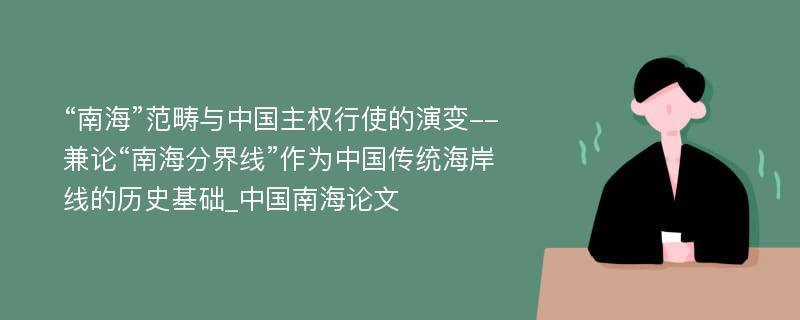
“中国南海”范畴及我国行使主权沿革考——兼论“南海断续线”作为中国传统海疆线的历史依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海论文,海疆论文,断续论文,沿革论文,主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3)02-0085-14
修订日期:2013-01-10。
由于国家海洋国土特殊的物理属性与地理属性,海洋国土的主权捍卫与治理十分困难。一直以来,我国学界普遍认为古代封建中国重视陆疆维护,轻视海疆维护,致使我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时,海疆危机频频,直接影响当代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事实上,从已掌握材料看,中国人的海疆意识古已有之。又由于中国历史上在亚洲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核心角色的扮演,使其与围绕中国海的国家交往基本处于主宰地位,①因此围绕中国海(包括中国南海)的海洋开发、海疆维护是存在的,且古往今来不断加强。同时,也确实存在与周边国家就南海的海洋开发与海洋管理的不对等状态。即使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发展低谷阶段,中国历代政府也不断适应并接受西方主权理念,顺应现代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迅速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融入国际社会,遵循国际政治秩序的一般法则与国际法,积极捍卫国家陆地与海洋国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不断增强,对南海诸岛以及中国传统海疆的主权宣示与维护也更加得力。
目前,中国南海诸岛归属问题的争斗日趋白热化,关键在于南海周边各声索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要求存在重叠与冲突。我国作为开发南海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在最早发现、开发、管理南海诸岛方面有着十分丰富与确凿的证据。但是按照1982年联合国颁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显然不能厘清历史上我国与东南亚诸声索国对南海诸岛主权诉求的复杂关系。当前,矛盾焦点集中在中华民国内政部于1948年向世界公开发行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中一条“南海断续线”的标示是否具有国家疆域即国界线的地位。这条“断续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政府通过地图标示的形式,正式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对南海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与管辖权范围。同时,这一国界线自颁布之日起至今60余年中,在我国涉及中国国家版图的地图中均无一不标示与体现,且在国际社会中无人提出异议。只是在1968—1969年西方学者论及南海蕴藏大量海底石油、天然气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后,才有所谓的“声索国”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并作出相应举动。如一些国家对南海诸岛的非法占有行动、菲律宾擅自将“中国南海”更名为“西菲律宾海”,企图通过修改海域名弱化中国对该海域拥有主权的历史性影响。因此,对该断续线的产生背景、划线依据及其合法性的认真考证很有必要。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南海”作为世界通用地名及其范围的考证,梳理有关“中国南海”演变的历史事实与关于边疆的基本理论,证明“南海断续线”的产生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它作为中国传统海疆线的地位,为我国“中国南海”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维系提供了历史与法理的有力证据。在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就南海诸岛主权归属讨论以及海洋划界博弈中,这应成为重要依据,不容犹豫和退让。
一、“中国南海”传统疆域四至考证
中国对南海的发现、认识、开发与命名,源于古代中国封建国家政治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与政治实力的不断加强。国家形态的出现,意味着疆域治理的开始。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诗经·江汉》有“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的记载。中国作为最早建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皇权国家,海疆思想古已有之。秦始皇统一全国,在今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设立“南海郡”,治所广州,虽为在陆地的政权建制,但由于岭南先民发达的海洋性文化生活特质,其控制范围已入南海海域。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立包括“南海郡”在内的岭南九郡,也是以中原王朝为统治核心,加强对南部濒海边疆的控制,并确定行政区划命名。这一时期,中国对南海控制所及包括环北部湾在内的南海北部地区。
我国古代与南海周边国家往来频繁,期间我国一般史籍文字对南海的记载又泛称其为“涨海”,这一名称活跃于汉唐以降直至明清。《后汉书》载:“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②鉴于当时交趾(今越南中北部)的地理位置,该地时而作为中国郡县时而作为中国藩属国的地位,可以肯定北部湾、海南岛以南水域均在中国海疆范畴。南北朝时期,南方各割据政权海上活动频繁,依托南海贸易实力大增。东晋末年,刘裕与卢循领导农民义军发生著名的南海海战,“虎骑鹜隰,舟师涨海”③,证明这一时期南海也即“涨海”已对传统中国具有政治地理的深刻内涵。这一时期,阿拉伯人是由西向东穿越阿拉伯海、印度洋、南海,成为与中国贸易的主角,在他们的海洋地理中“涨海”(Cankhay)即“中国海”④。20世纪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中外国学者经过多方考证,指出古代“涨海即海南岛迄满剌加海峡(今马六甲海峡)间中国海之称”⑤。而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则直接将中国古籍记载之“涨海”翻译为“南海”,可知传统中国海疆形成之早,并为当时世界所认同。自宋以来,“涨海”范围与今天的“中国南海”范围相同,并成为往来于此间的各国使者、商人、航海家所认同的共识。
隋唐时期,中西交通盛大空前,中国在南海水域的生产、经营以及政治控制不断加强。在官修《新唐书》中,专设“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录以广州为出发点,经九龙半岛,西沙、南沙海域,穿越南海通往东南亚甚至印度洋各国一条清晰的航道,沿途经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约1万公里。直至16世纪前,这是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⑥中国对南海的开发与利用程度之高,可见一斑。
元朝,中国政府经略南海,规模巨大。首先,1292年12月,忽必烈派福建总督史弼、高兴、亦黑迷失等征集士卒2万,从泉州出发,驾千艘战船出师爪哇,“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东西董山(据考证为今越南平顺一带海面),牛崎屿(亦作蜈蜞屿,今南沙群岛一带),入混沌大洋(南沙群岛一带海域),橄榄屿,假里马达,勾栏等山”进入爪哇,平定叛乱。⑦这一航海路线为明朝郑和下西洋时沿用,可见当时中国政府对南海的政治驾驭已覆盖南海诸岛。其次,元代郭守敬受命于中央政府,“南逾朱崖”,通过“四海测试”确立国家疆域四至,确立历法,其测试所之一,也是中国海疆之最南端就在今南海(黄岩岛)。⑧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对南海的认识与经营更为深入。元代,在以我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下,围绕南海对东南亚诸国的海商贸易、海上移民都很发达,我国航海业又将南海具体分成大西洋、小西洋、大东洋、小东洋等水域。元朝大德年间(1297—1307年)成书的《南海志》,依据中国海商与渔民在南海航海、作业的东西诸多航线,以文莱(古称渤泥)为南海之东、西洋的分界线。⑨尤其是,中国人主导往来频繁的东洋航线,即由江浙、福建一带航海经台湾岛附近水域、南过菲律宾西海岸、穿越黄岩岛、南沙群岛东部水域到文莱的往返航路,直至今日仍为南海周边多国所使用。此外,在我国南海周边地区并未形成长期稳定的封建国家,尤其是明清以来这些地区在全部成为西方殖民地的主权缺失之政治状态下,我国近800年的传统航路可作为该水域属于中国历史性水域的有力证明。
明朝,张燮在《东西洋考·舟师考》卷九中,专门就潮汐比较我国东海、南海之不同,“东海、南海,其候各有远近之殊”。该书中已将我国版属的东海、南海相区别,对所属南海已有清晰的界定。明清时期,我国各类国家及地理学者编撰的地图与书籍中,南海被标注为“大明海”,或“大清海”,以国名标注所属海域,也明显具有国家海疆的内涵。
明清以来,随着人们对南海错综复杂的地理地貌的了解,这一时期中国南海内的基本地理标志均在当时地图中标明,“七州(洲)洋”也即“广东外七洲洋”、“七州(洲)大洋”,指中国南海广大水域,中外史籍、地图均有记载。如Francisco Rodrigues绘于16世纪初的《中国地图》,在海南岛至昆仑岛之间,绘有“七洲洋”字样。⑩如乾隆时期《四海总图》中,大清国“中国南海”范畴包括从琼州直至中外分界的昆仑岛、茶盘之间,即“七洲洋”。这时期七洲洋成为南海的主要构成,在七洲洋东到吕宋及其周边岛屿之间,“沙头”、“长沙”、“石塘”等南海诸岛的中国名称标注其间,(11)说明当时的七洲洋包括所谓“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也即今之南海诸岛。道光时成书的《海录》所绘世界地图,以“七州洋”标注的海域直指南沙以及更南部的中外海境分界。光绪十三年(1887年)成书的《洋防说略》地图,七洲洋海域,东至马尼剌(今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南部涵盖千里石塘(南沙群岛),西至越南东海岸与万里长沙(西沙群岛)之间。(12)清末,历史进入近代,外交官郭嵩焘乘船经中国南海出使西方国家,记载“在赤道北13°,过瓦蕾拉(越南华里拉)山、安南东南境,海名七洲洋”(13)。
中国历史上,南海又称“南洋”,有广义狭义之分。一指“南洋诸国”,即中国古代对东南亚诸国的总称,主要指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诸国,因其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海边缘,故得名。(14)一是特指“中国之南洋”,以中国大陆为地理坐标参照命名所属洋面,并明确宣誓其归属。清朝时的南洋,包括今天中国南海诸岛在内的大部分水域。19世纪30年代颜斯综在《南洋蠡测》载:“南洋之间,有万里石塘,俗名万里长沙,塘之南为外大洋,塘之东为闽洋,夷船由外大洋向东,望见台湾山,转而北入粤洋,历老万山,由澳门入虎门,皆以此塘分华夷中外之界”(15),说明将南沙群岛以南附近洋面作为南海中外水界,并成为世界远洋航海界的共识。同时,中国南洋海面亦作“粤洋”,清朝官修地图明确注明:“广东全面濒海,东南值吕宋群岛(今菲律宾),南对婆罗大洲(今加里曼丹岛),西南际越南东境,海面辽阔,总名南洋,属广东省境。”(16)如此清晰勾勒出中国南海的范畴,且说明在清朝时,中国南海(粤洋)及其附属岛屿归广东省行政具体管辖。
16世纪,最早来东方冒险的海上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对中国南海及其岛屿的归属判断以及命名,也是源于航海时对这些岛屿与水域的中国渊源与中国属性的认识。据考证,16世纪葡萄牙航海图中,在现西沙群岛位置有“中国岛”(Chiis)的标注,其中永兴岛位置的命名有“Paxo港”、“I.dos Boicas”。其前者为海南渔民称永兴岛为“巴峙”的对音,后者为海南渔民称永兴岛为“有树林的岛”——“林岛”的意译,并在其下标注葡文(Cham),明确表明该地为中国渔民活动范围且归属中国。另有我国鸦片战争(1840年)前翻译外国人所绘制的地图,均在万里石塘、万里长沙等处(西沙、南沙群岛)标注“矸罩”、“干豆”字样,实为原地图葡萄牙文Cantao、或Canto(归属广东)的中文翻译,(17)这也从侧面说明西方航海者依当时习惯法,向世界揭露了南海及其附属岛屿归属中国的事实,并予以肯定。
两次鸦片战争后,以东印度公司为基地,西方列强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打破了传统亚洲政治秩序。中国人开始逐渐学习并顺应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世界的价值判断,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不断加强。这一时期晚清政府不仅加强陆疆疆域的勘察界定,也在与西方列强接轨的艰难探索中努力维护固有海疆。而“中国南海”之名实为在西方帝国主义兴起的全球化过程中,依据国际通用的习惯法规则界定地域的结果。
从已经掌握的资料分析,最早从文本与海图上将南海定义为“中国海”的西方国家应是英国。当时世界海权强国的英国作为侵略中国的主导,英国舰船多次侵入南海调查测量,并依据南海历史传统与当时开发占有形势,对南海水域及岛屿测量、命名、记录成册,陆续刊登于海军部编辑的航海指南和航海图中。1868年出版的《中国海指南》(China Sea Directory),记载了南海海域诸岛中大量中国渔民的活动,并根据显然是海南渔民岛屿命名的发音,命名“景洪”与“鸿庥”两个南沙群岛的岛屿。(18)据统计,仅19世纪80年代,英国以“中国海”为勘测对象的航海指南或地图就达6种。(19)英国对中国南海的关注,一直延续近百年,现已掌握的1885年版《海道测量及航海气象年鉴》、1923年《中国海指南》(China Sea Pilot)、1937年《中国海指南》,其中不乏对所谓“中国海”界内诸岛屿的情况描述,主要涉及中国海南渔民在这些岛上的生产生活、岛屿方位与命名,其中,对采用现代测绘技术定位的岛屿命名,也参考中国渔民的命名,这应是当时国际惯例。从中可见,西方殖民者对“南海”属于中国历史性水域的历史事实的认可与继承,其命名该水域遵从了“名从主人”的世界地名学原则与规律,是对中国传统南海海疆疆域的尊重。(20)
这种基于当时国际惯例以及国际法的作为,也为迅速转型的中国晚清政府所认可并接受。1876年秋,清朝外交官郭嵩焘及其随从张德彝乘外国船出使英国,行至北纬17°左右,记载“在琼南二三百里,船人名之‘齐纳细’(China Sea),尤言中国海也”。船经西沙群岛(英文名柏拉苏parasel),都记载为“中国属岛”(21)。至19世纪30年代,对“中国南海”的地理标示广泛存在于各国地图中,或称之为China Sea(22),或称之为South China Sea(23)。“二战”结束的1945年,“中国南海”之名广为流传,已越来越国际化,我国学者在对南洋与东南洋群岛的研究中指出:“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岛)乃南洋群岛之地大者,居中国海之中央,与粤之琼州南北遥遥相对。……(该岛)西与北皆中国海,南则爪哇海。”(24)
鉴于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在南海漫长演变历史中强有力的开发能力、实际占有能力以及巨大的影响力,“中国南海”的称谓正是在国际社会形成、不断成熟的国际法运用过程中,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识、接受,并演变成为当今这一水域的国际性正式名称。这也是中国对该海域享有历史性权利的有力证明。
二、“中国南海”清晰的海域界定具有中国传统海疆的地位
为了从庞杂的历史资料中考察我国南海地理范畴的形成与历史沿革,我们可以按照厚今薄古的基本思路进行,自宋、元始,经明、清两朝,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南海变迁,中国南海海域不断清晰。
西北界:中越交界自陆地始。明清以来,中越之间大部分时间秉承传统宗藩关系,虽时有边界纷争,多属于陆疆范畴。清初,国家海防极西在中越边境,“廉(州)多沙,钦(州)多岛,地以华夷为限”(25)。1885年中法战争后,以芒街作为两国陆地国界,中法又签订《续议界务专约》,其中第三款对海中各岛归属明确规定:“照两国勘界大臣所划红线,向南接划,此线正过茶古社东边山头,即以该线为界,该线以东,海中各岛归中国,该线以西各岛归越南。”(26)这也正是当时民国政府在南海划定由11条断续线构成国界线之前(北部湾段)两条线的划界依据。
西界:中越在南海西部水界,应在西沙群岛与越南近海之间。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成书的《海语》,已经明确指出,中国南海与外国海上分界为“分水洋”,“分水在占城之外罗海中,沙屿隐隐如门限,延绵横亘不知其几百里,巨浪拍天,异于常海。……天地设险以域华夷”(27)。占城,古代又称占婆国,大体在今越南中部。外罗海即越南中部广东群岛(Poulo Canton又称Culao Ray理山群岛)附近洋面。同时,该书又指出:在中越分水洋以东海域,专就“乌潴、独潴二洋以东”的“万里石塘”和“万里石塘”东南方的“万里长沙”设项记载,说明当时的“分水”已经把中国南海海域的三沙群岛与越南近海岛屿分开,“中国南海”已将现在的三沙群岛包括在内。(28)清初,我国由厦门至广南的航线为“过安南界,历七洲洋,取广南外之占毕罗山,即入其境”(29)。经考证,占毕罗山系指越南外罗海上一系列群岛中之一岛,不是越南当局所声称越南拥有西沙群岛(越南称之为黄沙与长沙)的一部分,(30)越南外罗洋作为中国南海与越南近海水界的分界是历史事实,也进一步印证明、清两朝中越南海西部海界一直延续未变。
对这一海上分界线,东南亚各国早已认同并以此作为海上航行时进入中国海的重要标志。1780年,暹罗国王郑昭遣使入朝中国,使者丕雅摩柯奴婆的《纪行诗》记载其从曼谷出发,经海路赴中国,经昆仑岛(Khao Khanun)由南向北沿今越南沿海北上,经占城(Muang Pasak)—大越港(Paknam Yuan Yai)—灵山(Intangtuab Utra),最终“始达外罗(Walo)洋,自此通粤道”,再过横山(今越南岛屿),“至此边界尽”,转针折东方,之后便经老万(Loban)舟入澳门,明确外罗洋外就是中国海范畴。该诗所记路程与清政府《清通考》卷297所录一一印证:“自曼谷启碇出港口……更二日遥望河仙,再二日过横岛及番薯岛,又二日抵昆仑山,亦曰军屯,转针越占城,前进二日半,得望大越港,后三日见越象山,再四日达外罗洋,过此则中国境,入老万港抵澳门。”(31)
再者,大量史实表明,中外南海西部重要分界标志为昆仑山(岛)(北纬8°40′,东经106°35′),在今越南段湄公河出海口海面。由外罗海下西洋,至昆仑洋,便真正离开中国南海(七洲洋)。自宋以来的南海航海界,昆仑岛一直是中国南海赴西洋诸针路的起点,如从昆仑山赴暹罗(今泰国)、昆仑山赴大泥国(今马来半岛一带)、昆仑山至六坤(马来半岛东岸)、昆仑山至麻六甲(今马六甲海峡)(32),昆仑岛以西称为西洋。清时,舆地学者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卷2载“七州洋之南,有大小二山,屹立澎湃,称为昆仑”(33),表明昆仑岛是七洲洋南界极限。同时,《清通考》作为专记清朝历代典章制度的法典也指出,有外国贡使回国,“自广东香山县登舟,乘北风用午针,出七洲洋,十昼夜抵安南海次,中有一山名外罗,八昼夜抵占城海次,十二昼夜抵大昆仑山”(34),清晰记录了外国使船在此即出中国之海境,完成出使任务,昆仑岛成为走出中国南海进入西洋的重要标志。
总之,中国南海西部与越南所属海域的分界线在广东群岛(越南)东洋面与我国西沙群岛洋面以西之间。1948年民国政府方域司所绘“断续线”,正是基于这一历史事实划出两条西部断续线的。
南界:早在宋代,对中国南海之南界就已有定论。当时任职桂林通判的中国官员周去非在关于中国与南海周边诸国交往的著述中指出,由南洋诸国去中国,“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趾洋,乃至中国之境”。同时指出“闍婆(爪哇古称)之来也,稍西北行,舟过十二子石,而与三佛齐海道会于竺屿之下”,之后沿同一路线来华。(35)“三佛齐”也即明朝爪哇以西的旧港(今之巨港),从旧港北上经加里曼丹岛西岸,之后向北进入占城新州港,经交趾洋可到中国洋面。另一位宋代宗室赵汝适,任职中国南海中外贸易管理要职的福建路市舶提举,通晓中国南海事务,指出当时中国南海“有所谓石塘、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36),并有航海图为证,这说明由外海进入中国海境,必经南沙、西沙群岛,同时,以交趾洋与竺屿为中外海疆之分界。因此,考察“上下竺”、“竺屿”的具体位置,是确定中国南海南界的关键所在。
对“上下竺”、“竺屿”的研究,有以为是新加坡岛的,有认为是亚南巴斯群岛(Anambas Is.)的,一般以为,“上下竺”,即所谓“东西竹”,便为现今马来半岛东南海上的奥尔岛(Pulau Aur),因马来语(Aur)是竹子之意,而“竹”与“竺”同义,故许多中外史学家长期如此定论。(37)而经我国史地学者考证存在错讹。首先,中国古籍有据可查的有关南海以“竹”命名的岛屿有多处,(38)以“竺”命名者少见,“竺”与“竹”意义有所不同,大多数古籍中“竺”专指古印度,或姓氏。其次,当时航海图一般以中外地名对音或中国地名命名岛屿,不可以意译相同而牵强附会。再次,奥尔岛地处中国下西洋航线西侧,在昆仑岛以西且纬度相当,与《岛夷志略》载“(昆仑)与占城、东西竺鼎峙而相望”(39)的事实不符。再者,奥尔岛至今为荒岛,与我国古代著述中“上下竺屿”存在部落社会不符。
真正的“竺屿”应在加里曼丹岛一带,因中国古史将“天竺”国(印度)又称“婆罗门”,故对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教派以及文化统称“天竺”。(40)宋时,东南亚一带受印度文化影响,加里曼丹岛一带尤其受印度婆罗门文化影响较深,故普遍称该岛为“婆罗洲”,阿拉伯人甚至称之为“印度岛”,遂有对婆罗洲以及附近岛屿“天竺山”的命名。《宋史·外国传》载,宋时注辇国(印度洋一带古国)遣使朝贡中国,到三佛齐国后,“度蛮山水口,历天竺山至宾头狼山(今越南藩朗一带海域),望东西王母塚,据舟所将百里,又行十二昼夜,度羊山、九星山至广州”(41),其西来路线是从巴邻旁或占卑,北经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西的蛮山和天竺山,进入中国海境,继续航行到中南半岛之藩朗海面,可望见百里之外的南沙群岛(以中国宗教传说之圣地“东西王母塚”命名),由此推断,天竺山(屿)应在加里曼丹岛西岸。据中外史地学者考证,今纳土纳群岛昔称“Dadu”,“竺”乃马来语“Datu”的对音,也即“natuna”的转音。时至今日,在纳土纳群岛最北端仍有地方称作“Tanjong Datu”,可译为“那都岬”,以及“Datu湾”,(今译达土湾)。所以,“竺屿”应指纳土纳群岛,而东西竺、上下竺与北纳土纳群岛与南纳土纳群岛对应(42),也与元代《岛夷志略》描述其“石山嵯峨,形势对峙,地势虽有东西之殊,不啻蓬莱、方丈之争奇”相符。(43)历史上经加里曼丹岛西岸,北出纳土纳群岛进入中国南海的航线由来已久,早在唐朝,义净和尚去印度取经,取道南海海路回广州,所经南海诸国多在苏门答腊、爪哇以及加里曼丹岛一带。(44)明朝《武备志》所载《郑和航海图》以及民间海道针路也清晰描绘出这一航海路线,从占城新洲港(今越南中部归仁一带)出发,为避昆仑山之险,至加里曼丹、爪哇时,由东、西董山(应为今越南平顺一带海面)分途,向南航行,途经东蛇龙山(或龙蛇山)、沙吴皮(均在纳土纳群岛之内),沿加里曼丹岛航行可至爪哇。(45)同样可以证明这条航线的是明朝我国与爪哇等国朝贡往来的官方路线:从占城出发,取灵山,经蜈蜞屿、冒山、东蛇龙山、圆屿、双屿、罗帏屿、竹屿,进入鸡笼屿、吉里门山,最后至爪哇新村,已经考证的东蛇龙山、罗帏屿等岛屿均属于今纳土纳群岛之一部分,且其命名都与当时的“竺屿”、“上下竺”存在紧密联系。(46)那么,可以断定所谓“天竺山”、“上下竺”、“竺屿”,当指加里曼丹岛附近岛屿,即今纳土纳群岛,而纳土纳岛的印尼文Bunguran,是Pingeran 的转音,意曰“边界”,中国古籍《混一图》称为“平高仑”,是其对音。因此,自宋元以来,纳土纳群岛北端(北纬2°30′—4°,东经108°—109°)是中国南海的南界,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明朝亲下西洋的官员费信在所著《星槎胜览》中,描述“东西竺”之地时确言:“东西分海境”,指出东洋航线北出纳土纳群岛后即进入中国海境,并介绍南海中有“长沙、石塘数万里”,将南海诸岛囊括在中国海界南界之内,它也恰恰是传统航线出入中国海的必经之地。直至20世纪20年代,海南琼海县渔民抄录的《更路薄》仍有墨瓜线(北纬5°22′)—浮罗丑未(Pulo subi即纳土纳最北沙吴皮群岛),墨瓜线—宏武銮(即故称平高仑Bunguran,也是印尼语“纳土纳群岛”的音译)等航海路线。(47)这证明我国航海海商以及中国南海渔民在南沙群岛从事航运、贸易、捕鱼等社会生产活动由来已久且延续至今,且纳土纳群岛以北中国南海境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海南渔民传统渔场这一历史事实。时至今日,我国海南仍有渔民依世代相传民间航海书——《更路薄》至曾母暗沙捕鱼,打鼓鸣锣飘放彩船,拜祭海神,中国文化远播于此。总之,现在婆罗洲西北海域附近的纳土纳群岛,自宋代以来就一直被作为中国海与外国海的交汇之点,也就是中国海境与外国海境的南部交界之处。
东界与东北界:早在13世纪之前,西方人还未到达我国南海东部地区时,“中国人几有史以来,皆与此群岛有接触,并充分知此群岛位置”(48)。中国人在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菲律宾(当时的吕宋、苏禄等地)贸易、移民频繁,且多为广东、福建人,对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起到重要作用,影响深远。移民由厦门、泉州出海,“西洋针路”往往习惯于沿着亚洲海岸向西航行远赴印度、北非一带。同时,以文莱为东西洋航线的分界线,船只赴麻逸(菲律宾古国)、吕宋、苏禄、巴拉望(今属菲律宾)、婆罗洲(加里曼丹岛)、爪哇等地,为避开七洲洋西部长沙、石塘(泛指南沙群岛)之险,选择沿台湾以东的海岸线行驶,沿菲律宾群岛以西洋面南下,今即所谓“东洋针路”。(49)明朝以来,中国福建航海家赴菲律宾诸岛、文莱(加里曼丹岛)的航线有四条:一是从福建太武山出发,经台湾澎湖屿、虎头山、笔架山、大港、至密雁港(吕宋岛北);二是从密雁港经麻里荖屿(今棉兰老岛)、玳瑁港、头巾礁、吕宋岛、猫里务国(吕宋岛西);三是从吕宋出发经沿岛西侧南下,至绍山、美洛居(今马鲁古群岛)、苏禄国(菲律宾群岛南部);四是从吕蓬、芒烟山、磨叶洋、巴荖圆(今巴拉望)、罗葡山(今菲律宾Palawan巴荖圆西南五更地方)、圣山(文莱国附近洋面)、长腰屿、直至文莱港口。(50)在这里特别指出,东洋航线所过洋面统称东洋,囊括今菲律宾各岛西部洋面;东洋航线作为我国航海家、商人长期活跃的海上活动场所,既与当时沿岸国家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同时长期控制航线所涉范围。总而言之,中国南海诸航路均以今日的西沙、南沙群岛作为航线的重要航标,并包括在该航线中国南海范围之内。我国古代航海指南书籍《顺风相送》之《定潮水消长时候》和《指南正法序》中均强调指出:能在南海安全航行的关键是“若进入七洲洋(中国南海),贪东七更,则为万里长沙(南沙群岛)”;“若船七洲洋落去,贪东七更,船见万里石塘(南沙群岛)……船若回唐,贪东,海水白色赤,见百样禽鸟,乃是万里长沙”;(51)南沙群岛成为进入七洲洋(中国南海)境内的基本地标。最新发现的明代福建航海家绘制的彩色绢帛航海图——《明朝东西洋航海图》,清晰地将这些航线标示其中,西沙、中沙、南沙群岛(包括黄岩岛)尽收入中国政府经济、政治管辖范围。(52)时至今日,中国海南渔民仍以南沙群岛为长期渔场,没有高超的航海技术以及代代相传的历史传统与经验是不可能做到的。明清以来,该水域作为中国南海(七洲洋)的一部分,一直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所谓“东到马尼拉,南到南沙群岛,西至越南东海岸,东经109°万里长沙(西沙)以东洋面”的中国海疆至此轮廓已逐渐清晰,民国时期“九段线”的划界依据也已十分清楚地呈现出来。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宋明以来,吕宋、苏禄、棉兰老、巴拉望等现属菲律宾诸岛屿,或为零散部落,或为中国朝贡藩属,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的统一国家,直至20世纪40年代,当时还称为“吕宋群岛”的菲律宾共1200岛屿,有人居者仅408岛,(53)可以推断:到1946年才真正立国的菲律宾,对自己版图内的岛屿尚不能有效占有和控制,又如何占有并控制黄岩岛呢?当时,其他南海周边国家也多为欧美各国殖民地,建立现代国家相对较晚。印尼1945年8月建国,马来西亚1957年建国,越南直至1975年5月才实现南北统一,文莱建国更迟至1984年2月。而越南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诉求却是继承原法国殖民者的扩张企图。显然,我国自汉朝以来作为长期稳定的封建帝国对中国南海及其附属岛屿的探索与长期经营事实,对“中国南海”的国际化命名产生的深远影响,足证该水域是中国历史性水域。而菲律宾以及其他声索国对南海及其附属岛屿提出主权要求以及修改海域名的企图,是无视中国在该地区长期存在的历史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通过对中国南海传统疆域四至的考证,可以发现,以中外历史记载以及中国历朝历代政府与人民经营、开发南海及其附属岛屿的历史事实,确定中国南海的界限,有以下几个关键地点:中越北部分界:交趾洋;中越西部分界:越南近海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外罗洋;西南分界:昆仑岛(北纬8°40′,东经106°35′)及其附近洋面;南界:加里曼丹西北岛屿北纳土纳群岛(北纬2°30′—4°,东经108°—109°);东界:南沙群岛以东与现菲律宾群岛以西洋面,北上直至台湾岛以东洋面(包括黄岩岛在内)。这与1948年民国政府划定的南海断续线基本吻合,这条断续线的标示均在中国传统海疆范围以内,符合南海历史演变事实,足证该线的划定有据可循,绝非主观臆造。
三、我国历朝历届政府在“中国南海”行使国家主权
3.1 古代中国封建制度下对中国南海管辖的践行
由于中世纪涉海技术水平的限制,对海洋疆土实施保护与管理最可行有效的办法就是“巡海”。据载,我国宋时在南海已经设立水军,加强海上巡逻。宋初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命王师出戍,设置巡海水师”,巡海范围南“至九乳螺洲……占不劳山……陵山东”。(54)九乳螺洲又称九乳螺山,旧指西沙群岛一带,而占不劳山(即上述之占毕罗山)和陵山(越南南部沿海城市)即为中越海域分界线。(55)
明清之际,一方面,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盛行,其中大多数国家踏海而来,我国政府必须加强海疆管理。为使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进行有序贸易,特设“海南卫”以维持中国南海秩序,并行使国家主权。如洪武十七年(1384年)“海南卫巡捕海上”,发现闍婆等国人14人,送至京师,并经中央批准遣送回国。(56)在与中国的贸易成为亚洲周边诸国重要经济命脉的同时,南海中西贸易带来的巨大财富则导致南海海盗猖獗。明朝中后期,中国政府不得不“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以避免国民在南海活动所带来的国防危险。明朝抵抗“倭寇”入侵的战事在我国东海和南海的广大水域进行,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政府曾联合占城在南海水域共同抗倭,“敕福建都指挥使司备海舟百艘,广东倍之,并具器械粮饷,以九月会浙江,候出占城捕倭夷”(57),得到占城方面的支持和配合。这一时期,民间贸易繁荣与海盗劫掠猖獗是南海中西交通的两大特色。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我国人民开发南海之盛,尤见政府维持海洋秩序,加强南海海疆军事防御与维护程度之深、范围之广。
清沿明制。清朝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1710—1712年),吴陞作为广东水师副将总理巡海事宜,其基本范围是:“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设法捕盗,奸宄屏迹。”(58)其巡海范围覆盖中国南海大部分地区。
由于我国在南海海疆的严格管理,因此出现了由中国政府、水师负责的海上救济制度。明朝时期,来中国朝贡、贸易的船只因海难漂流至中国南海,中国海疆管理机构都会倾力搭救并按照章程送至广州香山县等贸易口岸,并查明情况,周给口粮,使其附搭便船回国,如此案例《明实录》中俯拾皆是,清朝亦然。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两广总督杨应琚奏称:有马来由(Malayu,即今马来西亚)等国商船前往咖喇吧(Kalapa,今印尼首都雅加达),被风浪漂至“万州九洲洋”,后经该州(万州)查明,“依例外国船只被风飘至内地者,资遣回国”,后据广州香山县申报,将难番共12名经两次分别于十月与十一月“附搭便船回国”。(59)据考证,清朝万州九洲洋,也即西沙群岛及其洋面,因周边岛礁众多,故历史上人们又称“九洲洋”、“九星山”、也称前述的“九乳螺山”。(60)可以肯定,清初,七洲洋作为我国海洋疆土属于海南万州行政管辖,同时,中国政府对其他国家漂流至中国海境的难民实行海上救济,已经早于西方的所谓现代国际法,以当时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原则行使主权国家的主权与职责。
同时,自明朝中叶开始,西方殖民者以东印度群岛为基地,穿越南海殖民中国。至此,中国人开始以现代国家国界的视角审视传统南海海疆,并具体规划南海海疆版图。道光年间,清朝在海南岛崖州、儋州、海口分设协水师营,管理南海水域,其中最南端的崖州营“东自万州东澳港起,西至昌化县四更沙止,共巡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罗、占城夷洋”,中国海军巡海“中国南海”正是传统中国南海海域范畴,南沙群岛也包括在内。(61)光绪十三年(1887年)成书的《洋防说略》记载:“崖州(今三亚)在南……暗沙礁石所在有之。又有万里长沙,自万州迤东直至南澳。又有千里石塘,自万州迤南直至七洲洋,粤海天堑最称险阻”,是皆谈海防者所宜留意也(62),指出南海诸岛及其洋面是我国“粤海”海防范围。
清末,西方殖民者纷至沓来,海防日趋紧迫,中国政府加强对南海海防范畴的确定与布局,势力所及“东南值吕宋群岛(今菲律宾),南对婆罗大洲(今加里曼丹岛),西南际越南东境”(63),海面辽阔,完全覆盖中国南海,且与1948年中国政府划定的南海“断续线”管辖范围完全吻合。这种巡海传统一直延续到晚清新式海军建立后。
清末民初,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中国经历了由传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艰难过渡,对传统南海疆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维护与建设。同时,开始了中国对“中国南海”管辖的现代转型与治理。
1880年,正值中国近代国家建设的最有效期,在新疆与台湾相继建省之时,国家对海洋国土版图的认识也日益加深,对南海的治理上升到现代国家海疆层面。首先,依据当时的国际法,承担起维护现代国家对南海领土主权的责任与义务。如1883年,荷兰驻华大使要求清政府处理船只在东沙岛搁浅货物被掠照会,荷兰要求“和(荷兰)船在中国辖下海洋被劫,地方官闻报迅即设法查拿……和船在中国沿海搁浅碰坏,或遭风收口,地方官闻报即当设法照料”。当时负责对外交涉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立即接受,并积极营救。(64)其次,针对法国以及日本殖民者觊觎中国南海岛屿的企图,中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并宣示主权,如1898年抗议法国在西沙群岛建立渔民供应站,并成功阻止其侵略行径;1907年就日本人西泽侵占东沙岛(蒲拉他士岛)的行为,清政府通过对我国地方志、舆地书籍、中外航海图的证据收集,照会英日政府,力证东沙岛属于中国,最终以“收买”西泽物业的形式收回东沙主权,驱逐侵略东沙的日本人。(65)第三,遵循当时国际法对一国所属海域以及岛屿的归属判定原则,对南海水域地理特征以及所属岛屿进行命名、地理勘测、定期巡海,并建立行政管理机构,宣誓主权。如1909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派新式海军,分乘“伏波”、“琛航”、“广金”三兵轮,两次巡视西沙群岛,勘察测绘岛屿地理,绘制地图,并建立“筹办西沙岛办事处”,以“保海权”。(66)
3.2 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在中国南海的积极有效维权
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作为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在亚洲最早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民族意识不断增强。1933年法国侵占我国南沙群岛挑起“九小岛事件”后,民国政府因地制宜,在国际社会没有相应国际法维护南海主权的情况下,采取积极行动维权。尤其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盟军成员和战胜国,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收复被占领土,捍卫主权。中国南海及其附属岛屿归属中国,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确定的国际秩序下,中国作为战胜国依据国际法采取的积极有效的维权措施。
第一,紧紧抓住对中国固有海域及岛屿的命名权。民国政府先后于1935年1月和1947年11月由中国水路地图审查委员会和民国政府内政部方域司分别审核、颁布《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和《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67)将我国中国南海各群岛领土的全部定名公布于世,通过“名从主人”的地名学原则维权,当时没有任何国家提出异议。
第二,民国政府方域司召集中国历史地理学专家,如内政部代表傅角今、方域司科长郑资约、张君然等,经过大量的地理学考证与研究,以及实地测量,采用地图边界符号(断续线)表示中国南海所属岛屿所有权。经过1935年4月海军测量局绘制出版的《中国南海各岛屿图》,1936年公开发行的《中华建设新图》,1947年上半年出版“国防部测量、方域司”编绘的《南海诸岛位置图》,直至1948年将“南海断续国界线”(11条断续线)收入民国政府公开发行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68)向国际社会正式伸张南海主权,并得到广泛承认,也成为“二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成功收复被侵略领土的重要事实与法理见证。
第三,加强对南海诸岛的实际占领与经济开发。“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划归当时属于日本殖民地的台湾高雄市管辖。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归还中国,南海诸岛也应从日军占领下重归中国。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后,台湾气象局派员乘机动帆船“成田”号巡视南海诸岛,并向政府提交巡视报告。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决定将南海诸岛划归广东省管辖。1946年9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国防部”、“外交部”、“海军总司令部”研究决定,由“海军总司令部”协助广东省政府接收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并由海军派兵进驻各岛。经过周密准备,由林遵上校指挥,由“太平”号、“永兴”号、“中建”号、“中业”号等4舰组成进驻西南沙群岛舰队,中国海军分别于11月24日和12月12日到达西沙和南沙群岛,勒石铭记,举行接收仪式,派遣驻岛官兵,宣誓主权。1947年4月再次派舰队进驻永兴,为驻守官兵运送补给;根据国家气象组织意见,在岛上开展气象观测,建立航标灯桩;同时,随舰组织各专业单位涉及植物、地质、海洋、地磁、资源、铁路、码头工程等机构人员对西沙群岛自然条件、资源展开调查,并有华侨周苗福等随舰考察以考虑开发、建设西沙事宜。同年5月8日,“海军总司令部”又调“中业”号装运物资补给南沙群岛,直至1950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原驻西沙、南沙群岛的国民党海军军官撤往台湾,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驻防官兵所取代。(69)
第四、设置西沙、南沙专门行政管理机构,管理经营常态化。1947年5月,民国“行政院”据广东省政府意见,命令海军暂行代管各群岛行政工作。“海军总司令部”发布命令,设置“海军总司令部西沙群岛管理处”,张君然为海军西沙群岛管理处主任。在广州设置黄埔巡防处,“永兴”舰广州驻防,配合巡视中国南海。1948年3月成功实现永兴岛(西沙群岛)和太平岛(南沙群岛)换防,对该地管理常态化。
第五、坚守西沙、南沙群岛,抗议法国入侵。1947年1月18日,法国军舰“东京人”号驶抵永兴岛,强行登陆,要求驻守人员撤退,为我方严词拒绝,并令法军立即退走,全岛进入紧急备战状态。中国守军的坚决态度迫使法舰离岛,在附近海面停留24小时后撤离,后在属于西沙之珊瑚岛登陆。之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约见法国驻华大使梅理霭,申明西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质询法国海军在西沙活动之合法性。1月21日,“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谴责法国侵占我珊瑚岛。1月28日,“外交部”照会法国大使,抗议法军入侵珊瑚岛。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捍卫中国南海主权的史实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虽历经冷战爆发,国际社会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垒,中国政府始终以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身份作为进入国际社会的主体,坚守当时国际法基本原则,积极维护中国南海及其附属岛屿主权。对于中国南海作为中国传统海洋国土的维护,主要体现在:
其一,对于“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对太平洋地区领土与岛屿归属问题的清算,即所谓《旧金山和约》中,美英日等国对于我国南海诸岛归属私相授受表示不予承认并发表严正声明。就其中故意规定日本放弃对南威岛和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而亦不提归还主权问题,(70)我国政府明确指出:“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虽曾一度沦陷,但日本投降后,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接收。”并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威岛和西沙群岛之不可侵犯的主权,不论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有无规定及如何规定,均不受任何影响。”(71)这一声明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南海及其附属岛屿主权归属之基本观点。多年以后,才有中国南海周边国家,如菲律宾、南越、越南刚刚摆脱西方殖民地控制,建立独立国家,并继承其原宗主国的主张,宣称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这与我国历史上对中国南海及其附属岛屿的占有、管辖以及现代国家转型时期对中国南海及其附属岛屿现代国际法条件下的主权宣示与实际占领,无论是从历史性水域还是实际占领之迹象,都不可同日而语。
其二,对于中华民国在“二战”胜利后对中国南海及其附属岛屿主权宣誓的重要成果——南海传统断续国界线,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各种地图中,都继续标出这条断续线。195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去掉北部湾内的两条,改为九段线。即使是在1984年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后,仍保留我国一贯以来对中国南海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宣示。1992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更以国内法的形式将“九段线”所确定的中国南海海疆范围予以肯定与昭示。(72)“南海断续线”在中国地图中明确标示这一事实至今已60多年,其本身已成为中国政府维护我国南海海疆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历史事实与有力证据。
其三,对于他国侵犯我国南海及其附属岛屿的行为坚决予以有力回击。除了对任何一次其他国家对我国南海领土的侵略行为提出抗议外,1974年,针对当时南越政府将西沙群岛全部划归南越版图,侵占我领海,撞沉我渔船、侵袭我永乐群岛,中国展开西沙保卫战,最终夺回赤瓜礁,取得西沙保卫战的胜利。1988年,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第十四届大会,通过《全球海平面联测计划》,决定在我国南沙群岛建立第74号海洋监测站,并把任务交给中国。我国派科考船勘察南沙诸岛,并于1988年1月31日在永暑礁建立海洋监测站,越南当局出动军舰破坏、捣毁我检测设施,遂爆发“3·14海战”,经过海上激战,我人民解放军重新控制南沙群岛8个岛礁,取得南沙海战的胜利。(73)直到2012年我国南海行政机构“三沙市”的建立,均反映了我国政府捍卫中国南海及其附属岛屿主权的坚定立场。
四、结论
从“中国南海”地理概念的产生与演变可知,中国作为较早形成的中央集权封建皇权国家,很早就有海洋疆域的国家意识,并在以南海为媒介的中外交流与社会经济发展中,不断深化,积极践履。经历代政府与民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经营,至明清时期,“中国南海”已经基本确立其具体范围,并得到当时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中国政府以军事、政治管辖的方式进行传统海洋疆土的维系,古往今来,从未间断。
1840年后,在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南海面临列强殖民侵略、瓜分危机,当时的晚清、民国政府顺应来自西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理念(现代主权国家概念),依据当时国际法基本原则,积极维护“中国南海”及其附属岛屿作为中国传统海洋国土的主权,并取得一定效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南海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并积极维护至今。
1948年中华民国政府内政部方域司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的中国版图中“中国南海断续线”的标示,是在当时国际法对各国海权未形成统一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以地图测绘标示的形式维护主权的有力作为。这一“断续线”的划出,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是中国传统海疆维护向现代国家海疆维护的成功转型,既是对“中国南海”传统海疆范畴的考订与昭示,也是在遵循当时国际法前提下的主权宣誓,更是依托当时国际法维权的具体手段。该线具有中国传统海疆线的地位。即使在1982年颁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法新条件下,该线作为中国在中国南海的历史性权利线,也理应受到《公约》相关条款的尊重与保护。这是因为《公约》在规定新的海洋法律秩序,赋予各国新的海洋权益的同时,并不完全打破既有海洋法律秩序,不损害各国既得的海洋权利。(74)如《公约》第15条“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领海界限的划定”规定:“如果两国海岸相向或相邻,两国中任何一国在彼此没有相反协议的情况下,均无权将其领海伸延至一条其每一点都同测算两国中每一国领海宽度的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的中间线以外。但如因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而有必要按照与上述规定不同的方法划定两国领海的界限,则不适用上述规定”,尤见《公约》对历史性权利的极大尊重。国际法从诞生到发展成熟的内在逻辑演变,应对“二战”后我国就中国南海及其附属岛屿主权伸张作为予以肯定。因此,民国政府基于中国历史上对中国南海开发、管理、控制的事实所划定的“南海断续国界线”,其划界初衷是确定中国南海海疆并维护主权,演变到今天,已成为中国在中国南海享有历史性权利的具体范畴。该线在中国地图上的长期标示,本身也成为证明我国在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的重要依据,也是我国与南海周边诸声索国就南海问题磋商与谈判的关键性法理支撑。
注释:
①[日本]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该作者指出:在历史上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中形成的。
②(唐)徐坚著:《初学记》卷六,第6页,蕴石斋丛书。
③(南朝、宋)谢灵运著:《武帝诔》,见(清)严可均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33,第2618页,中华书局,1965年。
④据韩振华先生考证,十世纪时,阿拉伯人马素乌地《黄金草原》一书指出,从西向东航行须经七海,即波斯海、阿拉伯海、哈儿干海(今孟加拉湾),古逻海(今马来半岛东部海洋以及安达曼海),军突弄海(昆仑洋,即中外学者考证为今越南南部海域昆仑岛附近海域),占婆海(旧称占婆洋,古代越南南部占婆国近海),涨海(Cankhay)。阿拉伯语Cankhay正是中国语“涨海”的译音。之后,阿拉伯船长莫族《印度珍异记》则直接将此海描述为“中国之海”。
⑤[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交广印度两道考》下卷,《海道考》,中华书局,1955年9月版,第90页。
⑥司徒尚纪著:《中国南海海洋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⑦《元史》卷163,《史弼传》。又见[英]V.珀塞尔著,姚楠、董湘君译:《东南亚华人》,见《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
⑧韩振华:“元代‘四海测验’中的中国疆宇之南海”,元朝这次测量27点都比较精确,绝大多数测点结果与现在纬度差值在1°以下。可见当时我国先进的海洋地理测量技术下,对国家海洋版图界定的科学性。见《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7页,第98-102页。
⑨陈佳荣:《〈大德南海志〉中的东南亚地名考释》,http://www.docin.com/p-17170912.html.
⑩转引自韩振华:“七洲洋考”,《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页。
(11)(清)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下卷《四海总图》,台湾学生书局,《中国史学丛书》续编,第35种,1984年再版,第162、163页。此书作为清朝前期“防戌、经商必用之书”,多为海军官员“出大洋,歼海寇”所籍。
(12)《洋防说略》。
(13)(清)郭嵩焘著:《使西记程》。
(14)陈佳荣:《南洋新考》,http://www.world10k.com/blog/pdf/351-363.pdf.
(15)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帙。
(16)(清)廖廷相、杨士骧攒著:《广东全省总图说》,精抄本第一本,清光绪15年(1889年),南州书楼本。
(17)韩振华:“十六世纪前期葡萄牙记载上有关西沙群岛归属中国的几条资料考证”,韩振华编:《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6、168页。
(18)Reed J.W.,King J.W.,Main Route to China.China Sea Directory.London:The Admiralty,Hydrographic Office,1868。其中可见,英国以海南渔民对岛屿的俗称命名岛屿。如现在的景洪岛,即海南渔民俗称“秤钩”岛,此书记载为“Sin Cowe”,即“辛科威”岛,正是以海南渔民俗称为词源的;又如现之鸿庥岛,音译为“Namyit”,正是海南渔民所称的“南乙岛”。类似的南海诸岛命名有5-6个,足见英国殖民者以当时国际法原则对“中国南海”及其洋面的岛屿所属有清醒的认识与判断。
(19)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
(20)参见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92-594页。
(21)郭嵩焘著:《使西纪程》上卷,第7页;张德彝:“随使日记”,参见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第126页。
(22)参见外国古地图:《Malay Archipelago or East India Islands》J&F.Tallis,from the Illustrated Atlas of the World,1851; 《East India Islands》William Darton.c 1812,http://www.nansha.co/maps/1/ancient_maps_pracel.html.
(23)(新)尼古拉斯·凯琳主编:《剑桥东南亚史》,第67页,地图2.1:东南亚海岛国家(1880—1930)和第82页,地图2.2:东南亚大陆国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4)陈寿彭著:《南洋与东南洋群岛志略》,正中书局,1945年版(沪本),第20页。
(25)(清)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上卷,第7页。台湾学生书局,《中国史学丛书》续编,第35种,第93页。又见(清)王之春著:《清朝柔远记》卷二十,《沿海形势略》,中华书局,2000年4月版,第397页。
(26)黄月波主编:《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90页。茶古社汉文名“万注”,在今越南芒街以南一带。
(27)(明)黄衷著:《海语》卷三,昆仑山。《中国史学丛书》续编35,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34页。
(28)(明)黄衷著:《海语》卷三,昆仑山。《中国史学丛书》续编35,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34页。
(29)(清)嵇璜、曹仁虎、戴衢亨著:《皇朝通典》卷98,边防二,港口,柬埔寨,广南条,第46-47页;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鸿宝书局石印本。
(30)李金明:“越南黄沙、长沙非中国西沙南沙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
(31)《郑昭贡使入朝中国纪行诗译注》,自姚枏,许鈺编译:《古代南洋史地丛考》,香港商务印书馆,1958年8月第1版,第83、89、90页。
(32)(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中华书局版,2000年版,第176—178页。
(33)据考证,七洲洋之南的昆仑,又称昆屯,也即《新唐书》卷43(下)贾耽《广州通海夷道》中的军突弄山,自古以来为南洋往来必经之路。明朝费信著《星槎胜览》记载:“其山节然瀛海中,与占城与东西竺鼎峙相望,山高而方,山盘广远,海人名曰昆仑洋,凡往西洋泛舶,必待顺风,七昼夜可过。”俗云:“上怕七洲,吓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岛夷志略》中昆仑“与占城、东西竺鼎峙而相望”,昆仑山所在昆仑洋作为一片群岛所在,是七洲洋南下西洋后的重要航海地标,也是中外海域分界标志。
(34)姚枏,许鈺编译:《古代南洋史地丛考》,香港商务印书馆,1958年8月,第1版,第83、89、90页。
(35)(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卷3,外国门下,航海外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6页。
(36)(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赵汝适序,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页。
(37)(元)王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28页。另见(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卷3,外国门下,航海外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7页。
(38)中国史籍中,中国南海之“竺屿”(竹屿)分别有东西竹:《顺风相送》中福建赴西洋暹罗、马六甲、旧港必经岛屿,见《郑和航海图》48图;同样这一航线,仍有3处竹屿,见《郑和航海图》44、45与47,向达先生考证三者分别在今昆仑岛附近、暹罗港口、苏门答腊岛南端都鲁把旺外。见向达校注:《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页。同时,这些岛屿作为航标在航海针路中频繁出现。此外,东洋航线泉州往文莱一线,仍有竹山、竹篙屿(在牛嘴吼与宿务之间,即今菲律宾的cebu)。见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2、162页。
(39)(元)王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8页。
(40)《宋史·外国传》卷490,天竺国。“天竺国,旧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复曰婆罗门。”
(41)《宋史·外国传》卷489,注辇国。
(42)韩振华著:《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9、94页。
(43)(元)王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27页。
(44)(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6页。
(45)向达校注:《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2006年版,图43、44,又见第18页。又见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之甲,第70页。
(46)(明)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録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页。据韩振华先生考证,时至今日,在今纳土纳群岛东南仍有一小岛名叫“Soebi”,即沙吴皮的对音。东蛇龙山,则是马来语“Tuna”(泥蛇之意)的译音,也是今纳土纳群岛(Natuna)的词根。罗帏山也即马来语“Pulan Laut”的对音,在今natuna群岛北部的“北natuna岛”,今翻译为拉乌特岛。见韩振华著:《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47)韩振华著:《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101页。
(48)J.Crawfurd,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Ⅱ p.457 seqq,转引自(元)王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5页。
(49)Steiger,history of the Far East,1936,pp.202、203,见[英]V.珀塞尔著,姚楠、董湘君译:“东南亚华人”,《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
(50)(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经谢方先生在此书中的点较考证,东洋针路所涉海域包括雁塘,今吕宋岛西北坎当(condon);笔架山:今吕宋岛北部海外八部延群岛之一;傍佳施兰,今吕宋岛西部;玳瑁湾,今菲律宾吕宋岛仁牙因湾附近洋面;磨叶洋,即麻逸洋,今菲律宾民都洛岛西部洋面;巴荖圆,今菲律宾巴拉望岛;罗葡山,今菲律宾巴拉望岛南部巴拉巴克岛,直至位居加里曼丹岛之文莱附近海域。所谓“更”是我国古代航海航程的计算单位,每更约水程60里(2里=1公里)。
(51)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2006年版,乙:第108页,甲:第27、28页。
(52)明代福建航海家绘制的彩色绢帛航海图,现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绘制时间大约在明嘉靖朝或更早,明末为英国人收藏,2008年重新发现。参见刘义杰博客:http://blog.sina.com.cn/laoliu197703.
(53)陈寿彭著:《南洋与东南洋群岛志略》,正中书局,1945年版(沪本),第3页。
(54)曾功亮:《武经总要》卷二十一,《广南东路》泉州府志。
(55)关于中越传统海上分界,中越双方已有共识。[越南]高春育《大南一统志》第一辑,第五卷第23页,维新三年版(1908年),(转见昭和十六年(1941年)影印本,日本泷田纸器印刷株式会社印)载:大占屿:“一名尖笔锋,古名占不劳(俗名劬劳占),在延福县东海中,古名卧龙屿……本国与外国越海者以此为准,往运皆停泊取薪水”,据我国学者多方考证,大占屿即哩山岛,今越南沿海广东群岛中的主岛,据此分析,当时越南与他国航海者以此岛为越南海(外罗洋)与中国海分界标准。
(56)《明太祖实录》155卷,页2下。
(57)《明太宗永乐实录》卷182,页9上。
(58)(清)黄任、郭赓武著:《泉州府志》卷五十六,国朝武迹,第43、44页。同治九年本(1870年),另见(清)吴堂著:《同安县志》,光绪十一年(1885年),据嘉庆三年(1798)本重刻,卷二十一,武功,第72页。
(59)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总督广东广西等处杨应琚题本》。
(60)韩振华:“宋端宗与七洲洋”,《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6页。
(61)(清)明谊重修:《琼州府志》卷十八,海防,第5页,道光辛丑(1841年)本,又见钟元棣、邢定伦著:《崖州志》卷十二,海防志一,环海水道,第178页,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版。
(62)(清)徐家干著:《洋防说略》卷上,广东海道,光绪十三年(1887年)刻本。
(63)(清)廖廷相、杨士骧攒著:《广东全省总图说》,精抄本第一本,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南州书楼本。
(64)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光绪九年四月十八日。
(65)《清季外交史料》第3册,清宣统一年三月二十六日,第25页;再见于陈天赐:《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之《东沙岛成案汇编》部分,1928年版,商务印书馆,第59页。
(66)陈天赐:《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之《西沙岛成案汇编》部分,1928年版,商务印书馆,第3-23页。
(67)傅角今主编、郑资约编著:《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83-94页。又见佚名:《海军进驻后之南海诸岛》,附录之1-12页。
(68)傅角今主编、郑资约编著:《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83-94页。又见佚名:《海军进驻后之南海诸岛》,附录之1-12页。
(69)张君然:“抗战胜利后我国海军进驻南海诸岛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第93页。
(70)《国际条约集》(1950—1952),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335页。
(7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二集,世界时事出版社,1958年版,第30—32页。
(72)姜丽、李令华:“南海传统九段线与海洋划界问题”,《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第6卷,2008年版,第7页。
(73)黄胜有:“回顾中国南海上的两次海战”,中国网:2011年11月3日。
(74)赵建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在南海的既得利益”,《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