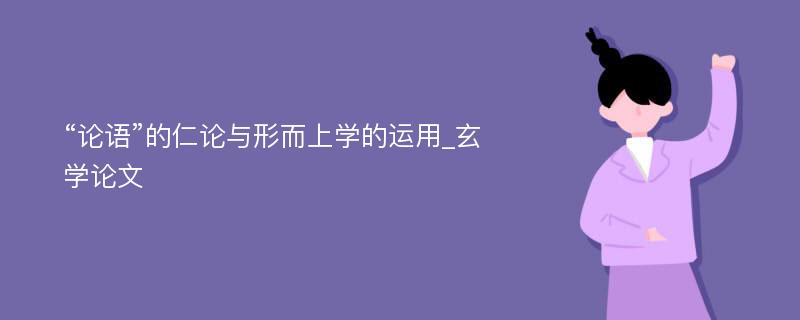
《论语义疏》仁论与玄学体用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玄学论文,体用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14)04-0049-07 魏晋时期,玄学渐兴渐盛,经学渐衰渐微;至南北朝,玄学与经学一进一退之势趋于缓解,折中玄儒在学者中盛行。从学术生涯及生平著作看,皇侃是以经学家闻名的;青年时受梁武帝赏识,被委以国子助教一职,教授五经之学,《论语义疏》盖其授课的讲义。《论语义疏》亡佚于南宋时期,所幸日本流传不废,乾隆年间得以重新传回中国,成为现存六朝义疏体著作唯一一部完帙,在《论语》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论语》本为儒家经典,然皇疏多引王弼、郭象等人之说并加以发挥,玄学倾向引人注目,玄儒关系问题遂成为讨论的热点,但至今仍存争议。一些学者肯定皇侃《论语义疏》的儒家主旨,认为玄学的影响是次要的、无碍大体①。然而,如果我们推原下去,便会看出,皇侃经学理论体系实建立在以“无”为本的玄学本体论的哲学基础之上②;由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皇侃在玄儒关系上所作的弥缝与融合。仁是儒学的核心范畴,以《论语义疏》仁论为考察视角,可从哲学层面窥测玄学对皇侃经学思想的实质性的影响。下面的研究表明,皇侃会通玄儒,在仁的内涵上以儒家“仁者爱人”的传统观念为价值取向;在仁性主张上则以玄学本体论及性分说为哲学依据,并将行仁为用、仁性为体的玄学体用观融入、贯彻在其仁论之中。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玄学体用观主要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即以玄道的“无”、“自然”等为最高之本体;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指体与用二重的逻辑结构:以体为本,以用为末,讲求崇本息末——这是肇始并流行于魏晋玄学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方法。考虑到玄学与理学在学术思想上的内在关联,以《论语》学另一经典著作朱熹的《论语集注》作为参照,对于某些问题的辨析讨论当不无裨益。 一、仁、行仁及仁性 对于什么是仁,孔子曾有一简单明了的回答:仁者爱人;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则是由仁达圣的追求与理想。《论语义疏》秉承此义: 诚爱无私,仁之理也。③ 仁以忧世忘己身为用。④ 仁者,施惠之谓也。⑤ 仁者,周穷济急之谓也。⑥ 仁者,恻隐济众。⑦ 仁者,博施济众也。⑧ 皇疏以“诚爱无私”、“忧世忘己身”、“施惠”、“周穷济急”、“恻隐济众”、“博施济众”等为仁的基本内涵,坚持了儒家“仁者爱人”的传统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皇侃大量汲取了王弼、郭象等玄学家的思想,但在有关仁的价值取向上,又表现出与玄学家的分歧,其中尤以与郭象的分歧最为突出。 言先能内自修己,而外安百姓,此事为大难也。尧、舜之圣,犹患此事为难,故云“病诸”也。卫瓘云:“此难事,而子路狭掠之,再云‘如斯而已乎’,故云:过此则尧、舜所病也。”郭象云:“夫君子者不能索足,故修己者索己。故修己者仅可以内敬其身,外安同己之人耳,岂足安百姓哉?百姓百品,万国殊风,以不治治之,乃得其极。若欲修己以治之,虽尧、舜必病,况君子乎?今见尧、舜非修之也,万物自无为而治,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云行雨施而已,故能夷畅条达,曲成不遗而无病也。”⑨ 郭象反对“修己以安百姓”的做法。其所谓“虽尧、舜必病,况君子乎”,是说若通过“内自修己”的途径去实现“外安百姓”的目标,即使尧舜这样的圣人也是行不通的,更不用说一般的贤人君子了。皇侃不同意这一观点,指出“内自修己,而外安百姓”虽然是圣人都不易做到的事情,“此事为大难也”,但却始终是儒家的理想与目标。这与宋儒的见解不谋而合。朱子注云:“盖圣人之心无穷,世虽极治,然岂能必知四海之内,果无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尧舜犹以安百姓为病。若曰吾治已足,则非所以为圣人矣。”⑩朱注之义与皇疏一致,两人的训解均与“恻隐济众”之义契合,体现了儒家仁的精神与立场。 仁的内涵确定之后,接下去便是行仁的问题。皇侃沿袭何晏“仁为行盛”之说,并将“行盛”之“行”解释为“五行”之“行”,从而将行仁与五行联结起来。《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章,何晏注云“仁者,行之盛也”,皇侃疏曰:“仁义礼智信五者,并是人之行,而仁居五者之首,主生,故曰‘行盛’也。”(11)而其中所谓“仁居五者之首”,乃是“就五行而论,则木为仁,火为礼,金为义,水为信,土为智”(12)。皇侃先将“五常”比附“五行”,再将“五行”之“行”进一步引申为“并是人之行”。我们知道,将阴阳五行作为人事依据,本是汉学的基本特征之一,《论语义疏》显然继承了这一思想: 谓文质、三统及五行,相次各有势数也。如太昊木德,神农火德,黄帝土德,少昊金德,颛顼水德,周而复始,其势运相变生也。(13) 侃案:五方正色,青、赤、白、黑、黄。五方间色,绿为青之间,红为赤之间,碧为白之间,紫为黑之间,缁为黄之间也,故不用红紫,言是间色也。所以为间者,颖子严云:东方木,木色青,木克于土……火克金……金克木……水克火……土克水。(14) 这里需要注意,以上两例的五行次序有所不同,前一例,“运势相变生”取木、火、土、金、水的次序,同于五行相生说;后一例“五方间色”中木、土、水、火、金相克之次,则又与五行相胜说一致。可见,皇侃深谙五行之说,对相生相克并有取用。 仁既是五行之首,行仁便在“人之行”中处于中心地位,故《论语义疏》又有“仁是万行之首”之说(15)。那么,人何以会行仁,行仁的根源是什么呢? “仁者,人之性也”(16),皇侃认为行仁的根源便在于仁性。皇侃接受玄学本体论,以“无”、“自然”等为最高范畴,并结合性分说,发展出他的自然气性论。这决定了其关于仁性的看法。 性者,人所禀以生也……人俱禀天地之气以生,虽复厚薄有殊,而同是禀气……然性无善恶,而有浓薄……性既是全生而有,未涉乎用,非唯不可名为恶,亦不可目为善,故性无善恶也。(17) 这是一种自然气性论的主张。自然意味着“性无善恶”,气性则意味着“厚薄有殊”。接着,皇侃承续郭象的性分说,指出仁性的分量,每人先天所禀,却又各不相同: 仁者,人之性也。性有厚薄,故体足者难耳。巧言令色之人,于仁性为少,非为都无其分也,故曰“鲜矣有仁”。(18) “性有厚薄”,进而有分量多少的不同,这仍是就气性而言的。若依程朱之见,仁性乃是理一,无可分割,岂有分量多少可言?事实上,在皇侃与程朱不同哲学体系中,“仁”的地位是大为不同的。试比较《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章双方的训解。《论语义疏》云: 仁者,施惠之谓也。施惠于事宜急,故当倚之而行也。仁劣于德,倚减于据,故随事而配之。(19) 《论语集注》云: 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则存养之熟,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20) 皇侃曾言仁“是德之盛也”(21),何以此处又言“仁劣于德”?原因便在于,“仁劣于德”中的“德”乃指全德;也就是说,在皇侃眼中,仁虽为“德之盛”者,却并非德之全者。而在程朱那里,由于仁已由“五行之首”上升为天理,相应地,仁也就由“劣于(全)德”变成“心德之全”了。 二、行仁为用,仁性为体 行仁既以仁性为根据,那么两者之间又具体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陆特进曰:“此章极辨智仁之分也,凡分为三段。自‘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为第一,明智仁之性。又‘智者动,仁者静’为第二,明智仁之用。先既有性,性必有用也。又‘智者乐,仁者寿’为第三,明智仁之功。巳有用,用宜有功也。”今第一明智仁之性……第二明用也……第三明功也。(22) 仁有二个层面,较高的层面是“仁之性”,较低的层面是“仁之用”与“仁之功”,也就是仁之行;“先既有性,性必有用”,两者构成体用关系,即以性为体,以行为用。宋儒的体用观同样区分仁的性体行用: 为仁,犹曰行仁……程子曰:“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曰:“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23) 在仁性为体、行仁为用的二重逻辑结构上,程朱的体用观与皇侃的体用观并无不同。 但与讲求“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理学体用观相比,玄学体用观更为注重体用之间的本末关系。玄学极力倡导“崇本举末”、“崇本息末”,即在于“本末即谓体用”的体用观(24)。《论语·公冶长》“汝与回也孰愈”,皇侃引缪播之言云:“学末尚名者多,顾实者寡。回则崇本弃末,赐也未能忘名。”(25)其中“实”与“名”即为体用、本末关系,依玄学“崇本息末”的原则,颜回“崇本弃末”,故为上;子贡“未能忘名”,故为下。同样,对于仁性与行仁而言,仁性为体,也即仁性为本;行仁为用,也即行仁为末。这样的体用本末关系,意味着后天的行仁如何,取决于先天所具的仁性。 辨行仁之中有不同也。若禀性自仁者,则能安仁也。何以验之?假令行仁获罪,性仁人行之不悔,是“仁者安仁”也。(26) 皇侃认为唯有本性为仁,即“禀性自仁”、“性仁”的人才能真正做到安仁,也就是说,“行仁之中有不同”,归根结底是由仁性的不同决定的。而每个人的性分既然各不相同,那么相应于不同分量的仁性,行仁的完善程度也将有所不同。 此谓贤人已下,不仁之君子也。未能圆足,时有不仁。如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后则一匡天下,九霸诸侯,是长也。(27) 皇侃认为存在仁性未能“圆足”的“不仁之君子”。以管仲为例,皇侃指出管仲虽有“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仁功、仁用,但因仁性“未能圆足”,故有“三归”、“官事不摄”等“不仁”之行。而仁性“未能圆足”的原因又在于其“中人”的人性品级: 管仲中人,宁得圆足?是故虽有仁功,犹不免此失也。(28) 我们再来看朱熹的看法: 愚谓孔子讥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俭,故斥其奢以明其非俭。或又疑其知礼,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礼。盖虽不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于此亦可见矣。(29) 朱子对管仲的评价是功大而“器小”。那么何为“器小”呢?《论语·八佾》“管仲之器小哉”,朱子注云:“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30)朱子言管仲“器小”,是说他“不知圣贤大学之道”、“不能正身修德”,也即后天的功夫不足所致。对比皇侃归因于先天之性未得“圆足”的主张,后天之“器”与先天之“性”间显有本质差别。 再如对子张的评价,《论语义疏》记载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为江熙之说:“堂堂,德宇广也,仁行之极也。难与并仁荫人上也。”(31)一为袁氏之说:“子张容貌难及,但未能体仁也。”(32)江熙称赞子张“仁行之极”;袁氏则认为子张“未能体仁”,言外之意,子张的仁行并非如其堂堂容貌那样“难及”。那么皇侃持何种态度呢?皇侃的看法是,子张“虽容貌堂堂,而仁行浅薄”(33)。显然,皇侃赞同袁氏的意见,且两人的观点恰符合性本行末的体用观:子张“未能体仁”(袁),故而“仁行浅薄”(皇)。 “仁行浅薄”的表现之一便是“利仁”: 智者,谓识昭前境而非性仁者也。利仁者,其见行仁者,若于彼我皆利,则己行之;若于我有损,则便停止。是“智者利仁”也。知仁为美而性不体之,故有利乃行之也。(34) 此君子无定名也。利仁慕为仁者,不能尽体仁,时有不仁一迹也。(35) 与“性仁”不同,“利仁”是“有利乃”行仁,缺乏内在仁性支撑,故滞于用的层面,带有功利色彩。那么,一个人若想提升仁的境界,须凭借何种途径呢?答案是,惟有希冀生而具有仁性;换句话说,为性分所限的人,仅靠后天的努力是难以企及更高境界的,因为“仁是行盛,非中人所能”(36),“仁是行盛,非体仁则不能”(37)。 仁的至高境界,唯有“体仁”者也即天性“极仁”的人(如亚圣颜子)才有可能达到: 唯颜氏之子,体仁无违,其亚圣之目乎?(38) 又一解云:“谓极仁之人也。极仁之人,颜氏是也。”(39) 这里的体仁,很容易使人想到王弼的体无。《世说新语·文学》记载: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 “圣人体无”既关乎理想人格的“圣人”,又关乎本体之“无”,其中之义值得深味。“体无”一词尤为关键,一般解为“对无的体悟或体证”。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何以圣人能够体悟到“无”而常人不能,圣人与常人间到底有何异同?对这一问题,王弼的回答是:“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无情也。”(《三国志·魏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也就是说,在情感上,圣人与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圣人超越常人之处在于“神明”。那么,圣人的“神明”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显然,这种“神明”常人靠后天的努力是无法获得的。如同圣人的“生知”源自于圣人的先天之“性”;作为天赋,圣人的“神明”当同样源自于圣人的先天之“性”。这样看来,“体无”之“体”便与“性”密切相关。性三品说与性分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有广泛影响,而无论性三品说还是性分说,均肯定人性存在先天等级差异。圣人处于人性的最高等级、圣人德合天地以及圣人之性与道相通,这三者实际上是一回事。而“无”即“道”,“道”即“无”,故“圣人体无”也即“圣人体道”,其实也就是“圣人之性与无、道相通”之义。皇疏既称颜子“亚圣”,又言颜子“体仁”,两者相合便是“亚圣体仁”,这与“圣人体无”显然不乏相通之处。不难设想,“体仁”之“体”同样与“性”相关,而这一点恰可从皇侃的疏解中得到印证:“知仁为美而性不体之,故有利乃行之也。”(40)以“性”言“体”,“体”便为“性体”,实即指“性”。皇侃又云:“利仁慕为仁者,不能尽体仁。”(41)显然,“利仁”的反面是“体仁”。将以上两例关于“利仁”的疏解综合起来看,若“性不体之”为“利仁”,那么“性体之”自然便是“体仁”。可见,“体仁”与前文所言的“性仁”、“禀性自仁”乃均就仁性而言。需要指出的是,“体仁”一词并非玄学首创,《易·乾·文言》已有“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之说,孔颖达释“体仁”为“体包仁道”,“体”训为“包含、容纳”之义。然“体仁”在《论语义疏》中具有更为丰富的玄学意蕴,我们或可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解读领会: 其一,“体仁”蕴含仁性圆足之义,也即指体仁者具有先天完满的性分。 仁者,人之性也。性有厚薄,故体足者难耳。巧言令色之人,于仁性为少,非为都无其分也,故曰“鲜矣有仁”。(42) “体足”意即仁性圆足,即指“体仁”。又《论语·雍也》“今也则亡”,皇疏云:“游、夏非体之人,不能庶几,尚有迁有贰”(43),意即子游、子夏由于并非性体圆足,故“尚有迁有贰”。另在关于《论语·雍也》“不迁怒”的疏释中,皇侃认为颜子“体仁”、“不迁怒”,即“好学分满所得之功”,其中所谓“分满”显即性分完满之义。 其二,体仁者“迹”异而“理”同。 孔子评微子、箕子、比干,其迹虽异而同为仁,故云“有三仁焉”。所以然者,仁以忧世忘己身为用,而此三人事迹虽异,俱是为忧世民也,然若易地而处,则三人共互能耳。但若不有去者,则谁保宗祀耶?不有佯狂者,则谁为亲寄耶?不有死者,则谁为亮臣节耶?各尽其所宜,俱为臣法,于教有益,故称仁也。(44) 颜渊无伐善,夷、齐无怨,老子云“少私寡欲”,此皆是仁也。(45) 殷仲堪云:“诚爱无私,仁之理也。”(46) 微子、箕子、比干、颜渊、夷、齐以及老子等人,常被称许为大贤、上贤,或可视作体仁者。微子、箕子和比于“三人事迹虽异”,然“俱是为忧世民”;颜渊“无伐善”,夷、齐“无怨”,以及老子“少私寡欲”,亦均合殷氏所言的“诚爱无私”之理。迹为用、为末,理为体、为本,体仁者迹、用虽有差分,而其理、其体则并无不同。 其三,贤人体仁,圣人体无。孔子为圣乃是公认的看法,即便特重三玄的魏晋名士,也将孔子置于老庄之上,并作圣、贤的区分。王弼的孔子“体无”,老子“未免于有”之说便道出了这一实情。体无者与道相通,“与天地合其德”(47);相形之下,颜子、老子等人虽堪称体仁,但由于“仁劣于(全)德”,故至多被视为大贤、上贤而难以及圣。《世说新语·言语》载有这样一件趣事:“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公问齐由何字,答曰:‘字齐由。’公曰:‘欲何齐邪?’曰:‘齐许由。’‘齐庄何字?’答曰:‘字齐庄。’公曰:‘欲何齐?’曰:‘齐庄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对曰:‘圣人生知,故难企慕。’庾公大喜小儿对。”贤人尚可志慕,圣人则难以企及。同样,体仁与体无间存在无法逾越的贤、圣之界。如果将体仁视为人之极的话,那么体无便意味着超越“人之极”而步入本体的境界。 故王弼云:“庶几慕圣,忽忘财业,而屡空匮也。”又一通云,空,犹虚也。言圣人体寂,而心恒虚无累,故几动即见。而贤人不能体无,故不见几,但庶几慕圣,而心或时而虚,故曰“屡空”。其虚非一,故“屡”名生焉。故颜特进云:“空非回所体,故庶而数得。”故顾欢云:“夫无欲于无欲者,圣人之常也;有欲于无欲者,贤人之分也。二欲同无,故全空以目圣,一有一无,故每虚以称贤。贤人自有观之,则无欲于有欲;自无观之,则有欲于无欲。虚而未尽,非‘屡’如何?”太史叔明申之云:“颜子上贤,体具而敬,则精也。无进退之事,就义上以立‘屡’名。按,其遗仁义,忘礼乐,隳支体,黜聪明,坐忘大通,此亡有之义也。忘有顿尽,非空如何?若以圣人验之,圣人忘忘,大贤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复为未尽。一未一空,故‘屡’名生也焉。”(48) 皇侃的这一大段疏解将圣贤之辨演绎得极为透辟。而所引诸家中,王弼自不必说,顾欢为南齐著名道教学者,太史叔明则“少善老、庄……其三玄尤精解,当世冠绝”(《梁书·太史叔明传》)。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以“无”为本的玄学本体论乃皇侃的立论依据。圣人“体寂”、“体无”、“全空”,故“心”可“恒虚无累”;颜子体仁却“不能体无”,故于行仁,“心”可“终身”“不违”,但于“空”却“其虚非一”,只能“心或时而虚”,终不能突破圣、贤之界。 由于仁在内涵上具有规定性而“未免于有”,因此即便是仁性圆足的体仁者也终究无法达成“恒虚”、“全空”的体无境界。贤圣悬绝的理念直到宋代才被程朱彻底打破。理学将仁性提拔为天理,名教的内涵融入本体之中,所谓“无形而有理”,玄学的“仁性”与“无”、“道”遂统摄到宋儒的“理一”之中,并成为每个人的天赋;在皇侃这里为性分所限的“非中人所能”,到了程朱那里便成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了。 ①参见焦桂美:《南北朝经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08—321页。 ②参见张文修:《皇侃〈论语义疏〉的玄学主旨与汉学佛学影响》,载《燕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③④⑤皇侃:《论语义疏》,见孙钦善、严佐之主编:《儒藏》(精华编)第10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3,535,321页。 ⑥⑦⑧⑨(11)(12)皇侃:《论语义疏》,《儒藏》(精华编)第104册,第496,355,270,479,355,243页。 ⑩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9页。 (13)(14)(15)(16)(17)(18)(19)(21)皇侃:《论语义疏》,《儒藏》(精华编)第104册,第245,381,495,218,515,218,321,520页。 (2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94页。 (22)(25)(26)(27)(28)皇侃:《论语义疏》,《儒藏》(精华编)第104册,第313,287,271,455,266页。 (23)(29)(3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8,67,67页。 (24)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汤用彤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 (31)(32)(33)(34)(35)(36)(37)(38)(39)皇侃:《论语义疏》,《儒藏》(精华编)第104册,第555,554,554,271,455,355,305,295,271页。 (40)(41)(42)(43)(44)(45)(46)(47)皇侃:《论语义疏》,《儒藏》(精华编)第104册,第271,455,218,301,354—355,452,453,507页。 (48)皇侃:《论语义疏》,《儒藏》(精华编)第104册,第405—4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