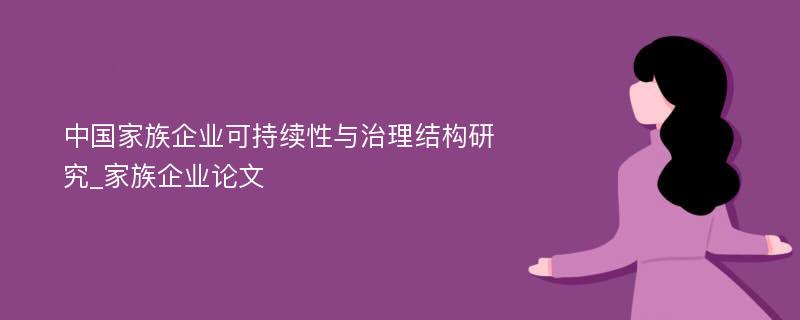
中国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与治理结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性论文,中国论文,治理结构论文,家族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关于家族企业的研究文献主要可分类为对家族企业制度的一般性分析,对海外家族企业的概述及对家族企业具体经营事项的讨论,而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问题却没能得到学术界、政府和社会的足够重视,个中原因或许有多方面:首先,由于历史因素,私营商户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直到今天,对于家族企业,人们的认识仍存在偏差;其次,传统家族企业的组织机构与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有较大的差别,家族企业被认为是保守、封闭、狭隘的经营模式的代表,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不相符,因而没有占据学术研究的中心地位;再次,“富不过三代”的说法为家族企业生命周期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显得“一目了然”,继续挖掘与其关联的课题似无太大必要;最后,就公司治理本身而言,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是公司法规以及对股份持有者及利益持有者权益保障日益完善的过程,遗憾的是,家族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合一的特殊性恰恰使其处于公司治理研究领域的边缘地带。
当前,私营企业在我国的社会地位与经济作用与日俱增,《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2月19日)指出“私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中最具成长性的经济力量”,私营企业的数量、规模都有了迅速扩展,且存活期得到延长,平均寿命已从5.5年上升至7.04年(注:见《2000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中华工商时报》2000年12月12日、2003年2月26、27日)。)。对比世界最古老家族企业排行榜(注:见美国《家族企业》(Family Business)杂志网站。),我国的家族企业显得颇为稚嫩:成立于公元578年的日本古米(Gumi)建筑公司以1400多年的历史位居榜首,排名最末的澳大利亚的布鲁斯德尔(Brucedale)公司距今也已有202年,我国的家族企业却榜上无名。
正如上文所述,与我国家族企业可持续性有关的文献并不多见,来自国外学者的著作近乎空白。由国内学者撰写的文献多为普通理论评述,鲜有针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性的经验研究。基于此,本文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出发,试图找到与家族企业可持续性有显著关系的部分因素。文章的理论框架追寻《内部治理、外部环境与中国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一文提出的扩展的家族企业可持续(ESFB)模型[1],并利用我国上市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与财务数据及相应的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家族企业价值(或托宾Q值)关系不显著;董事会规模与家族企业年龄、股权集中度比率与企业年龄都趋向倒U型相关;依靠增加流通股比率去提高企业的托宾Q值或许会危及家族企业的生存性。结合这些经验结果,对如何提高我国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文章的规范性含义有如下两点,一是业绩良好的上市家族企业可以寻求改变公司治理结构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性;二是业绩较差的上市家族企业则应依靠财务状况的改善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性。
一、理论思考
过去20年来的家族企业标准理论模型——家族、企业交叠模型将家族与家族企业视为相互链接的两个系统,系统之间的重合部分表示家族与家族企业的共同面临的战略管理事宜,例如企业延续、继承、所有者或经理人的生命周期等。但是,家族、企业交叠模型没有显性地揭示家族企业实现企业绩效的途径。从如何决定家族企业绩效的角度看,企业绩效的整合系统模型较家族、企业交叠模型向前迈进了一步[2],因为它给出了家族企业绩效的来源。该模型以资源依托理论为理论基础,视家族企业的家族部门、企业实体与个体成员为模型中的3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组成部分都拥有自我实现的独立体系,各体系之间彼此作用从而产生创造企业优势的资源与能力,最终使家族企业能赢得高于正常水平的租金。
斯塔弗德等(Stafford,Duncan,Danes and Winter)的家族企业可持续性模型(sustainable family business model,SFB)给予家族与家族企业同等程度的重视,家族或家族企业的行为既影响各自业绩,也影响对方的绩效表现[3]。SFB模型也是由家族与家族企业两个子系统组成,它们相互间的重合部分理顺了家族或企业交易中的干扰、资源交换与可持续性的关系。SFB模型较企业绩效的整合系统模型在理论上占优,因为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只在SFB模型中得到清晰反映,且在变量细节上,前者的刻画也更为详尽。例如,其资源与约束变量类似于企业绩效的整合系统模型中的资源与能力变量,SFB模型提及资源与约束应包括的因素,如家族大小、企业结构、对家族企业的劳动供给、经理人的努力,而资源与能力仅是相对模糊的概念。
奥申等(Olson,Zuiker,Danes,Stafford,Heck and Duncan)根据SFB模型给出了经验检验,她们将家族企业可持续性归为家族收入、企业收入、家族预期成就与企业预期成就等4个方面的可持续性[4]。她们的研究表明:(1)家族内部组织结构和就特殊情况的处理方式对总收入和所有者预期成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2)降低家族紧张度,为工作而减少睡眠时间和在繁忙时期雇佣临时工能增加企业收入;(3)认为自己企业成功的所有者睡眠较少,在繁忙阶段雇用临时工的可能性比认为自己企业没有那么成功的所有者要高;(4)企业资产、企业年龄、人事管理、所有者每周工作时间、家族雇员和雇佣临时工都会增加家族和企业两者的成功率。
家族、企业交叠模型、企业绩效的整合系统模型以及SFB模型的共同缺憾在于,它们都仅局限于家族与家族企业范畴,而没有考虑家族与家族企业以外的其他决定因素,例如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与道德环境。疏忽了外部因素,既不符合企业可持续性的内涵,也不能对我国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短暂的原因给予终极解释,但毫无疑问,这些理论为研究中国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作了理论铺垫。
参照道·琼斯公司对公司可持续性的定义(注:该定义系指“把握机会、控制源自经济、环境及社会发展的风险以创造股东长期价值的商业实践”。),我将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诠释为把握机会、控制源自经济、环境及社会发展的风险以获取家族与企业长期价值的行为及结果。这一概念应涵盖家族价值与企业价值——家族意志力、家族企业的经营绩效与存续期——的可持续性。研究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就是要探究如何实现家族与企业的价值在长期中延续。家族价值与企业价值并非等价概念,前者体现家族主观上的意志或判断(如奥申等的家族与企业的预期成就),后者偏重于企业经营的客观结果(如奥申等的家族与企业收入)。
国内许多学者分析认为,要实现可持续性,家族企业必须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并最终成为公众持股公司,原因不外有:家族企业由创业期进入守业期后,为了贯彻企业“做大做强”的策略,为了实现对规模经济效应的有效利用与多样化经营、促进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以及打破企业文化的封闭性,一切都离不开推行企业现代治理结构模式。然而,这些学者似乎都忽略了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底线——无论企业如何演进,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或家族出资者权益受到绝对保障的前提条件不应发生根本性的更改。也就是说,学术界关于家族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诸多论断未必周到地考虑了家族企业以存续为宗旨,尤其夸大了证券市场融资的意义。在全球范围,许多古老的家族企业得以数十代存活下来,与其没有上市交易有重大关系,因为企业不上市有利于家族对股权的掌控,家族能较好地规避股权稀释与企业控制权丧失的风险。事实表明,要获得可持续性,家族企业不一定需要走资产证券化之路,正如欧美许多家族控制的咖啡馆、旅店、手工艺作坊以及其他专业性厂家,它们并没有上市发行股票,也没有寻求多样化发展,但这些企业却往往存活了数个世纪。
家族企业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可谓历经波折、跌宕沉浮,其新的发展机遇不过是改革开放短短20多年来发生的事情。对于新崛起的中国家族企业,人们不愿看到它们重走过去的老路,而是希望其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助推器。实际上,中国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石,没有前者的长期贡献,很难想象后者如何实现经济健康、有效的持久增长。为了寻求促进中国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方法,清楚认识阻碍中国家族企业可持续性的各种原因是非常有必要的。苏琦、李新春提出的扩展的SFB理论模型总括了影响中国家族企业可持续性的内在及外在的两方面原因:内因指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与关系治理决定家族企业的主、客观绩效;外因包含社会、经济与道德环境因素,其对家族企业的主、客观绩效起到促进或制约的作用。由于该文只是作了理论探索,对与家族企业可持续性相关联的各决定因素的影响并没有相应地给出定量分析,所以,用数量方法进行剖析、为家族企业持续发展提供实证证据应成为本项研究的侧重点。
ESFB模型的理论框架可用来指导对中国家族企业可持续性的实证检验。类似于SFB模型,借助计量经济方法,ESFB不仅可以单独分析各子系统(如家族系统、企业系统、社会环境系统或道德系统)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性的影响,而且还可以剖析系统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
二、模型与数据
由上文可知,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可由模型中的内生变量来表达,外生变量则需体现家族系统与企业系统这两类因素。受家族数据可摄取性的限制,本文的研究姑且局限于中国家族企业的企业价值可持续性与企业内部治理的关系,重点是从企业系统角度着手剖析资源与约束变量对可持续性的影响。基于ESFB模型,我建立了围绕企业系统的计量经济模型,该模型由如下5个函数构成:
托宾Q值=F[,1](资金运营率,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比例的平方,流通股比率,流通股比率的平方,企业年龄)(1)
主营业务收入=F[,2](资金运营率,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比例的平方,每股盈利,股东权益,总资产)(2)
企业年龄=F[,3](流通股比率,流通股比率的平方,集中度比率,总资产,集中度比率的平方,董事会规模,董事会规模的平方)(3)
净利润=F[,4](企业年龄,托宾Q值,净资产收益率,净现金流,负债比率)(4)
董事会规模=F[,5](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比例的平方,企业年龄,有最大投票权的股份所占比例)(5)
模型中的内生变量为托宾Q值(公司市值与账面价值之比),主营业务收入、企业年龄(家族企业从创建之日起截止本文数据收集时间)(注:企业年龄在奥申等(2003)文中是外生变量,在这里将其作为内生变量来处理。)、净利润与董事会规模(即董事会人数)。前4个变量属于企业价值变量,它们是家族企业可持续性的替代变量(注:受制于数据缺乏,本文不考虑家族企业可持续性的主观变量。)。注意到董事会规模在不少文献里被设置为模型内生决定因素[5,6],本文也采取了相同作法,除了同时充当自变量的内生变量外,还选用随后的企业系统变量作为模型的自变量,它们包括总资产、集中度比例(企业前3位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和)、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规模的比例)、有最大投票权的股份所占比例(有最大投票权的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负债比率(总资产与总负债之比)、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与净资产之比)、每股盈利(净利润与总股本之比)、资金运营率(运营资金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董事会规模(董事会全体董事人数)、股东权益(所有者权益)、净现金流(财务报表中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减额度)与流通股比率(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等。该联立方程模型使对以下假设的检验成为可能:
H[,1]:独立董事比例与托宾Q值的关系不确定。在本文的数据收集过程中,独立董事身份的确认依据的是上市企业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的信息,加之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启动较为滞后(注:直到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始出台《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我无从得知家族企业中的独立董事是否真的符合学术意义上的“独立”。此外,关于独立董事对企业绩效的作用的讨论在学术界仍未尘埃落定。在意识到独立董事的贡献的同时,一些学者,例如罗森斯坦与怀特(Rosenstein and Wyatt),拜尔德与希克曼(Byrd and Hickman)和约翰与申贝特(John and Senbet)等,都认为独立董事没有能力促进企业价值的提高[7~9]。
H[,2]:资金运营率越高,托宾Q值或主营业务收入越高;负债比率越高,净利润越小。麦克诺非等(McConaughy,Mattbews,and Fialko)的维尔康申符号排序检验(Wilcoxon signed-rank test)证实了与上市非家族企业相比,上市家族企业意味着更高的市场价值、更高的营运效率和更小的资本结构风险[10]。看起来,家族企业好的财务状况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仍需要用更为贴切的计量经济模型去验证。
H[,3]:董事会规模与企业年龄间存在倒U型关系。学术界还甚少研究过董事会规模与企业年龄间的关系,不过,雅尔玛(Yermack)与艾森伯格等曾经得到过相关的结论,他们发现托宾Q值与董事会规模呈倒U型关系[11]。
H[,4]:集中度比率与企业年龄趋向倒U型相关。通常情况下,家族企业股权都会比较集中,控制企业的家族因而能控制经理层并解决好委托-代理问题(注:对已上市的家族企业来说,股权集中至少能使企业短期内免于股权更迭所导致的所有权流失。伯利与米恩斯(Berle and Means)就曾提出股权分散性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见参考文献[12]),该论点在德姆塞茨与列恩(Demsetz and Lehn)处得到了印证(见参考文献[13])。许小年与王燕(Xu and Wang)证明股权集中度显著正地影响企业绩效(见参考文献[14])。不过,德姆塞茨与维拉陇格(Demsetz and Villalonga)发现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间无显著关系(见参考文献[15])。),但股权过于集中又容易造成“一言堂”的局面,使企业因决策失误落败的可能性上升。
H[,5]:流通股比率与企业年龄的关系不确定。我国上市家族企业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流通股本大多仅占总股本的一小部分。上市为家族企业开启了资产重组之路,虽在一定程度上可解决其资金缺口,但家族色彩消退的风险也是同时并存的。如果以流通股份占总股本的比重上升为代价,即使企业能得到超常规的发展,但由于家族控制权渐失乃至企业性质发生更替,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反而会受到威胁。
本文借鉴了台湾大学黄光国给出的解释——由一个或几个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直接控制所有权或经营权的企业称为家族企业(注:许多文献都试图解释什么是家族企业,如当那利(Donnelley)认为,家族企业至少有两代人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家族利益为企业的发展目标;利兹(Litz)与莫里斯等(Morris,Williams,Allen and Avila)认为所有权和管理权都集中于家族的企业便是家族企业(见参考文献[16]~[18])。),从中国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浏览系统(注:版本号1.00,系深圳市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 中获取98家在上海、深圳两地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家族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根据这98家企业的各期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构建了一个面板数据库。此处样本符合上市企业第一大股东或最终控制者是自然人的条件。例如,符合此样本选择标准的上市企业有天通股份(第一、第二大股东为潘广通与潘建清父子);宏智科技(第一大股东为王栋),精伦电子(第一大股东为张学阳)等,它们都属于自然人直接控股的上市家族企业;自然人间接控股的上市企业有健康元(即过去的太太药业——朱保国通过深圳市百业源实业有限公司间接掌控),用友软件(王京文通过其控股的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上海益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及上海优富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掌控)等(注:一些国有企业经过改制之后,由自然人或民营企业直接控股的上市企业也被纳入家族企业范畴。)。
根据上述模型定型与数据,关联理论假设便可得到检验。探测性(exploratory)分析显示,H[,2]、H[,3]、H[,4]等3个假设获得了图示支持(注:篇幅所限,本文未能提供所有图示,欢迎感兴趣的读者来函索取。另外,维尔康申符号排序检验显示大于1的托宾Q值与小于1的托宾Q值不属于同一个统计分布(Z=15.9,prob>│z│=0.00)。),特别是经区分托宾Q值大于1与小于1两种情况之后,即前者代表的企业具有大于零的投资净现值(或业绩好),后者代表的企业具有小于零的投资净现值(或业绩差),H[,1]假设表述为独立董事比例与托宾Q值(>1)呈倒U型关系,而与托宾Q值(<1)呈U型关系似乎更为妥当,当然文章需对此进行严格的计量经济检验。
三、经验结果
探测性图示初步证实了前面提到的4个理论假设,其事实上起到巩固联立方程模型定型选择的作用。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我得到了与期望非常相符的经验结果(注:我的估算用到了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这是因为本文的联立方程模型与奥申等的定型有明显差异:后者每一个方程都包含完全相同的外生变量,只是内生变量有所区别,所以后者采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求解。而我的模型中每个方程使用的外生变量互有差异,且个别内生变量同时也是解释变量,因此3SLS较OLS更为合适。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能展示所有计量经济结果,欢迎感兴趣的读者来函索取。):资金运营率与托宾Q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负债比率与净利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董事会规模与企业年龄间存在不显著的正向关系;集中度比率与企业年龄、独立董事比例与托宾Q值都呈不显著的倒U型关系,流通股比率与企业年龄之间存在U型关系。当加入企业的虚拟变量与上市虚拟变量(企业上市后=1,企业上市前=0)后,董事会规模与企业年龄间在1%的显著性水平倒U型相关。
我还就对应托宾Q值(>1)与托宾Q值(<1)的样本值分别作了计算。当剔除小于1的托宾Q值后,资金运营率、企业年龄与托宾Q值的相关性变得不显著,集中度比率与企业年龄的倒U型关系则得到强化;独立董事比例与托宾Q值(>1)倾向于倒U型相关、与托宾Q值(<1)倾向于U型相关、与主营业务收入则呈显著的倒U型相关。值得一提的是,在托宾Q值取值范围内,该变量与企业年龄的U型关系都不显著,这无疑印证了H[,5]假设。
总之,理论假设H[,1]至H[,5]基本都通过了计量验证,尽管资金运营率与托宾Q值(>1)呈负相关、有最大投票权的股份所占比例与董事会规模呈正相关和理论预期不符,但由于被估参数统计意义不显著,因此,其结果并没有削弱本文联立方程模型的解释力。
四、讨论与结语
中国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长久以来得不到学术界充分的重视,国内外学者深入的理论与经验分析十分匮乏。为填补这一学术空缺,我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性与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令人鼓舞的是,文中的理论假设基本都得到数量确认。上市家族企业的独立董事比例对绩效较好的企业(企业的托宾Q值大于1)的影响被发现为先扬后抑;对绩效较差的企业的影响则正好相反;家族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绩效好或差的家族企业年龄间的关系都呈现倒U型,不过前者的关系更为确定(在1%的显著性水平成立);董事会规模则与绩效好的家族企业的年龄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倒U型相关,与绩效差的家族企业的年龄虽然呈倒U型关系,但统计上并不显著。
除此之外,本文归结了上市家族企业可持续性经营的政策启示:绩效不同的上市家族企业,其可持续性对策应当有所不同。对于托宾Q值大于1的家族企业,要实现有效的可持续性,前文经验结果(注:考虑到联立方程模型可能存在缺失变量,我在主干模型的基础上又额外增加了其他关联解释变量(例如年金支付比率、员工人数、股票市价等),模型的估算结果仍然保持足够的稳健度。) 得出其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以及集中度比例都不应过大,各自较合适的分布区间应在[6,9],[30%,40%]与[40%,60%]左右,意味着业绩好的家族企业可以寻求改变公司治理结构以获取企业长久的可持续性。例如,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未必能增加托宾Q值,但当其比例在[0,40%]区间以内上升时,却对主营业务收入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因此,一些企业(如诺基亚)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绝对多数的做法不一定适合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注意到流通股比率对托宾Q值与企业年龄的作用正好相反,这意味着如果尝试从扩大流通股的比率去增加托宾Q值,则很可能会对企业年龄产生负面作用。换言之,企业可以寻求其他路径(如提高资金运营率)而不是靠增发股票去改善托宾Q值。此外,提高净资产收益率,减少债务比率都有利于增进业绩良好企业的净利润的可持续性。
对于托宾Q值小于1的企业,它们也应谨慎于流通股比率扩大带来的危害,虽然流通股比率平方项的被估参数为正,但企业家族掌控的性质或许已发生了变化;由于统计不显著的缘故,董事会规模与集中度比例的扩大未必能使其自身的可持续性上升。反之,如果实施提高资金运营率与净现金流、缩减负债比率等财务措施,业绩差的企业却很有可能促进托宾Q值、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的可持续性。事实说明我国上市家族企业在提高营运效率,减少财务风险方面大有潜力可挖。再有,企业年龄的增长对托宾Q值小于1的企业也有显著的益处,即存活期的延续能提高业绩较差的企业的自身价值(托宾Q值上升),这与业绩好的家族企业有一定的区别。一个供启发的解释是人们或许对已树立名声的企业有更多的前瞻性展望,企业年龄长潜藏着企业在老化的信息,企业价值的期望值可能会打折扣;而对新兴企业的兴趣会比较多地停留在对企业以往历史的关注,企业年龄越长,企业的可信赖度乃至企业价值的期望值会越高。
值得中国家族企业认真审视的是企业是否应该上市。在中国,含家族企业在内的众多国内企业热衷于上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市资格是一种稀缺资源,少数企业藉此赢得“租金”的快速膨胀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其他企业仿效的样板。容易理解,在当前投机色彩浓重的中国证券市场,如果向公众发行股票能为企业迅速换取远远超出普通商品市场平均回报率的超额利润或能给少数股东(或利益)所有者带来高额利润,这样的“致富”路径就决不会被忽略。问题的关键在于,由此导致的家族财富快速积聚模式对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是否真的有好处尚存在疑问。早期的文献便已得到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融资结构无关的结论,指出股权融资受大型企业、新型企业和希冀依赖增加利润空间获得成长的企业的青睐,但较少地被年老的家族企业和希望保持家族控制的企业关注[19,20];再加上文中的研究结果也发现流通股比率增长对家族企业托宾Q值与年龄的可持续性并没有任何突出的好处,家族企业上市或增加直接融资的比例都隐藏着危机和风险。当然也不能排除某些家族企业股票融资并非出于追求财富效应的冒进行为,但既然流通股比率上升对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裨益不大,这部分家族企业也不妨对企业的融资策略再作重新思考,是否在优化内部治理结构以及改进财务结构投入多些精力,以期达到家族企业更健康、更长久的发展要求。
总而言之,上文所勾勒的诸多变量关系可归纳成两点规范性含义:一是业绩良好的上市家族企业可以透过寻求改变公司治理结构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性;二是业绩较差的上市家族企业应依靠财务状况的改善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性。
最后,本文至少存有两点不足:其一是对上市家族企业进行的实证分析仅限于ESFB模型企业系统的局部,系统其他部分的变量没有参与进模型的估算中来;其二是托宾Q值小于1的企业样本数量比较有限,这对模型估算的精确度来说会有一定的影响。鉴于此,将来的研究工作是需要在本文提出的计量经济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企业系统其他环节以及从属家族系统的定量与定性因素;收集补充非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对包括非上市家族企业在内的家族企业可持续性展开更为全面的实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