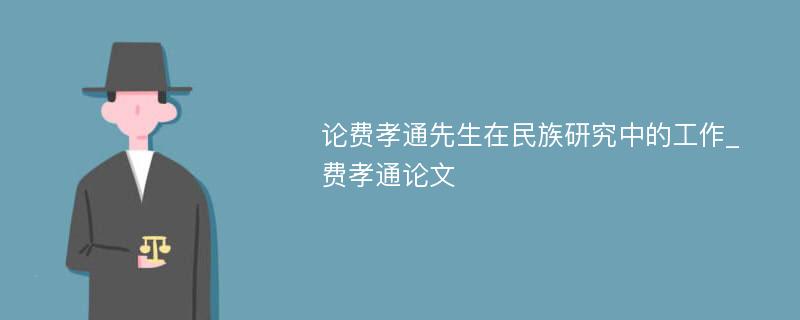
论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中的工作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工作论文,论费孝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费孝通先生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去世时,新华社电讯稿中评价他为“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我国已故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中,被称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者,只有费孝通一人。费先生学术造诣深厚,一生中还积极参与国家、社会活动,做出了特别的贡献。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担任过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可以说是位“参政”人物。他在世时和去世后,人们对他的“学术”和“参政”评价不一,主要的争议在于他究竟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是学者还是政治人物?[1]有人说他“亦政亦学总关情”。[2]费先生的一生,确实与中国政治结缘,有被打成“右派”的折磨,也有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风光。“参政”和他的“学术”确实纠葛在一起,剥离出他的“纯”学问似乎有点难。其实,说白了,就是由于一种“纯”学问价值观才造成对费先生学术评价的困惑。作为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为中国的民族学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正是他在中国民族研究中身体力行的“工作性”的结晶。
一、师承功底深厚 悟得应用真传
费孝通先生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学医,受当时革命思想的影响,于1930年转学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吴文藻(1901-1985)先生,这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起点。吴文藻在1926年就举起“社会学中国化”的大旗,致力于人才培养。费先生在纪念吴文藻老师逝世10周年大会上说吴文藻先生尤其注重培养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树立新风气的人才。[3]
吴文藻是费孝通步入学术殿堂的启蒙老师。费孝通晚年回忆说:
我在燕京三年,大部分时间用来自己读书,并跟吴文藻先生比较接近,我读了他书架上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书。我什么书都想念。这几年的阅读打下了我基本知识的基础。[4]
费孝通跟随吴文藻,不仅打下受用终生的学问基础,还确立了矢志不移的研究方向。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时,为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宏图,开始着手改造脱离中国实际的社会学。“吴老师把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引进到中国来,实际上也就是想吸收人类学的方法,来改造当时的社会学,这对社会学的中国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促进。”[3](P.379)吴文藻先生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引进社会学所阐发的真知灼见,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明确而具体的研究方向,对于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做出了独树一帜的贡献。[5]正是在吴文藻先生倡导、提携下,费孝通进入了人类学、民族学的广阔天地,打下社会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社区调查研究”的坚实基础,受用终生。费先生说:
1930年我转学燕京大学师从吴文藻老师学习社会学。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认识到要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吸收西方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和着重现实的分析是一条比较踏实可行的路子,因此我在1933年升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史禄国老师学习人类学。[6]
1933年费孝通在吴文藻的力荐下,进入清华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专攻人类学。费孝通说:
在吴先生看来首先要学会人类学方法,于是想到了就在燕京大学附近的清华大学里的一位教人类学的史禄国教授。燕京和清华两校是近邻,但是要送我去从史氏学人类学却不是那么方便。吴先生为此先说服了清华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在1933年招收学人类学的研究生,更重要的一关是要说服史氏愿意接受我这个研究生。[7]
费孝通能够进如愿以偿进清华学人类学,也与他的另一位恩师潘光旦先生的帮助分不开。费先生自己说:“我进清华研究院是一生中的一件重要机遇。这个机遇的得来是得益于潘(光旦)老师说服清华社会学和人类学系同意招收人类学的研究生,这在当时是件破例的创举。”[8]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建立于1926年,学校确定社会学与人类学并重的发展原则,将社会学系扩名为社会人类学系。1930年开始增聘教授,续招新生,扩充课程,并按课程的性质分为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类学等。1932年,更名为社会学及人类学系。1933年增设社会研究部。其间曾培养出唯一的一名研究生,即史禄国教授指导的费孝通。[9]
潘光旦(1899-1967)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他于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未及弱冠,博览群书,才华横溢,受到清华国学导师梁启超的赞赏。1922年从清华毕业,因出类拔萃,被保送赴美留学。在留美期间,他主修生物学,研习遗传学、优生学等。1924年获达茂大学学士学位。192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返国。1926年至1934年,他先后在上海地区的政治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东吴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沪江大学等校任教,1934年至1952年,任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于抗日战争中担任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潘光旦学问博洽,被誉为“学贯中西,融会古今,打通文理”,“游刃于自然、人文、社会诸学科之间,而无不运用自如者”。潘光旦达致一种“会通”,形成“新人文思想”,即以“位育”为中心的生物社会学思想。[10]
能够在学业上受到像潘光旦这样的老师青睐,是难得的幸事。对于费孝通来说,还不仅仅于此。他一生的学术,都受到潘先生新人文思想的激励。同时,他的人生道路,也和潘先生如影相随。可以说,潘光旦影响了费孝通一生,费先生在纪念潘先生的文章中说:
1938年我从英伦返国,一到昆明就又被这位老师吸引住了。我不仅在学术上跟上了他的新人文思想,而且在政治上也被他吸引到了同一条道路,归入当时被称为‘民主教授’的一群,还被吸收进民主同盟。从此我们两人就难解难分, 以致成了难师难徒。而且从1946年开始,我们又毗邻而居,朝夕相见,1957年后更是出入相从,形影相依。这种师徒的亲密关系一直到他生命最后一刻,一共有三十多年。这样长期的熏风沐雨,我应当是他的学生中受益最深的一个。[8]
加入民主同盟,成为“民主党派”一员,对费孝通的一生的学术、工作都有重大影响。费孝通与潘光旦的师生之谊,转化成患难之交。费孝通的学术和工作,深深地烙上了潘老师痕迹。
费孝通进入清华大学后,师从俄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Shirokogorov 1887-1939),受到严格的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科班训练。费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1994)。他说: “这项工作足足费了我一年时间。这是我踏进人类学领域的第一步。”“他给我的基础训练一直影响了我一生的学术工作。”[7](P.95,97)费先生晚年回忆说:“我跟史氏学习虽只两年,但受用却是越老越感到深刻。”[7](P.91)1934年费孝通初学人类学时,读过史禄国的一本名叫Ethnos的小册子。在史禄国的理论里,Ethnos是一个形成ethnicunit的过程,包含着一大套丰富的含义。费孝通晚年提出“多元一体论”,从史禄国ethnos的“动”态观中受到启发。”[16]
师从英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B.K.1884-1942),是费孝通成为国际上人类学、民族学知名学者的关键性机遇。
1936年,费孝通考取公费留学英国的资格。吴文藻先生当时到美国参加哈佛三百周年纪念会,见到马林诺斯基,向他介绍推荐已到英国的费孝通,马林诺斯基欣然接受了这位关门弟子。由此,费孝通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马林诺斯基专攻社会人类学二年。
在诸多西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吴文藻先生特别青睐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等人创建的功能学派(Functional School)。他称马林诺斯基“独树一帜”。1938年费孝通先生归国时,马林诺斯基将他尚未发表的《文化论》(What is Culture)赠送给他携带回来。在吴文藻先生支持和指导下,费孝通将《文化论》译成中文,发表于1938年6月出版的《社会学界》第10卷,后又作为《社会学从刊》甲集第一种出版。在英国学习,费孝通掌握了功能论的理论与方法,紧紧地抓住“文化”这个核心。他写了一篇《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1995),指出“把文化看作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人工体系,是马老师所开创的功能学派的基本观点。”[7](P.408)他跟马林诺斯基先学“文化论”,后学“文化动态论”,他以“动”的视角,领会功能论,深得真髓。他在《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1998)一文中,阐释了自己对马氏理论的解读,说:“我同意Kuper把马老师从文化的静态研究到文化动态研究的转向看成是她社会人类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转折。”[11]费先生一生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始终坚持功能学派的“用”字真经,同时又牢牢把握“动”的本质,把功能论用活。这是他做学问成功的一把钥匙。
作为学人,一生中能遇上一位有知遇之恩的名师就是幸运。费孝通得到吴文藻、潘光旦、史禄国、马林诺斯基这四位著名大师的点拨、青睐,可以说是大幸。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费孝通先生从师、敬师,修炼学问的“内功”。这是他成为学问大家的根基。这个根基,还要深深扎根在人类学、民族学深厚的实地调查土壤。费先生不负恩师们的厚爱,遵循老师的教诲,孜孜不倦,联系实际,“行行重行行”,施展“外功”。而新中国民族研究工作,为他提供了爆发内功、激活外功的广阔舞台。这个舞台,正是费先生成就学术功业的“学问社区”。
二、在民族工作中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研究
“用”是功能学派理论方法的立足之本,费孝通在他的学术生涯中,身体力行,别开生面,“用”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片学术新天地。
实地调查,是民族学、人类学这二门应用学科的生命力之所在,是学科发展的基本功。在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史上,功能学派的实地调查理论和方法具有划时代意义,被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 1908—)称之为“马林诺斯基革命”。[12]这个革命,就是对民族学实地调查创新,开拓了“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ao)”式的田野工作新局面。这是民族学实地调查发展过程的一次变革,一个里程碑。可以说,“参与观察”真正把民族学带进了“现代”。费孝通深得马老师的真传,说“马老师在把现代人类学者从书斋里拉进充满着新鲜空气的‘田野’”。[13]
费孝通在师从马老师之前,已做过二次实地调查,一是1935年携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实地研究少数民族,并著《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被吴文藻誉为:“立下了社区研究的基石。”[14]二是1936年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做农村调查,1939年由英国Routledge书局用英文版出版Peasant life in china,1986年译成中文《江村经济》。
费先生携带这二部文稿赴英,作为拜见马老师的“作业”,马林诺斯基立即发现《江村经济》价值,推荐出版,并写了一篇动情的序言。费先生晚年回忆这段历史,声明“我这本《江村经济》是一棵我无心插下的杨柳。马老师在序言对它的评语,我当时不仅没有预料到,甚至没有完全理解,也就是说我在江村调查时并不是有意识地要用此把人类学这门学科推进一步。”[15]马林诺斯基之所以特别看重这位来自东方年轻人的处女作,是有非同寻常的远见卓识。费先生自己解读:
我现在的想法,认为马老师写这篇序的目的,似乎并不完全在评论我这本书,而是想借这篇序吐露他自己心头蓄积着的旧感新愁。我在讲稿里已说出了我这一点体会,不必在此重复。他当时正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形势,心头十分沉重,所以说:“我们的现代文明,目前可能正面临着最终的毁灭”。他介绍我时,强调我是个“年轻爱国者”,他对我能有机会成为一个“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者,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真正“为人类服务”,竟流露出“时感令人嫉妒”,甚至他表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耐烦”,他用了“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来贬责当时的许多人类学者。他还自责“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这些话我现在看来正是一个寄寓和依托在拥有广大殖民地的帝国权力下失去了祖国的学者气愤之词。但是为了表达他的信心,紧接着说:“我认为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为达到这个目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较先进文化的研究。”[13]
费先生看到,他的马老师完成了“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第一步从书斋到田野的转变”这一步,又在探索“从野蛮到文明”的第二步,但“他在一生中并没有实现”。费孝通一生没有停止过田野工作的脚步,同时,作为“本土民族学家”,他迈开了马老师期待的“从野蛮到文明”的第二步,就是“迈向人民的人类学”。[16]
费孝通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真正开始的。其特色就是把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民族工作中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研究。费孝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有建树的大学者,深厚的学术内功无疑是基础,不倦的实践调查外功是门径,此外,积极参与民族工作也是重要条件,或者说是学问的张力。他在这种社会的张力下,自觉调适,游刃有余,成就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学术之途。
费孝通晚年以“从实求知”总结他自己的学术追求,特别出版了一本《从实求知录》。[15]他在与人类学家李亦园交谈中,阐释了“从实求知”的意义,他说:
我昨天送给你的这本书,书名叫《从实求知录》,“从实求知”这四个字表示了我的科学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就是实际生活,就是人民发展生产、提高生活的实践。从“实”当中求到“知”之后,应当再回到人民当中去。[17]
费先生的“从实”,基于平生“志在富民”的人生价值取向。[18]他说:“我选择学习社会学并把了解认识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使命,实现“志在富民”的愿望成为我一生追求的目标。”[19]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要“求知”,就是让科学知识造福于民。“知”从哪里来?从“实”中来。“实”不在书斋,而在社会中。费先生一生都在社会中从实求知。从实,就是不能脱离社会。费孝通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的转变,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在民族工作中执著地开辟自己学术研究的天地,是智者的选择。他在回忆自己民族研究的经历时说: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的研究工作重点转向了民族研究。现在回想起来,这次转向主要是由于当时客观形势的改变。
以我一生的学术经历来说,不同时期曾有不同的重点,有时是民族研究,有时是城乡研究。从个人选择研究对象来看,不仅决定于个人的兴趣,个人所处的客观条件也很重要。[6]
历史机遇给了费先生参与民族工作的条件,这是客观形势,也是他进行民族研究的客观条件。他在积极的民族工作中,密切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费孝通担任全国政协民族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他作为中央访问团副团长访问民族地区。他回顾这段工作时说:
由于我本人学过人类学,所以政府派我参加中央访问团。这对我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首先是我在政治上积极拥护民族平等的根本政策,愿意为此出力,同时我觉得采用直接访问的方法去了解各民族情况,就是我素来提倡的社区研究。因之我积极地接受了这项任务。我在1951年和1952年先后参加西南及中南访问团,并负责领导贵州和广西两个省的实地访问工作。这两年可说是我进行民族研究真正的开始。[6]
1952年—1957年,费孝通但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对筹建和建设这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大学做了许多工作。1956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是中国一项重大的民族工作,也是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空前创举。费先生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一使他兴奋的工作中,负责筹备和组织。然而,当他正在云南省准备进入实地调查时,却刮起了“反右”风暴。1957年,他被召回京,不久便被打成“右派”,被迫停止社会调查工作。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他受到猛烈冲击,直到1980年,才被公开改正了政治地位,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从此开始,费孝通称自己“获得了学术上的第二次生命”。他说:
合计起来,若从1935年瑶族调查作为我学术生命的开始,至今已超过60年,其中由于政治原因丢掉了23年,真正把时间主要花在学术工作上的至目前为止约30多年。我在第二次生命中,尽力想一天当两天用,把丢掉的时间捞回来,这个愿望固然不坏,能否实现,还得看天命。在我得到学术上的第二次生命时,正值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国民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各方面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身逢盛世,使我的学术工作又发生了一次新的定向。起初我还打算用我这第二次生命继续把民族研究做下去。[6]
1978年,费孝通由中央民族学院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任副所长。他在有关的会议上就少数民族研究计划做出报告和说明。他想把民族调查研究继续下去。然而,客观形势使他身不由己。自1980年以后,费先生时来运转,仕途亨通,担任过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尽管工作繁忙,他依旧保持学者本色,以学术为己任。1979年起任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1982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2年一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名誉所长,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他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振兴做出的努力和功绩,已是有口皆碑。在新的“客观形势”下,他把社会工作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把自己研究的方向,从社区研究转向“小城镇研究”,继而扩展到“区域研究”。而对于民族研究,他仍然是“旧情未衰,还是恋恋不舍”。[6]特别是在国际学术讲坛上,他堪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首席发言人”。
1978年11月,费孝通出席联合国大学在日本京都召开的东亚学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做了题为“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一些体会”的学术讲演。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费孝通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出现在国际学术讲坛现场。他在这次讲演中用乐观的笔调描述了“中国少数民族在这近30年短短时期的巨大变革。”并表示在中国的事实中建立起来的信心使他对“人类的前景充满信心。”
1979年秋,费孝通应邀赴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作柯明斯讲座(Cummings Lecture)的学术讲演。他这次讲演的主题仍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在“中国的现代化与少数民族的发展”这一题目下,费孝通提出了一些事关日后中国改革开放全局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尽管费孝通研究重点有所转移,但他心系民族研究的热情不减。他一直关心少数民族的发展,进行民族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把民族研究与民族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志在富民”是费先生民族研究的根本立足点。基于这一价值取向,他密切关注“中国的现代化与少数民族的发展”。他的民族研究,一是从中国少数民族现实出发,一是从民族工作需要出发。关注少数民族现代化的“发展观”是贯穿他的民族研究的主线。为西部开发出谋划策,关心扶植“人口较少民族”,呼吁重视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问题,是费孝通在他第二次学术生命期间为造福民族地区提出的三件大事。这些关系到民族发展的大事,是他在民族工作中的发现,也是他应用研究的实践结果。
在新的“客观条件”下,尽管他无法“集中力量搞民族研究”,然而他的民族研究没有终止,笔耕不辍。自1979年以后结合民族工作发表的民族研究论述50余篇。这些论述表明,费孝通不仅是一位尽职尽责的社会工作者,又是一位从实求知、锲而不舍的学问家。费孝通一生从来没放弃学术研究,但他也从不讳言自己研究的“工作性”。他说:
学术工作也是个人的社会行为,既不能摆脱社会所容许的条件,也还要适应社会演进的规律,这样才能决定自己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应当怎样进行自己的学术工作。这种自觉可以说是一方面既承认个人跳不出社会的掌握,而同时社会的演进也依靠着社会中个人所发生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这是社会和个人的辩证关系,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20]
费孝通在民族工作中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研究,为我们树立了学者型工作、工作性学术研究的典范。
三、实践“应用人类学”,在民族研究中建树创新的文化理论
费先生的民族研究的特色,可以用“贵在应用”来概括。他是实践应用人类学的一个楷模,一个大学问家。费先生一生著述丰富,其中有许多早已被评论者称为“应用研究”,而他本人也直言不讳说“自己的研究是为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1980年3月,他获得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颁发的马林诺斯基奖,这是国际人类学界对他的学述成就和贡献的肯定和承认。
对费孝通学术的评价,牵涉到人类学的价值以及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看法,这个问题海内外一直存在不同的评论。1997年,费孝通在自己的学术反思中特别提到:
去年九月在吴江与朋友们聚会时,一位来自英伦的友人提起我的同窗英国的艾德蒙·里奇(Edmund Leach)教授在人类学的价值问题上与我形成的差异。我与里奇可以说是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门下的同门弟子,里奇坚持认为人类学是纯粹的智慧演习,而我则觉得人类学如果不从实际出发,没有真正参与到所研究的人民的生活中去,没有具有一定的实践雄心,就难以获得自身应有的价值。里奇已先我而去世,我与他无法进行面对面的论辩,只能在他“缺席”的条件下“自言自语”了。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九九三)这一讲演稿中,我不仅向里奇对中国人类学者的评论作出理论上的回应,而且还承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对我的“应用研究”的影响,承认了儒家“学以致用”价值。[21]
费孝通引述了西方社会科学老祖宗之一韦伯的话语:用“value-free sociology”一词来形容社会科学,也用“vocation”一词来形容学者的追求与学术的定位。费先生尖锐地指出:
所谓“value-free sociology”就是要求社会学研究者在其研究中不要带着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观来观察社会事实,干预社会的客观存在,如果一定要翻译出来的话,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与价值判定无涉的社会学”。“vocation”一词,我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对应的中文词汇,实际上它既指一种才能又指一种具有感召力、超离社会实际的智慧,也许相当于中文中的“天职”一词。里奇的说法,大致说来是社会科学老祖宗之一韦伯的理论在人类学里的延伸。我们之间的差异,不是单独、偶然的现象,而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共同的问题,里奇怀疑我的学术实践的价值观,我则常想“value-free sociology”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21]
价值取向,是对于人类学“应用”产生歧义见解的根由。一种是联系实际,服务社会;一种是崇尚“天职”,超离社会。这确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分野。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用通俗的话说,叫做“两股道上跑的车”。
由于学术价值评判尺度的差异而引起的价值取向的争议,使费孝通反思到更深层的意义。他说:
充满“东方学”偏见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常成为非西方政治的指导思想,使作为东方“异文化”的西方,成为想像中东方文化发展的前景,因而跌入了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的陷阱。
东方社会为追求现代化和现代特性,如何避免在充满“东方学”偏见的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跌入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陷阱?怎样“医治”这一文化心理危机?在学术表述上应采用什么理论?[22]
费孝通自己的一生学术历程,已经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就是坚定地走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之路,联系实际,面向社会,把自己置身到“现代化”过程中,实践应用人类学。
费孝通正是在为少数民族发展的现实服务中实现民族学研究的学术价值。由于他的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工作性”,他又担任过重要职务,因而有人把他看成“政治人物”,进而怀疑他的学术研究含金量,贬低他学术成就的价值,形成一种偏见。费孝通作为学者,在工作中做学问,从实践中出理论。正是在“工作性”的研究中,他有所发现,提出了三个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影响的创新理论:
1.多元一体格局论
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演讲,提出了著名的“多元一体格局论”。他阐述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特定历史过程。我们今天的民族格局和民族关系,就是中国特定历史进程的一个横断面。中国民族关系历史,要求我们必须发展出一种基于我国民族关系现实的、合理的、优化的、稳定的族群关系理论,并以此理论建立一种有效协调我国族群关系的文化和体制。
费孝通的“多元一体格局论”不是在书斋里空想出来的,也不是为“纯学术”钻研出来的,而是在他的长期民族研究工作中发现,并逐步探索出来的。早在1957年,他就对“中华民族”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产生困惑,直到1989年,他才以“多元一体论”解开这一困惑。他说:
当我参加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我心里怀着一系列问题有待研究。这些问题一直挂在心上,我虽则1957年以后已无缘在实地调查中寻求答案,但并没有在思想申抹去。困惑我的主要问题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发生过什么作用和怎样去看待包含汉族和国内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
1989年夏我到威海暑休,当时已年近80岁。出于我对民族研究的留恋,老问题又涌上心头。我带了这本幸存的讲义,打算利用这近一个月的余暇,重新把这二十多年里的思考结合这本讲义,整理出一篇文章来,这时我正接到Tanner讲座之约到香港中文大学作一次学术讲演。我打算就用这篇文章作讲稿。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这篇文章中我初步走出了郁积多年在民族研究上的困惑,也提出了一些值得继续探索的观点。[6]
“多元一体格局论”提出后,引起国内外学界强烈反响。尽管人们对这一理论还有解读的歧义,但谁也无法否认,“多元一体格局论”是中国当代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理论的一个标志性成果。2006年10月10日下午,中国著名人类学家、台湾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乔健教授在“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70年学术研讨会”上演讲,高度评价费孝通的学术贡献,把费孝通和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并列。他认为费孝通对人类学、民族学的贡献在于从中国文化的观点转换了拉德克利夫·布朗等的功能概念,从而创立了在国际人类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功能论。他在随后的一次讲座中说:
我们可以看到费把历史概念融入功能论后,把功能论的整体观念由平面转为立体而且具有了时间的相度,把它变成四度的整体。这个东西在人类学理论上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和贡献。我叫它“历史功能论”。[1]
“多元一体格局论”是费孝通积平生之力完成的重大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建树,“工作性”的客观条件显现其中。
2.文化自觉论
“文化自觉论”是费孝通晚年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理论。他自己阐释说:
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3]
费孝通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从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去内蒙古鄂伦春聚居地区考察,这个长期在森林中生存的民族,世世代代传下了一套适合于林区环境的文化,以从事狩猎和养鹿为主。近百年来由于森林的日益衰败,威胁到了这个现在只有几千人的小民族的生存。90年代末费孝通在黑龙江又考察了另一个只有几千人、以渔猎为主的赫哲族,发现存在同样的问题。由此,他开始思考中国十万人口以下的二十几个“人口较少民族”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次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有针对性地谈到:
在扩大对话的范围内,这次研讨班从这个文化是否有界线的问题,引起了一位鄂伦春族的学员提出的文化存亡问题。鄂伦春是个长期在森林中生存的民族,世世代代传下了适合林区环境的文化,以从事狩猎和饲鹿为生。近百年来由于森林的日益衰败,威胁到这个现在只有几千人的小民族的生存。提出的问题是,从鄂伦春的立场看,要生存下去应当怎么办?其实这不仅是鄂伦春人特有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个现代人或后工业化人类的共同问题,是一个人类文化前途问题,值得我们研究文化的人重视和深思。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想到这是个人和文化的关系问题。人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维持和发展了自己的人文世界。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从人这方面去看,鄂伦春人碰到的是人创造了利用自然来为自己服务的狞猎文化,因森林的破坏受到了威胁。如果坚持原有文化,就会导致人的灭亡。现在正面对一个严酷的选择,保存文化呢还是保存人?如果按照我的文化是为人的认识,选择是明显的,就是要保持的是人而不是文化,这就是说鄂伦春人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23]
这里,费孝通先生针对文化“消失论”的担忧提出民族生存发展的出路在于,勇敢地适应文化变迁,“从文化转型上寻找生路”。由此,他提出了“文化自觉论”。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国的少数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如何有“自知之明”,在传统向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求生路、谋发展,这是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可以代表他对人文价值的再思考。[21]这种思考源于他的民族研究工作,源于他的民族地区实地调查。
3.文化资源论
费孝通一直关注西部大开发问题。在西部大开发深入展开之际,他特别提出西部文化资源论的思考。他在西北民族地区考察后说:
“保护、开发和利用西部的人文资源”,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个题目。我们研究人类学,研究人的文化。人的文化今后最高的发展方向,我认为,吃饱穿暖了之后,就要进入一个艺术境界,文化里面的最高一层领域就是追求美,追求艺术。
西北大地蕴藏的极为丰富的人文资源,如果我们要发展到我们的文化领域里面去,开展我们的人文建设,以及确立我们的文化走向的话,就要在研究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4]
在费孝通的倡导下,中国艺术研究院开展了“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推动了西部人文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研究的深入开展。费孝通提出“保护、开发和利用西部的人文资源”,蕴含着关系“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的重大学术思考。当前,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正在形成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面临许多现实的、理论的重大问题急需解决。费孝通的“文化资源论”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理论的支撑,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费孝通是特殊的历史机遇造就出来的一位大学者,“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是他平生学术研究的主题,实践为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是他的一生追求。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也有一个不断适应的“文化自觉”的过程。学术研究的“工作性”在他那里已成为一种自觉的动力。费孝通的生命及学术历程,有不幸也有大幸,有了“文化自觉”,才铸就出一个真正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本色。费孝通的“工作性”并非常言中的“行政工作”、“社会工作”、“政治工作”,他的“工作性”是历史机遇催生的,这也并非常人可求。费孝通就是费孝通,不可复制。费孝通的“工作性”给我们的启示应当是:所谓“纯学术”未必是学者的真经,人类学、民族学的前程“贵在应用”。历史机遇把费孝通的学术性与“工作性”纠葛在一起,难分难解,幸也?不幸也?只有站在“文化自觉”的高度,才能悟出这位大师的丰功伟业。
〔收稿日期〕2007-03-16
标签:费孝通论文; 吴文藻论文; 人类学论文; 民族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社会学论文; 潘光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