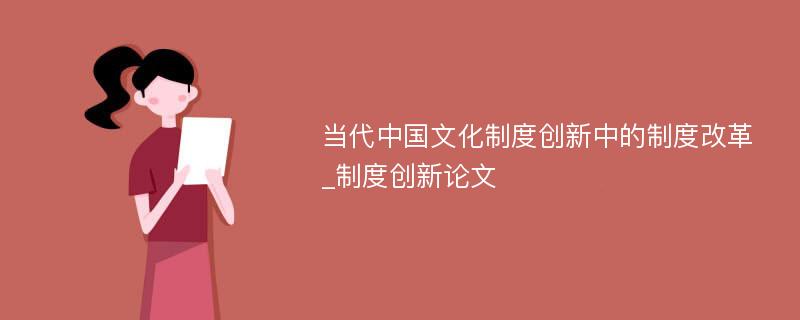
当代中国文化制度创新中的机构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机构改革论文,制度创新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0)04-0005-14
机构改革是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就计划经济模式遗存背景下中国文化制度条件而言,其在文化制度创新的存在地位和推进意义,就处在十分突出的社会转型结构位置,具有极强的中国问题针对性或者说中国事态具议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体制改革的宏观议题下,展开对这一长期纠缠文化体制改革的暗堡以拆解式的学理分析,从而为进一步的公共文化政策总体解决方案提供厚重知识背景支撑。
一
要想准确把握文化制度创新中机构改革的价值目标,必须先行认清何以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机构改革,这不仅涉及到改革的合法性,而且更深刻地涉及着改革的刀刃究竟伸向何处,才能使体制性的外科手术达到预期的疗治效果,因为现实的“政策能力”不足中我们面临着“从任何角度观察,政府未来所面临的不同层面的挑战,都要求其具有比现在更加大得多的能力来分析复杂问题和提供发展方案”①,同时历史遗留症结所带来的“执行效率”滞阻也往往使我们难以实现机构存在效果的“每一机构的责任通常就在于促进某一领域或区域的发展”②。
就中国文化机构的总体现状而言,无论是权力型管理单位还是技术型运作单位,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附属部门,无论是事业体制还是企业体制,无论是致力于公共服务还是致力于社会监管,通常所谓“体制内”的文化机构,其层级、型制和类别不管多么复杂,都可以纳入中国单位制度的命题统辖之中,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总体性文化制度支配下功能运营的国有抑或国营的机构授权实体。所有这些机构授权实体之所以能够被所谓“中国单位制度”命题所统辖,就在于它们既不是纯粹行政治理模型框架中所议及的那种“行动网络观念的另外一个灵感来自于新制度主义理论,一再体现其适应性。也就是设定在每一时空条件下,人们能够表达出一种制度秩序——一个制度序列(无需必然粘接),被人们认为无处不在”③,也不是作为纯粹管理运营技术分析逻辑起点的那种“将其价值定位于贮藏事务反馈信息的某种恰配性制度”④,而是中国语境中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特殊行政编制或治理建置。
对于这种中国语境条件下的特殊性,无论是其历史形成渊源还是现实制约因素,要想梳理清晰恐怕至少得多少本专著才能相对完形。但是我们可以在较少的篇幅内,将这些特殊性定位的文化机构给予形态特征的粗线条描述,并且非常简洁地表述为:
(一)权力身份与服务身份的混存。
处在这种混存之下,特定文化机构一方面或隐或显地获得一定比例的公权力分置,例如文物保护机构作为非政府组成单位却仍然能够代表政府行使这种保护的某些强制性手段,所以在其机构运行过程中就会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向权力靠拢,并以此作为机构命运的权力保护神和利益天使,就像卢梭政治本能学说所讨论的“附加更大的权力以守护其所拥有”⑤,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地承担公民社会政府公共职责的社会履约,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主要体现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功能呈现,例如博物馆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免费开放,并努力在开放中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以及充分显示其服务姿态,从而不得不在“持续的整体有效推进中,追求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的效率与责任”⑥。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文化机构的价值取向既显示为权力向度亦显示为服务向度,当两个向度处在一致性位置,机构的运行效率就会因功能内聚而发挥至极大值,相反,当两个向度处在非一致性位置,机构的运行动力就会因内在裂变而趋于滞缓甚至中断。为了防止极端情况的出现,绝大多数文化机构都选择权力向度而有意无意地躲避服务向度,其目的就在于寻求机构运行效率和存在利益的稳妥方案。
(二)公共利益与机构利益的混杂。
处在这种混杂之下,特定文化机构一方面不得不在公共财政的稳定支撑下最大限度地追求绩效指标的公共利益系数,其可能性在于它在逻辑起点上乃是行政治理框架中的系统设计产物,功能与效率对位效应客观上支持机构运行效益目标值的计量测评方法,因为任何一个文化机构本质上都符合“托管行为理论”的“组织行为和体制特征可以通过SEST属性来予以呈现”⑦;另一方面不得不在职工福利动机的驱使下最大限度地追求机构福利的政策允许值,其必要性在于无论是同一类型机构还是非同类型机构,在目前的体制环境下彼此间的职工福利实际状况往往天上地下,这只要比较同级图书馆与出版社或者同级出版社与石油企业之间薪酬与福利的换算关系就可以一目了然,因而也就迫使每一文化机构成为相对边际封闭的利益共同体,其社会规模抑或力量聚集强度远逊于美国体制背景下的诸如“往往具有决定性。无论如何,由于不同社会领域会按照集团等级制迅速建构,因而集团成员也就往往会在相对稳定的身份安排中连接一起”⑧。
现在的问题在于,当同一机构的运行注意力被混杂状态的公共利益与机构利益所吸引时,至少会存在注意力不集中的社会出场姿态,并且不排除在极端情况下机构利益会占据注意力的核心位置。一旦形成这种局面,机构就演变为个体之间利益结盟的制度保障平台,人们由此获得的将远不止是一个所谓养尊处优的铁饭碗,而是在服务公共利益的幌子下直接将公共资源配置,转换为利益结盟后实现机构利益诉求的无成本甚至无风险趋利工具,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各级大大小小的画院作为政府事业单位就是如此为那些终日自我标榜的画家提供利益机会的。
(三)履约职责与就业职责的混置。
处在这种混置之下,特定文化机构一方面代表政府向公民兑现其文化责任承诺,在其作为覆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个环节并努力实现其功能发挥的过程中,其绩效标杆主要绑缚于特定的履约职责刻度,关键就在于强化该机构“执行”过程中不致出现严重政策贴现的“好的理念在行政实施过程中消失殆尽”⑨;另一方面本身又成为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社会平台,从国家文化部到基层乡镇文化站,从各级文艺院团到不同类型的公益文化事业单位,一支庞大的文化从业大军(包括现职与离退休)使得千千万万的具体文化机构背负着缓释社会就业压力的政府使命,在特定意义上甚至是“维稳”的政治使命。
正因为如此,对微观层面文化机构的本体绩效诉求,常常就会由于类似的相关性功能附着而无法得以严格衡定,而在国家宏观层面,诸如机构网络编序、机构总量的成本效益控制、机构功能的项目测值绩效规范、机构设置与撤销的社会动力学机制以及机构内部的岗位目标分置等等,就都会因为社会就业平台的无条件设定而无法得以动态政策调控,其凝固和僵滞已经逼近官僚制结构的那种“坚守办公室是一种‘职业’”⑩,但由于所有这些机构并不完全具备官僚制所赖以支撑的权力杠杆,因而这种凝固和僵滞的负面后果就更加严重,甚至可以说完全丧失自我功能激活的内驱力。于是事态已经澄露得非常清晰,在对文化机构履约职责与就业职责的混置功能设定中,两种功能至少在制度安排层面形成内在动力耗损,这意味着它将最终成为文化政策执行过程中基层细胞谱系的集体麻木,从而也就进一步导致政府文化治理或公共文化服务的失灵。
如果作剥茧抽丝式的深究,这种特殊性所带来的跟进事态还在于,一种所谓“单位人”(或曰“机构人”)的中国式身份特权,从此就以各种社会优先性渗透进文化制度存在的不同环节与全部过程,这些可以具体指称为诸如“国家干部”、“单位职工”、“事业身份”、“全民所有制工作人员”乃至“文化战士”、“文化系统干部职工”等称谓方式的“单位人现象”,随着计划经济模式管理体制的退场,越来越以刺眼的旧有体制形貌在服务性政府转型的语境中成为新制度安排的累赘。在宏观管理或者管理技术层面,这一累赘不仅构成对效率的现实威胁,而且也会构成对公平的间接性威胁,所以也就迫使我们要对这一跟进事态给予解读,并将“单位人”的身份特征粗线条地描述为:1.就业非风险性,2.甄选非公平性,3.绩效非标杆性,4.身份非置换性。
1.就业非风险性。就业非风险性使单位人获得法律允诺以外的几乎一切允诺条件,使其与文化机构间建立一种非雇佣性就业关系,因而也就意味着不仅不是彼此间的双向选择,而且更加表现为两者间十分暧昧的互为依存,而依存的融洽性直接决定着更高体制层级给定的诸如政治首肯、业绩嘉许、成果奖励乃至投入追加,所以双方也就必然会为了融洽性增量而卷入机构运行过程中的深度合谋。处在这种深度合谋结构之中,表层就业关系所显示出来的各自角色定位已经完全没有实质意义,机构不会严格坚守其诸如“管理是一种权力,决定其中的个体应该发生些什么”(11),个体同样也就不会顾及诸如“行为人利用机构化的‘社会逻辑’以提供清晰的参照来决定其经济行为”(12)。
不仅如此,在“单位人”切分为“单位领导”和“单位职工”后,单位领导的从业要点就在于如何通过利益满意率来支撑来自上级领导的“民主考核”或“民意测验”,恰如单位职工的从业要点就在于如何通过对单位领导的无条件服从甚至谄媚来确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恰恰就在这两个从业要点中,一种消解体制张力和机构功能的互约意志应运而生,那就是认定单位人与单位之间具有天然的利益一致性及其现实存在的互为确证,而其中潜在置换的反体制性后果,则在于作为体制环节的具体文化机构,在单位化过程中不仅被单位人利益绑架,而且与文化制度设计的机构功能配置之间已经失去任何强制性或约束性,也就是文化制度对文化机构控制能力的“规划力量不仅消除个体的超凡发挥,而且还对身份集团进行分层”(13),在单位人就业非风险性及其对文化机构的利益绑架中,已经成为纯粹的纸上谈兵。
2.甄选非公平性。甄选非公平性使单位人的来历从一开始就表现得极其不明。这种来历不明当然不是履历模糊现象,而是岗位进入的合法性遭受质疑。之所以如此,首先由于没有岗位进入的统置性游戏规则,哪怕是单一计划经济时代政治立场识别与政治权利分享模式的极端化道路,或者是多元市场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甄选与岗位责任配置模式的纯技术化方式,虽然其规则运行过程中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尽人意,然而仍然要比目前所处的游戏规则失灵或缺席处境要好。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文化从业者进入文化机构及其具体岗位的统一规则必须迅速确立,否则就会在新的条件下不断重塑单位人形象,并且会有各种更加复杂的当下重塑方式,因为纯粹技术方案的诸如“结构效度证明挑选出来的抽象的个人特质和性格特征(如智力、诚信、创造性、进取心、勤奋和渴望)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14),对校正文化机构人事体制的制度性缺陷实在只能是杯水车薪。其次也由于没有从业定位的稳定程序。
非程序化的随意性进岗,不仅不能确保个体的素质状况或就业条件吻合岗位职责的实际要求,而且在宏大背景上更是对线上从业资格拥有者的社会公正性践踏和权利剥夺,典型的例证如全国大中小型图书馆的数十万个工作岗位上,充斥着一大批安置性眷属就业者,而高等院校年复一年毕业的图书馆学或者信息情报专业的专业人才,却因这种践踏和剥夺而被排除在专业工作岗位之外,其被动结果是,图书馆的资料收集水平及公众服务水平不升反降,该领域的国家公共资源利用率与闲置率均令人吃惊。
规则与程序缺失之后,甄选非公平性实际上就形成某种制度性庇护力量,使单位人在获得岗位准入的同时,也就获得一种排他性的社会选择优势与专属权利收益。其中社会选择优势使其逃离于竞争机制的残酷,从而在不参与竞争的安全位置享受福利社会结构下的就业快感,享受所谓“这类‘财富平均主义’因此携带着潜在的吸引力”(15);与此同时,专属权利收益实际上就是国民财富在公共资源的单位制过程中,被单位人以间接和隐形的方式给予再分配,直接占有则会受到相关法律的严厉制裁,而间接再分配则至多属于利益分配的灰色地带,于是专属权利收益从此就成为单位人与单位之间牢不可破的制度结构纽带,任何意欲绠断纽带的企图都将演绎为血与火的革命,因为这样的企图实质上就是摧毁既得利益及其分配秩序的“不仅是影响结果的一种能力,而且是凭此对别人的一种支配”(16)。
3.绩效非标杆性。绩效非标杆性使单位人成为机构设定最基本同时也最稳固的编制单元。这种离开岗位拟定机构编制的非常态体制措施,既是单位人利益特权在中国体制背景超强存在的结果,同时也是体制设计过程中不得不充分考虑其利益特权的原因,所谓“因人设岗”而不是“因岗设事”,就是对单位人势力挤压体制结构的最形象表述。处在因人设岗的体制妥协状态里,文化机构的全部绩效评估都不得不集中对单位人的行为测定,而这实际上就陷入了一个悖论性的误区:一方面是任何文化项目作为执行中的政策工具,其量化分解和计量测算都必须落实到一系列运行岗位,因为标杆管理一旦模型操控后就只能落实到“在机构中我们解读其功能及其作用”(17),而机构的结构功能必须由相应的岗位组合来予以实现,也就是说机构的有效组织取决于岗位的有效功能支撑,取决于进一步所谓“功能配置就在于高度具体化,生产的焦点即基于这种功能具体化”(18)。
这意味着制度设计的动力学取向其流程为:制度目标→宏观结构→机构功能配置→岗位责任指标分解→从业者归位,整体呈现为顺向度政策执行方案;另一方面却是文化机构中的单位人构成对机构的存在性控制,岗位虚设、泛设甚至不设乃是机构被控制的直接后果,任何自上而下的委托文化项目都必须回过头来以单位人的适应性和理解程度为政策实施起点,从而导致不仅机构内部岗位拟设的因人而异,而且导致机构存在方式、数量和功能诉求也都要充分考虑单位人大量存在的缓释压力,在更深层次,甚至宏观治理结构以及文化制度目标也都不得不受制于来自单位人庞大集团的逆向压力,受制于哪怕细节性的极端情绪表达时“通过传达个体内在表述和行为意图的信息,面部表情扮演着社会合作时重要的角色”(19)。
于是文化制度设计就必须或隐或显地嵌入一种逆向力学结构,那就是动力学流程的:单位人利益诉求→随机岗位拟设→机构负重与膨胀→宏观结构松散无力→制度目标消解,整体呈现为逆向度政策解构路线。正是这种功能向度的悖论结构,使得绩效非标杆性成为政府文化治理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中无法逃脱的体制宿命,成为单位人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演绎为生存贵族的投机主义通道,一切进入者都必然有违于“主体间性的道德诉求不能被延滞”(20)。
4.身份非置换性。身份的非置换性使单位人由隐喻的表征意义进入所指的社会符号给定。一旦获得此类社会符号给定,例如某一个体为某文化机构的国家干部或职工,也就意味着他将因此而终身享有与这一身份相匹配的政治荣誉、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以及福利特权等,所以身份给定在中国文化制度实际运行中具有社会意义的全称覆盖功能,诸如岗位定位、层级标识、职称评价、荣誉呈显、利益配置甚至档案存录等,几乎全都可以纳入个人性的实际身份指涉中,其通涉性可以与之比较的,大约只有原始部落社会结构中的身份符号,因为那个时候“社会身份的差异性并不大,有证据表明,还没有人获得那种最高身份,即要求精心安葬的身份”(21)。
虽然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知识界关于身份研究的知识谱系,无论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文化人类学,都呈现出极为明显的谱系延伸,但这些成果尤其是核心命名,在解读中国语境的复杂存在现实时其穿透力往往都会大打折扣,而遇到像“单位人”、“国家干部”、“文化职工”这一类的身份指涉,这种折扣甚至会尴尬到找不着知识领域或者学科框架,例如域值较为接近的“政治身份研究”及其所谓“身份是被清晰地辨别的,要么能够进入要么不能够进入诸如种族、阶级和宗教的范畴”(22),在介入当下中国体制框架中的身份事态之际,其语义指涉的有效性和问题针对性就极为有限。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就会放弃身份研究的理论视点,而是在命题引入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追求本土化介入状态。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介入心态下,我们终于发现机构改革中身份问题的复杂性不仅与“单位人现象”发生千丝万缕的因果联系,而且直接就是攻克文化机构改革堡垒的最大障碍。原因很简单,一旦个体在社会符号给定中获得机构内身份优势或者社会化的身份特权,它就成为非置换性终身符号,除非因其堕落法律底线之下并被司法机构裁定剥夺其相关社会权利,否则类似的终身符号及其所携带的利益配置权就将长期拥有。例如,在档案中保存有干部履历表者就不会成为“工人”或“打工者”,反之“工人身份”置换为“干部身份”在体制内同样难于上青天,“国家职工身份”则在包括干部和工人的情况下永远与体制外就业人员泾渭分明,哪怕其中有一位体制外就业者名叫康德或黑格尔。此种情形,在西方只有“贵族身份”的“在贵族一词的所有意义中,将附庸制和贵族身份两个概念混杂起来的这种意义,注定拥有最持久的生命力”(23),才有一些外部性的相似特征。
二
毫无疑问,中国单位制度及其进一步的单位人现象,对于中国文化制度的制度目标和结构功能,其影响必然深刻而全面,既有正面价值,亦有负面价值。当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型,当政府治理由权力型制向服务型制逐渐过渡,这些负面价值就更加暴露和凸显,成为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有效保障的阻碍力量,成为覆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顺利推进的体制肿块,因而也就成为宏观文化体制改革或微观文化机构改革的改革对象。所以,厘清改革对象的问题脉络,乃是确保机构改革真实性的基本前提。
机构规划缺失带来的普遍性后果,在于文化制度总体性设计框架的各个环节,不能合理配置功能传输的节点位置以及相应的机构填充,而是简单套用政治治理和行政管辖的框架结构,与权力分置相统一地进行文化机构划一性布局,由此形成的文化机构在总量、规模、类型、位置、功能取向及其效果目标等方面,就都缺乏体系独立运行的自稳结构和自衍能力,这一方面会导致整个文化系统难以实现“规划逐渐展示新文化理念在所有意旨方面的不断开始”(24),并由此导致该系统的非递进性功能弱化或者结构老化,另一方面则导致单个文化机构不能具备“通过建构过程中对体系的适度限制以寻求其自组织风貌中的具体功能”(25),也就是说,缺失使我们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都不能获取较好的体制生态,而失去体制生态的文化机构也就必然尽显随机性特征而非预期效果产物。
对此,人们较为敏感的是那些解释不清的非规范性体制现象和机构形貌,例如,尽管武汉的日常阅读量远远大于整个青海,但青海图书馆却是省级馆建置与配备而武汉图书馆是市级馆建置与配备,又例如,考察包头市城市聚居区可以用图书馆馆舍面积和图书册数指标,而考察呼伦贝尔盟游牧区又何以要用同样的指标尺度,诸如此类,报刊文献的质疑文字不乏尖锐,足见人们对于现行文化机构的设置方案与评价体系是深以为虑的。如果我们稍微上升至理性分析高度,就不难发现这些现象后面所隐蔽着的规划缺失后遗症,至少可以梳理出如下急待解决的弊端:
(一)总量设置不合理。
也就是说,无论是国家文化机构总量还是区域文化机构总量,都应该寻求到某些具有必然限制意味的参照物及其相应的参数,由此换算出国家文化机构总量或者区域文化机构总量,并由这一总量的动态变化来决定年度投入比增减的变化,芬兰实行的区域自治的办法就是着眼于“区域文化行政……包括决定设置公共图书馆和图书馆地区数”(26)。
与此相反,我们现行的机构设置办法基本上几十年一乘不变,国家文化机构总量是否符合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符合覆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基本要求、符合全球化提速条件下中国参与国际文化竞争以及展现大国文化综合实力的时代变化,至今未见任何详细的权威性论证文献,更不要说像瑞典那样在20世纪60年代全国性地公开讨论“现存文化机构以及新增文化机构的资源合适性”(27)。显然,一个缺乏总量科学论证的文化系统框架,在体制运行过程中一定存在根本性的运行效率误差。
(二)类型设置不合理。
也就是说,就国家文化制度的基本制度目标而言,例如就其中重要目标取向之一的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而言,一定有一套与之相匹配的政策工具及其政策执行的机构载体,于是我们就很容易从逆向追问路线来学理咨询文化机构究竟核心种类有哪些、基本种类有哪些以及辅助性种类有哪些,而其决策性回答则完全取决于哪些文化政策工具需要操作执行。在英国的文化政策体系中,文化专项征税、国家彩票和私营部门捐助乃是不同的政策调节工具,所以也就设置出不同种类的文化机构,其中为了企业捐助的有效操作而“既有民族遗产部门(DNH),也有专门服务于文化、媒体和体育的部门(DCMS),自1990年代末以来,后者就积极致力于鼓励企业捐助”(28)。
但是在中国现有的文化制度框架中,不仅文化政策工具缺乏系统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而且也直接导致文化机构种类设置的僵化模式,言及乡镇就一律是“综合文化站”,言及县城就一律是“三馆”,言及中心城市则一律是“标志性大型文化设施”,地域机动性、时效机动性、功能机动性和创新机动性等,在种类不变的工作程序背景下使文化机构的种类设置完全失去效用原则所要求的体制活性。显然,一种缺乏功能活性的文化机构种类设置方式,其运行结果只能是助长机构先于效用的机构形式主义。
(三)级差设置不合理。
也就是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几乎所有体制内的文化机构(包括国有文化企业)都依附于相关主管文化行政部门,并相应地被给予非权力化的级差设置,这种设置一方面使其不可能像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一样按行政权力分置大小来确立其行政级差,另一方面又使其不像一般社会机构那样取得平等的社会出场资格,因而文化机构的主体资质、服务规模、运行质量及绩效成果大小等,都不能成为该机构体制安排的核心支撑点,就仿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利润数亿元之巨却仍然被定格为科级文化机构,而中央国家机关很多部委的出版社负债累累还得享受正局级机构的功能配置,而这样的定格和配置在中国文化制度框架中并非只具有形式意义,恰恰相反,其资源拥有和相关福利配置等更具权力延伸的实际价值。
于是,如果我们站在适当的距离予以全景审视,就不难发现与官僚机构处于平行位置的亚官僚机构或者说文化官僚机构同样织成了巨大的依附性权力网络,这个网络较之韦伯所描述的“一般说来,至少在公共官僚制内,占据办公室位置就是生活支撑,这已是不断增加的事态,而且发生于所有紧密结构之中”(29),其情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此,问题实际上就转换为,究竟是何种理由使所有这些级差设置具有合法性,或者可以举证性地追问,将中国出版集团设置为副部级国有文化企业或者将中国国家画院设置为正局级文化事业机构,其级差究竟能有助于产业增量、事业拓值,还是由此就可以获得更强有力的机构功能支撑,抑或除了机构利益外就只剩下皇帝的新衣,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从制度设计和机构规划的宏观层面给予客观而冷静的反思,否则所谓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同步推进就将是一句空话。显然,当文化机构的运行支撑绑缚于对官僚制的无条件依附,其机构运行活力必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运行目标模糊表现在文化机构环节远胜于宏观文化制度框架,因为虽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过于缺乏义项澄清,而“建设覆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则至今未曾给予指标体系化的功能配置,但毕竟在指导思想和主体观念层面已经具有正确而明晰的选择,并且这种选择足以在未来的文化实践中渐进性地给予体制完善和意义填充。
但文化机构运行目标模糊情况就大不相同,这一方面会影响到特定文化机构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存在逻辑,也就是如何通过角色塑形和功能定位使其获得社会存在的必要性。例如,如果没有明确发展主旨引导下的“创新乃一种基本的非确定性要素,这不简单是缺乏已知事态发生的相关信息问题,更加重要的……涉及到能否在科学知识进步中不断获得新的重要的技术机遇”(30),那么也就意味着离开创新之途的文化机构迟早会被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所抛弃;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特定文化机构内在组织的管理效率和运行效益,即机构不能以项目的计量测值和年度绩效标杆支撑其可持续发展线性轨迹,按照管理学知识域所谓“知识及其行动并非基于诸如逻辑或理论化之类的抽象原则,而是依赖于怎样有效行动才能达到预期效果”(31),则目标模糊将会对文化机构的所有操作性运行造成致命的盲动主义倾向。
正是综合评估这两方面的影响,我们才将文化机构普遍存在的运行目标模糊,归结为以下三种最基本的体制危害内容:
1.体制授权不清晰。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文化机构既不是体制链上通过功能嵌合而发挥其执行力的分置单位,亦不是体制赋予其独立行使机构职能的法人单位。例如对于那些文艺院团而言,究竟定位于政治宣传主业功能、公共服务主业功能、艺术创新主业功能抑或市场趋利主业功能,不仅机构设置之初并无确定设计方向,而且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更加找不着重新准确定位的发展思路,为什么存在及如何存在的深刻疑问,长期以来就在非清晰授权的编制性保障下悬置,并且文艺院团往往也因为这种悬置而呈现出无目的延续、无危机生存、无创新苟且的游牧存在方式,它们就像听命于牧鞭暴响一样地等待着来自官方的随机性权力意志安排,所以往往新任文化部部长或者省(市)文化厅(局)长,简单随意地撤换一个院长团长就足以使文艺院团一切从零甚至从负数开始。
总体而言,体制授权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具体文化机构与机构运行质量、绩效责任和可持续性发展之间没有必然逻辑关系和行政问责结构,当然也就不存在那种塑造杰出机构的诸如授权作为原则“不仅决定着杰出机构的本质,而且也重新限定了机构领导者的作用和责任”(32)。
2.评价指标不规范。也就是说,尽管现行文化体制中单位考核对文化机构形成了一定的测评压力,例如民主化进程推动下全员职工的年度投票表决,就对该机构负责人至少会产生心理威慑,而奖励和福利不同程度地与文化机构运行状况挂钩,同样也会对该机构的所有成员形成惩罚机制或者激励机制。
但问题在于,评价指标非规范性的诸如偶然性状态及其所谓“如果你正准备让人去干,那么他们最初肯定干得不好,他们会犯错误,而你应该接受这一切”(33),定性分析状态及其所谓“经济学及组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需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理论之上”(34),甚至单纯领导意志状态及其所谓“机构影响力与人格偏见是如此交织,以至它们几乎密不可分,所以机构行为仅仅是个体行为的集合输出”(35),诸如此类乃至更多的表达形式,都会导致特定文化机构运行过程中的非可控性技术方案失效,这种失效的直接结果,就是目前我们所熟视的文化机构运行自为,以及这种自为状态下的去功能化、去效率化乃至一定程度的去社会化。
情况一旦被动至此,任何文化机构就都不过是一种存在形式,不仅在体制链条上是可有可无的一节,而且对于社会接受面和诉求意志而言,同样也就变得可有可无。毫无疑问,文化机构运行现状中的可有可无状态,在我国目前文化体制的总体结构中十分普遍,与国民文化生存的需求密切性乃至民生意义相去较远,某种程度上已经演绎为文化制度失灵的严峻现实。
3.服务对象不明确。也就是说,尽管机构运行的本体特征集中在机构自身的功能配置和管理效率,但影响其运行目标的力学结构要素还包括一个重要维度,那就是来自服务对象的作用力。
当我们把叙议的范围严格限制在文化机构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层面时,对象作用力直接会影响到机构运行目标的清晰与否,而当特定的文化机构在公共文化服务之际不能按照功能配置条件来锁定服务对象,而是显示出对象界面没有所指限定的空泛能指,就仿佛只追求图书馆“拥有7万7千多种报刊杂志,而且其中许多集中于拉丁美洲主题”(36),而忽视不同地区或不同功能的图书馆因服务对象差异所显示出的阅读人群重新倾斜。
实际上,即使是公共图书馆,也应该充分体现城市图书馆与农村图书馆的功能差异,更何谈公共图书馆与专业图书馆服务对象拟定的前提性区分,所以每一个具体图书馆由此也就应该极为精细地服务对象定位,甚至这种定位有时还应随着背景状况的变化而进行动态微调。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一切文化机构都必须在公共文化服务的体制功能结构中,寻找到自身服务对象的有限性定位及其这种定位的有序移动规律,由于中国背景下类型机构的复杂构成和受众覆盖情况的千变万化,所以在戏剧院团的观众群体设计问题上就必须因团而异,促使其功能与对象之间的有机嵌合,那种诸如在英国行之有效的所谓“文化、媒体与体育部(DCMS)通过其新观众介绍的能力而努力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由此可以设计将某些艺术带给更广大的观众”(37),在中国文化体制环境下,不仅起不到积极的机构功能促进效果,反而会给不同服务对象定位中的戏剧院团带来观众疏离的负面效果。
而现实的不利局面恰恰也就在于,绝大多数从事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机构,其服务对象定位仍然处于本能自发阶段而非理性自觉状态,所以定位的精确性和有效针对性均大打折扣,并且这种折扣最终也就以影响因子的力量对文化机构运行目标模糊的体制现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也就不得不陷落“公共服务失灵”(Public service failure)的“在其运行表的最低端摇摇晃晃”。(38)
绩效监管乏力既发生于机构内,亦发生于体制结构内甚至社会环境内,在不同层面具有其不同症兆和病态表现。无论在何种层面,只要文化机构的运行绩效处于非监管状态或者至少处于非有效监管状态之下,管理技术层面的诸如“一种设计工具往往成为苦思冥想出来的正确方案,或者向人们表明,某种确定的设计完全适应于相对应的竞争性环境”(39),或者公共行政治理意义上的诸如“无论采用何种公共介入形式,其效率都是需要给予重视之所在”(40),至此都将会从体制功能结构中流失。
当一系列类似的流失附着于同一个文化机构,也就必然带来一定程度的去功能化后果,于是机构本身也就演绎为体制链条上无法承载能量传输的形式符号。就这类形式符号化的文化机构而言,它的存在其积极意义唯有解决数量不等的文化从业人员的社会就业问题,而消极意义只要社会期待视野对文化制度运行逐渐失去起码的信任这一项,就足以将积极意义超量化抵消,更何况公共资源耗损以及公共财政的巨大成本支付,使得这类流失的代价大大超出了参数正常值。
实际上,如果我们对问题给予细密梳理,就不难发现,导致去功能化后果的所谓绩效监管乏力,主要有文化机构内部、文化制度结构中、社会环境中的制约力失衡这三点。
首先存在于文化机构内部的制约力失衡。诸如机构负责人权利专控及其这种专控所带来的“这里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掌权者可以通过用作隐蔽暗示的符号通信,对权力对象行使秘密控制,以限制或有选择地决定权力对象的信息供应;一种是不露声色地反复灌输某些积极或消极态度”(41),文化机构内部岗位设置功能紊乱及其这种紊乱所带来的“如果谁忘却了博物馆是一种现代机构,那么就会出现服务工具的去功能化,而且会在技术设计方案中刻痕为一种非功能化的制度”(42),甚至日常运行指标的自律缺失及其所带来的“大多数人都自以为他们干得很出色,但他们的这些估评常常是错误的……结果是使其一事无成”(43)。凡此种种,都会导致机构内部的制约力失衡,并进而导致特定文化机构因机构内绩效监管乏力而走向去功能化。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客观评估一下全国范围内的乡镇基层文化馆站的实际运作状况,就不难发现它们绝大多数失去绩效自律能力,因而也就绝大多数在去功能化生存状态中与广大农民的热情文化期待或者积极文化参与相去已远。
其次存在于文化制度结构中的制约力失衡。诸如外部制度接口非链接性及其所带来的“辖区性非稳条件虽然并不复杂,但却极难予以预测。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条件下,某些要素相对独立,而且具有非预见性”(44),不同机构间功能效果换算的非尺度性及其对“现代民主的实际贡献不在于新规则的发展,或者法学家所谓‘实体法’,而更在于‘程序法’的进步”(45) 的中国式疏离,甚至来自垂直方向或者平行方向的问责环节缺失及其这种缺失所必然导致的“尽管出现错误之后,必须有人为此负责,但不幸的是,通常耳闻到的处置是政府麻木不仁,其结果是,附加而至的问责十分困难”(46)。
所有这些制度结构本身存在的制约力失衡,其所导致的绩效监管乏力,实际上就是使得文化制度框架作为一个总体性目标系统,在功能目标不能预期实现的运营状态下,缺乏系统结构的绩效维稳力量和功能修复力量,从而也就使得该系统存在本身非常脆弱,甚至可能会导致每个机构性的功能环节都会程度不同地孤立游离于制度结构的功能链之外。
就我国文化机构的现状而言,之所以很多文艺院团出现权力膨胀的“一把手专权”现象,而且这种专权使得无数演艺从业者在住房、职称、工资、角色分配、演出机会甚至民主表达等诸多方面,饱受一种所谓“中国单位制度”的非法挤压,当然也就必然会导致挤压状态下院团绩效的递减趋势,就是因为这些文艺院团无论在垂直方向还是在平行方向都缺乏绩效监管和体制问责,缺乏对院团法人的权力限制和过失追咎,从而使其在绑架机构的投机主义胜利之后能够随意性地绑架中国文化制度,而当极限状况下个别绑架者被纪检或政法部门以反腐的名义进行清理时,事态就转换为另外一种性质,在这一转换之前所存在的大面积制度性耗损,往往就在合法化的遮掩中成为绝大多数文化机构行政虚设与问题叠加的共同宿命。
再次存在于社会环境中的制约力失衡。诸如主流媒体的报喜不报忧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它们更多地献媚于对官方权威的支撑而漠视价值均摊”(47),或者社会公众缺乏批评激情并在文化建设总体背景上显示出“公民政治性参予的失灵”(48),其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公众的监管性绩效批评,不能形成一种集合性的校正力量来对文化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干预,因而这些机构的运行状况及其绩效后果也就处在自闭结构中,这种自闭使得文化机构与社会文化延展割裂开来并且彼此互不制约和影响,文化机构由此演绎为文化人之家而不是全社会的公共平台。从如上三种分析不难看出,一旦绩效监管乏力,文化机构就成为断了线的风筝,与文化制度效力的设计初衷恰好背道而驰。
人事体制僵化对中国文化制度而言乃是久治不愈的顽症,至少自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革浪潮都无不波及到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更进一步的人事机制改革。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改革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文化体制改革每一次难以深入下去,恰恰还是由于人事体制僵化成为半途而废的最大绊脚石。其最终结果往往是,撤销重复机构时机构越来越大,缩小编制规模时人数越来越多,减少领导干部职数时官员该下的没下、不该升的照常升迁,诸如此类的被动后果,已经使得一切涉足文化体制改革或者具体的机构改革者谈虎色变、望而却步。
人事体制僵化在目前的文化体制条件下之所以成为瓶颈,是因为它在如下几个方面积习已深,那就是:A.个人身份与特殊利益的捆绑,B.具体岗位与一般职级的捆绑,C.一次机会与终身就业的捆绑。在个人身份与特殊利益的捆绑中,身份人或者说机构人获得行政干部或者所谓专业技术干部符号定位,这种定位不仅从一开始就不是人力资源测评甄选的结果,即压根儿就不会考虑素质规范测值的诸如“任何选择方法都必须面对的五种标准”(49),当然也就不会考虑综合开发使用涉及到的诸如“这些工作包括培训、就业发展、劳动关系、新的探索以及基本工资、附加薪酬、个人利益、服务质量与数量等的管理”(50),而且也不是岗位设置对人力资源目标诉求的结果,即特定的个人身份(例如院长、站长或者一级演员、一级编剧、一级美术师)以及这些身份所携带的特殊利益(例如工资级别、住房标准、医疗待遇或者补贴水平、交通工具配置档次等),乃是宏观政策层面前提性、无条件性甚至强制性、永久性的给定结果,当所有这些给定密不可分地捆绑在一起之后,就成为中国特色的既得利益存在方式,任何企图松绑乃至剥离的企图都会遭遇整个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既得利益群体的集体抵抗。
轻微抵抗表现为消极怠工、病假事假、言论过激、瓜分国有资产以及体制外经营等,严重抵抗则发展至机构瘫痪、集体上访乃至其它更极端的群发性、突发性公共事件,无论是轻微抵抗还是严重抵抗,都会形成一定程度对社会维稳形势的冲击,而这些冲击的最终博弈结果,很可能就是对机构改革的滞延或者终止性否定,至少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际历程已经确证了这一点。
在具体岗位与一般职级的捆绑中,岗位的行政职级化不仅使得岗位成为官僚主义在文化机构生存中的庇护所,而且使得一切进入岗位者在取得官僚符号的同时,也彻底掏空了岗位的功能定位意义。于是在文化机构的运行过程中,岗位已经不是功能实现的基本细胞单位,已经不复拥有公共文化服务的自在功能嵌位,而是被动性地置换为岗位占有者的随机性动态意志与自为状态,其中的管理机理差异在于,岗位管理中的功能实现是通过岗位功能的恒定性统置人的非衡定性,而岗位占有者管理中的功能实现则是通过对人的非衡定性约束去努力追求岗位功能的衡定性效果,日常表述中的所谓“养事不养人”与“养人不养事”的对称性表述,其机理性和学理性就在于此。由于“养人不养事”以及随之而来的具体岗位与一般职级的直接捆绑,任何文化从业个体就必然丧失对岗位职责的实际依附,转而代之以更宽泛意义上的身份效果诉求,代之以对人际关系的浓厚兴趣和对职级符号的高度关注,事态至此,那些制度设计专家所诉求的所谓“机构设计中权威性领导以及与激励的有效性均衡所带来的效益最大化”(51),至少在管理技术层面就完全不复存在,于是所有管理失效的文化机构,其运行的稳定性反过来就又不得不依赖于传统的官僚制治理模式和统置方式。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化制度背景下文化机构的运营状况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至少90%以上的文化机构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类似的体制返祖,现代化和改革成果的流失,是导致这些文化机构丧失服务效率和功能活力的深层原因所在,人的可变性要素意义在职级钙化中不仅僵化了人的潜能,而且也彻底僵化了岗位的功能。
在一次机会与终身机会就业的捆绑中,文化制度结构本身将机会调节的权力一次性地交给任何一个机会涉身者,而把就业压力以及不称职的风险永久性地担当下来,这种机遇与风险非匹配性的逆向错位,一方面导致从业者风险成本最小化和机会效益的最大值,也就是所谓“就业权的核心价值与理想状态总是在个人角逐的关注中竞争着”(52),被这种错位关系给予根本性的遮蔽,另一方面也导致文化机构风险成本最大化与机会效益的最小值,也就是所谓“通过评估和采纳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来提高劳动力的有效性,以确保具有高能力的人能被雇用,确保目标符合劳动力的质量和构成”(53),在逆向结构选择机制中失去管理意义和操作效力。
事态进展到这一步,中国单位制度的另外一种被动性就得以充分凸显,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在牺牲制度效率中使僵化的人事体制成为一种福利,甚至终身就业的特权成为从业者拥有的某种社会福利产品。恰恰就是这样一种隐形福利产品的存在,使得中国文化制度形成功能激活的巨大人事负重,对于具体的文化机构而言,这种人事负重足以在人力资源管理的非自主性、非可控性及非动态性中走向去功能化的泥淖。
三
既然我们已经能够较为清晰地梳理出文化机构运行中的基本问题及其存在特征,那么我们也就应该有针对性确立机构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基本操作思路,因为机构改革的正确选择必须首先与问题结构保持因果逻辑关系,否则任何想象力改革方案或者参照性行动路线都将在机构改革实践中失效,就仿佛那些笃信“在民主社会中,每一次新的技术浪潮都能够促进交流,同时也在公共领域带来新的治理意味”(54) 的西方公共政策专家,一厢情愿地在非条件限制下构想其“第四种组织”的社会均衡蓝图。因此,我们在从事文化制度创新中,就必须立足于文化机构的运行矛盾实际进行机构改革,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改革效果。
寻求机构改革效果的最大前提条件,在于超出此议层面的总体性文化制度设计,是否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基本价值诉求,是否符合国民日常生存的当前文化诉求和民族文化振兴的长久精神支撑,是否符合人类文化进展的普遍规律和文化自由衍生的一般本质,很显然,如果总体性文化制度设计与这样一些价值原则相背离,那么也就意味着国家文化制度层面至少存在某些制度缺陷或者结构性功能障碍,而当制度缺陷或者功能性障碍出现,或者出现更为深层的文化体制矛盾,那么即使机构改革的价值理想极大值得以实现,也依然无法实现文化机构诸如运行有效、功能嵌位、预期效率明显以及服务最大化等设定改革目标。
以文艺院团改革中的人事制度改革为例,至少在20年前就不乏所谓“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改革方案,但是,之所以时至今日仍然普遍遭遇身份转换难的老问题,之所以诸如此类的改革方案在操作层面难以深化和拓展,就是因为其所承载的具体国有院团,作为具体文化机构的任何转换、松动、激活乃至型制变异,无论其力度和功能覆盖程度有多大,都无法与总体文化制度的一般功能框架或者中国单位制度中身份利益结构的基本人事政策所抗衡,只要这种抗衡的非现实性乃是微观机构的宿命,那么任何微观机制改革都必然会无条件地受制于宏观制度的总体性制度条件。
而现实的最大症结恰恰就在于,文化宏观制度条件和国家基本人事制度环境并没有给这些技术方案以必然导向和必备支撑,所以细节性具体文化机构的人事机制突进就不可能走得太远,对此,任何涉身院团改革者都必须从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制度设计观中规划其改革方案,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甚至带来极大的社会隐患后果。
微观文化机构对宏观文化制度的这种依赖,在全球化时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在宏观文化制度的制度框架由国家边际内事态跨越至国际性事态,所出现的“不仅会在一国与另一国之间存在差异,而且会出现世界历史条件下走向现实的国家集团,密切为或者进一步根源于想象得到的观念类型”(55),会导致国家宏观文化制度的动态性加大和转换程度加剧,因而也就决定微观文化机构在机构改革过程中不仅政策坐标更加游移,而且对功能嵌位的外部条件适应性要求更加苛刻,这是因为进入全球事态之后,全球化的文化同质性较之地方化传统的文化多样性更加具有日常生存干预力量,进而也就意味着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同步性成为文化制度设计必须谨慎处置的严峻现实。
就中国文化体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实际运行状况而言,其所出现的同步性失衡主要有两种情况:
其一表现为微观融入时宏观滞后,即人们在文化机构改革中,往往于技术层面容易产生对先进管理经验和新兴功能方式的跨境认同,具体情形如图书馆功能推进中对有效信息采集与贮藏的机制更新,普遍更加强化“框架”的“机构的四级阶乃是信息运转阶段模式混合生成的产物”(56),从而使图书馆这样的机构在机构运行效率和综合服务质量等方面会产生较为明显的机制刺激效果,但问题是,由于一系列国家宏观文化制度改革离现代化制度突进还有遥远的距离,很大程度上还是权力治理模式和计划经济时代体制遗存的僵固状态,那么即使类似的机制刺激行为更加大幅增加,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图书馆作为文化机构的基本现状和基本生存命运。
对此,我们不妨看作制度框架在机制突进面前的非同步性制约,这种制约使一切细节性和技术化的文化机构改革局限在较低层次的价值上限。
其二表现为宏观转型时微观滞后,即人们在文化机构改革中,没有把宏观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成果和转型诉求等,有效地转化为具体文化机构的功能配置和机制创新,也就是在细节性和技术化层面看不到宏观转型所带来的制度活力和工具效率,没有在机构设计层面充分体现出“在功能配置中,部门管理者们通过具体的预设单元,促使其成为良好设计的工作岗位”(57),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宏观文化制度的制度目标,因细节性功能支撑力量的塌陷而出现迷失和消解。
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虽然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政策目标早已成为执政党和中央政府重要文本指涉内容,而且这种指涉甚至显示出政府文化治理结构服务性转型的历史转折,但是之所以不能在国民日常文化生存空间获得相应的转折效果,障碍就在于这一转折的价值选择不能落实到成千上万的文化机构功能配置中来,这些机构的宏观文化政策识别还局限在传统定势的诸如“在每一时空位置人们谈及的都是一种制度秩序——这样一种制度建构(并非必须粘合的),到处都被认为是占主导地位的”(58)。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讨论机构改革时,不能不优先考虑作为最大前提条件的宏观文化制度设计和总体性文化政策取向,否则一切讨论都会失真或者失效。
寻求机构改革效果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两个意义维度:1.效率性,2.正义性。
1.效率性。就效率性维度而言,尽管文化机构因现行体制条件的制约而强制性地被切分为中央单位与地方单位、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条条单位与块块单位以及体制内单位与体制外单位等,尽管这些单位因体制条件不同而出现运行状况的彼此间差异甚大,但一个突出的总体性特征就是,各自都在不同的梯级位置共同显示其运行效率低下。运行效率低下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机构投入产出严重不相匹配的通病,经济学家拟定的“在最初的投入产出研究中,雷昂替夫(Leontief)呈献出所谓封闭模型:所有的产出都被用作投入”(59),无论在中国文化机构的社会效益分析还是经济效益分析中,都难以找到完全获得解读效果的现实案例。
正因为如此,机构改革的出路就必须由此获得整体性转折效果,通过不同的机构功能激活,使得这些低效率运行中的文化机构走上高效率的快速车道。要么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在服务功能强化中实现社会效益的巨大延伸,形成整个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效果的诸如“发展所包括的不仅在于拥有产品和服务,而且更在于选择机遇中的充实、完满、有价值以及整体生存的价值方式”(60),进而也就在有效的制度安排中确保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成为理想形态的所谓“公民权乃是所有福利国家的核心要素,走向公民的权利诉求来源于自由传统”(61)。要么是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在生产功能升级中实现经济效益的大规模拓值,形成区域性乃至国家性文化产业竞争力的诸如“阿伯瑞尔,一个由罗伯特·斯维托拥有的杂志与有线电视王国,与环球公司一道从2004年始分享了巴西的有线市场”(62)。无论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还是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其机构运行目标都必将定位于效率最大化或者至少是效率优化,定位于机构功能活性的“内聚的结果促进核心竞争力,通过降低沟通成本来改善沟通渠道”(63),甚至包括在宏观背景上适应于转型社会变化的“后共产主义现代化往往被描述为这样一种转型,那就是从政府控制经济走向市场控制经济,包括某些制度变化”(64)。
2.正义性。就正义性维度而言,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行文化体制中的机构存在实际,至少存在着三种亟待校正的正义性缺陷:其一体现在文化利益分配方式的非平等性,其二体现在人力资源甄选的非平等性,其三体现在内部效益分配的非平等性。
所有诸如此类的正义性缺陷,从不同的方面制约着具体文化机构的文化服务公信力及其人们对其日常运转功能的依赖,因其如此,机构改革就必须从制度创新中抹平这些缺陷,从而实现文化机构的正义性价值存在目标。
事态一旦如此,不仅意味着一切有志于从事公共文化服务且具备高素质条件的人才,由此可以在动态性机会均等中获得人尽其才的服务机会,包括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动态性领导置换能够疗治那些顽固性的诸如“与改革型领导相比较,保守型领导更不愿意致力于革命性的、变革性的机构变化,而这样的致力能够产生因解构而走向功能完善的效果”(65);另一方面也使具体文化机构在其体制设计目标中将公共文化利益放在首位,从而能在公共文化生活境域充分显示出“福利政府的发展可以视为一种转型过程,从完全追求以阶级地位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的服务与利益,到追求特定领域以公民为基础的服务和利益”(66),甚至还包括在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利益安排的功能嵌位程序中寻求公民身份的公平正义,以及公平正义原则在所有政策工具和文化服务项目中计量测值而非“社会科学家们通过几条原则对这类问题以一种虚幻的诊断”(67);还有一方面则是内部激励机制核心要素的机构内公平正义,尤其表现在机构内部诸如职务提拔、职级晋升、住房分配、医疗保险待遇以及赏罚分明等生存细节,并且每一个这样的细节都直接指向机构能否保持正义存在状态的诸如“利益分享不仅是对分析出来的部门给予一定的奖金,而且更是单位所有成员的利益共享(年度低成本),就这一做法而论,基于集体更大于基于个体”(68),进而每一个这样的指向又都密切关联着机构功能价值目标的“何种设计恰好与价值取向吻合”(69)。
由以上简单分析不难看出,对于寻求机构改革效果的基本价值取向而言,效率性和正义性两个意义维度虽然分异性很明显,但在更深层次却是彼此紧密粘连在一起的,两者在文化机构的价值实现中既互制约又互为支撑,因其如此,我们在机构改革进程中就必须努力做到两者兼顾,彼此同步,否则在随后的机构运营中就会或早或迟地出现一系列非协调性的负面后果,而这种负面后果一旦成为普存事态,就将势必演绎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制度后遗症。
寻求机构改革效果的文化生产力解放,至少有三条无法绕开的体制路径,那就是:1.身份与岗位的剥离,2.就业与福利的剥离,3.机构运转与权力统置的剥离。
1.身份与岗位的剥离。从身份与岗位的暧昧关系而言,文化机构与整个中国单位制度的普存弊端一样,在消解人力资源自由劳动力活性的同时,也把一切进入体制内的劳动者个体与铁箍一般的工作身份、工作岗位、工作待遇、工作条件、工作评价乃至政治与人身档案等绑缚在一起,其中身份与岗位的固定与叠合,尤其具有国家强制意义和对机构进入者的无条件性。一旦这种强制意义和无条件性成为社会存在秩序中的一个肯定性环节,它就必然会对所有社会成员形成价值诱导和追逐性吸引,因而也就必然会造成一切进入肯定性环节者对这种暧昧的终身坚守及其对意欲进入者的巨大排斥。
无论如何,这种被动性局面都是计划经济模式的产物,都是由于文化体制改革还浅尝辄止于“部分地模仿于圆滑的语词、概念”(70),大批量的文化行政干部或者文化业务干部,还都处在身份层级与岗位层级的直接混居状态,还都必须现实地选择以岗位求取身份权力、身份福利乃至身份虚荣的体制栖身方式,由此岗位也就成为身份并进一步成为具体身份人穷力追逐甚至个人拥有的利益金矿、抗风险港湾以及权力再分配家庭遗产。
正因为如此,机构改革就必须有效地将这种身份与岗位的暧昧混居体制性地予以剥离,既不因人设岗,亦不因岗定人,从而在岗位的职位性和身份的动态性结构中求取人力资源市场的就业者入位,其入位的就业特征在经营性文化企业就将体现为诸如“通过开发个体化可能性,文化领域为青年人提供理想化空间,亦如它给政府提供更多的机会,形成不受传统雇佣成本及其限制的后工业自由经济”(71),而在公益性文化单位则会显现为诸如“随着经济衰退,加之与苏联出口贸易的回落,其对芬兰的打击就其强度和时间长度而言都超过瑞士,高失业率从1990年代一直延伸至新千年”(72)。这意味着身份和岗位剥离后会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给自由劳动者以更多的进入文化机构就业机会,第二种可能性是使一切文化机构的就业者既不能与岗位终生相守,亦不能对身份终生庇护,传统隐喻的所谓“铁饭碗”、“大锅饭”更加不复存在。相反,以业绩求取岗位的相对稳对性,或者以能力素质支撑身份符号,皆无不迫使所有涉身文化机构的个体以及以更加积极的人生姿态和就业表现来实现其自我价值求证,并通过价值求证的社会测评来换算其恰如其分的工资收入。
2.就业与福利的剥离。在就业与福利的非剥离状态里,作为遴选制的就业与作为非遴选制的福利获得体制性联姻。这种联姻既使得就业可以处于非遴选状态,同时也使得福利不得不常常遭遇遴选的风险并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普世性被单位福利的利益排他性所置换,其结果就是使得少数人通过非公平性投机行为逃避公平遴选所应面对的诸如“在这里,由于受到负责任的行政管理者们的强制执行,就业的法制化制度较之非政府部门影响更大”(73),而且一旦他们实现这种投机性就业机会攫取,就会在联姻制度安排的庇护下一劳永逸地转换为终身机会制或者机会世袭制,进而也就在机会贵族的终身就业状态中失去竞争风险及其这种风险所带来的进取压力。
一旦文化机构的就业者普遍缺乏类似的进取压力,机构功能效率目标以及所必然要求的内在体制活力,当然也就不复存在,而且会导致某一具体文化机构的活力衰减甚至负向度功能障碍,至此也就意味着奥斯特罗姆一向奏效的“活力参与者的假设运用”及其所谓“通常我都会强烈地提倡制度分析不要停留在一种或者仅仅是一种的理论工具来解读人的行为,除非他们愿意将其整个分析限制在他们的职位,并且这些职位乃是能被成功地进行简洁化、竞争化以及全息化的建模”(74),也将会因联姻体制的背景差异而难以施展其阐释威力,亦即新制度主义的任何效益分析方案在这里都缺乏逻辑前提。
实际上,在社会福利的普世性被单位福利的利益排他性所替代的事态里,其进一步的被动结果还在于,福利与就业的直接绑缚导致原本作为社会化的福利被机构边际内的单位人所占有和瓜分,这种占有和瓜分不仅消解了福利本质属性并走向诸如“福利项目,换句话说,因此不能经验其相同的公共支持水平”(75),而且还因为这种消解而使福利的设计效果与设计动机直接悖离,并在这种悖离中成为体制庇护下对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目标的进攻,其社会存在的否定性指向在于制度深层结构中的“按照某种理论,政府中的行政小团体,使得一些人将政府的机构利益嵌合为自身拥有,并且其特殊诉求在于,将这样的边际视为最有价值的空间覆盖”(76)。
很显然,当文化机构处在就业与福利的体制联姻状态,则就业贵族和单位福利制的无限蔓延就具有文化体制的必然性,就必然会使境遇中的具体文化机构在利益雪球和功能钝化中最终成为文化制度结构难以承载的包袱。因此,机构改革的一条重要路径,就是将就业与福利剥离,切除体制联姻的利益粘块,既解除就业贵族的利益分配优先性,使其全方位回归于人力资源管理状态的“对管理中更有效力的人事关系的寻求”(77),同时摧毁单位利益制的存在前提,让一切社会福利都能在公平正义的总体原则下成为普遍性的社会再分配现实,成为与单位和就业完全没有联姻可能的公共利益形态,则一切进入文化机构的就业者就唯有以劳动换取劳动报酬这一正确路径,就一定只能处于诸如标杆、绩效或者指标测量体系等的技术化衡定网络中,钝化、沙漠化乃至雪球现象都将因此而不复存在,因为每个人的命运从此直接取决于他对包袱困境的清晰认识和有效规避。
3.机构运转与权力统置的剥离。至于机构运转与权力统置的剥离,将不仅关涉着在何种程度上解放文化机构的生产力,而且关涉着在何种程度上真正确立中国文化机构的服务目标和社会责任取向。在机构运转与权力统置的功能叠合状态里,权力既不体现为制衡性的管理规程,亦不体现为强制性的技术制度,而是更多地体现为对公共资源权力化垄断的非理性膨胀。
这种权力化垄断的第一个向度是“层级一把手现象”中文化机构内部功能配置的个人统置,其统置后果是人、财、物及运行配置方式向机构领导者的无条件聚集,而无条件聚集也就使得文化机构的主要领导失去管理者角色功能的诸如“以新的设计将人们从传统等级制度锁闭中解脱,而带领他们走向更加循环、弹性和流动的管理系统,那将会带来劳动者的精神松弛并且更加努力地工作”(78),一旦角色功能转换,作为“一把手”领导的管理者就会相应地转换为具体文化机构的极权者,机构资源任其调配,机构人员任其驱使,机构财产任其挥霍,机构运行任其安排,除非外部置换力量或者法律干预力量足以更换机构领导人,否则这一切都将会在合法化假象的包装下成为无法抗拒的严峻事实,而且只要还是类似的制度安排,新的领导人很大程度上也会重新进入角色转换的权力游戏怪圈。
第二个向度是“资源的单位所有制”现象中公共文化资源被文化机构的单位化统置,这种统置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权力逻辑,那就是文化制度框架以权力分置的形式将公共文化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利用的权力委托给具体文化机构,具体文化机构则在边际内将这种分置转换为有限性统置,有限性统置再堂而皇之地彻底更改公共文化资源及其配置的公共属性,并在机构权力形态中转换为单位利益制度的专属资源存量,从而以一种中国特色的方式实证性地回答社会学议题的诸如“怎样使吸引理论解释人们在工作中为什么要加入一个团体?”(79)
由于人们很难在日常性的视知觉层面观察这些隐存状的逻辑,所以公共文化资源被特定文化机构权力化统置的现象就不会引起公众的社会关注,进而也就导致文化机构的机构运转是以一种权力统置的方式进行,即使这样的机构投身于公共文化服务,也至多不过是外在的姿态拟设而非内生性的功能价值目标,所以绝大多数的文化机构,其运行绩效或者运行姿态都更多地服从于文化行政系统的合法化自拟或必要性验证,而不是公共问责和社会监管下公共文化资源公正性与效率性相统一的最大责任实现,因而也就根本不会真正面对技术化精密测值其运行方式和运行效果的诸如“运作测值系统的目标往往非常简明,它们被导向去获取一系列的客观性,譬如提供什么是政府应努力实现的清晰公共陈述,又譬如提供‘清晰的目标感’,再譬如提供不断促进服务的关键”(80)。
毫无疑问,公共文化资源被单位化权力拥有之后,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在制度目标尚且受到威胁,更何谈所谓效率或者公平。因此,要想根本改变文化机构运行效率低下和运行方式自闭的被动局面,要想真正解放大批文化机构的文化生产力,就必须在文化制度创新中的机构改革环节,彻底实现机构运行与权力统置的剥离,既包括对内部权力统置的剥离,亦包括对外部权力统置的剥离,从而使文化机构的运行进入社会授权和社会监管的管理结构框架之中,不但能够有目的地逼近公共管理绩效诉求的“为了不致重复商业式涂抹,公共部门的管理就被冠之以‘公共行政’,表明不一致的原则——通过其自身的一般部门、自身的概念以及自身的职业阶梯来予以实现”(81),而且还能够有计划地逼近公共服务大众诉求的“位于公民权核心的正是这种超越狭隘利益并且认识到共同的社区利益和财富的能力。政府对于促进这种过程并且将这种对话提高到着重关注长期的社区利益能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82)。
总之,这种剥离的最终目的,就是促使所有的文化机构,通过改革来实现其资源共享与功能激活的转型,而转型后的文化机构就将成为高效率的文化服务单位或者文化经营企业,而不是传统的通过权力依附来达到文化资源垄断,并在这种垄断中最大限度地进入单位利益制的怪圈。一句话,最终目的就是根本性地从文化权力走向文化服务。
注释:
① Michael E.Kraft and Scott R.Furlong,Public Policy:Politics,Analysis and Alternatives,CQ Press 2007,P.58.
② Grover Starling,Managing the Public Sector,Harcourt 2002,P.396.
③ Barbara Czarniawska,A Theory of Organizing,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8,P.17.
④ Carol E.B.Choksy,Domesticating Information:Managing Documents Inside the Organization,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6,P.161.
⑤ Rousseau,The Social Contract,in Michael S.Kimmel and Charles Stephen (ed)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Pearson Education,Inc.2004,P.36.
⑥ Jean Hartley,The Innovation Landscape for Public Service Organization,in Jean Hartley,Cam Donaldson,Chris Skelcher and Mike Wallace(ed) ,Managing to Improve Public Servic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P.198.
⑦ Nandish V.Patel,Organization and Systems Design :Theory of Deferred Action,Palgrave Macmillan 2006,P.86.在此,缩略语SEST展开还原为Structure,emergence,space and time,意即机构生存实际上可以通过这些方面的要素量化分析来予以体征 呈现。
⑧ Jenifer Richeson,John F.Dovidio,J.Nicole Shelton and Michelle Hebl,Implications of Ingroup-Outgroup Membership for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s,in Ursula Hess and Pierre Philippot (ed),Group Dynamics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20.
⑨ Jeffrey L.Pressman and Aaron Wildavsky,Implementation,in Jay M.Shafritz and Albert C.Hyde(ed),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arcourt 1997,P.354.
⑩ Weber,Bureaucracy,in Michael S.Kimmel and Charles Stephen (ed)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Pearson Education,Inc.2004,P.215.
(11) D.C.Grover,Polici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Mohit Publications 2007,P.38.
(12) J.Kenneth Benson and Byung-Soo Kim,Institutionalism and Capitalism:A Diatectical and Historical Contingency Approach,in Harland Prechel(ed),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08,P.79.
(13) Weber,The Meaning of Discipling,in Michael S.Kimmel and Charles Stephen(ed)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Pearson Education,Inc.2004,P.238.
(14) 埃文·M·伯曼等著,萧鸣政译《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15) Tony Fitzpatrick,New Theories of Welfare,Palgrave Macmillan 2005,P.29.
(16) Colin Hay,Political Analysis,Palgrave 2002,P.173.
(17) Jan Jonker,Michel Van Pijkeren and Jacob Eskildsen,Trying to Understanding Management Models :An Explorative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Functionality of Management Models,in Jan Jonke and Jacob Eskildsen(ed) ,Management Models for the Future,Springer,2009,P.192.
(18) Richard M.Burton,Gerardine DeSanctis and Brge Obel,Organi zational Design :A Step-By-Step Approac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61.
(19) Pierre Philippot and Ursula Hess,Introduction:The Tale I Read on Your Face Depends on Who I Believe You Are:Intrudusing How Social Factors Might Influence the Decoder's Interpretation of Facial Expression,in Ursula Hess and Pierre Pbilippot (ed) ,Group Dynamics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P.1.
(20) Adriaan T.Peperzak,Intersubjectivity and Community,in Kevin Thompson and Lester Embree (ed),Phenomenology of the Political,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0,P.63.
(21) Willian A.Haviland,Human Evolution and Prohistory,Wadsworth 2003,P.293.
(22) Carol E.Harrison,Bourgeois Citizenship and the Practice of Asso ciation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in Graeme Morton,Boudien de Vries and R.J.Morris (ed),Civil Society,Associations and Urban Places:Class,Nation and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6,P.177.
(23) 马克·布洛赫著,张绪山译《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78页。
(24) Greg Young,Speak,Culture! -Culture in Planning' s Past,Present and Future,in Javier Monclús and Manuel Guàrdia (ed) ,Culture,Urbanism and Planning,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6,P.45.
(25) Hermann Haken,Information and Slf-Organization :A Macroscopic Approach to Complex Systems,Springer 2006,P.11.
(26) Anita Kanges,Cultural Policy in Finland,in Peter Duelund(ed) ,The Nordic Cultural Model,Nordic Cultural Institute 2003,P.97.
(27) Tor Larson,Cultural Polity in Sweden,in Peter Duelund (ed) ,The Nordic Cultural Model,Nordic Cultural Institute 2003,P.204.
(28) Rachael Dunlop,Funding from the Private Sector,in Sara Selwood(ed),The UK Cultural Sector:Profile and Policy Issues,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2001,P.166.
(29) Weber,Bureancrary,in Michael S.Kimmel and Charles Stephen (ed),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Pearson Education,Inc.2004,P.217.
(30) Stphane Ngo Ma and Michel Qur ,Innovative Behaviour,in Richard Arena and Christian Longhi (ed),Markets and Organization,Springer,1998,P.312.
(31) Paul M.Collier,Performativity,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in Jean Hartley,Cam Donaldson,Chris Skelcher and Mike Wallace (ed) ,Managing to Improve Public Servic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P.46.
(32) Warren Bennis,The Secrets of Great Groups,in Frances Hesselbein and Paul M.Cohen (ed),Leader to Leader,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9,P.320.
(33) Richard Templar,The Rules of Management:A Irrerent Guide for the Leader,Innovator,Diplomat,Politician,Therapist,Warrior and Saint in Everyone,Pearson Education,Inc.2005,P.25.
(34) J.Kenneth Benson and Byung-Soo Kim,Institutionalism And Capitalism:A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Contingency Approach,in Harland Prechel,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08,P.67.
(35) Stephen R.Covery,The Habits of Effectives Organizations,in Frances Hesselbein and Paul M.Cohen (ed),Leader To Leader,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9,P.216.
(36) Jaime Saruski and Gerado Mosquera,The Cultural Policy Of Cuba,Unesco 1979,P.31.
(37) Kate Manton,The Performing Arts,in Sara Selwood (ed) ,The UK Cultural Sector:Profile And Policy Issues,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2001,P.27.
(38) George Boyne,Public Service Failure And Turnaround:Towards A Contingency Model,in Jean Hartley,Cam Donaldson,Chris Skelcher and Mick Wallace(ed) ,Managing To Improve Public Servi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P.236.
(39) Orit Gadiesh and Scott Olivet,Designing For Implementability,in Frances Hesselbein,Marshall Goldsmith and Richard Beckhand(e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Future,Jossey-Bass Publishers,1997,P.56.
(40) Michael E.Kraft and Scott R.Furlong,Public Policy:Politics,A nalysis And Alternatives,CQ Press 2007,P.59.
(41) 丹尼斯·朗著,陆震纶译《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42) Barbara Czarniawska,A Theory Of Organizing,Edward Elgar,2008,P.51.
(43) Peter F.Drncker,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Inc.1999 ,P.164.
(44) Richard M.Burton,Gerardine DeSanetis and Brge Obel,Organizational Design :A Step-By-Step Approac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45.
(45) D.C.Grover,Polici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Mohit Publications 2007,P.218.
(46) Grover Starling,Managing the Public Sector,Harcourt 2002,P.155.
(47) Timothy E.Cook,Governing With The News:The News Media As A Political Institu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P.86.
(48) Roderick P.Hart,Citizen Discours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A Survey,in W.Lance Bennett and Robert M.Entman(ed),Mediated Politics: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 Of Dem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407.
(49) Raymond A.Nee,John R.Hollenbeck,Barry Gerhart and Patrick M.Wright(ed),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The Me Graw-Hill Companies,Inc.2006,P.153.
(50) Nicholas Henry,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Affairs,Pearson Education,Inc.2004,P.291.
(51) Marco Weiss,Efficient Organizational Design:Balancing Incentive and Power,Palgrave Macmillan 2007,P.192.
(52) Frank J.Thompson,Classics of Public Personnel Policy,Wadsworth,2003,P.353.
(53) 埃文·M·伯曼、詹姆斯·S·鲍曼、乔纳森P·韦斯特、蒙哥马利·范·沃特著,萧鸣政译《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8页。
(54) A.Kakabadse,N.Kakabadse and A.kouzmin,Balancing the-Democratic Project:The Fouth(p43) Organ,in Nada Kakabadse and Andrew Kakabadse (ed),Governance,Strategy and Policy:Seven Critical Essays,Palgrave Macmillan 2006,P.49.
(55) Joel S.Migdal and Klaus Schlichte,Rethinking the State,in Klaus Schlichte(ed),The Dynamics of State:The Formation and Crises of State Domination,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5,P.11.
(56) Martin J.Eppler,Managing Information Quality:Increasing the Value of Information in Knowledge-intensive Products and Processes,Springer 2006,P.85.
(57) Richard M.Burton,Gerardine DeSanctis and Brge Obel,Organizational Design :A Step-By-Step Approac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61.
(58) Barbara Czrniawska,A Theory of Organizing,Edward Elgar,2008,P.17.
(59) Thijs Ten Raa,The Economics of Input-Output Analysi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P.11.
(60) lira Me Guigan,Rethinking Cultural Policy,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4,P.99.
(61) Julia S.O Connor and Gillian Robinson,Liberalism,Citizenship and the Welfare State,in Wim Van Oorschot,Michaei Opielka and Birgit Pfau-Effinger (ed) Culture and Welfare State:Values and Social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dward Elgar 2008,P.29.
(62) Scott Lash and Celia Lury,Global Culture Industry:The Mediation of Things,Polity Press 2007,P.153.
(63) Nandish V.Patel,Organization and Systems Design :Theory of Deferred Action,Palgrave Macmillan 2006,P.196.
(64) Josef Langer,Niksa,Alfirevic and Jurica Pavicic,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Transition Societies,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5,P.14.
(65) Nicholas Henry,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Affairs,Pearson Education,Inc.2004,P.139.
(66) Julia S.O'Connor and Gillian Robinson,Liberalism,Citizenship and the Welfare State,in Wim Van Oorschot,Michaei Opielka and Birgit Pfau-Effinger(ed),Culture and Welfare State:Value and Social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8,P.37.
(67) Robert D.Putnam,The Prosperous Community: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in Elinor Ostrom and T.K.Ahn (ed),Foundations of Social Capital,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3,P.529.
(68) Richard M.Burton,Gerardine DeSanctis and B rge Obel,Organizational Design:A Step-By-Step Approac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101.
(69) Marco Weiss,Efficient Organizational Design :Balancing Incentives and Power,Palgrave Macmillan 2007,P.48.
(70) Alastair lain Johnston,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P.197.
(71) Angela Mc Robbie,Clubs To Companies,in John Hartley (ed),Creative Industries,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P.37.
(72) Bj rn Hvinden,Cultures of Activation:The Shif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Maintenance And Employment Promotion In The Nordic Context,in Wim Van Oorschot,Michaei Opielka and Birgit Pfau-Effinger(ed) ,Culture and Welfare State:Values and Social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8,P.209.
(73) Samuel Krislov,The Negro and the Federal Service in an Era of Change,in Frank J.Thompson(ed) ,Classics of Public Personnel Policy,Wadsworth 2003,P.283.
(74) Elinor Ostrom,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P.103.
(75) Michael E.Kraft and Scott R.Furlong,Public Policy:Politics,Analysis and Alternatives,CQ Press 2007,P.287.
(76) Joel S.Migdal and Klaus Schichte,Rethink the State,in Klaus Schlichte(ed),The Dynamics of States:The Formation and Crises of State Domination,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5,P.4.
(77) D.C.Grover,Polici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Mohit Publications 2007,P.87.
(78) Frances Hesselbein,The “how to Be”Leader,in Frances Hesselbein,Marshall Goldsmith and Richard Beckhard(ed),The Leader of the Future:New Visions,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for the Next Era,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6,P.122.
(79) Scott A.Myers and Carolyn M.Anderson,The Fundamentals of Small Group Communication,Sage Publications,Inc.2008,P.27.
(80) Barbara Townley,Performance Measurement Systems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Rationales and Rationlities,in Jean Hartley,Cam Donaldson,Chris Skelcher and Mike Wallance(ed),Managing to Improve Public Servic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P.134.
(81) Peter F.Drucker,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th Century,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Inc.1999,P.7.
(82) 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著,丁煌译《新公共服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