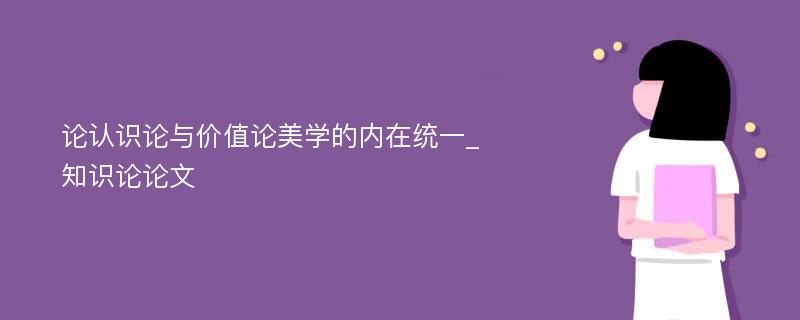
论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的内在统一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美学论文,知识论文,统一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在这里提出的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是一种根据知识论与价值论统一原则生成的美学。知识论与价值论作为哲学术语,是对应于它们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进行审思和评判的系统观念,这种观念在现有美学体系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在我看来,美学体系中的知识论与价值论观念具有三种结构关系:一是对立关系;二是交叉融摄关系;三是统一关系。只有第三种结构关系的美学才称得上知识论与价值论的美学。知识论与价值论对立是古典美学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在逻辑本体的设定中体现为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知识论与价值论交叉融摄是近现代美学的基本特征,其表现是体系构成中知识论或价值论某一方对另一方的融摄吸收,从而它们的内在结构关系不能视为是统一的,而是分离的。由于这种分离,近现代美学不是流于价值承诺的知识缺位,就是偏于堆砌知识的价值沉沦。因此,我用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这种新提法,来表达我对21世纪美学逻辑立法和体系更新的思考,目的有两个,一是以知识论与价值论统一法则对既有美学体系进行审思和梳理;二是把这种法则运用于美学体系的实际建构。无疑,两个任务都十分庞大而艰巨,本文所能做的只是就这一法则的核心问题——知识论与价值论的内在统一性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
一、价值承诺与知识还原的统一
知识论与价值论的美学,首先应具有价值承诺与知识还原的统一性。所谓价值承诺指整个美学体系对人而言,具有超拔现实、表达理想、实现终极归属的意义。价值承诺是在价值论审思、权衡下做出的,是价值论的实质性内容和基本构成。所谓知识还原指价值承诺的兑现,是用知识形式完成的。知识还原是知识论对价值论的转换,具有知识形式的现实性和有效性。知识论与价值论统一是美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这种统一建立在审美价值意义的承诺之上。从审美发展史来看,知识论与价值论的割裂造成很多弊端。例如,19世纪以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价值论争锋一直对峙不下,使得以价值底蕴做支撑的美学体系也分化为两种截然对立的路线,一种是主张“本质主义、客观主义、理性主义、实体主义和进步主义思维,其本质是对生活或现实的简化、遗忘和抽象”(注:李文阁:《生成性思维: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另一种是主张从“社会文化批判的立场,对社会文化中的支配和不平等现象特别关注,以及对新的理想的可能性的探讨”(注: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揭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生存、发展活动及其结果的意义”(注:熊在高:《“价值论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载《哲学动态》2002年第1期。)。不管是倡导普遍的虚幻本质,还是宣扬“批判”的人本价值,这两条路线最终都沉溺于传统价值学说的“乌托邦幻想”,把价值误导到与现实世界、人生相对立的永不通达之路。而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则认为,价值本体是人的意愿所归,这种意愿既不能独断为普遍的、理性的抽象实体,也不能臆想为可通过“工具理性”获得的“幻景”。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所说的价值的承诺,乃是超拔现实中导引出的一种未来生存。这种未来生存不是虚幻的,它通过知识论的转换、阐释,可具化为可操作、可运用的知识形式。怀特海指出,我们这个世界应该提倡能够综合所有条件(人的、技术的、环境的)以“产生伟大的社会”(注:[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3页。)的价值。这种价值是人的智慧和审美创造力最充分的体现,是人的高尚情感、坚强意志的活的塑造,是哲学、宗教、道德等人文理想与宇宙法则、自然规律和物质构因最完美的和谐。如此全面、现实而又体现人的健康意志的价值目标,是对有限现实的真正超拔,这就是价值承诺的含义。这种承诺把幸福概念赐予人的审美情感,使他们在美化的生活境界和艺术化的生存中感受到无比的愉悦。但是,传统美学,以及近现代美学并没有这样的价值承诺。它们通常视知识论与价值论为对立的两极,总是习惯于把现实划在知识论一极,认为现实是假的、丑的和恶的,而把理想划在价值论一极,认为理想是真的、善的和美的。这种极端化的思维趋向,使人们错误地理解审美,错误地把人的价值理解为独立于现实之外、能够用所谓意识中的否定性体验代替现实的东西。在我国当代美学中,也存在这种倾向,习惯于用“超越”、“否定”这类字眼表达美学的价值论本质,一些看似新的美学阐释往往用陈旧的“二元对立”模式表述出来,如潘知常认为当代美学“问题的关键在于阐释框架从知识论向生存论的转换”,“审美活动不存在什么普遍、抽象、永恒、本质……它是人类生命活动的自由表现。与此相应,审美活动也就不是越符合某种普遍、抽象、永恒、本质的就越美,而是越是成功地揭示了在场与不在场的统一,越是成功地揭示了事物之间的系统质、越是丰富地显现了这空无世界的无穷意味,越是极大地展现了想像的空间、越是令人回味无穷,就越美,就越是充盈着一种‘无名’之美、‘不可名状’之美”(注:潘知常:《超越知识框架:美学提问方式的转换——关于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载《思想战线》2002年第5期。)。肖鹰也认为:“现代化的双重性使人类的现代生存面临着理性与自由、个体与整体、技术与生命、精神与物质等多重互相悖反的矛盾。面对这些矛盾,美学始终站在人类自我存在的立场上,从人的内在精神发展和完善的需要出发,开拓和表达现代人文精神。”(注:肖鹰:《论美学的现代发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两段引文无疑都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当代美学的症结,但潘知常把审美活动理解为“自由活动”,理解为成功地“揭示”、“显现”这个世界的“系统质”和“无穷意味”——这“不可名状”的意味、本质,不仍然是一种“拈花微笑”般含糊抽象的本质吗?把价值与知识对立起来,实质上等于把价值放逐在现实之外,等于又回到了原本要“否定”的抽象价值方面。同理,肖鹰让现代审美价值奠基在对现代化双刃的悖反矛盾的消除上,实际上也是潜意识中在向古典的二元论价值结构靠拢。应该看到,美学观念对现代化矛盾的解决,是不能单靠所谓人文(自我)精神的完善就能实现的,恰恰是在审美创造中自我与整个宇宙、现实的联结,才把传统和近现代工具理性造成的矛盾给消解了,同时人也从有限境遇中超拔出来了,进入了自由、愉悦而且真实的审美境遇。
因此,价值承诺对于人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人存在的意义,也是与人的存在密切关联的宇宙、环境和一切相关条件存在的意义。但价值承诺只是一种意愿,它的兑现还要靠知识,靠知识的现实还原来实现。对人而言,知识既是生命的陈述和行为力量,也是智慧的过程和结晶。知识是真实的。真实的知识说明价值承诺并非虚妄。这就是知识还原的真义。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认为知识还原与价值承诺是统一的,甚至是一体的,我们只不过为便于分析略加分别而已。在知识论意义上,审美承诺的价值总体以知识存在的方式得到具化,或说显现和呈现。视知识论与价值论为对立的传统美学则认为,审美价值是一种“不可言说”之“道”,因此“具化”、“显现”是不完善的,只有用精神、用智慧来把捉才能领略到它的韵味。传统美学还认为知识所代表的是逻各斯理性传统,因此知识理性与审美截然对立。但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则认为,老庄美学之所以绵延千古,确是因为倡导了富有特殊韵致的美学观念。但这也只是对留存在人们内心的审美体验的描述,以为它是不可尽传、进而不可言传的。其实若真的停留于此,今天还会有老庄美学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老子·五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六章》)老子因喻设道,道喻合一,道被比喻的方式知识化了。庄子言“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第六》),从默冥玄会出发,庄子视道为对“自然”省悟所得,从而“道”性不可“受、见”,并非意味“道”体不可得传,所以他主张“体道”,说“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庄子·达生》)。《养生主》中庄子用“庖丁解牛”的寓言表明人与物、心与手、技与道的统一才是获致“道”的佳境。因此,纵然老庄在阐明价值本体观时,是与知识的本性对立言明的,但在讲“道”如何体悟、获致时,又是用审美的知识论规律,把价值转换为知识形式来看的。世界的物并无僵化如一的体性,事物的价值就在它的持续和转化之中。因此,视知识为理性的、没有什么审美性可言的观点,完全是站不住脚的。诚然,我们知道确有理性的知识系统,这种理性的所谓知识系统也不能视为美的。但这与我们所言的知识系统和知识形式不同,我们所讲的知识形式是结合审美的知识论与价值论而成的知识形态,这种知识形态展现价值,使意义现实化,因此它是审美的知识形式。换言之,审美知识形态对价值的转换乃是一种对审美价值的知识还原,价值只有在这种状态才能“为其所是”,否则就是僵死的、抽象的、枯寂的存在。对于知识还原,胡塞尔、海德格尔曾有过深入的思考。胡塞尔所主张的“直观”的原初给予性,就是用科学的知识论对自然主义知识论和心理学知识论的反动,因为“直观”中的知识具有“本质(价值)”的原初给予性,因此这种知识是现象性的,又是本质性的。海德格尔则指出“澄明”价值就是“去蔽”。在他看来,价值本然地在那里,你所要做的只是在作品中“建立一个世界”,并使这作品回到大地,从而作品在大地中说话,价值以它特有的知识形式获得“敞亮”。他说:“真理把自身设入在作品中,真理唯作为在世界与大地的对抗中的澄明与遮蔽的争执而现身。真理作为这种世界与大地的争执被置入作品中。”(注: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83页。)这里海德格尔强调的世界与大地的对抗,其实就是价值被遮蔽,还没有被现象化,而一旦被现象化了,就意味着“世界和大地的统一成立了”(注: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见《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可见,海德格尔所谓的“澄明”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知识的还原与呈现,由此,审美价值的承诺得到真实的兑现。
二、隐与显、有与无的统一
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的价值承诺体现为对现实的超拔,当这种承诺以知识形式呈现时,就意味着实现了价值承诺与知识支撑的统一,我们说这种统一是整体的,也是构成性的。构成性的知识论与价值论统一,是一种隐与显、有与无的统一。
首先,从审美价值构成来看,超拔有限是一种“有”,也是一种“无”。“有”说的是可能性目的属于一种未来的真实,因转化为知识形态而被人们所信赖。“无”则指超拔的否定性意蕴。否定就是扬弃,就是把人生和宇宙、自然和社会中一切负面的价值排除掉。古典美学把“有”与“无”理解成思性层面的东西,并且经常在审美体验中把“有”的一面与庸俗、局限、束缚、烦恼等等同起来,把“无”与无限、超越、解脱视为同意。结果价值构成中惟有“无”的意义在场,“无”成为生命价值的终极极限。例如,康德把审美价值建立在排除客观性的主观鉴赏上面。这种鉴赏与经验性知识无关,它的普遍性被设定为由先验的“共同感”所给予。“一个超验原理,只能是反省着的判断力自己给自己作为规律的东西。”(注: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页。)康德用抽象的“有”规定审美价值,由于主体的反省仍然难以确定,那种先验的共同感就只能是一种假定性的心理现象。黑格尔比它具体一些,认定审美价值就是一种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就是绝对的“有”,是对一切有限的超越。应该说,在西方这两位倡导“有”的价值论阐述中,蕴含着深刻的推崇人的独立性、自为性的价值意识,但那种形而上的“有”悬浮空中,远离现实,带有很大的虚幻性和欺骗性。与西方美学相反,中国古典美学则在“无”上做文章。老庄从宇宙论出发,认为“道”生于有无之间,其中“无”又是“有”的本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一章》)庄子把“无”视为道德价值的至高境界。《庄子·则阳》篇云:“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无不为”,至魏晋王弼则以无为本,主张“穷极虚无,得道之常”,“无之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残。用之于心,则虎兕无所投其角,兵戈无所容其锋刃”(注:楼宇烈校注:《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页。)。可见,“无”在中国美学的价值论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但这种“无”并非真无,仍然有一个“无”在,也就是说“否定”的价值意义是绝对的。由于把“无”绝对化,“有”成了否定和超越的对象,审美的终极就体现为一种人格的高蹈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虚化境界。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对“有”、“无”的设定很值得我们反思,因为他们理解的这个“有”与“无”,体现的是一种审美绝对理念。绝对理念的价值意义在于否定人生的有限性,但因为本体设定中排除的是与绝对审美理念相对的东西,实质上等于倡导了蹈向虚无伦理的审美价值,否定了现实世界和与人的创造相关的一切审美活动的价值意义,这显然是有悖于我们今天对审美价值的基本理解的。
为此,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主张不能确证审美价值为“有”或“无”的任一方面,偏于“有”或“无”任何一方,都会带来虚化审美价值现实性的风险。只有使“有”、“无”呈现出和谐一致的价值论结构,审美价值才凸现它积极的有效意义。那么,怎样才算“有”与“无”相统一的价值构成呢?说明这点涉及转换这个概念。一方面,价值是在“有”与“无”的中际发生质的变换的,“有无统一”是强化价值结构内在张力的体现;另一方面,转换不仅是价值构成内部的事情,也是价值构成之外知识构成要做的事情,因此把价值构成以知识构成转换出来,才算达成了审美价值最终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美学也是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认为知识理性不美,因而美学不可能是知识性的。它们无视审美形式、审美体验、审美理念所包含的审美逻辑和知识系统,把美仅仅看作飘忽的影像、流逝的风景;另一个极端是认为美学就是规律,就是客观事物的存在,就是理念实体。这种观念认为美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是统一对应的关系,因而世界上有什么,就会有什么样的美。美不是感受,而是认知;美不是体验,而是本质对象化。这种观念为了使实体性的美学知识与现有其他认知性知识建立起逻辑联系,也往往用美是关于事物特殊性的知识,或关于普遍性的知识,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知识等不同回答来完善美学知识的构成系统。然而,如果问这种美学知识的价值是什么,它们是否反映了人的审美的内在超越要求,回答就莫知所以然了。如上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就在美的知识是怎样一种“有”上争论不休,蔡仪的“美是典型”所要阐发的不过是“普遍规律与个性特征统一”这样一种认知法则;吕荧的“美是人的社会意识”,“美是一种观念”所阐发的不过是“美的感觉和美的概念、观念是统一的”(注:吕荧:《美是什么》,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1953-1957》(第1集),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278页。)这样一种认知结论;李泽厚所谓“美是社会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注:李泽厚:《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评朱光潜、蔡仪的美学观》,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1953-1957》(第1集),第266页。)和“美是自由的形式”(注: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第1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66页。)所阐发的不过是“社会性”或“实践性”的形象化这样一种认识。机械地把美学知识理解为确定的“有”只能形成直观浮浅的结论,因此不管你是否在界定时把审美知识与一般知识相区别,只要是确定“美就是那个”,这美立刻就被覆盖了、遮蔽了。所以,如果一定要比较一下,强调美是“有”远不如主张美是“无”更显出理论的深度。在这方面当代学者吴炫可谓独具慧眼,他的“本体性否定”和“局限性否定”概念包含了“批判与创造的统一”(注:吴炫:《论否定主义美学的三个原理——兼谈对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超越》,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7期。)和对现有美学知识种种“缺憾”的审思,但吴炫并没有从无转换为“有与无的统一”,就是说还缺乏知识论的支撑这一环节,原因是“否定”历来是一种过程的描述性概念,黑格尔是这样用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阿多诺等也是这样用的,最成功的使用否定概念是佛教美学中的“遮诠”式表述,这种表述用“否定此,也否定彼,更否定彼此之外的彼与此或彼与此之内的此与彼”来说明空性之如,吴炫的否定美学观则是把否定作为本体概念用的,这与“遮诠”的逻辑相违,也与“表诠”的逻辑相违,因此我们从他的价值否定不能过渡到价值兑现的知识还原。刘士林在这方面也有深入思考,他通过先验批判试图掘出非主流美学的价值论地位,但他由“否定”、“批判”过渡到“图式”概念的本体设定,就如同刚从一个陷阱逃出来又进入另一个布阵,这是犯了对价值论进行错误的知识论解读的缘故。
因此,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坚持从一种中道原则来处理“有”与“无”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认为知识构成与价值构成在美学体系中互为隐显,是有与无的统一;另一方面认为价值构成与知识构成的存在形式也是有与无的统一。有关价值构成的有与无之统一前面说过,至于知识构成的有与无的统一似乎更好理解。首先,美学的形态都借助符号而得其存在,符号本质索绪尔从知识理性出发确定为能指与所指的统一,而在东方美学看来,符号是一种假名,是一种“幻象”。道家美学“水中月、镜中花”的剔透玲珑;禅宗美学的不以言诠,“即心即佛”;佛教美学的不住色相,空性真如,都表明符号的本质既非实体,也非虚无。这比较符合审美符号的性质,但审美符号不能停留于假名、空如阶段,它的在场应该是一种价值形态的转换,即从价值有无的中际转换到知识有无的中际。知识有无的中际是这样一种形态,一方面审美符号把它所表达的内容都幻化为“无”,给人以价值超拔的体验;另一方面,价值的本质不仅在于超拔现实,还在于除幻破障,让整个世界与人进入一种价值实现的境界,因此符号的在场同时又喻示着“有”,喻示着可以通过非常系统的知识环节,为人有效地掌握,进而与实际世界发生关联。在古典美学和近现代美学中,价值设定的极端化造成主体价值、客体价值以及超现实的价值,都似乎与现在世界对立才显出超越意义,而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却糅合既往美学的合理成分,把知识形式理解为超拔现实后知识形式的重建,从而自然是有规律的,社会是有规律的,人生也是有规律的,但这些规律都不与审美价值等同,也并不矛盾,因为审美通过符号来利用这些规律,把它们转化来用以体现宇宙的、事物的以及人文的总体价值。同样,知识形式的重建也是价值的呈现,主体的自我觉醒、事物发展的意义、宇宙生态的和谐,这些价值都是存在的,但它们在价值形态的有无中际并不能成为现实的呈现,只有使它们到知识形态的有无中际,人才体验到自由,事物才具有意义,宇宙生态才实现一种平衡。这是一种当代文明的趋向,也是信息时代和技术时代对美学的呼唤,只有在这样一种美学的构架中,人才能够体现既有其自觉自由的意志、又不把自己作为宇宙的中心独断妄为,人的自身与他的世界、环境,人的目的与他的手段始终统一,科学与人文的全部价值和知识效用得到完美的发挥。
三、知识原创与价值伸发的统一
如前所述,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既有超拔性,又具现实性,是价值承诺与知识兑现的统一,根据这一基本的法则,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主张知识的原创性和价值的伸发性的统一。如果说承诺与还原统一的原则是对美学体系根本性质的阐明,有与无统一原则是对美学构成原理的阐明,那么知识原创与价值伸发统一的原则则是对美学归属性的阐明。归属性是美学的价值效用问题,也是美学的知识运用问题,两者都对美学非常重要,缺一不可。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对归属性问题阐发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把归属性定位为价值论与知识论统一的实践。仅有价值的实践只是思性的、经验的,在根本质性上与现实世界和人的审美才能的有效发挥脱节;仅有知识的实践而无价值的引导,这种实践是缺少智慧、没有美感生气,因而也是僵硬的和刻板的。知识论与价值论统一起来的实践,则依据知识论与价值论的审思、批判、幻化、具象功能,解决人和世界的美学根本问题——意愿趋向(审美信仰)与行动趋向(审美经验)的统一问题,因此它是对归属性问题的真正解决。
审美实践是一种特殊实践,也是一种普泛的,可以推广到生活、艺术、生产等方方面面中去的实践。作为特殊实践是说对审美价值的伸发:审美价值不能是原创的。主观主义美学相信价值可由人的臆想、梦幻随意创造,这是荒唐的。倘若如此,我们无时不在臆想之中,也天天都有梦,我们既然每时都在创造审美的价值,那剩下来的工作只要对梦和臆想进行分析归类就可以了,不用做其他的事情了。但审美价值也不是不可生成的。客观主义美学认为审美价值存在于永恒如一的客观观念之中,人所要做的只是发现它们,让它们由自在而自为。这同样是错误的看法。如果那样看,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何由体现?审美体验中刹那的精神升华何由解释?只能理解为神灵附体了。因此,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认为,价值不是人创造的,只能是伸发的——知识是人原创的,价值是在知识创造过程中伸发出来的。审美实践是知识原创与价值伸发的统一。
知识的原创是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的内在要求。因为知识论对价值论的转换既不能完全按照常规知识的法则生成,也不能按照价值的意义法则生成,它只能按照审美知识的特性更新、变异。审美知识具有同价值构成互为依托和超拔物质世界一般知识形态的双重性质。就前一方面来说,价值转换为知识在于是否能找到承载它的知识语言,只有在知识语言的确是用知识的方式而不是价值阐述的方式表达,并且传达了价值的意蕴时,才可说这种知识是原创的。因此,同样的价值构成倘若用不同的知识语言恰切表述,他们就都是原创的。例如,原始宗教的宇宙起源说本着一种朴素的肉体生命的价值观念被创造出来,这种观念相信宇宙具有像人一样的机体和魂灵,于是在世界不同地区都有所谓肉体地形学的学说。印度《梨俱吠陀》(X.90)描写普鲁什的肉体被分割后产生各种宇宙现象和社会集团,嘴里产生婆罗门,手——士兵,眼睛——太阳,脑袋——天空,脚——大地等。巴赫金指出基督教德国神话中亚当身体也由八个部分组成:肉来自土地,骨骼来自石头,血液来自海洋,头发来自云彩等等(注: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民间文化》中自注。《巴赫金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408页。)。中国也有类似的“混沌”无面目到盘古凿七窍而死之说。可见,价值构成必须转化为知识才能把人们的欲望、意志和种种内心的骚动凝化于现实冲动之中。但审美知识不能等同于一般知识,因为一般知识在古代多指技巧、技艺性的原理,是对事物现象反复感知形成的认识,一般被认为并不包含更多的道德与审美价值内容。为此,古代的价值就从一般的知识中超越出来,成为一种诗化的审美表达形态。在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时代,情况变得复杂起来,系统科学成为知识生成的背景;同时生存、环境的符号化、文化化使人的价值体验和价值观念更为细致和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也变异具有了双重的价值功能,即它既可以成为压抑人性的工具理性,服务于非人道、非公益的目的,如非正义战争、商业欺诈、信息黑客等;也可以成为健康价值的载体,宏扬高尚道德的使者,和培植审美心灵的创造性途径。于是,审美知识努力完善自身的存在形式,在按照知识论规律生成自身时,努力与一般科学知识相区别,以承载人性、表达健康的价值理念,并与世界、环境和一切存在之物的本然价值相吻合,对生活、艺术、工业等进行美化设计,为内心愿望安排文明的宣泄通道,最终使人的目的在现实中获得完美的审美呈现。
知识原创并不排斥知识复制的意义。古典时期的一般知识多是劳动者通过熟练操作产生出来,而审美(知识)多为知识分子冥思独想的产物。从而,孤独的知识分子和从事紧张劳动的人,他们价值观念的对立也体现在如何处理知识形式上。对普通劳动者来说,一般知识的重复只是事物因果联系的认知积累,不具备多少审美意义;对知识分子来说,哲学、宗教、艺术这些知识形式是特权利益和身份优越的证明,为此他们有意反对知识向普通阶层传播,反对知识的复制。近现代美学情况有了改变,复制与原创参半运行,手工制作的精美让人惊叹不已,工艺生产的批量化使不同产品具有相像的外观类型,因此服务于市场化的目的,复制也被认可,但人们在处理高价值含量的产品时,还是希望它们是原创性的体现,而不是什么复制品。
当代美学的知识形式,经过知识论观念的不断权衡、批判而展现出来,因此,知识原创应成为美学生成的主导趋向,但我们并不简单地反对复制,因为复制并不是知识存在的本质问题,充其量只是以某类型存在表达某类型价值观念,易造成审美价值的模式化、机械化而已。但我们别忘记,更重要的是审美价值的转换,如何把价值理想的超拔意义与生活、环境等关联起来。如果确有充分体现当代审美价值意蕴的作品,即使是复制的,也能在现实时空中起到一定作用。我们反对的是因复制而对知识原创性的有意削弱。这就要求我们随时调整自己与实际生活、事物存在的关系,以免被大量现实复制品和繁富的功利需求消解了内在的动机、理想,钝化了对环境美化的愿望。
就是在这样一种实践方式中,审美价值得到了伸发。审美价值的伸发成为与知识创造结合起来的切实的伸发。当代美学对于这两者的结合是不尽人意的。例如,实践美学看到了创造生成价值的意义,因而把社会实践视为审美的逻辑本体,这是深刻的。但实践美学把实践本体与审美本体混淆起来,以致审美实践与生活实践的区别只能由预置的普遍本质所规定,给人虚幻不实之感。实质上是知识的创造生成了价值。在知识未形成之前,审美价值酝酿于愿望中,只有冲动的意志而无具体的样态。只有知识形式确定了,审美价值才赖此运行,犹火借薪传,薪愈多燃烧得愈猛烈。其次,审美价值的伸发是其趋向性超拔特征和知识现实性特征的结合。后实践美学对此也不能正确理解。后实践美学看到了“自由、生命、超越”对人的价值意义,认为“自由、超越”是对工具理性的解脱,是人格完善的体现,这是对的。但他们就超越而论超越,离开审美的现实归属性来谈“超越”,等于否定了实践的现实效力。特别在信息和技术时代,更不能一厢情愿地谈论超越。所以我宁愿把超越这个词称为“超拔”,“超拔”说明价值论的基点虽在知识论之上,但“超拔”也是知识形式对现实的超拔,这样就赋予了价值论以现实性的可能。从而人既能以价值超拔体现审美的内在觉醒程度,也能以知识形式的外化体现价值超拔的文明化程度。越是对价值的呈现趋向健康和完美,价值底蕴也就越是伸发到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倡导审美价值的合理效用,这对当代美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人类审美发展史上,历来对价值实效性的倡导,都受到保守的与激进的双重攻击。如苏格拉底“美是有用的”的观点就受到理性美学和保守的知识权威与势力的激烈反对,苏格拉底也终以“诡辩”恶名而遭受不幸。在我国,近几十年来,倡导价值论的主张愈来愈引起重视,但总体上对价值实效性没有充分肯定,究其原因,一是受到了社会本质普遍论的抑制,二是受到生命超越本质论的抑制。这两种观念都以现实平庸和对人性束缚为由,极力推崇理想性价值,结果把审美价值从现实里驱逐了。因此,我写本文的目的,就是想澄清上述错误认识,以实现在生活、艺术和环境创造层面对知识论与和价值论不统一观念的消除。总之,知识论与价值论在美学中是统一的,知识论与价值论美学的高尚的超拔意识和现实性创造精神,应该能够成为21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合理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