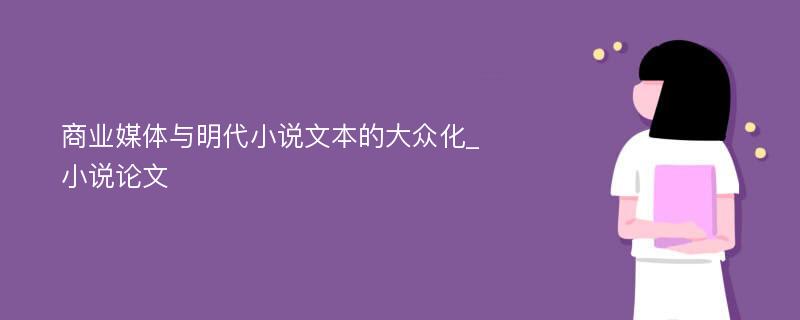
商业媒介与明代小说文本的大众化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媒介论文,文本论文,商业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物质的世界里,人类依靠物质而生存,使用物质手段改造环境,以此观察文学,文学便表现为因某种社会需要而产生、依靠特定物质手段而传播的事物。文学的内容往往反映了人们的社会需求,而文学的形式则是关于传播的各种物质因素的凝结。小说,尤其以文本的形式, 能够在大众中传播、被大众所接受,特别依赖物质条件的成熟和传播环境的形成。
提及明代小说,或称其“通俗小说”、或称其“市民文学”、或称其“大众文学”,种种称谓意味着明代小说确乎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考虑到小说文本传播的实现需要更高的物质成本,研究者多将小说的这种“通俗化”繁荣局面归功于小说的口头说唱传播和戏曲改编传播;而对于明代通俗小说的文本传播,是否达到大众化程度表示怀疑。[1] 通俗小说以印本大量行世始于明代。[2] 明代通俗小说是商业印刷文化的产物,具有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双重品格。[3] 明代形成市场调节下的“消费产业”,小说是消费文化的产物。明代小说的文本传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大众化”?对于小说来讲,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考察应该从作品的创作一直追逐到读者阅读后的反响,其中包括作品到达读者手中的方法与途径”;[4] 但是由于“公众”在任何时代实质上都是一个“能指”明确而“所指”含糊的概念,更由于除了文本,难以得到其他可以分析古代公众阅读小说的真凭实据,因此对于明代小说的所谓“大众化”问题,总是难得其真。本论文的出发点之一,即是试图借助对明代传播媒介的分析,讨论通俗小说文本传播与接受的最大可能性。
根据明代刻书技术的发展水平初步考察明代通俗小说的传播阶段,大致可以看出商业传播媒介在小说大众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5]
明代前期(洪武—成化),是小说传播沉寂期。明初统治者并未对通俗小说予以直接严厉的打击,皇帝甚至对小说极为迷恋,如正德皇帝朱厚照(1506—1521)南幸时,曾令太监深夜出宫,以五十金重价购回《金统残唐记》小说,以供“御览”。[6] 文人学士也时有染指小说,如成化进士林瀚在弘治、正德间(1488~1521)修订《隋唐志传通俗演义》,正德进士杨慎为之批点、作序。
印刷业的落后是小说传播未广的最大障碍。这一方面表现在,在明初官府和传统的刻书之地(福建建阳地区),书籍刊刻仍集中在儒学著作,“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宣德四年(1429)衍圣公孔彦缙不远千里到建阳购置图书。另外,技术落后,抄写是书籍流传的主要方式。洪武十五年(1382)从福建、湖广、江西、浙江、直隶招1910个书工,专事抄写。元末明初华亭人孙道明抄书数千卷;宋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江西人刘菘,“家贫力学,寒无炉火,手皲裂,而抄录不辍。昆山人叶盛,“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虽持节边檄,必携抄胥自随。”[7] 元末明初问世的章回小说《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按照当时的印刷技术和出版状况,似乎还不大可能出版和广泛传播。此时最大的官方印刷机构——司礼监经厂的规模:刻字匠150人,表背匠320人,印刷匠58人,共计500余人。按每人每天200余字,一年至多可一千多万字。[8] 洪武七年(1374)刊刻《宋学士文集》,12万余字,十个工匠五十二天才完成,平均每个工匠每天可刻两百余字,则《三国志平话》8万字,需要花一个月,《三国演义》70万字需要十个月。
因此,官府和民间抄录和刊刻的小说数量很少。当时主要的小说传播方式,是城市勾栏或乡村民间的说书,至于文本形式,则是抄本、缩略本或说书提纲本,以书坊刻本为主的小说文本形式显得粗糙、幼稚。正德四年(1509)建阳清江书堂刊行《剪灯新话》四卷和《剪灯余话大全》四卷。永乐年间(1403~1424)编纂的《永乐大典》中抄录有26卷元明之际的“平话”。成化七年(1471),金台鲁氏刊行四种通俗韵文——四季五更驻云飞、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新编寡妇列女诗曲。成化七年至十四年(1471~1478)北京永顺堂刊印了约13种说唱词话。
明代中期(嘉靖—万历)是小说传播繁盛期:这一时期,刻书重心从官府转入私家,刻书中心转入新的经济发达地区。谢肇淛《五杂俎》:“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州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
书坊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出版小说,而盛于万历。拥有十名刻字匠的书坊,当时规模已不算小。嘉靖三十四年(1555)无锡顾氏奇字斋刻《类笺王右丞诗集》,书共五六百页,用工“写勘3人,雕梓24人,装潢3人”,共30人。历时五个半月。这说明,在嘉靖时期,精刊仍然是很费时的。《小说书坊录》所录225种中,有120种出于万历。而建刻66种小说中,除5种不明年代,3种是正德、嘉靖时期,3种是天启、崇祯时期,55种是万历间刻本。小说从此进入了主要以文本形式和读者阅读为主的传播时代。民间流传和收藏小说更为普遍,成化时“故事书,坊印本行世颇多, 而善本甚鲜。”“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蔡伯喈杨六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有之。痴呆文妇,尤所酷好。”[9]
显然,至明代中后期,由于商业经济的繁荣,一个雏形的大众传播社会已基本形成。
一、商业印刷媒介与明代小说的大众化出版
小说大众化接受的物质基础是小说印本的规模化出版,而作为非主流意识形态表现物的小说,其规模化出版只能有赖于印刷媒介的商业化操作;利润是小说商业出版的决定因素,至明代中后期,小说获得商业利润的物质支持是商业印刷业发达后印刷成本的降低。
(一)商业资本介入民间书坊与小说的规模化出版
通俗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浓重的、无法抹除的商业色彩、市民色彩,与书坊结下不解之缘。现存最早的话本、讲史平话皆为瓦子所刻。明代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的兴盛与前代的基础固然密不可分,也受益于明代的文化氛围,但无论如何,书坊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小说的商业化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刷业商业资本的介入。虽然印刷业受官府的控制与干预,商业化发展与其他产业不同;但明代中后期商业经济的发达已经使印刷业成为重要的经营行业:包括出版(刻印)、发行(贩卖)在内的图书出版已经商品化,而民间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化印刷业尤其繁荣。[10]
商业资本的介入,使福建建安(建阳)、四川眉山(成都)、河南汴梁(开封)、安徽徽州(歙县)、江苏金陵(南京)、浙江武林(杭州)、山西平水(临汾)以及北京迅速崛起为著名的雕版印刷中心,形成全国最为重要的刻书印书中心。[11] 尤其经济发达的江南,由于雄厚的私人商业资本介入,出版业在全国独占鳌头,不仅江苏、浙江和福建是全国有名的出版中心,而且天下三分之二的印刷商业资本都集中在苏州和南京。[12] 小说的刊印也主要集中在江南。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两京遗编提要》:“余尝谓嘉万以来,大名刻书之盛,堪与苏、宁、徽、杭并驾。刀削之技或稍逊,而朴茂实过之。且所刻之书,皆有经济实用,则尤与东南异趣。”
明代私人印刷商业资本以书坊或坊肆的形式出现。周弘祖《古今书刻》著录明版书共计470种,其中367种为坊刻本(而且这些坊刻本绝大多数是嘉靖以后的产品)。书坊无论其数量还是规模,都达到相当的程度。书坊出现雇佣制度。 毛晋之子《影宋抄本五经文字跋》:“吾家当日有印书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书籍。”清钱泳《履园丛话》:“汲古阁后有楼九间,多藏书板,楼下两廊及前后俱为刻书匠所居”、“童仆皆令写书,字画有法”、“入门童仆尽抄书”。南京书坊多达93家,万历年间达到鼎盛。书坊每以“三山街书林”、“三山书坊”字样宣传,“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13] 建阳嘉靖《建阳县志》有“书坊图”,建阳书林有堂号姓名可考的约64家,[14] 苏州则37家,杭州书坊24家,北京10余家,徽州10家。这些民间的书坊有实力来承担小说的商业出版。以十八世纪中国向日本的书籍输出规模为例,1711年,到达长崎的中国船54艘中,6艘装载书籍,达140箱。这间接说明明代的书籍出版已达到相当的规模。
表1:清代对日输出图书个例
年份装载书籍船只来源地及船号 装载书籍箱数
171115号南京 93
51号南京 40
25号南京 1
19号宁波 4
37号宁波 1
10号宁波 2
171240号南京 82
57号南京 67
在书籍的发行、流通方面商业资本也大量介入。衢州府龙游商人投资经营着苏州的书籍业。归有光《送童子鸣序》:“越中人多往来吾吴中,以鬻书为业。”童子鸣即龙游人。明末“龙游余氏开书肆于娄,刊读本四书字画无伪,远近购买。”[15] 徽商业书籍业者甚多。明末南京十竹斋主胡正言就是休宁人。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读书人弃儒从贾,从事书业。徐北溟“补县学生,家酷贫,无以自给,乃赴杭州贩书为业”;[16] 鲍雯“急欲以功名自奋。既而连试有司,不得志……不得已脱儒冠往武林运策以为门户计。”[17] 福建长汀《马氏族谱·列传》载马氏家族“桢公以贸书往来于粤,四弟则忠公往来于吴”。著名书贾童佩从事贩书。
明代书坊以营利为目的。书坊刻书考虑市场需要与经济效益,这决定了出版者要将目光盯住市场,考虑什么样的读物才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从当时的传播与出版后的热销可以看出,新兴的通俗小说无疑有广大的市场。[18]
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小说多琐事,故其节短。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19] 出版通俗小说的可观利润,使通俗小说成为书坊刻书的重点。各书坊争着物色作者,收买小说作品。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序》:“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二刻拍案惊奇》:“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抄撮成篇,得四十种。”江苏书坊刻书,如九如堂、三多斋、大业堂、世德堂、周曰校、荣寿堂、天许斋、叶敬池、衍庆堂、五雅堂、尚友堂、贯华堂、萃文书屋、翼圣堂、仁寿堂、书业堂、甘朝士局、宝翰楼、崇德书院、绿荫堂、绿慎堂、聚文堂、宝文堂、掌珍楼、艺古堂、爱日堂等,都有多少不等的作品刊刻问世。[20] 现存的225部明代小说中,建本小说66种。书坊成为通俗小说的主要刊刻者。
书坊的参与决定了通俗小说的趣味,从现在所知的书坊刊刻书目可以看出书坊主作出种种努力以适应顾客多变的口味。明代后期历史演义、神怪小说成批大量刊行,书坊间的仿效和竞争当是重要的因素。明清之际的时事小说在短时间内冒出,又多文字粗糙、相互间抄袭、改头换面重刻,这无疑是书坊主操纵的结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书坊使小说的传播面迅速扩大。
(二)印刷出版的平民化与小说出版的大众化
印刷出版业走向大众化,首先必须具备这些条件:政府政策的支持、刊刻技术的发达和商业资本的介入。明代社会以教化为本,印刷出版业受到政府的保障和支持。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下诏,书籍、笔、墨一律免于征税。[21] 洪武十九年(1386)改革工匠服役制度,允许工匠纳银代役;成化时,纳代役银可以不再轮班服役;嘉靖八年(1529)废除轮班役。
小说的钞刻有赖于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物质指纸、墨、木材(雕版用梨、枣木),技术指工艺流程。
在降低成本方面,主要是纸、墨等原料和刻工成本的降低。
纸 明代是我国造纸技术的成熟时期,商业资本的介入,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22] 纸张生产主要在两方面影响小说印刷:一是竹纸的大量使用;二是技术上防蛀技术和再生纸的应用。竹纸的制造,始于隋唐,发展于宋元,而盛于明清。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竹子资源分布广、产量大,适合造纸的竹子不下五十种。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尤其江西和福建地区,从宋元开始就广泛运用竹纸印刷大众读物。嘉靖、隆庆以后商业化造纸生产日益发达,出现专门的规模不小的造纸槽坊。万历二十八年(1600),仅江西铅山县石塘镇一地,“纸厂槽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帮丁不下一、二千人。”[23] 由杭州人经营的“苏城纸业一项,人众业繁,为贸易中之上等。”[24] 竹纸产量超过棉纸跃居第一。
竹纸质量比不上棉纸,颜色暗黄,既薄且脆,易碎不宜久藏,但产量大,使小说的批量印刷成为可能:而且价格低廉,降低了小说印刷成本:“凡印书,永丰棉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棉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棉,厚不如柬,只以价廉取胜。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嘉靖、隆庆以后随着技术的改进,竹纸的质量又有所提高,万历以后竹纸的使用就更加广泛。胡应麟谈到当时的竹纸:“近闽中则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异才常,而坚数倍于昔,其边幅宽广亦远胜之,价直既廉而卷轴轻省,海内利之,顺昌废不售矣。”竹纸还具有了“防蛀”的功能:“印书纸有太史、老连之目,薄而不蛀,然皆竹料也。若印好板书,须用棉料白纸无灰者,闽浙皆有之,而楚闽滇中,棉纸宝薄,尤宜于收藏也。”[25]
小说印刷用纸,价格是关键。低廉的竹纸当然是首选。以竹纸中质量较好的江西、福建的“连史”、“毛边”纸为例,沈榜《苑署杂记》卷十五记载万历二十年苑平县支付的内府用纸各类纸价:“梨版三块,价一两二钱;大红纸十二张半,价减七分五厘;毛边纸五十张,价三钱;咨呈纸五十张,价一钱七分五厘;连四纸二十五张,价一钱七分五厘:大瓷青纸十张,价一两。”“毛边纸五十张,价三钱”,这个纸价,还高于南方。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燕中刻本自稀,……辇下所雕者,每一当越中三,纸贵故也。”如果按这个比例,南方的毛边纸应当“五十张价一钱”。另外将用过的竹纸回槽,“其废纸洗去朱墨污秽,浸烂入槽再造,全省从前煮浸之力,依然成纸,耗亦不多……名曰还魂纸。”(宋应星《天工开物》)这种再生纸的出现,更进一步降低了印刷成本。
墨 明代印刷所用的松烟墨,沈榜《苑署杂记》记载万历时的墨价为二笏一钱。书坊用墨大多是质量较差的次等炭墨,一斤约为五钱。
刻木 书坊刻板多用乌桕板,因为容易刻写上去。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闽本多用柔木,易就而不精,杭本雕刻时亦用白杨木,他方或以为乌桕板,皆易就之故。”
刻工 明代出现专门的商业刻字铺。正德时南京104行中就有“刻字行”。明人彩绘《南都繁会图》绘有“刻字”、“镌碑”的市招。明代苏州以雕刻书板闻名的可知姓名的刻工就有600余人。[26] 明代刻字工价很低廉。嘉靖四十三年(1564)福建所刻《豫章罗先生文集》后有木记:“刻板八十三片,上下两帙,一百六十叶,绣梓工资二十四两”。以一版两叶平均计算,每页合工资约一钱五分。万历四十年刊刻的《径山藏络律异相》卷一“题记”云:“字八千七百七十个,该银四两三钱八分五厘”,折合每百字三十五文。崇祯末年,江南刻工工资更为低廉。清徐康《前尘梦影录》:“毛氏广招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文银刻一百字。”每百字仅二十文。[27]。
在效率方面,主要是刊印技术、字体、版式、装帧等的改进。
活字版的应用 活字印刷在明代开始有较多的应用,但对于小说的出版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明中期“明人用木活字板刷书,风乃大盛。”[28] 祝允明《渭南文集跋》:“沈梦溪《笔谈》述活板法,近时三吴好事者盛为之。”活字印刷比雕版印刷效率高,费用低。“今世欲急于印行者,有活字。”[29] 无锡华呈“多聚书,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矣。”[30] 但活字印本与雕版印本相比:栏线——活字板框拼和而成,栏线衔接不密,时有时无,字体——字行排列不很整齐,大小粗细不一律,字体独自成形,笔画不交叉。墨色深浅不一。嘉靖时无锡华氏、安氏铜活字制作虽精巧,仍有“参差不齐”、“字句多所脱落”、“校雠甚疏,或上下互倒,或形近而互伪,亥豕鲁鱼,无页不有”的诟病。叶德辉《书林清话》云:“大约华氏所刻书,均不必可据。”
因此从目前所存的活字印本来看,活字印刷虽然在嘉靖年间福建的书坊已经用来印刷通俗类书,但还没有广泛适用于小说文本的印刷。明末始有木活字小说印本《于少保萃忠传》、《花幔楼批评写图小说生绡剪》。说明活字印刷虽然速度快,但技术尚不够稳定成熟,在效率与成本方面反而不如雕版印刷。
字体 万历以后,横细竖粗、横平竖直的特征更为规则,宋体字已经成为独立的印刷字体。版本学家称宋体字为“明匠体”。“匠体字者,流俗通用刻书之字体也。……明隆万时始有书工专为写肤廓字样,谓之宋体。刻书者皆能写之。”[31] 规则的字体虽然呆板缺乏流利生动而不甚美观,却更易于施刀刻字、上版刻写,提高刻字效率,有利于缩短出版周期,与出版的商业化适应。
装帧 明初到嘉靖隆庆书籍的装订一直流行包背装,至万历始广泛使用线装形式。线装书工艺简易,更节省了包背所需的硬封皮;又比如书皮,福建刊刻的书籍多不加封皮,这也节约了纸张,降低了书的成本。[32]
版式 明代小说的版式安排比其他书籍密集。[33]
表2:明代小说版式的变化
书名 刊行时期 行×字
半页字数
《三国演义》 嘉靖1522年9×17153
万历苏州舒载阳刊本10×20
200
万历余氏双峰堂刊本16×27
432
万历诚德堂熊清波刻本 14×28
392
天启黄正甫刊本上图下文15×34
510
15×26
390
上表以《三国演义》的刊刻为例,说明万历以后小说的版式安排越来越密集。这样可以容纳更多的字数,从而减少纸张而节约成本。
由于技术的革新、物质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明代后期出书非常迅速,从交稿到印出,只需要一个季节就成了。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记载毕自严的《留计疏草二卷》“于天启六年秋引疾辞归,是年冬此书即出。出书之迅速,颇为罕见。 ”《历年记》上载明季“京师之变未及两月,即有卖剿闯小说一部。”
明代中后期造纸业、印刷出版业的商业化进程使出版向着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向发展,小说的低成本、大规模刊刻成为可能。
二、商业传播机制与明代小说的社会化流布
书籍广泛而迅速地传播,依赖传播空间的扩大。而传播空间的扩大,其前提除了符号的复制即纸张印刷外,就是连结媒介和读者的社会交通网络的发达和出版印刷自由的确立。[34]
(一)商业交通及邮驿的发达与小说的流布
明代的交通依托运河和长江,形成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明代商人所著的《明一统路程图记》、《商程一览》、《江南绘图路程》、《士商规略》、《士商十要》描述了明代的交通路桥状况。[35] 明代“国家统一寰宇,遐陬僻壤,罔不置驿。”“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水马驿,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水马驿并递送所。”永乐时水驿41所、陆驿29所,急递铺“十里一铺”,共有14430所。驿路有十万大军把守,“吴舸越艘,燕商楚贾,珍奇重货,岁出而时至,谈笑自若,视为坦途。”为政府服务的驿船“私货多于官物,沿途售卖,牟取暴利,习以为常。”成化元年(1465)南京吏部郎中“运贡物不过一箱一柜,辄用一船,架待客三,多载私物”或“满载私货,附运闲人”。[36]
隆庆四年,徽商王汴历时二十七年编成《天下水陆路程》(又称《士商必要》),列全国水陆路程143条。南京至全国各地的长途路程11条、江南至邻近区域路程12条;15条水路连接苏松二府和各市镇县城。天启六年徽州人澹漪子编《天下路程图引》(又称《士商要览》)列出江南、江北水路100条,“江湖连接,无地不通”。[37] 交通费用也很低廉。北方车马正德时“凡一车必银一两”。[38] 《士商类要》记载的船价,从扬州到瓜洲三文,瓜洲南门渡大江至镇江码头二文,杭州府官塘至镇江“诸港有船,二文能搭二十里程。杭州至普陀山一线,三分至宁波府。
江南以太湖水系和江南运河为主干的水网,以较低的运费和较大的数量,实现商业流通。四川西部山区建昌(西昌)地区,“商贩入者,每住十数星霜,虽僻远千里,然苏、杭新织种种文绮,吴中贵介未披而彼处先得。”“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三反而北。”嘉定布“商贾贩鬻,近至杭、歙、清、济,远至齐、辽、山、陕”。[39]
随着交通的发达,民间邮政制度开始建立。登载在1921年交通部邮政总局《邮政事务总论》上的《置邮溯源》,认为,充分组织起来的或加以系统化的民用邮政——民信局,即所谓“信行”,其产生不更早于明朝永乐大帝年间。也就是说,明永乐年间出现专营民间通信业的民信局,海外华侨民信业,在十五世纪的明朝期间就已出现:
“他们利用各种运输工具,经商巨舶、运河小舟、脚夫等,尽一切可能便利公众。‘有需要特别快递者,就维持特别快班只要业务上有需要,不惜把营业时间延长到深更半夜;并且在中国最有吸引力的是让收信人也摊付一部分邮费,通常是一半’(引马士H.B.Morse语)”
“民信局处理信件却以迅速著称,当轮船还没有下锚停泊前,信件已被搬到小驳船上,边向岸上划去,边由信局代理人在舟中分拣信件,远在正规邮件之前,妥投到收信人手中去。”
“服务的取费总是很低廉的,按路程远近,酌收二~二十分(即制钱二十~二百文),但往往要讨价还价;按年结账,折扣优待,也不少见。
如须快递,寄信人在信面上注明较平时为高的资费,于投递时由收信人付给。”
“通常付给民信局的资费是非常低廉的,对比起来,欧洲的资费好像贵得几乎令人望而却步。”[40]
(二)小说的社会化流布方式
依赖于发达的交通网络和邮递发行渠道,明代的图书买卖相当发达。[41] 图书发行业已形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体系,在当时书籍数量不断增多、读者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这个发行体系能够有效地将大量的图书输送到它的需要者手中。常熟毛晋所刻书,“至滇南官长万里遣币以购毛氏书”,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说。[42] 崇祯间曹溶《流通古书约》说:“近来雕板盛行,烟煤塞眼,挟资人贾肆,可立致数万卷。”
图书流通渠道多种多样,专业的渠道如书市、书坊、书肆、书摊、书船等;业余的渠道如考市、负贩、货担郎、杂货铺等。
书市 图书发行集市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专门售书的集市,这种集市一般带有批发性质,其地点多在刻书发达的地区,购买者多是书商。如嘉靖《建阳县志》卷三记载,福建建阳县崇化镇,“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当地人称之为“书市”。
书市最发达的地方是北京、南京、苏州和杭州。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里中友人祝鸣皋束发与余同志,书无弗窥。每燕中朔望日,拉余往书市,竟录所无,卖文钱悉输贾人。”
“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
“燕中刻本自稀,然海内舟车辐凑,筐筐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第其值至重,诸方所集者,每一当吴中二,道远故也。辇下所雕者,每一当越中三,纸贵故也。”
“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适东地之会,文献之衷,三吴七闽典籍萃焉。诸贾多武林龙丘,巧于垄断,每瞰故家有储蓄,而子姓不才者,以术钩致,或就其家猎取之。楚蜀交广,便道所携,间得新异,关洛燕秦,仕宦橐装,所携往往寄鬻市中,省试之岁,甚可观也。”
“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
书市另一种为兼售图书的综合性商业集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凡燕中书肆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陆费逵在《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中曾对此加以介绍:“平时生意不多,大家都注意‘赶考’,即某省乡试,某府院考时,各书贾赶去做临时商店,做两三个月生意。应考的人不必说了,当然多少要买点书;就是不应考的人,因为平时买书不易,也趁此时买点书。”
书坊 刻(抄)售合一,从事图书出版、发行工作,明末清初毛晋的汲古阁即属于这一类型。书肆是单一的图书发行店铺,只发行而不雕刻(抄写)图书。书肆多在交通便道。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凡燕中书肆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苏州“书肆之盛,比于京师。”书坊大多开设在阊门内外和吴县县前。阊门南浩街和胥门一带是万商云集、樯桅林立的码头,苏州书坊开设在附近,便于将所刻印的书籍装载、运散到全国各地。
书摊 即售卖图书的摊点,一般设在市廛店铺周围。北京“凡徙非徙其肆也。辇肆中所有,税地张幕,列架而书置焉,若棋绣错也,日昃复辇归肆中。惟会试则税民舍于场前,月余试毕,贾归,地可罗雀矣。”杭州“省试则徙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人士诞辰也。上巳后月余,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明代马佶人著《荷花荡》传奇中有“不免在书铺廊外,摆个书摊,赚他几贯何如?”
杂货铺 兼售图书的杂货铺,又叫“星货铺”。它们遍布城市和乡村,甚至一些极偏远的地方也有分布,售卖杂货为主同时也兼售图书。《扬州画舫录》载,清代扬州曾有一乞丐作《小郎儿曲》,其内容为“男女相悦之词”,结果在当时极为风行。“近日是曲翻板数十家,达及荒村僻巷之星货铺,所在皆有。”
负贩 即是将书籍从出版地带到另一地区发行销售。或者是出版者托人顺路将书籍运送到其他地区的发行店铺。小说《儒林外史》中文瀚楼主人道:“目今我和一个朋友合本,要刻一部考卷卖,……我如今扣着日子,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去卖。”谢兴尧《书林逸话》:“按昔日刻书习惯,……刊成后,先以红色印刷,次乃用墨。以红印本分赠师友,墨印本送各地出售。”或者是商贩自己买下书籍再负贩于其他地区。商旅官宦去某地时顺路带一些书籍放到当地书肆寄卖,“寄鬻市中”。
货担郎 在销售其他货物的同时也有兼售图书的。其所售图书一般为通俗性读物,如兔园册子、戏曲唱本等。一些从故家大户散出的善本、稿本偶尔也会落入货担郎手中。如明代学者陈继儒即曾在货担郎手中买到过明代另一位学者王世贞的著作抄本。
书船 南方水道发达地区利用船舶作为图书的贩运、发行工具,称书船,又称书舶。据清荥阳悔道人《汲古阁主人小传》记载,明毛晋为搜求善本,经常在门外贴上告示,以高价收购图书,“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 叶德辉《峭帆楼丛书》卷首称昆山赵元益“但见异本即插架,估船市舶争前驱”;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谈到钱谦益以重赀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
可见,发达的商业交通网络之上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灵活的图书销售网络;依赖这一传播空间的拓展,小说有可能在地理空间上达到传播的最大范围。
三、小说书价与小说接受层的初步判断
影响图书定价的因素 明时图书的定价已形成一套特定规律,据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记载:
“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
“凡本,刻者十不当钞一,钞者十不当宋一”
“凡刻,闽中十不当越中七,越中七不当吴中五,吴中五不当燕中三,燕中三不当内府一。”
“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双印者,有单印者,双印与朱必贵重用之。凡板漶灭,则以初印之本为优。”
“凡装,有绫者,有锦者,有绢者,有护以函者,有标以号者,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焉,闽多不装。”
“当代板本盛行;刻者工直重钜,必精加雠校,始会梓人,即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钞录之本,往往非读者所急,好事家以备多闻,束之高阁而已。以故谬误相仍,达非刻本之比。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钞本价十倍,刻本一出,则钞本咸废不售矣。”
“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值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可见,影响图书定价的因素主要是:物质工本,如雕刻、手抄、用纸等;形式,如精粗、美恶、工拙等;内容,如真伪、时代的远近等;发行,如刻印地的远近等。需要注意的是,在影响图书定价的诸多因素中,发行最为活跃和复杂。因为很少明码标价,图书价格的随意性就很大,往往由书肆主人视具体情况而掌握。或者视读者贫富程度及是否急需而定,“问以交易有无定价?则云:‘各视其人为之。’”或者视图书库存多寡而定,“嘱买《大清会典》二册,礼部早经印刷完毕,买现成者约每部工价六十金上下。如要买须早寄银来,迟恐渐买渐少且要长价也。”[43]
图书定价实例及有关由此的推断 现存的明代小说很少直接在书上标明价码。目前所见,仅有两部。万历苏州龚绍山刊本《陈眉公批评列国志传》12卷223则,约40万字,“每部纹价壹两”。万历天启间苏州舒载阳刊本《封神演义》20卷100回,约70万字,“每部定价纹银贰两”。二两银子是当时购买一亩地的价格,按万历时的米价,《封神演义》折合米三石余,相当于六品官员一个月的月俸。《列国志传》一石四斗。以李渔的书做参照,可以推断这是当时小说的一般水平的定价。李渔南归降价销售书:“价较书肆更廉不论,每部几何但以本计。每本只取纹价五分,有套者每套又加壹钱。南方书本最厚,较之坊间所售者,一本可抵三本,即装订之材料工拙,亦绝不相同也。不用则已,用则别。”所列书目中的小说《十二楼》、《连城璧》每部各六本,一部书售价约三钱,“较之坊间所售者,一本可抵三本”,可推断坊间售价约纹银九钱。考虑到篇幅的因素,《封神演义》约七十万字,《十二楼》约十九万字,《连城璧》约二十五万字,书价总体上较为接近。
按照这个定价,通俗小说的接受者,诚然是有闲有钱阶级,即“买得起的必定是有钱的官绅地主商人及其子弟,租书铺的老板也会买。”[44] “元明时期……能买得起书,尤其是有余赀购买诗词、曲赋、小说等文学书籍的,主要还是皇家贵族、达官贵人、土豪富商或文人学士,一般老百姓是买不起这些文学书籍的,他们顶多只买些《万年历》、《居家便览》、《商贾要览》之类的实用书籍。因此,元明时期刻印文学书籍的接受对象,基本上不出皇家贵族、达官贵人、土豪富商或文人学士的范围。”[45]
可是先来考察一下通俗小说出版的实际出版情况。印刷媒介商业化,意味着利润是最大的目的。从现存建阳书坊刻本来看,由于书坊刻书纯以营利为目的,书坊主为易制速成,节约成本,追求最大利益,千方百计降低成本,比如使用质次价低的纸木或者缩板、出小字本、删落字句、合印甚至盗版。
比如普遍使用疏松的木料和脆薄的纸张印刷书籍,稍经刷印,即书板豁裂,字迹漫漶。福建人谢肇淛《五杂俎》:“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以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近来闽中少有学吴刻者, 然止于吾郡而已。能书者不过三五人,能梓者不过十数人,而板苦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胡应麟称:“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值最廉。余筐箧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纸张方面更流行拼接印刷,或直接,或横接,以节约用纸。
或者采取缩板:嘉靖十一年(1532)福建提刑按察使给建宁文“近时书坊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偏狭,字多差讹。”或者出小字本,文英堂、文锦堂都出过题“李卓吾评点”的《列国志传》小字本。或者删落字句,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复瓿。”或者盗版,“闽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46] 余象斗《四游记》:“射利者……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或者合印:崇祯雄飞馆主人雄飞合印《英雄谱》,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合刊,每半页上三分之一处印《水浒传》,半页17行,行14字;下三分之二处印《三国演义》,半页14行,行22字,即每半页共印546字。这样读者只要花不到一部书的价钱,就可以欣赏到两部书,书前还有一百幅精美的插图,还有名士评点。
以有明确定价的《封神演义》为例,这个版本不仅版式疏朗,而且有精美插图,又是在最讲究刻本质量的苏州刻成,相比较其他坊刊本,这一定价显然是偏高的。
表3:小说书价与版式的关系
书名 卷数版式、字数 页数 书价
封神演义 万历苏州舒载阳刊本 20卷100回
10×20,200 50页,100面 纹银二两
清覆明本8卷100回15×32,480 20页,40面
列国志传 万历姑苏龚韶山刊本 12卷10×20,200 60页 纹银一两
万历己卯(1615)本12卷11×20,220
内府抄本8卷 13×25,325
万历(1604)三台馆本 8卷 13×20,260
可以设想,如果以上述方式印刷,万历苏州龚绍山刊本定价“纹价壹两”《陈眉公批评列国志传》和万历天启间苏州舒载阳刊本“定价纹银贰两”的《封神演义》,其书价当大致在5钱或1两。按照我们对明代社会各阶层收入的大致分析,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大众可以接受的价格。[47] 因此,可以初步推断,明代通俗小说的读者群应当包括比皇族达官、富商文士更为广泛的低层“大众”。
可见,明代商业资本的介入促进了民间书坊的规模化发展,印刷媒介的商业化使通俗小说文本的大众化出版成为可能;商业交通与邮驿的发达,开拓了通俗小说文本传播的渠道,多样的小说社会流布方式,扩大了通俗小说的阅读范围。归根结底,明代通俗小说文本的广泛传播,得益于发达的商业传播媒介所形成的初步的大众传播社会。
标签:小说论文; 明朝论文; 嘉靖论文; 杭州南京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印刷工艺论文; 印刷行业论文; 少室山房笔丛论文; 商业论文; 印刷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