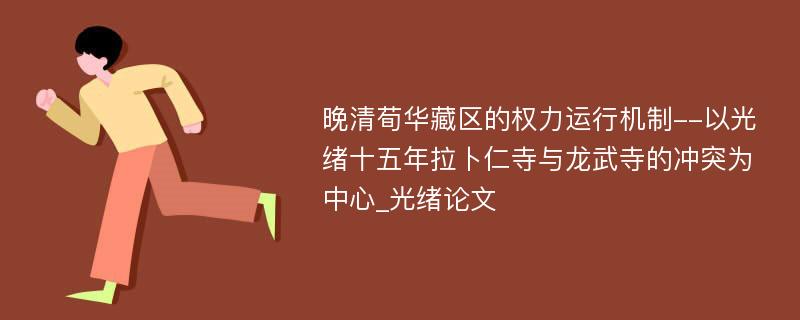
晚清循化藏区的权力运作机制——以光绪十五年拉卜楞寺与隆务寺冲突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光绪论文,晚清论文,十五年论文,权力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8)06-0072-06
循化藏区在中国历史上因其具有“汉藏走廊”的文化地理与政治地理区位,具有特殊的社会形态:在文化上异质于以儒家文化为基本指导原则的汉族社会;在政治上又异质于以藏族为主体的西藏。这就使循化藏区在中国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中具有非常典型的类型学意义,反映在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之上,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构造与内在机理。
一、循化藏区内部的权力构成及两大对立集团的形成
在划分区域社会的标准上,国内学界多有争论,概而言之,可以分为四种:政区说、自然地理说、多元取向说、历史过程与观念说。然而,正如黄国信所言:“区域的概念并非单一维度的……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种观念,动态而弹性。”①在研究中,不能仅仅依据单一标准来划定区域社会的界限,而是要在关照事件的连续性与整体性上,综合考察具体的“域界”。因而,我们认为循化藏区就是指清代甘肃省西宁府循化厅境内的以藏族为主体的居住区域,然而这里也并非没有变动,如光绪初年清王朝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后,鉴于南番佐盖地方买吾部落“远窎所城三百余里,催抚字,事事维艰,距洮州所城只一百数十里,详定改隶洮州”②。我们仍然把佐盖地区归入循化藏区的区域社会之内,故所谓循化藏区包括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合作市、夏河县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县、泽库县以及海东地区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南山地区,亦即当时人通称的“南番”与“西番”居住区。
英国著名社会史学家迈克尔·曼强调:“社会是由多重交叠和交错的社会空间的权力网络构成的。”③指明了社会是一个由各种权力关系编制起来的立体网络。那么编织起清代循化藏区的权力主要有哪些呢?我们的判断是:其一,以强制力为基础的国家政治权力,指王朝国家在循化藏区内的存在与统治机构设置及其在原有社会组织基础上的渗透与延伸形态所拥有的权力;其二,以宗教资源为基础的寺院权力,指借助于宗教资源——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基本宗教教义及其组织——使寺院特别是宗教领袖也就是活佛所拥有的权力;其三,以传统的部落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权力,指借助于传统的部落制度使部落首领所拥有的权力。
循化藏区自古就是藏族及其先民生活繁衍之地。由此,部落制度成为循化藏区的基本社会制度。故洲塔说:“甘肃藏区自形成以来至本世纪中叶,其社会一直以部落制度形式存在。部落制度贯穿了甘肃藏族社会的全部历史,其影响渗透到甘肃藏区社会的方方面面。”④部落制度不仅构成了循化藏区各部落内部社会权力形成与维持的基础,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部落存在的基本格局。清代,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循化藏区的传播,以及清朝所确立之“行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策略在循化藏区的推行。宗教势力迅速崛起,一些部落围绕着大型寺院形成了跨地域的部落联盟。至光绪朝,在清廷的默许下,循化藏区内逐渐形成了以拉寺和隆务寺为首的两大政教合一的寺院集团。此外,尚有沙沟寺(又称德尔隆寺)、黑错寺(今称合作寺)、卡加寺等小型的政教合一寺院集团,只是因为它们的势力相对弱小,在“南番”的相互竞争中不得不加入到隆务寺体系之内,寻求保护以对抗拉寺,可以将之纳入到隆务寺集团内。由此形成了隆务寺集团以隆务寺为首的“热贡十二族”自西,以沙沟寺为首的德尔隆寺院集团自东,对拉寺的包围。为了摆脱腹背受敌的困境,拉寺积极展开攻势,不断将自己的触角深入到隆务寺集团内部,试图通过渗透的策略,瓦解其联盟,寻找出路,扩张自己的势力。两大寺院集团之间的冲突自乾隆年间开始,逐渐升级,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方呈现出减缓的趋势,余绪则延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光绪十五年(1889)爆发的拉寺与隆务寺的冲突,就是在上述的逻辑链条中展开的,反映的深层次原因则是拉寺的演变策略受到了隆务寺集团的激烈反对,并最终诉诸于直接的武力解决。我们借助于光绪十五年发生在拉寺与隆务寺之间冲突的历史话剧,通过各种角色的表演与其各自的关系,即可对晚清时期循化藏区内三种权力之间的结构有一个透视性的了解。
二、当刚红布被杀事件与拉卜楞寺的反应
光绪元年,卡加因与隆哇争夺曼隆部落启衅,陕甘总督左宗棠遂令河州镇沈玉遂前往镇压。事后,沈玉遂“以番性崇信佛教,选择素为番众敬服之寺僧岁仓(今称赛仓)令其总管番族”⑤,并由左宗棠发给执照。赛仓活佛世系正式成为清朝授封的区域性政教首领,统领北起土门关南至合作之间、西至达麦长石头的大夏河流域段,辖治霍尔藏部落、南木拉部落、卡加部落、隆哇部落、合作部落及其各部落境内的寺院。⑥德尔隆寺院集团西毗拉卜楞寺,南接博拉、阿木去乎等部落,东邻佐盖买吾等,犹如一根楔子插入到拉寺集团之中,并控制着由拉寺通往河州以及兰州的通道,严重限制和约束着拉寺向东部的扩张及其与所属部落的联系。面对这种局面,拉寺并不甘心,积极寻找机会,向德尔隆寺集团渗透,争取权益。当刚红布⑦被杀事件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卡加寺及其卡加部落与隆哇部落的冲突因隆哇部落遭到官府的镇压而告结束,两者同时被划归德尔隆寺院集团,然而它们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真正的根除,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间,冲突依然不断。由于沙沟寺并未采取对卡加有利的措施,引起了卡加的不满,内部产生裂隙,这就为拉寺的介入、拉拢卡加提供了机会。其时,恰逢赛仓三世于1879年圆寂,沙沟寺大权掌握在总管千户大加手中。大加为了增强对各部落的控制,试图通过强硬措施架空所属部落土官的权力,首先引起了南木拉部落内部的反对。由是发展到光绪十五年,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便在酝酿之中了。此即会查本案的官员所称:“登果庄(即且先滩)、上下拉卜拉(即南木拉部落)、卡家、王尕滩于承纳循化番贡额粮,復为沙沟寺香火佃户,由来已久。后闻该寺既不知抚恤番户……卡家族江落寺捏力哇即江落捏哩哇,勾引登果庄当刚红布、上下拉卜拉、卡家、王尕滩男女番目,唆使一半番众,私投拉布塄寺,承租当差,番俗曰滚茶。”⑧南木拉居于德尔隆寺院集团的地理中心部位,私投拉寺,不能不引起与拉寺有长期积怨的沙沟、黑错集团的强烈反应,“沙沟愤怒,欲向且先滩与女头目之汪尕滩行兵”⑨。是年五月十一日,且先滩红布当刚因决定追随卡加寺投靠拉寺,遭到叔叔七老的反对,遂将七老杀死。是日,“沙沟大加怀恨,约了黑错捏力干、隆哇红布、卡家岁仓加己乔的,领上众人将旦刚妇人儿子、女子全家杀了,东西抢了,房屋烧了”⑩。
拉寺得知当刚红布被杀的消息,立即做出了反应,认为这是一个向德尔隆寺院集团全面进攻的好机会。不过,拉寺并没有立即把矛头指向距离自己较近的沙沟寺,而是选择了发生过多次冲突的黑错寺。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黑错寺原为拉寺属寺,乾隆年间与拉寺反目,投向隆务寺,致使拉寺耿耿于怀,存心再次收为己有。此即拉寺襄佐、法台声称:“沙沟、黑错两寺向归我寺管辖,嗣因黑错寺不守清规,动辄滋事,迭经我寺前身嘉木样呼图克图严加诰诫,勉为良善,熟料反挟仇恨私自投归隆务寺管属。……于今竟敢集众擅杀我寺熬茶佃户,以致寺属众番心各不服,亦复图谋报复。”(11)其二,源自章嘉活佛乾隆年间划定拉寺教区范围包括了循化藏区及巴燕戎格厅、贵德厅与四川境内部分区域的“僧俗汉番蒙古”(12),使拉寺致力于谋求上述地区的宗教权益。事实上,拉寺所依据的这些印据,均不为官方承认。陕甘总督杨昌濬与西宁办事大臣萨凌阿说:“该寺持有应追未缴旧据,屡次勾串生衅。……光绪元年,隆哇、卡家等处番族争夺供应,互相厮杀。经前督臣左宗棠派队惩办,将卡家等族交沙沟总管,有执照。是沙沟、黑错、卡家等处粮番不归拉布塄寺管束,历经办理有案。”(13)然而,拉寺并不甘心,以废印据作为口实,首先纠合所属部落向黑错寺发动了攻击,声言:“今查明他黑错仍是我的族分,我把黑错打过了。”(14)
三、事件的升级与官方的介入
当刚红布被杀事件发生之时,拉寺寺主嘉木样活佛正在黄河南蒙古郡王牧地游历。即由嘉木样拉章襄佐与工拭卜纠集卡加寺江洛捏力哇及十八昂欠(15)、买吾等族集众四千余骑,向黑错等处报复。五月二十九日,扎油、桑科部落攻打黑错寺所属黄卡庄。六月初一日,洮州厅所属佐盖买吾红布与卡加寺江洛捏力哇率领多化日、博拉、阿木去乎部落武装攻打黑错寺所属尕细庄,并将黑错寺所属17庄勒降(16)。黑错寺所属寺院、部落人心惶惶,纷纷逃散。其时,拉寺武装力量将黑错团团围住,通过奉办南番案西宁厘局委员候补知县张时熙与拉寺协调,遂由拉寺“派人传示各处撤队,该众番等均已遵从”(17)。
黑错之围虽解,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初九日,贺尔仓、沙沟寺、隆哇三处武装八九吾人扑至拉寺所属塘噶山,将伊寺所属该山之上下两庄番民全行掳去。于是,冲突继续升级。拉寺武装力量在买吾红布、江洛捏力畦的率领下,转头北上,进攻德尔隆寺院集团其他寺院、部落。沙沟捏力哇传谕所属各部落寺沟十头、霍尔藏、隆哇武装力量齐集隆哇、塘尕、札希地方堵御。六月初十、十一两日,双方遭遇。十六日,买吾等再用枪炮扑攻,霍尔藏等族接仗。
拉寺攻打黑错的消息传达隆务寺,引起了隆务寺的高度关注。这个拉寺的老对手在光绪年间一系列的竞争中,时常处于劣势,隐忍多时,图谋一雪前耻。故隆务寺沙力仓昂锁声称:“黑错、沙沟原是我们属下的,俱都知道哩。我们的属下番子,从前被拉卜塄加木样夺去我贺尔族六庄、官受十庄、多哇族二庄、加勿录曲三百家,那时代我应要出兵,亦害怕王法,死心忍了。今年又要夺我的黑错、沙沟……我们前后的事,思想是我们坐住哩么?”(18)六月十三日,由昂锁下里率领所属“热贡十二族”武装出兵(19)。十七日,隆务寺武装衔枚轻进,直扑拉寺,烧杀抢掠,并将所属拉加寺摧残一空。十八日,隆务寺武装又拆毁昂欠山庄,杀死拉寺捏力哇与阿木去乎红布等20人(20)。同日,隆务寺武装退驻上南木拉。不意该部落已经投顺拉寺,拒绝隆务军队驻扎。双方由此发生争执,隆务军队将该部落所属村庄抢掠焚烧。
拉寺在上南木拉吃了亏,心中不忿,听说黑错寺夕只仓、襄佐与捏力哇回归,遂由买吾红布、江洛捏力哇带队,准备于六月十九日再次攻打黑错寺。十九日,官军抵达黑错寺,双方各自撤兵。随后,在南线的冲突基本结束。
随着隆务寺的介入,于是“自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下旬,西南两番远近三四百里自杀焚烧,几有燎原不可扑灭之势”(21)。这就引起了地方政府的恐慌,积极实施干预。五月二十六日,循化厅同知长赟得知拉寺欲调所属各部落土兵进攻沙沟寺,立即差传拉寺襄佐、捏力哇,“责令各该处头人弹压散户,不得聚众闹事,自取灭亡”(22)。并予令隆务寺不准出兵,帮同打仗。六月初四日,又将双方启衅情形分别上报陕甘总督、西宁办事大臣,请求派兵镇压。六月初十日,长赟再次上报,声言:“……其凶残、贪暴、勒降拓土之心,实与元昊、赫连勃勃等无异,不日必为国家巨患。”(23)
循化厅的报告引起了杨昌濬与萨凌阿的重视,分别据实将拉寺与隆务寺冲突情形上奏。清廷谕令两者会商“迅即弹压解散,并饬挐匪首,讯明惩办”(24)。杨昌濬随即指令河州镇就近弹压,并委派循化厅同知、洮州厅同知、贵德厅同知会查案情。河州镇则委派统带沈福田,配合循化厅限期前往实地查勘、弹压、会审。
六月十八日,沈福田与长赟率队驰抵沙沟寺,饬令隆务寺昂锁:“即将兵在本境扎住,速即随差前来听候本府、统领面谕,替尔作主,秉公查办。”(25)次日,沈福田、长赟再次会谕隆务寺昂锁,约定十日不可打仗,说:“若再不收兵便不合道理……须多候几日,不可打仗。”(26)长赟亦知会拉寺,表示:“传调尔两造秉公讯明详办,就近办案,并不偏向那个。”(27)然而,对双方的安抚和震慑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在北线,冲突依然不断,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隆务寺武装又烧毁庄村多个。随后,七月初三日,循化厅同知长赟随带数十骑亲往拉寺查勘烧杀情形,并传集众僧开导利害。是日,隆务寺又抢去拉寺佃户多人。
进入七月后,随着统带马安良率队,会同洮州厅同知、贵德厅同知以及陕甘总督委员等到达南番境内,分别驻扎,就近进行弹压,争斗方才平息下来。随后,会办各委员分别传调两大寺院集团涉案主要人员到案,并查勘各处被烧杀焚掠之情形。然而,双方涉案人员并不如期到案。
不得已,各会办委员齐聚拉寺与沙沟寺适中之白土坡庄,一面好言安抚隆务寺昂锁,表示“尔昂锁原被一经谕调,即行前来投诚,必详请大宪恩施,按照古规番例上办理,不致锁拿提赴省垣西宁”(28),一面严谕嘉木样活佛、襄佐及十八昂欠“刻即将为首领兵之花利哇还布、江洛捏力哇、买吾红布及前票传所提各犯限三日内迅速一并交案”(29)。这样,延至九月初六日,冲突双方主谋人员方始全部到案。
四、冲突的处理结果与权力结构
委员们在白土坡商议按照番例番规议结,中心点就是,按照藏族地区的传统习惯,根据双方实际受损情况,互相顶抵,进行赔偿。由此,关于这次冲突的处理,大致上可以归结为:(1)登果庄、上南木拉与下南部拉及卡加等地,仍归沙沟寺赛仓活佛管辖,给循化厅纳粮,但须给拉寺熬茶(即送香火钱)作为隆务寺杀拉寺捏力哇的补偿;(2)互相顶抵损失,隆务寺短拉寺7命,由投靠黑错寺之多化日部落11户承抵,并令其归洮州厅管辖;(3)断令卡家寺僧佃仍归卡加千户管辖,别人不得冒充头目管束,沙沟岁仓只准租种卡加寺土地,不准干预别事;(4)关于滋事凶手卡加寺江洛捏力哇及拉卜楞、沙沟、黑错等寺管事头目由嘉木样等结保,以后永不滋事;(5)追缴拉寺所存旧据,勒令销毁,另立两造遵依条规,分给执照(30)。
案件处理的结果可谓出奇的冷落与平淡:作为肇事方的拉寺不仅没有受到“饬挐匪首,讯明惩办”的究办,反而还得到官方对其向南木拉等地收取香火钱的正式承认,拉寺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也扩展了自己的势力。为什么在地方政府看来一场波及方圆数百里的动乱,却又如此草草收场呢?
其实,这与清朝对循化藏区的施政及其所造就的特殊的权力运作机制有着根本的关联。循化藏区自雍正初年,因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反叛,使清朝得以挟军威而将其纳入到正式的统治系统之内,改变了该区出现的“自明以来……惟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营、伍官员”(31)的局势。并于其地设置循化厅与循化营、保安营、起台堡营。然而,循化藏区“清代名义上属循化厅,但羁縻之而已。”(32)这样,一方面清廷借助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宗教神权羁縻蒙藏各族;另一方面则借助传统的部落制度,通过设立土司或土官的方式,笼络循化藏区内的藏族上层,以便政府的驾驭并降低统治成本。所以,在谈及为什么不严加惩处拉寺与隆务寺的肇事双方时,杨昌濬与萨凌阿特意强调:“就番族擅自称兵构怨,作为不靖,即痛加剿办,予以惩创,原不为过。第究系番与番閧,当无实在抗官情迹。”(33)
因此,所谓羁縻,不过是处处仰仗“兵威”的震慑力量,即在维持地方统治时,清朝总是把强制性权威资源作为救命的稻草。然而所谓强制性权威主要通过其威慑力量来实现或达到自己的目的——经常性地动用这种资源的后果势必导致强制性权威退化为强制性权力,并最终沦落为赤裸裸的暴力。
而在土司与土官制度下,在各个部落内部基本上还维持着军政民政一体的权力体制。在该体制下,“大凡重大事情,必须经头人亲自处置,大部落头人还拥有独立的行政权、司法权、军事权等”(34)。因此,部落头人有处置属民的权力,而大部落则有处置小部落的权力。故而,隆务寺昂锁一再强调沙沟、黑错杀当刚红布是“他们自己杀了自己的人,与他拉卜塄并没有相干”(35)。不过,在大的部落或者部落联盟中,亚部落之间因为缺乏较为紧密的血缘关系,凝聚力并不如亚部落内部那么强,经常会因为安全等因素,导致大部落内部的分裂。当刚红布欲摆脱沙沟寺的管辖,究其原因,乃“大加依恃总管名目,僧俗的事情上,独断独行,又把旦刚百姓强行拴头。旦刚看见害怕,于今年正月内投了拉寺磕头,拴了头”(36),无外乎担心自己被千户大加吞并,寻求奥援。王尕滩女头目录毛加无非也是因为“温布连捏力哇二人,好心一些没想的,将我录毛加无端欺负一年的,尽想法害了”(37)。于是,两个亚部落的属民便在头人的指使下投靠拉寺。
循化藏区内格鲁派寺院政教合一制度的建立,完全得益于清朝得宗教神权政策。该种体制内,寺院以其宗教教义获得了一般藏族民众的普遍信仰,并通过“化身论”与“上师论”及相应的意识形态宣传,使藏族民众不仅心甘情愿地对寺院进行物质上的布施,甚至愿意为之献身。寺院因活佛而占有了宗教资源;而活佛本身也就具有了魅力型权威的色彩,从而使其信众匍匐在脚下。那些具有崇高地位的活佛的宗教权力就具有了无限的拓展性。一些部落头人为了能够继续统治自己的属民,也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就会将所属部落布施给寺院的活佛。如甘加千户就以拉寺施主的身份将“我族百姓地方募化与拉布浪寺”(38)。还有一些部落头人建筑寺院,将教权奉献给大的寺院,长此以往,也就被架空了权力,连自己都成了寺院的教民。
宗教制度凌驾于部落制度之上,活佛凭借宗教权威的角色将所属教区内的政权、经济权力与社会权力,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循化藏区内,部落组织也就具有了新的形态——以寺院为中心的超越血缘的地域性甚至跨地域性的部落联盟。当然,部落之间的竞争也就具有了新的格局,不再是单个部落之间的竞争,而是以寺院为中心的部落联盟之间的竞争。所以,循化厅在光绪十六年卡加寺与沙沟寺再次爆发冲突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案,明系岁仓、江洛争佃,暗系拉布塄与隆务两寺一则欲得南番,一则恐失南番。”(39)而寺院之间的教权竞争,亦以部落武装冲突为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
教权与部落权力相结合,寺院可以活佛之宗教权威相号召,部落则因背靠强大的部落联盟而有恃无恐,在力量的结合中增强着彼此的势力,对于循化藏厅的谕令,置若罔闻。如长赟在多次谕令隆务寺不得参加冲突未被遵守后,非常生气地质问:“尔昂锁自应听候官办,乃本府前已三次差人弹压,统帅沈前亦派弁弹压,何得抗不遵从?”(40)即使官方出动军队,部落武装也要视情况而定,只有在不能力敌的情势下,才会听命。如河州镇所属军队在弹压买吾的过程中,就出现了:“营务处出其不意,一耀军容,彼犹距寺八里,环列三大营,自十九至二十二与我军相抗三日。接奉营务处谕,地方官严谕,该耆老头目见事不善,始震慑退兵,拉马投诚。”(41)
其实,对地方官来说,他们很清楚寺院在背后所起的作用。会办委员对于隆务寺不遵谕令无可奈何,而对拉寺更是感觉无能为力。会办委员一再强调拉寺为“循化腹心之一害”,“文武官所不敢遽问者,以伊系属寄藉,如丑石一块,良莠不齐,投鼠忌器,各存自保之心,逐令其无所忌惮。”(42)实际上,地方官员所忌惮者有二:一是拉寺势力强大,且其活佛群体在循化藏区具有广泛的影响,一旦对拉寺动武,兵员过少则不足弹压,兵员过多则耗费过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长赟说:“拉寺……久为循化心腹之患……蒙番各地大半据为己有。……此案初起全循震动,附城四五十里中库、崖慢、夕厂三处番撒六百余名,悉被拉寺调去他处,可知约计实不下万众。”(43)故而,隆务寺昂锁不无嘲讽地说:“你王法有个礼信,是到如今坐在沙沟里,想拉卜楞你们的话莫遵的,他们若话听者遵是你们拉卜楞不敢去?”(44)其二,则是因为地方官员不敢触碰因清朝推行黄教政策构建起来的循化藏区寺院与朝廷之间的关系。故会办委员在调查拉寺后说:“番蒙各呼图克图多在此建刹,声势愈大,气炎愈盛。”(45)拉寺虽为地方寺院,却因寺属活佛多被封为驻京呼图克图而与朝廷中的诸多亲贵与权臣相互往来,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难予以致命打击,可能还会遭到反噬。
由此,在循化藏区内,地方政府只具有半失效的政治权力,不得不依赖军事上的强制力维护统治。而寺院则通过有效地运用宗教资源,使自身凌驾于部落权力之上,形成了纵横捭阖的局势。即使政府通过强制力来达到自身的目标,也不得不仰赖区域性的宗教领袖或政教合一体制发挥作用。故长赟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因不能拘拿到拉寺方面的主谋人物,强调:“须嘉木样来寺,方能完局。”(46)
由上可见,以部落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权力构成了整个权力运作机制的基垫,其他两种权力只有通过这一权力才能在循化藏区发挥作用。以宗教资源为基础的寺院权力在该区域内上升为魅力型的权威,虽然在总体上须仰仗清廷而取得相应的合法性、屈从于地方政府的强制力,然而在面对地方行政系统处理区域内事务时却具有相对的优越性,是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赖的基本力量。否则,地方行政系统所具有的政治权力,就很难真正发挥相应的效力,产生另外一种政府失效——行政体系所依据的汉族儒家文化的范畴与循化藏区地方性知识之间的文化张力导致的社会价值规范之间的异质。统治机构与地方性知识之间张力所产生的特殊的区域社会权力运作机制,基本上代表了整个汉藏文化走廊区域社会的基本特点。这些区域大致上囊括了整个康区和安多藏区,它们既与于西藏依靠宗教领袖实施的政教合一制度不同,也与汉族地区主要依靠乡绅实施地方社会自治的“家国同构”的权力运作机制迥异,呈现出一种变异型的区域社会权力运作机制。
注释:
①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07页。
②青海省档案馆藏《会办南番买吾、黑错争斗详报拟结折稿》,档案号:7—永久—2925。
③[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页。
④洲塔:《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⑤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5辑之杨书霖编《左文襄公(宗棠)全集》第4册,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4年版,第1884页。
⑥扎扎:《拉卜楞寺的社会政教关系》,青海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
⑦红布,又称红保、洪保,属于地方土官性质,即部落头人的通称。此多为南番的称呼,在西番为昂锁,又称起索、囊锁等。在隆务寺,特指辅助寺主夏日仓活佛(又称沙力仓)实施政教合一统治的土官。
⑧青海省档案馆藏《河州镇、贵德厅、循化厅会办南番案详报事》,档案号:7—永久—4643。
⑨(22)青海省档案馆藏《循化厅为差传拉卜塄寺香措捏力哇事》,档案号:7—永久—2686。
⑩(36)青海省档案馆藏《下拉卜拉旦刚庄控被沙沟寺抢杀事》,档案号:7—永久—4745。
(11)(17)青海省档案馆藏《奉办南番案西宁厘局委员候补知县张时熙禀查办情形》,档案号:7—永久—4397。
(12)青海省档案馆藏《拉卜楞寺襄佐安木将所写张家呼图克图给拉布塄寺的番字印据》,档案号:7—永久—4690。
(13)(21)(33)青海省档案馆藏《陕甘总督杨、青海大臣萨为甘肃循化厅属拉布塄寺番僧纠集买吾等族与黑错、沙沟、隆哇、隆务、卡家、扎喜等寺及上下火力藏等族互相械斗情形折》,档案号:7—永久—2965。
(14)青海省档案馆藏《拉卜楞寺为黑错族属上循化厅的禀》,档案号:7—永久—4643。
(15)拉章意为活佛的住所,在拉寺专指嘉木样活佛的住所。襄佐为音译,又写作相佐、香错、香措等,意为总管,帮助寺主处理政教事务,尤其是管理所属部落和对外事务,权力仅次于寺主。工拭卜又写作更擦布,意为代表,是嘉木样活佛派驻各寺的代表,行使政教两方的权力。捏力哇意为管家。昂欠在拉寺指仅次于寺主嘉木样的18位大活佛的住所。以上各词均为藏语音译。
(16)青海省档案馆藏《隆务寺为黑错寺所属各部落村庄被烧杀等情给循化厅的详报》,档案号:7—永久—4535;《黑错捏力哇、襄佐所供被抢杀情形》,档案号:7—永久—4755。
(18)青海省档案馆藏《隆务寺沙力仓昂锁为出兵事上会办番案各委员的禀》,档案号:7—永久—4544。
(19)青海省档案馆藏《隆务寺沙力仓昂锁为出兵攻打拉卜楞寺给循化厅的禀》,档案号:7—永久—4535。
(20)青海省档案馆藏《拉卜楞寺为被隆务寺兵抢杀寺院、村庄上会办委员的禀》,档案号:7—永久—4640。
(23)青海省档案馆藏《循化同知长赟续报查拉布塄焚杀勒降紧急情形》,档案号:7—永久—2681。
(24)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第9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13页。
(25)(40)青海省档案馆藏《会办委员、循化厅等为会谕严禁止兵事给隆务昂锁等的谕》,档案号:7—永久—4755。
(26)青海省档案馆藏《河州镇统领、循化厅会谕隆务寺昂锁十日内不可开战的谕》,档案号:7—永久—2679。
(27)青海省档案馆藏《循化厅为前往就近查办给拉卜楞寺的谕》,档案号:7—永久—2682。
(28)青海省档案馆藏《会办委员等为将公平办案、速来投案给隆务寺昂锁的谕》,档案号:7—永久—4533。
(29)青海省档案馆藏《循化厅为将为首滋事各犯提案给嘉木样呼图克图的谕》,档案号:7—永久—4059。
(30)青海省档案馆藏《会办委员因旦刚红布被杀所起拉卜楞寺与隆务寺等冲突的处理结果》,档案号:7—永久—4723;《甘肃布政使张、提刑按察使裕为卡加寺与沙沟寺冲突札循化厅》,档案号:7—永久—2944。
(31)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第1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5页。
(32)张其昀:《夏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6页。
(34)星全成、马连龙:《藏族社会制度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35)青海省档案馆藏《隆务沙力仓工拭卜等所供旦刚红布被杀及冲突事》,档案号:7—永久—4755。
(37)青海省档案馆:《还仓录毛加并众人等在各委员大人、循化大老爷上具的禀》,档案号:7—永久—4744。
(38)青海省档案馆藏《西宁办事大臣为甘家千户继任事札循化厅》,档案号:7—永久—2594。
(39)青海省档案馆藏《循化厅同知长赟为卡家、沙沟冲突上宪台的禀》,档案号:7—永久—2945。
(41)青海省档案馆藏《循化厅为买吾投诚上河州镇的禀》,档案号:7—永久—2678。
(42)(45)青海省档案馆藏《会办委员等为拉卜楞寺势力强大请示办结办法上的禀》,档案号:7—永久—2684 。
(43)青海省档案馆藏《会办委员为访查拉卜楞寺情形上的禀》,档案号:7—永久—2684。
(44)青海省档案馆藏《隆务沙力仓昂锁控告拉卜楞寺的禀》,档案号:7—永久—4545。
(46)青海省档案馆藏《循化厅为在拉卜楞寺访问情形上的禀》,档案号:7—永久—26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