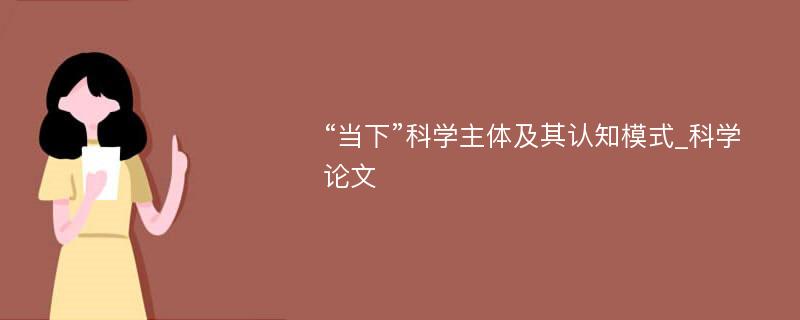
“在场的”科学主体及其认知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主体论文,模式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上对科学的看法常常因为主体与客体绝对的二元对立而陷入困境,这个困境使得科学的真理观要么滑向客观主义的绝对主义,要么滑向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这两种立场都没有恰当地反映出主体在科学实践中的恰当地位和作用。我们将以上述方式所看待的主体称为“不在场的”(non-present)科学主体。现代科学的实践活动和科学哲学的发展越来越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实践中的主体不仅是世界的观察者,同时也是塑造人类环境的参与者和知识形成的建构者,主体的具身认知结构(embodied cognitive structure)和其内化的社会文化状况都对知识的形成产生影响。库恩(T.Kuhn)之后,“不在场的”科学主体越来越受到质疑,比尤利(A.Beaulieu)提出科学知识的人类学研究需要从原来主体与客体“共置”(co-location)的观念,走向它们“共在场”(co-presence)的观念(Beaulieu,pp.453-470),即在科学活动中主体并非只是在物理上与客体共置在一个场所中,而是渗透在科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并成为科学知识建构和形塑“生活世界”(life-word)的一个基本的动力学力量。当前,随着对科学活动中认知行动者(cognitive agent)或认知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入研究,“主体在场的科学”受到广泛关注。吉尔(R.N.Giere)认为,对科学活动中认知主体的研究是继“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之后形成的又一次重要的观念革新,它形成了一个“科学知识的认知建构”的主张。(Giere,1992,p.XIX)
一、“在场的”科学主体和科学共同体
传统认识论认为认知者只是作为观察者存在,这种认识被杜威批判为“知识的旁观者理论”(杜威,第21页)。它制造了认知的主客二元论,使得主体在认知过程中处于沉默状态和完全被动的地位。在科学建构论的推动下,这种“不在场的”科学逐渐为一种注重认知主体及其行动的“在场的”科学所取代。主体“在场的”科学强调个体认知的首要性和科学的主观性,认为主体依赖一定情境作出判断。然而,就建构论本身来说,它的这种立场在批判传统的客观主义的同时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即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都“没有把握住科学家真正在做的是什么,都是对于科学活动的糟糕模型”。(Hackenberg,p.392)
为避免上述两个极端,新的实在论走向了第三条道路,它“既不能像传统启蒙科学那样具有离开情境的普适性,也不能像社会建构主义那样负载价值的特殊性,这种科学既承认有一个真实世界,也承认与世界的交往是有意义的”。(ibid,p.393)新实在论表现为多种形式,包括普特南的自然实在论和吉尔的透视实在论等。这种努力被认为是当前自然主义潮流中知识构建各种可实现通道的主要方式,它有利于消除认知二元论,实现主体的在场。(Collin,pp.18-19)这种实在论受到实用主义的较大影响,并强调“科学家提出的关于实体和过程的理论陈述是否具有现实合理性”(Giere,2006,p.3)的问题,因此也被称为“实用主义的实在论”①。
鉴于科学主义和建构论的不足,新实在论强调,知识并不是完全由客体属性决定的心智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而是一种由主体与客体共同建构的、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科学实践中的“不完全表征”;这既是一种主-客互动,也是一种理论-实践的不断循环。(李恒威、黄华新,第44页)
当我们谈论科学活动在场的主体时,我们既是指一般意义上的认知个体,更重要的是指完成科学任务的科学共同体。因为在现当代复杂的科学实践中,科学活动中的主体形式更多地表现为共同体。因此,要全面认识科学活动中的认知主体的地位、作用和表现形式,我们就有必要考察作为共同体的认知主体的认知活动——集体认识(collective cognition)。
二、科学共同体的认知形式——集体认知
集体知识或者说集体意识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那里。在他看来,知识是集体表征的产物。(涂尔干,第42-43页)受到涂尔干“集体意识”思想的影响,社会建构论强纲领采取了一种社会决定论的模式,认为一切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种思想虽然把科学共同体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却陷入了相对主义的困境而无法看到科学的实在性。之后,哲学家塞尔和吉尔伯特以个体间性为出发点说明集体知识的合理性,从而为科学共同体的认知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塞尔认为,集体的意向性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是常见的,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是“实用的而且确实是本质性的”,它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塞尔,第117页)社会实在的形成依赖于“集体-意向性”或者“我们-意向性”。它的实现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个体意识到自己是某个集体的一部分,把集体的目标当做自己行动的目的,并意识到其他成员也这么认为。第二个条件是认知活动是在一个共同的“建构性规则”下进行的,因而我们的行动必然受到这些规则的“调节”。但是这些规则并非是一张没有缝隙的网,行动者可以通过主动性的认知活动对规则进行重新阐释。第三个条件是对于自然物件的“功能的归属”。通过归属,共同体内的行动者才具有认知活动得以开展的工具。这种功能归属总是和一定的目的相关,即具有目的导向性。(同上,第113页)
然而,“集体意向性”的存在必须以“与观察者相关联”为前提。塞尔认为,只有社会科学才具有与观察者相关联的特征,即认知是依赖于观察者的;而“自然科学涉及不依赖于观察者的特征”。(同上)于是,塞尔的“集体-意向性”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并不能应用于自然科学。
吉尔伯特则推进了这一思想,认为集体知识不仅存在于社会科学中,也存在于自然科学中,并特别表现于“科学共同体”中。这种集体知识有别于个体知识,对科学的发展尤为重要。吉尔伯特批判了集体信念的累积性解释,认为应代之以一种非累积性解释,并以如下三个命题来表示:“(1)一个群体G相信p,当且仅当G的成员接受了p;(2)群体G的成员共同接受p,当且仅当p在群体G中是普遍知识;而且(3)群体G的个体成员都公开表示与群体G中的其他成员以假设性的承诺一起去共同接受p。”(Gilbert,1987,p.195)
在吉尔伯特看来,集体意向不仅是一种知识,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也是一种信念,具有伦理学意义。她用“多元主体”(plural subject)和“共同承诺”(joint commitment)这两个概念分析了集体信念的形成。
首先,集体是由具有参与意愿的多元主体组成的,他们在共同行动之前就具有一个共同目标。共同目标并不是事先设定好的,而是通过协商和规则在行动中制度性地或者临时性地产生出来。其次,一旦多元主体之间达成共识,就自然产生了“共同承诺”。共同承诺是对集体中成员的一种道德和制度约束,它保证了行动目标的完成。每个成员不仅有义务去遵守它,而且有充分理由去按照承诺行动。但是,个体也会有一定的能动性,从而与集体意向形成了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并共同参与着集体知识的建构。第三,对于成员来说,他必须意识到自己与集体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并且自觉地感觉到与集体的关联。这也意味着,当其他成员行动时,个体也会相应地采取行动。(ibid,1989,pp.200-202)
为说明个体更愿意获得一种共同接受的知识而不以知识为真或可能为真作为前提,吉尔伯特提出了共同接受(joint acceptance)模型,认为存在三个可能性:首先,集体认知过程是一种理性的协商过程。其次,影响个体愿意承担何种角色的个性和情感的因素会进入到集体知识的形成过程中。对于个体来说,他们更愿意和大多数人保持一致以不让其他人认为自己有些离群,而对于真理并不抱多大兴趣。第三,人们更愿意通过辩论而使自己的观点p成为集体知识,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认为p是正确的。(ibid,1987,p.197)
可见,集体意向性或者说集体认知的出现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多元主体的出现、共同目标、共同承诺和共同接受。和塞尔相比,吉尔伯特更强调个体间的协商和承诺的形成,或者说更具有政治学的色彩;不足的是,吉尔伯特忽视了塞尔提出的“功能归属”问题,即认知本身是有物质条件的。
总体来说,共同体中科学的事实构造是以集体认知的形式展开的。作为集体认知的条件是多方面的,它不仅需要个体间的共同承诺,同时也需要成员的共同行动及其相应的环境。然而,无论是塞尔还是吉尔伯特,他们理论中的集体成员都表现为人文主义下的人类。为能描述科学的丰富性和实践性,科学哲学家已经把非人类引入科学事实的构造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认知研究发生了后人文转向,这种转向促使集体认知模式不断修正和发展。
以科学共同体为单位,围绕着科学行动中集体知识的形成及其有效性等问题,集体认知的修正和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库恩和默顿为代表,提出了科学活动中主体认知的角色结构和作用,较好地解释了知识如何从群体过渡到个人的问题。为解决自身“结构化”色彩过浓的问题,角色认知需要走向角色丛认知。第二个阶段,以波兰尼为代表,认为科学中的认知不能只局限于科学制度或者共同体规定的显性知识,而应更加注重科学行动所需的意会知识。该模式解决了知识从私人性向公共性过渡的问题,并得到了后来科学论心理学派的响应。第三个阶段,主要以吉尔为代表,在当前认知科学的影响下提出了科学主体的分布式认知,认为科学活动是共同体中各方力量参与的结果,强调实践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该认知模式使得科学中存在的个体和社会、私人性和公共性、物质与非物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对立问题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决。
三、认知主体的角色辨析
库恩的范式革命之后,认知原子主义在科学论中失去了自身的解释力,科学中的主体从原来的“神圣”个体变成了共同体的成员。从个体到共同体,分析单位走向了群体和制度。那么,作为群体的先验知识是如何成为个体的知识的?知识是如何从共同体过渡到个体的?科学社会学家默顿以角色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科学家往往通过习得制度和文化规定,通过扮演一定角色,最终达到追求真理的目的。(默顿,第362-365页)
“角色”概念较早出现于实用主义先驱詹姆斯的思想中,其后在美国芝加哥学派学者库利(C.H.Cooley)和乔治·米德(G.H.Mead)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早期角色概念主要用于分析在社会行动中个体通过对“参照群体”的模仿、习得和内化而形成“自我”的现象,这种观点解释了文化中个体心灵的发展和成熟。随后,角色概念逐渐与社会地位相结合,指一定的群体结构对于个体的社会期待。作为社会学家的默顿则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对科学家行为的理解,他认为,“科学的社会结构具有其自己独特的地位序列和角色序列,它们通过复杂的社会选择过程分配给其成员”。(同上,第712页)但科学家并非是乌托邦中追求真理的圣人,他们也有自身的兴趣和利益考虑并具有特殊的人格。他们之所以能够实现“扩展确证知识”的科学目标,是因为个体动机受到了制度或者规范的规训。通过一定的角色扮演,“科学家内化了一定的价值和规范,并以之为行动的准绳”,从而实现科学的目标以达到追求客观性知识的结果。(Magnus,p.304)
科学家的角色通过一定的群体及其规范得到运作,比如作为“局内人”的精英群体对“局外人”形成了角色引导,通过师生关系群体隔代之间进行了角色塑造等等。然而,这样的角色概念带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被当代社会学家特纳(J.Turner)称之为“结构主义角色理论”(特纳,第49页)。它抹杀了个体因素对于知识的建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科学主义的认知困境。基切尔(P.Kitcher)也指出个体价值和制度目标之间并不冲突,他认为个体和制度的矛盾并不存在,个体性的介入只是制造了科学行为的主体性而并非科学知识的主观性。正是“把科学家视为传统经济学中的自我利益追求者”,科学才获得了有序性,从而不至于陷入默顿视野下的科学家所遇到的矛盾心理,科学的发展也不再是传奇。他甚至指出,正是由于科学家遵从项目计划以及自身的利益和兴趣,科学的资源和劳动力才得以合理配置,一些看起来不怎么有前途的科学项目才得到某些科学家的重视。(Kitcher,pp.303-389)所以,正是对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以及在此基础上通过规训获得的对规范的自愿服从,才既保证了科学的客观性,也保证了其实现的主体性。
因此,传统角色理论错误地把科学家当做个体的唯一角色来看待,而忽视了现实中的科学家承担着多种角色。从认知角度来看,科学家不仅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而且也是在日常世界中生活的人,这也正是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必须取代“科学世界”的原因。胡塞尔认为,人的生活是“自我意向的生活”,科学家只是日常生活中有目的和意向性的人;同时,科学活动只是一种“生活构造”,必须在“生活世界”中才能得到理解。(胡塞尔,第107页)因此,对科学主体角色模式的理解不应强调结构主义的规范性特征从而走向“结构泛化”,而应强调科学活动的互动性和行动者角色的建构性。必须认识到,行动作为行动本身得到考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科学活动的角色丛理论不能从一种对于科学实在的模型滑向一种模型的实在。(亚历山大,第176页)
默顿也承认个体价值和制度认同对于形成“客观知识”具有同样有效性,他认为“从发现中得到快乐和对科学同行的承认的追求”并不矛盾,它们是“同一个心理硬币的两个侧面”,其中“同一个心理硬币”指“促进知识”的价值观。(默顿,第465页)他进一步指出:“科学家的地位包含的不是单一的角色,而是复杂多样的一组角色”,科学家不仅可能是研究者和教学者,也有可能是管理者和把关者,同一角色内部也有可能分化出多种子角色。(同上,第712页)在当今社会学中,默顿所说的复杂角色被称之为“角色丛”,指在日常生活中因承担多项任务而在规范上具有多重社会期待的现象。因此,科学家既是科学研究的从事者,同时也可能是家庭生计的承担者,个体角色内容不能单一化。
通过“角色丛”的引入,个体就不只是规范的被动接受者,而且也是规范的积极建构者。同样,科学活动中的主体就不仅是角色的扮演者,而且也是角色的领会者。从实践的角度看,“角色丛”使得个体的主体性和社会规范下的客观性得以结合起来。根据特纳的理解,对于角色的理解既要强调其本身的功能性(实现外在目标),也不能忽视其“沉积性”(个体获得了回报和满足)和“代表性”(体现一定的文化价值)。(特纳,第56页)在科学活动中,主体通过互动和角色建构实现了扩展确证知识的目标,也使个体获得了回报和满足;这两者并不冲突,它们往往在一定的文化价值下实现了互相适应。
四、意会认知——行动中认知
不管是布里奇曼的操作实在论还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都认为知识或者科学应作为一种行动来理解。行动往往由主体来完成,既然这样,科学就成了“科学家的活动”,甚至是“科学家个人的活动”。(《布里奇曼文选》,第8页)无论是科学概念的确定还是科学理论模型的提出,都必须从“我”出发并在“我”的操作中得到实现,因而科学具有“私人性”特征。
然而,私人性的科学如何走向公共性呢?布里奇曼把这个问题称之为科学的“双重性”问题,即“我的科学”不同于“你的科学”。(同上,第31页)为解决这个问题,具有私人性的科学必须获得共同的意义或者使用共同的注释文本,以获得公共性。但是,文本意义的获得和使用是有条件的,而且这个条件往往会发生变化,因而还是会遇到“双重性”的问题。
斯金纳也对“自然科学中的私密事件”问题做了探讨,提出私密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由强化获得的“条件看见”和由计算、分割等获得的“操作看见”的混合物组成的。(斯金纳,第255-256页)通过强化性的条件以及对于对象的实际或想象的操作,再加上可显示、可表达的感觉识别和无法言说的操作技能,共通性的信念和公共性的现实就进入了私密性的经验,于是知识就既具有经验的主体性,也获得了现实的有效性。他举例说,人对于雨可以有多种反应:雨可能会让你躲避它,或捧在手里喝它,或因之准备收庄稼。(同上,第259页)那么,哪一个反应是由“雨”产生的?事实上,我们首先会以一种先定假设去判断它。然后,在特定背景下通过操作来获得其自身的意义。比如,突然下起的雨对于在路上行走的你来说,只是一种会把你淋湿的液体;然而,若是在干旱的时候,雨对你来说就会有更多的正面意义。
从这里可以看到,知识的获得有三个互相联系的环节:首先是承认物理对象本身,其次是个体通过强化获得的对该对象的反应,再次是在一定情境条件下主体对该对象的实际操作。在斯金纳看来,认识的获得通过“反应性行为”和“操作性行为”得到完成。(张厚粲,第253页)我们的认知既是“吝啬”的,通过反射来行动;同时也是复杂的,以行动来确证和发展。然而,无论是角色理论还是布里奇曼的操作实在论都侧重于第二个环节,强调的是一种库恩意义上的相对的实在论:主体的认知总是受到共同体规训所获得的先验结构的制约,是情境条件的产物。这种认知模式具有群体中心主义的特征,既强调群体信念的限制性,也强调群体界限的明确性,从而忽视了物理对象、身体以及主体对该对象操作所带来的认识论意义。波兰尼提出的意会(tacit)认知对此做了较好的处理。他对斯金纳提出的两种行为进行了重新阐释,并提出意会认知以企图把它们结合起来,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观察、理论的个人性和公共性的矛盾。他把面对物理对象并对之产生的概念化反应称之为“焦点意知”(focal awareness),它常以系统的、公共的、可言传的知识形式表现出来;对对象进行操作并通过身体完成行动的过程称之为“支援意知”(subsidiary awareness),它是我们认知得以完成并获得意义的“线索”,常以非系统的、体验的、技能化的知识形式隐藏其中。(波兰尼,第120-123页)通过意知的整合,身体进入了知识的构成中,并形成了“在场”的认识连续体。在意会认知体系中,“支援意知”是最主要的,它提供了行动所需的技能。人的认识并非是一种先验决定的僵化结构或者陷入结构化牢笼的被动反应,而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认知在行动中以“突现”来完成自身的发展,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科学知识也是如此。因此,对波兰尼来说,不管是科学中的观察还是理论模型的选择,都是一个实践问题。正如查尔默斯(A.Chalmers)所指出的:科学中的知觉或者观察并非是被动的和个人性的,它常常是主动的,并通过行动本身获得自身的公共性。(查尔默斯,第33-36页)主体总是带着一个主动的姿态在操作中完成每一次认识活动,在实践中以实验的态度来面对每一次操作,并通过自身的调适和修正,最终保持一个自主的主体形态。在行动中,科学家通过直觉实现了科学发现和科学创造,然而一切直觉只有在科学的实践和操作中才会发生。因此,“通过考察技能的结构,我们就能够掌握科学家个体参与的本质”。(Polanyi,p.51)
作为科学认知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奇(C.W.Savage)通过研究发现,在自然主义化的基础主义经验论框架中,弱基础主义为有意识的人类知识提供了一种自然主义的理论框架,而强基础主义为无意识的人类知识提供了自然主义的理论框架。(Giere,1992,pp.214-224)这种观点肯定了无意识知识的重要性以及与自然主义的关联,可以说是对科学的意会认知理论的积极回应。
沿着操作主义的路径,波兰尼的意会认知体系认为知识是行动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发展中生成的,该模式较好地填补了科学的个人性和公共性之间的鸿沟,并给予集体认知以更多的物质和身体因素。从共同体的角度看,波兰尼强调了规训在科学认知中的作用,凸显了身体的能动作用。在规训中,身体只是作为共同体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存在;在知识的构造中,身体则作为共同体文化的积极建构者而存在。通过意会认知这个概念,波兰尼较好地说明了科学中认知的构造性特征。
然而,意会认知模式在强调知识的过程性和突现性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先验结构本身对于知识的透视性影响,也因为这样,它眼中的科学带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色彩。另一方面,该模式虽然强调了身体的重要作用,然而对于身体的技能以及身体扩展的工具却没有深入的探讨。
总体来说,无论是默顿的角色论还是波兰尼的意会认知论都强调了人类行动者在科学事实构造中的作用。但是,作为一种人文主义式理解,两者都忽视了非人类、物质、自然等在科学共同体进行认知活动中的作用。
五、分布式认知——弥散的行动者
在实践论的影响下,对于科学的解释不断出现自然主义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所要强调的并非是主体在科学中的建构作用,而是主体与主体、主体与非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这种观点认为,主体与非主体在科学中具有平等的地位,都是科学得以实现的重要源泉。因此,如何调动认知主体的“资源”成了当前科学是否得以有效地构建的重要话题。
哈金(J.Hacking)曾指出,科学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一种认知行为,它更多的是一个“理论、仪器、数据和分析互相协作的实体”。(Hacking,p.30)皮克林较早关注到这方面的问题。通过气泡室发展历史的研究,他指出科学实践是各种力量阻抗与适应的辩证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相互构造”,“人类力量与科学文化的物质维度和概念维度彼此融合,并在相互作用中实现稳定”。(皮克林,第69-72页)皮克林注重科学主体本身作为实践力量的“冲撞”意义,而后来的吉尔则更注重科学行动中认知主体的选择,科学中的理论、仪器、数据等都成了认知得以展开的“认知资源”。
吉尔提出了科学的“认知资源”概念,他认为“科学家对对错的判断以及研究内容的选择受到了他们自身‘认知资源’的影响,这些‘认知资源’包括他们经验的理论、使用的数学方法以及写电脑程序的能力等”。(Giere,1992,p.468)随后,吉尔吸取认知科学的最新成果,把认知在多主体的共生协作中通过“资源”的运作而完成的现象叫做“分布式认知”,从而把“认知资源”的概念进一步扩大了。对于分布式认知下的科学,吉尔则称之为一种“透视的科学”(ibid,2006,pp.13-15)。这种认知模式消解了对象和认知主体的两分法以及物质与意识的二元论,同时也解决了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矛盾。
以往人们考察世界时,常常假设对象与主体的对立。这种观点认为,离开对象越远,具有的物质特性就越少,比如静态的、受动的、无意识的、可分析的;离开身体越远,具有的心灵特性就越少,比如动态性、主动性、意识性、具身性。
然而,生活世界的主体本身就处于世界之中,世界并非是对象化于主体。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J.Gibson)为了描述生物与环境之间的互补性,提出了“可供性”(affordance)概念,认为“个体在知觉环境的同时也在知觉自身”。(Gibson,p.127)因而,认知首先是“在场”的,而并非是“主观心灵”的内在运作或者“出场”的“客观世界”的外在框定。非二元论下的主体认知特征可称之为“居间性”②,认知以对象主体化和主体对象化的形式进行。心灵不再是一种与物质相对立的东西,相反它与对象共同构建了一个行动的认知体系。主体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并非是离开环境和历史的随意彰显,而是个体的一种适应社会之后的能力的体现。当普特南定义心灵是一种能力的时候,事实上就把心灵的内涵加以扩展了。直到吉尔这里,作为透视的主体认知结构才得到全面表述。吉尔提出科学的“认知资源”和“分布式认知”的概念,以说明主体和世界本身并非处于两极,而是组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结合人类与非人类、物质与非物质的认知体系。于是,主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体,而是从个体走向了一个没有二元区隔的主体。在这个主体中,不仅包括仪器、机器等物质性的东西,而且也包括信念、兴趣、利益、角色等非物质的东西,原有的人文主义式的主体为一种后人文主义式的去中心化的主体所替代。另一方面,认知主体的边界完全被模糊化,主体、客体以及科学知识的生产环境都成为弥散的行动者(actor)。
科学的分布式认知或者扩展后的认知模式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刻画:
首先,认知是分布的,而并非只局限于人脑。它已经跳出了人脑本身,走向一种扩展形态,既具有身体、器具等物质形式,也具有设计、数据、观念等非物质形式。不同的人通过同一工具观察同一个事物往往具有相似印象,认知本身携带的物质性保证了我们行动的有效性和功能上的现实性。不同的人在同一场合看到杯子中的水会形成共同的认识,用不同的脑成像技术制作的大脑图其结构大致相同。
其次,科学中认知主体具有透视结构,往往渗透着身体的生物特性以及群体的价值、信念和利益等。在科学活动中,群体价值、利益和生物特性等通过身体以及制作的工具得到体现,比如色盲者和正常人对于同一幅画的色彩看法不一,用不同的光学理念制作的天文望远镜获得的是反映不同侧面或者体现不同层次的星空图。
第三,主体往往通过参与实践以使认知得到实现,并把物质性和主体性带入到实在的建构中。如同一个地域的地图可以制作成不同方式,例如可以是交通图或山径图或水利图。只有通过特定情境下的操作,认识才得以开始,否则认识本身要么停留在物质层的假设中,要么停留在主体自身的冥想中。总而言之,科学的分布式认知从透视性出发,经过扩展以后,实现了认知从群体过渡到个人,以参与性特征保证了认知从个体走向群体,以物质性和身体性特征实现了认知从心灵走向世界;这里,心灵与对象不再是二元对立的。
分布式主体认知体现了主体性与规范性相互作用的辩证结构,打破了心灵和物质的原有区隔和科学家身体和知识的“实践二元论”,使得科学论一向关注的人类与非人类、身体与世界等二元区分得到了消解,也使得众多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所关心的缺失的身体得以回归。由于二元分立的消解,科学中存在的人类与非人类的差别就不再存在,科学变成了一个交错着身体、器具、物质却又充满着意义的活的世界。
然而,科学不仅是主体性的,也是主体间性的,它是主体间沟通的结果。应该看到,科学不再是二元论框架下追求的客观性,而是基于实在的一种沟通理性,这是认知二元性消解后的必然结果。分布式认知或者扩展的认知形态为解释科学行为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方案,但作为一种行动理论却显得不够有说服力。
六、结语
通过引入“在场”的概念,科学主体的认知研究得以展开,并逐渐形成了一场认知建构的“革命”。为解释当前科学的发生和发展,做到言之有理又持之有物,实现科学主体性和实在性的结合,当今逐渐形成了关于主体认知实现的各种有效模式。这些模式既是科学主义影响下对于科学实在性坚持的产物,也是建构论影响下对于主体性强调的结果,并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汇聚成流。在科学主体认知研究的冲击下,新的科学实在论强调心灵之于世界的间接性与行动之于世界的直接性的统一,它不再是“绝对意义的客观性”,也并非是“规训意义上的客观性”,而更多的是一种“辩证意义上的客观性”。(Megill,p.223)
从传统的“上帝之眼”思维中走出来,角色认知强调科学共同体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对于角色认知来说,它试图解决共同体的知识如何成为个体的知识这一问题,从而缓和了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由于角色认知本身所具有的结构化色彩太浓,在其后的发展中被强调角色领会的角色丛理论所取代。
意会认知则试图解决私人性的个体知识如何具有公共性的问题。受到操作主义的影响,意会认知认为科学行为应作为行动来加以考察,并强调科学发现和发展的默会性和非形式化,这种思路很好地弥补了角色认知存在的不足。然而,在走向“个体知识”的同时,它却不可避免地淡化了科学的规范性、形式化和物质性等特点。
受到认知科学理论不断完善的影响,吉尔的分布式认知更具包容性,它使得物质性和主体性、身体和世界共存于科学之中。这种模式虽然具有解释的有效性,却不具有本体论地位。此外,该模式需要在实践研究中进行不断检验,并通过与认知科学的持续合作来改进其内在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该模式更具现实有效性和理论解释力。
科学主体的认知研究促进了科学哲学与其他众多学科和领域(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合作,把角色、意会认知以及分布式认知等概念引入科学论,大大拓宽了现有科学论的研究范围,解决了困扰“不在场”科学的众多问题。它有效地消解了科学认识的主客二元对立以及科学中存在的人类与非人类二元对立的局面,有效地解决了科学的个体性与公共性、知识和行动之间的内在矛盾,推动了科学实在论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尽管这三种模式从不同方向解决了科学论中的众多难题,但其自身都存在一定问题,需要不断改进。在当前强调行动的实践科学指导下,修正本身不仅需要大量田野研究的支持,更需要加强与行为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合作。
注释:
①在皮克林看来,“实用主义的实在论”是指他提出的“冲撞意义上的实在论”,借此可摆脱传统实在论的表征困境;吉尔也同样认为实在论必须在实用主义意义上提出,其目的是为他提出的透视主义方法找到可靠性基础;索勒等人提出“实用主义的必然性”理论,以避免必然主义和偶然主义都具有的极端倾向,并为迪昂-奎因问题找到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案。(Pickering,p.218;Giere,2006,p.13;Soler,p.228)这三种方案都采用了实用主义的路径,以试图解决科学实在论(又称为绝对实在论、必然主义、反映论)和相对主义(又称为偶然主义)之间存在的对立困境。它们都强调实在论问题必须在实践中谈论,强调科学的过程是一种操作和行动,而且可以在操作和行动中找到可靠性基础。
②波兰尼曾提出“内居”的概念,以说明认知以对象主体化和主体对象化的方式运作。“居间”概念的含义与波兰尼的“内居”概念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分布式认知系统在克服二元论中所起的作用,以此说明科学中的认知主体并非处于极端,而是在两极之间,具有辩证结构。
标签:科学论文; 认知发展理论论文; 角色理论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活动理论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