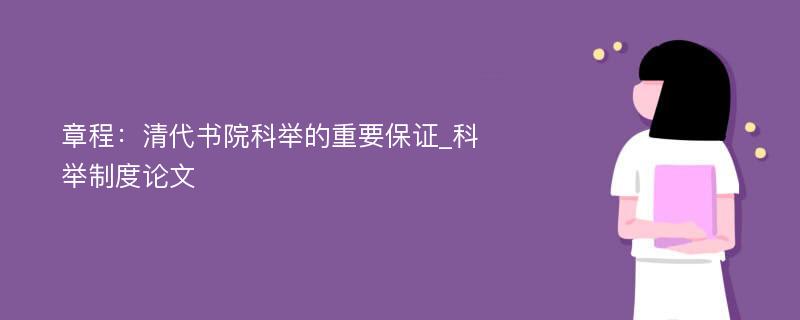
章程:清代书院科举化的重要保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清代论文,章程论文,书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书院章程是指书院为维系书院正常运转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也称规程、学程、条例、馆规、日程、条规等,最早的章程是由南宋状元徐元杰制定的《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清代大多数书院普遍采用章程来实施管理。满族入主中原之后,通过不断调整文教政策,取消书院长期以来盛行的讲会制度,使之成为宣讲程朱理学和培养科举人才的机构,书院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使书院在培养科举人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多数书院都通过制定和完善章程,将书院的各项管理以制度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其成为清代书院为科举服务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书院与科举关系在微观层面的具体体现。本文从书院山长选聘、生徒甄别和经费资助三个方面对清代书院章程如何为培养科举人才服务展开论述,以获教于各位方家。(注:书院教学管理亦是章程的重要内容,但因篇幅限制,在此无法详述,笔者将另外撰文论述。)
一、延聘山长——科甲出身为基本条件
山长是书院的唯一学术带头人、主讲兼行政首脑,是书院实施科举教学的核心人物(注:一般来说,每所书院都有一位山长,只是名称不同而已。但也有极少数的书院没有设山长一职,如《桐乡书院志》云:“书院必有山长,惟桐城各书院俱无,皆因经费不足也。吾乡书院亦费绌,未能专请山长。”)。因而书院的创建者或者修复者都十分重视山长的选聘工作。一般来说省会书院的山长选聘是由督抚决定,而府州县书院山长聘任则因创办或修复主体的不同,而有官府推荐和乡绅公举两种方式。但随着由官府推荐的弊端日渐显露,以公举方式选聘山长成为一种普遍方式,有的书院还明确表示不需要地方官吏推荐。
为使书院山长选聘规范化,大多数书院都制定了相关的章程,从“德”和“学”两个方面对聘任山长的条件进行了严格规定,辽宁的聚星书院规定山长须择“经明行修、素有名望者”,“必品学端优,堪为士林矩矱”。[1] 其中“学”方面的要求一般是以科甲等第为标准的。大多数书院在选聘山长时,明确要求被聘者为科甲出身。甘肃的五泉书院明确规定:“书院掌教宜择品学兼优、专以训课为事之举人、进士,由兰州府以礼聘请。”[2] 广东相江书院也有类似的规定:“书院掌教,递年由绅士公同访定已登科第、品学兼优之先达,禀请本府查实,具关延聘,不由官荐,以致有名无实。”[3] 科甲出身成为书院聘任山长的必备条件,正如程廷祚所言:“山长之选,限于资格,非翰林甲科不能与,而多不得志于仕进之人。”[4] (p1432)书院选聘科甲出身者担任山长是科场激烈竞争在书院教学、管理过程中的重要表现,也是书院为科举服务的重要保障。
在选聘山长时,章程对被聘任者出身的要求是根据书院层次的高低而定的。换言之,书院选聘山长出身的高低与书院层次的高低基本是一致的。层次较低的书院选聘山长时,对其科甲出身的要求相对较低,府州书院一般由进士担任,大多数县级、乡村书院则是由举人、贡生或副榜担任。而在总数达4000余所的清代书院中,数量最多的书院是县级、乡村书院,因此举人和贡生应该在书院山长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这可以从刘伯骥先生对清代广东书院山长出身情况的统计结果中得到应证:“最多为举人(198名),其次为进士(150名),又其次为贡生(76名),翰林(33名),副榜(18名),生员(13名)。”[5] (p261)在其统计的515人中,举人出身的山长占38.4%,贡生占14.8%,副榜为3.5%,进士出身的占29.1%,翰林为6.4%,生员占2.5%。在这一统计中,进士、举人、生员和翰林出身的山长占总数76.4%,表明科甲出身成为书院山长的普遍要求。不仅如此,举人和贡生的比重为56.7%,占书院山长总数的一半以上,明显地反映出层次较低的书院在选聘山长对其科甲等第要求相对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著名书院是以学术造诣为选聘山长的首要条件,而且在其章程中也没有明确规定山长的出身,这是否意味着这些书院对于山长的出身没有要求呢?笔者以清代几所著名书院山长出身的史料来回答这一问题。在清代岳麓书院的37位山长中,有22位进士出身,5位举人出身,1人制科出身,史料不详或者没有出身者10位,其中有进士和举人占总数的7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乾隆十年(1745年)房逢年任山长开始,至岳麓书院1903年改制完成的158年,历任山长都是进士出身。(注:毛德琦编:《白鹿洞书院志》卷5《主洞》,转引自《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页1150。另李才栋的《白鹿洞书院史略》提到了张文瑞、罗启曾任白鹿洞书院山长,但二人均是太学生。)清代岳麓书院“发科者称极盛云”,[6] 应该是与这些科举出身山长言传身教息息相关的。康熙时期白鹿洞书院先后有7人出任山长,其中除邵良杰为解元之外,其余6人均为进士出身。③ 据有学者统计,雍乾嘉三朝白鹿洞书院山长中影响较大的有23位,除1人(吴嵩梁)为举人之外,其余的22为山长全部为进士。[7] (p151-155)江苏《如皋县续志》卷三所载《安定书院院长题名录》共录山长10人,全部为科甲出身,其中进士2人,举人8人。[8] 江苏暨阳书院乾隆三年至道光年间的32位山长中,进士出身的18人,举人出身的10人,制科出身的1人,其余3人为副贡,科举出身者占暨阳书院山长的90%以上。[9] 由此可见,这些著名的书院尽管没有严格规定山长的出身,但山长基本上都有较高的科举功名。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学术大师基本上都是科甲出身,因此对于这些专门选聘学术大师担任山长的书院来说,科甲出身就成为可以忽略的条件了。
章程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山长选聘上,而且为保证山长在科举教学中充分发挥作用,书院章程还对山长的管理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不少书院规定必须选聘科甲出身的本地士人担任山长。江西东湖书院规定“书院必请本邑先生,首科举,次乡举,次明经,择其中年过五旬,文行著望者,廪县具关敦请。同隶本籍可以常住在院与诸生讲贯。”[10] 云南广南士绅在公议《培风书院条规》时提出,由于山长经常不到馆履行职务,导致广南地区“百余年来科目寥寥”。为改变这一局面,除继续实行“非科甲出身者不得延请”的规定外,士绅们决定聘任本地人,“兹数年来,科目遂兴,在籍孝廉不少,嗣后采访公论,即延本地科甲主讲,庶可长年驻馆,不至于半途而废。”[11] 不少章程对山长亲自到书院任教也进行了规定。河北广泽书院不仅要求山长应由科甲出身者出任,而且规定不能聘任因居住在外地而不能经常在书院主持教学的人为山长。[12]
书院还通过加强薪水的管理,促使山长更好地履行教学职责。湖北墨池书院对山长亲自到书院任教有严格的规定,通过提高山长的待遇,“岁致束脩银二百两,薪水银一百二十两”,以解决山长因“因道路僻远、脩脯菲薄,不亲身到馆,致虚考课”的问题。有的书院将山长的薪水与其是否到岗工作联系起来,如果山长一月不到书院任教,就将该月的束脩和薪水支给代课者,以达到“重月课而收实效”[13] (p1571)的目的。
可见,章程不仅对选聘书院山长的科举出身有严格的规定,而且还将山长任职期间的管理作为重要的内容,以保证书院的教学效果,这充分体现出章程在山长选聘、管理这一环节上为科举服务的作用。
二、甄别考试——选拔应举生徒
书院章程不仅重视山长的选聘和管理,而且对生徒选拔也有相当详细的规定。书院生徒入院学习之前要参加甄别考试(即入学考试),主要考察其对科举制艺知识的掌握程度。书院的考试程序基本上和科举考试是一致的。一般是由监院呈请地方官府公布考试日期,然后各地生徒至监院处报名投考。大多数书院规定甄别考试一年进行一次,考试的时间一般为正月、二月或前一年岁末。如河北的龙冈书院规定:“书院每年二月初二日开课。先期由县出示晓谕,生童赴礼房报名备卷。至期齐集书院,听候本县扃试。”[14] 湖南凤凰敬修书院的甄别考试时间为每年的十一月。[15] 而广东相江书院甄别考试的时间为十二月,“生童两日扃门考试,须复试一二次,以拔真才而昭公允。”[16] 有的书院在正式的甄别考试之后,还可以为因有特殊情况而缺考的生徒进行补试。广东粤华书院甄别考试的时间为每年二月进行,称之为“大甄别”。[17] 此后,又允许因路途遥远或特殊情况没有按时参加考试的生童随课补考,考试时间为四月初三日官课之后。这种方式与岁科试的录遗、大收等十分类似。考试前,报考生徒还需要身着标志科举身份的衣服拜见主考官,辽宁聚星书院规定:“甄别场,生顶帽,童缨帽,齐集点名时,行一跪三叩首礼毕,礼房当堂发卷。”[1]
有的书院将甄别考试与科举考试的第一级考试——童试联系起来。如《彝山书院重定章程》规定:甄别考试的关防措施与科举考试基本一致,士人参加书院甄别考试时,不仅必须结保,而且外州县的考生必须携带已经参加过童试的证明材料。试卷的处理程序也与正式的科举考试基本相同,录取的标准与科举考试以“程文为去留”相同。陈寿祺在为鳌峰书院制定的章程中云:“凡书院考课生童,谓之甄别,义在选贤绌恶,异于岁、科小试,弥封校阅,徒凭文字去取也。”[18] (p418)
甄别考试录取与否的决定权一般掌握在主持考试的地方官员手中,如巡抚陈宏谋规定,岳麓书院正课、附课生员是由湖南各地地方官吏选送或学政录取。[19] 湖南的龙潭书院规定:“肄业生由州尊甄别,录取送院。”[20] 即由州长官录取。由于正课生、外课生需要由书院提供一定数量的膏火,(注:有的书院外课生没有定额,亦无膏火。如河北的燕山书院规定:“外课生童无定额。每逢官课,饭食由院中供给。”(见《遵化县志》卷17,缪彝:《燕山书院条规》,清光绪年间刊本。))各书院都对这类生徒的名额有相当严格的限制。如道光年间苏州紫阳、正谊两书院的生徒人数达到了一千三四百人,但正课和外课生徒的数量却相当有限。据陶澍所订《苏州紫阳、正谊两书院条示》根据紫阳、正谊两书院原有生徒数量,将紫阳书院内课生增加至50名,外课生为100名;正谊书院正课生增加至40名,外课生为80名。尽管数量上有所增加,但内、外课生徒数量在生徒总数中还只是占相当小的一部分。
在录取生徒时,不少书院还将生员、监生和童生分别录取,并规定各自的正课、附课生定额。胡林翼在为湖南箴言书院所定的章程中,对甄别考试录取生徒定额中生员和童生的名额都有明确的规定,“取正课生监十五名,正课童生十五名,附课生童十名。”[21] 湖南的狮山书院规定:书院甄别时,“生监正课十名,副课十名,童生正课二十名,副课二十名。”[22] 河北临津书院每年一次招生时,“取定肄业生五十名,童八十名。”[23] 一般而言,书院在招收生徒时,给予生员、监生的名额明显多于童生,这并不是由于参加甄别考试生员和童生人数的多数来决定的,而是由于书院的目标大多在于培养能够在乡会试中脱颖而出的举人、进士。
不少书院为满足更多生徒参加乡试的需要,还在乡试年份增加生监的招生名额。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岳麓书院规定在乡试年份,增正课二十名,附课十名。[19] 粤秀书院于乡试之年也增加招生人数,“增取正课生监二十名,以足一百名之数,外课生监增取十名,以足五十名之数。”[17] 四川莲峰书院不但在乡试之年增加招收20名生员,而且在童试之年也增加20名童生的招生名额。[24] 这些增加招收的生徒在书院学习的时间都相当短,一般为半年左右,主要是进行考前的强化训练。如陕西玉山书院规定增加名额招收的生徒学习时间为“以二月为始,八月停止。”[25]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科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至清代中后期不仅出现了主要招收生员的书院,还有正式招收举人肄业的书院。明清官学体制虽然没有为举人提供学习场所,但大多数举人的学习生涯并未结束,他们还需要通过强化训练参加竞争更为激烈的会试与殿试。为满足举人的这种需要,不少书院招收部分举人入院学习。嘉庆十三年(1808年),阿克当阿在梅花书院招举人入院肄业,开清代书院招收举人的先例,(注:阿克当阿在《文昌楼孝廉会文堂碑记》中云:“校课孝廉实自扬始”。(见《扬州府志》卷19,清嘉庆十五年刊本。))阿克当阿在梅花书院的建筑后面,“广其舍为孝廉会文之所,”每月对举人进行考课。[26] 道光十六年(1836年),管辖浙江杭州、嘉兴和湖州地区的地方官吏有见于浙江地区举人无肄业之所,要求敷文书院增加孝廉月课。于是,敷文书院特别筹集八百四十两银子作为孝廉月课的经费,并根据经费的多少确定招收杭州籍的举人内、外课各18名,附课20名,还专门制定了《敷文书院增设孝廉月课章程》对于举人的招收和考课进行规范,该章程规定:举人参加敷文书院的甄别考试还需要履行类似科举考试“投牒自进”的报考手续,杭州府的所有举人,包括丁忧在籍和已经成为教官但还没有赴任的举人都可以前来参加考试。
随着举人数量的增加,不少地方还出现了专门招收举人的书院。上海龙门书院就主要是招收举人和监生,龙门书院课规规定:“住院肄业诸生额共三十名,每年十一月由道甄别,及三、八月投课,录取各属,挨次补序。”[27] 同治年间,天津新建会文书院亦为“专课举人”的书院。[28] 针对广东各书院只招收生童肄业的现实,广东布政使设立应元书院以专课举人。[29] (p261)此类书院还有福州的正谊书院、江西的孝廉书院、浙江的三台书院等。有的书院则同时招收童生、秀才和举人,并根据生徒层次的实行考课、教学。如《宝晋书院规条》不但规定了生员和童生的数量,而且还于道光七年(1827年)开始设立孝廉课,为举人提供进一步学习科举知识的场所。
书院章程通过对招生进行相当详细的规定,通过对生徒所掌握知识的考察,从生源上保证了书院科举教学的正常开展,这是书院为科举服务的重要条件。
三、经费资助——为生徒应举提供保障
大多数书院还通过给予膏火、奖励和宾兴费等经费资助的方式鼓励生徒读书应举,并以章程的形式对经费资助进行管理。《龙门书院章程碑记》规定:正课生员、童生每名每月可以获得膏火银八钱。附课生员、童生每名每月获得膏火银五钱。与四川龙门书院给予科举身份不同的正、副课生分别相同的待遇不同的是,大多数书院给予生监的膏火要高于童生,如贵州的黎阳书院生员正课领膏火钱320文,副课领膏火240文,童生正课领钱240文,副课领钱160文,[30] (p1828)显然,生员生徒的膏火远远高于童生。广东丰湖书院也是如此,正课生员每名每月给膏火银一两五钱,正课童生同样为四十名,每名每月给一两。
有的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书院提供给生徒的膏火数量还相当可观。广东应元书院《章程》规定举人的膏火为:每年以十个月计算,内课三十名,每名每月给银三两。外课二十名,每人每月给银二两。[31] (p270)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书院发给生徒的膏火银相对就要少,如辽宁聚星书院生徒膏火就相当少,甄别考试取生员超等三名,每名每月给予膏火钱十四吊,取生员特等四名,每名给予膏火钱十吊;取童生上等五名,每名每月给予膏火钱十二吊,取童生中等六名,每名每月给予膏火钱八吊。”[1] 这所书院生徒的膏火就明显少于地处经济相对发达的应元书院。
有的书院膏火的发放是根据生童家庭的经济情况、是否住院学习、学习的态度与成绩等情况区别对待,以使膏火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保证更多的贫寒之士和勤学的生徒读书应考。粤秀书院的规定是:对于住院认真读书的生徒的膏火依据规定全额发放,而对于在居住在院外的生徒的膏火则要扣除一半,将其作为住院学习而无法获得正课资格的生徒的膏火。对于无故不参加考课一次者,扣除当月膏火三分之一;两次不参加考课的,扣除膏火的三分之二;连续三次不参加考课,由监院查明没有特殊原因的,则要被除名。[17] 书院的膏火、奖励不仅能为生徒安心读书应举提供经济保障,而且也是促使生徒努力学习的动力。
在膏火之外,书院还对参加乡会试的生徒予以资助——宾兴之费,以解决他们因经费短缺而不能顺利赴考的问题。这不但从实际上解决经济窘迫生徒的困难,也是对生徒学习科举之学的鼓励。刘伯骥先生对广东书院宾兴费的分配有过详细统计。[5] (p295-296)笔者根据方志对浙江书院宾兴之费进行了统计:
院名 年代 总额归各人分派
资料来源
金华丽正书院 光绪十三年
陈文 捐廉1000贯存典以息崇肄业生宾兴费
(光绪)《金华县志》
永康培文书院 光绪十二年
应寿椿捐田二百亩零七厘八毫,出租收入,每年 (民国)《永康县志》卷2
200石
永康崇功书院 道光三十年
侯饶谕捐资四百千文生息以作宾兴之费 (民国)《永康县志》卷2
嵊县辅仁书院 乾隆五十三年 拨田八十亩分给阖邑乡会试路费 (同治)《嵊县志》卷6
石门崇文书院 道光六年
县令捐廉洋银2000元生息资助参加正科乡试诸
(光绪)《石门县志》卷4
生。道光十四年李永廉捐银500两,作为恩科及
会试生徒提供费用
上虞经正书院 道光十二年
徐迪惠捐田100亩作为公车路费 (光绪)《上虞县志校续》
卷37
太平鹤鸣书院 乾隆二十四
徐任培增拨学田为诸生膏火岁修及宾兴之用
(嘉庆)《嘉庆太平县志》
年 卷5
新昌南明书院 嘉庆十年
陈 捐田10亩为文武科举乡试路费
(民国)《新昌县志》卷5
江山文溪书院 同治十年
何锡霖捐田作为文武乡会试经费 (同治)《江山县志》卷4
杭州敷文书院 道光十六年
共计400两均分给在书院肄业一年以上的参加
《敷文书院志略》碑文
文会试者,作为路费 《敷文书院增设孝廉月
课章程》
除广东和浙江书院之外,其他省份的书院亦为生徒提供宾兴费,并且还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发放办法。如山东《营陵书院章程》规定:以两千串为生徒赴考旅费的基金,每逢大比之年,由监院提取利息以后,将八成半作为乡试旅费,一成半作为会试旅费。为保证经费发放的到位,乡试旅费要求参加乡试的生员凭入场卷票领取,会试旅费则由举人本人到书院当面领,如果领取旅费而没有参加考试的,需要将钱交还书院。有的书院则是将科考前几个月的膏火累积以后,再发放给赴考生徒。杭州敷文书院是将考课的五个月经费总额平均发放给参加会试的举人:在会试之年,将二、三、四、五、六五个月的考课经费共计银四百两作为宾兴费,根据书院肄业举人的数量平均分配,按照敷文书院的招生人数为56人,平均每人可以得到盘费7两多。有的书院则允许生徒预支膏火,湖南敬修书院规定乡试之年,生员可以预支5个月膏火。[15]
不少书院提供的宾兴费还有固定的来源,并通过章程将其管理制度化。如上表所列浙江书院宾兴费多是以宾兴田生息作为来源。而云南的碧晓书院乡、会试资助经费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嘉庆庚午、癸酉岁科两试,廪生等议将认保童生画押钱捐集,以作会试等卷金、程仪之费”;一是道光四年(1824年),贡生严诚捐银100两。书院将这两项经费购置房产并生息得银787两,以资助参加乡会试考试的书院生徒,并制定了详细的管理条规:每年乡试卷金每名送银二两(以后随着候积蓄增加而增加);新中式举人参加会试的宾兴费为每名送银五十两(其有本科不能参加会试的,下科照例送五十两)。陈科会试举人的宾兴费为每名送银十两;新科进士每名送银二十两。对于参加武举的生员也发放宾兴费,武举乡试卷金每名送银一两。[11]
有的书院还将平时由于生徒不到课而扣除的膏火作为参加乡、会试考生的盘缠,墨池书院规定:考课不到生童,根据缺考课的次数扣其膏火,并在每月的支放簿内登记扣出膏火的数量,另行存放。累积到乡试之年的六月,从其中提出100贯作为初次参加会试的举人的盘费,根据人数平均分配之外,其余的经费全部用于本年度乡试的盘费。
有的书院不仅资助生徒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而且还为贫寒的生徒参加童试提供经费。嘉庆十七年(1812年),粤秀书院续增条规中对此有明确规定:在书院生徒回乡参加县试、府州试、院试时,生徒可以根据回家的路程分别预支1-3个月的膏火。如果在考试的年份无膏火可以预支,便可以在从书院扣除的缺考课生徒的膏火中支取,而不住院的生徒是不能享受这一待遇的。为防止考生预支膏火之后,生徒不参加考试而挪作他用,粤秀书院要求预支膏火时,生徒必须由监院出具证明文书,然后由生徒参加县试时上交给官学的教官,待该生考完之后可以从教官那里领回文书,以作为书院请假和领取膏火销账的证明。[17] 粤秀书院照顾贫寒考生的制度不但详细,而且还体现出书院充分利用经费来激励生徒读书应举的作用。
清代书院十分重视章程在书院管理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其来规范书院的山长聘任、生徒甄别、经费资助等,使书院为科举服务的功能得到充分显现,这是清代书院科举化的重要表现。然而,章程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围绕书院为培养科举人才服务这一目标,失去了书院自身本来应该具备的特点,这也预示着书院这种独立于官学、私学之外的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在逐渐消失,必将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停废而从制度层面消失。
标签:科举制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