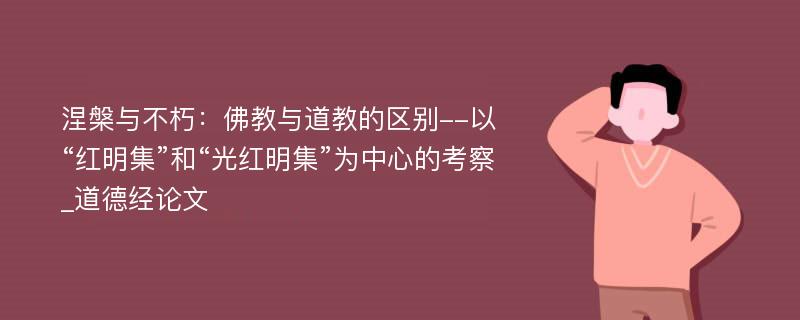
涅槃与仙化:佛、道终极解脱思想的差异——以《弘明集》、《广弘明集》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异论文,思想论文,中心论文,弘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思想史发展过程中,东汉时期佛教的传入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而由此引发的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释、道三教论争更是直接影响到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及整体格局。中国传统思想中儒、释、道三元互补结构的形成就是这一论争的结果。日本著名印度学家、佛教专家中村元曾说:“从后汉至唐宋,儒教、佛教、道教这三教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在文明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①从中国文化整体发展的历史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论争乃是中华文明首次遭遇印度文明这一异质的、高度成熟文明体系的挑战。对此,我们不能仅把佛教传入中土看成是一种宗教的植入,而且还应注意佛教所承载的印度文明之核心价值观念,其基本概念、核心命题,诸如因果报应、三世轮回以及以出世主义为导向的终极解脱境界等等,都是印度各大宗教诸如婆罗门教、印度教、耆那教等共同信奉的。因此从文明传播的角度看,佛教传入中土及其由之引发的绵延八百年以上的与中国传统思想儒、道之间的争辩,乃是当时世界上两大主要文明体系首次大规模交锋。
就思想层面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论争主要表现为佛教与道家、道教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争论。其中在生命哲学方面,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辩。佛教与道教虽然都是以出世主义为导向的宗教信仰体系,然而由于双方在了证的终极境界、对生命价值的看法以及思维方式等诸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二者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论争中,思想之间的交锋极为激烈。在论争过程中,通过对双方立教宗旨、教义教理的比较,我们可以窥见中、印两大古老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
一、无生与无死——佛、道终极了证境界的差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论争就思想层面看,主要表现为佛教与道家、道教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争论。佛教最初是通过与中国本土的道教相比附传入中土的,后汉至东晋之前,中国人接受佛教都是把它看成神仙方术的一种。对此,佛教方面也不忌讳,当时佛教徒都积极攀附道教。不少论者都注意到早期佛教采用道家、道教的概念、范畴以传译经典。例如早期佛经翻译家安世高、支谶、支谦都采用道家的无为、气、本无、自然等概念来翻译佛典。后汉安世高在翻译《安般守意经》时就使用气概念:“身但气所作,气灭为空。”又云:“安谓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支谶译《道行般若经》时,也将诸法性空译为诸法本无,用色之自然来表达色即是空。然而,随着佛教传入的深入,中土人士对佛教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于是佛教与道教的诸多义理差异自然也显现出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道之争,并非仅仅是争夺社会地位,而是通过论辩来把握各自思想的特色。
较早对佛、道两教根本宗旨进行分辨的是活跃于东晋、刘宋时的道士顾欢,他在《夷夏论》中分别用正真之道、正一之道综括佛、道二教:
寻圣道虽同,而法有左右。始乎无端,终乎无末。泥洹仙化,各是一术。佛号正真,道称正一。一归无死,真会无生。在名则反,在实则合。但无生之教赊,无死之教切。切法可以进谦弱,赊法可以退夸强。(《南史》卷75《顾欢传》)
顾欢在此用无生、无死来分判佛教与道教,称佛教为无生之教,道教为无死之教。并据此扬道抑佛,区分二教的优劣。他的这一观点对佛、道二教特点的把握很贴切,对后世影响也很大。唐代不少道士都是沿袭并发挥这一观点来批评佛教。释法琳《辨正论》引道士李仲卿《十异九迷论》说:
夫等无生灭,其理则均,导世引凡,不无差异。但生者物之所以欣,灭者物之所以恶。然则生道难得,必俟修功,灭法易求,讵劳禀学?是知腾神驾景,自可积劫身存;气尽形殂,固当一时神逝。此教门之殊二也。(《广弘明集》卷十三)
这是用道家的重生思想来批评佛教以涅槃寂灭为终极归依的立教宗旨。对于道教追求无死、佛教追求无生这一立教宗旨的差异,东晋南北朝时不少崇佛者也都注意到。然而他们并不据此以为这是佛教的弱点。像僧愍、谢镇之、袁粲、刘勰等崇佛者在比较佛、道两教立教的根本宗旨之后,反而依据佛教涅槃解脱论对道教以长生为依归的重生哲学予以批评。僧愍《戎华论折顾道士夷夏论》在回应顾欢《夷夏论》时就说:“道则以仙为贵,佛用漏尽为研。仙道有千岁之寿,漏尽有无穷之灵。”(《弘明集》卷七)他认为佛教以漏尽为终极了证境界高于道教的长生。而谢镇之在《与顾道士书》中,更进一步分辨佛法与道法的根本差异,对中土道教的长生之道进行批评:
佛法以有形为空幻,故忘身以济众;道法以吾我为真实,故服食以长生。且生也可养,则及日可与千松比霜,朝菌可与万椿齐雪耶?必不可也。若深体三界为长夜之宅,有生为大梦之主,则思觉悟之道,何贵于形骸?假使有形之可练,长生不死,此则老宗本异,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犹于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恋恋于檐宇哉!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圣之体。虽复尧、孔之生,寿不盈百,大圣泥洹,同于知命。是以永劫以来,澄练神明。神明既澄,照绝有无,名绝四句。此则正真终始之道。(《弘明集》卷六)
这是依据佛教的生命观来说明肉体生命存在的虚幻不实,只有以精神觉悟为归依的了证之途才是真正超越之道。而针对前述顾欢主张佛、道两教所达至之解脱之境,“在名则反,在实则合”的看法,袁粲、刘勰均认为两教终极了证境界有着根本差异。袁粲说:
仙化以变形为上,泥洹以陶神为先。变形者白首还偕,而未能无死;陶神者使尘惑日损,湛然常存。泥洹之道,无死之地,乖诡若此,何谓其同?(《南齐书》卷54《顾欢传》)
刘勰在《灭惑论》也说:
夫佛法练神,道教练形。形器必终,碍于一垣之里;神识无穷,再抚六合之外。明者资于无穷,教以胜慧;暗者恋其必终,诳以仙术,极于饵药。慧业始于观禅,禅练真识,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药驻伪器,故精思而翻腾无期。(《弘明集》卷八)
袁粲、刘勰两人用练神与练形来分判佛、道两家的超越论,尽管并不完全准确,但却无疑触及到佛、道两家生命哲学的根本差异。这其实也是中国现世主义文化与印度出世主义文化的一个根本分歧所在。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具有重生的特点,这在道家、道教中表现尤为突出。道家、道教的核心概念是道,证道、修道是其思想的主轴线。我们综合道家诸种文献之论道文字,可以看出两种较普遍的述说倾向。其一是从宇宙论的角度来展开其道论,以为道与天地万物的创生有直接统源。其二则论道时每每牵联人的生存,认为在终极的、玄冥的道与人的生命之间存在着贯通的、难以分割的牵缠。对此,依据道家的各种文献的载述,或许可以概之以“生道合一”。生道合一是道家在展开其道论时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在道家看来,作为超越性的终极实体,道乃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内在于万事万物之中,而在我们生存的世界中唯有人才会自觉地在我们的现实生存中对道的存在发出追询。因此,从终极的道体的角度来看,人之生命的意义并不单纯局限于其类的范围之内,亦即只对人自身呈现意义,同时也是道体显现其自身,实现自我觉醒的一个媒介,因而具有整全的终极意义。道通过人的生存而达到自我醒悟,其外在表现形式便是人的证道、体道行为。对此,道家的生道合一思想就是这样一种有助于人类摆脱其自我中心的拘限,以体证大道为中心以规范现实生命意义的核心观念。因而,任何一种现实的生命都是精神与肉体的统一体。人的肉体不仅像印度宗教与哲学认为的那样是其精神的载体,而且更重要的是人据以生成、发展其精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人还以肉身为根基切入其周围的生活世界,以达致对世界的领悟与认知,从而最终实现其主体间性。由此可见,脱离肉身而单提神光的生命,只能是一种抽象的生命。道家的生道合一思想扣紧肉体与精神统一的主题,其论现实的生命不仅重视其精神层面,而且也贯穿于作为生命的晕圈及视域场景的肉体层次。这实在是一种整全的生命观。正是在这一方面,道教继承、发扬道家的基本精神,将关注的焦点聚集于肉身,希图通过对构成肉身生命因素的精、气之修炼来契证道体。内丹术就是道教企图以肉身为基础以实现生道合一的具体表现。考虑到法国著名现象学家梅劳·庞蒂对躯体的非凡哲学思考,道教以躯体及其组成因素精气神为下手进路以逼近道的方式,并非失之于粗俗,相反倒是中国古代重视整全性思维的难得典范。道理其实很简单,无论道体如何精妙,而体道者都是拖着肉身在悟道、论道。像笛卡尔、黑格尔那种飘荡于肉体之外的“我思”、“绝对精神”只能是一种源自有血有肉之人脑的观念构设。而在西方哲学中这一原则直到胡塞尔现象学独特的观物视角出现以前,尚未有学者对躯体的哲学意义进行严肃的思考。而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对身体的否定式态度同样也没有看到形、神之间的贯通性与统一性。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学术界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以为在道家、道教之间,其基本精神存在着断裂。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道教关注肉体生命、重视斋醮科仪甚至热衷于神灵崇拜等行为乃是一种悖道的举措,是与道家尤其是庄子主张通过精神修炼以契证道体,获得精神解脱的飘逸思想背道而驰。有人甚至将道教对道家精神的推阐称之为精神堕落,认为从道家到道教的演变,并不是道体不断彰显自身的递进过程,相反,道教对肉体生命的过分执着遮蔽了永恒的道之光辉,因而乃是道的一种粗劣的蜕变。这一主张看似很有道理,其实没有看到生道合一是全部道家、道教赖以成立的基础性思想。生道合一不仅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次,而且也体现在生命的肉体层次。对于这两个不同的层次,道家并不像今人所设想的那样壁垒森严,不可逾越,而认为两者可以互相贯通。道家之提出精、气、神概念,并重点强调精气神三者的联系与转化就是这一贯通的具体表现。另外,庄子虽然重视以梦论、生死论来展开其道论,以生命之梦的觉醒来诠释体道的真正意义,这些思想固然是纯粹从精神层次来论述生道合一,然而庄子也并非完全放弃对肉身的关注,其《大宗师》所论之道便涵盖着肉体生命的层次。因此,从道家到道教的演变并非道家精神的堕落,而是道之体相更为全面的显现。将体道与肉体长生不死联系起来,这是道家在演述其道论时所执守的一个基本信念。这一信念乃是奠基于生命与道之内在契合性的思想基础之上。对此,先秦道家重要思想家之一的文子作了经典的表述,其言:“生者,道也。”文子以生字表征道,充分体现了道家对道之生成特性的强调。文子的这种思想乃系道家思想家的共同主张,所不同的是他对生道合一原则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
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最高实体,以超验的形式存在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道家确立了道的遍在性与超越性。然而尽管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分有道,但却只有以人的行为为中介,道体才能实现自我醒悟。这样实际上意味着人的生命过程对于道显现自身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此人的生命本身就具有超越自身有限存在的形而上的意义。人的现实生命存在包括肉体与精神两大层次。对于肉体生命与道的贯通,自始至终便是道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重生传统及思维的整全性。
道家自创始人老子开始,就对道体的生成性格,尤其是道与肉身生命的贯通表示出关注。这从老子演述其形上道论的方式中可以看出。老子展开他的道论主要从两方面着手:其一是通过对天地万物起源的追询来展现道体的生成性格,在此基础上老子确立其宇宙论。按照老子的理解,宇宙万物与道存在两种层次的关系:首先宇宙万事万物都体现道。正是道的遍在性、超验性决定它对宇宙万事万物具有贯通性。其次从存在时间的先后来看,道存在于宇宙万物之先,是万物之母。在宇宙论意义上确立的道是道家生道合一思想的重要根基。因此我们可以说,道之创生天地万物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举动,而是由其内在的生成本性决定的,一句话,道不得不生,天地也不得不成。宇宙的生成是道实现其自身的必然过程。其二老子在展开其道论时还对人的生命尤其是肉身生命表示关注。这种考虑主要在于道论下半截,即道通过人的生命意识而实现自身醒悟。在老子看来,人的现实生命尤其是肉体生命乃是人们体道的基点。套用一个禅宗术语来表述,即人们的体道行为要有一个入处。而人的现实生命正是这一入处。正是居于这一思路,老子在书中反复申述了肉体长生的问题。例如五十九章提到长生久视之道,三十三章论及“死而不亡者寿”,而六章、十章更论述了各种具体的养生之术。其典型的句子如:“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后世道教内丹学派正是通过对老子创立的道论及养生术作创造性的诠释来奠定内丹道的学与术双重根基。
老子之后的道家在演述其道论时,大体继承了老子的这一思路,对道之基本生成特性作了更为具体的论述。庄子对生、道的贯通虽然主要从生命的精神层面来理解,但他也不绝对排斥道与肉体生命的关联。例如《庄子·大宗师》在论述道之及物作用时,就指出此道“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项得之,以处玄宫。……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可见,在庄子看来,得道与长生(彭祖)或仙(黄帝)有着必然联系。庄子这一思想在《外篇》中亦有体现,《在宥》借广成子之口对体道与长生的联系作了论述。其言: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无思虑营营,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汝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我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汝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汝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身可以不老也。
此显系将修道与修身等而观之,以为至道之精泽及人身,必有长生之效。庄子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从肉身生命的层次肯定了生道合一的原则。此外道家、道教的重生传统在《易传》中也有呼应,《易传》提出“天之大德曰生”这一思想命题,并将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冲动提升为一种抽象的精神品性。中华民族正是在这种重生的内在精神的驱动下,数千年来顽强地展开着与自然的抗争,终于孳孳不息,繁衍壮大。
相比之下,佛教对生命的看法就颇为消极,其苦、集、灭、道四谛说首先对人生下一苦的价值判断。而其达至的终极了证境界涅槃,更是要彻底止息生死轮回,从一切烦恼系缚中解脱出来。《大乘义章》卷十八就说:“灭诸烦恼故,灭生死故,名之为灭。离众相故,大寂静故,名之为灭。”与此相关,对于身体的看法,佛教也是持否定态度。鸠摩罗什所译《禅法要解》述修持之禅法,有一种对身体做“不净”之观想:
自观身中三十六物,不净充满。发、毛、爪、齿、涕、泪、涎、唾、汗、垢、肪朑、皮、膜、肌、肉、筋、脉、髓、脑、心、肝、脾、肾、肺、胃、肠、肚、胞、胆、痰瘤、生藏、脓、血、屎、尿、诸虫。如是将种种不净聚,假名为身。(《大正藏》15册286下)
这是认为人的身体乃是由上述三十六种不干净之部件合聚而成,禅观就是通过这种不净之观想以使修习者对身体产生厌恶的心理,以最终放弃对身体的执着。不少佛经还宣扬通过摧残身体来修炼,例如东晋所出《佛说菩萨本行经》就说:“今为法故,以身作灯;持是功德,用求佛道,普为十方无量众生作大光明,除去众生三毒痴冥。……时诸会中,皆悉默然,于是大王即便持刀授与左右,敕令剜身作千灯处。出其身肉,深如大钱,以酥油灌中作千灯。”(《大正藏》3册113)受此种思想的影响,我们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有不少佛教徒仿效佛经中记载的药王菩萨,施行烧身修炼。例如梁慧皎《高僧传》在“亡身”中,就记载姚秦时释法羽践行烧身修炼:
释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为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头陀之业。羽操心勇猛,深达其道。常欲仰轨药王,烧身供养。时伪晋王姚绪镇蒲坂,羽以事白绪,绪曰:“入道多方,何必烧身,不敢固违,幸愿三思。”羽誓志既重,即服香屑,以布缠体,诵《舍身品》竟,以火自燎。道俗观视,莫不悲慕焉。(《高僧传》卷十二)
这种烧身修炼行为的背后是与佛教对身体的负面看法密切相关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道教执持的以身心统一为特征的生命观不同,以佛教为代表的古代印度文化信奉身心分离主义,认为人的真实生命体现于精神的“自我”中。对此,婆罗门教圣典《奥义书》提出“阿特曼”即神我实体概念来表征。不过与西方身心分离思想不同,婆罗门教认为神我是有超越意义的,《奥义书》就提出“梵我一如”的思想命题,以搭设自我与终极超越实体大梵之间过渡的桥梁。相比之下,佛教更提出无我、非我的概念,对灵魂实体也进行否定。不过无论是婆罗门教还是佛教,一无例外都信奉生命轮回的学说,把人的再生视为个体追求解脱的必由之路。对此中村元评论说:“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都详细讨论有关人再生的问题,把轮回的过程看作是追求解脱、追求正果的必由之路。”②佛教的六道轮回思想(佛教这一思想是印度传统思想的一般主张,婆罗门教也信奉轮回),就是认为个体生命是在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等六种生命形式轮转的。而佛教的终极了证境界涅槃则是摆脱轮回之后,达至的一种精神绝对寂静之状态。这种思想的高明之处是看到不同生命形式的关联性、延续性,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统一主义。这种再生思想所显示的生命视域较中国传统生命观相比无疑很独特。由于在生命轮回之旅中,身体不过是灵魂之寓邸,在轮回过程中其实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其轮回的真实主人是自我、灵魂。因此印度各种宗教都对身体采取一种否定态度。而在魏晋南北朝三教论争中,崇释者对道教成仙证道说的批评,也是将其修炼之果位定为未脱轮回的诸天以达至的。按此逻辑,道家、道教成仙证道显然就不是终极的解脱之境。
二、因缘与自然:佛、道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村元在比较古代印度与中国两大古老民族思维方式之后,认为双方存在重大差异。印度民族重视对普遍性、抽象性之真实存在的追求,而中国则偏爱个别性、特殊性的个体存在。③这一概括诚然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然而我们同时也应看到中、印民族的思维方式也有不少相同之处,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双方都在人的自身寻找生命超越的根据,因而有着很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这与西方天启宗教例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很不相同。德国哲学家凯瑟琳(1880-1946)评论以中、印为代表的东方思想时曾说:“当我们去寻找道德和宗教的真实基础的时候,当我们发现了‘实在’就存在于我们自身的时候,古代东方的智慧就像黎明时分冉冉升起的太阳,向我们放射着光芒。”④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虽然中、印都共同遵循内在超越的思路,但与印度人重个体精神现象分析不同,中国人尤为重视现实生活。这在道家表现为关注对道与世关系的讨论。这可谓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路。
在魏晋南北朝佛道论争中,佛、道双方都通过有意识地比较佛、道二教来把握两教的特点。因此,这种义理论争对于加深了解两教的根本宗旨无疑是有益处的。北周的甄鸾在《笑道论》中就分别以“因缘”、“自然”两概念来综括佛教、道教教义教理的特色,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其云:
佛者以因缘为宗,道者以自然为义;自然者无为而成,因缘者积成乃证。(《广弘明集》卷九)
与道家、道教重视自然原则不同,早期佛教认为世界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均无其独立自性,因而是不真实的。这种通过分析主义的思维途径来论证事物虚幻不实的作法为其后大乘佛教所继承。大乘佛教进一步提出缘起论以对世界做性空的价值判断。这种通过层层分析达至的空相对中国传统重视和合的思想传统,实在缺乏强制性。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人根本就不认为和合的事物不真实,反而认为事物只有通过和合才能达至更高的善与美。这应当与中国古代重视综合性、整体性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像刘宋高僧慧琳在《白黑论》中就对佛教的缘起性空理论予以驳斥:
今析毫空树,无伤垂荫之茂;离材虚空,不损轮奂之美。明无常增其渴荫之情,陈苦伪笃其竞辰之虑。(《宋书》卷九七《天竺迦毗黎传》)
贝锦以繁采发挥,和羹以盐梅致旨,齐侯追爽鸠之乐,燕王无延年之术。恐和合之辨,危脆之教,正足恋其嗜欲之私,无以倾其爱竞之惑也。(《宋书》卷九七《天竺迦毗黎传》)
这显然是用中土的和合论来对抗佛教的缘起论。魏晋南北朝时,崇释者在比较佛、道二教宗旨后,还对道家、道教的道论进行批评。南齐萧子显认为道家之道存在本末分隔,缺乏一体贯通性:
道本虚无,非由学至;绝圣弃智,已成有为。有为之无,终非道本。若使本末同无,曾何等级?佛则不然,具缚为种,转暗成明,梯愚入圣。途虽远而可践,业虽旷而有期。(《南齐书》卷五四《高逸传后论》)
这是认为道以虚无为体,难以修习。与此不同,唐初高僧慧琳则从道与自然的关系着手,直接批评道缺乏恒常性,因而难以充任终极实体:
通人曰:纵使有道,不能自生,从自然出。道本自然,则道有所待。既因他有,即是无常。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王弼之言,天、地、王、道,并不相违,故称法也。自然无称,穷极之辞,道是智慧灵知之号。用智不及无智,有形不及无形。道是有义,不及自然之无义也。(《广弘明集》卷十三)
这是通过对《道德经》“道法自然”的解读,以为道源于自然,乃是有待之体,因而无法与自然比肩充当最高实体。这一批评其实是对《道德经》自然概念的误解,因为在《道德经》中自然并非实体概念,而是用以描摹道之运行特性之摹状概念。不过崇释者对道家道论的这种批评,也有助于道家厘清对道的界定。客观地说,先秦道家在推演其根本道论时,以发生论为归依的道生论与通向本体论的道本论交缠一处,这就使得道的含义缺乏清晰性和明确性,这无疑不利于彰显道的超验性、空灵性。其后道教重玄派学者吸收佛教般若空宗的非有非无概念来规定道,就显然是吸收了来自佛教的批评。⑤
三、菩提与道:《老子》梵译的争议
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曾诏令学贯中、印的一代高僧玄奘将《道德经》译为梵文。此事在中、印文化思想交流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道德经》的梵译乃是中国传统思想首次正式输出,这就一定程度上打破前此在中、印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只是单纯扮演输入国的形象。可惜的是当时印度文化并未认真考量《道德经》所蕴含的深刻思想意义,致使梵语本《道德经》在印度长期寂没无闻,对印度思想未能产生应有的影响。考虑到当今《道德经》在全球译本种类之多,仅次于基督教的《圣经》,印度人长期冷淡《道德经》,实在是一种遗憾。
考佛教文献,这次《道德经》梵译之举是依东天竺国王之请而发起的。对此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记载:
贞观二十一年,使臣李义表自西域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义表告以中国未有佛法之前,已有圣人说道传经,在俗流布。彼王曰:“卿还本国,译为梵言,我欲见之。”太宗即下敕,令玄奘法师与诸道士对共译出。
关于此事,道宣《续高僧传》卷四、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四也有记载。唐太宗对此事很重视,专门在五通观组建翻译班子,参与者除佛教方面的玄奘之外,还有当时高道蔡晃、成玄英等。然而在翻译过程中佛、道两家产生的争端,在思想史上却颇具意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道这一核心概念的翻译,到底是译为“菩提”(bodhi),还是译为“末迦”(marga)。对此,玄奘认为译为“末迦”更合适,但道士们都表示反对:
诸道士等一时举袂曰:“道翻末迦,失于古译。昔称菩提,此谓之道,未闻末迦以为道也。”奘曰:“今翻《道德》,奉敕不轻,须核方言,乃名传旨。菩提言觉,末迦言道,唐梵音义,确尔难乖,岂得浪翻,冒罔天听。”道士成英曰:“佛陀言觉,菩提言道。由来盛谈,道俗同委。今翻末迦,何得非妄?”奘曰:“传闻滥真,良谈匪惑,未达梵言,故存恒习。佛陀天音,唐言觉者,菩提天语,人言为觉。此则人法两异,声采全乖。末迦为道,通国齐解,如不见信,谓是妄谈,请以此语问彼西人:足所行道,彼名何物,非末迦者,余是罪人。非惟罔人,当时亦乃取笑天下。”(《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这里争论的焦点是将道译为梵文的菩提,还是末迦。玄奘主张译为末迦更合适,因为梵文末迦有道路之意。这显然是单纯从道路之意理解道概念,没有顾及道在《道德经》中还兼有最高实体、终极了证境界、方法等更重要的意义。而成玄英等高道则认为更应注重道概念的超越意义。其实玄奘法师之所以不肯用菩提译道实在是潜藏着对道教思想的轻视,认为老子之道无法凑泊于佛教菩提之境,这实在是由于他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抱有偏见所致。例如他认为河上公所撰《道德经》序文:“同巫觋之淫哇,等禽兽之浅术。将恐西关异国,有愧卿邦。”(《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考在玄奘之前,同为佛经四大译家的鸠摩罗什就将菩提译为道。《大智度论》卷四称:“菩提,名诸佛道。”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在注《维摩经》时也说:“道之极者,称曰菩提。”这说明如果从超越层面来理解道,那么将其译为菩提是合适的。其实道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极为奇特的概念,它体现中国哲学的独创性。从我国现存文献来看,先于《老子》而出现的《尚书》、《诗经》都出现了道字,如《尚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诗经·邶风》的“道之云远,曷云能来”。从这些语句来看,它们中有些已对道作了一定程度的抽象,道已具有某种抽象的含义,如《尚书·说命下》的“道积于厥躬”即是。然而,在《尚书》、《诗经》中,道尚未达到最高的抽象,它尚未成为最高的、具有终极实体特性的概念,充当这一角色的是带有浓厚人格意志色彩的天。
正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第一次对道作了最彻底的抽象,从而为中国哲学创立了一个最高的终极实体概念。从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角度看,这是思维的一次突破,它为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然而,老子的道并不像古希腊哲学中作为始基概念的水(泰勒斯)、气(阿那克西曼德)、不定者(阿那克西美尼)甚至德谟克利特的原子。道既具有创生天地万物的特性,因此无疑它是宇宙万物赖以创生的终极实体;同时道又超越有形物质世界之上,它是永恒者,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最终栖宿、归依之处所。同时道又与宇宙万物并非绝然隔离,道遍在于宇宙万物之中,其存在与宇宙万物具有贯通性。此外,道还有方法、规律等含义。总之,道作为一种最高实体既是超越的,同时又是内在的。从这个角度看,道虽然与菩提的含义并不完全切合,因为菩提并无最高实体之意。然而从道同时又具有方法、规律方面看,将道与佛教表征最高智慧的菩提相互格义也不见得太出格。退一步说考虑到佛教的终极了证之境与道家相较有所不同,那么音译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教争论的历史看,关于佛、道名相之间意义差异的分辨一直为佛教徒所关注。玄奘之前北周高僧道安在《二教论》中就着力分疏诸如佛与觉、菩提与道、泥洹与无为、般若与智慧等意义差异:
问:西域名佛,此方云觉;西言菩提,此方为道;西云泥洹,此言无为;西称般若,此翻智慧。准此斯义,则孔、老是佛,无为大道,先已有之?答曰:鄙俗不可以语大道者,滞于形也;曲士不可以辨宗极者,拘于名也。案孟子以圣人为先觉,圣王之极,宁过佛哉!故译经者,以觉翻佛。觉有三种,自觉、觉他、及以满觉。孟轲一辨,岂具此三菩提者?按大智度,译云无上慧。然慧照灵通,义翻为道,道名虽同,道义尤异。何者?若论儒宗,道名通于大小。《论语》曰:“小道必有可观,致远恐泥。”若谈释典,道名通于邪正。《经》曰:“九十有六,皆名道也。”听其名则真伪莫分,验其法则邪正自辨。菩提大道,以智度为体;老氏之道,以虚空为状。体用既悬,固难影响。外典无为,以息事为义;内经无为,无三相之为。名同实异,本不相似。故知借此方之称,翻彼域之宗,寄名谈实,何疑之有?(《广弘明集》卷八)
道安在此对佛、道两家基本概念的分疏是很精准的,这说明此时佛教徒对佛教思想的了解已越过初期的格义阶段,转而追求佛典之本意。然而,从诠释学角度看,佛经翻译本身就是两种文化、思想的对话、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实并不存在什么经典本意的问题,因为思想的生命就在于创造。反倒是一些创造性的误读、误译,对于思想创造更具意义。从佛教发展历史看,中国佛教慧命的确立并不在于单纯传袭印度佛教,而在于依据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印度佛教予以创造性的诠释,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宗派。
以上我们依据《弘明集》、《广弘明集》等原始文献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论争几大主题进行逐一梳理。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以佛教东传为契机,中、印两大古老文明第一次在文化思想层面上相遇并展开激烈的交锋。由于印度文明以宗教出世主义为导向的文化对中国以现世主义为中心的伦理本位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互补性,因此中国人在初次遭遇这种异质文化冲击时的确感到心灵的巨大震撼,以至在一定范围内出现对本土文化全盘矮化的声音。这无疑是中国文化遭遇的首次挑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文明在应对印度文明主动挑战的过程中,对佛教采取的开放、接纳、改造的系列姿态,使得印度佛教为适应中国社会的特殊土壤而做出适度的修改,从而最终造就了极富思想创造性的中国佛教。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此后佛教以中国为基地对东亚各国进行全面辐射,最终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公元十二世纪之后,佛教在印度由于种种原因而绝迹,中国反而代之而起成为宣播佛教的主要中心之一。就中国文化来看,佛教及其所承载的印度思想的传入,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视域,提高了中国思想的思维抽象能力,弥补了中国文化现世主义导向过于强烈的俗世主义弊端。
从世界文明的大视野看,作为世界两大古老文明的中、印文明在历史上的冲突、交锋及其所采取的解决途径,为当今全球化时代解决各文明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借鉴意义。当前我们正处于多元文明并存、竞争的全球化时代,以科技文明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文明正全方位影响、冲击中华古老文明,这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华文明第二次遭遇另一异质的、高度发展文明的挑战。我们注意到中、西文明的正式交锋,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的话,迄今已持续一百七十多年,而且这一过程仍未终止。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佛教传入为契机引发的长达八百年以上的中、印文明交锋相比,其规模、影响度以及时间跨度都差可比肩。因此,今天我们通过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印文明交锋的历史,无疑有助于我们应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从而为中华文明进一步完善指明方向。
①中村元:《比较思想史论》,吴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3页。
②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林太、马小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5页。
③中村元说:“(印度思想)无视个别和特殊的东西,而关注于普遍的东西,对于普遍的重视表现为偏重于抽象概念,而抽象概念又被赋予了实体性。”“中国人的思想倾向同印度人正相反,他们无视普遍的东西,而关注个别的或特殊的东西,特别是依赖于感觉,重视具象的知觉。”中村元:《比较思想史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7、169页。
④转引自中村元:《比较思想史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页。
⑤像南齐的周颙就认为道家的义理只达至有无之境,与佛家的非有非无相比,尚欠一途。其《重答张长史书》说:“尽有尽无,非极莫备。知无知有,吾许其道家,唯非有非无之一地,道言不及耳。”(《弘明集》卷六)
标签:道德经论文; 佛教论文; 道家论文; 日本道教论文; 道教起源论文; 道教传播论文; 文化论文; 集古今佛道论衡论文; 南北朝论文; 读书论文; 菩提论文; 道教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