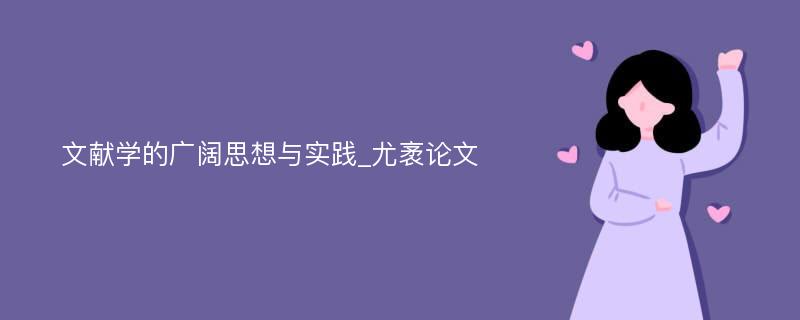
尤袤的文献学思想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尤袤是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曾做过国史院编修官、秘书丞、太子侍读等职,有机会阅读大量的皇家藏书。他建有遂初堂、万卷楼等专供藏书之用,其藏书量在当时首屈一指。尤袤将其所藏图书编成一部《遂初堂书目》①,该目被视为第一个著录版本的目录学著作,开启了版本目录学的先河;刊刻了李善注《文选》,世称“尤袤本”或“尤刻本”,在《文选》版本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遂初堂书目》、尤袤本《文选》为中心,结合相关文献,考察他在文献学领域的思想和成就。 一 尤袤的目录学思想 作为一部私家藏书目录,《遂初堂书目》内容虽简单,且没有解题,但在目录学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开创了古籍目录著录版本的先河。 宋代是雕版印刷发展的高峰期,同书异本逐渐增多,若不记录版本,不利于后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尤袤特别注重目录与版本的有效结合,在《遂初堂书目》中注意记录各种版本,如旧监本、旧杭本、杭本、旧本、京本、江西本、高丽本、川本大字、川本小字、吉州本、严州本、越本、越州本、湖北本、池州本、秘阁本等。虽著录版本者不足全书百分之二,且集中于经总类与正史类,但其开创了目录著录版本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叶德辉《书林清话·古今藏书家纪版本》云:“自镂板兴,于是兼言板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②叶氏所言一方面指出雕版印刷发展对版本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遂初堂书目》是第一个记录版本的目录学著作。尤袤之后,明清书目多记版本。如明代晁瑮编《宝文堂书目》,偶记版本于书名下;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注有宋本、元本、旧抄、影宋、校宋本等字”③;清代更加注重版本,尤其是宋元版,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偶注版本,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钱曾《述古堂书目》“卷首均别为宋板书目”④,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更直接以板本命名。尤袤可谓开辨别版本之风。 《遂初堂书目》注重广罗异本,尤其重视善本。同一本书,会著录多种版本,如《史记》有川本、严州本;《前汉书》有川本、吉州本、越州本、湖北本;《战国策》有旧杭本、遂初先生手校本、姚氏本等;《山海经》有秘阁本、池州本等。考察其所记版本,以浙江所刻最多,叶梦得曾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⑤叶德辉《书林清话》亦云:“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胪载旧监本、秘阁本、杭本、旧杭本、越本、越州本、江西本,吉州本、严州本、湖北本、川本、池州本、京本、高丽本,而南宋中盛行之建本、婺州本,绝不一载,岂非以当时恒见之本,而遂不入于目欤。”⑥由此可见,尤袤在收藏时有强烈的版本意识,杭州本质量高,故收藏较多,福建本质量差,所以不予收藏(或不记录在案)。 《遂初堂书目》还有一个特点,即重视史学,尤其是当代史学文献的收集。北宋灭亡后,图籍被掳掠一空。南宋建立后,致力于文献的收集。南宋馆阁藏书多为本朝史籍,尤袤长期在南宋三馆及秘书阁供职,曾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尤氏的书,尤其是史书,许多当是从皇家馆阁中抄出,故在其藏书中,本朝书籍占有很大比重。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了解宋代史料提供便利。《遂初堂书目》虽未有明确经史子集的分类,而在实际编目中,依然遵循着四部分类法,其中经部9类,史部18类,子部12类,集部5类。其中,史部分类中有四处较为特殊,为尤袤首创,分别是:国史类、本朝杂史、本朝故事、本朝杂传。史部之书共980部左右,本朝大约280部,占史部总数的三分之一。仅从数量方面便可看出史部在《遂初堂书目》中的重要地位。尤袤重视史学,一方面与他的官职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时代学术思潮在他身上的体现。国史等类目的创立,无疑有助于保存当代史料,为后代保存、研究前代历史提供便利。 二 尤袤的版本学思想 《遂初堂书目》著录版本并非偶然,有其历史原因,是“雕版印刷的发展在历史文献学上的反映,或者说,因雕版印刷而随之产生的文献版本问题已引起了学者的足够的重视”⑦。两宋时期是雕版印刷发展的高峰期,随之而来的是刻书成为一种风尚。朱熹曾经感慨“平日每见朋友轻出其未成之书,使人摹印流传而不之禁者,未尝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之不远也”⑧,可见当时滥刻之风。不仅如此,刊刻时以意改书的情况也大有人在。苏轼云:“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⑨ 尤袤亦刻书,但其刻书态度端正,质量较高。据现存史料可知,尤袤至少刊刻过《文选》《山海经》《隶续》《申鉴》《玉堂集》与《河南集》等六种古籍。尤袤《文选跋》云:“踰年乃克成……淳熙辛丑上巳日晋陵尤袤题。”袁说友《文选跋》亦云:“阅一岁有半而后成,则所以敬事于神者厚矣。”由此可知,尤袤当在淳熙六年(1180)下半年始刻《文选》,于淳熙八年(1181)上巳日完工。又,《梁溪遗稿》文抄补编中存有一篇《山海经跋》,跋文后标明“淳熙庚子仲春八日,梁溪尤袤题”。尤袤当于淳熙七年(1180)农历二月刻《山海经》。又,《四库全书·目录类二》提要记: 《隶续》二十一卷,宋洪适撰。适既为《隶释》,又辑录《续》,得诸碑依前例释之,以成是编。乾道戊子始刻十卷于越,其弟迈跋之。淳熙丁酉范成大又为刻四卷于蜀,其后二年己亥德清李彦颖又为增刻五卷于越,喻良能跋之。其明年庚子尤袤又为刻二卷于江东仓台,辇其版归之越。⑩ 洪适《盘洲文集》卷六十三《池州隶续跋》载:“明年(淳熙七年)锡山尤延之刻二卷于江东仓台,而辇其板归之越,延之与我同志,故郑重如此。”(11)由此可知,淳熙七年(1180)尤袤还刊刻了两卷《隶续》。又据《梁溪遗稿》文抄补编《申鉴题辞》所记可知其于淳熙九年(1182)刊刻过《申鉴》。《郡斋读书志》卷五下《附志·张文定玉堂集二十卷》记: 右张文定公方平之文也。公字安道,宋城人。明道二年以茂材异等擢为校书郎。神庙时参大政,元佑六年终于太子少师致仕,赠司空,谥文定公。出入两禁垂二十年,一时大典多出其手。刘忠肃尝序其《玉堂集》二十卷,乃在东坡所序《乐全集》四十卷之外。淳熙九年,锡山尤袤重刻于江西漕台。(12) 可知淳熙九年(1182)尤袤还刊刻了张方平《玉堂集》二十卷。从淳熙六年至九年,尤袤连续四年致力于刊刻事业,至少有五部成果问世,可谓成果颇丰。晚年仍坚持刻书,据《河南先生文集》附录《杂见事实·河南集跋》载: 师鲁集二十七卷,承旨姚公手录本。予往尝刻师鲁文百篇于会稽行台,今乃得阅其全集,甚慰,因付梓行之。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师鲁,一再传而后有欧阳氏、王氏、曾氏,然则师鲁其师资云。淳熙庚戌,锡山尤袤延之跋。(13) 淳熙庚戌应即绍熙元年(1190),尤袤在1189年前后刻印尹洙《河南先生文集》,时已年过花甲。 以上六部古籍的刊刻,一方面与时代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也源于他对书籍的热爱与官职的便利,同时也与他的文献学思想密切相关,可以说,这些古籍的刊刻正是他文献学思想的真实反映。 第一,坚守学术,择优而刊。 《文选》主要分李善注与五臣注两种,从五臣注诞生之后,直至宋朝初期,一直为世人所重,李善注则居于下位。其中虽不乏支持李善注者(14),亦无法扭转整体趋势。北宋天圣中(1023-1032),刘崇超上言:“李善《文选》援引该赡,典故分明,欲集国子监官校定净本,送三馆雕印。”这说明李善注的价值重新被世人发现。在刘崇超的建议下,北宋国子监刊刻了李善注《文选》。从此,李善注的地位逐渐上升。苏轼亦赞赏“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15),批评五臣注“真俚儒之荒陋者”(16)。像苏轼这样的大文豪,在学术领域的号召力与影响力非同凡响,甚至可以改变一个时代的学术走向。尤袤就深受其影响,放弃当时流行甚广的五臣注和六臣注本《文选》,敏锐地选择了李善注。他在《文选跋》中说:“贵池在萧梁时寔为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载,威灵赫然。水旱疾疫,无祷不应。庙有文选阁,宏丽壮伟,而独无是书之板,盖缺典也。今是书流传于世,皆是五臣注本。五臣特训释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独李善淹贯该洽,号为精详。虽四明赣上各尝刊勒,往往裁节语句,可恨!”尤袤对于李善注、五臣注的认识与苏轼等人一致。 第二,汇集众本,谨慎校勘。 清人讲究版本,尤其珍视宋元本,而在翻刻时则存在究竟是保留原貌还是校改的争议,这属于文献学理念不同。五代至北宋时期,是刻本产生的初期,在刊刻时自然与清人想法不同,宋人刊刻一本书不容易,在上版前定要仔细选择版本、认真校勘,尽可能呈现出一个价值较高、错误较少的版本。《册府元龟》卷六〇八记载:“先是后唐宰相冯道、李愚重经学,因言……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乃奏闻。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经注……先经奏定,而后雕刻……”(17)类似之例,数不胜数。这种做法在宋代是普遍的,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由于宋代的校雠学家学识渊博、态度认真,故而校勘出来的版本往往可信度很高,这也是后世看重宋本的一个重要原因。 尤袤也继承了这种校勘传统,在有多种版本可以参校的情况下,并非完全依照底本刊刻,而是广校众本,尽可能校出一个错误率低的善本。徐锴《说文系传》尾载尤袤《说文系传题跋》: 余暇日,整比三馆乱书,得南唐徐楚金《说文系传》,爱其博洽有根据,而一半断烂不可读。会江西漕刘文潜以书来,言李仁甫托访此书,乃从叶石林氏借得之。方传录未竟,而余有补外之命,遂令小子概于舟中补足。此本得于苏魏公而讹舛尚多,当是未经校勘也。乾道癸巳十月廿四日,尤袤题。(18) 通过“此本得于苏魏公而讹舛尚多,当是未经校勘也”一句,我们可以隐约看出尤袤赞成在校勘过程中改正舛讹之处,而非保留原貌的错误,这样有利于促成善本的产生,但前提是有校改依据。可以进一步证明此观点的证据便是淳熙七年池州本《山海经》的刊刻。尤袤在跋文中说:“予自绍兴辛未至今,垂三十年,所见无虑十数本,参校得失,于是稍无舛讹,可缮写。”尤袤辗转三十年,通过参校十数个版本,终于校勘出一个基本没有舛讹的本子,然后才加以缮写、刊刻。通过校勘,他还得出了《山海经》是先秦古籍,并非时人所言为后人所作的论断。可见其并非单纯校勘,还进行了一番深入研究。《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地理类“山海经十八卷”云:“今本锡山尤袤延之校定。”(19)尤袤之后,《山海经》才成定本,这是尤袤的一大贡献。另外,《遂初堂书目》记有“遂初先生手校《战国策》”一书,应是他拿“旧杭本”与“姚氏本”对校后得出的一个品质较高的版本。 《宋史》云:“袤少从喻樗、汪应辰游。”(20)汪应辰《文定集》卷一〇《跋贞观政要》记载: 此书婺州公库所刻板也。予顷守婺,患此书脱误颇多,而无他本可以参校。绍兴三十二年八月,偶访刘子驹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后唐天成二年国子监板本也,互有得失,然所是正亦不少,疑则阙之,以俟他日闲暇寻访善本,且参以实录史书,庶几可读也。(21) 尤袤与汪应辰的校勘思想非常接近,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且在学术上志同道合。因此,尤袤的学术思想,是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潮的一个缩影。 第三,疑则阙之,以俟知之。 《梁溪遗稿》文抄补编存尤袤《申鉴题辞》:“荀悦书五卷,观其言,盖有志于经世者。其自著《汉纪》尝载其略。而范晔《东汉书》亦摘其篇首数百言,见之《悦传》。近《汉纪》会稽郡已版行,而此书则世罕见全本。余家有之,因刻置江西漕台。但简编脱缪、字画差舛者不一,不敢以意增损,疑则阙之,以俟知之。淳熙九年冬十月己亥、锡山尤袤。”(22)《申鉴》与《山海经》情况不同。《山海经》世存多种版本,故而尤袤历经三十年,广校众本,目的是尽可能校勘出一个“稍无舛讹”的本子。而《申鉴》版本世所罕见,尤袤家藏一本,无其他版本可资参校,但惜其传之未广,故而刊刻以惠学林。在缺乏版本依据的情况下,尤袤即使发现“简编脱缪、字画差舛者不一”,仍不敢轻易校改,而是采取“疑则阙之,以俟知之”的处理办法。这种做法无疑是谨慎的,是校勘古籍的正确之道。 总之,尤袤的校勘学思想符合文献学发展方向。清代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亦提倡不轻改古书,而他在刻书时也只做到不轻改而已,遇有明显错误,又有底本为据,他还是会改。近代校勘学家章钰在《程雪楼集》跋文中说道:“老辈校勘之学,略分两例:一在存古,如覆刻经典古本,稍涉异同,则另撰校记,以备考证。一在求是,如唐宋以下著述,根据旧本,既灼知其脱误之处,获有佐证,亦不敢依样壶卢,为全书复留创痏。”(23)这些为后世文献学家遵循的法则在尤袤时便已使用。 三 尤袤的文献学实践 具体而微地探讨尤袤文献学实践成果,今天可以依据的完整资料主要有两部,一是《山海经》,二是《文选》。我们在从事《〈文选〉旧注辑存》过程中,就以尤袤本为工作底本,比勘众本,发现胡克家《文选考异》指出的尤袤误改之例,多有误判。原因在于,他所依据的是一个屡经修补的翻刻本,我们俗称其为胡克家本,又因其参校本有限,仅有袁本、茶陵本两种,分属六家本、六臣本,与李善本系统不同,出现这些错误可以理解。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文选》版本,如日本所藏《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下简称集注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国台湾省故宫博物院所藏北宋国子监本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尤袤本《文选》等(24),系统完备,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 袁说友在《文选跋》中说:“《文选》以李善本为胜,尤公博极群书,今亲为雠校,有补学者。”尤袤《文选跋》亦云:“虽四明、赣上各尝刊勒,往往裁节语句,可恨!”通过以上两句,我们可以得出三个信息:一是尤袤手中有多种《文选》版本,可供校勘之用;二是他在刊刻《文选》时必校勘过;三是袁称尤本“有补学者”,则其较底本定有改动,不可能完全依据底本。既然如此,尤袤本《文选》中应存在其校勘后留下的痕迹。 仔细查阅尤袤本《文选》,确发现较多校勘痕迹,个别字的剜改、两字间有空格、某处文字挤在一处,或一个字占两个字格等现象。森野繁夫先生因此认为“中华书局本成了尤本初刻本以后几度补刻的版本”(25)。但此观点并未得到学者们的赞同,学界仍普遍赞同程毅中、白化文先生的观点:“从胡刻本就可以看出,乙丑重刻的补版绝不止一页,而且在乙丑以前已经有好几次修补,可是在这个尤刻本中却一无所见。再从版面看,重刻的目录、《同异》非常模糊,而初刻的正文部分却比较清晰,显然不是后印本,而是一个初版的早期印本。”(26)据袁说友《文选跋》可知,尤袤本《文选》从校勘到刊刻完毕仅用时一年半。尤袤本《文选》于淳熙八年(1181)刊刻完毕,那么在淳熙六年便已开始校勘。据现有资料可知,尤袤淳熙七年(1180)刊刻过十八卷《山海经》与两卷《隶续》。尤袤本《隶续》现已不存,而《山海经》现存一帙。检《山海经》版心,未发现重刊字样,当为初刻,然版心刻工处较为模糊,故一些刻工姓名难以辨别,其中可辨认的有李彦、曹但、金大有、张拱、王明、刘彦中等。这些刻工并为尤袤本《文选》的刻工。由此可知,尤袤在淳熙七年、八年时雇用同一批刻工同时校勘并刊刻了三部书。又据尤袤《山海经跋》可知,他校勘十八卷的《山海经》花费了三十年的时间,而六十卷《文选》从校勘到刊刻仅用时一年半。因此,我们大胆猜测,尤袤应该是采用了校勘与刊刻同时进行的方式,在发现错误时,通知刻工进行修改,但考虑到时间与成本问题,不能整版换掉,故而造成了我们现在见到的修版痕迹。其实,查看尤袤本《山海经》也可发现类似现象。如《山海经上》(27)第六页注文“槀苃香草”四字占两字格,明显较周围拥挤。又,第十页“滂水出焉”注文“音滂沱之滂”,其中“沱之滂”三字占两字格,挤在一处。又,《海外北经》第八的首页“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注文“《淮南子》曰:龙身□足”,两字间有空格。但因《山海经》特殊的段落格式以及注文内容较少、较为简单等因素,许多内容即使修改也很难看出痕迹。结合以上诸条,我们认为国家图书馆所藏宋淳熙八年池阳郡斋刻本《文选》当是初刻,其中的修版痕迹系尤袤所为的可能性更大。那么,尤袤是如何修版的呢? (一)在原版基础上通过局部剜改以增减文字,因此,某些行款略显拥挤或稀疏。此类修版较易发现,数量也最多。 1.卷三十七第十五页“窃不愿于圣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惨毒之怀”。 案:尤袤本此句正文挤在一处,考北宋本无下“有不蒙施之物”六字,然集注本与尤袤本同。胡克家《文选考异》谓:“茶陵本云五臣再有‘有不蒙施之物’六字,袁本再有,云:善无‘有不蒙施之物’六字。案:此初无,尤修改添之。《魏志》再有,善亦当再有,传写脱去也。”(28)尤袤本底本当无此六字,尤袤据其他版本增补。 2.卷三十第十二页(29):“纷虹乱朝日,浊河秽清济”句注文“《战国策》张仪说秦王曰……”。 案:尤袤本“秦王曰”三字挤在一处,应较底本多一字。考北宋本与尤袤本同,集注本无“秦”字。故此处尤袤本底本应与集注本同,无“秦”字,尤袤据北宋本或其他版本增补。 (二)在原版基础上进行个别字的局部剜改,这种情况主要是针对单个字的校勘,校勘后的字会显示出与周围字不同的墨迹、字迹。此类校勘较难发现,需仔细排查。 1.卷九第三页:“于是上帝眷顾高祖,高祖奉命,顺斗极,运天关”句注文“《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令”。 案:尤袤本“令”字明显有描改痕迹,北宋本此处阙,考奎章阁本、赣州本并作“命”字。尤袤本应发现底本此处有误,故剜改该字作“令”。 2.卷三十一第十六页“百年信荏苒,何用苦心魂”句注文“人生要死,何为苦心”。 案:尤袤本注文“要”字明显与周围字体风格不同,考北宋本作“恶”,集注本与尤袤本同,作“要”。由此可见,尤袤本底本当作“恶”,尤袤据其他版本改作“要”。 (三)有断版痕迹,此类情况较易发现,在整部尤袤本《文选》中数量不多。 1.卷十一第二十二页中间五列有明显断版、补版痕迹。仔细考察发现,其中“大哉惟魏,世有哲圣。武创元基,文集大命”句注文尤袤本作“武,武帝。文,文帝。并见《魏都赋》。《毛诗》曰:世有哲王。《尚书》伊尹曰:天监厥德,用集大命。孔安国曰:集主命于其身”。北宋本此处阙,奎章阁本与尤袤本同。然考明州本并无“武,武帝。文,文帝。并见《魏都赋》”一句。据此推测,尤袤本盖因补以上十一字,故将此五行重新刻版。 2.卷五十七第二页中正文:事君直道,与朋信心。虽实唱高,犹赏尔音。注文:《论语》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宋玉《对问》曰:曲弥高者,其和弥寡。曹植《求自试表》曰:或有赏音而识道。 同页正文:弱冠厉翼,羽仪初升。注文:《礼记》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吕氏春秋》曰:征鸟厉疾。《周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案:自前一句注文“弥高者其和弥寡”至后一句注文“吕氏春秋”止,这部分内容共占一行,该行上端有明显的断版痕迹。该行二十六字,正常应二十一字,因注文是双行,故共多出十字。考北宋本,无“礼记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句,恰为十字。胡克家《文选考异》云:“袁本、茶陵本无此十字。案:此即尤误取增多者。”(30)然集注本有此句,可见并非尤袤“误取”。尤袤本底本原无此句,尤袤据其他版本增补,但由于增补字数较多,为方便或节省成本,仅将此行重刻,故而造成了断版、补版痕迹。 (四)尤袤校勘、刊刻《文选》亦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因此,仅据集注本与北宋国子监本还无法解释所有尤袤本中的修改痕迹。如卷五十七第十二页“值国祸荐臻,王略中否。獯虏间衅,劘剥司兖”句注文“潘岳《阳肇诔》曰:将宏王略。沈约《宋书》曰:司州,汉之司隶校尉也。武帝北平关、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兖州,后汉居山阳,武帝平河南,居滑台”。案:尤袤本此段注文宽疏,考集注本、北宋本并有“劘与摩音义同”。此种情况,有可能为后人删改,但亦有可能是尤袤所为,胡克家《文选考异》便持此观点,“注末有劘与摩音义同六字。案:有者是也。尤删移,非。”(31)据集注本与北宋本,我们可以知道尤袤本的底本原是何样,但仅据现有资料无法找出尤袤参校并据以修改的版本。 上述一些问题暂时得不到解答,但通过对尤袤本与《文选》版本的比勘仍可以总结出尤袤在校刻时的一些特点。首先,尤袤校勘内容多集中于注文,正文极少。其次,尤袤校改有版本依据,并非随意修改。第三,尤袤本底本并非是北宋本、集注本,但从校改痕迹反映出的实际情况判断,北宋本与尤袤本底本最为接近。北宋本于景德四年(1007)首次刊刻,大中祥符八年(1015)毁于大火,天圣年间(1023-1032)又重新据当时藏于太清楼的副本刊刻,因副本为“损蠧”之本,故此本只能称之为北宋国子监递修本。我们现在所见即为北宋国子监递修本。因此,尤袤本与其存在差异是必然的。尤袤本的底本应是一个与北宋本十分接近、同属一个系统的单李善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