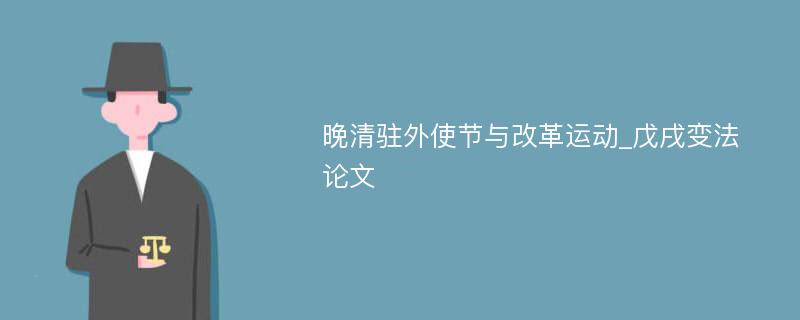
晚清驻外使领与维新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新运动论文,晚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中国向海外派驻使领,始于1875年8月郭嵩焘出使英国。 两年后,清政府应郭氏之请,首次向新加坡派驻领事,随后又先后向日本、法国、德国、俄国、美国等国派出公使,在南洋、日本、澳洲等地的商埠设立了领事,并逐渐建立起一套驻外使领制度。截止到1911年,清政府先后在英、法、美、俄、德、奥等16个国家派驻有公使,在新加坡、槟榔屿、仰光等世界各地的45个商埠设立了领事。
据不完全统计,从1875年到清末,有姓名可考的驻外公使、领事达60人之多,如果加上使领馆的参赞及其他人员,人数将更多。他们作为晚清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不仅对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对晚清驻外使领及其随员与维新运动的关系作一探讨。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乃为驻外及出使归国人员与维新运动的直接关系。至于早期出使人员对维新运动的思想影响,在此不予涉及。
一 吕海寰、伍廷芳等人与维新运动
维新运动期间驻外的公使,计有驻英公使龚照瑗、罗丰禄,驻俄公使许景澄、杨儒,驻法公使庆常,驻德公使吕海寰,驻美公使伍廷芳,驻日公使汪凤藻,驻朝公使徐寿朋等。驻外领事则有驻新加坡领事张振勋、刘玉麟,驻槟榔屿领事张鸿南、谢荣光,驻菲律宾领事陈纲,驻横滨领事吕贤笙、杨士燮,驻神户领事余佑蕃、邹振清,驻长崎领事杨枢,驻箱馆领事洪涛,驻汉城领事唐绍仪、汤肇贤,驻仁川领事唐荣浩,驻海参崴商务委员李家鏊,驻檀香山领事杨蔚彬,驻旧金山领事冯咏蘅、余思诒、张荫棠,驻纽约领事徐乃光、施肇曾、钟宝僖,驻古巴领事黎荣耀,驻嘉里约领事许鼎霖、胡鹏年等。至于各使领馆的参赞、随员人数,至今尚无人作详细统计,不得而知。
客观地讲,维新运动期间驻外的使领们都与运动发生过直接关系。早在1896年7月30日,因有人奏请派令学生出洋, 清廷就曾谕令各出使大臣“酌量奏调”(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出版,第4页。)。百日维新开始后,清廷又应人之请,于8月21日谕令出使大臣督同各领事,在英、美、日本等国华侨聚居地方创办学堂,培养人才;同时令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法公使庆常、驻美公使伍廷芳等就近购译善本西书,“汇送总理衙门呈览”(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出版,第58页。)。9月11日,清廷又应孙家鼐之奏, 谕令各驻外公使在使馆内就近编译“洋务巨帙”(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出版,第84页。)。因此,当时无论各驻外使领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如何,都无一例外地与之发生了直接关系。当然,各驻外公使并不仅仅是被动地执行清廷的指示,一些人对新政表现出了极大热情,他们主动上奏朝廷,鼓吹变法,支持新政,并取得了很好效果。在这一方面,以驻德公使吕海寰和驻美公使伍廷芳最具代表性。
吕海寰早年追随李鸿章,后经李推荐,任出使德国、荷兰大臣。维新运动开始后,吕氏不仅是《时务报》、《知新报》的热心读者(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40页。 ),而且于百日维新前夕,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主动上奏朝廷,系统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注:《出使德国大臣吕海寰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24页。)。其变法主张主要包括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内政方面主要是练兵和筹饷;外交方面主要是睦邻和安教。在讨论筹饷问题时,他提出了整顿税则、修改关税的主张。这就涉及到了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
伍廷芳在整个维新运动期间曾先后4次上奏朝廷,鼓吹变法。 其变法主张主要包括:
首先,时势所迫,不得不变,失此不图,后悔莫及。1898年2 月10日,伍廷芳因见教案迭起,而内治无权,因此上奏清廷,请求变通成法,亟图补救。百日维新开始后,他在所上奏折中进一步强调了变法维新的重要性,说:“今时事方艰,强邻逼处,胶事甫定,旅顺、大连湾、威海、广州湾之事,循生迭起,如环无端,边患愈危,疆土日削。……乃者列邦密谋,报章腾播,因利乘便,同以瓜分为言,是直以波兰待我也。其所以迟疑却顾不即决裂者,以中国地大物博,骤难并吞。又恐宰割不平,互相争夺,适启天下之兵,误欧洲太平之局耳,其心岂尝须臾忘我哉。及今亟变尚可有为,失此不图,后悔无及。”在同一份奏折里,他还指出:“帝王不相沿袭,制度惟贵因时,泰西各国百年来,日益强盛,风气聿新,我与为邻,岂复能拘守成法。”督促朝廷痛下决心,速决变法大计:“凡有应兴应革诸务,当与在廷臣工通知时事者,熟计利害,内决圣断,毅然行之。”(注:《出使美国日国秘国大臣伍廷芳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3页。)
其次,变法图存,首在自强,自强之要,首在内治。早在《奏请变通成法折》中伍廷芳就指出:“窃查近来边衅之开,每起于教案。而教案所以多者,推原祸始,则由昔年与之订立条约,许以遍地传教,不许以内地通商,殊为失策。……今欲预弥其变,惟在内治有权。”(注:伍廷芳:《奏请变通成法折》,《伍廷芳集》(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7~48页。)百日维新期间,他又在上奏中指出:“夫我欲图存,惟在自强,自强之要,先在内治,内治既定,外侮无自而启。”(注:《出使美国日国秘国大臣伍廷芳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3页。)他所说的内治,在当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奏请变通成法折》中,他认为,要想内治有权,必须废除领事裁判权。百日维新开始后,他在上奏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变革内政的思想,兹述如下。
政治上,破格用人,固结民心,整饬吏治,矜恤刑狱。所谓破格用人,即不受资格限制,广求人材;所谓固结民心,即试仿泰西各国方便之政,特旨裁罢一切苟且之计、苛敛之条,朝廷宣宽大之诏,廊庙下罪己之诏。所谓整饬吏治,即请旨饬下各疆臣,罢无谓之虚文,除供应之陋习,务求循吏谨牧养民;并明诏部臣,酌汰循行之文牍,画一歧两之成案。对整顿财政,他主张请旨饬下户部派司员之才略干练、明习时事者,赴日本考其理财之法,详究得失,择善而从。如有未尽事宜,随时饬知各驻外使臣留心考订,以备参酌。对刑狱制度的改革,早在《奏请变通成法折》中,他就曾要求朝廷饬下部臣,采各国通行之律,折中定议,勒为通商律例一书,明降谕旨,布告各国。所有交涉词讼,彼此有犯,皆以此为准。百日维新开始后,他在上奏中再次主张请旨饬下刑部,参取西法之良,以为录囚之助。伍廷芳的这一主张,在清末改制过程中得以实现。
军事上,广储将才,慎选海军。早在百日维新之前,伍廷芳就曾上奏朝廷,主张京营绿营参用西法。后在上《请求变通成法折》时,又提出借材异邦当以美国为宜的主张(注:伍廷芳:《奏为清廷借材异地当以美国为宜片》,《伍廷芳集》(上),第51~52页。)。百日维新开始后,他在上奏中再次指出:要培养必胜之将,不仅要武科改制,武备设堂,讲求经武,而且应在平时严格要求。对于海军,他主张江浙闽粤等近海各省,慎选兵勇,重建水师,以抵御外侮。
经济上,讲求农务,振兴矿务,维持商务,策励工艺。对农业,他主张分饬各省有司,考求西法,搜采各国有裨农务之书,择要译录,广为传播。仿犁锄之新制以尽地利,验粪田之化学以究物情。并于学堂学会,加意奖励,多方诱掖,其学有成就者,分别鼓励,使其转相传播,分诣郡县,就地垦荒,给以执照,优以利益。对振兴矿物,他主张请旨专派矿物大臣,择地分驻,新董厥事。纠华商联络公司,任洋商分认股票。对维持商务,在《奏请变通成法折》中他就主张请旨密饬总理衙门,将各国通商一条通盘筹算,逐渐扩大与各国的通商贸易。百日维新期间,他又在上奏中特别指出:“请旨饬各省督抚,体察地方情形,于各口镇繁盛之处,奏请简派商务大臣,专访究各国通商事宜,参互考订,以图振兴内地商务。所有员绅归其遴选,商业归其保护,章程有不便者酌予更易,丁役有索扰者立为提究。大者上闻,小者专决,官民一体,疴痒相关,弊端悉除,利市百倍。”(注:《出使美国日国秘国大臣伍廷芳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6~37页。)对工艺制造,他主张仿照西方各国,推行专利制度。
此外,他还主张平治道路,推广报馆。
在当时,直接上奏朝廷是高级官员的特权,大多数出使人员,特别是各使领馆的参赞、随员无此资格。但是他们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积极参加了这场变法运动。当时各报刊登的关于新政和外国情形的文章,有许多就是由驻外使领馆人员撰写或翻译的。在翻译西文西报方面,以驻英使馆翻译陈贻范、驻美使馆翻译周自齐和驻海参崴商务委员李家鳌最具代表性。《时务报》创刊后,陈贻范经人介绍,应汪康年和梁启超之请,为《时务报》翻译英文稿件。据笔者查考,维新运动期间,陈在《时务报》刊出的译文有第39册、40册的《俄人蚕食太平洋迤北边地考》,第54册、55册的《英京日报馆访事人郎夺君游藏被难略述》,第55册的《英国威思德敏思偷读书堂章程》,第59册、60册的《英相沙侯要议院宣论东方事》,第61册的《英议院绅及外部侍郎宣读东方事》,在《昌言报》刊出的译文有第4 册的《伯爵金盘里在议院论英国外交事宜》和第5册的《英相沙侯答伯爵金盘里议论外交事宜》等文。 周自齐在当时不仅积极为《时务报》寻找翻译人才,而且亲自动手翻译,《时务报》第46册所刊《美国新定禁止粗劣各茶出口条例》即为其所译。李家鏊出国之前,就愉快地接受了汪康年和梁启超的邀请,兼充俄文报译事(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55页。 )。据查,《时务报》第51、52册的“俄文报译”即为李家鏊所译,内容涉及日本武备、中德军务、胶州兵事、西伯利亚铁路经费及俄国远东驻兵等情况。
二 出使归国人员与维新运动
维新运动期间出使归国人员为数甚多,据笔者所知,当时直接参与变法运动的计有张荫桓、黄遵宪、李维格、姚文栋、宋育仁、汪大钧、陈季同、徐建寅、邹代钧、马良、马建忠、陶森甲、黄致尧、黄庆澄、张祖翼、张美翊、杨文会、蔡钧、蔡锡勇、郑孝胥、钱恂等,如果加上其他不知姓名者,人数将更多。
讨论出使归国人员与维新运动的关系,如果不是抱有某种偏见的话,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张荫桓。百日维新期间,身为总理衙门大臣、处在中枢位置的张荫桓,积极参加了这场变法运动,光绪皇帝也将其视为股肱,许多新政事务都命其负责办理。如8月2日,光绪皇帝命在京师专设矿物铁路总局,特派张荫桓与另一位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专理其事,所有各省开矿筑路一切公司事宜,俱归统辖,以专责成。”(注:《戊戍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8~49页。)8月10日, 光绪皇帝又命张氏和王文韶负责在“所有各处铁路扼要之区,及开矿省份”,增设学堂。(注:《戊戍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3页。)同一天,御史杨深秀奏请招商承办津镇铁路,光绪皇帝命张王二人“酌核办理”(注:《戊戍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3页。)9月2日,给事中庞鸿书陈请创修铁路开拓矿物,光绪皇帝立即命张王二人“酌核具奏”。9月12日, 詹事府左中允黄思永奏请由国家设立铁路矿物公司,任听各国商人入股。光绪皇帝又命张王二人“妥议具奏”,并采纳了他们“请勿庸议”的建议。(注:《戊戍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84页。)当然,张荫桓在当时并不是被动地参与变法,机械地执行光绪皇帝的谕令,而是抱着积极参与的态度,并曾多次主动建言。仅百日维新期间,他就连续三次上奏。他还根据光绪皇帝的谕旨,让梁启超议定康有为所上的《请励工艺奖募创新折》,然后由总理衙门奏定章程,“颁行天下”(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48页。)。
在当时的出使归国人员中,像张荫桓这样既处在中枢位置又得到光绪皇帝垂青者毕竟是少数,其他人,除前驻英使馆随员邹代钧、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驻德使馆参赞徐建寅等人因受地方官保荐而或被送部引见、或命督理农工商总局外,大多数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加维新运动。综观他们在当时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组织学会,创办学堂,发表演讲,宣传西学知识,鼓吹变法维新。维新运动时期是学会、学堂等近代社团和文化机构蓬勃兴起的重要时期,当时成立的大多数学会,都有出使归国人员参加,如北京强学会,张荫桓曾列名其上;上海强学会,邹代钧、黄遵宪、黎庶昌等均曾列名会籍。出使归国人员不仅积极参加康梁筹设的进步团体,而且亲自创办学会、学堂,传播西方文化,鼓吹变法维新。如武昌的译印西文地图公会,就是邹代钧在陈三立、汪康年、吴德潇等人的帮助下于1895年创办的。南京的测量学会,则由前驻英法使馆随员杨文会与刘聚卿、茅子贞等人于1897年创办。成都的蜀学会由前驻英使馆参赞宋育仁于1898年4月创立。维新运动期间最为活跃的湖南时务学堂和南学会, 也都有出使归国人员参与其中。黄遵宪、邹代钧及前驻英使馆随员李维格等人不仅参与了南学会创办活动,并在会上多次发表演讲。黄遵宪就曾在会上以“论政体公私必自任其事”为题发表演讲,鼓吹地方自治。(注:《黄公度廉访第一二次讲义》,《湘报》第5号,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出版。)
第二,创办报刊,撰写文章,鼓吹变法。维新运动时期是中国“民报勃兴时期”(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13页。),当时各种新式报刊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出现。 从 1895 年到1898年,三年之中,新出现的报刊即达数十种之多。这些报刊的创办和经营,又多与出使归国人员有关。例如,当时影响最大的《时务报》,就是由黄遵宪与吴德潇、邹凌瀚、汪康年、梁启超五人共同创办的,李维格则是该报英文稿件的主要译员。《渝报》和《蜀学报》由宋育仁一手经办,《求是报》的创办人之一是前驻德法使馆参赞陈季同,《工商学报》则由刚刚回国的驻美使馆参赞汪大钧创办和主编。出使归国人员不仅创办、主编新式报刊,而且撰写文章,鼓吹维新变法。这方面可以宋育仁和汪大钧为代表。
宋育仁在1897年就曾著成《泰西各国采风记》,鼓吹维新变法,后来又在《渝报》和《蜀学报》上先后发表了《本报序例》、《复古即所以维新论》、《原学校》、《守御论》、《时务论》等文。其中以《时务论》最具代表性。在该文中,他从十三个方面论证了西艺、西学及西政在中国古已有之,并从十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复古改制,并指出:“前之言十三效者,酌行为十四事,诚富强之要术,古今之明验,而犹非以为治本也。”(注:宋育仁:《时务论》,第13~14页。见《皇朝经世文新编·通论》。)什么是治本呢?在他看来,即通下情,明教典,核名实,课民职。在谈到通下情时,他特别指出:“外国凡有举废,皆询于上下议院。两院议成而后谋定,国主报可而后施行。虽有植党而交讧,未有欲陈而无路者也。凡有陈告,皆无所壅,交讧之久而是非亦见。夫非必能所行俱善,然两议而决所长,两端而从其众,此必有多取于顺民情者矣。”(注:宋育仁:《时务论》,第13~14页。见《皇朝经世文新编·通论》。)
汪大钧于1896年以参赞的身份随伍廷芳出使美国,回国后,汪又在《时务报》发表了《保富篇》、《论变法当务为难》等文。《工商学报》创刊后(1898年9月),他又在该报上发表了《工商学报缘起》、 《拟设中国商务公司劝商场议》、《钞币私议》等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保富篇》和《论变法当务为难》二文。在《保富篇》中,他批评清政府借抽取厘金、捐纳、牙帖、普捐以及息借商款、发行昭信股票等聚敛民财的错误做法,说“以是言富,吾恐其愈贫也;以是言强,吾恐其愈弱也。”他认为,谋国是者,应该考虑藏富于民,即恤小民之身家,培闾阎之元气,免苛派,禁抑勒,删款目以杜舞文,节员役以绝中饱,利之所在,鼓舞而振兴之,弊之所丛,改弦而更张之。如此,三五年后,中国便康阜可期。他还探讨了中国“仁政”不能施行的原因,说:中国之患,不在仁政之不举,忠爱之不发,而在君民隔阂,上下交征,恩屡降而未逮于民生,款屡集而不归诸实用,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情之不通”(注:汪大钧:《保富篇》、《论变法当务为难》,《时务报》第64册,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版。)。
在《论变法当务为难》中,他认为危害中国的主要有三事,即科目、资格和例案。“科目废才,资格废官,例案废事,循环往复,遂中膏肓。”因此要根除三害就必须废科目,破资格,除例案。“然而望科目以梯进取者,守资格以邀贵显者,缘例案经营奸宄者,齐州之大,奚止百万。其人又率皆缙绅之族,清要之班,狡黠巧猾之徒,一旦改弦更张,必惧而协以谋我。”所以说,“非布新之难,而除旧之难也”。他认为:“大厦将倾,工师缩手,是必易其梁栋,去其朽蠹,徒粉饰支柱无益也。若以易梁栋去朽蠹为不便,而粉饰支柱焉,一旦栋折榱崩,居其下者,有能幸免者乎?我不除而人除之,不如及早而除之也,我不布而人布之,不如及早而布之也,勿狃目前之损益,而计大局之安危,上无畏心,下无阻力,庶难者不终难,变者可终变乎?”(注:汪大钧:《保富篇》、《论变法当务为难》,《时务报》第66册,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版。)对维新变法的成功充满决心和信心。
第三,翻译外国书报,宣传新知识;帮助推销新报刊、新书籍,传播新文化。与旧式封建士大夫相比,晚清出使人员具有如下特点:1.都曾到过或正在国外,有些还是国外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沐浴过欧风美雨;2.大多数都懂得一门甚至几门外语,对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为他们在维新运动期间翻译西文西报,宣传新知识、新思想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许多报刊刊登的关于外国情形的文章,就或由出使归国人员翻译,或为他们在任时的旧译。仅以《时务报》为例,该报第1至11册连载的《华盛顿传》, 为原驻日本横滨兼筑地领事黎汝谦及随员蔡国昭旧译。第13至15册连载的《奥斯加马国铁路商办条例》及第17册刊登的《法国印花税章程》等则由原驻西班牙使馆参赞兼代办公使黄致尧翻译。第31册、32册的“英文报译”一栏由李维格翻译,后面各卷虽由他人翻译,但均由其勘定。第31册至33册刊登的《西悉毕利亚铁路考略》由原驻英、法、意、比等国公使馆参赞钱恂翻译。第41册刊登的《伏尔铿制造股会章程》为徐建寅在德国时所译。第46册至第50册的《美国合邦盟约》则由原驻美使馆翻译官蔡锡通翻译。此外,陈季同也在自己创办的《求是报》上先后发表了自己翻译的《拿布伦立国律》、《拿布伦齐家律》、《法兰西报馆律》、《卓舒及马格利小说》等文。
出使归国人员不仅投书新报刊,宣传新知识,新思想,而且积极帮助推销新书刊,传播新文化。当时出版的各种新型书刊在全国各地均设有派报处,许多派报处就是由出使归国人员负责经营的。如邹代钧就曾经在湖南帮助经销《时务报》,一年之中使《时务报》在湖南的销量从每期几十册上升至600多册,为湖南维新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 驻外使领及其随员在维新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晚清驻外人员在维新运动中的活动具有特别的意义,并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就吕海寰、伍廷芳、张荫桓等人的上奏来说,在当时均曾受到光绪皇帝的重视,并被以谕旨的方式加以推行。对吕海寰的上奏,光绪皇帝在8月8日批示:“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王大臣切实妥实具奏。”(注:《出使德国大臣吕海寰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24页。)作为新政内容之一的铁路矿物总局,虽不能说是应吕海寰的建议而设立的,但很难说与其毫无关系。对伍廷芳在上奏中指出的“京营绿营参用西法”的建议,光绪皇帝曾谕令军机大臣会同督办军务大臣,暨神机营王大臣、八旗都统“妥速具奏”。后来王大臣议奏,一致认为:“改练洋操,为练兵要著,各省绿营练勇,叠经谕令认真裁并,一律挑练,著该将军督抚,归入前次户部兵部议覆御史曾宗彦请改操折内,一并迅速筹议,切实具奏。神机营业经挑选马步官兵万人,勤加训练,即著汰弱留强,实力讲求,务成劲旅,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骁骑营,两翼前锋护军营,均著以五成改习洋枪,五成改习洋机抬枪……其八旗汉军炮营藤牌营,著一并改用新法,挑拣精壮,如式演练,以成有用之兵。 ”(注:《戊戌变法》(二), 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3~34页。)对伍廷芳在《奏请变通成法折》中提出的修改律例的建议,清廷在百日维新期间曾电寄伍氏:“前经总理衙门议覆伍廷芳奏请变通成法案内,饬令该大臣,博考各国律例,及日本改定新例,酌拟条款,咨送总理衙门核办,现当整饬庶务之际,著伍廷芳迅即详慎酌拟,汇齐咨送,毋得迟延。”(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9页。)另外,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还曾发布一道谕旨,令工部会同管理河道大臣等负责挑挖京城内外河道沟渠,修垫各街巷道路(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73~74页。)。对此梁启超曾说,这道上谕是应康有为的建议而发布的。不过,就上谕的内容看,恐怕与伍廷芳在7月23 日上奏中提出的“道路宜平”等主张亦不无关系。
同样,百日维新期间张荫桓提出的各项建议也都得到光绪皇帝的重视,并被以上谕的方式加以推行。仅9月5日一天,光绪帝就针对张氏的上奏发布三道上谕。如张氏曾奏请“增修内政以戢民志”,光绪皇帝发布上谕说:“国家振兴庶务,尤以通达民隐为先,各直省州县,于听讼一事,久不讲求,往往于户婚田土钱财细故,任意积压,累月经年,书役门丁,因之藉端讹索,愚民受累无穷,亟应实力整顿,以除积弊而恤民隐。”除令重为刊印曾国藩当年所撰的《清讼事宜》及《清讼功过章程》外,同时命令:“著照该侍郎所请,于原定功过章程外,增补道府功过章程。所属州县局员,有记大过三起以上者,道府记过一次,六起以上者,记大过一次,记功亦如之。其有徇隐在先,续行举报,或揭参隐匿,提案清结,除将州县局员,分别轻重参撤记过外,道府亦即比例记功,凡实缺计典,候补委署,以及年终密考,俱以清讼之功过,分别予夺优劣,该将军督抚府尹等,务当认真考核,实力奉行,以期政平讼理,不准虚应故事,视同具文,并将遵办情形,迅速具奏。”(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73页。)再如张荫桓曾上奏请饬实行团练,光绪看到后又发布上谕:“办理团练,既可辅兵力之不足,亦即为举办民兵根本,实为目前切要之图。……著各省督抚,按照张荫桓所奏,一律切实筹办,各直省限三月内,广东、广西限一月内,各将筹办情形,先行覆奏。”(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74页。)同一天,光绪帝还就张氏所上“胪举将材请旨简用一折”发布上谕,将张氏所保荐的多位武官或著交部带领引见,或著开复原官原衔,发往山东交张汝梅差遣委用(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75页。)。
当然,由于维新运动后来遭到慈禧太后的镇压而失败,大多新政措施也很快被废除,吕海寰、张荫桓等人的变法主张自然也无法幸免,但我们不能因此便否认他们在运动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其次,就黄遵宪、宋育仁等人实践活动来看,他们在运动中虽不能像吕海寰、伍廷芳、张荫桓等人那样,引起光绪皇帝的重视,但对推动运动的发展,扩大运动的声势,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许多进步团体为其所创办,许多进步报刊为其所经营,许多活动为其所领导。但是,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不是某个人的政治冒险,因此,如果没有众多新型知识分子的参加,仅凭康有为,乃至康门弟子,即人们常说的“康党”,运动的规模、声势便不会如此之大,影响也不会如此深远,而驻外使领及其随员就是这些新型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或许有人会说,没有驻外人员的参与,维新运动照样可以发生。这有可能。但问题是,这些人参与了,其中某些人,如黄遵宪、宋育仁等,不仅是参与,实际上起着领导作用。当然,具体到每一个人,他们在运动中的态度、活动、影响并不完全一样,但作为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参与,在当时对推动运动的发展,壮大运动的声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次,一些人虽然没有像黄遵宪、宋育仁等人那样,在运动中积极组织进步团体,创办新式报刊,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宣传西学知识,鼓吹变法维新,他们仅是为各种新式报刊翻译西文西报,传播西学知识,但他们的活动在当时仍具有特别的意义。戊戌维新运动首先是一场政治变革运动,但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作为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在当时虽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大同思想,但他将其置于遥远的将来,认为眼前只能行小康,即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出于各种考虑,甚至连设立议院的主张也不再提起。当时的许多驻外或出使归国人员,他们虽然没有机会系统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他们对西方各国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的认识深度和宣传力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康梁等人。如黎汝谦翻译的《华盛顿传》,就不仅仅是在介绍华盛顿个人,同时介绍了美国的历史和政治制度。黎氏在该书《凡例》中明确写道:“是书虽华盛顿一生事迹,而美利坚全国开创事实,与夫用兵征饷和制度人物之大致,无不备具,故阅是书,则美国未辟以前,既辟以后,数十年中之事,皆了如指掌,则谓之美国开国史略亦可。”(注:黎汝谦:《华盛顿全传·凡例》,《时务报》第1册。 )至于蔡锡通翻译的《美国合邦盟约》,就是1797年9月17日制定的《美国宪法》, 陈季同翻译的《拿布伦立国律》、《拿布伦齐家律》,则可能是《法国宪法》和《法国民法典》。因此,他们的翻译活动不仅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而且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即使是那些单纯翻译介绍国际形势、西方各国制造技术和科学知识的活动也同样具有其独特的意义。戊戌维新运动既是一场政治改革运动,也是一场民族救亡运动,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近代中国,几乎所有的政治改革都是在内忧特别是外患的刺激下发生的,而中国人所能够认识到当时的外患,除了列强的侵略外,开眼看世界、走向世界,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出使人员长期驻外,对国际形势有相当的了解,他们将有关文章翻译介绍给国人,这无论对开启民智还是促进民族觉醒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些翻译介绍外国制造技术、科学知识的宣传活动表面看来与维新运动了不相关,事实上却密不可分,因为近代思想启蒙不仅包括宣传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同时也包括传播科学知识,反对封建迷信。因此,对驻外及出使归国人员,不论他们在认识水平上有多大差距,只要在当时介绍了域外知识、传播了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就应该予以肯定。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即当时的驻外及出使归国人员,究竟是维新派还是洋务派。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维新派和洋务派的区别。一般说来,维新派主张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而洋务派则反对这种改革;维新派主张民主自由,号召冲决封建的网罗,而洋务派则视此若洪水猛兽。双方在对待西艺的态度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准此,我们似乎可以说,黄遵宪、宋育仁等人应属维新派,张荫桓、徐建寅等人可被视为洋务派。至于其他人,则很难说是维新派还是洋务派。比如邹代钧,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向国内介绍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学者,他积极参加了维新运动,变法失败后,他更是痛惜不已。但是在湖南办理新政期间,他和谭嗣同、熊希龄等矛盾重重,认为谭、熊太“猖狓”(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2756页。),他尤其不同意康、梁的变法措施, 甚至将变法的失败归因于康、梁的激进,说:“康、梁之罪甚大,旧党恶之,尚是否各半,其有害于新政,则非浅鲜,千载一时,为此辈所败,言之痛恨。”(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1页。)又比如早年随薛福成出使的张美翊,当时一面为薛福成整理遗稿,一面积极参与维新运动。但他与邹代钧相仿,主张采取缓进政策,他说:“吾辈此时宜后名而先实,一切务从平地筑起,徒以空言号召天下,断无益处,且有流弊。平时立论,务平正易行,不必过激,朋友相遇,务彼此相助,互为规劝。”(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1760页。)政变发生后, 他对军机四章京的被深表婉惜,说:“新政四人,皆伏重刑,为之一哭。”并表示:“吾辈总以慎言慎事为要……处此时势,惟须尽我可为之事,如劝学明农,奖掖后进,开通民智,则教一人得一人之益,教一乡得一乡之益,至出位之谋,如变法、保国与守旧不死者为仇,似不值得。”(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第1762页。)他虽称梁启超为“良金美玉”,国之“通才”,但对康有为却无好感,说“南海之氛甚恶”(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1758页。), “康所为诸事皆不惬人意”(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1762 页。),预言其变法“不终”。在听说光绪皇帝被禁锢后,他甚至将祸源归因于“变政党”,说:“变政党之罪,其可恕乎?”(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4页。)
邹、张二人和康、梁的区别不在于变不变法,也不在于变什么,而在于如何变。他们不同意康、梁的托古改制变法理论,不同意康、梁在变法时与守旧派针锋相对,而主张采取更为稳妥的、为各方面均能接受的方式进行,也正因此,他们将变法的失败归于康、梁的激进。当时与邹、张二人类似的驻外和出使归国人员不是少数。他们不属“康党”,也非洋务派,他们是一批曾经到过国外,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在当时积极参加了维新运动,为推动运动的发展,促进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