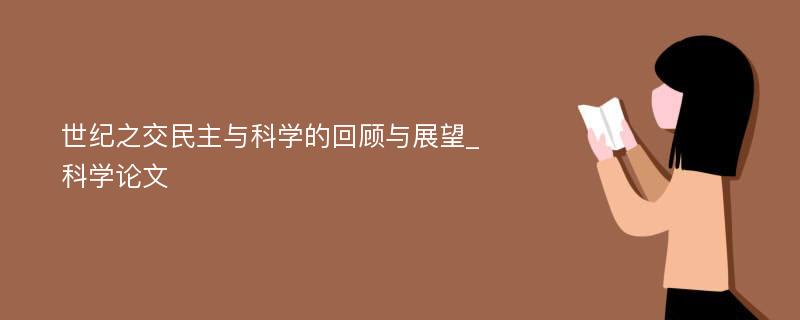
世纪之交对民主与科学的回顾和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民主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主与科学是完全的舶来品,在我们固有的传统中既无此种概念也缺乏其文化上的基因。历史上的“民本”思想,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注:《孟子·尽心下》。),“民可载舟,亦可复舟”(注:《纲鉴合编》卷廿《唐纪·太宗皇帝》。)之类,常为固守传统的人士所乐于引用,以为近代西方的“民主”观念,我国古已有之。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者有本质的不同;至于科学,更是近代西方的产物,中国古代,只有实用的技术,如营造、冶铸、器械、园艺之类,即使是这些实用技术,在中国古代也被认为是术数小道甚至是奇技淫巧,不登大雅之堂,为士君子所不齿。中国的传统思想、价值观念及其政治经济制度,如果没有遭遇到近代西方列强的短兵相接,也许还可以在自我陶醉的梦境中继续昏睡两三百年而无从改变。但是历史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强邻胁迫的现实压力已使国家陷于积贫积弱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于是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内部的开明派,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其间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摸索,终于发现:西方之所强、中国之所弱,最终的根据,乃在于民主与科学之有无。于是他们万分虔诚地邀请“德先生”与“赛先生”来中国。然而“意志可以移山,却难以动摇传统”(注:引自《胡适口述自传》第八章唐德刚注引蒋延黼先生语)。对于“德、赛”两先生,传统社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极端顽强的抵制,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之间,实即民主与专制,科学与愚昧之间一直进行着殊死搏斗,这种斗争直至目前才显露出胜负的端倪。
一、民主与科学和近现代中国
传统的中国历来自认为世界的中心。从周秦以来,对于中国以外的地区,总看成是文化落后的蛮荒之地,其文明发展程度,总是与中国的京城的距离成反比。在这样一种近于迷信的成见中,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与士大夫保持了一种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意识与自恋情结。当然,这种意识的产生决非毫无根据,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东临大海,西负高山,北地荒寒,南方瘴湿,遂认为自己处于天下之中,是首善之区。加以数千年间,周边地区的确没有产生从文化优势上能向中国挑战的民族。西北方强悍的民族虽曾屡次入侵,然而,其文化均非中土之比;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虽然与汉文化形成颉顽之势,并很大程度影响、丰富了汉文化,但历史上的印度毕竟从未构成对中国实际的压力与威胁。然而西方殖民者的东侵,使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支强大的势力决非当日匈奴可比,称之为“夷”,呼之为“奴”,讲求觐见之朝仪、礼节,把贸易说成“纳贡”,种种由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下派生出来的政治面子的游戏,对于实实在在的威胁,终究无济于事,反而形成历史的笑柄。直到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最终彻底失败,这种“世界中心”的地位终于在一部分士大夫之中产生动摇,不久,也从“天朝”的迷梦中惊醒了。
“思想解放”是近年来较为时髦的概念,意指从固有的不合时宜的陈旧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我想,鸦片战争失败所造成的冲击、引发观念的改变,应当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轮思想大解放,更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因为它完全打破了“中国是世界中心”这一延续数千年的迷信,第一次把眼光投注于中国之外的广大地区,第一次认识到大洋彼岸、流沙之西也存在着与我们一样甚至超越于我们的文明。尽管这种承认是痛苦的,但却不能不面对,因而一切自欺欺人的伎俩均无意义了。
这种情势促成了一系列由浅入深的变革的进程,自然也造成了保守力量对变革的抵制与反对。最初的变革仅仅是在器物层面,当时的改革派,简单以为,西方之强大,仅在“船坚炮利”,只要取彼之长,即可置其于死地,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注:魏源《海国图志叙》。),沿着这一思路,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洋务运动”,在物质经济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出现短暂的虚假繁荣,所谓“同治中兴”。然而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肥皂泡破灭了。现实迫使人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与思考。于是开始把变革的目光投注于制度层面,鼓吹变法、维新,直至革命,一时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章太炎等风云际会,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的反复较量与奋斗牺牲,最终革命派取得了胜利,推翻了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然而举国欢腾之后,人们很快就发现,制度的变革,并未改变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使中国富强起来。所以孙中山先生临死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注:孙中山《总理遗嘱》。)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何处呢?到了“五四”前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发起思想文化层面的大变革,终于找准了病根,也开对了药方。他们对一切旧的思想文化、风俗传统发起猛烈攻击,认为这些均是阻碍中国富强进步的拦路虎。他们的攻击不免过激,但在当时却是无可厚非的。当一只“老虎”正在吃人时,首先的任务是将它击毙而决不会想到老虎的一身有多少宝贝。它身上的宝贝是以后加以利用的问题。他们对中国国民性作了最深入犀利的批判,他们把遮盖在外部的诸如“礼、义、廉、耻”、勤劳、勇敢、甚至“精神文明”的美丽外衣一起剥去,暴露出大多数国民灵魂深处的“奴隶劣根性”,不知有自我,不知有自由,只善作顺民,是一切专制暴君达其目的之最好的工具。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国民,如不加以改造,中国决无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他们把准了脉搏,找对了病根,自然也就开出了有效的“药方”,这付药方仅两味“药”:民主与科学。
“五四”时期的先烈、学者们提出民主与科学作为救国之道,决非向壁虚造,我们从前述的历史过程中可知,这是符合逻辑的发展,是鸦片战争以来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由于民主与科学观念的流布,“五四”前后二十年间,思想活跃,思潮迭起,多元并存,蔚为大观。这种形势当然也造就了一大批有独立精神的文化人,他们的思想、学术,人格,个性,形成了一道耀目的风景线,昭示于未来。
然而,回顾“五四”以来社会实践,我们也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吸取,自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王朝以后,名义上建立了所谓“民国”,实际上,接踵而来的是连续几个反人民的政权,如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中间还闹了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的丑剧。在这些政权的统治之下,对内专制独裁,对外妥协屈辱,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理想完全落空。只有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人民的利益,力求实现民主,保障人权,他们奋起向反动政权抗争,得到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最终打跨了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新中国——真正的人民共和国。
当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对中国人民而言,这是获得了实现民主、发展科学的空前良好的契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代伟人毛泽东,也未能把握好这个机会。他并未把“德、赛”两先生完全“解放”出来,而是企图利用新政权的制度优势,以超越民主与科学的方式,把国家引上现代化富强之路。实践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
对民主与科学的真正解禁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近代以来“第二轮”思想解放运动所促成的一系列改革开放举措,同时由于邓小平同志的政治设计,中国才开始起飞,走上富裕之路。二十年间,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也得到了弘扬。
二、民主与科学的文化意义
在1999年“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之际,无论是政界,还是理论学术界,以及青年学子,均普遍对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加以充分肯定。人们认识到,对于社会发展变革而言,固然离不开政治、经济层面的改造,但那只是“硬件”内容,更重要的是,要使社会变革更加彻底、充分实现,那还是有待于“软件”——思想文化层面的改造。当然这种改造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并非主观任意可以决定的。一般而论,总是先产生对固有状况某种程度的怀疑,也即有了一定的觉醒,然后通过先觉者作舆论的鼓吹,逐渐造成声势,蔚成所谓“思想解放”的运动,接着便产生变革现实的行动。这种行动多由经济、政治层面变革在前,思想文化层面变革在后,待思想文化变革完成,才算是社会变革的真正的完成。我们以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一共有三次思想文化层面的变革:“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是属于正面意义的变革,其历史积极作用与影响,至今犹存;而毛泽东同志搞“文革”,主观上也是进行思想文化上的社会变革,但由于背离了民主与科学,而其前期的经济、政治变革均误入歧途,所以起了巨大的负面作用,将在历史上留下相当深远的消极影响;至于第三次思想文化层面的变革,当前正在推进发展之中。而这次变革完全属于民主与科学的复归,因此,这次变革完成之日也即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对这三次变革,从哲学上观察,乃是完成了黑格尔所说的“正、反、合”之辩证运动的一个大圆圈。令人不无感叹的是,这个圆圈的复归耗去了中国人民近整整一个世纪的时光。
不过尽管今天举国上下对民主与科学在总体上有了较一致的认同,但对其具体内涵仍有不少歧见与不同理解。甚至可以说,从“五四”先贤邀请“德、赛”两先生来中国时起,就一直存在着理解上的分歧。比如说“民主”,这本来在西方就有多方面的含义,有时它是指一种政治制度,有时则表示为一种生活方式,有时也被说成是人们追求自由、平等、宽容这些目标的一种理念。当它被接纳到中国来之后,由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下政治境遇所构成的“国情”的作用,自然就产生“见仁见智”的结果,我们翻阅99新版的《辞海》,“民主”条目下,就有一些人们一直使用的意义,如“庶民之主宰”,与“专政”相对的概念,与“专制”相对的概念,还有一种与“集中”相对的概念等等。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就看使用在何处,由于通常广泛的多义性的使用,确实使我们对“民主”这一概念的普遍意义产生了模糊。如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在广大民众和干部中,一提起民主,马上就与集中联系到一起,意思是民主好象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放任行为,是一个必须以集中来加以引导制约的东西,否则就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坏结果;又如讲“发扬民主”往往与“加强法制”成为一个组合,这本来是对两者作同样强调,是十分正确的;但许多人却对之作了错误的理解,仅仅将民主作为法制的手段,法制成了唯一目的。科学也如此,甚至更有过之。“五四”先贤对科学均极为虔诚,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无不把科学视为神圣,以为科学万能,可能解决一切社会、人生问题,以至形成了一种“科学的宗教”。这在中国传统社会充斥愚昧、迷信、落后的情况下自有其理由。然而这种对科学的极度崇拜实际也成了一种“迷信”,开了唯科学主义的先河,最终产生负面的影响。二十年代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虽以科学派的胜利告终,但回顾历史的发展,实在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内容。比如人生价值问题,心灵问题,终极关怀问题,伦理道德问题等等均非单纯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在这些方面,也许“玄学派”看得更深一些,至少说他们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除了这种对科学的偏激态度外,更为普遍的是,长期以来对之作实用主义的理解,也即是:“有用”就是科学,无用就不被承认为科学,而这个“用”,仅仅局限于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尽管这种“利益”后来改换成为“社会效益”,而产生的消极后果,则是同样的。在强调现实利益、效益的思想指导下,往往急功近利,被看重的仍旧是实用的技术,所谓“科技”,重心在“技”,而科学的精神却被消解了,因为科学精神并不能立竿见影的创造出多少看得见的效益来。以致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究竟是不是科学始终是不断受到质疑的问题。
那么,什么才是对民主与科学的较准确的理解?其文化意义又当如何呢?我们以为,这至少可以从纵与横两方面加以说明。从纵向而言,民主与科学实际上是社会迈向工业文明时期在宏观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特征。就此点而论,这是历史决定论的,是普遍规律。换言之,一切进入工业文明的国家、地区均不能拒绝民主与科学,而一切处于农业文明的国家与地区则必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与科学。由于这种分歧,我们便可以明了,近百年来我国追求民主与科学之艰难,传统社会抵制之顽强,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农业文明的劣根性。有鉴于此,我们面对工业化国家之文明成果时,不仅应虚心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应以谨慎求实的态度,采纳其民主的体制,对其政治运作尤其不可轻率斥之为“假民主”之类,因为民主与科学固是工业文明的“专利品”,并不以我们的好恶而改变的。站在前工业社会的立场上,对工业社会的“民主”所发出的责难往往带有封建专制主义偏见的色彩,不管如何“振振有词”,委之于“国情”需要,其实均不能经受历史的考验。
从横的方面说,即是透彻把握了解民主与科学的本质,以及由此本质衍生创造出来的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与氛围。对于民主概念尽管东、西方众说纷纭,而且将其作为一种理论、学术的研讨对象也许可以长期研究下去,但其本质的内容应是毫无疑义的。它绝对是“专制”的对立面。它是为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所乐于接受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社会成员有说话的机会,有听到一切言论和消息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选择生活途径的机会,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与形式有效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并监督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由这种本质衍生出来的必然是一个趋向于自由、平等、宽容,互相尊重,保障人权,珍视个体生命与人的价值以及丰富多元的文化环境。当然,我们在讨论民主时,不能忘记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其基本点有两条:一是我们的民主必须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之上;二是让上述民主的权利真正能落实到社会大多数人特别是劳动人民头上。若从现代西方国家实行民主仍存在弊端视之,与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相比肯定尚未臻至善之境。但就当前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实即现代化)过渡阶段而论,民主仍是政治制度的最佳选择,而且是无法绕开的必由之路。至于科学,其本质乃在于求真。它是人类通过理性来探求、反映世界的真实状况,揭示其内在的规律。伴随这种探求,人类的视野不断开阔,知识不断丰富,然后通过技术的转化成为有实用价值的成果,最终造福于人类。我们承认,对人类而言,前述“技术转化”的过程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并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真正的科学应是“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的,它纯粹是“精神的自我扩张”,其本身并不应由任何利益与权势所驱动,也不考虑其实用价值的。由于科学的这种独立自足的特性,故使科学追求显现出崇高的品质。拉普拉斯写《天体运行论》时可以不接受拿破仑的“把上帝写进书里”的劝告;陈景润在六平米的破屋里用手电躲在被子里照样搞他的《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均是这崇高的展现。中国历史偏重实用的文化传统(当然也是农业文明的特征)对科学的损害是巨大的,对任何事物总是将有用、无用置于首位,而将真、伪放在其次,即如陈景润的数论研究,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很难说能产生什么实际效益。因而曾遭到不少国人的怀疑与嘲笑,甚至批判。陈之所以后来受到礼遇,大概主要还是因为外国人的发现并赞好的缘故,这是极为狭隘的观念。从科学的求真的本质出发,也可衍生出一系列科学精神的内容:如主张科学的自由探索,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承认科学是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不承认终极真理;对不同意见采取宽容态度,不迷信权威;提倡怀疑,批判;倡导科学无国界等等。这些才是科学的活的生命。我们只有做到对科学精神的坚持与尊重,才算是真正的尊重科学。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与民主实为同一文化“基因”,是一对孪生兄弟。我们的社会如不能接纳真正意义的民主与科学,以及伴之而生的那种文化环境与氛围,实现现代化是决无可能的,或者只是由鼓吹而造成一种现代化的幻觉——虚拟现代化而已。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些担心均成为多余了。
三、世纪之交对民主与科学的展望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路线以来至新的世纪之交,二十年的发展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二十年里,我们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民主与科学在我国大地如何重新扎根、并一步一步成长的,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地相信,在新的世纪里,民主与科学将在我国有更长足的发展进步。这决非凭空臆测。而是有着下列坚实的理由。
首先,从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国连续两代领导集体均十分关注与重视民主与科学的建设与发展。他们不仅具有发扬民主,尊重科学的坚定信念,而且由于他们丰富的政治实践与领导才能,故能够既稳妥而又有成效地推动我国民主化进程与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扬。在这方面他们的确表现了高超地政治艺术。比如邓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不久,就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他在大会上的发言提出一系列精辟的观点,如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以及重视人才问题等等。(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5-100页。)1986年在会见李政道时明确表示: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3-184页。)他对科学事业的这种高度重视使中国大地迎来科学的春天。而小平同志有关“民主”的议论与思考,在其有生之年从未中止过。他多次强调: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而发扬民主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与关键所在。(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而江泽民同志在这方面忠实继承了邓小平同志,采取了许多具体步骤使群众对民主与科学的要求一步步得到落实。
其次,广大群众对民主与科学的普遍要求是一个重要保证。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有了巨大变化,这必然使之产生更多新的政治、文化需求。可以认为,在这些方面群众提出的要求愈高,则说明政府取得的成就愈大。这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当民众对政府一旦没有了要求,则要么说明了政府的无能与落伍,要么反映了民众的彻底失望。当前我们看到的正是群众对民主与科学文化的日益迫切要求,而国家领导人又是能够顺应并满足群众这种要求的改革家,所以可以认为,对德、赛两先生而言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机。
第三,近百年来,民主与科学在我国的命运,为我们提供了正反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这是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换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前且不去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十年间,凡是发扬民主,提倡科学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事业就兴旺,现代化进程就加速;而一旦偏离民主,不尊重科学,事业就遭到挫折,人民就经受磨难;实践证明,当一个社会,从上到下均缺乏民主与科学意识时,不需多久,全社会就会陷入毫无理性的疯狂状态。如“大跃进”与“文革”时代就是如此。这些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已成为中国人民值得永久记忆的宝贵精神财富。这对于我们走向未来的任何时刻坚持民主与科学的方向与理念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第四,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宽一点,更可以看到,民主与科学已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正如我们所断言: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形势的主流,而这必须依靠民主与科学才能实现。这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加以说明:一方面民主与科学的体制可以保障国际社会和谐安宁与经济文化的繁荣;从历史上看,一切专制独裁的国家、政府均或多或少地给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当今世界上一些实行专制的国家,自我封闭的国家,不思改革的国家,总是搞得民生凋蔽,发展迟缓,看不到前途,甚至在这些国家中,还有的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那就更加危险,等于“自杀”。“放眼世界,胸怀全球”的结果,更加坚定了我们对民主与科学的信念。
第五,上面虽讲了若干理由,然而最重要的理由还是在于: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民主与科学成为唯一合理的选择。缺乏了这一理由,也许以上理由尽管全都存在却完全不能发挥作用。计划经济时代是很难生长出民主与科学的因素的。因为“计划”的根本特点总是少数人代替多数人决策,最终也就是由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即使这些少数人是真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陷于主观盲目性,自然就谈不上民主,也谈不上科学;而市场经济则完全不同,在市场中,人人均要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决策合理,发展顺利,决策失误,咎由自取。很显然这种体制客观地培育人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风险意识。具有这些素质的民众乃是推进民主政治与科学精神的的坚实的基础与天然的“选民”。
从以上这些理由,我们可以坚信: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一定会在中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
标签:科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邓小平文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