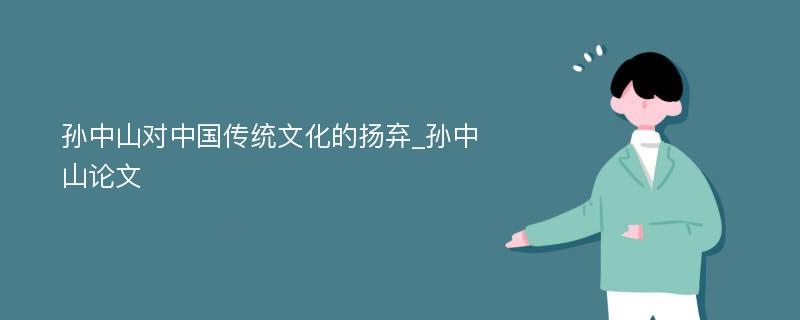
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文化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主要表现在对“固有智能”、“固有道德”、“民本思想”以及“大同”思想的改造和吸收,凡利国、利民者则扬之,否则就弃之,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
关键词 孙中山 中国传统文化 扬弃
自西方文化涌入中国以来,如何对待有过辉煌的历史,却又沉疴积痿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人们深深思考着的问题。探讨孙中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态度,对我们评估传统文化,构建未来文化不无借鉴意义。
孙中山所使用“文化”一词的涵义十分广泛,在1895年以前,基本上属于“文治”、“以文教化”这一类,后来他亦在此意义上使用过。1922年他在桂林学界欢迎会上说:自秦汉以后,“政府一天专制一天,不是焚书坑儒,便是文字狱,想种种办法去束缚人民的思想,人们那里能够自由去求文化的进步呢?”①在此,“文化”一词的含义显然是指“文化——精神论”。1924年他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则把我们过去“固有的知识”、“固有的能力”都看作是我们“很好的根底和文化”,认为要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必先恢复我们民族的这些“固有精神”②。从“文化”的概念出发,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对“固有智能”的肯定
所谓“固有智能”,其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智”,即“固有的知识”,“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种政治哲学”③;二是指“能”,即“固有的能力”,也就是指古人曾所具有的非凡的才能,这又突出地体现在他们所创造的辉煌的古代文明上。孙中山认为,要恢复我们民族的精神和地位,就必须恢复我们民族的那种“固有知识”和“固有的能力”,也就是说必须对“固有智能”加以肯定。
那么,究竟孙中山对“固有智能”是怎样进行肯定的呢?
首先,看其对“固有知识”的肯定。传统文化中的“修齐治平”之道,即孙中山所说的“固有知识”或“政治哲学”,其根本点是修身,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④。因此,儒家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⑤”。在孔子看来,修身就要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⑥。从而修成一种比较独立的“人格”。孟子则从“性本善”,即从人性论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一个人修成完善人格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认为人只要通过对本性“善”的发扬,“人皆可以为尧舜”⑦。传统文化中那种通过修身而养成一种初步独立的“人格”,把它推到“治国平天下”就是一种“国格”,“国格”概念实际上便是一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传统文化中的这种“人格”和“国格”观念,是孙中山吸取的重要思想资料。他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讲演中,不惮其烦地对中国古代的“固有知识”进行肯定,认为它是中国文化的“真谛”。他说:“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畴,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象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把一个个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⑧。因此,孙中山强调国人都应从修身做起,磨炼意志,砥砺品德增进知识,以达治国平天下,即建成真民国之目的。
孙中山强调每个人都应努力去修身,但他认为,在当时,修身对于革命党人、军人、学生尤为重要。因而他对这三者的修身尤为重视,为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尽相同的修身要求。对于革命党员来说,他认为,修身首先必“正心”,以树立起高尚的人格。若不“正心”,党员只“存心做官发财”,那党员的人格便非常卑劣,这就必然会丧失人心,而“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因此,孙中山一再向党员郑重指出:党员一定要“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⑨。对军人的修身,孙中山认为,关键是要修“智、仁、勇”军人之精神。以使自己能“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舍生以救国”⑩。对于学生,孙中山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树立救国大志。因为学生求取学问应该是为了“拿学问来救国”,“图国家之富强”。学生如果不立大志,那么“十年窗下任你读书几许卷,终亦无补于国家,只一书锥而已”(11)。因此,孙中山要求学生一定得“学问志愿两者并行”,以修成大器,服务于国家。这样,就使孙中山所提倡的修身与儒家的修身,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目的上都有了根本的不同。
其次,看其对“固有能力”的肯定。孙中山说:“我们除了知识外,还有固有的能力,现在中国人看见了外国的机器发达,科学昌明,中国人现在的能力当然不及外国人,但是在几千年前,中国人的能力是怎么样呢?从前中国人的能力还要比外国人大得多”(12)。“在心性方面”,中国古时的考试制度,“最为平允,为泰西各国所无”(13);中国古时的监察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绩”(14);中国的文字,其历史已“逾五千年”(16);在物质文明的方面,孙中山说:“自古制器尚象,开物成务,中国实在各国之先。而创作之物,大有助于世界文明之进步者,不一而足”(17)。他曾以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磁器、丝、茶等为例,反复证明了古人具有卓越的创造能力。认为“如果从前的中国人没有能力”,“便不能发明”这些东西。“可见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中国人固有的能力还是高过外国人”(18)。
我们知道,孙中山并不是一个崇古主义者,他对“固有智能”的肯定,是为了恢复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恢复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地位,是服务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的。他在对我们民族的“固有智能”进行肯定时,也看到了我们民族的不足,认为当时外国机器发达,科学昌明,而中国“农工事业,犹赖人力以生产”,因而指出要“用我们的本能”,去“学外国人的长处”(19)。这就使他把对“固有智能”的肯定与向西方学习相结合,并把他自己与那些夜郎自大者从根本上区别开来。
二 对“固有道德”的扬弃
“固有道德”即旧道德,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孙中山所说的固有道德,主要是指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说:“讲到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20)。这些伦理准则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经过长期的修补、凝固,成为人们安身立命、处世待人和追求自身完善的圭臬。一方面,由于它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对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曾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它对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亦起过帮凶的作用。因此,孙中山认为,对这些旧道德,“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21)。
忠,是传统道德里一个重要的德目,它所包涵的内容虽多,但核心却只有一个,即指“忠于君”。《论语》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忠,以及“临之以在则敬,孝慈则忠”的忠,其义都是指忠君之道。针对这种“忠”,孙中山说:“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所谓忠君的;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当然“不忠于君”,但“还是要尽忠”,“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个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22)。这样传统道德里以忠君为主要内涵的忠,经孙中山改造,成为了一种以“忠于国”、“忠于民”为基本内容的新型政治道德观。
孙中山论孝,是把它同忠字联系来加以论述的。他阐述道:“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所谓“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便是一死”(23)。就是说,国民能为国、为民“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才算是“把忠孝二字讲到了极点”,这样国家便能富强起来。因此,孙中山在此所讲的孝,其含义显然是等同于“忠于国”、“忠于民”的忠。
关于“仁爱”,孙中山说:“中国古来学者,言仁者不一而足”(24)。古时言仁者虽多,但精细研究的首推孔子。到孔子时期,仁才指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并把它与“爱人”联系起来,提出“泛爱众,而亲仁”,“仁者爱人也”(25)。孔子的这样仁爱思想后来被孟子继承并加以了发挥。但孔孟的仁爱是有等级、亲疏之分的。墨子则提倡“爱无差等”的“兼爱”。对于中国古代丰富的仁爱思想,孙中山说:“据余之所见,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博爱之谓仁’,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与夫爱父母妻子者有别”(26)。孙中山在此所说的仁爱,即“公爱”,显然更接近于墨子的“兼爱”。但他认为,传统的伦理思想里虽有“公爱”之思想,而无“公爱”之“实行”,只是“徒托空言”。因而那只能算是“救人之仁”和“救世之仁”,即只能算是“乐善好施”的“慈善家之仁”和“救济众生”的“宗教家之仁”。因此,他要提倡第三种“公爱之仁”,即“救国之仁”。“何谓救国?即志士爱国之仁,与宗教家、慈善家同其心术,而异其目的,专为国家出死力。牺牲生命,在所不计”(27)。但要达到这种“仁”,“须有一定之主义”,只有心中有了一定的主义后,“始可以成仁,始可以成功”。“主义维何?三民主义是也”(28)。在他看来,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等“革命先烈,前仆后起,视死如归,即为主义而牺牲”的楷模,是“救国之仁”的典范。这就使传统论理中的仁爱思想,被孙中山改造成为近代中国广大仁人志士为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关于“信义”,孙中山说:“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信用”(29)。孙中山在此把传统道德里的“信义”运用于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中,一方面体现了他对旧道德的改造,但在旧道德里,信往往与忠联在一起,义常与礼搭挡,这就需要我们去细心地分析、选择。而孙中山对此却未能论及,这就使其对“信义”的改造,难免显得过于粗糙。
关于“和平”,孙中山说:“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廉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30)。又说,中国与印度的交通自东汉以来就已经开始,“彼此以和平相往来”,“互相钦敬,互相爱慕”,“更可以证明中国的民族性是和平的,不是空言”(31)。从孙中山所论及的和平内涵来看,它不仅是指中国人的一种天性,或说民族性,或固有的民族精神;同时也是指一种国与国相处的基本准则。这自然是传统德目里“和平”的内涵所覆盖不了的。《中庸》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32)。就是说一个人如能使自己常保持“中和”的境地,就能随时通达而左右逢源,而要达此善境,则必须拥有“平直”的心境,在日常行为中则必须“温良恭俭让。”这种要求人们在修身养性时所应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所应遵循的一种行为准则,与孙中山所论及的和平,显然是具有很大区别的。
三 对“民本思想”的吸收
孙中山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吸收,在十九世纪末,主要侧重于对其“富民”、“保民”思想的吸收,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说:“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脉”,“养民”之根基,“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量,山泽之利未尽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难乎!”因此,他力劝统治者“急设农里”以劝其民“垦荒”、“修水利”,认为这样才能“养民”、“富民”(33)。两千多年前的荀子在《富国》中说:“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国家自富。商鞅的看法则更具见地,认为富国有赖于民开发地利,并尽力于农。他说:“为国之数,务在垦草”,“民泽毕农则国富”(34)。当然,孙中山在重“农桑之大政”时,亦提倡大兴“格致”之学,认为只有讲物理、化学,广用机器、电力,才能以“省财力”,并认为国家还必须有“保商之善法”,使“货能畅其流”,这样才能“有以裕民”(35),而古代的先哲自然是提不出这种重商主张的。
如果说,十九世纪末孙中山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吸收、利用,还未从根本上跳出君民关系的范畴,并试图通过统治阶级来谋求民富国强之路,那么,到了二十世纪以后,便很快否定了君的存在,放弃了对统治阶级的任何妄想,而把古代的民本迅速发展成为近代的民权。
二十世纪初,民族危亡的加深,激起有识之士对传统文化作更为深刻的反思,究竟要不要以民取代君,实行民主共和,成为当时一切关心祖国命运的人所探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自由、平等为武器,以实现民主共和为目标,对传统的君权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他们庄严的宣称,“二十世纪之天地,盖断不容专制余威稍留其迹”。君主必须废弃,专制政治必须彻底扫除,“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36)。尽管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对专制文化的批判,对民主共和的讴歌,在某些方面未免有些幼稚,但他们对存在几千年之久的“君权”的否定,无疑是对传统文化改造的一次重大突破,尔后皇冠的坠落,则是这种否定发展的必然结果。孙中山本人也在这种对皇权的否定以及对“民”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而把古代的“民本”发展成为近代的“民权”,具体表现为“民有、民治、民享”思想的提出。
在民有方面,孙中山把四万万人看做是民国的主人。他说,新成立的“民国以四万万人为主人”,“主权在民,民国之通义”(37)。并庄严宣告:“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族所可独占”(38);国家,“非一人之国家,乃我人民之国家”(39);国民,“乃民国之天子”(40)。在民治方面,孙中山说:“从前之天下,在专制时代则以官僚、武人治之,本总理则谓人人皆应有治之之责”,“故余主张以民治天下”(41)。“共和国家,重在民治”(42)。既然“共和国为人民之国,”那么,一切就应“合全国人民为之”(43)。否则,民治就是空话。在民享方面,孙中山指出:“天下既为人人所共有,则天下之利权自当为天下人民所共享”(44)。“国内的事情,要人民去管理,国内的幸福,也是人民来享受”(45)。
孙中山这种以民有、民治、民享为特征的民权思想,固然大量吸收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内涵,也受传统民本思想中那种朴素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但是,孙中山的民权与古代的民本自然有着质的不同,古代的民本强调的是君民关系的处理,以吸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教训,因而无论古时的先哲发出怎样震聋发聩的宏论,都只仅从怎样有利于君的统治出发,道出了民与君的利害关系,而不可能把民摆到国家主人的地位。孙中山则把国民奉为天子,并主张制订法律规章,以从根本上保证“国民居于尊严之地位”。同时,古代的重民是为了保君,重民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孙中山则要从根本上变更国体和政体,用三民主义去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
四 对“大同”思想的因袭
孙中山对大同思想的因袭,首先体现在他不仅把大同世界看作是其三民主义之最后归宿,而且亦认为它是“人类进化之目的”。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46)。在孙中山看来,他的三民主义之归宿是民生主义,而民生主义之目的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而他的民生,不仅包括中国的民生,也包括全世界的民生,因而他说:民生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47)。孙中山认为,人类进化之最终目的也是在实现大同主义。“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那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48)。并说:“倘进化前途无所障碍,只有进而无退,则世界大同,可指日而待”(49)。
其次,体现在孙中山受古代“均贫富”这一类大同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受太平天国大同主义思想的影响。孔子曾说:“不患寡而患不均”(50)。孙中山说:“我人所抱之宗旨,不过平其不平,使不平者底于平而已矣”(51)。而他的“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地”(52),与太平天国所规定的“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是有相通之处的(53);他的“有事同干、有福同享,一国安宁富厚,则个人亦安宁富厚”(54),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太平天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思想的因袭。但孙中山不主张“均分富人之资财”。认为“主张均分富人之资财,表面似合均产之旨,实则一时之均,而非永久之均也”。因此认为“欲永弭贫富之阶级,”必须“舍此而另作他图”(55)。
传统的大同思想,虽然反映了被剥削被压迫者的美好愿望,但毕竟是小生产者的乌托邦,因而不论古代的思想家把大同世界描绘得怎样美好动人,但从没有人找到通往大同的路径。孙中山虽然因袭了大同主义的思想,但却并未把它当作一种乌托邦的幻想,而是把大同思想与他的三民主义相结合,想通过对其三民主义的实现,最终建立一个使“愚者明之,弱者强之,苦者乐之,”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大同”社会。
他在《民权主义第一讲》中说:“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56)。因而他从“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出发,力排少数人垄断政治之弊害,高举平等的旗帜,揭露批判欧美代议制度之弊端,认为“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57)。因此,他坚决反对完全仿效欧美,指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58),1924年,他明确宣布“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表示坚决抛弃西方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以图建立“代表全体平民利益”的政府(59)。他认为在中国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即可由“小康”而至“大同”。
如前如述,孙中山把“大同世界”看成是其民生主义的归宿。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提出了“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认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为救济工人,“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为“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国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60)。这就使古老的大同思想具有了崭新的时代内容。
纵观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扬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始终是围绕着是否有利于“国”、“民”这个轴心来进行的,凡利国、利民者则扬之,否则,则坚决弃之。其实,自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对于中国本位文化取舍的探讨,都是围绕着如何有利于国家、人民这个主题来进行的,但由于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和重新认识与思想家本人的教养、地位密切相关,因而往往同时代的人对传统文化的取舍和归宿不同。在十九世纪末曾为中国文化的变革英勇斗争的康有为和严复,最终走向了传统文化的复归。而孙中山则能始终保持一种开放型和进取型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显然更有利于使传统文化为现实斗争服务。
当然,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亦存在某些不足。主要是他对旧文化的扬弃缺乏足够理性的、系统的剖析,以及对某些封建性杂质批判不够。如他在对“固有智能”进行肯定时,把传统文化中那种落后的家庭、宗族观念也一同肯定下来;他在改造“固有道德”时,未能对旧道德中的糟粕予以坚决批判。这种不足,不仅反映出孙中山文化观上的某些薄弱环节,而且也透视出他那一代人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所表现出的某些矛盾心理。因此,我们在看到这种缺限与不足时,主要应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政治文化氛围中来加以说明。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苛求前人,也才能使其得到合理的科学的解释。
注释:
①(16)(10)(24)(26)(27)(28)(48)(17)依次为《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68-69、179-180、16-23、22、22-24、24、36与196、191页。
②③⑧(12)(14)(18)(19)(20)(21)(22)(23)(24)(30)(46)(47)(56)(59)(60)依次为《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49-251、247、250、353、250-251、252、247、243、244、246、394、355、262、120、121-121页。
(54)《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349页。
④⑤《大学》。
⑥《论语·雍也》、《论语·颜渊》。
⑦《孟子·告子上》。
⑨《孙中山选集》下第463页。
(11)(38)(41)(44)(45)依次为《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57-560、628、629、174页。
(42)(43)为《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213、345页。
(37)(40)(39)(49)为《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319、349、95页。
(15)(51)(55)为《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33、509、508页。
(13)(33)(35)(37)(57)《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78-282、10-15、12-14、213、327-328页。
(58)《孙中山全集》第六卷56、第一卷第328页。
(25)(26)《论语·学而第一》。
(31)《国父思想学说精义录》第632页。
(32)《中庸》。
(34)《商君书·算地》、《商君书·靳令》。
(36)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50)《论语·季氏篇》。
(53)《洪秀全文集》,第1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