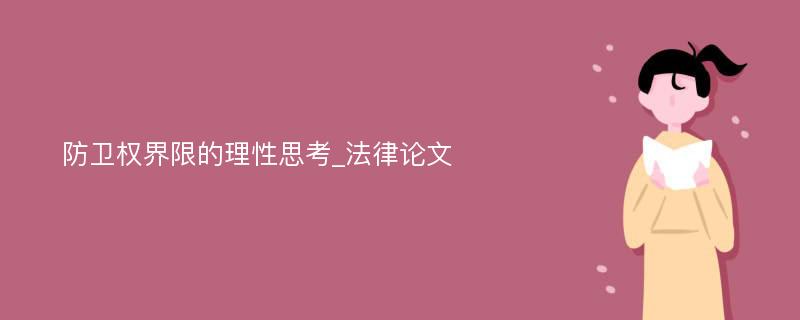
防卫权限度的理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权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后的新刑法典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由此开创了我国无限防卫权刑事立法化的先河。这一规定的立法用意,主要是为了纠正过去司法实践在处理防卫过当案件时普遍存在的一种偏严的倾向,鼓励公民更好地利用防卫权,以保护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可是,防卫限度的正确把握是能够在立法上毕其功于一役,得到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吗?无限防卫权的合法化,对于我国刚刚起步的法治建设,究竟是利耶?弊耶?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刑法学界。
一、防卫权的嬗变
防卫权由人的防卫本能发展演变而来,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历史渊源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
根据人类社会发展史可知,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因而,动物具有的某些本能,例如,防御或反击的本能,人类也同样具有,但由于人类高于动物,因而,从脱离动物界的那天起,人类的防御或反击本能就与动物的防卫本能发生了质变。两者的差异在于,人类的防卫本能受大脑和理性的支配,动物的防卫本能则不受任何理性的约束,纯属一种自然的冲动。
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人类的防卫本能逐渐具有了社会的属性。它不仅受人类理性的支配,还要受法律的制约。个人对外来侵害进行抵御或反击的行为若对社会有利,统治者就赋予其合法的地位,个人的防卫权就为法律承认和保护;反之,个人的防卫权就要被剥夺,面对外来侵害,人们只能忍受。可见,防卫权由个人的防卫本能,发展为整个社会意识所认可的权利;防卫行为由私人报复行为,发展为合乎社会利益的法律行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质的飞跃。
随着不成文法向成文法的变迁,正当防卫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另一重要变革——从不成文法的习惯上升为成文法的规定。例如,汉穆拉比法典第21条规定:“自由民侵犯他人之居者,应在此侵犯处处死掩埋之。”在我国,《尚书·舜典》中的“眚灾肆赦”,日本刑法学家就认为兼有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的双重意思。(注:参见徐朝阳:《中国刑法溯源》(一),商务印书馆印行,第126—135页;)
及至封建社会,法律对正当防卫的规定更加详尽、广泛而系统。《汉律》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意思是说,没有正当理由未经主人同意,进入室、宅、庐、舍、车、船这些居住的地方,侵犯人身自由的,当时打死是无罪的。而集我国封建法律之大成的《唐律》关于“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注:参见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178页。)的规定,被公认为是封建法律关于正当防卫规定的典范。
在西方近代法制史上,最早在刑法中明确规定正当防卫的,是1791年的法国刑法典。该法典第6 条规定:“防卫他人对于自己或他人生命而杀人行为时不为罪。”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规定对于防卫权行使的限度没有作出任何限制。之所以如此,是因其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影。1791年的法国,正是历史上著名的启蒙运动的发源地。饱受中世纪对人性的极端束缚和压抑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中世纪以来的神学教条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彻底的批判。在他们看来,一切违背人性的禁欲主义统治者都是应当推翻的暴政。只要不影响其他社会成员行使同样的权利,个人权利就不受任何限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种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法律思想影响下,正当防卫作为保障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免受急迫不正当之侵害的自力救助方式,被视为天赋人权之一,当然也不受任何限制。可见,无限防卫权的刑事立法化,主要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产物。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垄断的出现,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法律思想越来越难以满足保护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于是,一种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律逐渐取代了启蒙时期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法律。反映在正当防卫理论上,就是不再将正当防卫看成是维护个人利益的行为。而是将其视为维护社会利益的法律行为。因而,防卫权的行使,应以不对社会利益造成危害为限;否则,就和不法侵害一样具有社会危害性,同样为社会和法律所反对和禁止。受其影响,刑事立法上开始规定防卫过当应负刑事责任,甚至主张防卫须出于不得已。例如,1979年日本刑法第36条对正当防卫作如下规定:“(一)为防卫自己或他人的权利,对于急迫的不正当侵害而采取的出于不得已的行为,不处罚。(二)超过防卫限度的行为,根据情节,可以减轻或免除其刑罚。”
从上述正当防卫制度和防卫权发展演变的历史不难发现,正当防卫制度从其萌芽、发生到发展,与人类社会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进程基本是同步演进的。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对正当防卫制度的规定有所差异,但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脉络,那就是:社会文明程度越高,法律就越发达完备;法治的精神越是深入人心,公民的防卫权行使的范围也就越益狭小。因而,与日益发达完备的正当防卫制度相比较而言,防卫权的范围不是日益扩大,而是日益萎缩,其基本的运行规律可以概括为:原始社会的防卫本能→奴隶社会有限制的防卫权→封建社会膨胀的防卫权→资本主义社会前期的无限防卫权→资本主义社会后期严格限制的防卫权。
二、防卫权价值探析
自然复仇是人类防卫的原始形态。在原始社会,复仇和防卫都是作为惩罚形式被共同生活准则所许可。自从人类社会产生国家,并通过国家制定法律,行使惩罚权惩罚违法犯罪行为,为全体公民提供法律保护起,便结束了以复仇作为防卫形态的历史。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法律机构发达以后,生杀予夺之权被国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杀人的权利,杀人便成为犯罪的行为,须受国法的制裁。在这种情形下,复仇自与国法不相容,而逐渐的被禁止了。”(注: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页;)于是,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治的权力,即刑罚权由国家统一行使,就成为法治原则的集中体现。与刑罚权的行使日趋泛化如影随形的是,刑罚适用的真空自刑罚问世以来就不可避免。刑罚因犯罪而存在,但刑罚与犯罪之间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实现。这是因为,刑罚适用的首要条件是人,无论是刑法典中规定的静态形式的刑罚,还是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的动态形式的刑罚,其适用和运作都离不开人。刑罚作为惩治犯罪的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在其适用过程中,必然会与另一些要素发生冲突和摩擦,在与这些因素的摩擦和碰撞中,刑罚的能量受到削弱,以致在某些严重的犯罪行为面前束手无策,从而出现刑罚适用的真空。这种真空现象,在合法权益遭受急迫的不法侵害损害时尤为明显。因为,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必须严格依照诉讼程序进行,这样,虽然可以使不法侵害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毕竟合法权益已经受到损害,并且,这种损害有时是难以挽回的。为了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尽可能地保护合法权益,防卫权这种依靠公民自身力量实现权利自保的权利,其存在也就成为必然。可以说,正是防卫权的存在,才使刑罚真空给国家权威造成的损害多少得到一定的弥补。那么,能不能够由此演绎出这样一个结论:必要的防卫权就是无限的防卫权呢?
三、无限防卫权刑事立法化的质疑
任何权利都含有规范,任何规范都不可能完全得到实施。如同“无政府的政治自由会演变为依赖篡权者个人的状况,无限制的经济自由会导致垄断的产生”(注:[美]E· 博登海默著,邓正来和姬敬武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76页。 )一样,无限制的防卫自由不仅会导致血腥复仇和暴力杀戮,而且会动摇刑罚适用的根基,导致国家法秩序的松驰和法律的软弱无能。这决非笔者危言耸听,而是因为:
首先,无限防卫权会引起国家责任的不恰当转嫁,从而有破坏法治的危险。自从有了国家和法律,防卫权就始终是以刑罚权的必要救济措施而不是替代物的面目出现。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惩治犯罪、保护合法权益始终是国家的责任,而不是公民的法律义务。因而,国家将无限防卫权交给公民,表面上看,扩大了公民的防卫自由,但在这种权力的下放和转移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呢?是国家责任的逃避,是国家的软弱和法律的无能。它表明:面对汹涌的犯罪浪潮,国家已经精疲力尽,无能为力,因而,公民们,你们自救吧!可是,这现实吗?犯罪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要从根本上予以防治,需要的是由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形形色色的因素所组成的一个全方位的、多层次的综合治理系统。既然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的刑罚权,在严重的暴力犯罪面前尚且无计可施,更何况私力救济性质的防卫权呢?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将社会治安状况的根本好转完全寄希望于公民的防卫权,这会把防卫权置于一个不应有的高度而使其过度膨胀,最终则只能使防卫权的行使走样变形。如若那样,与其说是法治的进步,不如说是法治的悲哀。
其次,无限防卫权的合法化,有可能导致新的不法,进一步激发严重的暴力犯罪。刑罚和防卫从外在的表现形式来看,都是对犯罪的一种侵害,可是,刑罚代表的是一种基于普遍意志所产生的对犯罪的报复,而防卫作为防卫人个人主观意志的行为,多少是防卫人仇恨心理的一种宣泄。社会中的个人并非都是理性的,尤其是在面对紧迫的不法侵害的时候。无限防卫权在法律上的确立,无疑冲垮了防卫人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使其会在情欲或利害关系的支配下,产生强烈的报复心理,不顾一切地进行防卫,直至置被防卫人于死地而后快。这岂不是法律对血腥复仇的公开认可和纵容?法律在制止一种暴力犯罪的同时,又公然允许另一种也许是更为严重的暴力犯罪,这样的法律,还能够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起法律神圣不可动摇的权威,从而使民众爱法、守法吗?当然不能。最终,无限防卫权不仅不能成为防范暴力犯罪的长鸣警钟,反倒成了激发严重暴力犯罪的“催化剂”,这恐怕是立法者始料未及的吧。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这种论点是建立在公民的文化和法律意识还较薄弱的基础之上的,而文化国对法治国的取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律怎么能够拘泥于眼前的现实而丧失其应有的超前性呢?诚然,法治国将被文化国取而代之,西方某些发达国家现在已在向后现代社会过渡。但我们中国的国情是怎样的呢?“就文化程度来看,据统计,还有20%左右的文盲和半文盲。‘法盲’虽然没有统计,估计可能比文盲更多一些。不仅在群众中有相当数量的‘法盲’,就是在干部中也还有不少‘法盲’……”(注:转引自冯军著:《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886年版,第222页;)这样的国情、 这样的现状决定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需要的是现代化而不是后现代化,需要大力加强的是法治国而不是文化国的建设。“在法律领域,如同在其他一切文化课题上,自家的活法先要摸清。予以温情与敬意的细细体会,然后复述出它的说法,接受其为当下生活所必需的资源,使老传统变成新传统。在此过程中,立法,如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的大感慨:‘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须以一般现行生活状态为蓝本。’至于“现代”还是‘后现代’,在绝大多数人口仍为农民的今日中国,可借寅恪先生一语:‘固非妄说,却为赘论也。’”(注:许章润:《说法 话法 立法》, 载《读书》1997年第11期;)
再次,无限防卫权在刑法中的确立,违背了人道主义的原则,使刑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公正的价值轨道。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康德就再三告诫人们:永远把人类(无论是你自身还是他人)当作一种目的而绝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来对待。(注:参见[英]·A·J·M· 米尔恩著:夏勇、张志铭译:《人的权利和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179页;)所谓永远把他当作一种目的来对待,就是永远把他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人来对待,而不管他可能碰巧具有的任何外在价值。但是,什么才是永远把他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人呢?如果一个人不只是被当作一种手段来对待,那么就存在必须如此对待他的一些方面和不得如此对待他的另一些方面。“他不仅不得被任意地杀害,他的生命也绝不能遭受不必要的危险;他的行动自由绝不能受到专横干预;他绝不能受到无故的侮辱或羞辱;他绝不应该遭受无端的暴力;他必须总是获得公平和体面的对待,而且只要可能,就必须解除他的痛苦。这样,尊重生命、免受专横干预的自由和礼貌就成了共同道德的原则。”(注:参见[英]A·J·M·米尔恩著:夏勇、 张志铭译:《人的权利和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179页;)无限防卫权的刑事立法化恰恰背离了上述宗旨,无疑是在向世人昭示:当合法权益遭受严重暴力侵害的时候,犯罪人的一切权利都可以牺牲,只要这种牺牲能够保护社会合法权益。无疑,为了达到保护社会合法权益的目的,犯罪人被当成了工具。他被排斥在人类社会之外,而不是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员而存在。法律剥夺了他本应和其他社会成员一起享有的作为人类伙伴的资格,“他是在做奴隶,或者至多是只家养的宠犬。”(注:参见[英]A·J·M· 米尔恩著:夏勇、张志铭译:《人的权利和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 )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被否弃,刑法的生命力则因而被扼杀,最终,因对功利的过于盲求,而逐渐陷入庸俗化刑法的泥谭。
最后,无限防卫权在刑法上的确立,不仅超越了立法者的能力,而且使得司法的独立进一步沦为立法者理想化情绪的牺牲品。
法治的实现,首先有赖于一个国家是否有尽可能完备而公正的法律体系。但是,如同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完全相同的社会冲突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社会现实的丰富性和法律语言的有限性之间所存在的永远难以逾越的鸿沟,决定了任何一部法典都只能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描述,而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具体的事实情境,并给这种情境以十分确定的法律后果,正所谓“法有限,情无穷”也。因此,法律要有作为,首先便应明白自己的有限性。立法者绝不能是理想主义者,“没有谁有权让别人作他理想的试验品,何况在中国,这‘别人’又动辄以十余万万生灵计,占了五分之一的人类。(注:许章润:《说法 话法 立法》,载《读书》1997年第11期。)无限防卫权在刑法上的确立,恰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不同犯罪人的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也不可避免在存在着差异。不同的犯罪有着不同的社会危害程度,即使是同一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也还有预备和未遂之分。因而,公民在什么情况下享有防卫权,防卫权应行使到什么程度才是公正的、合理的,断然不可由刑事立法预先制定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而应由法官秉承立法宗旨,根据案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裁量。所以,修订后的新刑法内将无限防卫权予以合法化,不仅违背了立法的客观规律,而且扼杀了司法的独立。而司法独立作为权力制约的根本,是司法行为得以排除社会上的非正当因素,尤其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干预和经济势力对具体诉讼活动的影响,从而为诉讼活动建立起一种超然于世的公正形象,确保司法审判的纯洁性和权威性的基本前提。公正对于独立客观上的依赖,决定了司法独立的丧失必将导致法律正义性的毁灭。因此,无限防卫权的刑事立法化,使人不能不对正当防卫制度前途以及刑法公正价值目标的实现产生疑虑。
总之,自由不等于纵容,“每个人在行使其权利和自由时,应该只受那些由法律所规定的旨在确保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适当认可和尊重的限制和约束……”,这种限制和约束应当“旨在满足一个民主社会中的道德,公共秩序以及普遍福利的要求”,(注:《联合国宣言》第29条。)对于防卫权这种可能伤害他人的权利来说,尤其应当如此。修订后的新刑法典关于无限防卫权的规定,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大缺憾,在目前尚无他法可以改变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应尽量从严把握无限防卫权适用的前提条件,以确保刑法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当然要从根本上弥补这一缺憾,关键还在于立法者克服其理想化的立法倾向,在日后的刑法修订工作中彻底废除无限防卫权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