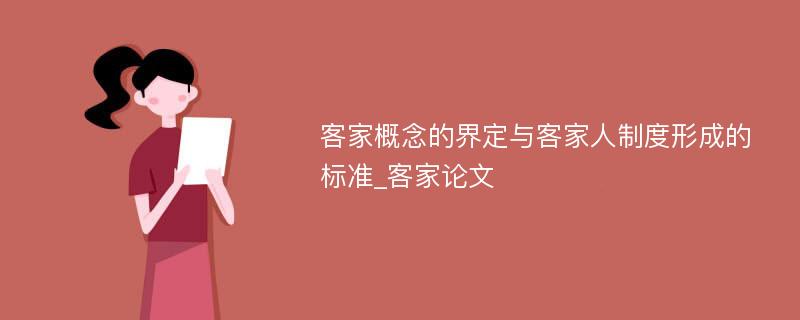
客家概念的界定与客家民系形成的判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家论文,判据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客家概念的界定是客家研究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客家共同体的归属,而且还涉及如何判断客家共同体形成的年代。因此,不少中外学者都试图给予合理、科学的界定。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界定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试就国内学者对客家概念的种种界定作一评述,然后根据民族学理论和客家共同体的特征,并博采众家之长,提出一孔之见;最后对与之相关的客家形成的判据作些分析。
一、客家概念的界定
国内学者对客家概念的界定颇多,较具代表性的有如下数种:
一是客家是汉民族共同体内的一个民系。这一界定是我国客家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罗香林先生提出的。罗先生于30年代首创“民系”这一术语,并用于客家问题研究,从而得出如上界说。也许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罗先生对客家概念只作宏观的界定,但如若细读其名著《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仍可在字里行间看出其微观界定的思路:“鄙意欲定客家界说,自时间言之,当以赵宋一代为起点。客家居地,虽至今尚无普遍调查,然依其迁移所届,大体言之,其操同一客语而与其邻居不能相混者,则以福建西南部,江西东南部,广东东北部,为基本住地,而更及于所迁之各地,此就空间言之者也,鄙意凡属客家之基本住地,自赵宋以来之文物或活动,除极少数不能并计外,大体皆可认为客家之文物或活动。吾人研究客家问题,固当上溯源流,下瞻演变,然基本对象,当不能离此地域此时间一般操客语之人群及其活动之迹象。” 〔1〕罗先生认为,“欲定客家界说”不能离开地域、时间、文化,特别是客家文化标志的客家方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罗先生这一界说已成为当今客家学界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二是“什么叫做客家人呢?我认为可以概括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立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的心态(即客家精神)。凡是符合上述稳定的特征的人,就叫做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2 〕这是当代客家研究者李逢蕊先生从民族概念的内涵共性和构成民系的特性相结合的角度对客家概念所作的界定。这一界说,在宏观上明确了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分支;在微观上指出了客家民系的特征——“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的心态”,应该说比罗香林先生的界说进了一大步。不过尚有不足之处:其一,共同生活在一定区域是民族或民系形成的必备条件,这点对于客家民系来说尤为独特,故应在界说中有所体现;其二,我们研究的客家概念是历史性的概念。“凡是符合上述稳定特征的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这种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逻辑推理,似乎欠妥,容易产生歧义;其三,从语言学上讲,用“客家语言”欠妥,应为客家方言。
三是“客家是汉民族共同体的一个分支。其祖先祖籍中原,自东晋至两宋之交,由于战乱等种种历史原因,陆续迁入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山区中,在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化而逐渐形成的一个具有比较独特的客家方言、风俗习惯及文化心态的稳定的民系。”〔3〕这是江西师范大学王东林副教授提出的界说, 是他在对民系理论作了探索,并提出民系概念〔4〕之后, 再根据客家的特征而对客家概念作出的界定。这一界说涵盖了客家的民系属性、客家先人的祖籍、客家形成的区域和客家的主要特征,比较完整,但文字表述欠简练,显得过于累赘。
四是“这个客家共同体,是南迁的汉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遗民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人民,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5 〕这是嘉应大学房学嘉先生提出的“新论”。这一界说只说客家是南迁汉人与古越遗民混化的共同体,而未明确这个共同体是属于哪个民族或哪个民系的。但是,如果据民族学理论细细品味房先生行文,便不难看出这个共同体“非粤种,亦非汉种”。为了弄清这一界说的内涵,我们不妨引录房先生在《客家源流探奥》中的一段论述:“客家人与整个汉民族、古代百越族究竟是怎么一种关系?已故客家研究大师罗香林先生在30年代发表的《客家研究导论》中说:‘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个支派’。……罗氏在50年代发表《客家源流考》时,对上述论点作了重大修正:‘客家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里的一支’。‘客家是中国民族里的一支,他们的先民,就是因为受了边疆部族侵扰的影响,才逐渐自中原展(辗)转迁到南方来的。’在这里,罗氏将《客家研究导论》中的‘汉族’一词改为‘中国民族’、‘中华民族’。在这里,笔者将其理解为‘中国各民族大家庭’之意,而‘汉族’是这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汉族’修正为‘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是客家学研究的一大进步,是罗氏对客家学研究的重大突破。”〔6〕何为“重大突破”? 房先生至此尚未破题。他接着写道:“笔者近年来专事客家学的田野调查,获取了一些客家民间文献,以及采访录音等。根据这些资料,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分析论证,笔者认为,罗氏关于‘客家是中国民族里的一支’说似可以再前进一步,即客家人并不是中原人。”〔7 〕“历史上并不存在客家中原南迁史。”〔8〕至此, 何为“重大突破”便明白无疑了,即:客家共同体是一个民族,但不是汉族,而是古百越族。这也是“新论”想言而未敢直言的真正内涵。
从上述可以看出,房先生“新论”的理论支撑点是罗香林先生的一句话,即“客家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里的一支”。如果按现代意义来理解,“中华民族”当然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但必须指出的是,罗先生这句话是其名著《客家源流考》第二节第一句话的前半部分,其后半部分为“所以在未讨论客家的源流和组成以前,须先把中华民族的构成,及其有关事变,说个明白。”〔9〕接着, 罗先生论述了“中夏”、“华夏”或“中华”等名号和意识的由来,然后用光汉子《中国民族志》的观点总结说:“其后到汉代,中国的威力益增,国人竞以‘振大汉之天声’自诩,而中夏系统的中华民族,便又常常称为汉族”,〔10〕可见,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用汉族,而在《客家源流考》改用“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并没有对客家学研究有“重大突破”:“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就是汉族!这只不过是房先生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罢了。
只要稍微了解客家研究史的人都清楚,房先生“新论”其实并不新,它实际上是某些外国传教士早年提出的“客家民族论”的翻版。这种“客家民族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曾造成极恶劣的影响,因此早已为客家学者所屏弃。关于这一点,华东师范大学王东副教授在《客家学导论》第三章第三节里作了详尽评述,本文不予赘述。
客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只有放在特定历史时空下进行研究,才能得出可靠的科学结论。在上述4种界说中,前3种界说是把客家概念放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的,所得结论虽不甚完善,但还是能反映出人们对客家认识的历史进程。正是基于此,笔者根据民族形成的理论和客家民系形成过程及其特征,博采众家之长,就客家概念或客家界说表述如下: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分支,她是古时中原人南迁到赣闽粤间的山区,同化和融合了有关土著居民而逐渐形成的具有较独特客家方言、风俗习惯和文化心态的稳定共同体。此说既吸收了上述前3种界说的合理部分, 同时强调了两点:一是客家民系是古时中原人迁移到赣闽粤间山区后才形成的,这就一方面划清了与“泛客家论”的界线,同时严格限定了迁移到并定居于上述地区的古时中原人,才是客家先民;二是客家先民同化或融合了有关土著居民才形成客家民系。这样,一则与“纯种论”划清了界线,另则在同化或融合上明确了主次关系,即南迁中原人为主,而有关土著居民为次,因而被同化、被融合。窃以为,这一界说涵盖了客家民系的属性、形成条件、形成的主体及其主要特征,似应比较科学、比较完整。但此乃一孔之见,有待专家学者评说。
二、客家民系形成年代的判据
客家民系形成于何时?目前尚众说纷纭,有五代宋初形成说〔11〕、唐末宋初形成说〔12〕、明代中期形成说〔13〕、东晋始北宋成形成说〔14〕、南宋形成说〔15〕、南宋末明代中形成说〔16〕等等,它们大多是根据客家方言形成年代的判断来推断的。由此可见,第一,客家民系形成是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进程,且有关史料匮缺,在此特殊情况下,研究者仅用客家方言来推断,并能取得大致趋同的成果,是难能可贵的。第二,客家民系的形成由诸多要素决定,而且它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仅以方言为判据来判断其形成年代,尚欠不足。再者,客家方言的形成年代尚未确定,仍在推断之中,如若其推断的形成年代稍有偏差,必然会影响对客家民系形成年代的推断结果。因此,要比较准确推断出客家民系形成年代,必须有三个甚至四个判据。由于目前尚无现成的民系理论可用来确定这些判据,笔者借用民族形成的四大要素(即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素质),并结合上述客家概念界说,对客家民系形成的历史进行分析后认为,共同地域、客家方言、风俗习惯和文化心态似可作为推断客家民系形成年代的三大判据,通过三者相互印证,似能较准确地推断出客家民系形成的年代。
共同地域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前提条件、客家民系形成年代的基本判据。
民族发展史表明,民系和民族一样,都必须有一个共同地域供人们共同生活,共同劳作,相互影响,逐渐“磨合”,才得以形成。所以,共同地域是民系形成的前提条件。客家民系形成的共同地域为赣闽粤交界的“小三角”(常言为客家大本营),这早已是客家学界的共识。至于南至海南岛三亚市、北至四川广汉、东至台湾彰化形成的“大三角”,则为客家民系形成后向外播迁而在国内形成的分布区域。
根据罗香林等学者的研究,客家先民不是一步跃入客家大本营地区,而是由北而南一站一站地移入其间的。如东晋南渡的中原人(第一次迁徙)有“秦雍流人”、“司豫流人”、“青徐流人”三支,除极少数进入赣闽粤交界地外,绝大部分居于大江南北近600年之久。 到了南诏内侵和黄巢造反引起第二次大迁徙时,这部分中原人的后裔才有相当一部分迁入江西中北部,然后再迁入客家大本营。其近者(多)到达赣东赣南各地,其稍远者则(多)抵福建宁化、长汀、上杭、永定等地区,其更远者(少)已达广东惠州、嘉应、韶关等地。〔17〕宋高宗南渡,元人入侵,引发了客家先民第三次大迁徙,一方面,部分中原人经长江流域直接进入赣闽粤“小三角”区;另方面,赣闽交界地区成为宋元交战之地,居于此地的客家先民纷纷南逃,进入粤东、粤东北地区。
至此,客家先民的大规模迁徙运动就基本结束,他们开始在大本营内过着比较稳定的生活。由此可以推断,就整体而言,客家先民自宋末元初就开始在共同地域“小三角”共同生活、共同劳作,繁衍生息。但如上所述,共同地域是民系形成的前提条件,而不是民系形成的标志。从客家先民到客家民系,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相互认同、相互“磨合”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还同化或融合部分当地的土著人,才逐渐形成与周边民系不同的特性。也就是说,客家民系形成的年代应晚于元初。所以,共同地域只能判断客家民系形成年代的上限。即便如此,如果用此判据来衡量上述几种形成说,便发现其中五代宋初形成说、唐末宋初形成说和东晋始北宋成形成说不能成立。
客家方言是客家民系的标志,客家民系形成年代的主要判据。
“方言是全民语言的分支,是全民语言的地方变体。方言是某个社会内某一地区的人们所使用的,有它自己的特点。”它“是由于一个社会内各地区不完全的分化或是几个社会间不完全的统一而造成的”〔18〕,是识别和划分民系的第一要素。
客家方言是客家先民自东晋至元初经历三次大迁徙后,在赣闽粤“小三角”区的特定时空下形成的现代汉语八大方言之一。它是客家民系交际和思维的工具,是客家民系成员彼此认同的坐标,是其内聚力的成因,因而也是客家民系有别于其他民系的最基本标志。
与其他方言相比,客家方言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变化极为缓慢,因而被语言学家视为语言演变和发展的“化石”。只要找出储存其内的有关信息,便可测定其形成的年代,进而较准确地确定客家民系出现的年代。
客家研究大师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曾说过:“我很想将客语给它做一番实地检验,将其词汇、音读、以及语句结构,用语言学方法记录下来,再用中国音韵学固有法例,分析它声纽、韵部、呼等、以及四声等等,与中土各期各地诸音韵参合比较,推求其间递演嬗变的痕迹所在,一以表白客语实际与本体,一以推证客家与其他族系的交互关系……”但囿于当时客观条件而未果。后人对客家方言也多有研究,但多重于史料钩沉,轻于实地调研,因而进展不大。近年,深圳大学张卫东副教授提出“语言学推断”设想〔19〕,认为困难虽多,但完全可能实现。他还运用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推断,得出的结论是:“客家方言的产生,不可能早于十四世纪(即《中原音韵》时代),也不可能晚于十七世纪初叶(即《西儒耳目资》的时代),当是在十六世纪前后,即公元1500年前后,也就是明朝中叶,这结论,比罗香林先生所说的‘赵宋一代’(十至十三世纪)晚许多,比我以所谓的‘宋元之际’(十三世纪)晚三百年。”〔20〕据现有史料,正史中首先提及客家方言的是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编修的《惠州府志》和《兴宁县志》,但这并未表明客家方言就形成于此时。因为中国传统史籍向来只注重官场的政治事件,而忽视对人民生活、生产方面的记载,所以上述二《志》记载客家方言的年代肯定比其实际形成年代要晚。这里存在一个“时差”问题。由此可见,从现有史料分析,张卫东先生运用“语言学推断”所得结论—“公元1500年前后”是比较准确的。据此,笔者认为,用“语言学推断”所得的客家方言形成年代,是判断客家民系形成年代的准确判据,而史籍记载的客家方言出现年代则只能判断客家民系形成年代的下限。
风俗习惯和文化心态是客家民系精神意识和价值观的体现,客家民系形成年代的重要判据。
人类是生物机体与文化活动的产物。一定地区的地理环境不仅是人类生存的空间和人文精神的地缘背景,而且作为人类生态环境和生存资源必定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风俗习惯和价值取向。因此,地域的差异不仅给人们带来自然机体的差异,而且也使人们在风俗习惯和文化心态等方面形成差异。这就是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和精神意识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客家作为汉族的一个民系,儒家文化是其主导思想和精神核心。这是客家与汉民族其他民系的共同之处。但是客家是其先民几经迁徙,历尽千难万险才陆续到达赣闽粤交界的大本营,在重峦叠嶂,交通险阻、相对封闭、统治者鞭长莫及的山区繁衍生息而形成的民系。这种特殊的人地关系造就了客家民系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心态既有与汉民族共同体相同之处,又有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这种风俗习惯和文化心态既有稳定性,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变,又有潜在性,它表现在不自觉的行为方式和思维定势。据此,如果将客家先民自聚居之时起至其后某历史时期(如明代中叶)分成若干时区,研究大本营内不同地域居民在同一时区内的风俗文化事象以及由这些事象所反映的精神意识和价值取向,一旦大本营内不同地域居民的风俗文化事象在同一时区内具有相当的共同,即可判断客家作为一个新兴民系已经形成。
王东先生利用大本营内嘉靖时期各种县志的史料对此作过分析研究。他认为,客家大本营内不同地域居民的基本民俗文化事象及由此事象所反映出来的精神意识和价值取向,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以佛道为主的宗教信仰等,在明代中叶显现一致性。因此,客家形成年代应划在明代中叶。〔21〕但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叶之前,客家人的活动极少见于正史,而且文化事象发生的时间与正史的记载常有时差性。因此,为了提高判断的准确性,在继续翻检正史史料之同时,一方面要加强对明代中叶以前客家风俗文化事象的实地调研,以便掌握更多的确凿史料;另方面要注意对谱牒史料的比较与运用,因为其内载有较多可用的风俗文化事象史料。唯有如此,用此判据来判断才较为准确。
三、余论
进入本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客家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不少学者提议建立客家学,以推进客家研究。这是一个极为有益的建言。要建立一个学科,须备多项条件,明确研究对象则为首要者。但就目前而言,客家学研究的对象——客家,其概念并不清晰。尤其是近年出现“泛客家学”,使之更为模糊。正有鉴于此,笔者试用民族学理论,并结合客家民系形成过程的特点,对客家概念提出窃以为较为合理、科学的界说,旨在促进客家学早日建立。
本文提出的共同地域、客家方言、风俗习惯和文化心态三大判据,前者只能判断客家民系形成年代的上限。中者,若以“语言学推断”确定其形成时间,则可较准确判断客家民系形成的年代;若以正史记载确定其形成时间,则只能判断客家民系形成年代的下限。后者,大体上与中者相同。鉴于客家民系形成的复杂性,以及正史记载甚少,史料匮乏,最好三大判据同时运用,相互印证,方能较准确判断客家民系形成年代。本文只就如何判断客家民系形成年代提出一种思路,而未作详尽推断,因为详尽推断是个相当复杂的过程,须另文讨论。
客家是个历史范畴,客家民系既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又是一个历史范畴的客体。如果从其先民南迁(东晋以降)算起,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如果从这个民系形成(暂且定为明代中叶)算起,也有500 年历史。正如对任何问题研究都离不开对历史过程分析一样,对客家问题的研究一定要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不然就会造成概念上的混淆,不能获得科学的结论。这种情况在客家学界早已存在,而且日益严重,有必要加以廓清。下面仅举二例略作分析。
其一是客家人与客家先民问题。
笔者阅读一些客家研究论著时常常见到如下一些文字:“客家人是汉民族的一支民系,南迁分五个时期,第一次东晋‘五胡乱华’……”“客家人从中原迁徙于中国南方乃至世界各地……”有的论文干脆用《客家人的几次南迁》作标题。这些文字让人获得两个信息:第一,客家人等同于客家先民;第二,客家人是从中原迁徙而来,并不是在赣闽粤“小三角”区形成的,因而便有人著文把秦汉时代南来戍边定居的士卒说成是最早的客家人。客家人与客家先民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两个特定概念。其区分时限应以客家民系形成前后为界,即经过三次迁徙而进入大本营直至客家民系形成之前的中原人,为客家先民;而客家民系形成后的则为客家人。据此,罗香林先生在论述客家源流时提及的五次大迁移,前三次应为客家先民的迁移,后两次才是客家人的迁移,因此不能笼统地称为客家人五次迁徙。如果这两个概念一旦混淆,许多问题就是非难辨,“客家先民”一词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客家的个性就难以判明。
其二是客家与汉民族的问题。
“中国最卫生、勤劳和进化的民族,就是客家人。”“客家人是刚柔相济,既刚毅又仁爱的民族……”“客家是中国最优秀的民族……没有客家人,便没有中国革命。换言之,客家精神,(就)是中国的革命精神……”如前文所述,这类观点是某些外国传教士在30年代提出来的。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这类观点早已为中国学者所批判和否定。然而时至今日,这类观点仍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我们某些客家学者的论著里,作为论述客家精神的立论依据。如果这并不表明某些客家学者在民族与民系方面无知的话,那只能说明他们治学不严。
客家研究是学术研究,最讲究科学性。上述两例表明,如果不把研究对象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研究,那必然会产生偏差,轻则引起不必要的纷争,重则会严重影响客家研究的深入开展。
本文引述了一些同仁的不同观点,旨在进行对比论证,并无不恭之意。
* 本文于1997年12月7日收到。
注释:
〔1〕〔9〕〔10〕〔11〕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张卫东、王洪友主编《客家研究》第一集,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6 页、11页、41页。
〔2〕李逢蕊:《客家人界定初论》,《客家学研究》第二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3〕〔4〕〔14〕〔15〕汪祖德等编《中华客家研究论丛》第一辑,江西人民出版社,第60—61页、54页、62页、42页。
〔5〕房学嘉:《试论客家共同体的初步形成时期》, 《客家研究辑刊》,1994年第1期。
〔6〕〔7 〕〔8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 广东高教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2页、3页。
〔12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 台北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71页。
〔13〕〔21〕王东:《客家学研究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143—144页。
〔16〕〔17〕张卫东:《客家文化》,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19页。
〔18〕高名凯等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 第221—222页。
〔19〕〔20〕张卫东:《再论客家民系形成年代的语言学推断》,刘文章编《客家宗族与民间文化》,香港中文大学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