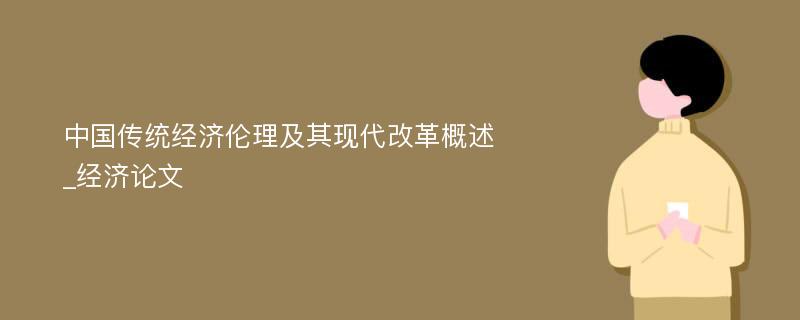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及其现代变革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伦理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大课题,靠一人一时是不可能完成的。本文只能根据现有的认识作一粗略的论述,很不成熟,提出来供大家讨论、批评。
一
研究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必须把握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经济类型”的三个基本特征:以小农经济(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本商末”的经济结构;以父系单系家长权威为轴心的宗法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家族主义”文化同样制约着经济领域的人际关系和经营模式;以及高度集权的“传统型”的君主统治结构,政治、经济一体化,“国家权力—王权决定产权”,民间私有产权始终没有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就在这样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的环境中,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根本不同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伦理,其主要表现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反映“经济结构”、“产权关系”的伦理模式——“重公轻私”,“重义轻利”
“农为邦本”、“农本商末”,这是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为维持这种经济结构,就必须抑制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因为,如若让商品经济自由发展,就必然会促使小农经济的解体,造成小农因贫富分化破产而动摇立国之“本”。因此,在秦以后的两千多年中,“重农抑商”一直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君主统治的基本国策,“故明君莅国,必崇本抑末,以遏乱危之萌”(王符《潜夫论·务本》)。所谓“抑商”,不是要取消工商业,其实质在于抑制商品经济按其自身运行机制的自由发展和手工业、商业产权的私有化;具体的表现就是国家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打击民间工商业,对主要工商业,如盐铁业实行“官营”、“专卖”,强化国家对工商业的垄断和控制,国家权力—王权决定产权。这就确立了传统经济的产权伦理和经济价值观,即重“公”轻“私”,重“义”轻“利”。同样,在农业经济领域,田产私有从来就没有得到制度化的法律保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始终是历代王朝君主的统治观念,“朕即国家”,“天下”之人也都尽入“吾彀中”,为“君父”的“子民”。受“皇恩”的“子民”既无独立、自主的产权,连“个人”本身也是从属于“国家”的。国家(王权)不仅有对田产的最终“处置权”,而且牢牢地掌握着农业田产的“收益权”(分配权),以名目繁多的税赋和力役、兵役,攫取农民的剩余劳动,甚至是剥夺其求生存的必要劳动和人身自由;作为国策的“重农”,其最终目的还是在国家“公利”的旗号下,要求“子民”重“公”、重“义”,为王朝而奉献一切,以维系庞大的官僚—军队的统治体系。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重公轻私”、“重义轻利”,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权伦理和经济价值观的体现,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质,是中国古代经济伦理的核心。还应指出,手工业商业“官营”、“专卖”,权力进入产权领域,就必然产生官商结合,权—利互动,导致腐败。
第二、植根于宗法家族制的经营模式——“家族主义”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结构,由此形成了强大的“家族主义”文化传统。它不仅支配着社会各领域的人际关系,而且也支配着经济领域的生产经营模式。“农为邦本”,而从事农业生产的是广大农民,因而也谓“民为邦本”;“民”作为单个的民都从属于一家一族的宗法结构之中,所以也可以说“国之本在家”、“家齐而后国治”。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既是社会最基本的生活、教育单元,同时也是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由于传统家庭家族结构具有“宗法”性质,因而生产经营模式也就有了强烈的宗法型“家族主义”的文化特色。其基本特征是:“同居共财”,家就是一财产共同体,父家长有绝对权威,掌握全家的“共同”财产,成员无经济自主权,家族整体利益至上;具有强烈的人际等级意识和族类意识,内具亲和力和凝聚力,外具排异性和分散性,信任感仅限于家庭—家族范围,而不扩大至非亲非故的异姓关系,社会信任度低;为家庭生存和家族生命延续、光宗耀祖,是家庭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随着历史的传承和积淀,这种“家族主义”成为中国文化和经济伦理的一种强大传统。
第三、利益分配的伦理原则——礼以定分,贫富均平
中国古代社会财富的分配权掌握在君主集权国家手中。统治者为稳固其统治秩序,实行的是等级分配制度和“均平”原则。前者是指社会纵向结构的财富分配,即荀子所说“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荀子·礼论·正制》),也就是所谓“礼以定分”。在荀子看来,这就是分配的“正义”,符合社会的等级关系的秩序。后者是指社会横向层面的利益分配,用以防止“贫富不均”,勿使贫富过于悬殊。历史上,凡是出现土地兼并严重,造成“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社会动乱之时,统治者就会使用手中所掌握的“最高权力”,施行“限民名田”、“均田”、“占田制”等政策,且主张“禁百姓卖田宅”,打击兼并,以防止农民破产,就是所谓“贫富均平”。孔子首唱“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汉董仲舒释“均”为贫富均衡,“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均平”,不是绝对平均,而是贫富“各得其分”(宋朱熹、近代康有为对孔子提出的“均”都作如是解)。“礼以定分”与“贫富均平”相辅相成,是中国传统的由统治者所坚持的最基本的利益分配伦理原则。
第四、消费行为的伦理原则——力戒奢侈,崇尚节俭
就实际情况论,中国古代的个体消费模式大致有三:广大贫苦农民处于裹腹粗衣状况,很少有市场消费,属于“压缩型”的低消费;一般中小地主往往以半自给为主,必要时辅之以市场消费,属于“节俭型”消费;还有一种则是“豪奢型”消费模式,其行为主体是高官缙绅、富商大贾。但就社会舆论和价值导向而言,除了个别如《列子·杨朱篇》那样宣扬享乐主义,像《管子·侈靡》那样张扬奢侈消费,大多数学派和思想家都倡导节俭,反对奢侈。《尚书·大禹谟》载:“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言:“俭,德之共(洪)也;侈,恶之大也。”墨子把“节用”作为自己学说的一面旗帜,认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老子视“俭”为“三宝”之一。韩非也提倡“俭于财用,节于衣食”。孔子主张弃奢取俭,荀子训诫人们应“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荀子·儒效》)但节俭不能有违于礼,应“节用以礼”。儒家提倡“节俭”,更有其德性修养之义,断言“俭可养德”,倡导“俭以养廉”。总之,“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咏史》)。力戒奢侈,崇尚节俭,是中国传统消费伦理的主导价值观。
第五、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劳动美德——勤劳敬业
在“农业”社会,“民以谷为命”,勤于耕作,敬于稼穑,是得以自给自足之根本。《左传·宣公十二年》有言:“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孔子指出:“生财有时矣,而力为本”(《说苑·建本》)。墨子认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吕氏春秋·上农》谓:“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可以说是对勤劳敬业美德的概括。以后,诸如:“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务本者,勤之谓也”,“勤力有业”,“劝俭必先劝勤”等等,不绝于史。
第六、关于市场行为的道德原则——倡导“诚信”,反对“竞争”
战国、西汉时期,商品经济相当活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畅通。人们已经认识到“诚信”对于市场贸易、货物流通的重要意义,荀子总结说:“商贾憝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荀子·王霸》)同时也反对“造伪饰诈,趣利无耻”的行为,主张“明督工商,勿使淫伪”。但是,由于“重农抑商”,尤其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专卖,国家垄断工商经营,在由此而造成官商结合的同时,民间工商业和工商业者始终处于被压抑和岐视的地位,视商业为“奇邪之业”,“无商不奸”成为社会普遍的思维定势;而国家垄断和官商勾结,则又严重地窒息了市场的平等、自由竞争(价格竞争),从而也就阻碍了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转型。既倡导“诚信”,又反对“竞争”,这是中国古代商业经济伦理的又一特点。
二
从上面简略勾勒可见,“国家权力决定产权”及其价值形态——“重公轻私”、“重义轻利”的产权伦理,是中国古代经济伦理的核心和要害,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历史命运。
显然,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在本质上是与市场经济伦理相对立的,它不仅不适应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且也不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说,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对“传统经济伦理”进行根本的变革,并在变革中建立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体系。
事实上,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启了“传统经济伦理”的现代变革。当时,随着洋务运动以及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围绕着为什么要兴因工商实业和怎样兴办工商实业这两大问题,展开了一场关系中国近代工业化命运的大辩论,涉及经济伦理的主要问题是:为何要兴办实业?根据什么样的经济伦理来兴办实业?这后一问题的实质就是产权论理。顽固派、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都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清廷顽固派固守“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传统伦理,打着“民为邦本”的幌子,指斥兴办近代工商实业是败坏农业、“夺民生计”,认为“国之强弱在德不在器”,“在人心不在技艺”,力图将近代商品经济扼杀于襁褓之中。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论,其政治目的虽在于“卫社稷”、“保名教”,但毕竟摈弃了视机器为“奇技淫巧”的怪论,从工具论的意义上,为办洋务、兴实业的合理性找到了价值依据。并认为用机器、修铁路“实系为民兴利,并非与民争利”,是富民强国的需要,驳斥了顽固派的“机器夺民生计”谬论。由此突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将“抑末”改为“重末”,认为“欲自强必致富,欲致富必先经商”(《洋务运动》六)。张之洞还明确提出了“本末并重”这一关于经济结构的伦理原则。但是,由于中国近代工业化是外激型的,自然形成了“官为之倡,商为之继”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官权支配商权。因而,企业体制必然出现“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政府垄断的现象,其实质就是产权官有或产权官控。这就造成了企业经营管理上的“以官护商,以商辅官”,也即所谓“官商兼顾”、“官商合力”、“上下一体”、“忧乐与同”的家族式的管理伦理模式,有人甚至把官与商比喻为父子关系。基于这种产权伦理,洋务派反对自由竞争,认为竞争只会导致“群起逐利,私作奸伪,不顾全局,以致百业皆衰”(《张文襄公全集》卷37),仍未摆脱“传统”的束缚。
维新派和革命派的观点具有明显的近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把古代“民本”思想与近代西方伦理学说相融合,鼓吹开民智、新民德、兴民权、富民生,确立“富民生”为发展近代实业的伦理动因和价值目标。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认为“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发达资本,振兴实业就是“要解决民生问题”;批判“重农抑商”,张謇提出立国之本“在乎工与农”,康有为提出“以商立国”,梁启超主张“以工立国”。革命派更认为“重农抑末者迂儒之谬论也”,“今欲救其弊,必自行重商主义始”。一反“土为邦基”之说,提出“商工农矿,立国之基”;反对官权控制企业,主张产权独立、自主的经济自由主义。康有为提出实业“宜纵民为之”,“官但保护,而勿干预之”(《戊戌变法》二)。梁启超高喊“自由竞争”,严复则根据孟德威尔“私利即公益”的公式,针对儒家“分义利为二者”的陈式,提出“义利合一”、“群己一致”的观点,以此反对权力干预,提倡自由贸易、开明自营、公平竞争等一套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原则。革命派孙中山明确指出三民主义“皆为平等、自由主义”,宣称“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益可预卜”。主张“各种官吏的障碍,必当排去”,朱执信则强调企业“独立自营之精神”,以经济自由主义原则,论述了企业产权自主、独立的伦理原则。
近代的经济伦理变革,突破了“传统经济伦理”体系,确立了“工商立国”、“实业救国”和企业产权独立、自由竞争等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伦理理念,为发展中国近代工商实业和推动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伦理辩护和精神支撑,其成绩和历史作用应予充分肯定。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在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官僚资本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下,民族资本发展艰难,十分薄弱,在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对“传统经济伦理”的变革。
建国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没有也不可能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继续变革“传统经济伦理”的历史课题,却形成了传统经济伦理“现代变革”的新的起点。就是说,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传统经济伦理”改变了原生形态而获得了新的形态,体现了“传统”的“韧”劲;“传统”的东西,只要没有完全中断,它总是会通过不同的历史形态而延续着,因此,正如希尔斯所说:“它是现在的过去,但它又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2](P16)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变革对象,主要的已经不是原生态的传统经济伦理。而之所以要研究“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则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已成为“现在的一部分”的“传统经济伦理”。
当今的“传统经济伦理”的现代变革,我想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产权伦理的变革。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就是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特征就是社会资源主要通过市场来实现配置,这就必须进行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的改革,确立多元的具有产权自主的独立的市场主体,确立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里就包含着产权伦理的深刻变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问题上,不是越“公”越好、“公”的成份愈纯愈好。不仅“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企业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而且要鼓励、引导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产权的合法性,确立平等的“国民待遇”地位,并从政治上肯定从事非公经济的人员“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往的那种重“公”轻“私”、贵“公”贬“私”,甚至是兴“公”灭“私”的传统的产权伦理和价值观念,确立了“公”、“私”共存、平等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产权伦理和价值观念。在产权伦理上的现代变革,其实质在于从伦理上突破所谓“财产所有权等级观念”,即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把财产权利按照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给予不同价值地位的观念。这是“传统经济伦理”现代变革的重大成果,推动并将继续推动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其真正地确立起来并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则必须以行使财产权利的自由和行使财产权利所承担的社会义务之间的统一为核心,进一步回答财产权利合法性的道德基础。
第二、关于利益分配伦理原则的变革。在利益分配上,我们早就否定了“礼以定分”即宗法式的等级分配制度。但是,“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分配伦理仍有相当严重的影响。传统的“贫富均平”虽有防止和反对贫富悬殊的价值内涵,但这是在“不患贫”即低效率、甚至无效率前提下的分配伦理,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的普遍贫穷,虽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传统的分配伦理,确立“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的方针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平”,既是指机会的公平即过程的平等,也包含了要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同富裕的结果意义上的公平。后者也是一种贫富均衡,但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不患贫”、低效率前提下的“均平”,而是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在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基础上实现的“公平”,防止和克服贫富两极分化,最终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效率与公平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循环,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这就是传统分配伦理现代变革的真谛之所在。
第三、关于传统的商业诚信与现代的“市场信用”。倡导“诚信”,是古代经济伦理的优良传统。不过,古代的“商业诚信”实指商贾“憝悫”、百工“忠信”,是行为者的个人品德,属道德人格范畴,是社会的“诚信”道德规范的个性体现,因而也可称之为“商人诚信”。同时,古代的商业诚信仅通行于“民间”——一种由亲缘、乡缘联系起来的狭小、封闭的“熟人社会”,交易双方实际上是一种“人格化交换”,“诚信”则体现为“人格担保”。因此,古代的“商业诚信”与现代的“市场信用”不是同一个概念。马克思说:“信用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也只有在以资本或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的出现”。[4](P534)这里说的就是“市场信用”,它超越了“熟人”关系,是“陌生人”之间市场交易、商业契约即“非人格化交换”的伦理关系,是契约双方要求信用的权利与履行信用的义务的双向统一关系,也就是兑现承诺、履行契约的可靠性。其中包涵了市场主体的“诚信”道德,但由于市场主体具有“经济人”的品格,“市场信用”必然要求表现为“制度”约束,即“信用制度”。而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市场信用”还成为一种特殊的交易行为、交易的对象,即所谓“信用交易”。所以,“市场信用”又是信用道德、信用市场和信用制度三位一体的“信用体系”。可见,作为一种商业道德,“信用”与“诚信”相通用,而作为一种“制度”、“体系”,“信用”就不等同于“诚信”;我们平常说“信用制度”,而不说“诚信制度”,正反映了这两个词的不同含义。显然,通行于“熟人社会”的传统商业诚信,可以是建立现代“市场信用”的文化资源,但却不可能直接转化为“市场信用”。值得注意的是,习惯了“熟人”关系的商业行为,一旦进入非人格化交换的“陌生人社会”,就会因面对“陌生人”而丢失“诚信”人格,甚至在利益的驱动下,利用“诚信”而“杀熟”。因此,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传统的“诚信”美德只有在融入“信用制度”的情况下,才能对“市场信用”建设产生积极的作用,而作为“制度”和“体系”的“市场信用”则需要重构,对此,我们任重而道远。
第四、关于家族企业与“家族主义”传统及其变革。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个问题日趋突出起来,成为商界和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所谓“家族企业”,是指企业的产权属于或受控于同一家族,同一家族至少有两代主持这家公司或企业的经营管理,是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家族主义”之体现于企业经营管理,或曰“企业家族主义”则是一种“企业文化”。家族企业与“家族主义”有内在的关联,但不是同一概念,不能混为一谈。这里,重要的不在于“家族”的组织形式,而在于“家族主义”的文化内涵。应该看到,经过自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和近20多年来的计划生育国策的有效实行,原生态的完全宗法式的“家族主义”在现实生活中虽已不再存在,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仍以新的形态产生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民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中的“家族主义”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企业主(家长)为主宰的辐辏式管理模式,或曰“人治”模式;子继父业的家族传承观念;强烈的族类意识,信“内”疑“外”,社会信任度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等。诚然,这些传统的文化意识在家族企业的创业阶段,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毕竟与现代企业的管理文化相悖,随着企业的不断扩大和发展,显露出“家族主义”文化的消极作用,成为企业发展的“陷阱”。事实上,许多著名的家族企业,除了“子继父业”,对“家族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在不断的反思中都有所变革,如实行股份制、聘用职业经理人、增强民主管理意识和人才竞争意识,提升企业的“社会资本”。这种趋势表明,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管理科学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家族企业的文化内涵正在发生着质的变革,这就是一些著名的家族企业具有活力之奥秘所在,可能也是在当今世界上家族企业仍是“最普遍和最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之一”的重要缘由。总之,研究“家族企业”,应把“家族企业”的组织形式与“家族主义”的企业文化区别开来,这样才能解读现代“家族企业”现象;家族企业也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就是说,在外力的推动下,家族企业应不断变革“家族主义”的文化传统,实现现代企业文化与家族企业组织形式的融合,从而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获得新的活力。
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仅为举例而已,但也足以说明,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体系,必须进行“传统经济伦理”的现代变革。
三
最后要指出的是,“传统经济伦理”的现代变革将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所提出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所谓“路径依赖”,就是人们过去所选择的制度,在其变迁中会产生一种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使制度沿着既予的路径往下走。如果原来的路径是错误的,那就会使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而一旦进入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这里的关键是,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在这种制度下获得既有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力求巩固这种制度,阻碍进一步变革,哪怕新的制度较之更有效率。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正式制度的变迁中,而且存在于非正式制度(如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的变革中。当然也存在于“传统经济伦理”的变革中。例如,为什么在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中很难改变“通路子”、“拉关系”的“关系伦理”现象,而且愈演愈烈?其原因就在于传统“熟人社会”那种“人格化交换”伦理的路径依赖。由熟人间诚信所产生的“人格担保”交换方式,在其长期演化中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定势或集体无意识——“熟人可信”、“熟人可靠”、“熟人好办事”。正是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形成了一种游离于制度外的“关系伦理”,并在“利益”的作用下不断地自我强化,成为一种久治不愈的“伦理顽症”,这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是屡见不鲜的。一种突出的表现是,利用“政企不分”、“行政审批制”(这些制度也已形成“路径依赖”)这些“平台”,通过各种不正当的、非法的手段,通路子、拉关系,“一回生、两回熟”,而一旦“关系”搞掂,就会获取“双赢”效益,甚至以较低“成本”攫取大利、暴利。正是在这种“利益”驱使下,“关系伦理”泛滥成灾,成为建设“市场信用”、经济公正的巨大障碍。其他如传统的产权伦理、分配伦理、“家族主义”等也都存在着“路径依赖”,对此,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1995年5月4日,诺斯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作题为《制度变迁理论纲要》的讲演中指出:“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样一点: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么进行的。我们必须非常了解这一切。这样,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因素,选择我们有哪些机会。”这也就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中为什么要研究“传统经济伦理及其现代变革”的缘由。
标签:经济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家族企业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商业竞争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 工商论文; 商业论文; 社会企业论文;
